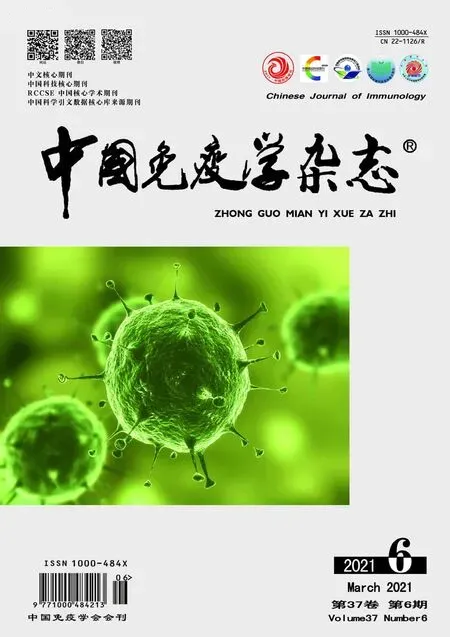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在神经炎症中的作用①
李 灵 丁艳平 邵宝平(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兰州730000)
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5′-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AMPK)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真核细胞的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是生物体内最主要的能量感受器和调节器,分布于各种与代谢相关的器官中,通过调节脂肪酸、胆固醇、糖原和蛋白质合成及脂肪酸和葡萄糖摄取和分解维持机体能量平衡。机体发育过程中,AMPK可通过调控Ⅲ型磷脂酰肌醇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PI3K-Ⅲ)促进自噬发生发展,还可通过直接或间接调节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活化受体-γ辅助活化因子-1α(peroxisome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γcoactivator-1α,PGC-1α)功能促进线粒体合成及负调控细胞增殖。此外,疾病发生过程中,活化的AMPK也可通过改变其代谢途径调节下游通路,影响细胞凋亡过程、生长因子受体水平、细胞周期进程、血管生成及能量代谢等,从而发挥机体保护作用[1]。
神经退行性疾病是大脑和脊髓神经元发生不可逆性病变、神经胶质细胞过度增生及异常蛋白在胞内累积产生细胞毒性并导致细胞代谢失调所引起的慢性、进行性功能障碍疾病,包括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和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MS)等,其病因尚未阐明,且无法治愈。近年研究表明,AMPK激活在神经炎症及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发挥神经保护作用,但同时存在相反的证据。本文综述AMPK及其在神经炎症中机制的最新研究进展,为神经炎症及其他炎症性相关疾病的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方法[2]。
1 AMPK的结构及其活性调控
1.1 AMPK结构 AMPK是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几乎所有组织中高度保守的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由1个α催化亚基、1个β调节亚基和1个γ调节亚基组成,各亚基存在多种构型,α亚基包括α1和α2 2种亚型,β亚基包括β1和β2 2种亚型,γ亚基包括γ1、γ2及γ3 3种亚型,分别表达于不同组织和器官中,α1亚基主要分布于肾脏、肝脏、心肌和脑组织中,α2亚基主要分布于心肌、骨骼肌和肝脏中,β1亚基在肝脏中高表达而在骨骼肌中低表达,β2亚基与β1相反,γ1和γ2亚基广泛分布于各组织中,γ3亚基在骨骼肌中高表达。各亚基共可组成12种AMPK复合物,发挥重要生理功能。α亚基N端为1个激酶结构域,包含1个保守的丝氨酸/苏氨酸激酶区和Thr-172位点,其磷酸化可激活AMPK,其中间部分为1个自抑制区(autoinhibitory sequence,AIS),C端为1个β亚基结合区(β-subunit interacting domain,β-SID)。β亚基主要由2个保守的结构域-KIS和ASC组成,其中KIS是β亚基的功能性糖原结构域,而ASC结构域是保证整个复合物稳定性和活性的关键,β亚基C末端还有1个α亚基和γ亚基结合区(α,β-subunit interacting domain,α,β-SID)。γ亚基主要由4个串行重复的胱硫醚β-合酶(cystathionine-β-synthase,CBS)组成,主要用于核苷酸结合。当能量缺乏时,AMP、ADP可与CBS位点结合,Thr-172位点磷酸化从而激活AMPK,引发下游能量稳态修复机制,维持细胞内ATP水平[3]。
1.2 AMPK活性调控 AMPK作为一种能量传感调节器,其活性可被细胞内外各种信号直接或间接调节以响应局部能量需求并维持全身能量稳态,包括缺氧、葡萄糖剥夺、热休克、饥饿等引起AMP/ATP比值改变、钙离子浓度或激素细胞因子水平改变、上游AMPK激酶(AMPK kinases,AMPKKs)、活性氧自由基(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及部分外源性小分子药物,其中,体内AMP(ADP)/ATP水平是调节AMPK活性的最主要方式[4]。当AMP或ADP结合于γ亚基可改变AMPK构象,使AMPKKs更易于与AMPK结合,同时防止已被磷酸化的Thr-172位点(p-Thr172)被蛋白磷酸酶2A和2C去磷酸化,提高AMPK催化活性[5-6]。但ATP结合至γ亚基不仅可降低AMPK催化活性,还可提高p-Thr172去磷酸化速率[7]。因此,当有氧代谢增强等引起细胞内ATP含量上升、ATP/AMP比例升高均可抑制AMPK活性。一些酶,如PP2A和PP2C可降低已磷酸化的AMPK活性。此外,AMPKα亚基上的AIS也可抑制AMPK激活,这种抑制效应可被AMPKKs消除。细胞内3种主要的AMPKKs分别为:肝激酶B1、转化生长因子激酶1及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激酶2,均通过磷酸化Thr172位点激活AMPK。部分免疫因子和细胞毒因子也可影响细胞内能量稳态间接激活AMPK,包括炎症趋化因子、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及ROS等[8]。
目前已合成一些可作为AMPK激动剂的外源小分子药物主要分为2类,一类主要通过抑制线粒体呼吸链复合物Ⅰ活性改变AMP/ATP比例进而间接激活AMPK,主要有二甲双胍、α-硫辛酸、噻唑烷二酮、胍基丙酸、多酚、环化生长素及天然药物有效成分,如白藜芦醇、槲皮素和小檗碱等[9]。另一类可直接作用于AMPK亚基激活AMPK,如噻吩并吡啶酮衍生物A-769662、苯并咪唑类化合物及5-氨基咪唑-4-甲酰胺核苷酸等[10-11]。
2 AMPK在神经炎症中的作用机制
神经炎症的重要病理性特点为小胶质细胞(microglia,MG)激活。MG是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先天性免疫细胞[12]。正常生理条件下,MG处于未活化状态,维持枢神经系统稳态和正常神经活动。当发生神经炎症时,MG被迅速激活,出现细胞形态、免疫表型及功能等分化[13]。根据激活条件不同,激活后的MG主要分为M1和M2 2种亚型。M1型为促炎型MG,是MG受到过度或长时间刺激分化的亚型,可分泌大量促炎因子,如IL-6、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等,同时减少神经保护性营养因子分泌,加重炎症反应,通常可由脂多糖和IFN-γ诱导产生;M2型为抗炎型MG,可由IL-4、IL-13或IL-10诱导产生,激活后可分泌大量抗炎因子,如精氨酸酶-1、TGF-β及IL-10等,发挥抗炎作用[14-15]。研究认为可通过调节MG激活状态及其分化亚型调节机体炎症反应适宜程度,为治疗神经炎症、神经退行性疾病及其他炎症相关疾病提供方案。研究发现,MG的细胞能量状态在自身激活及亚型分化中起重要作用,如未活化的MG主要依靠氧化磷酸化生成ATP,而激活后的MG对糖酵解的依赖性增加,M1型MG主要通过糖酵解产生能量,而M2型MG主要通过氧化磷酸化产生能量[16]。此外,线粒体功能、糖酵解速率及葡萄糖利用率也影响促炎因子的转录和翻译过程,与AMPK密切相关,提示AMPK可作为神经炎症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潜在调节因子[17]。
MG的适当激活是大脑应对内源或外源性刺激的自我保护机制,但MG过度活化将诱发严重的神经炎症效应,是多种疾病病理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如糖尿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精神疾病和各种脑损伤[18]。在这些疾病体内外模型中均发现,MG过量激活、抗原呈递能力提高、促炎介质如TNF-α和iNOS表达上升及抗炎介质如IL-10和TGF-β表达下降[19]。抑制MG过度激活及促进MG 2种激活表型转变(M1→M2)是避免神经炎症过度发生的关键[20-22]。研究发现,AMPK主要通过抑制NF-κB信号通路抑制促炎因子表达激活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erythroid 2 related factor 2,Nrf2)信号通路促进抗炎因子表达,调节mTOR信号通路调节细胞能量状态、自噬、氧化代谢及其他机制发挥抗炎作用[6,23-25]。AMPK激活及其在神经炎症中发挥的抗炎及神经保护作用机制见图1。
2.1 AMPK与NF-κB信号通路 NF-κB是真核生物中广泛存在的一类转录因子蛋白复合物,是细胞应答外界有害刺激的早期转录因子,其相关信号通路在神经炎症各阶段均起重要的正反馈调节作用。正常生理状态下,NF-κB以与其抑制蛋白(inhibitor of NF-κB,IκB)结合后的失活状态存在于细胞质中,当受到促炎因子如IL-6和TNF-α刺激后引发IκB泛素化降解,释放具有活性的NF-κB,NF-κB进入细胞核,靶向促进促炎介质表达,促炎介质表达后增加NF-κB含量,放大炎症反应[26]。研究表明,AMPK可通过多条途径抑制NF-κB活化,发挥抗炎效应,主要包括AMPK/SIRT1/NF-κB、AMPK/PGC-1α/NFκB、AMPK/p53/NF-κB和AMPK/FoxO/NF-κB 4条信号传导途径。

图1 AMPK活化及其在神经炎症中的分子机制Fig.1 AMPK activation and its molecular mechanisms in neuroinflammation
AMPK/SIRT1/NF-κB是最主要的抗炎途径,SIRT1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NAD+)依赖的第3类组蛋白脱乙酰酶,主要通过对靶蛋白脱乙酰化作用调节机体关键生理过程,如葡萄糖/脂质代谢、脂肪酸氧化、细胞自噬/凋亡和衰老等[27]。研究表明,SIRT1可通过抑制MG激活减轻神经炎症反应,可能涉及糖原合酶激酶-3β(glycogen synthase kinase-3,GSK3β)/磷酸酶及张力蛋白同源物基因(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ue deleted on chromosometen,PTEN)信号通路[28]。SIRT1在海马区的表达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而在神经炎症及神经退行性疾病大鼠中表达进一步降低,同时伴有NF-κB和下游促炎因子表达上调及DNA甲基转移酶1表达下调[23]。而AMPK可通过上调细胞内NAD+水平激活SIRT1,激活后的SIRT1通过去乙酰化p65直接抑制NF-κB活化和下调促炎因子表达,反过来,SIRT1又可促进LKB1脱乙酰化,进一步促使AMPK活化[29-30]。
PGC-1α是一种核转录辅助激活因子,维持机体正常能量代谢,是机体重要的炎症调节因子,如PGC-1α基因敲除小鼠对致炎刺激更加敏感,其骨骼肌和血液中NF-κB和促炎介质表达均上调[23]。而AMPK可通过磷酸化PGC-1α的Thr177和Ser538位点激活该转录因子,进而抑制NF-κB活化,防止机体因过度炎症反应受损。此外,SIRT1也可通过去乙酰化激活PGC-1α。AMPK/p53/NF-κB和AMPK/FoxO/NF-κB是其他可能的抗炎途径。肿瘤抑制因子P53和FoxO都是能量代谢、细胞增殖和炎症调节中重要的转录因子,AMPK可通过磷酸化P53和FoxO直接激活上述转录因子,抑制下游NF-κB信号传导[31-32]。
AMPK还可能通过磷酸化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eNOS)调节NF-κB信号通路。研究发现,虾青素处理大鼠神经炎症明显减轻,脑梗死面积、脑水肿体积及皮质缺血半影区细胞凋亡率明显下降,p-AMPK、p-eNOS及抗炎因子如IL-10表达上升,NF-κB和促炎因子如IL-6和TNF-α表达下降。给予AMPK抑制剂可明显降低虾青素的神经保护作用,说明AMPK/eNOS/NF-κB可能参与抗炎机制[33]。此外,AMPK还可负调节TLR4介导的炎症反应。TLR4可通过TLR/MyD88/NFκB信号通路调控MG自噬和炎症反应,与野生型细胞相比,AMPK-α1缺陷型小鼠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中促炎因子表达升高,而抗炎因子表达降低,其机制可能为机体响应细胞内高于正常浓度的TLR4刺激。黄芪甲苷生物活性较强,可用于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给予慢性轻度不可预知刺激(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CUMS)+LPS制备的小鼠抑郁模型黄芪甲苷治疗可降低小鼠海马区IL-6和TNF-α含量,并显著降低TLR4表达,干扰AMPK表达可导致CUMS小鼠或LPS处理的BV2细胞和原代MG中TLR4表达下调,并消除部分抗炎作用,证明AMPK可作为TLR4的负调节剂抑制NF-κB激活,增强抗炎能力[34]。
2.2 AMPK与Nrf2信号通路 与NF-κB信号通路相反,Nrf2信号通路主要在炎症反应发生后通过抗氧化级联反应发挥保护性抗炎效应,因其在抗氧化和抗炎症相关基因表达通路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被认为是治疗神经炎症和炎症相关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潜在靶标。Nrf2是细胞内抗氧化应激的重要转录因子,激活后可转移入细胞核,与抗氧化反应元件作用诱导多个下游多个基因如谷胱甘肽-S-转移酶、血红素加氧酶-1、谷氨酸半胱氨酸连接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表达,发挥细胞保护作用[35]。但Nrf2激活的上游机制尚未阐明,目前研究普遍认为其抗神经炎症机制由AMPK激活所诱导[36]。MG激活介导的神经炎症在局灶性缺血性中风的发生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HP-1C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可同时激活AMPK与Nrf2的双重激动剂,可明显减小短暂性脑缺血大鼠脑梗塞体积和改善神经损伤,其保护作用与AMPK/Nrf2通路介导的M2型MG增多有关[37]。脂肪因子趋化素Chemerin是新近发现的脂肪因子,向新生小鼠生发基质出血模型注射重组人源脂肪因子72 h后可明显促进小鼠脑室周围M2型MG增殖和聚集,改善神经功能,同时提高中枢神经系统p-CAMKK2、p-AMPK、p-Nrf2表达,并降低IL-6和TNF-α表达。给予AMPK抑制剂后可增强细胞内促炎介质表达,表明Chemerin可通过促进CAMKK2/AMPK/Nrf2途径改善生发基质出血诱导的炎症反应,且M2型MG可能是这种保护效应的主要介质[38]。一些具有抗神经炎症作用的药物如丹酚酸C、木质素化合物、金耳发酵液提取物及其主要多酚化合物没食子酸和鞣花酸等发挥效应的分子机制均涉及AMPK/Nrf2信号通路激活,为炎症性疾病的治疗方案开发提供了潜在策略[39]。
2.3 AMPK与mTOR信号通路 mTOR是细胞内分化增殖、能量代谢、氧化应激及蛋白合成等重要生物学过程中重要的调控因子,在体内主要以mTORC1和mTORC2 2种形式存在[40]。研究表明,AMPK-TSC1/TSC2/TBC1D7-mTOR途径可能介导AMPK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发挥抗炎和神经保护作用。TSC复合体(TSC1、TSC2和TBC1D7)是一种具有GTP酶活性的异源三聚体,当其被AMPK磷酸化激活后,可抑制mTOR表达。当mTOR被抑制后,一方面可减弱缺氧诱导因子1介导的糖酵解基因如乳酸脱氢酶、磷酸甘油酸激酶1、醛缩酶A及磷酸果糖激酶L转录,抑制糖酵解途径,进而抑制MG活化增殖,同时促进机体氧化代谢,提高M2型MG分化[41]。低浓度mTOR抑制剂Rapamycin可明显减少LPS诱导的MG促炎介质(iNOS、NO、COX-2、PGE2、IL-6和TNF-α)表达,通过小鼠脑黑质区定位注射实验及实时荧光定量PCR、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研究进一步表明Rapamycin可以非自噬依赖性方式抑制MG激活,保护神经元免受炎症损害,沉默mTOR表达后可产生相同实验结果[42];另一方面,抑制mTOR可增强细胞自噬,介导凋亡细胞死亡,如白藜芦醇可改善脊髓损伤大鼠运动功能并减少神经炎症发生。免疫荧光分析、ELISA及Western blot实验显示白藜芦醇处理后,大鼠体内p-AMPK、Beclin-1及微管相关蛋白轻链3(LC3)-Ⅱ/LC3-I比例显著上升,p-mTOR含量显著减少,而自噬抑制剂可部分减弱白藜芦醇的神经保护作用[43]。但研究发现,持续激活的AMPK可促使神经元萎缩和细胞凋亡,可能与过度抑制mTORC1表达,进而产生过强的自噬,破坏细胞内其他重要生理过程,促使神经元萎缩和细胞凋亡有关[44]。体内实验证明,AMPK激动剂和mTORC1抑制剂雷帕霉素可加剧6-羟基多巴胺氢溴酸盐(6-Hydroxydopamine hydrobromide,6-OHDA)诱导的小鼠脑多巴胺能神经元细胞凋亡,采用siRNA敲除细胞自噬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Beclin-1基因可有效改善神经元凋亡,AMPK抑制剂或mTORC1可产生同样的缓解作用,说明长时间AMPK激活可能以mTOR依赖的方式损伤CNS[45]。
3 AMPK与神经炎症的关系
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如AD、PD和MS等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常伴有以MG激活为主要特征的神经炎症反应,而在疾病发生发展的不同时期均可观察到AMPK及其各亚基在神经细胞中表达失调的现象[46-47]。AD患者大脑及APP(swe/ind)和APPswe/PS1dE9小鼠AD模型中,磷酸化AMPK(phosphorylated AMPK,p-AMPK)表达上调,且在缠结的神经纤维中存在超常磷酸化的微管相关tau蛋白和p-AMPK共表达[48];经6-OHDA和鱼藤酮诱导产生的PD细胞模型中AMPK和p-AMPK表达明显上升,而在PINK1基因缺陷型PD大鼠模型中AMPK和p-AMPK表达下降[49-50];mSOD1G93A转基因ALS大鼠模型中观察到AMPK活性自症状发作就开始增强的现象[51]。在源自SOD1 G93A小鼠的胚胎神经干细胞和SOD1突变体的运动神经元细胞系中也观察到同样现象[52]。尽管AMPK活化与神经系统疾病的具体关系尚未明确,但近年研究表明AMPK激活在神经炎症及其诱发的神经元病变中发挥神经保护作用。敲除小鼠的AMPK-β1亚基可导致严重的神经元损失及星形胶质细胞异常增殖[53]。敲除AMPK-α亚基的小鼠对致炎刺激如LPS和酒精更加敏感,蛋白组学分析显示其脑内促炎介质(IL-6、TNF-α和iNOS)表达明显上升[54]。借助外源AMPK激动剂的实验也很好地证明了AMPK在神经细胞中可有效发挥抗炎作用。AICAR可促进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NGF)诱导的轴突生长,同时减少在星形胶质细胞适宜培养条件下生长的PC-12细胞中的神经突增生抑制现象[55]。研究表明AICAR可通过阻断促炎介质表达、促进下游抗氧化基因表达(COX-2、TGF-β和IL-10)减轻LPS诱导的炎症反应[56]。白藜芦醇是一种天然的AMPK激动剂,可在LPS诱导的小鼠胶质细胞C8-B4神经炎症中发挥抑制炎症级联反应的作用,机制可能为通过抑制TLR4、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NF-κB)和激活磷酸化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ion 2 homolog 1,SIRT1)、AMPK信号通路抑制MG激活,防止神经炎症过度发生[57];其他体内外研究也同样证明AMPK在神经炎症中发挥保护作用。硫化氢是机体重要的气体信号分子,参与多个重要生理过程。硫化氢处理LPS诱导的MG系-BV2细胞可大量激活AMPK,显著提高p-AMPK含量,同时下调促炎介质IL-6、iNOS、TNF-α等表达,促进MG向M2亚型分化,减轻炎症症状[58]。KMS9920是一种被认为可靶向治疗神经炎症的新型合成药物,体外实验发现其可提高BV-2细胞中p-AMPK含量并增强其活性,同时上调HO-1表达,抑制促炎因子表达,在早期抗炎信号转导中起重要作用,是神经炎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潜在的治疗药物[59]。由于现有的AMPK激动剂均存在AMPK非依赖性作用,即上述AMPK激动剂还存在活化AMPK之外的功能,尚无直接方法证明AMPK激动剂的神经保护作用均是由AMPK活化引起的,需要进一步探讨可更加精准靶向作用于AMPK活性的方法阐明AMPK在神经炎症中的确切作用[60]。
但AMPK并非仅充当神经炎症保护因子的角色,一些情况下,其可能产生潜在的不良反应,如促使神经元萎缩和细胞凋亡等[61]。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病模型的早期阶段观察到持续的AMPK活化诱导神经元凋亡,同时伴有磷酸化哺乳动物雷帕霉素受体蛋白(phosphorylated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p-mTOR)、磷酸化蛋白激酶B(phosphorylated protein kinase B,p-Akt)及磷酸化叉头蛋白3a(phosphorylated forkhead box O3a,p-FoxO3a)含量降低,抑制mTOR和Akt信号传导途径可导致神经元发育不完全而萎缩[62];同样,谷氨酸对发育中的大脑具有神经毒性,而AMPK是这种神经毒性的关键介质,向发育中的大鼠注射谷氨酸导致其氧化应激增强,诱导AMPK持续性活化、ROS产生、神经炎症及退行性病变,采用AMPK抑制剂或siRNA干扰AMPK表达可有效减少谷氨酸诱导的神经毒性,同时证明花青素可以AMPK依赖的方式将谷氨酸诱导的神经毒性的严重程度降至最低[63]。
AMPK在神经炎症中相对立的作用反映AMPK调节神经炎症的机制错综复杂,提示应根据细胞类型、生物能量状态、疾病发展阶段等综合考虑AMPK活化的结果。如在不同条件下AMPK活性与细胞凋亡的关系可能是双向的,在某些水平上AMPK活化可促进细胞存活,但在更高强度或更长的持续时间内,其会促进细胞程序性死亡,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最适当的AMPK活化水平,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神经保护作用,同时限制其潜在的不良反应,为临床试验提供参考。
4 结语
AMPK因其MG活化及极性调节作用被认为是神经系统疾病的潜在治疗靶点,随着研究不断深入,AMPK在神经炎症中发挥的作用逐渐明朗,但随之而来更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AMPK的12种异构体在不同病理条件下是否存在差异性表达及其是否发挥不同作用、如何选择AMPK活化水平及药物激动剂的种类才能保证MG的最适激活程度及M1/M2活化亚型的最佳平衡状态、不同疾病中MG的最适激活程度和M1/M2活化亚型最佳平衡状态如何确定、M1亚型是否总是有害或M2亚型是否总是有益以及AMPK在神经炎症中其他尚未发现的调节机制。此外,讨论AMPK在神经炎症中发挥的具体作用时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如实验模型(小鼠品系及所用细胞培养物的类型等)、细胞能量状态、疾病发展阶段及AMPK激动剂的种类和剂量等。现有研究均停留在临床前阶段,如何用于临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