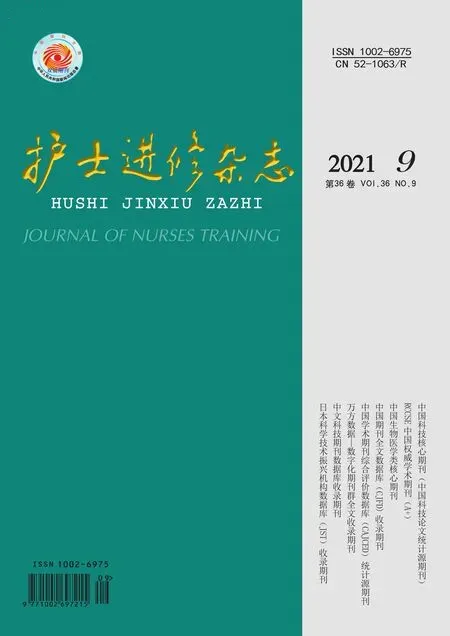社区老年人孤独感、社会隔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谢颖 赵庆华 肖明朝 王俊 黄欢欢 许文馨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 400016)
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2.54亿,占总人口的18.1%[1],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且呈现出“三多一少”(慢病老人多、失能老人多、高龄老人多,子女少)的特点。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且逐渐向慢病化、多病化方向发展,老年人极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2]。有多项研究[3-5]证明,孤独感与社会隔离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通过早期识别其影响因素进行干预可预防不良健康结局的发生。孤独感与社会隔离虽为不同的概念,但经常互换使用。孤独感是实际和期望的社会关系之间差距的主观感知;社会隔离是个人社会关系中客观量化的不足,通常以社会网络的大小或联系频率来衡量[6]。老年人可能有社会隔离而不会感到孤独,或者即使有足够数量的社会关系也会感到孤独。目前国内研究[7-8]主要是将孤独感与社会隔离分开探讨其影响因素,尚未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探讨其影响因素的共性与个性。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老年人的孤独感与社会隔离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制定减少老年人孤独感与社会隔离的干预方案提供理论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0年3-6月选取重庆市5个社区的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调查对象在社区居住≥1年。(2)年龄≥60岁。(3)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1)身体有重大疾病、精神疾患、意识障碍、老年痴呆不能完成询问者。(2)表达不清,沟通障碍者。
1.2调查工具
1.2.1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包括居住地(城镇或农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居住方式、慢性病数量等。
1.2.2UCLA孤独量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s,UCLA) 由Russell等[10]编制,中文版量表[9]包括正序条目11个与反序条目9个,共20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4级评分,即从不、很少、有时、一直,依次得分为1~4分,反序条目则相反,总分为20~80分。20~34分为低程度孤独感,35~49分为中等程度,50~80分为高等程度。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
1.2.3社会网络简化版量表(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 6,LSNS-6) 由Lubben等[11]编制,包括家庭网络(3个条目)与朋友网络(3个条目)2个维度共6个条目,每个条目按0~5级计分,0、1、2、3、4、5分分别代表没有、1位、2位、3~4位、5~8位、≥9位,总分为0~30分,总条目得分<12分表明存在社会隔离,各部分条目得分之和<6分表明存在家庭隔离或朋友隔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
1.2.4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由肖水源[12]编制,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共10个条目。量表总分66分,<20分表示低水平社会支持,20~30分为中水平社会支持,≥30分为高水平社会支持。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
1.2.5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Family adaptation,partnership,growth ,affection and resolve,APGAR) 由 Smilkstein编制,张作记等[13]翻译并修订的中文版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包括家庭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5个条目,每个条目采取3级评分法,“经常这样”计2分,“有时这样”计1分,“几乎很少”计0分。总分0~3分表示家庭功能严重障碍,4~6分表示家庭功能中度障碍,7~10分表示家庭功能良好。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1.2.6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 由美国学者Lawton等[14]编制,包括6项躯体生活自理能力(穿衣、吃饭、洗澡、室内行走、上厕所、上下床)及8项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打电话、购物、做饭菜、做家务、洗衣服、乘坐公共汽车、吃药、管理钱财),共14个条目。每项采用1~4级评分,依次为自己可以做、有些困难、需要帮助及根本无法做。总分14~56分,14分为完全正常;15~21分,轻度功能受损;≥22分,重度功能受损。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1.3调查方法 本研究在获得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后采用一对一询问的调查方法,调查人员是经课题组统计学老师统一培训的3名护理学本科生。调查人员在排除第三方干扰的情况下,由调查人员口述问卷内容,根据老人的所表达的意思填写对应的选项,以保证问卷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问卷经检查核对后现场收回,本研究共发放问卷520份,回收有效问卷506份,有效回收率97.31%。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EpiData 3.1软件进行问卷双录入,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采用人数和构成比进行描述,分类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老年人孤独感和社会隔离的相关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老年人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调查506名社区老年人,年龄60~99岁,平均年龄(71.24±7.55)岁。低程度孤独感老人411名(81.2%),中度孤独感老人71名(14.1%),高程度孤独感24名(4.7%);处于社会隔离的老人136名(26.9%)。
2.2影响老年人孤独感与社会隔离的单因素分析 在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收入、居住方式、慢性病数量、日常生活能力、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及是否发生社会隔离方面,不同孤独感程度的老年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居住地、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收入、居住方式、吸烟、慢性病数量、医疗费用支付情况、日常生活能力、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孤独感程度方面,社会隔离组与非社会隔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影响社区老人的孤独感与社会隔离的单因素分析(n=506)
2.3影响社区老年人孤独感、社会隔离的多因素分析 将孤独感程度与是否发生社会隔离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回归分析模型。自变量赋值,见表2。分析影响社区老年人孤独感与社会隔离的风险因素。慢性病数量、日常生活能力、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居住方式与发生社会隔离是孤独感的主要影响因素,独居老人发生孤独风险比与配偶或子女居住的老人增加4.885倍,日常生活能力障碍的老人发生孤独风险比日常生活能力完好的老人增加3.074倍,慢性病数量多于3种的老人发生孤独风险比慢性病数量2种及以下老年人增加1.478倍,见表3。

表2 自变量赋值情况

表3 社区老年人孤独感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n=506)
2.4社区老年人孤独感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年龄、日常生活能力、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及孤独感程度是发生社会隔离的主要影响因素,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生社会隔离的风险比80岁以下的老年人增加1.793倍,处于高程度孤独感的老年人发生社会隔离风险比中、低程度孤独感老年人增加8.361倍,见表4。

表4 社区老年人社会隔离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n=506)
3 讨论
3.1社区老年人的孤独感与社会隔离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区老年人中等及以上程度孤独感比例为18.8%,社会隔离比例为26.9%,低于马潇斌等[15]对高龄老人中、重度孤独感发生率的调查,原因与本次调查的人群选择为≥60岁的老年人有关,低龄老年人身体机能未明显下降,有利于维持较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的孤独感较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表明,我国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发生率为34.9%[16],低于本研究调查的社会隔离发生率,可能与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少有关。本研究结果也低于李少杰等[17]对济南市农村老年人社会隔离发生率调查,可能与本次调查人群纳入了农村与城市的老年人有关,中国老年人的社会隔离状况具有较大的城乡差异性[18],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外流,空巢现象严重,且交通不便会影响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必然会加重老年人的社会隔离风险,而对于城市则交通便利且基础设施较完善,老年人普遍收入较高,子女经济状况相对较好,代际关系较为紧密,有利于增强老年人的社会联系。国外也有研究[19]表明,老年人孤独感与社会隔离的发生率分别为30%与50%,与国内有一定的差异。因此,老年人的孤独感与社会隔离问题普遍存在,应引起重视。可借鉴国外经验,老年人孤独感与社会隔离干预方案制定应从个人层面转向机构和公共卫生层面,管理者首先需识别孤独感与社会隔离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制定个性化或结构化的干预策略,主要内容包括提高社会技能、增强社会支持、增加社会互动机会与解决社会认知不足4方面,通过创建友谊教育课程、交友自愿计划、互联网技术互动游戏以及自我管理会议等活动,帮助其维护或重建朋友圈和家庭圈,满足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需求,为老年人营造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20-21]。
3.2社区老年人的孤独感、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分析 社区老年人的孤独感、社会隔离是主客观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多因素分析显示,社区老年人发生了社会隔离(孤独感),其发生孤独感(社会隔离)的风险会显著增加,孤独感与社会隔离互为风险因素,共同作用可导致心血管疾病、认知障碍、抑郁症等不良健康结局发生[22]。多因素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日常生活能力差、社会支持水平低与家庭关怀度低均是孤独感、社会隔离的危险因素。日常生活能力越差,老年人产生孤独感与社会隔离的风险高,这与景翔等[23]的研究结果一致。日常生活能力差的老年人在人际交往中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与障碍,限制其社会交往与社会参与,难以建立与维持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从而增加孤独感与社会隔离风险。另外,本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水平低,老年人产生的孤独感与社会隔离的风险高,这与韩影等[24]的研究结果一致。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与社会各方面包括亲属、朋友、同事、伙伴等社会人以及家庭、单位社团组织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联系程度,通过其联系可帮助个体获取一定资源,满足个体的需要[25]。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社会情感选择理论认为老年人更愿意经营好家庭成员与亲密朋友组成的网络,并不断收缩其它的社会关系网络,扩大积极情感,减少消极互动[18]。家庭成员的支持作为老年人的主要社会支持来源,尤其在老年人遭受某些应激性生活事件时,通过与老伴、子女、亲密朋友的聊天,互相关怀、支持与鼓励,维持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对负面情绪起到调节和保护作用[26]。
3.2.1慢性病数量与独居是老年人产生孤独感的危险因素 研究[27]显示,多种慢病共存的老年人往往具备更少的社会网络资源,由于多种慢病共存必然会损害健康功能,健康功能障碍将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关系质量,从而增加其孤独感风险。对于独居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较大,与Chen等[28]研究结果一致。随着原有家庭凝聚力与代际间的亲密性逐渐被破坏,加之老年人失去了来自配偶的情感性与工具性支持,独居老年人从家庭成员中得到的实际支持与预期支持之间的差异会导致强烈的失落感,导致老年人孤独感的发生。
3.2.2年龄是老年人产生社会隔离的危险因素 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更有可能经历诸如空巢、亲友去世、残疾及患病等生命事件的冲击,这些负性事件会削弱老年人维持社交网络的能力,减少社会交往及社会参与,最终导致社会隔离的发生。因此,社区管理者在制定策略时,应重点关注高龄老年人的社会关系变化,呼吁给予高龄老年人更多的社会支持与家庭关怀,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对于身体状况受限、活动能力有限的老年人,可借助信息化手段如QQ视频、微信等形式增加社会参与,降低社会隔离风险。
综上所述,老年人是产生孤独感与社会隔离的高危人群,本研究通过探讨社区老年人孤独感与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为制定减少孤独感与社会隔离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参考依据,应重点关注高龄、多种慢病共存、日常生活能力差、家庭关怀度与社会支持低的老年人,强化代际支持功能,鼓励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社会活动,建立多方社会支持体系,减少老年人孤独感与社会隔离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