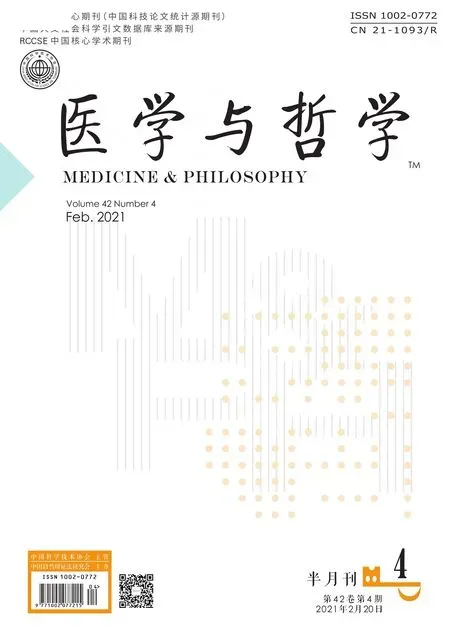汉译佛经之“四大病”辨识
郜林涛 黄仕文 黄仕荣
滥觞于吠陀时代的“四大说”,原为印度古代哲学思想中受到普遍关注的关于物质世界“极微”理论的基本认识和核心内容。佛教予以吸收改造而别出新解,突出强调事物的“无自性”,既讲“性空”,又讲“妙有”[1],并将其构建成自己的基本教义之一,认为宇宙万有皆由地水火风“四大”和合而成,且关乎其生灭变化。佛教医学则援引“四大”来进一步解释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神识现象和病理变化,并用以归纳药性,指导治疗和摄生防病,从而将“四大说”建构成自己的理论支柱[2-4]。佛教医学“四大说”对我国古代哲学和传统医学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又重新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尤其是佛教医学对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对身心疾病诊疗的独到作用,越发令人叹为观止[5]。本文在佛教义理和“四大”哲学思想以及佛教医学“四大说”基本理论的指导下,较为系统地爬梳了汉译佛经中“四大病”之相关内容,并参考中国传统医学和现代之相关研究,对“四大不调”所致“四大病”之病因病机、病相病处与疾病分类等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整理和诠释,庶几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1 佛教“四大”及其“和合相违”的辩证关系
佛教以为,地水火风“四大”系构成一切色法之最基本要素。一切物质现象均依“四大”而生灭变化,故亦称“四大种”[6]。元素之“四大”具有生因、依因、持因、立因、养因,故称能造之色。“四大”各持自性不改,故而所造之色法就有多种之差别,故亦谓之“四界”。“四大”称其“大”者凡三义。《俱舍论颂疏论本》:“大种谓四界者,标也。三义释大:一体宽广故谓四大种,遍所造色,其体宽广;二增盛聚中,形相大故……三能起种种大事用故……一义释种,与所造色,为所依故,故名为种。大则是种,故名大种。能持自性故名为界。即地水火风者举数,能成持等业者明用。地能成持用……水能成摄用,火能成熟用,风能成长用。坚湿暖动性者出体,地坚水湿火暖风动。”[7]“四大”同时通于一切色法,独立各具,然于不同色法之中,其中之一大较为增盛,其余之三大乃摄其中。此诚《瑜伽论记》卷一四所谓“一切色聚必具四大”[8]。“四大”有内外之分别,有情肉体之“四大”称“内四大”,体外之“四大”则为“外四大”。“内四大”是构成有情色身形骸之基本元素,生理上各有对应归属。故此,有情之肉身亦称“色身”“四大身”。同时,“内四大”也是假合的,彼此间充斥着重重矛盾与冲突,从而又常常表现为各种病理变化。《弘明集》卷五:“夫四大之体,即地水火风耳。结而成身,以为神宅。”[9]《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10]《大智度论》卷一九:“是身四大和合造,如水沫聚,虚无坚固。是身无常,久必破坏。”[11]203《杂阿含经》卷七:“诸众生此世活,死后断坏无所有,四大和合士夫。身命终时,地归地、水归水、火归火、风归风,根随空转。”[12]44
佛教将“四大”之间的联系总括为“和合相违”。《佛祖三经指南》卷下:“虽乃四大扶持,常相违背……四大扶持者,谓四大有互相扶持之意也,如水得火而不寒,火得水而不燥等;常相违背者,谓四大之性升降动静,互相乖反也。既有扶持之功,又有违背之害,故有生老病死之累也。”[13]“和合”表现为四力均等,互具融摄,相倚相住,相资相翼。《大般涅槃经集解》卷六一:“四大亦无有业者,四大力虽均等,至各不相似,四力皆等。”[14]《大毗婆沙论》卷一二七:“问此四大种于一切时不相离耶……若有地界无水界者,便应干散,今不散者水所摄故;若有水界无地界者,便应流治,今不流者地所持故;若有地水无火界者,便应臭烂,今不烂者火所熟故;若有三界,无风界者应不增长,今增长者风所动故。”[15]663可见,地水火风“四大”暂时之和合,既为“坚、湿、暖、动”四大体性之假合,亦是“持、摄、熟、长”四大业用之假合。从“相违”看,“四大”又表现为时时违反,各各侵害,交叉触忤,增损相克。《摩诃止观》卷七:“复当知四大成身,二上(按:指风火轻举)二下(按:指地水沉下),互相违返。地遏水,水烂地;风散地,地遮风;水灭火,火煎水。更相侵害,如箧盛四蛇……四大相侵,互相破坏,是为坏苦。”[16]87《诸经要集》卷一九:“夫三界遐旷,六道繁兴。莫不皆依四大相资,五根成体。聚则为身,散则归空。然风火性殊,地水质异。各称其分,皆欲求适。求适之理既难,所以调和,之乖为易。忽一大不调,四大俱损……既一大婴羸,则三大皆苦。展转皆病。俱生煎恼。四大交反,良由苦报……片失供承,便招病苦……良由身为苦器,阴是坯瓶,易损难持,四大浮虚,亟相乖反。”[17]由此可见,“四大”之间既对立又统一,两者是同时俱在,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所以是辩证的对立统一,使得由“四大”所构成的一切事物都是稳定、变动、凝聚和分化的过程[18],简而言之就是生灭变化。盖因佛法之故,佛教多言“四大违和”之“常在”,或喻之曰“四蛇相逐,恒相残害”,是故有情众生则“常病”。《佛说众许摩诃帝经》卷五:“众生之身,业惑所感,四大和合,性相违反,老病死苦。”[19]《大智度论》卷十:“圣人实知身为苦本,无不病时。何以故?是四大合而为身。地水火风,性不相宜,各各相害。譬如疽疮,无不痛时,若以药涂,可得少差而不可愈;人身亦如是,常病常治,治故得活,不治则死。以是故,不得问无恼无病。”[11]131佛教“四大说”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既为佛义圆寂理论之倚托,又为医学生理、病理和治疗理论之概括[20]。
2 “四大不调”辨识

生理状态下,“四大”之“体性”与“势力”均等,视为“四大调适”或“四大安稳”。《四分戒本如释》卷八:“无病者,谓四大调适,无诸疾苦。”[30]《大毗婆沙论》卷三三:“谓彼外道,身无楚痛,执为无病……彼尚不知,四大调适,名为无病。”[15]17这种“无病”状态在佛教看来却只是暂时的或相对的。与之相对,“四大不调”却是“常态”。《止观辅行传弘决》卷八:“初明实病中,云四蛇者以譬四大,于中复以鸱枭性升以譬火风,蟒鼠居穴以譬地水。”[31]《金光明经文句》卷四:“譬如四蛇初在箧时名生,四蛇力敌名壮,互相强弱名病。蛇斗困暂息不动谓为调适,息已复斗,蛇羸如老,蛇绝为死。”[29]66由此可见,“生老病死”整个生命的过程,也就是“四大”之“和合相违”的过程。“和合”乃为生为身,“相违”则招致病患,甚而“四大欲散,魂魄不安”,“四大分散,是名夺命”。一切皆所谓“虽乃四大扶持,常相违背”[13],一切皆在于“四大”是有因缘聚散的,由此色身则无常、不实、受苦,而救治之要即在于纠偏协调之。《大般涅槃经》卷八:“譬如四大,其性不同,各自违反。良医善知,随其偏发而消息之。”[32]651可见,佛医所谓“四大不调”既是病因病机,亦为病相病处,甚或代指疾病之称,实为一多层次之综合概念,谓之“总纲”,当之不过矣。
3 “四大病”之病名、病因病机、病相与病处辨识
佛教“医方明”位列“五明”之第三,而“知医疗”则位列“先明世法十门”之第二,足见佛教向来之重医。佛医要求“疗者必瘥”的所谓大医王或良医须备具“善解四明,妙通八术”,“四明”或谓之“四德”“四法”“四仪”“四善巧”。《法华经疏》:“一知病,二知病因,三知治方,四知差已不生。”[33]《杂阿含经》卷一五:“有四法成就,名曰大医王。一者善知病,二者善知病源,三者善知病对治,四者善知治病已当来更不动发。”[12]105《阿毗达磨俱舍论》卷二二:“夫医王者,谓具四德,能拔毒箭。一善知病状,二善知病因,三善知病愈,四善知良药。”[34]《瑜伽师地论》卷一五:“云何医方明处?当知此明略有四种,谓于病相善巧,于病因善巧,于已生病断灭善巧,于已断病后更不生方便善巧。”[35]356《涅槃义记》卷二:“何者八术?一知病体;二知病因;三知病相;四知病处,或在五脏,或在支节;五知病时,平旦发者是如此病,如是等也;六者知药,识其药体;七者知治,知如此药治如是病;八者知禁,知如是病服如是药,忌如是食。”[36]从内容上看,“四德”与“八术”主要还是针对疾病诊断,而所依据的主要还是“四大说”。
3.1 佛医言“病”与“四大病”之病名
佛教将众生现世所患之病疾称作“因中实病”,因其有形有相,有具体病因,因以为名。析言之,此“因中实病”应为“实病”之下之“果病”,而“果病”才是众生“四大不调”于身所现之病相,是为“身疾”之所属[37]。《方广大庄严经》卷五:“所谓病者,皆由饮食不节,嗜欲无度,四大乖张,百一病生,坐卧不安,动止危殆,气息绵惙,命在须臾,以是因缘,故名为病。”[38]《大般涅槃经》卷一二:“病谓四大毒蛇,互不调适。”[32]435佛教“观身如箧”,以为“有身皆苦”“有漏皆苦”“有身必有病”“有生死则有病”,苦就是病态,而病疾的发生是在“内四大”自身增损违和的基础上,复因寒暑外感、嗜欲无度、饮食不节、卧起无常等造成色身地水火风“内四大”平衡失调所致,诚然亦与“四大”之强弱相关。上溯至姚秦鸠摩罗什所译《孔雀王呪经》中就有“热病”“风病”“火病”“水病”有关“四大病”之具体译名之记载。《佛说佛医经》中则明确称地水火风为“四病”。隋代智顗在其所述《摩诃止观》卷八中更加具体阐释了“四大病”之病因病机与具体命名“规则”。其云:“四大不顺者,行役无时,强健担负,棠触寒热。外热助火,火强破水,是增火病。外寒助水,水增害火,是为水病。外风助气,气吹火,火动水,是为风病;或三大增害于地,名等分病;或身分增害三大,亦是等分,属地病。此四既动,众恼竞生。”[16]106由此可见,除“地大病”之外,其余“三大病”均则“偏盛”者而名之。此外,亦有依据“病相”和“病性”命名者,如“黄病”“冷病”“热病”等,且各个“四大病”皆有多个不同译称。在某些经文中,四个“四大不调”也即四个具体的病名,如“水大不调”即为“水病”。
3.2 “四大病”之病因病机
佛教致病说凡数种,总以“四大不调”为最重要之缘起。佛医拔病首在“明病由”,或言“明病起因缘”“知病因起”。《高峰和尚禅要》:“良医治病,先究其根。纔(按:“纔”乃“才”之异体字)得其根,无病不治。”[39]佛医援引“四大说”之旨重在阐释病因病机,以为色身现世“四大病”皆缘于“四大不调”,然依佛经所说亦有“或总或分”之别。总而言之,“四大不调”即病因病机之“总纲”,或直接将其作为疾病之定义,从而成为疾病之代称。分而言之,则体现在言说“四大病”之具体某个病的发病特点上。《毗婆尸佛经》卷上:“四大假合,虚幻不实,稍乖保调,即生苦恼,此名为病。”[40]《修行本起经》卷下:“人有四大,地水火风,大有百一病,展转相钻,四百四病,同时俱作。”[41]《十诵律》卷二:“病者,四大增减,受诸苦恼。”[42]《大明三藏法数》卷四:“身病谓身因四大毒蛇,互不调适,以致诸病所生,故名身病。”[24]可见,佛医以“四大不调”定义“身病”,而“病”主要就是色身所发生的“四大增损”“此增彼损”的病理病机变化过程,前提是“四大假合,虚幻不实”。《摩诃止观》卷八:“病起因缘有六,一四大不顺故病,二饮食不节故病,三坐禅不调故病,四鬼神得便,五魔所为,六业起故病。”[16]106所列六大病因(实赅病机),“四大不顺”居位其首,余者多为宗教医学之特色使然,姑且不论。此外,佛医在阐释病因病机时也认识到“内外相应”的致病特点。上所言“四大不顺”者确为发病之“内因”,然佛医亦认识到诸多“外缘”之致病性。因此,身病当有“内外二因”。《四谛论》卷一:“身界毒蛇触忤名病。复次病有二种,一身二心。身病复有二种。一因界相违,名缘内起;二因他逼触,名缘外起。”[43]《随相论》:“病从内外缘生。外谓寒热不平等,饮食不调适,故致病苦;内者或行多令四大弱,或坐多令四大弱,四大弱故成病。上界外无寒热不平等,饮食不调适之缘;内四大既强,无有行坐过差之缘,故不得有病苦。”[44]以上诸经所解之病因,言“内因”者,“四大不调”为其主,其言“界相违”亦“四大不调”之谓也;所言“外缘”者,凡寒热不平等、饮食不调适、行坐过差、卧起无常数种。总论则“病从内外缘生”,别言“缘内起”“缘外起”者,亦“病从内外缘生”之义,断非两类身病之谓也。念及佛经有言“四大强”“四大强弱” “四大假合,虚幻不实”,臆断此说“内因”之“四大弱”犹言传统中医之“正气虚”或“体质弱”。仅举一例,有待考覆。《迦丁比丘说当来变经》“汝等四大强建,心坚意猛。勤行精进,可得度苦。若复一旦身心微弱,而为老病所见踰蹈,悔无所及。”[45]此处“四大强建”对言“身心微弱”,其义自见。总之,佛医虽未具言病机之详,然综其所说,实涵传统中医所谓“正邪相争”之意蕴,同时也体现了“阴阳失调”和“升降失常”之部分属性,无他,“四大”间固有之体性与业用及其“和合相违”之辩证关系使然矣。此外,佛医说病多言“偏发”“偏起”或“偏盛”,而罕言“偏衰”“偏损”,这主要体现在“单因素”致病的特点上。在说明综合性致病因素时,则言“杂”“兼”“等分”“总集”“三集”“三俱”等,且集中体现在“地大”致病的特殊性和“地大病”的发病特点上,故有所谓“三大增,一大病”之说。此外,其余“三大”在出现“增盛集合”时也会出现如同地大致病时“一大增,三大病”,这种“一因多病”的严重情况。容举一例,有待深玩。《大宝积经》卷七三:“又时身内风界增盛集合。彼增盛集合时,能枯燥水界,亦能损减火界。于时枯燥水界,损减火界已,令人身无润泽,亦无温暖,心腹鼓胀,四支掘强,诸脉洪满,筋节拘急。彼人尔时受大苦恼,或复命终。”[46]
3.3 “四大病”之病相与病处
佛医虽将病苦视作大苦之“内苦”,但首先认识到的还是其表现于外的“病相”,而佛医所谓的“观病相”,其实就是“审症求因”。这与传统中医关于“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和“司外揣内”的认识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维摩经略疏》卷七:“以众生病从四大起……众生四大所成应同,亦现四大所成。四大即是成病之法。”[47]“四大病”各有对应之病相和病处,两者相当于传统中医学之症状和病位,且两者密切相关,同属于诊断学的内容。佛医拔病祛苦,同样也是通过病状貌和病位的认识,藉以了知病疾之根缘。生理上,佛教医学是以“内四大”来阐释有情色身之组织结构及其功能活动,病理状态下则亦可藉以解说“四大病”之病相和病处。其中,佛医释“病相”亦有“或总或分”之别。总而言之,是有“五相”,当为身心病疾种种病状之总括。《瑜伽师地论》卷六一:“当知病苦亦由五相。一身性变坏故,二忧苦增长多住故,三于可意境不喜受用故,四于不可意境非其所欲强受用故,五能令命根速离坏故。”[35]642分而言之,则又在“四大”体系下依其各自之体性与业用,别言“四大病”各个之病相与病处。《入阿毗达磨论》卷上:“此四大种,如其次第,以坚湿暖动为自性,以持摄熟长为业。”[48]《法观经》:“身有三十二物者,计发、毛、爪、齿、骨、皮肉、五藏十一事属地;泪、涕、唾、脓血、肪髓、汗、小便七事属水;温热、主消食二事属火;风有十二事。”[49]《摩诃止观》卷八:“若身体苦重,坚结疼痛,枯痹痿瘠,是地大病相;若虚肿胀胮(按:“胮”同“膀”,“浮肿”义)是水大病相;若举身洪热,骨节酸楚,嘘吸顿乏,是火大病相;若心悬忽怳,懊闷忘失,是风大病相。”[16]106佛经中主要还是按照“四大病”之病名及其所属之病位分类罗列,然见诸佛经所载,详略不一,多寡相殊,犹且散见和凌乱,甚或矛盾偶见,亦有待综核考辨。《佛说五王经》所云:“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四百四病同时俱作。地大不调,举身沉重;水大不调,举身膖(按:“膖”同“胮”,即“膀”)肿;火大不调,举身蒸热;风大不调,举身掘强,百节苦痛,犹被杖楚。”[50]此经在论病处时通言“举身”,显然未按“四大”之所属而赘分。某些佛经还认识到病相是动态变化的,此皆关乎病程之久暂、病情之轻重和四大身之强弱等。《金光明经疏》:“治病药者,病难有四。一风、二痰、三热、四等分。此四种各有三品,一者可治,此是新病,四大犹强也;二者恒治不差,此是四大过伤也;三者不可治,见有必死相故。”[51]值得一提的是,唐道世在其所撰《法苑珠林》卷九五和《诸经要集》卷一九中均例举了“四大增”与“四大损”两类病相,较之群经统言之例尤显特别而罕见。从名称和内容上推断,似有分别病相为“虚实”之涵义。实为难得,良可深究。
4 “四大病”与疾病分类
“四大说”是为佛教医学之总纲[20]。因此,以“四”为体系赘分疾病类别,是亦无疑,自当识其“四种”以名身病为当。《佛说佛医经》:“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土属身,水属口,火属眼,风属耳。”[52]值得注意的是,佛经中关于“四大病”说及其具体的分类存在着一定的争议。首先,即使在“四大病”框架下,病疾之数亦有或三或四之差异。本从“四大病”或“根本四病”,却又有“三大病”之说。《佛说七处三观经》:“世间有三大病,人身中各自有。何等为三?一为风,二为热,三为寒,是三大病。”[53]两者之分歧之要点即在于是否认可“地大病”之独自存在及其有关诸多“异称”上。由于佛教史上对此异议较大,且各有依据,有待深入研究与厘清辨证。其次,某些佛经在“四大病”的体系下,依据病因、病性等将“四大病”再二分为“冷病”和“热病”。《大智度论》卷五八:“四百四病者,四大为身,常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冷病有二百二,水风起故;热病有二百二,地火起故。”[11]469最后,亦有认为“身病有五”者。《大般涅槃经》卷五:“所谓病者,四百四病及余外来侵损身者。”[32]392《大般涅槃经》卷一二:“身病有五,一者因水,二者因风,三者因热,四者杂病,五者客病。客病有四:一者非分强作,二者忘误堕落,三者刀杖瓦石,四者鬼魅所著。”[32]435此谓第五种身病“客病”之四因皆所谓“余外来侵损身者”,故不为“四百四病”之所属。考其所因之四,则几近于传统中医学“三因论”之“不内外因”。因此,深耕佛教医学尚需认识“四大病”与“身病”之异同。
5 结语
“生老病死”本为缘起世间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也是现世众生必须正确面对的现实问题。其中,“病苦”对世俗的身心均有重要的影响,故而它不仅是世间医学要解决的切身问题,也是佛法需对治的重要内容[54]。因此,知医方术、与乐拔苦、普度众生素来就是佛教之基本理想。佛教依据“四大”之体性与业用创立“四大说”,以为“四大不离”而成色法,“四大假合”乃致色身,“四大和合”谓之生,“四大调适”谓之安,“四大不调”谓之病,“四大分散”谓之死。“四大”关乎“生老病死”,不可谓不大矣!佛教医学则以“四大不调”为“主体”或“总纲”,结合“缘起”“三法印”“四谛”和“五蕴”等哲学思想来认识色身,看待生死,定义疾病,并对有情众生现世“因中实病”之病名、病因病机、病相病处、病理属性和疾病类型加以诠释和归纳,逐步形成了包含审症求因、治病求根、知病授药、瘥后防复、瞻病养护、医学伦理和应时摄生等丰富内容的,虽然散在但却相对完整的独特的医学诊疗体系。因此,“四大说”作为佛教医学之基石,是其善待有情众生之方便法门,既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一定的科学性,其间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就使得佛教医学天然兼具宗教、医学与哲学等多重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