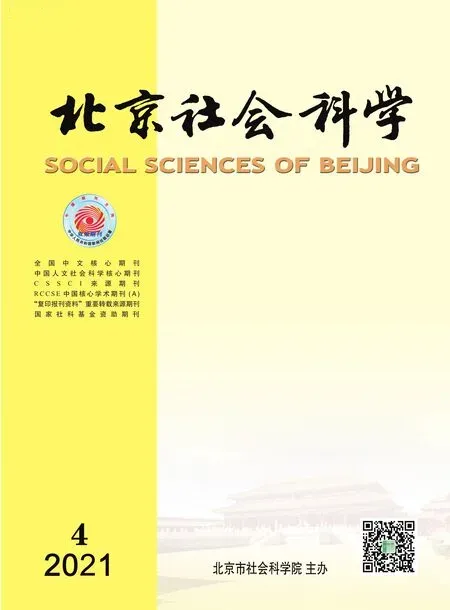《筱园诗话》象喻式表达的新变及意义
宋长建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州 510006)
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言说大体上含有两个层面的问题:“说什么”与“怎么说”。在以往的诗学研究中,学界偏重于考察说了什么,而对“怎么说”的层面,涉足较少。[1]以朱庭珍《筱园诗话》为例,研究者主要致力于内容的解读:比如“有真我”“积理养气说”“自然论”等诗学命题,[2]对清代诗坛的论述,[3]对杜甫、严羽和中原诗学的接受,[4]以上讨论在不同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都没有从言说方式进行观照。事实上,在《筱园诗话》中,象喻式表达被朱氏视作重要的批评策略,频繁用于诗学阐释。因此,文章拟围绕意象类型、阐释功能、审美价值、形成原因等问题,考究《筱园诗话》的象喻式表达,进而探寻其中的诗学意义和启示。
一
从历史上来看,诗学批评中的“立象见意”[5](P194)法起源甚早。比如《诗经·大雅·烝民》中已有“吉甫作诵,穆如清风”的说法,是以清微之风化养万物来比喻清美之诗感益人心。[6](P901)而后,钟嵘《诗品》将其广泛应用于诗歌品评。[7](P1-30)受此影响,后世说诗家也多以此法诠释诗学,如严羽以禅为喻建构诗歌品级,[8](P10-11)谢榛以书法为喻说明诗歌的学习方法,[9](P1164)叶燮以草木为喻诠释诗歌的发展变化,[10](P39)均是此种批评方式的延续。职是之故,有学者将类比与譬喻式的论诗方式定性为以诗话为主体的中国诗学的三大特点之一。[11]但在一些诗话中,这种论诗只是偶尔涉及,显得零散,类似《筱园诗话》这样将不同类型的意象大量运用到创作、鉴赏、批评等各个层面的著述,比较少见。接下来,拟从意象类型和诗学阐释两个方面,对这一特征展开具体分析。
(一)意象类型丰富多样
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特别注重意象的营造,[12](P176-179)力求寻找种类多样、内涵丰富的意象来为其诗学的阐说提供正确的参照。这些意象在运用中体现出显著的类型特征,以喻体的知识属性为标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表1 《筱园诗话》的意象类型

续表
从表1可以看到,《筱园诗话》的意象涉及佛禅、自然、人物、典故、艺术、兵法、仙道、神话、器物、医学、历史、幻术、杂剧、地理等多个方面,与此前的一些诗话相比,种类上明显丰富了许多。[13]这些意象的连缀使用,展示出多门知识的并连,犹如将散离的玻璃碎片拼合成水晶球,从不同角度折射出的光芒,使朱庭珍能够以多样的视角诠释诗学问题。同时,也为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读者提供了多元的认知媒介。其中的一些新奇意象,比如道教中的“金丹术”、杂剧中的“鱼龙百变”、堪舆学中的“急脉缓受”等,在批评实践中,多有出人意表之效,更加能够容纳朱氏对诗学的积极思考,他的许多开创性见解便是由此传达出来的。
在众多意象中,朱庭珍使用最多的是禅佛意象,这便提醒我们注意他在论诗中对以禅喻诗的强调。在镜花水月、华严楼阁等常见的佛教意象之外,他还择取了拈花微笑、哪吒之拆肉还母、拆骨还父、另由莲花化身等佛教词汇、故事,将佛禅之思巧妙地融入诗学批评,在晚清的诗学语境中,进一步深化了“论诗如论禅”的诗学观念。[8](P11)
(二)传统诗学的系统阐释
如果说丰富多样的意象类型只是《筱园诗话》象喻式表达表面的鲜明特征,那么,从表达的意义进行审视,其所具有的阐释功能则是深层研究的重要议题。大体而言,《筱园诗话》以意象来阐释的诗学问题具有系统性的特点,涵盖创作、鉴赏、批评三个层面,以下分别述之。
1.讲解诗歌创作
(1)阐发炼识之道和艺术构思。关于炼识之道这一话题,前人多有论及。范温《潜溪诗眼》谓“学者先以识为主”,[14](P371)叶燮《原诗》谓“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10](P150)并认为“识为体而才为用”,[10](P150)他们都强调了识见的重要,但并没有指出具体的求识路径。针对这一欠缺,朱庭珍以成佛、修仙为喻,明确提出了传承前人真知灼见的解决办法,“然炼识之道,不外乎得真传而已,……释家最重传法,一脉亲承,衣钵密付,然后能明心见性,……成佛作祖。道家内丹口诀,亦须密得指授,而后能性命双修,……以证仙班”。[15](P2213)在构思方法的示范上,朱氏也多有发明:“作诗先贵相题,题有大小难易,内中自有一定之分寸境界。作者务相题之所宜,以为构思命意之标准。……七子之浮声空调,正坐不知相题行事,一味击鼓鸣钟,高唱‘大江东去’,所以分寸不合,情景不切。”[15](P2215-2216)此处的“大江东去”,不难使人想到有关苏轼的故实,俞文豹《吹剑续录》言:“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16](P95)这位幕僚可谓知言,比况精妙。“杨柳岸,晓风残月”出自柳永名作《雨霖铃》,传递出柔情万种的感觉,故宜妙龄女子缓拍细腻清脆的红牙板而歌。“大江东去”指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气象阔大,豪放有力,若非关西大汉击打铿锵有力的铁绰板,则不能传达出词人的澎湃豪情。借助这一典故,朱氏使人清楚地认识到:就像演奏音乐所需的人物、乐器应该以歌词的内蕴为参照,诗歌的言辞、用典、篇章布局也应当依据诗题而定,如此方能合乎分寸,情景真切。
(2)指点作诗技巧。朱庭珍虽然认为诗歌创作没有一定的法则可循,但他同时又指出由法则入手,经过对法则的超越,才能达到无法即自然的境地。[15](P2203)由于此种观念的影响,他特别重视诗法的学习,讨论了修辞、表现方式等问题。比如“诗不可入词曲尖巧轻倩语,不可入经书板重古奥语,不可入子史僻涩语,……若夫已入歧途者,宜及早回头,……如康昆仑之于段师,虽失之东隅,犹可救之桑榆也”。[15](P2275)“段师教康昆仑琵琶”典出段安节《乐府杂录》:“段奏曰:‘且请昆仑弹一调。’及弹,师曰:‘本领何杂?兼带邪声。’昆仑惊曰:‘臣少年初学艺时,偶于邻舍女巫授一品弦调,后乃易数师。’段奏曰:‘且遗昆仑不近乐器十余年,使忘其本领,然后可教。’诏许之。后果尽段之艺。”[17](P23-24)此处以琵琶的学习比拟诗语的锤炼,认为词曲中的尖巧之语、经书中的板重之语以及子史中的僻涩之语,就如同康昆仑少年所学,由此入门,其结果就是“杂有邪声”,不能学得真正本领。故而,只有以正体为准,才能补救先前的缺失。此外,朱庭珍还解析了议论这一表现方式在短篇小诗中的用法:“短篇小诗,亦有不可无议论者。……须不尽而尽耳。……夫不尽而尽者,情深于中,韵溢于外,言简意赅,词近旨远。如画家缩本,咫尺具万里之势,则不尽而已深尽之。”[15](P2209)短篇小诗如同画家缩本,不能详尽描写所表现的对象,如果使用议论,则能在狭小的篇幅里,生发出深远的意蕴。基于这样的认识,朱氏指出不能因为宋人以议论为诗,神味索然,被后人讥讽,就完全抛弃议论,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2.表述诗歌鉴赏
(1)辨析诗人优劣。在朱庭珍之前,已有诗评家将意象运用于众多诗人的品鉴,最为人熟知的是王世贞。他在《艺苑卮言》卷五评拟了明代107家诗人,数量极大,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比喻存在“泛而不附、缛而不切”的缺陷,[10](P331)比如:“高季迪如射雕胡儿,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靓妆,巧笑便辟。刘伯温如刘宋好武诸王,事力既称,服艺华整,见王、谢衣冠子弟,不免低眉。袁可潜如师手鸣琴,流利有情,高山尚远。”[18](P2497)此处以射雕胡儿、燕姬靓妆,刘宋好武诸王、师手鸣琴分别类比高启、刘基、袁介的诗歌,语言可谓华丽,但其评说较为空泛。读者若追问譬喻的对象是诗人的古体诗、近体诗亦或是整体风格,王氏既没有延伸解释,也认为不必交代。化约至此,难怪惹得叶燮的抱怨。相较而言,朱氏对象喻式表达的使用,显现出不同的面貌。
其(诗道)变之善与不善,恒视乎人力,……至东坡则天仙化人,飞行绝迹,尽变唐人面目,另辟门户,……在宋人中独为大宗。[15](P2204-2205)
如鲁男子之学柳下,九方皋之相马,其性情契合,在笔墨形色之外,盖以神契、以天合也。故能自开生面,为一朝大作手。后人效法前人,当师坡公,方免效颦袭迹之病。[15](P2280)
在这里,作者先以天仙化人称誉苏轼的诗歌创作能够摆脱唐音宿习而有所开拓,自成一家,从而确立了个人在宋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借此论证以人力求变化的观点;后以鲁国男子、九方皋之事作比,从学习的层面,引申前说,指出苏诗新变的关捩在于东坡善于从性情处体味古人的佳处。在此基础上,朱庭珍认为后人效仿前人,也应像坡公这样,由此悟入,才能避免单纯模仿字句、声调的弊病。又如,对杨慎的评价,“以齐、梁绮丽为宗,词胜于格,肉多于骨,有春华而欠秋实,终非上乘禅耳”,[15](P2277)借“春华”“秋实”之喻批评他的诗歌仅有妖娆富丽的辞采而缺乏遒劲刚健的风格。
朱氏对黄景仁的评价更显精彩,从中尤其可以感受到意象化语言特有的表达效果:
黄仲则才力恣肆,笔锋锐不可当,如骁将舞梨花枪陷阵,万人辟易,所向无前,自是神勇;又如西域婆罗门,吐火吞刀,变幻莫测,具大神通。仲则七古佳篇,造诣颇似如是。……然自非大将本领风度,能不动声色,立摧强敌,而弥见整暇,如武侯以纶巾羽扇,指挥百万兵,进退分合,从容自得;又如郄縠敦诗说理,祭遵雅歌投壶,虽为将不失名士风流也。佛家贵正眼法藏,不尚神通。拈花微笑时,万法俱化,不屑以神通见,而自在神通,充满法身,不可思议,何必演幻法乎?诗家亦然。[15](P2237-2238)
此段鉴赏先以“骁将舞梨花枪陷阵”“西域婆罗门,吐火吞刀”等富于动态性的战斗场面和幻术表演,赞许黄景仁七古佳作的豪迈和奇特,之后从反面立喻,以武侯将兵、郄縠敦诗、祭遵投壶、拈花微笑等源于兵法、典故、佛教中的不同场景,委婉地说明黄诗尚未达到通神的化境,借此彰显“万法俱化”“无法之法”[15](P2203)的诗学观点。还需注意的是,在清代,除了朱氏,其他人对于仲则七古,也多有褒奖,袁枚说:“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顾孙杨各擅场。中有黄滔今李白,看潮七古冠钱塘。”(《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末句称前后两首《观潮行》为钱塘观潮诗之冠。孙星衍谓:“仲则《圈虎行》为七古绝技。”[19](P382)但与朱庭珍的品鉴比起来,上述品藻就显得较为平常,正因为朱氏采用了博喻的方式,以种类多样的意象进行比况,使得诗学表述形象可感,给人无限的遐想与回味,而且从长处和不足两个方面,更为完整地描绘了黄诗的艺术特征,从而扩大了批评力度。
上引譬喻都具有惬心贵当、内涵明晰的特点,与王世贞的模糊不清形成鲜明的对比。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朱氏的品鉴既具体指明了譬喻的对象,又对意象的背景有详细的解说,比如在批评黄氏七古的缺陷时,作者是在阐明“佛家贵正眼法藏,不尚神通”的基础上进行否定的,从而使其表述呈现出明白真切的效果。
(2)评骘前人诗歌选本和诗学观点。一是对诗歌选本和选本评语的批评。朱庭珍以鱼目混珠、碔砆混玉为喻,指摘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搜罗不当,“徒夸别裁之鉴,未脱门户之私”,以为选诗应以识力为主,不能“按图索骏,执相求禅”“执格律如奉法吏”,[15](P2237)从诗选的视域,再次强调了识见的重要。又以“鲁、卫之政”作比,阐明欧阳修和王安石的诗歌造诣不相上下,借此批驳王士禛《古诗选》的评语未为精当。[15](P2242)
二是辨析诗学观点。朱庭珍说“王元美谓茶陵之于李、何,犹陈涉之启汉高,文襄则抑而不录,何党同伐异,颠倒是非,一至于此。”[15](P2234)王氏用历史上陈涉、刘邦在反秦上的前后相续解释李东阳诗论对李梦阳、何景明的影响,道出了李东阳发七子派先声的事实,但也隐含有高下之分的意味。经过对这一比附的反驳,褒扬了李东阳在明代诗风转变中的贡献。又如对沈德潜以书法喻诗的质疑:“沈归愚先生云:‘作古诗不可入律,作律诗却须得古诗意。正如作书者,写隶篆八分,不可入行草楷书法;作行草楷书,却须得隶篆八分法,同此意也。’人以为妙喻妙论,予独不以为然。”朱庭珍认为古诗和律诗在体格、气象、法度等层面均有不同之处,所以不必以“五古平淡之味,施之五律,以求高瘦;以七古苍莽之气,行之七律,以破谨严”。[15](P2220)实际上从遵循诗歌体制的角度否定了沈德潜以偏概全的做法。
以上论述均从譬喻切入进行剖析,为我们绎释古代诗论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从此入手对前人的见解展开甄别,并非易事,若疏于理性的考证裁断,则可能出现认识上的误区,对袁枚的驳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随园诗话》持论多无稽臆说,所谓佞口也。如谓律诗如围棋,古诗如象棋。作古体,不过两日,可得佳构,作律体,反十日不成一首,是视律难于古也。[15](P2226)
关于这一说法,叶晔恰有一番议论可资参证,他通过梳理以棋喻诗的源流发展,认为袁枚此喻的本意“并不是写作层面的法度宽者(古体诗)为易、法度严者(近体诗)为难,而是法度严者(近体诗)在格律规制下要达成天工状态更难”,指出朱庭珍没能从袁枚的视角出发,换位思考,其理解“从创造层面回落到常规写作层面”“算是一次典型的因诗学偏见而造成的错误阐释”,[20]此乃识见。这也提醒我们真正掌握和理解古人的象喻性言说,需要结合诗评家的诗学倾向及所用譬喻的发展历程进行细致的考索,如此才能较为准确地还原出特定语境下的隐喻内涵。
三是阐发诗学理论。朱庭珍还以意象作比,诠解了一些诗学概念、命题,强化了象喻性言说的理论色彩。如对“诗有内心”的解读:“老庄告退,山水方滋,……盖有内心,则不惟写山水之形胜,并传山水之性情,兼得山水之精神,……使读者因吾诗而如接山水之精神,恍得山水之情性,不惟胜画真形之图,直可移情卧游,若目睹焉。此之谓诗有内心也。”[15](P2218-2219)以绘画作譬指谓诗歌的审美功能,直将作家创作和读者接受接连起来置论,同时也分辨了诗歌和绘画两种艺术形式在表现山水时的区别。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用不同的物象探讨了大家、小家等品第概念,[21]使其内涵更为清楚:
大家如海,波浪接天,汪洋万状……又如昆仑之山,黄金布地,玉楼插空……其中无美不备,无妙不臻……无所不有。……大名家如五岳五湖……是已造大家之界,特稍逊其神化耳。名家如长江、大河,匡庐、雁宕,各有独至之诣……特不能包罗万长,兼有众妙,故又次之。小家则如一丘一壑之胜地,其山水风景,未始不佳……特气象规模,不过十里五里之局,非能有千百里之大观……然其结撰之奇、林泉之丽,尽可擅一方名胜,故亦能自立,成就家数也。[15](P2241)
上述评价分别以大海、昆仑山,五岳五湖,长江、匡庐山、一丘一壑指代大家、大名家、名家、小家的特征,给人一种等级森严的印象,这就使我们对艺术造诣不同的诗人有了更清晰的把握和体认。
概而言之,朱庭珍不仅以意象为喻,阐释诗歌创作规律,还将之推广到文体、功能、鉴赏批评、理论表述等多个层面,可说是将整个诗学体系“具象化”了,使其解说呈现出摇曳生姿、诗意盎然的语言面貌,增强了诗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对于读者来说,格外容易接受理解,也便于运用。再者,其中的譬喻大多具有深切著明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含义模糊、表述不确的局限,强化了诗论的批评效力。汇而观之,《筱园诗话》对象喻式表达的运用,极具示范性,可视为以意象为喻,阐释诗学问题的一个绝妙文本。
二
除了将象喻式表达系统运用于诗学阐释外,《筱园诗话》还对一些旧有譬喻进行了精辟的阐发,发掘出新颖的隐喻内涵,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象喻性言说的发展。下面以“哪吒之拆肉还母,拆骨还父,另由莲花化身”“火色俱纯,金丹始就”“鱼龙百变”“急脉缓受”等清新奇特的意象为例,对其运用中的新变之处做更进一步的分析。
(一)“哪吒化身”:禅宗故事的诗学引申
“作乐府须音节古,词意古,神味气骨无一不古,方许问鼎。……必也能如哪吒之拆肉还母,拆骨还父,另由莲花化身,始是真正法身,非色身也。”[15](P2257-2258)据现存史料,哪吒割肉析骨之事最早见于《景德传灯录》,天台山德韶国师上堂说法时,有僧人问道:“哪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后于莲华上为父母说法,未审如何是太子身?”[22](P1943)《五灯会元》有类似的说法:“哪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后现本身,运大神力,为父母说法。”[23](P116)从上可知,哪吒割肉析骨后,身份转变,“运大神力”,所以能坐于莲花上为父母说法,但并没有莲花化身的情节,此事在明代《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才出现:“世尊亦以其能降魔故,遂折荷菱为骨,藕为肉,丝为筋,叶为衣,而生之。授以法轮密旨……遂能大能小,透河入海……而帅之灵通广大,变化无穷。”[24](P330-331)详细描绘了世尊如何运用荷花,借物还魂,将哪吒化身为一个神通广大的尊神。对于“析骨还父,析肉还母”之说,善卿《祖庭事苑》谓:“然于乘教无文,不知何依而为此言,愚未之知也。”[25](P174)由于目前没有明晰的文字说明,只能进行推测,即割肉析骨之事应该是宋代禅宗演译而来,是苦行、舍生等修行观念影响下的产物。《大庄严论经》说:“此身不清净,九孔恒流汗,臭秽甚可恶,乃是众苦器。”[26](P324)《四分律》记载了割肉布施的故事:“生食其肉、饮其血,乃得行十善……即取利刀自割股肉、以器盛血,授与彼人。”[27](P951)可见,身体是修行的羁绊,唯有抛却这一外壳,才能得证果业。理清了这一点,我们讨论的重点便可以落实到哪吒故事与诗歌的关联性上。
目前所见最早明确以哪吒类比诗歌的,是南宋的严羽。他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说“吾论诗,若哪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即是从哪吒舍生表现出的勇猛无畏来取喻的,以之标榜自己敢于“明目张胆而言”,追求“沉着痛快,显然易见”的效果。[8](P234-236)相形之下,朱庭珍以哪吒为喻解说乐府创作,除了着眼于这一故事包含了“舍弃”的意味,与诗家讲求的打破成规相吻合,他更侧重从哪吒由莲花化身后的结果“现本身,运大神力”立喻,以此彰显诗歌创作中的主体才能。根据传统看法,乐府之工在于音调节奏须用古人遗法,有依咏和声之遗意,辞须古穆精奇,但若一味模仿,则与自身无涉,在得古人声律、意境之后,要能自寓怀抱,出以新意,方可“见真正法身”。这与前文对苏轼的表彰是一致的,是以人力求变化的体现。
(二)“金丹始就”:道教炼丹术的诗学化用
“五古以神骨气味为主,愈古淡则愈高浑,火色俱纯,金丹始就,故不可染盛唐以后习径,戒其杂也。”[15](P2209)“火色俱纯,金丹始就”,源诸道教的金丹术,被视为得道成仙的主要途径。对此,不妨挪借刘一明《象言破疑》里的一段话作为注解:“金者,坚刚永久不坏之物;丹者,圆满光净无亏之物。古仙借金丹之名,以喻本来圆明真灵之性也。此性在儒则名太极,在释则名圆觉,在道则名金丹。名虽分三,其实一物。儒修之则为圣,释修之则为佛,道修之则为仙。”[28](P539)这段话揭示了金丹的象征意义,而以之比况诗歌,至迟不晚于北宋。据张振谦的研究,这种譬喻方式可以称为以仙道论诗,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在于道教内丹学在宋代的风行,受此浸染,当时的文人将金丹术纳入诗学阐释的场域。[29](P292-295)黄庭坚的说法可能是最早的用例,他在《与洪甥驹父》中说:
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30](P1905)
这里的“灵丹一粒”即是道教内丹修炼术的常用术语,用来指称诗人的主观思想和精神修养。[29](P297)此后,以金丹论诗的方式受到宋代文人的认同,陈与义说“陈无己诗如养成内丹”,[31](P52)白玉蟾言“学诗有似学仙难,炼句难于学炼丹”(《赠诗仙》),均以金丹修炼的长久与艰苦来说明作诗的艰辛。[29](P301)与前述用法不同,朱庭珍是以纯粹的火候指代诗歌的取法典范,其比附基于炼丹与作诗“戒杂”的共同趋向,以此阐明五言古诗的创作若想达到古淡、高浑的境界,就需要效法阮籍、陶渊明、谢灵运等名家,而不能掺杂盛唐以后的习气。
(三)“鱼龙百变”:大型杂剧的诗学推衍
“大家如海,波浪接天,汪洋万状,鱼龙百变,风雨分飞。”[15](P2241)其中“鱼龙百变”的历史渊源最早可追溯至汉代的“角抵”之戏。《史记·大宛列传》有如下记录:“汉使还,而后(安息)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32](P3173)由于西域眩人幻术的传播,[33](P215-224)最终形成了鱼龙曼延——这一融合幻术、杂技、马戏、歌舞、逗引等不同元素于一身的大型表演艺术,[34]《汉书·西域传赞》说,“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曼延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35](P3928)张衡《西京赋》对该表演角色众多、规模庞大、情节复杂、变化百出的特点有过最为细致的描述:
巨兽百寻,是为曼延。……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辚囷。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蝹蝹。……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36](P76-77)
另外,《隋书·音乐志》也描述了这一表演在北周、北齐、隋代的延续和繁盛。[37](P342-381)庾信留仕北周时,应当看过这一表演,并最早以之称道宇文逌行文富于变化的特征,《谢滕王集序启》有云“譬其毫翰,则风雨争飞;论其文采,则鱼龙百变”。[38](P554)从表面来看,朱庭珍很可能化用了庾信的说法,但取喻的角度及其意旨大不相同,前者是从鱼龙百变的整体特征出发,以其千变万化的形式和广博的内容概括大家的创作风格,后者则仅仅着眼于变化一端,来形容文采。根据英国诗人奥登对大诗人的定义,[39](P44-45)这一比照可谓极其贴切。
(四)“急脉缓受”:堪舆术语的诗学移用
这些新奇的意象超越了人身、自然、器物等传统象喻在言说和把握事物时的局限,具有独特的有效性和解释力,为我们提供了新颖的诗歌观照方式,缓解了读者的审美疲劳,令人耳目一新。
三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能够确定朱庭珍是有意识地以象喻性的言说方式,对传统诗学及其历史进行总结及思考,以此架构起独立的、极富个人印记的诗学论述,可以说他的这种表述策略相当成功。如果这一结论可以成立,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朱庭珍为什么要采用象喻性的言说方式来表达他对诗歌的理解?哪些因素影响了《筱园诗话》象喻式话语实践的形成呢?对此,或许可以借鉴异域的眼光进行考索。本维尼斯特认为:“话语必须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任何一种表达都假定了一个说话人和一个听者,在说话人身上存在一种以某种方式来影响他人的意图。”[45](P208-209)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话语所做的事要比使用符号来标明事物多得多。我们必须揭示和描述的正是这‘多出来的东西’。”[46](P54)依照他的看法,话语研究就是要发掘这些多出来的东西,即是把话语“还原到现实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去,就是要追索那些使话语实践所以 可能的社会历史规则”。[47]基于上述考量,可以从作者意图和历史情境两个角度,来发掘这一话语实践的形成原因。
(一)指示初学
朱庭珍自序有言:“郡中同人偕及门二三子,日载酒过从,争问诗法于予。愧无以副诸君厚意,乃以笔代口,述予见闻所及,为诗话四卷付之。”[15](P2201)由此看来,《筱园诗话》乃是因当地学诗之人“争问诗法”而作,显示出指引做诗门径的宗旨。这一点在施有奎《穆清堂诗钞·序》中有更为详实的说明:“语诗者无智愚,皆取正筱园,筱园亦孜孜不倦,接引恒如不及……留昆华为久,问途者日以众……筱园结社以进同人,后生小子有蒸蒸日上者。”[48](P412)职是之故,如何以有效的方式传达自己的诗学经验,让诗歌初学者能够熟悉具体的创作技法,就成为朱庭珍面临的重要问题。
对于这个难题,他的前辈诗人有过深刻的体会,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说:“文之难,而诗之难更尤。”[49](P24)叶燮在《原诗》中说:“我今与子以诗言诗,子固未能知也。”[10](P94)在感慨言诗之难后,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象喻性的言说方式。司空图说:“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49](P24)叶燮谓:“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晓然矣。”[10](P94)章学诚的表达最为直白,他在《古文十弊》中陈述时文法度的学习时指出:“塾师讲授《四书》文义,谓之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拟于房室,则有所谓间架结构;拟于身体,则有所谓眉目筋节;拟于绘画,则有所谓点睛添毫;拟于形家,则有所谓来龙结穴。随时取譬,然为初学示法,亦自不得不然,无庸责也。”[50](P589-590)明确提出“随时取譬”是为初学示法的需要,自有其存在价值,惜乎未连及诗歌学习,但古代诗文有相通之处,连类而推,结论还是显然的。由上可见,象喻性的言说方式乃是传达文学经验的方便法门,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故而,被朱庭珍系统地运用于诗学问题的阐释,以接引后学。
(二)历史情境的规约
对于《筱园诗话》,蒋寅认为“所述无甚创见”,[51](P596)这一判断从诗学理论创新而言有说服力,因为从朱庭珍所阐述的诗学概念、命题来看,如“无定法而有定法”“变”“积理养气”“识为尤先”“诗以超妙为贵”“诗中有我”,前人都已讨论过,观其文本表述,大多是对旧有诗论进行充实、深描,让诗学论述趋向精微细密,其价值诚如蒋氏所言,“综合古今之长,深化传统命题,集前人诗论大成之气象”。[51](P596)此外,从当地诗坛的评价中也可部分印证朱氏在诗学发明上的欠缺。袁嘉谷《卧雪诗话》说:“言定法,言无定法,妙有神悟。笔虽常语,识出阮亭、随园上。”[52](P343)由云龙《定庵诗话续编》云:“朱筱园先生诗话,宗旨正大,尤以《论诗绝句》五十首,为其特识。”[53](P620)以上诸家从识力、宗旨等角度赞许了《筱园诗话》,但对其理论创新则没有提及,倒是指出了“常语”的一面,即所论乃老生常谈,人所共知。
结合传统诗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知道这种情形实在无须苛责:“中国古代诗学的理论框架到明代已告完成。”[54](P19-20)“自从王渔洋以神韵解决了美学理想层面的问题,神韵论就成为古典诗学最后一个有体系的学说,此后再无建立新理论体系的可能。”[55]朱庭珍对此很清楚,既然在“质”的层面,即诗歌理论上不能“成一家之言”,不如从“文”的立场,即言说方式上设想出新的可能性,以之为更新诗学话语,寻求新鲜表达效果的路径。他没有直接说出这一意图,但从《筱园诗话》对旧有譬喻的新颖阐发上,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考察一个文本时,我们不应该只注意文本说了些什么,而且还要留意文本没有说出的东西,以及它含沙射影地暗示的东西”。[56](P52)笔者认为朱庭珍“没有说出的、暗示的东西”,即是以象喻性的言说方式建构个人的诗学话语,是在“影响的焦虑”下做出的抉择。
余 论
《筱园诗话》中的一些新奇意象含蕴了独特的审美观和精到的诗学见解,凸显了朱庭珍的言说智慧和所达到的认识高度,其中隐含的知识背景,关涉着动态的观念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朱氏的话语方式。通过考察诗话中的意象类型及其阐释功能,进而从知识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发掘象喻式话语的生成过程和认知逻辑。由此,学界能够从“说什么”和“怎么说”两种视域,更全面地把握这种古老的审美方式,这对于实现“在中国发现批评史”的学术理念是有所助益的。
注释:
[1]李建中.中国文论:说什么与怎么说[J].长江学术,2006(1).
[2]参见杨开达.《筱园诗话》述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2);陈良运.论《筱园诗话》的诗学价值[J].思想战线,2003(3);司保峰.朱庭珍诗学理论研究[D].复旦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何世剑.朱庭珍《筱园诗话》之“诗法”说[J].南昌大学学报,2004(1);张同娟.朱庭珍诗学思想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3]李瑞豪.《筱园诗话》对清代诗坛之研究[J].贵州文史丛刊,2012(3).
[4]何世剑.朱庭珍“杜诗学”综论[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论朱庭珍对严羽诗学的接受[J].中国韵文学刊,2008(1);赵江薇.朱庭珍诗学对中原诗学的吸收与发展[D].云南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
[5]张伯伟称为意象批评法。参见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6]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7]叶嘉莹.钟嵘《诗品》评诗之理论标准及其实践[C]//.叶嘉莹.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8](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9](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C]//.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清)叶燮著,蒋寅笺注.原诗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1]方汉文.当代诗学话语中的中国诗学理论体系——兼及中国诗学的印象式批评之说[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12]按:这里的意象是就文学理论批评而言的,是一种“批评意象”,不同于文学创作中的意象。参见高文强.“批评意象”刍议[C]//.戚良德主编.中国文论(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3]比如同样以诗评为主的《沧浪诗话》《谈艺录》,它们所使用的意象都没有《筱园诗话》丰富,前者涉及佛禅、器物、典故、兵法、音乐、人物、书法;后者涉及典故、器物、绘画、音乐、织布、文体。参见(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明)徐祯卿撰,龚宗杰点校.谈艺录[C]//.陈广宏、侯荣川编校.明人诗话要籍汇编(第6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14](宋)范温.潜溪诗眼[C]//.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清)朱庭珍.筱园诗话[C]//.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6](宋)俞文豹.吹剑续录[C]//.朱易安,傅璇琮,周常林主编.全宋笔记(第7编,第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
[17](唐)段安节.乐府杂录[C]//.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明)王世贞撰,魏宏达点校.艺苑卮言[C]//.陈广宏、侯荣川编校.明人诗话要籍汇编(第6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19](清)黄景仁著,李国章标点.两当轩集·附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0]叶晔.论袁枚的“以棋喻诗”说及其源流[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
[21]按:陈良运认为这一品评“审美描述与理性判断并行,大有助于对历代诗人创作实绩作较为准确的判别”,参见陈良运.论《筱园诗话》的诗学价值[J].思想战线,2003(3);蒋寅指出朱庭珍的品第“用意象化的语言形容过其间的差别,……争奈意象化的类比终究弹性很大,读者的理解会有很大不同”,在此后的研究中,作者又将朱庭珍的表述与英国诗人奥登对大诗人的定义进行了比较,认为其优点是“一目了然且给人深刻印象”,参见蒋寅.家数·名家·大家——有关古代诗歌品第的一个考察[J].东华汉学,2012(15);在中国发现批评史——清代诗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传统的再认识[J].文艺研究,2017(10);汪涌豪将家数视为诗学范畴,剖析了它在文学批评中的具体应用,参见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可并为参看。
[22](宋)道原著,顾宏义译注.景德传灯录译注·卷二五[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23](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4](明)阙名.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5](宋)善卿编正.祖庭事苑·卷六[C]//.新编卍续藏经·禅宗著述部(第11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26](后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卷十二[C]//.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缘部(第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27](后秦)罽宾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五二[C]//.大正新修大藏经·律部(第2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28](清)刘一明著,腾胜军、张胜珍点校.悟元汇宗[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29]张振谦.道教文化与宋代诗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0](宋)黄庭坚著,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续集卷一[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31](宋)方勺.泊宅篇·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2](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二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3]按:常任侠引用大量材料论证鱼龙曼延是本土杂技结合西域幻术推陈出新的产物,参见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34]按:黎国韬通过细心论证,认为“鱼龙”“曼延”是两种不同的表演形式,并将“鱼龙幻化”界定为中国古代早期的戏剧之一,参见黎国韬.“鱼龙幻化”新考及其戏剧史意义发微[J].文学遗产,2017(4).
[3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6](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7](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一四、一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8](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9]英国诗人奥登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序言中指出:“一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则下列五个条件之中,必须具备三个半左右才行。”其一,他必须多产;其二,他的诗在题材和处理手法上,必须范围广阔;其三,他在洞察人生和提炼风格上,必须显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其四,在诗体的技巧上,他必须是一个行家;其五,就一切诗人而言,我们分得出他们的早期作品和成熟之作,可是就大诗人而言,成熟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老死。”转自余光中.大诗人的条件[C]//.余光中.余光中谈诗歌.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
[40]杨志平.论堪舆理论对古代小说技法论之影响[J].海南大学学报,2009(6).
[41]陈才训.文章学视野下的明清小说评点[J].求是学刊,2010(2).
[42](清)薛雪.一瓢诗话[C]//.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43]龚宗杰.古代堪舆术与明清文学批评[J].文学遗产,2019(6).
[44]参见吴承学.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的批评[J].文学评论,1994(1);古风.以锦喻文与中国文学审美批评[J].中国社会科学,2009(1);闫月珍.器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文心雕龙》为中心[J].中国社会科学,2013(6);冯晓玲.自然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J].文艺理论研究,2019(3).
[45]Emile Benveniste,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M].Coral Gables FL: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1.
[46]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trans. A. M. Sheridan Smith,London:Routledge,1989.
[47]周宪.文学理论:从语言到话语[J].文艺研究,2008(11).
[48]张国庆选编.云南古代诗文论著辑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9](唐)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50](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2014.
[51]蒋寅.清诗话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2](民国)袁嘉谷撰,沈蘅仲、王淑均校点.卧雪诗话·卷三[C]//.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53](民国)由云龙撰,沈蘅仲、王淑均校点.定庵诗话续编·卷上[C]//.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54]蒋寅.清代诗学史(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55]蒋寅.肌理:翁方纲的批评话语及其实践[J].文学遗产,2019(1).
[56][美]波林·罗斯诺(Pauline Marie Rosenau)著,张国清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