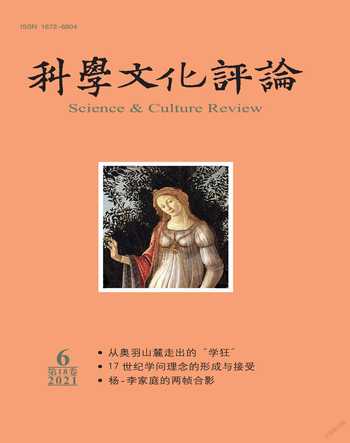追寻自然哲学家的足迹评《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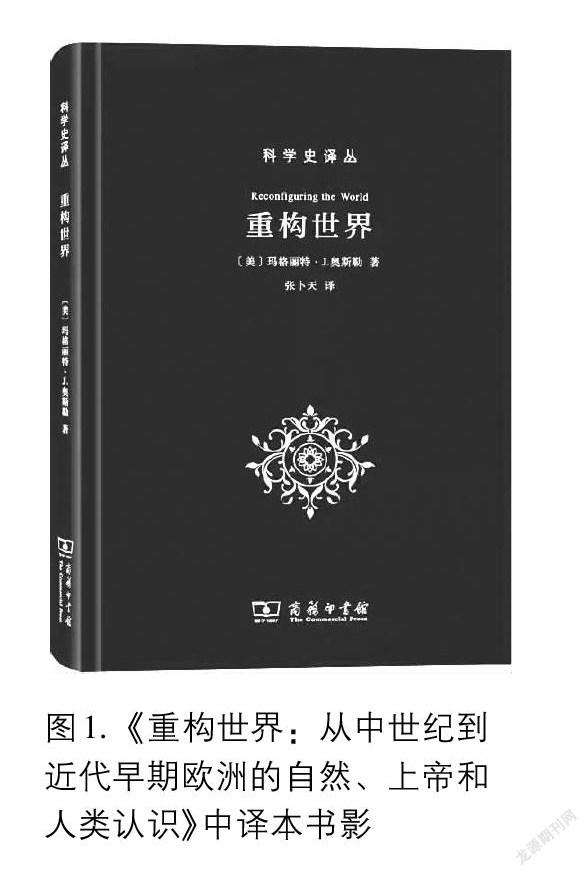
(美)玛格丽特·奥斯勒著,《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239页,定价48.00 元。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21-07-30
作者简介:葛业静,安徽宿州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史、科学技术与社会。Email: geyejing@mail.ustc.edu.cn。
近代科学的起源、自然观与世界观的转变一直是西方科学史关切的要点。“科学革命”这一概念的创造无疑为思考该命题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工具。按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观点,科学革命的根源和成果是近代科学,而意识的世俗化、现代人的主体主义、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转变等只是“一个更为深刻和基本的过程的伴随物和表现”([1],页2)。迪昂(Pierre Duhem)则认为“近代科学战胜了中世纪哲学及其顽固的鹦鹉学舌”是由一系列细小却从未间断的进步积累而成([2],页58)。由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科学革命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莫衷一是,即使“科学革命”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为其确定符合历史事实的起止时间依然面临困境。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对赫尔墨斯主义知识传统的研究,使大受冷遇的西方神秘学重新被审视。玛格丽特·奥斯勒(Margaret J. Osler)的《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图1)则延续了该传统,采用独特视角来揭示近代科学的历史根源。
该书立足于科学史,大胆地跨越科学、宗教、哲学和观念思想史,探讨赫尔墨斯主义、占星学、炼金术等神秘主义传统,以及博物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等旧时流行文化,旨在丰富近代早期科学史的整体演进图景。“以往这些思维模式要么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要么被丢进了非理性的垃圾箱”([2],页222),传统科学史观中的“阻碍因素”是时候应该重新考量了。然而,正如该书的标题和副标题有意识地缺席“科学”二字那样,奥斯勒对是否存在科学革命的判断非常审慎。她秉持的认知是:只有寻找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对自然和物质世界的认识和回答,才能够“试图理解这个异国他乡的居民的语言和习俗”([3],页3)。
一 全书结构和研究内容
本书从近代早期欧洲精神生活的传统——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不稳定的联姻切入,尤其关注1500—1700年之间被现代科学排除在外的重要自然哲学论题。
第一章通过“学科界限”“大翻译运动”“占星学”“天文学”“炼金术”“博物学”和“医学”等关键词清晰地勾勒出下文重要线索。奥斯勒是明确的反辉格。以占星为例,作者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的许多思想家反对占星学而看不到它为天文学的基础研究所提供的强大动力”([3],页22)。基于奥斯勒对占星学和天文学关系的密切关注,格雷戈里·古德(Gregory A. Good)甚至认为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托马斯·库恩撰写著名的《哥白尼革命》(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以来,史学界的最大变化之一”[4]。
在第二章里,奥斯勒并未先验地将为人所熟知的“和谐整体宇宙的解体和宇宙的无限化”([1],页2)当成变革主线。她首先考察人文主义在拯救文本破坏和恢复古典著作的重要作用,进而唤醒人们对医学等学科的兴趣。在寻找神学和宗教与自然认识之间的正面关系中,又明确了宗教改革对科学史的深远影响。尽管哥白尼日心说被放至最后,但从托勒密地心说到新天文学日心说的故事仍然足够引起注意。去中心化的描述风格,进一步支持其观点——“每一种发展都有助于瓦解已经统治了两千年的世界观”([3],页76)。
第三章的描述随着数理天文学的继续推进,尤其是望远镜的引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和宇宙论面临深入侵蚀。或许是同行对此段历史颇为熟悉,作者并未着墨太多,转而重点讨论对《圣经》的解释问题。例如,在与天主教会的斡旋中,伽利略采取一些明智而又不得已的临时性策略——“把理论处理成假说就可以再次自由地讨论哥白尼主义”([3],页89)。本章继续将天文发展与占星变革结合考虑:“重新强调观测不仅成为评价天文学理论的标准,而且也称为评价解经方法和传统占星学说法的标准。”([3],页97)
第四章对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的哲学研究充分体现作者的学术兴趣。奥斯勒放弃使用流行的机械论哲学来解释自然哲学,综合考虑机械论哲学家与宗教和神学的关系,这与韦斯特福尔(Richard S. Westfall)的偏好有所不同。事实上,历史上的每一行为、情节和观念背后都蕴藏着争论和冲突,这“为17世纪自然哲学多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概念框架”([3],页118)。
第五章阐述了“移动边界”“混合数学”的有关内容,这足以吸引读者。运动科学和视觉科学这两个边缘性的“混合数学”分支,逐渐撼动了亚里士多德科学分类和中世纪的学科结构。尤其是在伽利略、笛卡儿、惠更斯和牛顿等自然哲学家笔下,运动和物质的概念被转化,严格的数学推理被内化于物理学和机械论哲学。力学和光学的向前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学科界限,数学物理学这一门新学科从这一过程中产生,亚里士多德体系由此逐渐废弃。
第六章阐明了18世纪之前化学和炼金术二者的模糊界限。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及其追随者的化学论哲学及其应用,尝试取代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盖伦等传统权威。波义耳是机械论哲学的信奉者,“一切化学过程,包括金属的炼金术转化,都可以用机械术语来理解”[5]。但事实证明,波义耳将化学纳入机械论哲学的雄心未能达成,反而是“传统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所说的要素对于推进化学知识特别是理解燃烧更有用处”([3],页166)。
第七章回归生命主题。近代早期生命研究因其交叉性质消解着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并部分瓦解了机械论哲学。在19世纪“生物学”一词出现之前,自然哲学家广泛通过恢复古代本文、观察实验、田野调查甚至追溯医学和神学的关系去研究生命。遗憾的是,这些活動“并没有在单一的学科标题下统一起来”([3],页185)。本章即展示神学如何与博物学、医学、药学、解剖以及传统生理学复杂交织。
第八章的主题是“牛顿与上帝”。奥斯勒称,“17世纪自然哲学、数学和天文学的许多发展在牛顿的工作中达到了顶峰”([3],页186)。牛顿“为哥白尼时代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其著作“也代表着学科界限的重大转变”([3],页186)。有趣的是,牛顿追溯古代传统佐证其工作的合法性,认为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已经预示了他对自然的数学化,并确信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败坏了古代的见解”([3],页209)。
“尾声”呼应“引言”。正如奥斯勒强调,“不是要追溯过去以寻找现代科学的起源”,也“不是要发现自己所关注的事物在过去得到了哪些扭曲反映”([3],页3)。关于是否发生了科学革命,一个可能答案是:思想抑或社会的变化“尚不等同于近代科学的出现”,那种被称为“科学革命”或“近代科学的兴起”的历史现象仍然要到将来才能出现([3],页213)。
二 科学编史学思想及方法
1. 自然哲学和科学的语境论阐释
奥斯勒倾向淡化甚至刻意避免提及“科学革命”的概念假设。她认为历史的书写和建构并不只是对过去自然哲学家观点和文本的随意采撷,否则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当代辩论。在科学革命问题簇的研究中,当代学者与17世纪自然哲学家相比显然更倾向于反映现实关切而忽视历史的语境。希腊思想在拉丁西方所处的语境与古代思想家最初提出他们的语境有所不同,况今日乎。至于什么是语境,奥斯勒称“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语境就是文本本身”([6],p. 212)。
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哲学家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若干替代品之中选定了通过物质和运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机械论哲学。伽桑狄发现在近代早期复兴的伊壁鸠鲁主义恰能成为他的唯意志论神学和机械论哲学的辩护工具,终生致力于对伊壁鸠鲁原子论的修正,使之与基督教神学相容。在原始物理语境中,奥斯勒展示伽桑狄是如何一步步通过对原子和虚空、运动和变化的观察与实验、思考与探索来制定一种新的概念框架。奥斯勒声称,“对伽森狄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全面介绍,包括对他所引用的许多资料来源的详细分析,将取代目前存在的支离破碎的、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和不合时宜的研究”([6],p. 226)。与伽桑狄切入哲学问题的方式不同,笛卡儿试图从他认为自明和确定的某些原理推出其哲学。
语境主义同样彰显在探讨牛顿、上帝和万有引力这一有趣话题之时。牛顿对数学和物理学的兴趣可以通过《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光学》(Opticks)等著作反映出来,但他试图调和神学与自然哲学的努力却经常被忽视。牛顿手稿中有至少100万字的炼金术内容,“可能有助于牛顿为物体常规的机械论属性补充了吸引力和排斥力”([3],页200);250多万字的神学主题,“使他更加关切如何引入和解释吸引力和排斥力”([3],页202)。很显然,“在不同的语境下,观察、实验和数学在寻求自然认识方面各自扮演着新的角色”([3],页211)。这种语境论阐释,凸显出历史话语的特殊性,增进了对当时自然哲学家所扮演角色之理解。
2. 非本质主义与反辉格解释
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目前关于科学和宗教以及“科学革命”的认知与创新。奥斯勒对本质主义的反思从未间断,她认为假定的“科学”与“宗教”的本质主义解释不能充分反映历史语境中显而易见的流动性和可渗透的边界[7]。她反复强调“历史上的过去是异国他乡”([3],页3),而她的任务则是尝试理解其文化。按照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思想,自然和机械、物理学和力学主题之间泾渭分明。因此使用传统分类标准实质上是维护了本质主义观念。16世纪末,僵化的本质思维被打破,新的运动概念出现,构成“一种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和宇宙论的根本拒斥”([3],页126),旧有区分方式和亚里士多德宇宙渐趋模糊直至完全消除。在论述近代早期的化学时,两位重要的化学家——范·赫尔蒙特(Van Helmont)和波义耳均受到神秘学的影响。范·赫尔蒙特深受帕拉塞尔苏斯的影响,但这没能阻挡他的化学成就,其理论和实验工作皆超越了前人。奥斯勒提出一个新论点,即,许多评注者和化学教科书作者宣称波义耳是“近代化学之父”是错误的。论据来自波义耳自己写下的话。而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波义耳远非把他的化学建立在一种近代元素概念的基础之上,而是质疑是否有这样的东西存在。”([3],页163)的确,从自然哲学家的视角理解科学,避免陷入本质主义的窠臼,也尽可能地排除科学史研究的辉格色彩。
3. 寬泛的历史主义方法
奥斯勒反对历史的先验设置,把历史看作是在历史语境中而不是当下语境中被理解的事件。本书以历史行动者——自然哲学家的视角,叙述着关于自然界的古老观点如何被取代,并从他们的视角来概括不同类型的主体之间有保留的或绝对的支持或反对。还是以精彩的占星辩驳为例:在神学领域,从圣奥古斯丁开始的基督教神学家谴责占星;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逐渐接受;后来的新教改革者则对此看法不一。在哲学领域,皮科等人不断对占星学发起攻击,占星捍卫者乔万尼·蓬塔诺(Giovanni Pontano)等不得不引经据典予以回应。在自然哲学领域,近代早期的大多数天文学家们使用占星“往往是为了满足其赞助人对历书、出生和预言的要求”;到17世纪末,占星已经风光不再,自然哲学家“也没有表示出太多兴趣”([3],页95)。不仅仅是占星话题,混合数学、炼金术、博物学、宇宙图景的机械化、自然哲学的数学化等均采用了宽泛的历史主义方法。从历史的主体来寻求自然认识变化的原因,通过他们的回答得出结论,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
三 学术价值与研究特点
一是打通传统学科边界,提出看待“科学革命”问题的新观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神学与自然哲学的深刻联系是现在无法想象的。“科学”一词被自然哲学家用以描述个别学科,由此产生“没有一种刻画把握住了所有这些学科共同的性质”这一困境([3],页211)。如果无法突破传统学科分类的桎梏,仍局限在现代性的“科学”这一隅,那便会遗漏许多与科学兴起有所贡献的因素。事实上,非科学因素为科学提供的动力远超乎想象。例如,理解赫尔墨斯宇宙论的关键——天地之间的对应——“从而获得关于特定对应的知识”([3],页43);地理大发现和域外探险推动着实用数学、医学和博物学的发展;开普勒的天文学模型不仅“解释了行星的次序”,还“把轨道比例与音乐和声和占星学联系了起来”([3],页69),这种洞见造就了《宇宙的奥秘》(Mysterium Cosmographicum)。奥斯勒没有陷入怀疑主义的误区,既肯定与近代科学相伴而生的其他问题,也承认哥白尼天文学的深远影响,认为日心说质疑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和物质理论及其形而上学支撑,“使一种新物理学和新自然哲学变得更加必要”([3],页76)。开普勒充分理解哥白尼的初衷,抛弃匀速圆周运动的理想假设完美地解决困扰已久的行星问题,“从而使天文学与物理学之间的学科关系发生了彻底改变”([3],页71)。奥斯勒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一种着眼于过去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为科学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3],页76)。以辉格史观解释近代科学兴起的图景其结果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基于这种解释,奥斯勒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还没有出现。
二是研究視角独特,以历史行动者的视角全面审视自然哲学家的作品、问题、观点及目标。奥斯勒始终认为“当时有教养的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与现代科学认识世界的方式非常不同”([3],页1),因此拒绝先验的“科学革命”假定。拂去被忽视的历史陈迹,采用行动者的第一视角,力图揭示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自然、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复杂关联。避开传统的“科学革命”主题然后审视自然哲学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一切皆有问题、一切皆无定论”[4]。亚里士多德哲学、运动、物质与力等关键概念作为不同时期的隐喻,为解释自然现象提供当时“最合理的”框架。显然,按照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语境,“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类标题是矛盾的。奥斯勒认为这不是为了表达矛盾,“而是大胆地表明了在过去150年间学科界限发生的变化”([3],页194—195)。
三是重新考察对比原始材料,叙事目标由解释“已知”到追求“未知”。奥斯勒的对原始材料的处理游刃有余,不再执着于怎样解释相关史料,而是还原式地剖玄析微,以期洞彻其科学产生之根源。其哲学背景和研究专长使得本书叙事在历史复杂性和史实证据性的张力之间实现了巧妙的平衡。奥斯勒对自然哲学和神学进行了更为均势的处理,还包括神秘学、博物学和医学等,力图达到重要的主题和情节无有遗漏。奥斯勒清楚地知道潜在的读者群以及应该向读者传达的科学起源的观点是什么,这极为难能可贵。读罢此书后会对科学起源问题有更好的理解。
本书也有一些不足,首先,奥斯勒显然受到“科学革命”怀疑论的影响,但却没有充分展示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从这一出发点的历史记叙方式与其他书籍并未有明显不同([2],页658)。其次,对长时段历史的概括和描摹,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碎片化特征。面面俱到的做法易使部分读者认为缺乏主轴和难以抓住重点。对宏大叙事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细节深度。
瑕不掩瑜,本书“对相当复杂的问题和情节进行了精美的压缩总结,而且没有牺牲可理解性,也没有明显失真”[8]。对科学起源的追问还在继续,通过追寻自然哲学家的足迹,奥斯勒在史学层面为科学起源的探索与创新提供了绝佳的元素和视角。其所采取诉诸于历史的方案和综合式处理方式,使两百年科学史图景变得更加清晰,也为进一步思考科学革命问题提供了有益补充。
参考文献
[1] 亚历山大·柯瓦雷. 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M]. 张卜天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2] 弗洛里斯·科恩. 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M]. 张卜天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3] 玛格丽特·J·奥斯勒. 重构世界: 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M]. 张卜天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4] Good, G. A.. Book Review, Reconfiguring the World: Nature, God, and Human Understanding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Early Modern Europe[J]. Physics in Perspective, 2012, 14(2): 253.
[5] Lunteren, F.. Clocks to Computers: A Machine-Based “Big Picture”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J]. Isis, 2016, 107(4): 767.
[6] Osler, M. J.. The Search for the Historical Gassendi[J].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2011, 19(2).
[7] Osler, M. J.. Mixing Metaphors: Science and Religion or Natural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in Early Modern Europe[J]. History of Science, 1998, 36(1): 107.
[8] Harrison, P.. Book Review, Reconfiguring the World: Nature, God, and Human Understanding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Early Modern Europe [J]. Isis, 2011, 102(4): 749—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