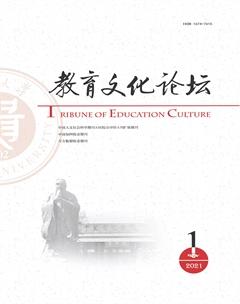印度教岩凿神庙建筑特征分析
摘 要:在印度教神庙建筑史上,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是里程碑式的一组石窟建筑。多石的自然环境是开凿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的客观条件,其营造者和开凿年代未有定论,建筑史家和艺术史家的意见始终徘徊在康坎孔雀王朝和卡拉丘里王朝之间。所有雕刻都是以大神湿婆的家族成员为主题,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第一窟因此被稱为“湿婆之家”。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第一窟的主要建筑特点是十字形平面,整体构造分为主窟、庭院、翼窟三个部分,三个窟口,深受佛教石窟的影响。
关键词:象岛石窟;印度教;岩凿神庙建筑
中图分类号:B9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1-0104-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1.016
在印度教神庙建筑史上,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组石窟建筑,其间所表现出的建筑技术、建筑模式、造型艺术(雕刻、雕塑)等,无论就学术意义还是就艺术价值而言,都无一例外地体现出了令人心悦诚服的成就。无名的能工巧匠因势利导,在绵亘陡峭、坚硬无比的石壁之上,以极为简陋的工具却施展出了无比娴熟的精湛技术和工艺,开凿洞窟,雕琢石柱,雕刻神像,历经数载,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程,造就了印度教艺术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大宗精华之作。
象岛石窟的建筑与艺术源自宗教实践活动,它对于虔诚的印度新教徒的生命成长和精神养成至关重要,曾经颇受孟买一带的印度教徒顶礼膜拜,偶受王公大臣巡行礼拜。然而,自18世纪至1947年印度共和国成立前,在印度这个素有“宗教博物馆”美称的国度,却鲜有本土学者关注并且对之进行深入研究:第一个原因在于象岛石窟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在航海技术尚未普及的时代里,越过波涛汹涌的印度洋,对于财力物力不足的普通信徒实则是一项近乎难以完成的使命;第二个原因便是象岛石窟中的5座印度教岩凿神庙,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唯一的铭文也不知去向;第三个原因在于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后,地处印度洋上的象岛先后被葡萄牙人和英国人所占据,阻拦了教徒和学人们进入象岛石窟。我国学术界对象岛石窟的关注度不高,力作少见,只有以王镛为代表的少数学者从艺术学的视角对之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与阐述[1]325-333,从印度教岩凿神庙史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的论著更是少之又少。
鉴于上述缘由,本文力图以文献和实物互相印证,辅之以2016年11月田野考察期间所采集的数据和日志进行佐证,管窥象岛石窟中所表现的印度教神庙建筑的特征,以及阐明其对于日后达罗毗荼式神庙建筑的深远影响。
一、象岛名称的由来
与中国历代修史风气盛行不衰不同,印度历来便是一个缺乏记载历史传统的国度,加之信徒们向来把神庙视为神祇借助人力所为的建筑,使得包括象岛石窟在内的众多印度教岩凿神庙没有留下精确的建造日期,就连营造者究竟为何人这一至关重要的细节,往往也成为后世研究者们极为棘手的一个学术难题。探究象岛名称的由来及其寓意,看似微不足道的考证功夫,实则意义极大,且涉及了语言、历史、宗教、建筑、古代印度洋贸易等学科知识,对厘清马哈拉施特拉邦印度教岩凿神庙建筑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可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学术问题。
在孟买附近的当地语言中,阿拉伯海中由两座山组成的这座岛屿被称为珈拉普里(Gharapuri),意为“石窟之城”。艾力卡·查克拉瓦蒂(Ilika Chakravarty)认为,珈拉普里一词系由古语阿格拉哈普里(Agrahapuri)和斯里普里(Sripuri)逐渐演变而来,二者的含义分别为“城堡之城”和“财富之城”[2]16。通过对上述三个词汇含义的解读,不难看出,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下,象岛曾经是集石窟、城堡、财富于一身的繁华之地,在一度繁荣的印度洋商业往来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事实上,印度境内的诸多石窟建筑都与商贸往来关系密切,著名的佛教石窟阿旃陀石窟群“临近古代商路”[3],原因在于“商人需要佛教的护佑,佛教僧团的发展也离不开在家信徒的支持”,所以“佛教石窟往往闹中取静,开凿于临近古代商路要冲的山间”[4]。包括佛教石窟(第1—12窟)、印度教岩凿神庙(第13—29窟)、耆那教岩凿神庙(第30—34窟)的埃洛拉石窟群距离阿旃陀石窟不远,同样位于连接北印度和南印度的古商路要隘之处,这组闻名于世的石窟群背后隐隐透露出了“区域性王朝”(Regional dynasty)强大的经济实力与虔诚的集体信仰力量。卡拉丘里王朝(约550—625年)、拉什特拉库塔王朝(约753—982年)、早期遮娄其王朝(约544—757年)雄厚的财力和高昂的宗教热情,历经数个世纪,造就了印度艺术史上的一组石窟建筑奇观。张同标研究表明,埃洛拉石窟、阿旃陀石窟、象岛石窟位于从恒河流域到西南出海口孟买的商贸要道即南方大道(Dakshina Patha)上,正是彼时繁荣昌盛的商贸经济供养了这些石窟[5]。
象岛(Elephanta Island)位于北纬18°58'和东经72°581/2'之间 [6], 距离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买大约11公里,热爱古代石头建筑的游客在印度门(Gateway of India)前可乘船前往参观,大约一小时航程便可抵达。作为天然港的孟买,在连接北印度、德干高原、南印度、印度洋诸国之间互通有无的商业活动之中,向来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言其是印度次大陆进入印度洋必经之地的说法可谓是言符其实。距离孟买阿波罗码头十来公里之远的象岛石窟群,与萨尔赛特岛石窟群,以及距离孟买市区40多公里的坎哈利石窟群[7],都受益于印度次大陆本土和印度洋诸国之间经久不衰的商贸往来,正是在商业当中获利颇丰的区域性王朝出资开凿了这些佛教和印度教石窟(印度教岩凿神庙)。如此庞大的工程,唯有王朝力量的介入,才能把热情高涨的宗教情绪转化成为有形的建筑物,任何个人和教派团体断然没有实现化无形信仰于有形实物的强大经济实力。
现今语境里所谓象岛一词和珈拉普里所蕴含的原初寓意相去甚远,不仅丢失了建筑与财富双层意思,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外来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本土印度教文化之间势力角逐的强弱态势,尽管此种态势只是于特定时空里的人事器物而言,但其间所映射的异时异地既同步也不同步的诡异辩证尤为意味深长。1458年5月20日,葡萄牙航海家维斯科·達伽马的船队抵达印度卡利卡特,该事件揭开了印度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于时空二维度上接触与碰撞的序幕,也是象岛这个极为形象但却西化意味尤为强烈名称之由来的本源所在。1534年,葡萄牙人在岛上发现一头整石雕琢而成的大象,遂将该岛屿命名为a ilha do Elephanta[2]16(象岛)。1814年,石象的头和脖子掉落。再后来,石象剩余部分也破碎坍塌了。1864年,这些破碎和坍塌的构件被转运到了孟买的维多利亚花园,并被重新组装成了一尊雕塑[6]3。所谓象岛一词的来历,大致情况如此。作为殖民者的葡萄牙人对于该岛屿的原初名称及其寓意并不了解,只是以点带面,把岛上诸多雕塑之一的石象作为其名称。日后,象岛一词便频繁地出现于西方学者与旅行家们的学术论著与旅游日志当中,笔者学力所及的英文论著都全部采用了Elephanta Island,而非Elephant Island这一正确的英文拼写。“久假而不归”,就连现今印度本土学者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这个西方殖民主义色彩尤为强烈的名称,个中缘由值得深思。印度境内的印度教岩凿神庙一向都是以印度民族语言为载体,以印度教经典如《吠陀》《往世书》《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里的特色词汇而命名,唯独象岛石窟例外,这大概也是其往往令人忽略却又无比重要的一个“特征”。
二、象岛营造者与开凿年代
界定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的营造者,是一个令建筑史家们困惑不已的问题,迄今为止尚无说服力很强的答案面世。乔治·米希尔指出,辨别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的供养人、工匠以及此地一度盛行的印度教教派,并无确切可信的信息,因而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10]。葡萄牙人入主孟买一带后,曾经在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第1窟(主窟)的北窟口上,发现过当时无人能识别的石刻铭文。1540年前后,石刻铭文被运送到了葡萄牙本土,国王若昂三世(Joao Ⅲ)曾组织人手对之进行破译但无功而返。之后,石刻铭文出于某种原因而不知去向了,界定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的营造者便难上加难了,不得不从包括神话传说等渠道里去寻找蛛丝马迹。概而论之,与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营造者有关的神话传说,主要有以下3种截然不同的版本:第一种版本将之和大史诗《摩诃婆罗多》联系了起来,认为是般度5兄弟开凿了这组印度教石窟;第二种版本则是阿修罗之王巴那(Bana)和其美丽无比的女儿邬莎(Usha);第三种版本则将其归功于东征而来的亚历山大大帝[11]。
然而,神话传说终究不能等同于史实,探究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营造者究竟为何人必须另辟蹊径,方能作出可信度高的结论出来。结合洞窟形制、雕刻和壁画的内容与艺术风格、平面图一致的同类石窟(萨尔赛特岛石窟和埃洛拉第29窟杜尔玛·莱那)综合分析,可以确定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开窟的年代大概为公元6世纪中叶。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9]之间,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发生在公元前327—前325年之间,这两个时间系列与印度教神庙建筑史界公认的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的开窟年代(公元6世纪)相去甚远;而阿修罗之王和女儿邬莎建造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一事,更是没有具体的年代流传下来,显然不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学术论断。迄今为止,象岛诸窟内并无古代木质遗物发现,主窟(第1窟)的壁画残破不堪致使难以辨认,加之管理权限、田野考察时段、实验设备器材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对之进行C14测定无疑是痴人说梦罢了。探究其开凿年代只能依赖文献记载,以及参照建筑史家与艺术史家们的推断了,而后者一定程度上是本文所能采用的唯一研究方法。
对于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的营造者,建筑史家与艺术史家们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主流观点则始终徘徊在康坎孔雀王朝(Konkan Maurya Dynasty)和卡拉丘里王朝(Karachuri Dynasty)之间。以沃尔特·斯平克(Walter Spink)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是卡拉丘里王朝的国君斥资修建。卡拉丘里王朝存续时段为公元6世纪至7世纪之间,疆域大致相当于今日印度共和国的古吉拉特邦、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大部分地区,康坎海岸(象岛所在地)也在其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10]。这个印度教王朝为人所熟知的君主有克里希纳一世(Krishina I,约550—575年)、桑卡拉伽那咖(Shakaranaga,约575—600年)、菩提罗阇 (Buddharaja,约600—625年),这三位君主乃是印度教毁灭之神湿婆的虔诚信徒。史书所载二事,尤其值得当今治印度教神庙史者关注与思考:其一,象岛乃是印度教兽主教派的大本营,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便是这个教派的祭祀与布道场所,第一窟(主窟)的建筑形制、平面布局、雕刻等都是为兽主帕特有的宗教仪式而有意为之;其二,菩提罗阇在位期间,在印度教神庙建筑领域成就很大的早期遮娄奇王朝和卡拉丘里王朝交恶,曼伽莱萨(Mangalesa)和补罗稽舍二世(Pulakesin Ⅱ)率领海军攻占了象岛,卡拉丘里王朝自此退出了西印度的历史舞台。沃尔特·斯平克等人认为,6世纪中叶至 7世纪,卡拉丘里王朝都有效地控制着包含象岛在内的康坎海岸,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的主体工程完成于克里希拉一世统治时期,在该岛屿所发掘出的大量铜币理应是为了支付工匠们工钱而特地铸造的金属货币。铜币正面铸造的人物是克里希拉一世,背面婆罗米文字乃是卡拉丘里王朝所通用官方文字。
沃尔特·斯平克等人的观点受到了以卡尔·坎嗒拉瓦拉(Karl Khandavala)和希拉南达·萨斯特里(Hirananda Sastri)、MA·嗒凯(MA Dhaky)为代表的艺术史家的质疑。他们认为,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的营造者是康坎孔雀王朝而非卡拉丘里王朝。卡尔·坎嗒拉瓦拉、希拉南达·萨斯特里、MA·嗒凯等学人的立论,依然是建立在对康坎孔雀王朝疆域的推断之上,即认为公元6世纪至7世纪之间,康坎孔雀王朝有效地控制了囊括象岛在内的康坎海岸,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就是该王朝的国君们所开凿。关于在象岛上发掘出的铜币,并不能证明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乃是克里希拉一世所为,卡拉丘里王朝所铸造的铜币是当时康坎海岸一带广泛使用的商业货币,象岛发掘出的铜币乃是货船航海触礁后的遗留物,而并非是支付给在象岛上从事宗教建筑工程工匠们的工钱。
就学理的客观性而言,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系卡拉丘里王朝开凿更具有说服力,该结论基于如下理由:第一,卡拉丘里王朝具有明确记载的三位笃信印度教兽主教派的君主,而康坎孔雀王朝则没有;第二,在象岛上发掘出来的钱币,更是一个卡拉丘里王朝曾经统治过康坎海岸的有力佐证;第三,萨尔赛特岛的印度教岩凿神庙、埃洛拉石窟第29窟杜尔马·莱纳、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三者之间具有诸多相似之处,而杜尔马·莱纳业已被学界多数人认定是卡拉丘里王朝所开凿。
三、象岛与湿婆之家
在行会内师徒之间采取口传面授的专业语境之下,程序化和规范化是印度教岩凿神庙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所有印度教岩凿神庙都有固定的建筑模式,都遵循同样的建筑原理,都采用相同的建筑流程工艺。就施工工艺而论,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和佛教石窟以及耆那教石窟并无任何不同之处,都是采用“减法”从原生岩石当中开凿出洞窟作为建筑空间,然后在洞窟里继续作业,精雕细琢出并无实际功能的建筑构件、雕刻以及绘制壁画,等等。就建筑构件而论,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和佛教石窟以及耆那教岩凿神庙则是同中有异——同者为柱子、壁柱、支架、横梁,异者则是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有圣所伽尔巴·格里哈,而佛教石窟和耆那教岩凿神庙则无此建筑构件。建筑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共计5个洞窟,第2—5窟或未完工,或洞窟形制面积特别小,或损毁严重,雕刻壁画全无,研究价值不大。
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第1窟于198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世建筑史家和艺术史家们美其名曰“湿婆之家”,原因在于窟内所有的雕刻都以大神湿婆(Siva)、其妻帕尔瓦蒂(Parvati)、其子象头神伽内什(Ganesh)和战神卡尔蒂凯伊(Kartikaye)、七圣母(Matrikas)为艺术题材,以印度教圣典里的故事情节为内容,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湿婆及其家族成员复杂多变的性情与寓意深远的面相。在清凉幽暗的洞窟里,人力苦心雕琢的石壁成了雕刻家们施展才华的道具,石窟建筑构件成了映衬无比精美之雕刻的背景。本文接下来探讨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第1窟“湿婆之家”在建筑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
1.选址
印度教神庙的选址和水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神庙通常建造在天然水体的旁边,如拟建神庙附近无天然水体,则人工建造净身池取而代之。把神庙建筑与水体连接起来,首当其冲的原因是印度教盛行到圣地(提尔塔)朝圣,而水和神庙建筑则是构建圣地提尔塔一个不可或缺的宗教元素。学者斯特拉·克拉姆里斯奇(Stella Kramrisch)指出:“仪式上而论,无论处于何方,一座神庙的地址就是一个提爾塔(Tirtha)。”[11]5又云:“提尔塔是位于河岸、海滩、湖泊旁圣地的名称,寓意为渡口和通道。”[11]2可见,四周临海的象岛无疑是印度教徒心目当中极佳的圣地提尔塔,加之位于古海洋商路的咽喉之处,能从一度繁荣昌盛的商贸往来当中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养。卡拉丘里王朝选择在此地开山凿窟,既是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出发来思考问题,也有归属于精神层次上的宗教活动须有归属于俗世的商业活动来支撑,更与水这一元素在印度教祭祀仪式里特殊的功能有关。在印度教种姓制度所构建的传统社会当中,“洁净”与“污垢”是两个极为重要的观念,水被视为能去除“污垢”从而实现身体与灵魂“洁净”的中介物,在圣水圣河里沐浴亦然成了印度教徒们时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宗教仪式。四围临海这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也就成了虔诚印度教信徒们在参拜“湿婆之家”前,进行去除肉体和灵魂上不洁之物的有利条件。南亚气候炎热潮湿,进入印度教神庙必须脱鞋,斯里兰卡最大印度教神庙纳鲁尔神庙位于贾夫妠(Jaffna)半岛,要求男性必须赤裸上身方能进入。局外人无法理解的脱鞋、赤裸上身、沐浴等行为,在印度教教徒心目当中却意味着是对神祇的虔诚和实现人生终极目标解脱(Moska)的必然途径,神庙建筑乃是圣地提尔塔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到圣地朝圣能获得无上的功德。
多石的自然环境是卡拉丘里王朝选择象岛开窟凿庙的另外一个客观条件。如以建筑材料来衡量,大体而言,印度教神庙可以划分为木质神庙、砖头神庙、石头神庙以及近世兴起的钢筋混凝土神庙,而石头神庙无疑是四者中的精华之作,无论就建筑成就还是就造型艺术价值而言,都达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度。本文所论的印度教神庙系石化阶段的神庙,即建筑材料为质地坚硬的原生石和料石,石化阶段的神庙则是印度教神庙建筑史上艺术价值最高的建筑。如以建筑方法来划分,石化阶段的印度教神庙可以划分为岩凿神庙(rock-cut temple)和石砌神庙(stone-built temple)——前者采用减法工艺在原生石内部开凿而出,后者采用加法工艺用料石层层堆砌而成。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第1窟可谓是岩凿神庙当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显例,而象岛多石的自然环境则是其独具一格之建筑问世的客观条件,黑色火成岩(black trap)遍布全岛,质地坚硬且不易风化,是雕琢石窟的天然绝佳材料。在石雕艺术繁荣的那个时代,卡拉丘里王朝的建筑师和雕刻家们,仅仅以简陋的锥子和凿子为工具,却把自身的艺术才华施展得淋漓尽致,在象岛的黑色火成岩内部雕琢出了鬼斧神工般的岩凿神庙建筑出来。印度是石窟建筑的起源地,马哈拉施特拉邦是印度境内石窟建筑的集中之地,其地汇聚了160多座印度教岩凿神庙,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第1窟既是功能齐全的宗教建筑,也是一件无比精美的艺术品,或隐或显地体现了印度教深奥的宇宙观,这在其建筑平面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2.平面
印度教神庙建筑的平面布局体现出了统一性和一致性的特点,所有印度教神庙都按照被称为瓦斯图·普罗沙·曼荼罗(vastu purusha mandala)的宇宙图式进行布局和修建,“一座印度教神庙就是一个微型宇宙,亦即按比例缩小的宇宙结构的复制”[1]250,而“瓦斯图·普罗沙·曼荼罗是所有印度教建筑形式的平面图”[11]22。不难看出,梵文瓦斯图·普鲁沙·曼荼罗一词由三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含义不同,瓦斯图代表存在的范围,普鲁沙是宇宙原人的名称,曼荼罗指的是任何封闭的多边形。瓦斯图·普鲁沙·曼荼罗的基本图形为长方形,根据具体的需要,可以演变为正方形、六边形、八边形、星形等封闭多边形,印度教神庙正是以这些封闭的多边形为平面图进行设计和修建的,其间所蕴含的程序化、传统主义的倾向尤其浓厚。
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第1窟的设计遵循了瓦斯图·普鲁沙·曼荼罗的总体原则,但又因地制宜,从象岛山形地势的具体情况出发,对长方形的基本平面图进行了改进,开创性地设计出了平面为十字形的印度教石窟神庙。平面为十字形的印度教石窟神庙尤为罕见,就整个印度境内的情况而言,没有任何一座印度教石砌神庙的平面为十字形,平面为十字形的印度教岩凿神庙屈指可数,只有象岛石窟主窟、撒尔赛特岛的乔格斯拉瓦石窟、埃洛拉石窟第29窟杜尔马·莱纳三座,三者都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近乎一模一样的十字形平面、风格和主题相同的雕刻,隐约暗示着这三座印度教岩凿石窟神庙乃是同一批艺术家在同一时期内所建,三者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在十字形平面所构筑而成的洞窟空间里,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第1窟内部巧妙地划分出了东西与南北两条中轴线,给寻道者带来了一实一虚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体验。第一条中轴线的起点北窟口,终点为南墙石壁。寻道者自北而南,目力所及的是巨型雕刻《永恒的湿婆》(Sadashiva),象征宇宙的创造、维持、毁灭的三面湿婆豁然可见。功力深厚的雕刻家借助有形之物的形式,惟妙惟肖且恰如其分地刻画了大神湿婆的三种面相,即温柔相(Vamadeva)、恐怖相(Bhairava)、超人相(Tatpurusha)[1]328。第二条中轴线起点为东窟口,终点为西窟口。问道者自东而西,途经圣所(胎室)伽尔巴·格里哈 (garhba-griha),目力所及的是寓意深远的林伽约尼。在幽暗寂静的岩石空间里,雕刻家化无形为有形,化具体为抽象,把大神湿婆和其配偶雪山女神帕尔瓦蒂以象征物林伽与约尼的方式呈现,借此表达了阴阳合而万物生的哲理与宇宙观。
3.建筑布局
象島印度教岩凿神庙第1窟建筑分为主窟、庭院、翼窟三个部分,整个建筑布局极为巧妙,功能齐全,神圣湿婆家族每个成员的雕像皆在石窟建筑空间里占据了一方之地。其中,主窟的建筑布局最为引人注目,东窟口、西窟口、北窟口三个窟口通向了神秘肃静的人工洞穴空间,与惯常石窟只有一个窟口比较而言,主窟三个窟口带来了更多的光线,由此造成了更为强烈的明暗视觉对比。这在世界石窟建筑史上是为数不多的奇特建筑现象,印度境内除了撒尔赛特岛的乔格斯拉瓦石窟、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第1窟、埃洛拉石窟第29窟杜尔马·莱纳之外,再无他者。主窟的圣所伽·尔巴·格里哈位于东西中轴线东端约4/5处,建筑师们匠心独运,大胆地打破了石窟建筑(印度境内包括佛教石窟、印度教岩凿神庙、耆那教岩凿神庙)圣所开凿于后壁的惯常建筑范式。这在世界石窟建筑史上无疑是一个屈指可数的创举,印度境内仅有象岛印度教岩凿神庙第1窟的主窟采用了这种奇特的建筑模式,物以稀为贵的背后折射出了匠人们的智慧和对冥冥之中神灵的虔诚敬仰。除了三个窟口和圣所伽尔巴·格里哈之外,主窟的石柱、横梁、雕刻也引人注目,这三个建筑构件透露出了浓郁的木质阶段和石化阶段的印度教建筑特征,既反映出了木质建筑和石质建筑之间密不可分的前后关联,也反映出了石质建筑对于木质建筑的突破与创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主窟的窟口、圣所伽尔巴·格里哈、石柱、横梁实则都充当了映衬与陈列雕刻的舞台和背景,都是为了表现雕刻主题人物大神湿婆至高无上的神力而刻意为之。北窟口的《瑜伽之主》与《舞蹈的湿婆》,南壁上的《永恒的湿婆》《持恒河者》与《半女之主》,西窟口的《湿婆诛杀安达卡》《湿婆与帕尔瓦蒂的婚礼》,东窟口的《湿婆和帕尔瓦蒂掷骰子》与《罗波那摇撼凯拉萨山》,这9副浮雕寓意深远,以动静结合的艺术手法,在原本呆板冰冷的石头上把毁灭之神湿婆复杂多变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
四、特征与影响
象岛石窟群由建筑、雕刻、壁画三部分构成,每一部分都有自身独有的特点,每一部分都对同时代和后来的印度教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一部分又和其他两个部分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共同组成了象岛印度教神庙艺术宝库的有机整体。由于年代久远,自然力的诸多因素不停地腐蚀,加之人为的破坏,象岛石窟面临着日益损毁的境地,建筑构件、雕刻、壁画都有不同程度的毁坏,壁画毁坏程度尤为严重,现今只能隐约瞥见其残留的蛛丝马迹。
象岛石窟群深受佛教建筑的影响,其建筑和雕刻都具有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早期佛教建筑的某些印痕。通常的观点认为,印度教神庙是在佛教建筑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就建筑具有在时间上前后延续的特点而言,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印度教神庙绝非是对佛教建筑的简单复制与模仿,而是不断试图摆脱其影响,不断努力地创造出符合自身教义和宇宙观的建筑形式。象岛石窟不落窠臼,同样被佛教岩凿石窟建筑打下了深深的痕迹,但又遵循了印度教神庙建筑的发展模式和规律,具有很多有别于佛教建筑的特征。
第一,象岛石窟主窟的平面为十字形,并且有三个窟口,是一种极为独特的印度教岩凿神庙。印度教神庙遵循着特定的建筑范式,通常按照被称为瓦斯图·普鲁沙·曼荼罗的平面图进行布局和建造。瓦斯图·普鲁沙·曼荼罗是方形的宇宙图式,体现了印度教天方地圆的宇宙观,几乎所有印度教神庙的平面都按照这种宇宙图示进行设计和修建。象岛石窟主窟不落窠臼,独辟蹊径,创造性地运用了另外一种平面图,这在印度教岩凿神庙当中极其罕见。大多印度教岩凿石窟神庙都只有一个窟口,或开凿于东方,或开凿于西方,或开凿于北方,极少数开凿于南方。象岛石窟主窟开凿出了三个窟口,分别位于东方、西方、北方,这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创举,一方面为进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另一方面对于通风和采光也大有益处。在印度境内,十字形平面、三个窟口的岩凿石窟神庙并不多见,除了象岛石窟主窟、孟买附近的撒尔赛特岛石窟、埃洛拉石窟第29窟杜尔马·莱纳之外,其他地方再无这种类型的神庙,个中原因值得思索和探究。
保守主义是第一个原因。印度教是一种民族性极强的宗教,出生是一个人是否为印度教教徒唯一的标准,换言之,一个人之所以是印度教徒是因为父母是印度教徒。血统决定了一个人是否是印度教教徒,血统决定了印度教具有浓厚的排他性,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印度教教徒,排他性决定了印度教具有不易变革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的倾向贯穿了印度教神庙发展的整个历程,尽管历经了若干王朝的兴衰,尽管所处的地理环境迥然不同,所有神庙的布局、式样、风格、构件等都极少改变,呈现出延绵不断地发展但又前后一致的特点。象岛石窟和埃洛拉石窟惊人类似,早期遮娄其王朝的神庙和帕拉瓦王朝的神庙彼此影响、大同小异,东南亚爪哇、普吉岛、中国泉州等异域的神庙和印度本土的神庙并无两样。异时异地,建筑却有着令人惊讶的类似之处,这是印度教神庙建筑史上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固守保守主义的建筑师们,严格遵守传统的建筑工艺,不愿意越雷池半步,大多时候按照瓦斯图·普鲁沙·曼荼罗设计出了平面为方形而不是十字形的印度教神庙。
修建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难是第二个原因,平面为十字形、有三个窟口的岩凿石窟神庙首先面临着选址困难的问题。开凿岩凿石窟神庙的地址,需要选择在有大量坚硬石头存在、交通较为便利的山腰或悬崖上,这无疑给建筑师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也是日后岩凿石窟神庙被石砌神庙取而代之的主要原因。在山腰或者悬崖上开凿出三个窟口,再借助这三个窟口层层推进,从实体岩石中开凿出石窟来,也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后盾,绝对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修建岩凿石窟神庙的巨大困难,决定其数量极少,和石砌神庙相比可谓是沧海一粟。有人作过粗略的统计,印度大约有1 200座岩凿石窟神庙,其中大约有800座属于佛教,200多座属于印度教,其他为耆那教神庙[12]独立式的石砌神庙,选址容易,建造容易,取代岩凿石窟神庙是必然的趋势。自公元10世纪起,印度教神庙多为石砌神庙,岩凿石窟神庙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第二,象岛石窟主窟的圣所有四道门,这在印度教神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杰作。一般而言,印度教神庙的圣所只有一道门,或朝向东方,或朝向西方,或朝向北方,极少数朝向南方。据目前历史学和考古学所掌握的情况而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开凿有门的圣所,仅此象岛石窟主窟一例,其他地方再无这种有四道门圣所的踪影,就连平面同为十字形的撒尔赛特岛石窟、埃洛拉石窟第29窟杜尔马·莱纳的情况也如此,二者的圣所都只开凿出了一道狭窄的门出来。四道门的圣所除了有便于通风和采光的好处外,还能让信徒们围绕其逆时针绕行时,从四个方位都能瞥见大神湿婆的象征物林伽,拉近人神之间的距离,增强信徒们对神的虔诚之心。修建有四道门的圣所有很多工程上的技术难题,在缺乏现代大型工程机械的时代,加之对静力学的原理不胜谙熟,建筑师们只能凭借已往积累的经验,几乎是在直觉的驱使之下,在坚硬无比的玄武岩内部,开凿出规模巨大、造型独特的圣所出来,委实是一个建筑史和艺术史上的奇迹。
第三,象岛石窟残留了木结构建筑的痕迹,也保留了很多佛教巖凿建筑的诸多元素。就建筑材料而言,印度教神庙历经了木头神庙、砖头神庙、石头神庙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并不是彼此独立发展的阶段,而是相互影响、有时相互重合的,很多神庙同时运用了木头、砖头和石头三种材料,同一座神庙使用砖头和石头的情况最为常见。印度气候炎热,木制建筑容易腐烂,保留下来的木头神庙几乎没有,但木头神庙曾经长期地存在过,并且对砖头神庙和石头神庙具有极深的影响,导致了砖石神庙建筑当中残留了大量木质神庙的遗痕,象岛石窟的情况也如此。仔细观察象岛上5座印度教石窟,便不难发现很多建筑构件并没有任何实用功能,而仅仅是作为装饰性的构件保留了下来,这在支架和横梁这两个构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构件支架不起任何支撑重物的作用,构件横梁也不起任何连接柱子的作用。象岛石窟开凿的时代还处于木、砖、石混用的时期,这时期的建筑往往采用木头作为建筑材料,建筑师们在修建木头神庙的基础之上,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建筑师们猛然间面临在石头内部开凿出石窟神庙的要求,显得有些无所适从,思维和建筑经验都还停留在木头建筑上,自觉与不自觉地把修建木质神庙的经验和思维运用到了开凿岩凿神庙之上,其唯一的后果便是在石头神庙之上留下了很多木质建筑的痕迹。关于木质建筑对岩凿神庙的影响,有学者曾经这样精彩地评论道:
当岩凿建筑活动在西印度开始的时候,艺术家们缺乏开凿石窟的先前经验。通常而言,他们被当作木匠训练,因此被称为在石头上加工的木匠们。这样的后果是,早期的岩凿石窟只是木质建筑在石头上的翻版,具有很多木头建筑的痕迹。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早期石窟的建筑时代是根据其所包含的木质遗痕来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艺术家们经验的增加,木质建筑对岩凿建筑的影响逐步降低了。[13]
建筑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文化现象,研究建筑史也不是仅仅罗列各种建筑的形态和风格,建筑是特定的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等很多因素的综合反映,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前后联系与彼此影响进行的研究实则没有多大意义。从前后联系、彼此影响的时空关系来考察,象岛石窟和佛教建筑之间又有不可割断的内在关系,具体而言是佛教建筑毗诃罗的再版与变种。毗诃罗在汉语中被称为精舍,即佛教和尚生活起居之所,印度佛教岩凿建筑大多为毗诃罗,支提窟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佛教和尚们通常不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地停留,而是云游四方,以宣讲佛法为终身追求的目标和唯一的生活方式。然而,在漫长的雨季里,外出极不方便,而且危险重重,佛教和尚们就选择待在同一个地方,进行冥想静修和阅读经典等宗教活动,毗诃罗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了。毗诃罗采用岩凿建筑工艺,先在岩石内部开凿出一个列柱大厅出来,然后在左边、右边、后方的石壁上开凿出一系列小石窟,供和尚们生活起居之用。一般的毗诃罗形制简单,往往只是一个小石窟,内部并无他物,但埃洛拉石窟群的一些毗诃罗,内部却雕凿出了石床和石枕头。象岛石窟便是模仿毗诃罗所开凿出来的印度教岩凿石窟神庙,但又对毗诃罗进行了布局上的调整,以适应印度教祭祀和布道仪式的具体需要。在象岛石窟里,毗诃罗左边、右边、后方石壁上的小石窟数目减少为一个,而且位置移位到了列柱大厅曼达波内的左面,成了供奉湿婆林伽的圣所伽尔巴·格里哈,左边、右边、后方石壁上不再开凿小石窟,而是用与大神湿婆有关的9幅浮雕取而代之。修建象岛石窟的建筑师们对毗诃罗进行了扬弃,保留了其精华之处,去除了不适合印度教仪式的建筑元素,创造出了印度教神庙建筑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出来。
参考文献:
[1] 王镛.印度美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25-333.
[2]ILIKA C.Tourism Development in Small Islands: A Case Study of Elephanta Island,Maharashtra,India[J].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2015(3):16.
[3]王云.丝路佛教石窟系列(二)——印度后期佛教石窟[J].中国美术,2017(9) : 129.
[4]王云.丝路佛教石窟系列(一)——印度早期佛教石窟[J].中国美术,2017(7):112.
[5]张同标.印度埃洛拉石窟第12窟的八大菩萨造像[J].吐鲁番学研究,2018(2):31.
[6]HIRANANDA S.A Guide to Elephanta[M].Delhi: Manager of Publications,1934:2.
[7]体恒.古代印度石窟寺僧人生活用水情况——以坎哈利石窟和敦煌莫高窟为例[J].法音,2018(10):22.
[8]GEROGE M.Elephanta[M].Munbai: Jaico Publishing House, 2002:96.
[9]毗耶娑.摩诃婆罗多(一)[M].金克木,赵国华,席必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9.
[10]杨旭彪.6—9世纪的印度教神庙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17:101.
[11]STELLA K.The Hindu Temple:Vol. I[M].Delhi:Motilal Ranarsidass Publishers, 1976:5.
[12]DHAVALIKAR M K.Masterpieces of Rashtrakuta Art: the Kailas[M].Bombay: D.B. Taraporevala Sons & Co. Private Ltd,1983:1.
[13] DHAVALIKAR M K.Monumental Legacy: Ellora[M].New Delh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3.
(责任编辑:蒲应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