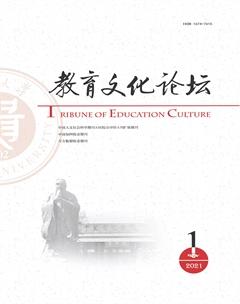“不滞”与“不离”:阳明心学视域下的良知与知识之辨
龚晓康
摘 要:明代中晚期,“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转换为“良知”与“知识”之辨。一般的观点认为,阳明强调致良知的道德实践,故而对经验知识有所忽略,甚至是以德性消解了知识。也有学者认为,阳明虽强调致良知之工夫,但并未轻忽知识之价值,知识有其独立的地位。事实上,阳明在论述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关系时,明确有“不滞”与“不离”的说法:良知不依见闻而有,为见闻生成之场域,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见闻之知源于意、物的分化,为良知的客观呈现,故“良知不离于见闻”。究言之,阳明既非以良知取消知识而落入泛道德主义,亦非以知识泯灭良知而落入唯知性主义,而是在承认知识价值的同时回归良知本体之澄明。
关键词:阳明心学;良知;知识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1-0033-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1.006
如所周知,张载区分了“德性所知”与“见闻之知”两种不同的知识路径。前者为人先天所具有的天德良知,故“不萌于见闻”;后者出于感官的知觉作用,依之而形成后天的经验知识。王阳明承继张载之说,认为德性之知“是为良知,非知识也” [1]261。那良知与知识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呢?学界对此有争论。一般的观点认为,阳明强调致良知的道德实践,故而对经验层面的知识有所忽略,有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冷天吉认为,王阳明过分强调了儒家为学的成圣目标和德性工夫,“忽视人的认知与知识在德性培养中的作用”[2]99。赵卫东持相近之观点,认为王阳明“抹杀了知识在成德中的独立价值,表现出重德性而轻知识的倾向”[3]。丁为祥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排除或屏蔽了外向的格物穷理与知识追求”[4]13。也有学者提出了另外的观点,认为阳明虽强调致良知,但并未轻忽知识之价值,知识有其独立的地位。余英时指出,王阳明的学说虽是反智识主义的高潮,但“并不含蕴王阳明本人绝对弃绝书本知识之意”[5]。刘述先认为,阳明坚持要把德性与见闻两下分疏开来,“实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6]。彭国翔甚至认为,阳明学坚持良知与知识异质性的立场,“反而更具有契接西方科学思想的学理基础” [7]。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良知与知识之间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可以相互促进与补益。张学智认为,阳明的致良知教是德性与知性的结合,每一个致良知的行为都会导致“知性的明敏和德行的深粹”[8]36。张明、王建明指出,王阳明主张德性与才艺知识的一体成就,“德性的修养自然会带来才艺的养成,而才艺的养成也会促进德性的成就”[9]43。刘荣茂分析了阳明学派“游艺”与“养心”中的知识面向,认为“心学修养为求知学艺提供了精神归宿”,同时,“知识技艺在心学中获得显著且独立的地位”[10]167。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唐君毅的论述特别值得关注。他将德性之知与知识之知的关系概括为四种:一是德性之知直接通过知识之知而表现,二是成就知识之知乃德性之知所决定,三是以知识之知为手段以达成德性之知,四是德性之知未能充分满足时对知识之知的抉择与承担[11]278-284。但是,唐先生是在承认知识之知与德性之知各自成立的基础上讨论的,对于德性之知如何转换为知识之知的问题则未能有清晰的阐明。事实上,关于良知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王阳明有着明确的说明:“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12]77那良知与见闻(知识)之间的这种“不滞”与“不离”关系究竟有何意蕴呢?良知如何能开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呢?致良知的工夫排除了知识的进路吗?诸如此类的问题,皆有待于进一步澄清。
一、良知:知识生成之场域
一般而言,知识的生成源于人之认知活动。在认知活动中,有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的区分:认知主体具有认识的能力并且作用于认知客体,而认知客体不过是认知主体所把握的现实的对象事物。认知主体与认知客體的交互构成了人类的认知过程,同时两者共同构成了人所在的“世界”。对于这种流俗之见,西田几多郎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在认识活动中,除了作为纯然活动之统一的“我”,以及相对于“非我”的 “我”之外,“也必须存在着将‘我与非我的对立内在地包含的东西,也就是说,必须存在着让‘意识现象得以内在地产生的东西。” [13]西田将这种意识活动得以产生的东西称为“场所”。
如果借用西田的“场所”概念,那我们可以发现,阳明所言的“本心”即相当于认知活动得以可能的场所。何以如此?本心既创生了天地万物之本原,又与天地万物神感神应,为前对象化、前概念化、前理论化的源初境域,依之而有主体与客体的分化。一方面,“心之所发便是意”,意识为本心之流行发用与明觉感应,并构成了认知活动的主体。另一方面,“意之所在便是物”,作为认知活动的客体根本上也是源出于本心。质言之,作为认知主体的自我与作为认知客体的外物皆源于本心的发用,而本心也就成为让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场所”。
本心为“即存有即活动”者,既是天地万物之最终本体,亦是天地万物的创生力量,为意识活动的真正本源。阳明谓:“夫人心本神,本自变动周流,本能开物成务。”[12]2 115天地万物生生不已,不过源于本心之造化。良知即是心之本体,故阳明亦谓良知为万化之本原。他曾以良知的收敛凝一与妙用发生来说明“世界”之隐遁与开显:“夜来天地混沌,形象俱泯,人亦耳目无所睹闻,众窍俱翕,此即良知收敛凝一时。天地既开,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闻,众窍俱辟,此即良知妙用发生时。”[12]116故而,人心与天地一体,上下与天地同流。质言之,良知为万物隐显之源初境域,故阳明谓之为“乾坤万有基”。
本心既开显出天地万物,亦与天地万物感触神应,阳明以虚灵明觉概括之:“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12]52分而言之,本心具有虚无、灵动、光明、觉照等性质。
首先,何谓本心之“虚”?阳明以太虚喻之。心之本体如太虚般广大,含摄万物而不为万物所障碍:“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饐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12]1 317天地万物皆在本心中发用流行,而于太虚之本体无所妨碍。
其次,何谓本心之“灵”?天地万物既由人心所生成与开显,则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 [12]118。依于人心一点灵明,万物呈现出意义与价值。阳明追问道:天没有人心一点灵明,则谁去仰他高?地没有人心一点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人心一点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故而,人心一点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12]136。在人心灵明的感触神应之下,天地万物生生不已而成其自身。
再次,何谓本心之“明”?阳明谓人心自能散发光明,故有“心体之光明”的说法。心体光明朗照万物,而不为万物滞碍,故良知之发见流行“光明圆莹”[12]93。而且,天地万物皆有生灭,而心体光明却为永恒,所谓:“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12]829当然,常人百念纷然杂兴而流入昏愦之中,须是磨去思虑尘念之昏蔽,则“自然里面生出光明”[1]272。
最后,何谓本心之“觉”?人既为天地之心,则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12]86知吾身之疾痛者,为心之同体感应,表现为悱恻不忍:“故顺天地万物之理则心安,不顺天地万物之理则心有不安,安与不安之际,其名曰‘知。”[12]1 633心之安与不安,吾人之良知皆能自我觉察,故阳明谓良知能知得意念之善恶:“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12]1 019即使是小人,也具有自我觉察之良知——小人虽为不善,见君子则必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可见其有不容自昧之良知。当然,良知之知善知恶,非是知得善恶之知识,而是本心悱恻不忍的感通能力。
本心之虚灵明觉即是良知,那良知所知者究竟为何呢?阳明谓良知只是“知个天理所在”。本心之发用流行,自有其天然条理,即是所谓的“天理”。在阳明这里,天理并不是指僵化的道德教条,而只是本心“不容已”之流行,“理也者,心之条理也”[12]294。天理乃是本心的活动秩序,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12]294因此,天理不外于本心,是为“心即理”。这也说明,“天理”只是本心流行的条理,并非认知意义上的知识。
严格说来,良知并无特定之物为其对象,只是朗现无对的心体的觉照,非是基于对象化的认知,故不在主客关系中呈现。换言之,良知并未落入能所的对待,只是心体自身的神感神应,故阳明谓之为“独知”。阳明喻良知如“灯”,自身本具光明,在照了他物之时,亦能照亮自身:“明德只是良知,所谓灯是火耳,吾兄必自明矣。”[1]252灯之火,在照亮众物的同时,亦照亮灯之自身。良知亦如是,其对天地万物之开显,也是本心之自然明觉。牟宗三指出:“惟在表示由超越的道德本心之知用来反显德性心灵之无外,亦即心体性体之无外,性体道体之无外,而实无认知意义也。”[14]良知并无内外的分别,其不依见闻而有,实与见闻无关,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这也意味着,良知为人所先天具有,无需后天之学虑,反诸自身即可证得。
概言之,本心既能生成天地万物,亦具虚灵明觉之功,为“即存有即活动”者,亦为前对象化、前概念化、前理论化之源初境域。然依于作为“场所”之本心,而有对象化、概念化、理论化的认知活动,这就需要进到对意识层面的讨论。
二、知识:良知的客观呈现
前已论及,本心虽为寂然不动之本体,亦具有感而遂通的性质,其发用流行则为现实世界。也就是说,本心具有不容已的力量,它生生不已而周流六虚,即需要在经验世界显现出来。当本心发动而落实于个体生命时,则有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化。那这种分化是如何形成的呢?意识发动之时必有与之相待的对象,这就导致了浑然一体的本心的分化:意念活动之发动者成为“自我”,意念活动的对象成为“事物”,由此而有主体与客体的对待,而主客的相合则有“知识”的产生。从另外的角度来说,“知识”开显出了对象世界。
首先,依于本心之发用流行,而有人之意识活动。“心之所发谓之意”,本心的流行依于个体生命时,则有个体意识的产生。而意识活动所具有的知觉思虑,根本上说来,源于良知的虚灵明觉。阳明谓:“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12]52分而言之,依良知之“虚”,而有意识活动之场域;依良知之“灵”,而有意识活动之动能;依良知之“明”,而有意识之明辨;依良知之“觉”,而有意识之觉知。故而,意识的根本在于良知,所谓“意之本体便是知”[12]6。当然,意识虽源于良知之应感而动,但与良知又有着根本的不同:良知只是本心自身的感应与朗照,意识活动却必基于主客的对待。
其次,意识活动生起之时,即有本心的分化。这是因为,意识之生起必有其对象,“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12]100,意识自身不能为空,其必指向特定的事物,“凡意之所在,无有无物者”[12]1 305。当然,此处所谓的事物并非指外在意识的客观存在,而是说意识生起之时必有其意向对象。因此,事物的现起不能离于意识的意向作用,是为“意之所在”;而意识自身又源于本心體发动,是为“心外无物”。既然事物只是意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那事物就并不能外在于意识而存在,故阳明弟子王龙溪谓之为“分别影事”[15]274,为呈现于意识中的影像而已。
最后,依于意、物的对立,而有知识的建构。意识具有知觉思虑之功,依于感官而能分别事物,故眼能辨五色,耳能辨五声,口能辨五味,鼻能辨五臭。在感官与事物相接之际,种种感觉得以产生,进而形成见闻之知。因此,见闻之知基于主客的相合,正是一般意义上的经验知识。
见闻之知既然需要在感触知觉中呈现,那就必囿于见闻活动而受制于经验。换言之,经验知识既为内外相合的产物,那它必定依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呈现出相对的性质:首先,见闻之知依于个体的感官,为感官所限并有现实的差异;其次,随着时代的变迁,见闻之知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最后,知识的建立依于名言概念,故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之间存在着差异化的发展。这是因为,见闻之知的形成需要诸多的因缘,而因缘又时刻处于变化之中,依之所形成的知识便具有相对的性质。
但是,见闻之知看似为感官的作用,实则源于本心的流行。《王阳明年谱》所附“《天成篇》揭嘉义堂示诸生”有云:
是天地万物之声非声也,由吾心听,斯有声也;天地万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视,斯有色也;天地万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尝,斯有味也;天地万物之变化非变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变化也:然则天地万物也,非吾心则弗灵矣。吾心之灵毁,则声、色、味,变化不得而见矣。声、色、味、变化不可见,则天地万物亦几乎息矣。[12]1 352
天地万物之声、色、味、变化,虽依于感官而呈现,然能辨其声、色、味、变化者,实为本心之虚灵明觉。依于人心之一点灵明,则有天地万物之声、色、味、变化,“世界”才得以开显出来。职是之故,我们也可以说,“知识”乃是一种解蔽,让那不可思议之本心,得以显现为万物芸芸之“世界”。
既然事物乃是依于本心而得以显现,那事物之理亦不能离于本心。阳明谓:“此心在物则为理。”[12]133“理”并非事事物物所定然具有,而是本心流行于事物时所呈现的条理。因此,物理并不能外于本心,只是本心的客觀显现而已:“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12]47职是之故,阳明谓“致知格物”,乃是致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能得其理。依此而言,“天理”与“物理”只是一个,前者乃是就本心之自然流行而言,后者乃是本心流行于事物而言。
这种依于本心所现的事物之理,如何能具有客观的性质呢?这就涉及人与人之间共同在世的主体间性问题。《传习录》所载“《天成篇》揭嘉义堂示诸生”云:
吾一人之视,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听,其声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聪也;一人之尝,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虑,其变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12]1 352
依文中所说,人既为人,则有相同的感官;有相同之感官,则有相同之感觉。所谓一人之视,则为天下之人所同视;一人之听,则为天下之人所同听。事物之颜色、声音等,并非事物的本来属性,而是依于人之主体间性,从而呈现出客观性:一方面,天下之人皆同有目之明、耳之聪,依之而可形成共通的感知觉;另一方面,依这种共通的感知觉,人之所视、所听则具有了客观的性质。
进而,世人依于共通的感知觉,而以名言言说之,则建构出共同认可之“知识”:一方面,事物本来只是蔽于混沌之中,因为名言的作用而得以与他物相区分,从而显现于世并具有客观的性质,进而被视为现成的存在者;另一方面,事物被符号化而进入了名言概念体系,人们依这而确定其性质及相互关系,作出判断与推理,从而形成所谓的“知识”,依之而建构出观念的世界。
事实上,阳明把见闻之知的根源归结为本心,这就回答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一方面,这种知识不能离于见闻经验,离开经验便不能产生;另一方面,见闻之知并非单纯的后天感知印象,而是有着本心的先天作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本心具有统觉的作用,能分别经验的杂多而将其形成为客观的对象,进而作出判断的联结以形成知识。由此看来,知识虽然是从见闻开始,却并不能说从见闻中发源。这也就表明,见闻之知既包含了先天的成分,也包含了后天的经验,实由先天与后天结合而成。因此,见闻之知具有两方面的性质:因其源于经验,故能不断地产生新知识;因其源于本心,故具有普遍必然性。
当然,这些知识既然由主体间性所建构,也就具有了独立的地位与客观的价值,并不能以个体的任意而否定之。正因为如此,阳明虽强调致良知,然亦不废知识之习得。请看如下之对话:
昔有问:“人能养得此心不动,即可与行师否?”先生曰:“也须学过。此是对刀杀人事,岂竟想可得?必须身习其事,其节制渐明,智慧渐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后世格物之学所以为谬也。孔子自谓军旅之事未之学,此亦不是谦言。[1]260-261
“养得此心不动”,作为致良知之工夫,意指本心不为私欲所扰动。然“行师”为“对刀杀人事”,需是“身习其事”以获取足够之知识,而知识毕竟源于耳闻目见,故非靠玄想即可获得。事实上,阳明之所以成为杰出的军事家,与其早年研习兵法有莫大的关系。他还写有《观稼》诗,表明他对日用知识之重视:“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种蔬须土疏,种蓣须土湿。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12]734因此,阳明反对将致良知与求知识相混滥。在他看来,致得良知者,并不能增长知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12]106圣人之为生而知之者,专指圣人自能明白良知本体,至于天下事物,圣人亦须学而后知。
综言之,本心为主客认知活动生成的源初场域,见闻之知不过是本心的发用流行。见闻之知依赖于本心的分化,然本心却不依赖于见闻,故“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见闻所形成的一切知识都只能是经验的,但一切经验对象及其知识依于本心而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良知开出了知识,或者说,“良知不滞于见闻”。但是,良知并不能直接开显出知识,知识的构建必定基于主客的分化。换言之,圣人并非无所不知,知识需由见闻而有。因此,知识虽然具有相对的性质,但却具有独立的地位。质言之,知识不过为良知之发用,为良知于经验世界的客观显现,同时,知识丰富了良知的内容。就此而言,阳明并没有落入消解知识的泛道德主义。当然,知识毕竟以主客的分化为前提,这就有可能导致对良知的遮蔽。
三、遮蔽与澄明
前文论及,心体之虚灵明觉,为良知自身之感应,不依于见闻而超越于见闻,是为“良知不滞于见闻”。意、物皆源于本心,两者相待而生,表明本心具有能动的力量,其发动而为意识,意识又建构出对象。知识生成于意、物分化之际,虽然缘于见闻并为见闻所限制,但因主体间性的作用而有其客观的意义。
事实上,意识在指向对象的同时,也设定出个体自我,即对作为“非我”的事物的设定,也意味着对“自我”的限定。在陽明看来,本心广大无碍,造化万物,周流六虚,其间并无自他之分别,而与万物神感神应,由此而可谓“仁者以天地万物本为一体”。故而,“大人”乃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则为“小人”[12]1 015。小人为形骸所桎梏,遂以天地万物为外在者。依于意识的这种执定作用,小我与外物皆成为现成的存在者。
作为认知活动主体之自我,相较于本心之“大我”而言,只是落于经验世界的“小我”。这个“小我”拥有意识的分别功能,它在设定“自我”的同时,也将与自我相待的“非我”设定出来。此即是谓,良知作为心之本体,纳万物为一体,本无内外之分。然由于意识的执定作用,人遂落入“小我”之中,以小我为真实之自我,这就是牟宗三先生所谓的“良知自我坎陷”。认知主体由自由无限心之自我坎陷而成,它“执持自己而静处一边”而成为认知主体,同时亦把“物之在其自己”之物推出去而视为对象[16]。但在笔者看来,良知并不能自我坎陷,坎陷良知者实为意识之执定,其将主客视为实在的存有,从而遮蔽了真正的本原——本心。当世人堕于知解意识的分别时,也就意味着陷于名言所编织的观念世界,而遗失了作为源初存在的本心,虚灵明觉之良知遂为知识所遮蔽。
小我受到非我的限制,也就成为有限性的存在。但是,小我毕竟源于本心,其试图超越非我的限制,而追求一种无限性,这就表现为人的冲动与欲望。依王龙溪所说:“高者蔽于意见,卑者溺于利欲。”[15]383高明者桎牿于意见,为固有观念所局限;卑下者陷溺于嗜欲,为感性欲望所支配。无论是欲望还是意见,皆源于意识的滞碍分别,伪妄不真而于心体有所妨碍。阳明有谓:“闻日博而心日外,识益广而伪益增。”[12]289因此,若不以良知作为道德践履的根本,只是单纯以追求名物度数为目的,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12]31。知识之增长非但不能使人行善,反而会成为良知之害。
故而,阳明谓良知与见闻之知实有层次上的区分,“致良知”为圣门教人“第一义”,而求见闻之末则落入“第二义”[12]77。前者是在心地上用功,以摆脱私欲与私意的束缚;后者乃多学而识,尚依赖于感性经验的运用。相较于“第二义”的知识之求取,“致良知”具有更为本原的地位如果说致良知为实践理性的话,那求知识便为理论理性。在阳明这里,实践理性虽然不离理论理性,但却具有优先的地位。有人问阳明:“知识不长进如何?”阳明回答说:“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12]15在阳明看来,为学工夫之次第,须是先致得良知,以知天理之所在,方为学问的根本头脑。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概括之:
首先,良知能为知识的获取指明前行的方向。世人多以追求知识为要务,“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其实,知识不过是依见闻而假立者,事物无限则知识亦无限。对于无限的经验世界,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全部知得,“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12]106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并非其拥有丰富的经验知识,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故阳明批评朱熹的格物穷理说落入支离,“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12]109。显然,阳明强调良知对知识的指引作用。对知识的认知需要奠基于本体之上,方能具有伦理上的规范与实践价值。
其次,良知能为知识的获取提供内在的动力。人之所以具有道德的动力,不在于知识的多寡,而在于良知的有无。阳明举例说,人若真有“诚于孝亲的心”,则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人如若真能葆有良知而诚于孝,则自有冬温夏凊之行为。此中道理在于,“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12]3。在本心良知的驱动下,人自然会去思考如何做出适宜的道德行为。亦即是谓本心具有不容已的力量,能够超越感性的束缚而为见闻之知提供动力。
最后,良知能为知识的获取提供清明的理性。阳明注意到,就知识的学习而言,存养本心者易于成功,欲望泛滥者则难以为之。他以学射为例说明,小人“懆于其心者其动妄,荡于其心者其视浮,歉于其心者其气馁,忽于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因小人心之不存,故不可谓之为学。反之,君子之学于射,则善存其心,“心端则体正;心敬则容肃;心平则气舒;心专则视审;心通故时而理;心纯故让而恪;心宏故胜而不张,负而不驰。”[12]262可见,君子之于射,内志既正,外体则直,而后可以言“中”,故射可以观君子与小人之德。阳明所言,类似于西方哲学的“理智德性”,即一个心平气和、全神贯注、不计得失之人,其德性之清明更有利于知识的学习。
当然,阳明以见闻之知为“第二义”,并没有否定这种知识的作用。其实,良知非为抽象的理体,而是必然流行于经验世界,故良知之流行不离于见闻。从某种意义上说,经由见闻而获取知识,乃是致良知工夫的根本要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意识本为良知之应感而动,故良知之流行并不能外于意识之思虑,“思是良知之发用”[12]78。良知固然超越于思虑,但却非是断绝思虑。而且,“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12]120人之良知多为私欲所遮蔽,正是缘于意识思虑之助发,才得以让良知之虚灵明觉,得以在现实世界中呈现。因此,良知精明不离意识之思虑,即不离意识思虑之知识。另一方面,良知之显明不离事上磨练的工夫,而事上磨炼又不离见闻知识的作用。阳明云:“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12]117所谓的存养心性,并非离却事物而堕入空寂,相反,应是重视人伦物理之习得,在事上磨练中涵养德性,而这不离见闻觉知。对于是否需要讲求“名物度数”的问题,阳明认为既不能将其作为“装缀”,亦不能“全然不理”[12]23。就此而言,良知并不能离于见闻,而须见闻之知以助发。
事实上,良知与见闻之知皆源于本心,故两者拥有共同的本原,但又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良知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为“大知”;见闻之知“才有执着意必,其知便小矣”[12]93。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见闻之有无与知识之多寡,而在于见闻有无私欲执着之染污。若无私意执着的染污,则见闻皆归于良知之流行。阳明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12]78故阳明并不反对多闻多见,只是认为见闻应以致良知为本。他甚至认为,“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12]78。良知流行而为见闻,见闻之外并无良知可致。人若能在见闻酬酢之际,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无一毫私欲执着之遮蔽,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12]134。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废绝知识以成就良知,而是应破除知识中的私欲执着。若能如此,则知识当下即可转变为良知的流行,是为心学的“转识成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良知与知识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非一非二的关系。在根本上,知识依于良知而有,但知识形成之后即有其独立的地位。但知识若失却良知之指引,则易助长人之恶行;知识若为良知所指引,则成为良知之发用。因此,既不可将致良知与求知识截然对立,也不可将两者混为一谈;致良知者需要求知识以增长智慧,求知识者需要致良知以回归德性。进而,阳明试图和会朱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在他看来,尊德性与道问学其实只是一事,“如要尊孝之德性,便须学问个孝;尊弟之德性,便须学问个弟。学问个孝,便是尊孝之德性;学问个弟,便是尊弟之德性。”[12]1 547尊德性不能离却道问学,是为“良知不离于见闻”;道问学不能离却尊德性,是为“良知不滞于见闻”。因此,不是尊德性之外别有道问学,也不是道问学之外别有尊德性,两种工夫不容割裂,实可以相互资益。
四、结语
要言之,心之虚灵明觉即是本然之良知,其发动而有意与物之间分离,故良知实为认知活动生成的源初场域。良知既为吾人先天之心体,不因后天之见闻而有,故其能“不滞于见闻”。本心发动而为意识之时,则有意识与外物的分化。意识活动的发动者视为主体,其所指向之对象则为客体,主客相合而有“知识”。因此,良知虽为认知活动的“场所”,但并不能直接开显出知识。确如牟宗三所言,知性主体的建立,需是基于良知之坎陷,只有在意、物的分化处,方能有所谓的“知识”。知识的形成既然依赖于内外之因缘,那其必定具有相对的性质。但是,知识的形成在根本上源于本心的作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正是由于主体间性的作用,知识不但具有客观的性质,也具有独立的地位与价值。知识依于良知而生成,又不断地敞开经验世界,充实着良知的具体内容。
但是,知识毕竟基于主客的对立,故有可能遮蔽良知,故需良知以作为指引。同时,良知毕竟要依于见闻,方能有客观的呈现,故良知亦不离于知识。因此,问题不在于知识之有无,而在于有无意识之执定:若有意识之执定,则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若无意识之执定,则知识成为良知之发用。故而,心学区分良知与知识,自有其理论上的重要意义,不但保住了知识的独立地位,也回答了道德如何可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阳明“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之说,乃是一种即知识而超越知识的中道知识论:一方面,他虽然重视致良知的工夫,但非以良知消解知识,从而陷入泛道德主义;另一方面,他看到了见闻之知的作用,并未排除知识的进路,而是在承认知识价值的同时回归良知本体之澄明。
参考文献:
[1]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补编[M].束景南,查明昊,辑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2]冷天吉:知识与道德——对程朱、陆王、船山格物致知思想的考察[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3]赵卫东.分判与融通——当代新儒家德性与知识关系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6:83.
[4]丁为祥.宋明理学的三种知行观——对理学思想谱系的一种逆向把握[J].学术月刊,2019(3):5-16.
[5]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0:296.
[6]刘述先.理一分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119.
[7]彭國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M]. 北京:三联书店,2005:377.
[8]张学智.王阳明研究的知识进路[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4(6):36-39+118.
[9]张明,王建明.“成色”与“分两”:阳明心学视域下的德艺观[J].教育文化论坛,2020(3):43-48.
[10]刘荣茂.“游艺”与“养心”:阳明学派的知识面向——以顾应祥、唐顺之为中心[J].哲学与文化,2020(6):167-178.
[11]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278-284.
[12]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新编本.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13] 西田几多郎.西田几多郎哲学选辑[M].黄文宏,译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163-164.
[14]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571.
[15] 王畿.王畿集[M].吴震,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6]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10.
(责任编辑:杨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