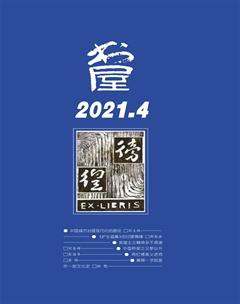再忆傅高义老师
当2020急景残年之时,美国再掀狂澜的新冠疫情加上晴天霹雳般的傅高义老师噩耗,令我多日寝食不安。天地苍茫,凛冬已至,临风怀想,不禁百感千端萦怀,于年末写下悼诗一阕:
悼傅吟
惊闻哈佛傅高义教授骤逝,哀感无端。傅者,父也。傅老师唤我为“中国儿子”,我们见面必以“父子”相称。
天涯枯辙颇离枕〔1〕,厚衾暖月忘夜沉。
树蕙唯知荫涸泽,滋兰但识解危心。
诗存诸往启来者〔2〕,文立孤标试石金。
牛渚〔3〕溯源悲俛仰〔4〕,登舟空忆泪沾襟。
〔1〕颇离枕,见温飞卿:“水晶帘里颇离枕。”古指留宿处。只身留美第一年后,洛城加大因故忽然断了原来承诺的奖学金,傅高义老师马上把我邀到哈佛担任研究助理,并请我住进他的家中。
〔2〕《论语》:“诗,告诸往而知来者也。”
〔3〕牛渚,寓“知音遇合”。语见《世说新语》:晋朝贫士小工袁宏于牛渚遇谢将军赏识的故事。李白诗曰:“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4〕王羲之《兰亭集序》:“俛仰之间,已为陈迹。”俛仰,即俯仰。
此诗,又引出了更多的久远追忆。
1980年,因为傅高义老师的热心建议和推荐,我方才有改变人生走向的赴美留學旅程。但我当年从洛杉矶加州大学到哈佛大学——自太平洋至大西洋的“两洋水”之行,却有许多琐细关节不易言述。比如,我的“哈佛生涯”,说来其实是“二进哈佛”,一如上述注释里所言:1982年春我抵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读研一年后,因指导教授学术休假一年,校方竟然中断了原来承诺给我的奖学金,我的学业一时陷入中断尴尬,生活也处在孤立无援之境。时任哈佛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的傅高义教授听闻,马上给我寄出了东亚中心的正式邀请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邀我担任他的研究助理,并请我住进他在哈佛校园的家中,不但一解我的燃眉之急,也因之打开了哈佛学府的高槛大门。哈佛一年后,加大的指导教授学术休假结束回返校园,他马上设法帮我争回减免学费的奖学金,我于是又在1984年秋天回到加州大学校园,继续修读完成我的东亚文学硕士学位课程。加州大学采用的是学季制(三个月为一学期)。我于1985年夏天获得硕士学位后,傅高义老师又一次邀请我再赴哈佛,同以访问学者身份受邀到费正清东亚中心,并再次住进了他的家,继续担任他的中文研究助理。
两次进出、头尾两年半的哈佛访学生涯,与傅高义老师夫妇的朝夕相处,成为我当年的留美经历中学旅最充实、“含金量”最高的“高光”段落。因为“哈佛”天然具有的高台阶与宽视界,还有“访问学者”身份的选课自由与时间宽裕,我能有机缘把自己完全浸润在跨学科的书籍学养的海洋里——参与和旁听东亚中心每周的各种与中国有关的讲座,以及住家附近的犹太博物馆、艺术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与科技馆随时举办的各种活动(科技馆的电影厅是我最常流连的场所,可以免费观看各种新近流行的电影和文献片)。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占据了书库角落的一张固定小桌,把书库各门类自己列了计划要读的书籍择出堆在一角,那里是我每日潜心读书写作的僻壤静界(我的留学生小说集《远行人》的大多数篇什完成于此)。我以哈佛身份证购买了“美利坚即景剧场”的年度演出季套票(看六场演出只需三十八美元),两年间几乎看遍了当时在哈佛上演的所有先锋实验戏剧(由观剧引发,1988年北京《读书》杂志以连载五期的大篇幅,刊发了我与画家袁运生共同署名的“关于西方现代艺术的胡言乱语”系列);忘记是哪一位学长建议,我还曾多次到建筑学院的阶梯课室旁听设计比赛评图,记得其中一次是围绕波士顿市政厅的改建设计方案评图,各种标新立异的设计及其激烈火爆的争议让我大开眼界,用今天网络语汇,则是“脑洞大开”。更不必说,对于我这位古典音乐的“发烧友”,圣殿般的波士顿交响乐厅和哈佛纪念堂音乐厅以及那个闻名遐迩的超过百年历史的哈佛男声合唱团,那一场场无与伦比的音乐会了。特别是,与“文革”后最早留学哈佛的第一批中国大陆人文学科的学兄学长如赵一凡、张隆溪、巫鸿、叶扬、冯象等的日常交往交流,还有哈佛华裔教授如张光直、杜维明、赵如兰等对我们的关照教诲,所给予我的特殊滋养了(那时候杨联陞教授还健在,可惜与我们交集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据张光直教授告诉我,每月最后一个周五在赵如兰教授和陆惠丰教授家轮流举行的“康桥新语”华裔文化沙龙(开始叫“康桥夜谭”),就是他们几位哈佛华裔教授有感于校园内的中国大陆和台港人文留学生愈来愈多,特意为促进美中多地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而用心开设的。“康桥新语”沙龙日后成为坚持数十年、在美国东部院校名声显赫的一个文化景观,东部各校许多名家教授与博士生都常常闻风而至。我呢,当时是沙龙里的“茶童”,大家叫我“茶博士”(Dr.T,借用当时电视肥皂剧里一个搞笑角色的名字),专门负责给与会学长们沏茶递水和递送每晚的夜宵八宝粥。
正是傅高义老师为我敞开了哈佛学宫的大门,使我得以纵情畅游在知识与学术的溪涧、河川与海洋里,像海绵一样、花蕊绒毛一样,吮吸着科学与人文的诸般雨露阳光和精神养分,完成自己去国前夕立下的“把自己彻底打碎,再重新捏吧回来”的生命重塑宏愿。这是傅老师赋予我这一生命的奇迹,我将感恩终生,铭记终生。
我当然知道,近时坊间对傅高义老师及其学问文章的评论见解趋于两极化。而对此“两极化”议论最敏感、也最能包容的,恰恰正是傅高义本人。记得2011年秋天在耶鲁,傅老师把两大厚本的中、英文版《邓小平时代》赠予我的当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对我这本书的评价,无论在美国或在中国,都有两极化的评论。喜欢的,有很高的评价;批评的,也把话说得很重。其实,这两方面的意见,我都很了解,也很能理解,虽然我仍旧是坚持自己的基本判断的。他在耶鲁关于这本书的讲座上的开场白,也是重复说着同样的话。而傅高义老师多年来多次对我说过的——正如他一直在美、中、日三个文化、政治系统里身体力行地在做着的——则是他重复多次的另一句话:“Bridge。”“我一直想要做的,就是在各种两极化的看法和差异之间,搭建一道桥梁,我做的就是桥梁Bridge的工作。”他早年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是如此,近年的《邓小平时代》更是如此。近时坊间很多谈论傅高义的文字,会引述笔者前述拙文里提及的傅老师对我谈到的从“局外人”(outsider)到“局内人”(insider)的角度,以及“在中国语境中去认识中国”的意见。但上述话题,其实每次都是在傅老师提及他最喜爱的一位学生——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时提及的。他多次向我感慨:他是从Perry身上,领悟到这个要从“局外人”转化到“局内人”的角度去认识中国的道理,这就是“在中国语境中去认识中国”的意思。在我看来,无论傅高义或林培瑞——我深为熟悉的这两位观点去向或许不一定一致的洋人汉学家,都是两位极难得的、真正爱中国、“把中国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的人。林培瑞是“爱之深而责之切”,而傅高义则更多地取“了解之同情”的角度。关于这个“了解之同情”的说法,傅高义老师也曾在好几个访谈中提及。此说,其实出自陈寅恪先生三十年代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的开篇:“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而在陈寅恪先生之前,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言里也曾说过:“(读此书)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了解之同情”与“温情与敬意”,用傅高义老师自己的语言,就是做“Bridge”——搭建在国族与文化差异中的交流交通的桥梁。或者,也就是近期许多回忆傅老师的文字里不断提到的“同理心”与“共情能力”吧。
都说“岁月不欺”。但岁月却常常欺负我们的时光记忆——对许多时间节点的追忆,会发生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误差。比如近时纪念傅高义老师的诸篇文字里都提到:他是于2000年自哈佛大学荣誉退休的,那件印有他的漫画头像的T恤上也有“2000年退休纪念”的字样。但因为我记得自己的父亲是2003年末去世的,我在文中提到的,在傅老师称我为他的“中国儿子”的那个酒会上,我明确提到了自己刚逝去的父亲,这样的记忆又是异常清晰的(我甚至记得我当时用的是什么英文单词去表述),那就应该是2004春天的事情啊。难道,那次活动,不是2000年傅老师荣退的哈佛酒会,而是日后哈佛大学专门为纪念傅老师退休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的酒会?(耶鲁史景迁教授荣退一两年后,耶鲁校方也专门为此筹办了一个专题学术研讨会。)我也只能这样去解释自己的记忆浑误了。
附录一:
我写给傅老师夫人Charlotte Ikels(艾秀慈)的悼念卡的文字(中文本):
Dear Charlotte,接到傅老師骤逝的噩耗,我和妻子孟君都震惊哀痛不已!悲伤的心情至今没能平复。傅老师是我生命中的贵人、灯塔和人生的楷模!他不但是搭建在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一座美好的文化桥梁,也是照亮我生命的一道美丽彩虹。他真的是我的“美国爸爸”,而我也以能成为你们的“中国儿子”为荣!我深深感受到您的哀伤和震撼,请接受我和孟君的深切哀思与安慰,和对傅老师永远的怀念!
您们的“中国儿子”苏炜和孟君
2021年1月2日于耶鲁
附录二:
我们的“中国儿子”
——为苏炜的中文著作序
傅高义
当1980年我第一次能够踏入中国去做研究的时候,我和我太太Charlotte Ikels教授住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我们作为大学的客人在中大校园住了两个月。在那期间,我们可以参加中山大学的一些活动,并对广东做一些初步的研究,参观学校、公社和工厂。
就在1980年的那个夏天,我有机会认识了一些中山大学的教授和学生。苏炜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苏炜当时是中文系文学专业的,他是学生文学杂志《红豆》的主编。他很有文学才情,已经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我和我太太看到,那时的苏炜有很多朋友,在中山大学的各种活动中表现很活跃。那时候,正是1977年恢复高考不久,一些大学的教材还没有全面修订,大学的许多建筑也比较老旧,正在修复中。苏炜向我们介绍了大学生的生活。那时八个学生住在一间宿舍里。学生的伙食非常简单,穿着也非常朴素。每天早晨都听到高音喇叭在播报新闻。校园里没有电视,当然更没有手机。
在我们抵达中国之后的那些年里,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是高中毕业那一年进入大学的。但是苏炜却不同,他在那个年龄时像很多其他同龄人一样正在农村插队,他和众多在农村插队的学生一起准备高考,最后通过考试才进入了大学。虽然苏炜的年龄比那些高中一毕业就上大学的学生大一些,但是他的气质仍然像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他的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总是带着渴望学习的光芒。
苏炜成长于广州一个大家庭。我们后来有机会认识了他的家人。他们当时住在广州一个比较简陋的家里。他的家人看起来都是知识分子,他兄弟姐妹中的大多数都考上了大学。当时的大学生都很害羞,不习惯也不太敢跟外国人打交道。苏炜却很愿意与我们见面,帮助介绍中国的情况,告诉我们他“下乡知青”的经历。他解释说,他当“下乡知青”,是因为他当时被下放到海南岛的一个农场。我和我太太后来得到许可,可以去海南岛参观;而苏炜也被允许陪同我们一起去海南,回访他当时下乡的一个有名的国营农场。那里有一个国家热带研究所,位于苏炜下乡的农场附近,对许多国营农场的橡胶树进行研究。
苏炜带着我一起回到了他曾经下乡的村子。那是苏炜离开已经四五年以后第一次回去。当一个老农看到苏炜时,立刻大叫“苏炜!”然后紧紧抱住他,就像抱住一个多年不见的儿子。他看到苏炜非常高兴,苏炜也非常高兴,他们真的像是分别了多年的父子一样。
我在中山大学认识苏炜几年以后,苏炜作为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进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以后,他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许可,并成为我的研究助理。
苏炜在哈佛大学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住在属于我和我太太的房子的一个房间里。那时我自己的孩子都已经上了大学住在别的地方。我和我太太真的把他视为我们的儿子。即使苏炜已从中山大学毕业,并且获得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硕士学位,他仍然保有一个年轻男孩的活力和好奇心。那时苏炜又继续发表了一些小说,他用中文和我谈话,通过帮我阅读他写的小说,来教我学习中文。在哈佛期间,苏炜有很多朋友都是中国学生。他的房间成了中国同学晚上聚会的最佳地点。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美国的生活和在中国的经历。
苏炜还在继续写他的小说和散文。我和太太都为他能在耶鲁大学教授中文感到非常骄傲。我从我们的耶鲁朋友中听到,他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老师。我们也为他的长篇小说被翻译成英文并正式出版感到异常兴奋,同时我们也为他中文精选文集将要出版,感到由衷的兴奋和骄傲。我们仍然认为他是我们的儿子——“干儿子”。
2018年5月23日于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