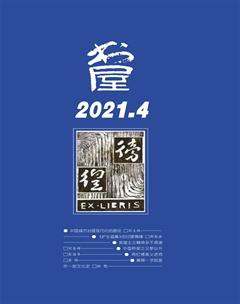熊希龄的“诗教”
秦燕春
一
湘人被视为国土疆域中性格甚为鲜明的一类。钱基博先生直以“地气刚坚,民风强悍”拟之。但诚如深知湘人根底的沈从文所言,此地于激进与保守两路常各趋其极。我的理解则是,激进或守旧,取舍并不第一重要,一旦取舍则一定要“趋极”,或者才是此地人最有风格的选择。也正因此,某类于“趋极”之风中极力“守中”且同样是用“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趋极”的力道来“守中”的人物,湘省就尤其难得。
这种心性特别又典型的湘人,湘西名城凤凰第一个中进士点翰林之人、之后更成为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便是极好的典范。
熊希龄紧凑忙碌的一生中充当过各种要角。不仅1898年“湖南新政”年少气盛是核心骨干,不少要务都一任在肩、奔走在先。即使经历了“戊戌政变”被革职管束,他也尽力襄赞地方教育乃至专注实业,更在1903年赵尔巽专折保举复出后,高调参与了“易代之际”许多关键时刻。1913年8月受命出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算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峰,却短暂仓促而祸乱丛生,仅仅维持八个月,1914年2月他就在一片羞辱声中辞职下台。对于这位视“保全名节”直如“八十老翁过危桥”(1910年3月9日致熊燕龄、熊岳龄函)的传统儒士而言,他的伤痛一定苦不堪言。
这其中悲欢,熊希龄并非没有预感,“今以浮暴之徒,造成一寡廉鲜耻世界,虽孔子复生,无补于世。希龄拟俟蒙边少定,即归营实业,不复与闻政事”,所谓“与现在之暴烈分子、腐败官僚两派绝不相容”。因此,这民国总理任上又带上了些“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特有的悲壮色彩。
1914年,熊希龄辞去国务总理及财政部长后于民国政坛渐行渐远,转身继续他早年热心亦擅长的教育工作。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平民教育之外,1920年10月,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收孤贫儿童的“香山慈幼院”的成立让熊希龄投入了余生大部分精力。身为世界红十字总会中华分会会长、南京国民政府赈款委员,在一波接一波的天灾人祸、战火纷飞面前,熊希龄照样任劳任怨,一秉其“实干”、“傻干”乃至“硬干”、“穷干”精神埋头做去。
价值判断与道德观念经常陷入混乱的清末民初时局,对熊希龄这种实干心性其实很不利。他不仅经常要背上些莫名其妙的骂名、例如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参议会中激进派人士视其为“前清猾吏”,也似乎因此很难有舒舒服服施展拳脚的余地。叶景葵在《凤凰熊君秉三家传》中叹他“平生似遇而实未遇,欲有为而终不可为”。揆诸其一生际遇,可谓知根底语。
因为“无可如何且洁身,保全人格作诗人”(《题画菊》)的现实无奈,一生自负“办事”而无意文学的熊希龄居然也留下了不算单薄的诗词作品,至于朋友都会刻意提醒这位“实干家”不要搁意于诗:
经济文章付外篇,独将吟玩遣华巅。
苍生犹望资霖雨,不信山泉老偓佺。
身为功底深厚的翰林学士,熊希龄如果试图吟风弄月,他并非没有机会。但他的诗词就是他的性情,一以贯之。庚子年(1900)因政治变故避处湘西,《题蜀葵》中“物生原不贵,劲节始能奇。夕影虽偏向,孤心终不移”,以及《题雨景山水》中“故山千万叠,烟雨暗难开。不畏风波恶,一帆归去来”,都是励志语。1930年,好友谭延闿过生,熊希龄写下《金缕曲·戊辰冬寿谭祖庵五十生日》,称道谭氏“十七年来坚苦事,要全凭旋转乾坤手。容与忍,是首功。书生故态犹依旧。共流连,笑谈欢乐,顿忘昏昼。末路故人多变节,谁是始终成就?真不负平生操守。”坊间广为流传关于熊希龄早年画“木棉花”自题“此君一出天下暖”的故事更像后世针对慈善家生平志业的事后盖棺,未必真实。倒是谭延闿本人写过一首极耐人寻味的《豆花》诗:“自是人间有用身,不矜香色斗芳新。城中何限闲花草,只与游蜂哄一春。”用来形容熊希龄一生包括诗词写作,居然都十分允当。
熊氏诗词风格稳健遣词端庄,据说丹青也颇见功夫,但他显然并不在艺事上太花心思,甚至早年还自谦称“本无学术,只管办事,不知其他”(1898年7月15日《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这并不妨碍熊氏诗学其实饱含了丰沛的精神意义:一位传统中国老派士绅特有的价值关怀,作为核心与基本的人格养成与情性化育,自然而然于诗学世界中丰沛流溢,并进而反身润泽其精神质地。
二
一生以其特有的实干、傻干乃至硬干、穷干精神锲而不舍救国救社会的熊希龄贡献最为卓越者最终落实在了慈善教育。甚至对于教育,他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破坏原为建设初”,对于清末民初这最先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儒者而言,现实的业力汹涌显然远远突破了他们的精神預期,例如民初新进政治人的教育素质令他深感意外,“瓦釜雷鸣钟毁弃,不堪重读老人书”(《题顾子用所藏马相伯先生序稿》),连教育也都已经很难维系他们曾经熟悉的理想教育了。
曾经对新建的民国怀有与时俱进希望的熊希龄被民初政局的翻云覆雨伤透了心,尽管当此乱世他算得上大节无亏。1926年12月3日,熊希龄写下《丙寅十月二十九日为淑雅夫人五十初度赋赠》长篇叙事诗,于中基本涵纳了自己五十六年来的系列遭际与反复思考。“余志在澄清,反为操莽嗾”可谓是民初最后的士人一片伤心之语。他不是不懂得,也不是不明白,只是他此刻仍然必须选择“澄清宇内”的有为法,这是传统之“士”的宿命。
熊希龄自知在逆流而动,“历尽冰霜气未孱,晚霞天半拥朱鬟。可怜世界皆成紫,独有孤山不改颜”(《为叔通画朱菊并题》),却至老豪气不衰,“奋斗艰难已半生,斩蛟射虎气纵横。回思三十年前事,梦里犹闻击楫声”(《题三十年前照片》)。于此,必须考虑到他独特的近代湖南气质,所谓学必“经世致用”,所谓“龄本草人,生性最戆,不能口舌以争,惟有以性命从事”(《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所谓“实际能医读死书,古人曾有带经锄。埋头硬干和穷干,怯弱身心病自除”(1934年10月3日《甲戌八月廿五日平民教育促进会景慧中学校纪念熊朱其慧夫人寄赠》)。
1919年因为调停“南北和谈”失败被指为“五四运动”的幕后推手,熊希龄伤心宣布“迩来厌倦政治已达极点,且深觉世界虽变,人心不变,政治社会均属罪恶之薮”(1919年5月17日《声明退出和平期成会不再过问政治致和平期成会联合会电》)。但终其一生他都没有真正放舍过“天下”。1910年写给兄弟的信函中尚有如此温热的关怀:“盖吾人所担当者,国家之事,关系于公众安危,非一人一家可比。故以世人比兄弟,则兄弟为亲,而以国家比兄弟,则兄弟为轻,国家为重也。……古人云:公极则私存,义极则利存。义利之界不容紊也,紊则求荣反辱矣。……夫人当境遇困难时,愈宜站定脚跟,不为利动,不为苟且之事,方是豪杰。”(1910年3月9日《批评其不识大体致寿峰三弟捷三七弟函》)
兵荒马乱的生民流离在熊希龄不足古稀的一生中基本一直都在持续。他日常生活的具体感受就是“头绪纷纭中,挂一恐万漏。东扶西又倒,此起彼又仆”。对于民生疾苦,他始终就是“放不下”。这是不能“放下”,更是不肯“放下”,这是儒者的“民胞物与”,更是佛门的“大乘菩萨”。因为“彝师、泽老均已化去,仅余鄙人,奔走道途,一事无成,殊有愧于作者矣”(1915年9月1日《告知旅途情况致朱淑雅夫人函》),对于他所继承的传统而言,“神州袖手”都是无法接受的逍遥,他一定也应该继续“有为”,即使这“有为”需要不断调整、经常饱受委屈。
关于不再参与彼时愈演愈烈的军阀政治,熊希龄是毫不动摇的,写于1918年的《戊午和赵式如双清别墅原韵》中他视此退步抽身为具有自知之明的急流勇退、壮士断腕之举:
树色山光雨后匀,长松不改四时春。
双泉石上湍流急,似策当机勇退人。
但退出政界乃至实业都绝不意味着放弃责任。他一直在各个领域埋头苦干,更时时都在努力体现一种“忘我”的精神、探索一种以“无为”、“出世”之心行“在世”、“有为”之法的可能性。1917年1月5日他写下《登泰山绝顶观云海》,即表达了这种于“真空”中行妙有的愿景。1918年的《戊午旅行江南题栖霞寺天女散花图》同样毫不犹豫宣称自己投身苦海的决心:“扰扰何时见太平,众生苦痛已非轻。原凭妙手回春力,不治维摩治众生。”
时隔四年之后,香山慈幼院已成立有日,《游森玉笏》(1922年5月)再次重申了这一发愿:“远看塔影漾湖波,又听群儿唱晚歌。唯念众生无限苦,万松深处一维摩。”
虽处居家而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却常修梵行的维摩诘居士是他追随在心的表率。如何能够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直心正念真如,亲证平等实相;具足恒沙烦恼无量功德,起方便教化,使一切众生除心源上之烦恼、显心源上之功德。这应该是深喜佛教的熊希龄最看重的。
三
发愿尚属容易,一生坚持甚难。无巧不成书的是,熊希龄早年有个斋号即是“有恒”,正见其心志。熊氏生命最后二十年操持慈善幼教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艰苦备至。借着他善于实务的实干、傻干、硬干、穷干精神,他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
罕见的是,熊希龄正面批评1919年前后发起的这波“新文化运动”,但这位晚清新政曾经最勇锐无惑的老“运动员”于此的实际批评恐怕无所不在:“近年国人浮慕文明,偏重物质主义,对于精神教育弃之不顾,虽学业技能皆有所长,而于人情物理毫无常识,即饮食、居处、言语、动静、应对、进退之间,亦觉其杂乱粗鄙,无秩序,无条理,无轻重,无缓急。”(1928年《慈蒙新课本序》)
香山慈幼院坚持“教育意义,重在审辨真伪,明定是非,若因回避责任而自欺欺人,即属教育破产,人格破产”,养成“人格”一直被他视为无论践行教育理念还是养成社会环境的最重要标准,“养全他的廉耻”成为慈幼的核心(1922年6月《香山慈幼院创办史》“现在的缺点”)。依其慈爱细腻的天性以及与时俱进的精神,传统教育出身的熊翰林甚至对于儿童的天性应该如何顺势而教,都有入微考量。而从对“学生自治会”的效果深感满意可以看出,熊希龄依然是那个晚清时期最乐于和西方对接的新锐的现实派。
他很传统,看重“妇顺”的美德,但他又有很现代的一面。1928年侄女生日他写诗以祝,重申“贤母良妻”时论之外,更强调“蒙养”与“母教”的关系,对女性做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充分尊敬:“家事即职业,工作独女负。男实依赖者,是言诚不谬。”1929年他亲自撰写《慈幼院女校上工歌》中也表达了这一思考:“一家生活女当冲,男儿何有功?亲井臼,习烹缝,尤须薄记工。”
熊希龄生命后期对“平民教育”投入甚多,一则配合了清末民初启蒙救亡的时代趋势,二则,其实是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生灵涂炭的现实压力让这位“务实”的干家不得不先顾吃紧处,完其慈悲救世的一腔关切:他先后创办了北京北洋平民工读学校、湖南平民大学、长沙兑泽学校、孔道学校。1921年12月与蔡元培、黄炎培等人创办中华教育改进社,1924年8月由其夫人首倡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靠什么支持此际人类摇摇欲坠的精神世界?儒学之外,熊希龄对佛教的好感与亲近是毋庸置疑的,这也同时成为他一生最强有力的思想支柱。
1898年,那场大病之后,对于因缘果报之说就颇令熊希龄生信好之心。1916年4月11日,身在常德的他写给夫人信札中已经在明确索要“余之佛教书”。对于熊希龄一生的意义取舍而言,他是佛徒还是儒生,或者对道教是否有实践都不是第一要义,关键在于他一直坚信“信道创于前,行慈继于后”。早在1910年1月15日写给堂弟熊岳龄处世产业函中,已经涉及如下几个熊希龄待人处事的原则:其一,“(合于商业破产之法)即问之于心,对天地鬼神而无愧”;其二,“吾辈做事,只要合理,即格外险阻,亦复何惧”,“信之一字胜于身命,苟合乎义,即为弟事挂误,亦所甘心”;其三,“古之君子,惟患难乃见其真”,“艰难仗友生”。无论“天地鬼神”还是“合理”守“信”,都是恪守现实标准之上还另有道义原则,对于熊希龄和他稔熟的文化传统而言,人格教育原本就关乎信仰问题。
“法到圆时犹应舍,虚空粉碎有何哀。”(《游台山中台》)因为这种信仰的力道,熊希龄埋头“办事”的一生——他有多忙,看其一生存世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各种电报公函,最可见得逼真——主调与基调始终都是积极光明的。佛教中“色身非净,法相非真。四大和合,亦非我身。何物為我,我实不存。我既无我,朽骨何灵?凡相虚妄,焉用佳城”的基本理则,对于熊希龄的生命状态,并无消极避世的味道,而是一直向更积极救世的层面转化,此即1932年春《为香山生圹自撰墓志铭》中的宣称:“今当国难,巢覆榱崩。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誓身许国,遑计死生!或裹马革,即瘗此茔。随缘而化,了此尘因。我不我执,轮回不轮。”
因为活泛而务实的性格,熊希龄并不拘泥于自己的背景与趣味,他考虑到学生未来的就业情况,主张香山慈幼院行白话教育——回思清末“湖南新政”中的类似举措,则熊希龄实在是晚清最勇锐新进之人。他自己后期经常为婴儿教保院撰写白话标语对联,亲自用“醉桃源”词调为香山慈幼院的孩子写下《上床歌》、《下床歌》、《饭前歌》、《饭后歌》、《上课歌》、《下课歌》等系列口语化的歌词。这位按理只会将“玉米”称作“苞谷”的湖南翰林,居然学会了使用“棒子”这个北方民间称谓!
1937年,在“淞沪抗战”的枪林弹雨中,一生务实年近七旬的老人每天坚持打坐,却依然坚守在救亡一线,一如既往做了许多琐碎朴素、没有华词丽句却件件人命关天的事:
当战事初生时,亦有劝余远走者,余以老病之躯,又无官守言责,本可行就安全之地,但以国难当前,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以求其良心之所安,故决计留沪,与红十字同仁从事救护工作,设立临时医院四所,难民收容所八所(此专指十会而言,其他团体尚有百余所),共救出伤兵千余人,难民十五万余人。
这是熊希龄1937年9月20日身在沪上写给内侄朱经农的信。仅仅二个月之后,他遽然病逝香港。
因为暮年豪举,所谓“艳词清福”,熊希龄六十六岁高龄续弦子侄辈的毛彦文还留下生命中空前绝后一批“情书”而令后人议论纷纷。其实,熊希龄性格的真挚细密同样体现在私生活,例如他终生反对纳妾。熊希龄垂老和毛彦文结合更带有寻觅志同道合“同志”的意味——在其身后继续他和亡妻坚持多年的“香慈”事业。情路坎坷而又恩深意长的毛彦文“有协助他办理此事的能力、热情与爱心”。至于何以诞生了那些和熊希龄绝大多数诗词风格迥异的“艳情”之作,这其实要从毛彦文本人的情感际遇讲起。经由这段婚姻,我们会有机会见识到“凤凰才子”共感共情的精神风姿。熊希龄不仅是清末与民国在政治、实业、教育皆能独当一面的科举能人,就其处理与毛彦文的感情的方式而言,他更像全新的人物——或者我们不妨说,传统文化养成的儒者与君子也并不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爱的能力”。这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