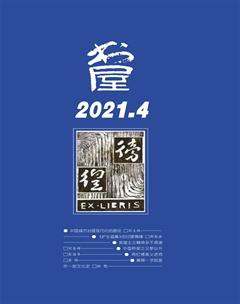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杨昌济
夏剑钦
“学通中外,道冠古今”,这是杨昌济于1917年上期应聘到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课初次与学生见面时,校长汤松在教室黑板上书写的八个大字。汤校长接着介绍说:“杨先生在英国和日本留学九年,对于中国固有的学问,也有很深的研究,真可说得上学通中外。而且具有崇高的品德,和社会革命的伟大精神,秉公持正,实践躬行,说他是道冠古今,确非谀词。”
杨昌济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也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父亲,更是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湖南新文化运动骨干的精神导师。他一生“好学之笃,立志之坚,诲人之勤,堪为师表”。他痛恨封建制度,向往社会改良,追求民主自由,崇尚众庶平等,利用讲坛宣传新文化,批判封建文化。他勤于著述和翻译,利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发表文章,介绍西方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并联系国内实际,提倡民主和科学,宣传新道德。据毛泽东回忆,在当年最敬佩的老师当中,杨昌济是“印象最深的”一位。1936年,毛泽东同记者斯诺谈起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情形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西行漫记》)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昌济不愧为中国革命伟大领袖和导师的导师。
非改革不足以图存
杨昌济(1871—1920),辈名宏棻,字怀中,号华生,册名昌济,出生于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今开慧镇开慧村)下屋杨家。杨家原居于长沙县金井的蒲塘,据《蒲塘杨氏族谱》,是十三世祖杨世纶高祖父于清乾隆年间迁居清泰都板仓冲的,并逐渐成为一户耕读之家。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田,庠名万英,是“邑庠生”,他们都有了俗称“秀才”的功名。祖父杨象洛,字书翔,又作书祥,读过不少古书,但积学不第,曾捐过一个“例贡生”,终生以授徒为业,关心时政,是儿子的蒙师。母亲向氏,是平江县石洞书香门第向泰椿之女,其祖上鲁斋公为理学名儒。长兄杨昌运,字荣生;一个姐姐;弟弟杨昌恺,字瑞生,过继给叔父为子。杨昌济排行第三。
杨昌济自幼发愤读书,效仿古人闭门不出,持之以恒,且聪慧不凡,故七岁发蒙之前,就能背诵不少古诗。后在父亲这位塾师的调教下学习“四书”、“五经”,还阅读了周敦颐、二程、王阳明等人的宋明理学著作和曾国藩的著作。光绪十年(1884)他父亲逝世。1889年他考上“郡庠生”(秀才)。嗣后,他于1890年、1893年两次参加乡试,想考上举人,均未能如愿。其间,他曾在长沙城南书院读过一段时间的书,并在那里结识了同族青年杨毓麟,认为他“固工文辞,有远识,其不可及处,尤在其言有物,出于至诚,盖并世所罕觏也”,后对自己的影响很大。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湘人自湘军以来的虚骄之气顿挫,使杨昌济的思想也受到很大震动。“自马关合约缔结以后,国中人士知非改革不足以图存”,所以他也很快投身到湖南的维新运动。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不顾山长王先谦的守旧、反对变法,积极参加了谭嗣同等人组织的南学会和不缠足会,并经常出席南学会举办的讲演会;所撰《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一文,被南学会评为第三名,并刊载在《湘报》上。
在這一时期,杨昌济结识了谭嗣同,对谭氏提出的维新改良主张热烈拥护,对谭氏敢于“冲决网罗”的大无畏精神十分敬佩,对谭氏“以民为主”的民主思想和“仁以通为第一义”的哲学思想衷心服膺。从这个时期杨昌济的日记,可知他不仅读了谭嗣同特别推崇的王船山著作《读通鉴论》、《宋论》和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等,还认真研读了以“张三世”为改良变法理论依据的《春秋公羊传》。同时他还刻苦自学英文和日文,准备出国留学。
戊戌变法的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被害,给杨昌济以深刻的刺激。他一方面更加钦佩改革者的爱国热情与牺牲精神,“觉得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论语类钞》);一方面从失败中总结教训,认识到变法图强光靠“自上而下”是难以成功的。其《达化斋日记》曰:“法之变有二,有变之自上者,有变之自下者。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今者上稍稍变矣,然而不可恃也,非不可恃也,吾不在其位,则吾为无权。”而要“变之自下”,就必须“竭力学问、竭力教化”,要变科举、变学校、变学术,而“变学术,变之自下者也”。最后还必须依靠“小民”的力量,使“民智大开”;而要开启民智,就必须用“世界之知识”以“指导社会”,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才能使社会进步。为此,杨昌济于1902年参加赴日留学考试,获官费留日资格,于1903年2月踏上了留学日本的征途。
寻求知识的世界之旅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杨昌济与陈天华、刘揆一、朱德裳、石陶钧、陈家瓒、吴家驹、曾继梧、廖楚珩等人一道,从长沙乘船赴日本。这年他三十三岁,为同行中最长者。启程前改名“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五日十时发长沙,十二时泊三汊矶。十日,买舟登岳阳楼,杨昌济作题壁诗曰:“大地龙争日,英雄虎变时。苍凉万里感,浩荡百年思。日月自光曜,江山孰主持?登楼一凭眺,此意竟谁知?”同行者朱德裳认为此诗绝佳,“盖绝类谭浏阳先生云”(朱德裳《癸卯日记》)。一路上,杨、朱二人讲求文字、西文字母及拼音之法,学习英文,并且相约:“在东京除上讲堂外,以译书为私课,随译随印,以饷同胞。”二十九日下午一点抵达日本横滨,三月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科。
1903年前后,来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特别多,且多有一种执着的忧国之心,他们在日本办的刊物达二十多种,其中有杨度、杨毓麟等湖南留日学生创办的《游学译编》。该刊以政治革命、种族革命为宗旨。1903年5月,杨昌济的《达化斋日记》部分在《游学译编》发表,宣扬个性解放,尊重个人理性,“天地万物,以吾为主”,并强调变法维新。同到日本的新化人陈天华在1903年夏创作的《猛回头》初版后,便在当年10月《游学译编》第十一期刊登了“再版《猛回头》”的广告,称:“是书以弹词写述异族欺凌之惨剧,唤醒国民迷梦,提倡独立精神,一字一泪,一语一血,诚普渡世人之宝筏也。初版五千部,不及兼旬销罄无余,因增订删改再版。”陈天华随后又写出《警世钟》、《狮子吼》等宣传革命的读物唤醒国人,这些都使杨昌济非常激愤,立志要抓紧求学以报效国民。
1904年,杨昌济因嫌弘文学院速成科太简浅,转入普通科学习,主要学习日本语言文字及中、小学课程。经过三年学习,他从弘文学院毕业,随即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入文科英语部。在英语部肄业期间的1908年,同乡好友杨毓麟充任清政府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的秘书,与蒯同行的还有正在英国阿伯丁大学读书的章士钊。杨、章向蒯介绍了杨昌济的人品和学问,于是蒯光典便调杨昌济前往英国深造。
1909年农历三月,杨昌济进入英国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学制三年。在这里,他接受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不仅教学方法先进,以“讨论课和启发式教学”取代了有二百六十年历史的老的苏格兰式的做报告记笔记的教学方式,而且有一批在学术上处于世界最前沿的教授。在认真听课和参与学术讨论的同时,他系统地研究了西方的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从古代希腊、罗马哲学,到近代英国、法国、德国的哲学;从资产阶级早期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卢梭、斯宾塞尔、赫尔巴特等人的哲学思想,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各种现代哲学家流派,杨昌济都进行过比较详细的探索和分析。对于伦理学上的各种主义,如禁欲主义、快乐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等,他都广泛而深入地进行过探讨和比较。据宣统二年(1910)二月初十日出版的《教育杂志》第二期报道:杨昌济“所修伦理学科,曾得分数九十分以上,足称优胜”(转引自张旭《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翻译家卷》)。
在此期间,好友杨毓麟已辞职来阿伯丁大学研习英文。1911年阴历闰六月,杨闻知黄花岗起义失败,忧党人之牺牲,愤清廷之腐败,自投利物浦大西洋海湾殉国。杨昌济感事悲惜而作《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后发表在1914年《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期。
1912年7月,杨昌济以优异成绩从阿伯丁大学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去德国进行了九个月的学术与教育考察。因为他在阿伯丁大学时,已通过对新理想主义者詹姆斯布莱克巴里的学习,培养了对德国理想主义传统,尤其是对康德主义及新康德主义伦理学的兴趣,加之他还想研究德国的学校系统和教育思想,所以他还要考察德国,以完满结束他那“寻求知识的世界之旅”。
强避桃源作太古 欲栽大木拄长天
1913年春天,四十三岁的杨昌济回到国内,当时清政府已被推翻,民国已经成立。因他出国留学的经费是由湖南省资助的,按照当时规定,学成归国后必须回省工作五年。他是一位严守信诺的人,尽管他的留日、留英同学范源濂等人此时已在北洋政府当了教育总长,他也不愿失信,直接到北京、上海等地去工作。而且那时湖南督军谭延闿想聘请他出任湖南省教育司长,他也坚辞不就,而应聘到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课程。省高师是当时湖南的最高学府,也是第一次开设这类课程,其影响自然很大。因此,从1913年至1918年,他还先后或同时兼职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和长沙第一中学任教这些课程,或增设修身、心理学等课程。
由于杨昌济道德高尚、知识渊博,又思想进步,所以他在每个学校讲课,都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许多学生不仅在课堂上专心听他讲课,而且课余还成群结队到他的“板仓杨”寓宅求教。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章甫、罗学瓒、张昆弟等,更是他家的常客。在毛泽东当年就读的第一师范第八班教室的墙壁中央,有杨先生亲手书写的一副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表明他已自闭桃源,与世无争,把桃源当作自己理想中的上古时代,为国家培养有用的拄天栋梁之材。这种专心育人以救天下苍生、挽狂澜于既倒的精神与豪迈气概,对青年毛泽东一辈当然影响甚大。
在长沙教书期间,杨昌济为了提倡和宣传新文化,在大量阅读、讲授西方各种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著作的同时,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翻译和评介,并将此视作人生的一大乐事。在他看来,翻译与评介都是为了“输入文明”,“为社会增一分精神之财产”,“要将时代改造成为进步的时代,必须改造国民的思想,吾国变革虽甚激烈,但国民之根本思想,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待于哲学之昌明”(《劝学篇》)。因此,他改造时代的实践,一是从身边的学生教化入手,二是从自己对西方科学的译介入手。他撰写了大量论文和讲义,翻译了许多外文著作,正如他当年的学生舒新城在《杨怀中先生遗嘱》一文中所说:“先生昔在岳麓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心理学、教育学,于讲义之外,并本个人研究之心得,及摘译东、西之名著,另著《心理学(讲义)附录》、《教育学(讲义)附录》,二者言理之精,较讲义尤为过之。”舒新城还说:“他教我们伦理学及伦理学史,为时不过一年,但他所给我们的影响很大。”
杨昌济对外文著作的译介,尤为重视英国哲学方面的作品。这一则因为他历来重视哲学对人的教化作用,认为“人不可无哲学思想”,“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劝学篇》)。二则因为他在英国研读哲学、伦理学和教育理论时,就阅读过英国许多著名哲学家的著作,尤其是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尔的著作。他的译作《斯宾塞尔感情论》、《结婚论》和论文《哲学上各种理论之略述》,都是他向国人输送和介绍西洋哲学的重要作品。
至于这一时期杨昌济在伦理学方面的建树,那更是尽人皆知。他出生理学世家,又深得西方伦理思想的精髓,故对伦理学更情有独钟。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连载其《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后收入“东方文库”第三十五种,题为《西洋伦理主义述评》,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17年前后,杨昌济一面在湖南一师任教,一面翻译日本伦理学家吉田静致的《西洋伦理学史》。学生毛泽东认为“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便把先生的译稿工整地抄录下来,足足抄了七本,并在同学间传阅。
杨昌济在湖南任教五年,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章甫、向警予等一批新文化青年都出自他的門下。他还经常与学子们严肃地讨论时事政治,鼓励他们努力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风,练就一副强健的体魄。在杨昌济的循循诱导下,这群青年不断进步,并且经常围绕“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生活向上”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这种讨论的结果,便导致了我国“五四”时期最早的社团之一——新民学会的成立。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谈到新民学会发起的缘由,除“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或即“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做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可见1918年4月由毛泽东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其精神领袖其实就是杨昌济。
北大良师英年早逝
1918年夏天,已兑现约定服务本省五年的杨昌济,因北洋政府任命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反动统治使湖南教育受到极大摧残,而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赴任北京大学教授。蔡元培期望他“为中国哲学树一强国之基础,使东、西学术思想冶为一炉,而成为中国独立之伦理学和教育学,不至偏于取材他国,而置我民族之特点于寒灰槁木之中,毫不重视”。杨昌济在北大主讲两门必修课——伦理学和伦理学史,都极受欢迎。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北大师生最为活跃,各种组织、社团和刊物纷纷涌现。杨昌济十分关心新文化运动,曾与胡适、马叙伦、陈公博、梁漱溟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并应许德珩等人之约,给《国民》杂志撰写了《告学生》一文,以号召学生担负“唤起国民之自觉”的重任。1918年9月15日,他在《新青年》第五卷3号发表了译作《结婚论》,考察人类男女关系产生之种种行为,“遂至生道德之判断”。此文一经发表,即“在昏暗知识界产生了颇大影响”。
他还时常与身边的青年讨论一些时事中的热门话题,并订阅专论外国“波日西维克”(布尔什维克)的英文杂志作为讨论素材。如湖南宜章人邓中夏那时也在北大读书,他和毛泽东等便与过去在长沙一样,每逢星期天必到鼓楼豆腐池胡同九号的杨家参加讨论。
杨昌济身在北京,仍十分关心湖南的新民学会,积极支持学会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他介绍陪同赴法学生进京的毛泽东认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使之得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当时在北大真正有远见、能看得起毛泽东这位临时工的教授,是李大钊、陈独秀、杨昌济、邵飘萍等几位杰出者。特别是李大钊,给了毛在工作和学习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引导,引导着毛从最初的一个自觉的革命者,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确定了自己的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1919年下半年,杨昌济因身体不好而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养病。他当时并未感到自己病情的危重,读了《少年时事》的《少年,驰骋》诗,他还动魄惊心,说:“我虽未老,然已届中年,但吾气浩然,仍怀迈往无前之志,以百年为期,尚可作五十年之研究也。要之,学贵日新,与年俱进,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吾示曰:我这少年的精神不能死。”入冬以后,病势转重,先是胃病,继转浮肿,12月初住进北京德国医院,不幸于1920年1月17日竟以未满四十九岁的英年离开人世。他病逝前,还给章士钊写信,举荐毛泽东、蔡和森二人,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并再次把女儿杨开慧托付给毛泽东。对此一代哲人的匆匆离世,学界为之震惊、悲恸。蔡元培校长说,“北大以他为荣”,“惜本校失此良师”。更有一副挽联说得精妙:“记我公易箦三呼,努力,努力,齐努力;恨昊天不遗一老,无情,无情,太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