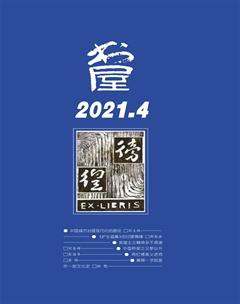章太炎眼中的台湾
杨儒宾
章炳麟在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过程中,他的一支古奥之笔像一把凌厉的吴钩越剑,曾发挥了极大的力量。在创建民国的过程中,晚明的想象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他在《光复军志序》一文中曾说及年轻时的一段心事:“弱冠,读全祖望文,所述南田、台湾诸事甚详,益奋然欲为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黄书》,志行益定。”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多记晚明烈士事迹,多有与台湾相关的历史。其中所记沈光文、徐孚远诸人传记,即为明末复社名士而流寓台湾者。章太炎的晚明情结又见于他的另名“太炎”,对章炳麟事迹稍微了解者,皆知他的“太炎”意指黄太冲(宗羲)及顾炎武(宁人),顾、黄、王(夫之)号称明末三大家,他们三人与清末的改革派与革命志士有深厚的思想渊源。我们如视明末、清初三大家为清末民初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共同思想导师,也说得过去,章太炎是他们的“学生”。
由于章太炎的学术渊源,我辈对章太炎的相关思想自然会有较深的共感。有次因要查阅章太炎对黄宗羲与郑成功的理解,知道他有文章名曰《书〈原君〉篇后》及《台湾祀郑延平议》,但查遍他的全集,怎么翻也翻不到,后来才查到这两篇文章见于1898年的《台湾日日新报》,章太炎当时为《台湾日日新报》记者,曾为此报写些文化及时事评论之类的文章。
章太炎在1898年因“戊戌政变”被清廷通缉,后因得日本友人馆森袖海之助,渡海到台湾出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借以避祸逃生。章太炎其时三十岁,思想仍處于保皇立宪阶段,很同情康、梁的政治观点,他来台后,思想仍没变。他在台期间虽然才半年多,但此时期是他思想极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著作《訄书》仍在修订中,有些重要的文章与诗文也陆续出现,这些文字多刊载于《台湾日日新报》中,在后来的各种《章太炎全集》中皆没有收录,此空缺多少造成了我们理解章太炎的不足。
章太炎在台湾待了半年多,在那个时代第一流的中国士人中,有这么长时期的第一手台湾经验者殊不多见。更重要的是,台湾有两个因素和他的思想有极深的连接,一是明郑因素,一是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前者构成了他晚明想象核心的一环,后者构成了他积极参与政治的现实因缘。这两个与台湾相关的因素很自然地汇在一起,形成他坚强的民族主义理念。1902年,章太炎在东京发起纪念1661年在昆明牺牲的南明最后一任皇帝永历帝。在文中,他号召海内外华裔子孙不要忘记汉族之恸,凡我浙人,不要忘掉张苍水;凡我滇人,不要忘掉李定国;凡我闽人,当然不要忘掉郑成功。章太炎此时的呼吁响应着他弱冠二十岁时的心事,事实上也回荡着他步上台湾时的情念。
台湾之行,章太炎对台湾显然曾有很高的期待的。果然,他步上台湾不久,即于《台湾日日新报》发表《台湾祀郑延平议》,祭祀郑成功。章太炎在此文章中,高度赞美郑成功在隆武、永历年间的英烈表现,可惜天不假年,英雄中道而夭,没有完成光复遗志。“惜乎中道夭丧,复失苍水替其辅夹。嗣王窘世,仅蹙蹙守边辐,然明氏支庶依以自全者几二十年。衣履弗改,共和弗革,抑岂非王之遗烈欤!”“衣履弗改”意指明郑还保留了大明的衣冠文物;“共和弗革”意指明郑仍维系大明帝系,以永历年号纪年;“苍水”则指张煌言,郑成功的复国同志,章太炎终生佩服的义士。章太炎逝世,其墓即依傍在张煌言墓旁,从其遗志也。
章太炎还将郑成功与三国的东吴相比,认为郑成功不忘故国,保大明衣冠于孤岛,其道德远超过孙吴。他说:“延平当永历之亡,犹奉其年号握玺勿坠……呜呼!其贤于吴也远矣!”章太炎对郑成功情有独钟,在面临生命交关的“苏报案”时期,他撰有《郑成功传》一文,高攀延平郡王,伸反清复明的大义。我们以后还会看到他将郑成功和洪秀全并称为“郑洪”,视为明亡、民国兴之前反清运动的代表。
章太炎的明郑情结不是个人情怀之事,虽然他的私人感受可能更强烈,他对郑成功或明郑的评价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价值意识。明郑肯定论一直是台湾四百年来明郑史观的主流,也是包含1949年来台一代人士的共识,胡适、牟宗三诸先生对明郑的评价皆极高,视为民族精神的体现。唐君毅到了台南,走进明郑所建的孔庙,一再低首徘徊,不忍离去,两天之间去了两次。台湾人有很强的明郑情结,多有这样的精神构造,这是不少研究台湾文化的学者都曾注意到的现象。
章太炎浙人,浙人在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复明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著名的殉国烈士刘宗周、祈彪佳、陈子龙、张煌言,著名的海外乞师者或飘零扶桑的畸儒朱舜水、张斐、心越、独立,都是浙人。如果我们要列出那个时代参与抗清活动的浙籍儒者,其名单将会长得难以罗列。更重要的是,江南反清领袖鲁王即在绍兴即监国位,舟山群岛在当时的抗清运动中,与金门、厦门等地都是第一线的赫赫战区,郑成功的军事活动也多在闽、浙沿海展开。浙、闽、台等东南沿海省分在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复明运动中,与两广、湘、赣的西南省份互为犄角,成为当时反抗意识的神经中枢。章太炎在反清复明运动失败后两百多年重履台岛,而此岛屿竟已落入日本帝国之手,他的感叹可想而知。
也许他对台湾曾有过太高的期许,等他亲履斯地后,不免有所失望,用他的话讲,“意兴都尽”。可想见地,他期望此地有民族英烈,沧海遗民,最好属于士人阶层者,可与共学论道。他显然没有碰到,而且,很可能还会碰到他极难接受的人。他于1899年离开基隆,东渡日本后,曾操旧业,再编《民报》。他在《民报》上有一文名曰《台湾人与〈新世纪〉记者》,在此文中,他将一位“台湾人”与一位“《新世纪》记者”痛骂了一顿。这位《新世纪》的记者是位无政府主义者,章太炎未指名其人是谁,但读者如稍微了解章太炎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瓜葛,此未指名记者的身份颇堪玩味。另一位台湾人的名字,章太炎指名乃曾为台湾法院通译的赖雨若。章太炎所以撰文痛骂这两个人,乃因他们两人身为汉族,却都以异族的语言论说述事。《新世纪》记者姑且不论,赖雨若言行似乎颇有“汉人学得胡儿语,争向墙头骂汉人”之意。对章太炎而言,这种事情当然是极严重的道德瑕疵。
章太炎对明郑以下的台湾反抗传统耿耿此心,萦胸难忘。《台湾人与〈新世纪〉记者》此文中,章太炎感叹道:“郑成功驱荷兰人,存明祚于斯岛二十除岁……乙未割让以还,简大狮辈复起与日本抵抗。”
章太炎《台湾人与〈新世纪〉记者》文中所说的赖雨若真有其人。赖雨若(1878—1941)乃嘉义地区名士,出身老世家。他于1911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高等研究科,为台湾首位法学硕士,后来通过高等文官考试,成为当时台南州轄下第一位台籍辩护士(律师),他还担任过第一届嘉义街协议会员。
但章太炎大概还不知赖雨若还有其他经历,赖雨若后来曾与嘉义地区士绅苏孝德、林玉书等人组织茗香吟社、嘉社,扶掖风雅,颇负乡里清望。我曾收藏一件他与当时《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主编魏清德唱和的诗作,常见的记游主题的七律。虽不见特别,但可想雅致。苏孝德有外孙,一位台湾“中山大学”的教授,我和他有些来往,稍稍侧闻过其外祖遗事,也稍为了解日据时期,嘉义士绅经营的汉文化活动。赖雨若即曾在家乡开设义塾,免费教授乡人“四书”、“五经”等。更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他获颁为“抗日烈士”,“中研院”台史所收藏有他的文书数据。
从赖雨若现有数据所显示的内容看来,他似乎不太像章太炎所说的那般忘本。否则,“抗日烈士”的头衔如何得来。章太炎当然不会说谎造假,但以一次的交谈作为其人人格的判准,难免失准。从赖和、林幼春、连横到苏孝德、赖雨若,反抗的色彩递减,但他们对汉文化还是有情感的,不会忘本。
赖雨若有什么特别会和自己利益冲突的“抗日”行径,因而赢得“抗日烈士”之名,后人不得而知,但章太炎对他的行径的愤慨,或许还是发泄得太早了一点。如果我们平心静气观看日据时代的知识人,尤其具有旧文化涵养的知识人的行径,赖雨若的反应应该不特别,也不该蒙受过分的恶名。章太炎文中对台湾士风的批判未必周全,主要是他在台期间,局促于万华一带,和台湾士人交往不多。我看到和他交往较密的大概只有连横,章太炎曾为他的《台湾通史》写序,颇赞扬此书的价值。章太炎还曾赠给连横一件行书条幅《雅堂索字书赠》,文字为“蓑墙葺屋小于巢,胡地平居渐二毛。松柏岂容生部娄,年年重九不登高”。据说是1914年写的。章太炎与连横的交往时间大概不在他旅台期间,而是在连横于民国成立后定居上海,彼此才相互认识的。
他也知道赖雨若不能代表台湾人,事实上,赖雨若很可能也不是他想象中的台湾人。章太炎在同一篇文章中即对自己的台湾人观作了修正。他提到这样一件事:“今岁四月,云南人开独立会于锦辉馆,将以内拒胡清,外抗皙种。一弱女方十岁,抵余前,致楮币十圆,以助独立者。主干问其姓氏,曰:台湾人也。此非弱女所能为,盖其父兄属以授受者。即明台湾虽裂,犹有不忘故国之心。于是知种性之不可芟夷也。”
章太炎比起他同代的政治竞争对手梁启超、孙中山来,他居留台湾的时间最长。梁启超来台两个星期,孙中山来台四次,最长住了四十四天,章太炎则长居半年以上,但他对台湾的影响远不如梁启超、孙中山。梁启超影响了林献堂的议会请愿运动,孙中山影响了蒋渭水的农工运动甚至整体的革命路线,梁、孙两人无意中都参与了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反抗运动。章太炎因为经常蜗居在万华的剥皮寮住处,很少走动,他和台湾士人、社群没什么来往。
章太炎与台湾社会的互动主要是在1949之后,其影响是间接地影响,因为章太炎其时业已辞世,墓在西子湖畔,长伴他一生景仰的乡贤张煌言。他的影响是由他的门生与门生的门生渡海传艺所致。章门这群团结的学生透过章太炎精湛的文字、训诂等小学理论主导了台湾高教体系的台师大、政大、文化的中文系学术研究方向,俨然成为以前台湾小学界势力最大的一系,号称章、黄(侃)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