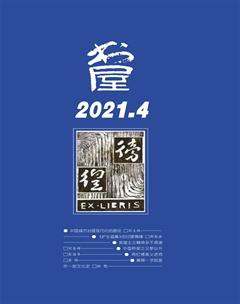“经济人”和湖南人
陈彩虹
一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有这样一句话:“人是经济理性的。”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的言行会表现出契合“经济常理”的状态来,不会违反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定、规则和规律。人类的经济活动千姿百态,但归结起来,无非是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如农民种粮食盼个好收成,商人做生意期待有赚头等。因此,所谓“经济常理”,具体化就是“收益要大于成本”或称“净收益”一类的计算和计较。主流经济学认为,只要是人,就有这样的理性,古往今来,东方西域,概莫能外。具有这样理性的人,经济学称其为“经济人”。
湖南人,从通常的意义讲,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文化概念。当我们说起“湖南人”时,一方面,是指出生于湖南或长期在这个区域之内生活的人,这是“湖南人”的地域属性;另一方面,是指由于湖南地理、社会、历史、民族和习俗等,塑造出来具有特殊性情的这样一类人,这是“湖南人”的文化属性。我們在此谈到的“湖南人”,显然是偏重于性情的,其中“湖南”一词不只是表示地理区域,更是附加上了文化的内涵。或许这样说更简明、贴切,“湖南人”是湖南文化的产物。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湖南人当然是“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具有“收益要大于成本”的经济理性。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一点,湖南人便不过是天底下所有“经济人”中的一部分而已,不会有什么新鲜出奇的地方。然而,“湖南人”既然是本地文化的产物,基于湖南文化不同于他乡文化,更有别于异国传统和价值观,那么,带着湖南地域文化的“经济人”一定有所不同,他们肯定能够从一般的“经济人”群体中分离出来。就此而言,“湖南经济人”是存在的,将其独立化出来进行讨论,有历史和现实的基础。这样一来,我们引发了一个蛮大的问题:和一般的“经济人”相比,“湖南经济人”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呢?
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很明显,主要是从人的动机角度来定义的。它告诉我们,在经济活动中,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会有“收益要大于成本”的动机。但是,这种动机能不能最终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净收益”,转变为多大的“净收益”,那是不确定的。换句话说,光有动机,并不意味就一定有动机指向的结果,“净收益”从动机到实现,还存在一个“经济人”需要去作为的过程——“经济人”的动机重要,作为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正因为如此,不同文化底色的“经济人”,一定会有不同的作为,这便使得“湖南经济人”有了不同于一般“经济人”的特殊之处。自然,我们也就有了文章可做。
二
湖南文化塑造出来的湖南人的性情,显然不会单一,但“霸蛮”的特点是突出的,得到了各方较为普遍的认同。“霸蛮”大致可以解释为一种人的意志,即不顾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限制,不遵循于常理,不在乎成事与否,还不计后果而执拗采取行动的意志。从不少湖南人“霸蛮”的故事看,这个词语是褒是贬,不仅取决于故事正面或负面的结局,还取决于讲故事人的情感倾向。由于“霸蛮”体现了横竖都无畏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气度,就精神和气度本身,它是受到肯定的。相当多的湖南人都认为“霸蛮”是优秀性情,引以为傲。
我们知道,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奔着“收益大于成本”的“净收益”目标去的。“净收益”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经济人”创造出来的。追问一句,“经济人”又是如何创造“净收益”的呢?回答是创新。颇有意味的在于,经济学的理论、流派和观点林林总总,对诸多经济问题争议不休,在这一问题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
当湖南人秉持“霸蛮”的性情来从事经济活动,向着“净收益”的目标进军时,会是如何的局势呢?他们会有“创造”和“创新”一类的作为么?不无遗憾,实践观察表明,“霸蛮”这种性情,不是优势的经济行为的意志基础,它仅仅在极为特殊的情形下可能会有某种经济意义上的“作为”而已。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活动是诸多参与者比产品、服务、技术及商业模式的竞争,与时俱进者方可立于不败之地。源起于“霸蛮”的意志力,由于它“不屈从于常理”,人们的经济行为大多会沿着两个极端方向展开:要么不顾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定、规则和规律,固执盲目地去进行所谓的“创造”和“创新”,即使屡战屡败,依旧我行我素;要么一成不变地坚守既有的产品、服务、技术及商业模式,故步自封,抱残守缺。不论何种行为走向,很清楚,它们都和“净收益”的经济活动目标相去甚远。湖南人的“霸蛮”性情是无法转化为“经济人”合理行为的。从根本上讲,“霸蛮”性情与“经济人”的理性是相悖的。如果说,“湖南经济人”硬要拿“霸蛮”的性情来搞经济活动,恐怕是只有败多胜少的结果。
“霸蛮”当然也不是完全一无是处。经济活动有时是市场中争时间、夺空间和比耐力的竞赛,当各种条件错综复杂、掣肘严苛时,如果某些“经济人”具有强大的意志力,敢于捅破关隘,赢得时间和空间,便可先声夺人,争抢到“净收益”。湖南人的“霸蛮”,正好是产生这种非凡意志力的厚实土壤,它赋予了“湖南经济人”独有的市场竞争中夺取“净收益”的一件利器,非其他“经济人”可以比肩并论。在这里,“霸蛮”是近似于创造,还等效于创新的,因为它有着获取“净收益”的功效。不过,从实践来看,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少,由“霸蛮”抢得“净收益”的故事寥寥无几。有几分可悲的是,这少之又少的案例竟不时被人们夸大,“霸蛮”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被莫名其妙地抬举到了一定的高度。
既然“霸蛮”性情在经济活动中会是如此的“作为”,我们就不得不说,湖南人要搞经济,还是少点“霸蛮”为好,最好是不要“霸蛮”。
三
和“霸蛮”相对应的反义词叫“灵泛”。湖南人日常用“灵泛”表达的意思,是指人很聪明、灵活、会平衡四面八方利益、会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等。基于我们对“霸蛮”的理解来认知“灵泛”,它主要是指符合常理,不认死理,不“一根筋”地简单、蛮横和粗暴处理事情。有意思的是,湖南人中并不只有“霸蛮者”,也有“灵泛人”,而且是活跃在经济生活中的“灵泛人”。
例如,当我们说湖南的常德人会做生意,并尝试去挖掘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时,“灵泛”这个词很容易浮现出来。这里的暗喻是,“灵泛”性情有助于“经济人”对“净收益”目标的追求,常德人的“灵泛”一经运动起来,作用于经济活动之中,必定会赢得“收益大于成本”的那个余额,这就是“会做生意”的内涵。可见,与“霸蛮”完全不同,“灵泛”和“经济人”的理性及理性下的目标高度一致,是值得湖南人在经济活动中大加提倡,并且下意识去塑造和培植的性情。
然而,就现实格局论,“灵泛”不是湖南人的主性情,“霸蛮”才是。在充满着“霸蛮”性情的世界里,要让“灵泛”的人多起来,多到一半,再超过一半,最后成为主流的性情,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况且,文化的存续,性情的固有,是许多代人传承和演变的结果,眼前“霸蛮”的现实,自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尽管说,在经济活动中,“霸蛮”难以合拍“经济人”的理性,难以支持“湖南经济人”去实现更多、更大的“净收益”的目标,但它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里,特别是在需要人的强大意志力去作为的一些社会历史关键事项上,仍然有其神奇取胜的一面,仍然闪耀出熠熠的光辉。
结论就是,在经济活动中,湖南人需要学得“灵泛”点,少点“霸蛮”。但“霸蛮”并非没有存在的价值,不必全然毁弃。泼水不要将孩子一起泼掉,这是超越经济学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