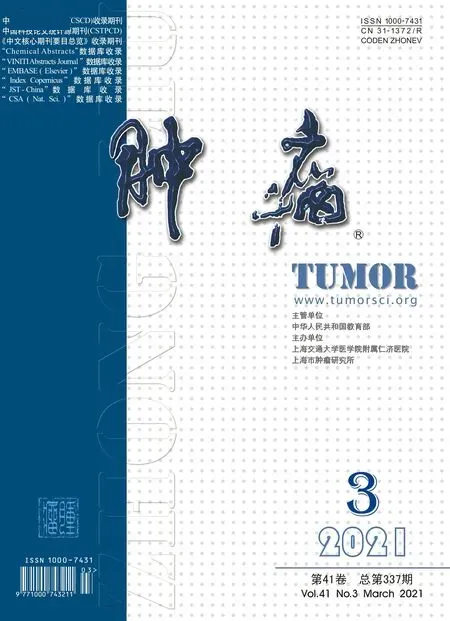手术影响肿瘤转移机制的研究进展
杨玉雪,蒋晨宇,王 杰,许建华,袁 旭,蒋一鸣
手术是大多数早期实体瘤患者最主要的治疗手段,但根据流行病学的数据统计,术后常有肿瘤复发转移的发生,并且具有很高的死亡率[1-2]。有研究者提出,这可能与手术操作导致的肿瘤细胞脱落致使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ur cells,CTCs)增多相关[3-4]。然而,在某些全乳房切除术的患者中,肿瘤的物理破坏极小,几乎可以排除术中肿瘤细胞脱落的影响,但仍能观察到术后有部分患者发生转移,由此提示这种机制并不能完全解释肿瘤切除术后转移的原因。
最近有研究表明,结直肠癌甚至在原发肿瘤被发现前,就可能已经转移[5-6]。因此有研究提出,在各进化阶段的肿瘤细胞均可能出现高侵袭性的亚克隆群,即不同阶段的肿瘤细胞均能远处转移,甚至在早期阶段,一部分肿瘤细胞就已经形成了亚临床病灶[7]。在免疫监视作用的制约下,肿瘤细胞无法增殖,从而成为无法用仪器检测到的细胞团块,即形成亚临床病灶或处于休眠状态。处于休眠状态的肿瘤细胞又因手术刺激而复苏,逐渐形成仪器可见的转移。
本文将就目前手术引起肿瘤转移的机制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手术影响肿瘤转移的主要机制
手术引起的应激、炎性反应和伤口的愈合等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的调节、炎性反应因子的释放、血管生成以及免疫抑制和转移前生态位(premetastatic niche,PMN)的形成等方式影响肿瘤细胞的生长。而这些机制往往相互促进,并以滚雪球的方式,增加围手术期肿瘤细胞逃离休眠的可能,最终形成术后转移,导致疾病复发。
1.1 应激激素的释放
手术引起的应激反应是一个复杂而异质的过程,包括心理改变(如恐惧、焦虑和疲劳)和生理效应(如手术创伤和疼痛)。其主要由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SNS)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轴介导。
外科手术使SNS激活后,儿茶酚胺从神经末梢局部释放,并从肾上腺髓质释放至全身;另外,SNS还可以促进花生四烯酸的代谢以促进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的合成;与此同时,肾上腺皮质则释放糖皮质激素。有相关研究显示,糖皮质激素虽有免疫抑制的作用,但对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抑制和肿瘤促进的作用相当有限,而儿茶酚胺和PGE2则是促进肿瘤转移的关键介质[8]。
此外,许多肿瘤均会上调自身肾上腺素受体的表达水平[9]。应激产生的儿茶酚胺便能直接作用于肿瘤细胞。LI等[10]研究发现,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NE)和肾上腺素(epinephrine,E)促进肝癌细胞的侵袭和转移作用,是通过单胺氧化酶A(monoamine oxidase A,MAOA)抑制E能系统及其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信号的转录活性来完成的。其中,MAOA是一种儿茶酚胺神经递质降解酶,能够降低血液循环中儿茶酚胺的水平。LIU等[11]研究发现,激活β2肾上腺素受体可以促进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的裂解和核易位以及癌细胞的转移潜力。此外,β肾上腺素受体的激活还会在结构上改变肿瘤细胞,使其更具侵袭性[12]。有研究表明,SNS的激活不仅能调节巨噬细胞浸润的程度,还能调节包括环氧合酶2(cyclooxygenase-2,Cox-2)、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IL-8以及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等细胞因子的释放,并最终促进血管生成和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诱发炎性反应和抑制免疫反应,导致肿瘤复发转移[13-15]。其中,MMPs是一类能够降解细胞外基质的蛋白水解酶,而MMP-9可通过水解VEGF的分子结合结构域,来增强VEGF在肿瘤微环境中的生物利用度,进而增加激活休眠肿瘤细胞的可能[16]。
1.2 手术引起的创伤
由于手术操作对人体造成的创伤,人体组织将募集多种炎性反应细胞,并释放大量细胞因子,来帮助伤口的愈合,如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PGE2和IL-6等。在动物模型中,伤口未愈合的小鼠肿瘤转移的发生率明显高于伤口愈合的小鼠[17]。另一项临床研究则表明,术后炎性反应会促进结直肠癌患者的复发[18]。总之,局部和全身性炎性反应可能共同激活了休眠的肿瘤细胞或诱导了残留的肿瘤细胞增殖。
KRALL等[19]利用休眠小鼠模型发现,手术伤口修复所致的全身性炎性反应可诱发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数目升高;相较于使用抗Ly6G抗体耗竭休眠小鼠模型的中性粒细胞,通过成簇的规则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CRISPR)/CRISPR相关蛋白核酸酶9(CRISPR-associated nuclease 9,Cas9)基因敲除技术抑制单核细胞向巨噬细胞转变的所需的关键的细胞因子(C-C)基序趋化因子配体2 [chemokine(C-C motif)ligand 2,CCL2]的释放更能使休眠的肿瘤细胞增殖;在上述实验的基础上,研究者们还发现巨噬细胞可诱导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表达的上调,并抑制CD8+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免疫监视。LINDE等[20]的研究也同样支持了巨噬细胞的促转移作用;该研究在自发乳腺癌小鼠模型中发现,巨噬细胞可以被趋化到早期乳腺病灶的导管上皮内,并诱导早期乳腺癌细胞发生EMT。
此外,有相关研究发现,IL-6通过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κ-B,NF-κB)上调T细胞免疫球蛋白及黏蛋白域蛋白4(T-cell immunoglobulin domain and mucin domain 4,TIM-4)并促进非小细胞肺癌的转移[21]。另一项研究则发现,IL-6可以通过肺癌细胞的COX-2/PGE2通路诱导EMT的发生,从而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侵袭和转移[22]。
有研究表明,PGE2能募集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以及促进巨噬细胞向M2型巨噬细胞转化等抑制免疫[23-24],并有助于肿瘤血管的生成[25]。
除此之外,手术中的创伤也可能破坏局部脉管系统,引起伤口灌注不足,从而导致局部缺血或缺氧。曾智锐等[26]发现了缺氧促进胰腺癌PANC-1细胞的迁移和侵袭的具体机制,其是通过钙蛋白酶(Calpain)2蛋白介导E-钙黏蛋白(E-cadherin)表达下调和波形蛋白(Vimentin)表达上调完成的。
1.3 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utrophils extracellular traps,NETs)
外科手术导致的局部和全身性炎性反应,还可以引起持续数周的NETs的形成,这同样是促进肿瘤转移的一项重要机制。
一般认为,NETs主要是由颗粒蛋白和DNA细丝结构所组成,多在感染时诱捕微生物。有相关研究则表明,NETs可以通过整合素(integrin)β1介导的相互作用来捕获CTCs[27]。此类被捕获的CTCs更易在血管腔内黏附生存,并在MMPs的作用下,进一步外渗[28]。NETs还可以通过激活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STAT3)和NFκB等途径,诱导现有残留病灶的增殖;并且术后对NETs的抑制有力地抑制了先前观察到的新转移性疾病的加速发展[29]。因此,NETs不仅能增加外科手术过程中释放的CTCs的存活率,以增强转移灶的建立,还能使肿瘤早期阶段形成的亚临床病灶中休眠细胞的增殖。然而,有最新研究表明,NETs并不只是捕获CTCs,更是吸引肿瘤细胞的趋化性因子,能够和肿瘤细胞表面的卷曲螺旋结构域蛋白25(coiled-coil domain containing protein 25,CCDC25)特异性结合,使肿瘤细胞感知NETs,并激活整合素连接激酶(integrin-linked kinase,ILK)/β-parvin信号途径,以增强细胞的运动能力,促进肿瘤细胞迁移[30]。
1.4 免疫抑制状态
一般认为,抗肿瘤免疫主要是由T细胞和NK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发挥作用。在动物模型中,抑制细胞免疫已被证明可以加剧肿瘤转移[31]。
由于手术操作对人体造成的创伤程度不同,术后的免疫抑制状态会持续数天至6个月。在此期间,休眠肿瘤细胞将更容易进入免疫逃逸阶段[32]。除此之外,手术还会诱导多种免疫抑制性分子和免疫抑制性细胞的增加,从而加剧免疫逃逸。
1.4.1 抗肿瘤免疫细胞的数量和活性下降
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与NK细胞是人体最主要的抗肿瘤细胞,术后其数目的降低将促进肿瘤的生长。有研究表明,大部分白细胞均可表达儿茶酚胺和前列腺素的受体,儿茶酚胺和前列腺素可直接降低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和NK细胞的活性,导致抑制细胞免疫[33]。此外,应激产生的儿茶酚胺和前列腺素还能抑制抗原呈递细胞中IL-12的产生,从而降低辅助性T细胞1(T helper cells 1,Th1)的增殖,并刺激淋巴细胞群向Th2细胞转移[34]。Th1细胞产生的减少还会受到糖皮质激素影响,这最终破坏了Th1细胞和Th2细胞的平衡,导致免疫抑制[35]。
1.4.2 免疫抑制性细胞的数目和活性提高
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ur 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是人体主要的免疫抑制性细胞,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PD-1)是人体主要的免疫抑制性分子。
Treg是一种高度免疫抑制性的CD4+T细胞,术后可迁移至炎症部位,并抑制CD4+T辅助细胞和CD8+T淋巴细胞等的抗肿瘤免疫功能[36]。有研究报道,术后Treg显著增加与肿瘤复发相关[37-38]。
MDSCs可抑制T细胞、NK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的免疫作用,促进肿瘤细胞生长,并促进血管生成;其数目的增多和预后不良相关,可被视作预防术后肿瘤转移的靶标[39]。最近有研究表明,手术激活MDSCs的免疫抑制作用可以通过磷酸二酯酶-5的抑制来逆转;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如西地那非)可以下调术中精氨酸酶1(arginase 1,ARG1)和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表达,从而恢复MDSCs的免疫功能[40]。
TAMs分为M1型巨噬细胞(经典激活途径)和M2型巨噬细胞(替代激活途径)。M1型巨噬细胞主要存在于炎性环境中,其可以通过呈递抗原来抗肿瘤;而M2型巨噬细胞则主要存在于肿瘤微环境中,其可促进肿瘤的增殖、侵袭和转移[41]。术后产生的PGE2还能促进巨噬细胞向促肿瘤M2表型的分化[42]。最近有研究表明,转录因子CCAAT/增强子结合蛋白β(CCAAT/enhancer binding protein β,C/EBPβ)通过调控β肾上腺素,使巨噬细胞向M2表型转化,从而抑制抗肿瘤免疫反应[43]。周新等[44]发现,TAMs还能通过激活STAT3信号通路促进尤文肉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及血管拟态形成。
有研究显示,手术创伤可提高PD-1在T淋巴细胞的表达[45]。相关实验进一步指出PD-1/PD-L1可诱发肺癌患者术后T细胞功能障碍,从而增加术后转移的风险,其潜在机制可能与T淋巴细胞中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3(caspase-3)的表达升高相关[46]。
1.5 血小板的活化
术中将有CTCs的增多,并伴有更多血小板的释放。CTCs一旦进入血循环中,就会迅速与血小板结合,并结合纤维蛋白沉积,这有助于形成物理屏障,防止血流剪切力的破坏和NK细胞的清除[47-48]。有研究表明,血小板会促进肿瘤转移[49],过多的血小板也同样会降低患者的存活率[50]。在小鼠模型中,抑制血小板等的凝血途径,可大大降低癌症转移的发生率[51]。
2 围手术期预防肿瘤转移的辅助治疗
由于上述机制多发生在术中和术后短期内,这为围手术期遏制肿瘤转移的风险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针对围手术期的疗法,包括非甾体类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s)、β-肾上腺素能阻断剂和免疫疗法等可能会更好更有效地减少肿瘤细胞生长增殖的机会,以降低患者术后复发转移的可能。
2.1 NSAIDs
近年来,NSAIDs(如阿司匹林、双氯芬酸和布洛芬等)已应用于普通人群的结直肠癌预防试验中[52]。一项纳入2 308例患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围手术期使用NSAIDs可以降低结直肠癌术后转移风险,其中77.2%患者使用的是布洛芬,22.4%患者使用的是双氯芬,其余患者使用其他药物,[多因素分析校正的风险比(hazard ratio,HR)=0.84,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为0.72~0.99,P=0.042][53]。另一项涉及15 574例患者的队列研究揭示,围手术期给予NSAIDs与降低肝细胞癌肝切除术后癌症复发风险之间相关(HR=0.81,95%CI为0.73~0.90,P<0.001)[54]。长期使用小剂量阿司匹林[优势比(odds ratio,OR)=0.73,95%CI为0.54~0.99]和长期使用非阿司匹林非甾体抗炎药(OR=0.57,95%CI为0.44~0.74)与降低结直肠癌风险相关[55]。以往有研究表明,阿司匹林可以通过靶向乙酰肝素酶,抑制血管生成,防止肿瘤转移[56]。一项纳入977例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与对照组(基于氟尿嘧啶为主的新辅助化疗)相比,阿司匹林作为新辅助放化疗的辅助治疗药物联合治疗直肠癌可降低局部复发率[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RR)=0.37,95%CI为0.17~0.84,P=0.017],并提高5年生存率(RR=1.29,95%CI为1.14~1.46,P<0.001)[57]。在基础研究中发现,术前应用酮咯酸,可以降低注入E0771和4T1等细胞的转移性肺癌小鼠模型的肺转移[58]。而在一项纳入1 834例患者的荟萃分析中,酮咯酸可以降低乳腺癌复发率(HR=0.59,95%CI为0.37~0.96,P=0.03)[59]。NSAIDs除了针对消化系统肿瘤的预防和治疗外,对于其他部位肿瘤亦有一定疗效,如可降低肺癌(RR=0.88,95%CI为0.79~0.98)、乳腺癌(RR=0.90,95%CI为0.85~0.95)、子宫内膜癌(RR=0.91,95%CI为0.84~0.98)、卵巢癌(RR=0.91,95%CI为0.85~0.97)和前列腺癌(RR=0.93,95%CI为0.89~0.96)的风险[60]。
2.2 β受体阻断剂
LIU等[11]研究发现,ICI118551(一种β2肾上腺素能受体拮抗剂)可以有效抑制NE或E诱导的SMMC-7721细胞的侵袭和失巢凋亡。近期,2项Ⅱ期临床随机试验表明,术前使用β受体阻断剂普萘洛尔或联合Cox-2抑制剂依托度酸可减少乳腺癌患者原发肿瘤内中促转移和促炎性反应基因的表达[61-62]。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表明,依托度酸联合普萘洛尔治疗组结直肠癌的3年复发率为12.5%,相较于安慰剂组的33.3%明显更低(P=0.239)[63]。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表明,对于Ⅱ期乳腺癌患者,围手术期应用普萘洛尔与降低肿瘤复发相关(HR=0.51,95%CI为0.23~0.97,P=0.041)[64]。
2.3 免疫疗法
免疫刺激剂可以激活手术诱导的免疫抑制。在注射CT-26细胞的结肠癌肝转移模型小鼠中,术前使用免疫刺激剂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4激动剂GLA-SE和TLR9激动剂CpG-C可有效阻止转移过程[65]。此外,有研究发现,术前利用免疫刺激CpG-C与β受体阻滞剂普萘洛尔和COX2抑制剂依托度酸联合使用,更能有效限制注射MADB106细胞的乳腺癌肺转移模型术后转移率,并提高生存率,而并非单独使用这些干预措施[66]。
疫苗作为经典的免疫激活剂,已与外科手术结合使用。有研究表明,围手术期使用流感疫苗或溶瘤病毒可抑制手术诱发的NK细胞功能障碍,并减少临床前肿瘤模型中肿瘤的转移[67-68]。
有研究者提出,围手术期使用PD-1/PD-L1抗体(如纳武单抗和派姆单抗等)可降低肿瘤细胞对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凋亡的诱导,增加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毒性,从而提高患者的整体存活率[69]。
3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手术可通过应激激素的释放、全身和局部的炎症反应、NETs形成和细胞免疫的抑制等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进而引起患者术后复发转移。笔者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手术依然会是早期实体肿瘤的首选方案。并且,部分早期患者往往只需单纯局部手术治疗,无需系统治疗,就可以长期无病生存。然而,从理论和临床实践均有证据表明,手术和肿瘤转移的促进关系。由于围手术期CTCs数目大量增多,休眠肿瘤细胞将被唤醒,这意味着在此期间会大大增加术后肿瘤复发转移的可能。笔者所述手术与转移的促进关系,并非建议拒绝手术,而是为了更好的减少围手术期间CTCs的播散,并尽可能消除围手术期促进休眠肿瘤细胞生长的因素。因此,可以在围手术期用适当的药物去改善术后的复发转移,但这还有待于更多的前瞻性和大样本临床及基础研究的支持。此外,笔者认为除针对围手术期治疗外,目前仍有几点难点需要努力探索:(1)寻找能更早发现肿瘤的检测技术或生物学标志物;(2)寻找休眠肿瘤细胞的治疗靶点;(3)寻找最适宜的麻醉药物和麻醉方式。随着研究进展的深入,手术促进肿瘤转移的机制将逐渐揭开,这会更有利于寻找和研发更有效的药物,以阻止手术引起的肿瘤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