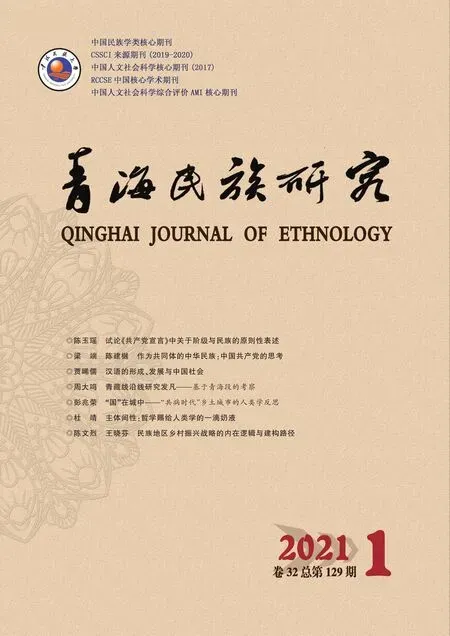从叛将到神灵: 明甘州地区武烈帝信仰研究
——以《武烈庙旧迹记》为中心
郑炳林 赵世金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20)
明代在狭长的河西走廊设立十二卫三所,由陕西行都司统辖,在行政建制上为都司——卫——千户所三级制,是典型的军管型政区,在九边重镇中占据异常重要的作用。 大量卫所的设置,使得河西地区有数量众多的兵力驻守,而该地区又时常遭受蒙古的劫掠,为明代边防建设带来巨大压力,使得“边兵之苦百倍于腹里”。 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增强武力建设之外,明朝政府又在河西地区大力提倡忠义、武勇、循吏等儒家思想精神,试图以“文化化边”的政策缓解巨大的军事压力,所以武烈帝信仰成为河西地区新引进的民间信仰之一。
一、武烈帝信仰的流传
武烈帝,即隋末将领陈果仁的封号。 关于陈果仁(又作仁果、仁杲、杲仁等)的记载,见述于新旧《唐书·沈法兴传》。[1]据《新唐书》列传第十二载曰:
沈法兴……隋大业为吴兴郡守,东阳贼楼世干略其郡,炀帝诏与太仆丞元祐讨之。 义宁二年,江都乱,法兴自以世南土,属姓数千家,远近向服,乃与祐将孙士汉、陈果仁执祐,名诛宇文化及……遂定江表十余州,自署江南道总管。 闻越王侗立,乃上书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公,承制百官,以陈果仁为司徒,孙士汉司空,蒋元超尚书左仆射,殷芊左丞,徐令言右丞,刘子翼选部侍郎,李百药为掾。
《旧唐书》所载与上述内容基本一致,我们根据所载内容可知陈果仁为隋太仆丞元祐部将,后在隋末炀帝被杀之时,与沈法兴合谋,擒住元祐,起兵自立,后被沈法兴封为司徒。 所以在正史中,陈果仁的形象并不光彩。 而在作于唐玄宗天宝年间的《隋司徒八绝碑》(以下称《八绝碑》)中,陈果仁的事迹与正史记载不一。 该碑撰者为龙兴寺僧人德宣,而原碑毁于明,碑文在《全唐文》中有收录,“后之崇奉撰述,皆本乎此碑”,所以《隋司徒八绝碑》[2]对于武烈帝信仰的形成有特殊的作用。 据载:
……公讳杲仁,字世威。其先豫州颍川人也。十七代祖寔,为太丘长。 六世祖陈武帝……祖嵩,字元皎,陈羽林郎将。……父讳季明,字元(玄)焕,陈江州司马兼岭南道采访使, 寻拜给事中。 ……公器局宏伟,风神酒肃。年八岁能文章,随父任在都宅,与吏部侍郎阴铿接住。 ……年十八,州将举秀才,送上台,对策于玉阶。 举朝称之曰:“使孙宏之文,李广之武,与子同时,则并驱连衡矣!”帝曰:“朕与儿俱太丘之后,家风不坠,复见于兹,”特授监察御史,寻迁江南道巡察大使。 ……大业五年三月,长白山大洞内有狂寇数万,公奉诏平之,授秉义尉,寻授朝请大夫。 九年正月,奉诏平江宁乐伯通叛徒十万,授银青光禄大夫。 十三年,奉诏平东阳娄世干贼徒二十万,隋主嘉之。 ……属隋季分崩……奉诏询江东晋陵耆老:“隋故司徒陈杲仁身有八绝,可得闻乎? ”耆老逡巡而称曰:“言八绝者,一忠、二孝、三文、四武、五信、六义、七谋、八辨。 ”……大业中,天门沈法兴起义兵于湖州,闻公名,原来投公。 ……法兴欲割据常州,诈结父子之义。 ……法兴潜谋,诈称疾亟。 公往问疾,乃觉中毒,走马而归。 ……公以武德二年岁次庚辰五月十八日薨,享年七十二。
据《八绝碑》可知,陈果仁司徒之职并非沈法兴所予,而是隋朝册封。 讨伐娄世干时,他统领全军,非元祐之部将。 他也没有参加沈法兴的叛乱,并为其所害。 总而言之,在《八绝碑》中,陈果仁为忠勇、孝义、干吏的化身,是儒家文化中典型的完美之人。 而根据叶舟考证认为《八绝碑》中陈果仁的形象完全为唐王朝统治者所构建,所以许多事迹均为其构造。[3]
当然,陈果仁的形象自《八绝碑》确立之后,他即被唐代政府立祠供养,正式列入官方祀典。 其后历朝政府对于陈果仁的封赠不断升级,而陈果仁也屡次在关键时刻显灵。 唐乾符四年(877 年)陈果仁被封为忠烈公,中和四年(884 年)又于封号之前加“感应”二字。 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与吴越两个国家相互交战,均称陈果仁助阵,并争相上表请封。 在梁开平四年(910 年),吴越王钱镠将陈果仁加封为福顺王。而在显德二年(955 年)周世宗命李谷南征,吴越王钱俶率兵夹击,因陈果仁显灵,钱俶所部皆大败。 所以自唐主册封其为武烈帝,封其夫人轸氏为武烈后。 后经宋、元两朝的进一步推崇,武烈帝信仰在江南地区大行,其显迹事迹也越来越多。而明代对于民间信仰政策采取了新制,取消岳、镇、海、渎及城隍的封号, 使其不再具有传统的人格神性质,同时宣布“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词,皆宜革去”[4]。 但是这种国家的强制行为,并未得到民间的支持,“人习昔时尊号,仍称烈帝”。 但是对于陈果仁烈帝的信仰带有独特的地域性特色,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在浙江、江苏、江西等地有广泛的分布,尤其是江苏地区,据叶舟统计武烈庙的分布多达十几座。但是在明清时期的河西甘州地区也有武烈帝信仰的存在,为河西地区新引进的民间信仰之一。

图1 武烈庙分布图(叶舟《民间信仰的多元图景——以武烈帝陈果仁为例》)
二、甘州武烈庙及《武烈庙旧迹记》碑文
武烈庙,在张掖清源殿之西,为明代天顺三年(1459 年)总兵宣城伯卫颖所建,并撰写碑文。卫颖,在《明史》中有传,附于其父卫青传记之后。 载曰:
次子颖,正统初,袭济南卫指挥使。 景帝立,奉诏入卫,再迁至都指挥同知。 ……天顺元年,以夺门功,封宣城伯,予石券,出镇甘肃。
卫颖为松江华亭人,由夺门之功而被授予宣城伯,出镇甘肃。 松江地区,为武烈帝信仰的中心区域,所以他将自己熟知的武烈帝信仰引入河西。 卫颖在河西地区广修祠祀,其中尤以二郎庙、武烈庙最为典型。 另外,他重新修筑了真武庙(天顺六年)、城隍祠(天顺七年)、崇庆寺(天顺七年)等,这些祠庙在明代甘州地区的宗教信仰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将武烈帝、二郎神、真武庙等同置于甘州城,体现出卫颖重视武功、重视边防建设的同时,对于“文化化边”这种政策的推崇。
《武烈庙旧迹记》,据《陇右金石录》记载:“武烈宫碑,在张掖清源妙,今佚。 ”[5]而《甘州府志》载:“明武烈宫记在清源殿西,祀隋大司徒陈仁杲。 明天顺三年总兵宣城伯卫颖建修,旧有匾文。 ”现存有乾隆十八年廪生田敏根据明代的断石残文而撰写的《武烈庙旧迹记》[6],文录如下:
武烈大帝庙旧在街北,居民有求必祷,祷必应。前明天顺二年,印绶监太监蒙公泰与甘肃总镇卫公颖重建于今所。 帝之显灵事迹,详勒于碑,以为不刊典型。 因世远年湮,文章字迹缺略不全,卧扑尘埃者,历有余年。 今春,阖郡为官长记功德磨砻之,将刻之木。 余适授徒庙中,目睹其断石残文,约略其大概;帝常州人,姓陈氏,太父暠,字元皎,仕陈为羽林郎。父明,字宝焕,为江州司马、岭南采访使。迨帝名仁杲,字世威,生梁己巳,英姿照人,顶有匿,孝友性成。 八岁属文,十三而经史通习,人咸谓:“再生东家某。 ”十八登进士第。 陈太祖谓曰:“朕与卿太邱之后”云云。 迁江西道巡察大使,摘伏发奸,名闻天下。及后主失政,叹曰:“忠臣不事二君。 ”遂归田里,随南游。 群盗并起,有荐其可用者,犹坚不起。 人曰:“与其守节于乡里,孰若除暴于天下? 苟执不起,如苍生何? ”不得已赴命,拜秉义尉。
大业五年,命鞠长白山叛寇,诛止其魁,人心悦服。 又有某贼聚兵十万,肆暴金陵,帝以为不喻以祸福,恐延无辜,使告之曰:“能悔过速降,父母妻子可免也,不然族灭无遗类矣。”不听,遂进兵讨平之。又贼某某及娄世干据东阳,帝率兵剿其众,拜大司徒。沈法兴者,帝之妻父也。 起兵吴兴,欲倚帝谋据常州,而帝精忠大节,确不可移。 又李子通者,亦聚众江北,与法兴为援,惧帝不敢动。 二人计穷,法兴乃称疾危走告,帝以亲故,不意其诈,饮酒中毒鸩,帝死,实武德三年五月十八日也。 一日阴云蔽空,昼晦如夜,忽闻空中厉声曰:“汝贼安生! ”法兴即中矢死,其威灵如此。 唐太宗诏旌其功,封武烈公。 后梁封福顺武烈王。周加以帝。宋时赐庙额曰“福顺武烈显灵昭德大帝”。 初末事实,大略如此。 呜呼! 忠烈动天地,仁义著人心,而英灵之在天,依然威烈之在世也。 辅翊纲常,匡襄社稷,千载而下,瞻庙像而俎豆常新,诵芳踪而威灵如睹,忠肝义胆,起懦廉顽,胡意自陈,迄今千有余岁矣。 一旦碑残纪缺,仪型忽泯,能勿感慨系之乎? 虽帝之为灵,昭若星日,奚必假碑,而永耀然。 不见其石,遂忘其人,碑之所系,岂鲜浅哉? 夫人有寸长微美,尚思表而闻之,况帝德在伦常,功垂寰字,坐视其湮没废坠也? 吾人读书怀古、尊贤远奸者其谓何? 愚因摹其残缺者补缮之,镌为木碑,志其始末。 若大其微迹,复勒之匾额,永垂不朽也,不能不仍望于后之君子。
虽然该碑为清代乾隆十八年廪生田敏所撰,但是碑文内容完全按照明代天顺时期的匾额所作。 由碑文内容可知,武烈宫建于天顺二年(1458 年),由镇守太监蒙泰与甘肃总兵官卫颖所建。 两人曾合作修建清源庙,并有碑记,现存于张掖大佛寺。 从田敏所撰碑文内容来看,与《八绝碑》所载内容基本一致,那么在明代河西地区,为何对于武烈帝如此推崇? 这与当时明——蒙古在河西地区大的互动格局密切相关。

表1 卫颖在甘州地区所修寺庙
三、明—蒙古互动格局下河西地区对“战神”“猛将”的推崇
武烈帝相关事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数次统兵作战的故事,包括大业五年(609 年)平定长白山大洞内之数万狂寇、大业九年平李子通部将乐伯通叛徒十万、 大业十三年平东阳娄世干贼徒二十万、解除隋末沈法兴割据常州之威胁等。 在陈果仁死后,又在不同时期的战争之中,有显灵的灵迹故事。在统治者看来, 陈果仁是维护统治的 “战神”“猛将”, 对于战争的胜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在明——蒙古互动格局之下正需要这样的“战神”“猛将”来维护边防稳定,并在战争中占据主动作用。
自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陕西行都司西迁至甘州,表明明朝政府将河西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军政单元,将其地位迅速提高。 永乐元年(1403 年),“命后军左都督宋晟佩平羌将军印,充总兵官,镇甘肃”[7],设立甘肃镇。 甘肃镇“据三秦之上流,控全陕之扼塞”,“为关陇重地”[8], 甘肃镇的设立在于防御蒙古、扼制西域,阻隔蒙古与青海、西藏的联系,使得河西地区在西北边防体系中能够成为一道有力的防线。 在有明一代,甘肃镇的防务体系有三:一是依托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统领下的军政合一的卫所,共十二卫三个守御千户所。 二是以墩堡、边墙、驿站组成的内部防御系统。 三是以关系七卫及茶马贸易组成的外部防御体系。[9]明朝政府在不断完善河西地区防御体系的同时,也不断派遣重臣巡视甘肃边防或专督兵马诸项事务。 虽然明朝政府希望通过以上诸项措施, 能将河西地区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但是蒙古诸部对河西地区的不断入侵或者寇掠,表明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自明朝建立就存在的边患问题。 在宣德、正统年间,甘肃镇就受到阿台、朵儿只伯以及瓦剌也先诸部的袭击。 仅从宣德九年(1434 年)至正统三年(1438 年),阿台、朵儿只伯等先后六次寇掠甘、凉、山丹等地。 在明景泰、天顺时期, 鞑靼部首领孛来多次入侵甘州、 凉州、永昌、山丹、西宁、庄浪等地。 据《明实录》所载,达延汗自成化至正德年间,其部大规模入寇甘、凉、永昌、古浪等大约30 余次,给河西地区造成重大灾害。 嘉靖时期巡抚都御史赵锦所撰《行都司题名记》[10]中对于明代中期以后, 河西边地的局势有详细的论述,即:
惟西北之边有九,全陕寔当其三。 而甘肃又为关陇重地,东有金城之固,西有玉关之严,南有祁连之屏翰,北有合黎之拱护。 辖甘、凉、山、永、肃、镇、西宁、庄浪十五卫所之官军,抚赤斤、蒙古、罕东、哈密、安定、曲先、苦峪诸部落之蕃族。 近而藩垣四镇,远而纲领九边。通玉帛于天方,列氈庐于疆场。黄河黑水、青海流沙、昆仑崆峒,际天极地,巍然一大镇也。 ……爰自成化年[3]来,吐蕃番酋,敢肆悖逆,仇袭哈密,虏忠顺以西迁;侵逼瓜沙,逐羌戎而内徙。 声教虽及乎昧谷,藩篱实彻乎敦煌。 且西海为寇,窃据南山,皆番虏环居,套贼出没于河湟,瓦剌睥睨于嘉峪,千古之金汤,始多事矣。
赵锦作为镇抚之臣, 长期在河西地区任职,对于河西地区的形势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从其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明——蒙古互动格局之下河西地区边防的严峻形势。 虽然明廷及镇抚之臣为了遏制这种情况也做出过极大的努力,其策略多集中在屯垦、马政、巡边、筑城等方面。 曾担任甘肃巡抚的杨博、许进、赵载都试图从以上诸项事宜入手,努力改变河西地区受到蒙古诸部侵扰的这种形势。 曾在成化、弘治时期任职于兵部的张海认为:
御戎之道,当先固我疆场。 如永昌、镇夷逼近甘、肃,今永昌既被杀掠,而镇夷人户牛羊茁壮,虏尤垂涎,两路孤悬,实难防守。 宜择有谋勇者二人,各率游兵二千,互相策应,内既无虞,徐图其外,则番族小丑不足治也。
而对于吐鲁番部侵逼,他提出六项策略,即定酋帅、除乱本、访夷情、固封守、预调度,这六项措施成为边臣镇守河西的基本方针,[11]但是外敌入侵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有明一代, 河西地区虽然为明朝政府掌控,但是蒙古对于其入侵毫无间断。 所以,针对这种形势,如何有效的对河西地区实行治理成为重中之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兵政安边,永镇提封。钲鼓旌麾,兵之耳目。三军仰望,坐作起伏。行阵齐整,巍巍堂堂。战胜攻取,武功载扬。河西大镇,控制戎羌。兵威远及,万里遐荒。庙庭爰建,神居既妥。轮奂翚飞,节镇之左。 元霜初降,肃设令行。 洁牲醴齐,祀事孔明。 神歆礼奠,锡我百福。 千万斯年,封疆永肃。 ”[12]在军事上来说,明朝政府设立甘肃镇,为九边重镇之一,加强军事方面的控制。 而对于军队的领导或者管控离不开优秀的将领, 在武烈宫修建者蒙泰、卫颖的眼中,隋末被赋予神灵化的陈果仁则最具代表性。 陈果仁数次统兵击败数十万敌军,在信仰者心目中其为一个很重要的战神。 所以明朝政府在河西地区大肆宣扬忠义之道,广修忠节祠,建立忠节碑。 例如祭祀毛忠的武勇祠、祭祀芮宁的襄愍祠、祭祀许铭的许公祠、祭祀王纲的悯忠祠等,另外,在嘉峪关、酒泉等地大量的关帝庙、忠武庙的修建,而这些人物大多都死于王事, 朝廷极力推崇这些人物。而陈果仁的事迹正好可以作为“猛将”“战神”的典范来进行弘扬。
另一方面在明景泰至天顺时期,河西地区受到外部军事威胁严重,在此情况下,镇守太监蒙泰于景泰七年(1456 年)任职于甘肃,卫颖于天顺元年“出镇甘肃”[13],而卫颖为明直隶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正是明代武烈帝信仰的中心地区。 武烈宫的修建仅仅在两位守边人物上任之后不久,他们极希望于塑造新的神祗来达到为河西地区的安定做贡献的目的。 在此情况下,卫颖将非常活跃于常州地区的武烈帝信仰迁移至河西,成为维护河西安定的新的代表。
四、武烈帝之“八绝”与明代河西地区对“循吏”的希冀
据《八绝碑》记载:“洎我大唐之有天下也,日月悬而天地再造,历数年而车书一统。 圣人御宇,万国来朝。 奉诏询江东晋陵耆老:‘隋故司徒陈杲仁身有八绝,可得闻乎? ’耆老逡巡而称曰:‘言八绝者,一忠、二孝、三文、四武、五信、六义、七谋、八辨’。 ”后各举例证,证明八绝并非虚言。 “梁大同中,义兴县与晋陵竞太湖田,数年不决。 太守命公断之,咸悦服焉,直若朱弦。 梁末断太湖之田,是非明白;陈初劾长山之贼,真伪纠分。 两造平反,声驰省阁;片言折中,誉出乡闾,公之忠也。 公事后亲,亲病须肉,时属禁屠,肉不可致。 公乃割股以充羹,刺血写《法华经》,为先妣修复。 孝深骨立,情慎色难……公之孝也。 ……入江写月,光含夷水之珠;词花飞叶,彩丽蜀城之锦,公之文也。 而边寇不宁,戎马屡驾,百川潜讨,三略阴谋。 巨力取而拔山,功归第一;神镩来而破的,中必叠双。 凶徒而恶叶同飘,逆党共春冰一泮,公之武也。 豁达大度,泓澄春陂,胜必推人,失乃向己。 ……公之义也。 既忠且信,十室彰夫子之名;密契深期,千里命巨卿之驾。 确乎不拔,惕若有孚,公之信也。 攻城略地,秘策权宜,进楚食而离范增,夺胡鞍而输李广,公之谋也。 折角天先,共朱云而并操;悬河不竭,与郭象而连词,公之辩也。 ”所以在“八绝碑” 中陈杲仁被塑造成古代官吏中的优秀模范—循吏。 所谓循吏在《汉书·循吏列传》有较为精辟的定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14]。 而《明史》中有关循吏的记载颇多,正传载循吏30 人,并且附载93 人。而这些人物大多数清廉节俭、仁义爱民、政绩卓著,尤其是在开垦荒田、兴修水利、施教易俗等方面有卓异的表现。 另外,这些循吏也受到民众的拥护,他们贤名远扬。
明—蒙古互动格局之下的河西地区,则更加需要“循吏”来治理该地区,例如嘉靖年间赵载担任甘肃巡抚,他修建“持敬亭”,并撰写碑记,认为“甘肃西北,极边四环,夷虏兵庶于战斗,食艰于转轮,民苦于彫瘁,计窘于外援,势危于孤立。 视昔之广州南北殊绝,矧学术经济不迨,古人励志勤力,视侃当何如从兹步于亭,睹其扁恒,惺惺然,亭名持敬。 ”[15]要求在任官员需要在道德上“持敬”,即敬德之聚也。河西地区处于极边之地, 自然灾害多发, 并且在明—蒙古的互动格局之下,时常发生蒙古军队的抢掠,造成巨大压力。 所以蒙泰、卫颖选择外武内文的陈果仁作为河西官吏的新偶像,希望能够为河西的吏治带来新变化。
由于甘肃地位重要, 所以甘肃镇官员的设置,设“巡抚都御史一员”,驻扎甘州城。[16]另设镇守太监、总兵官、副总兵官、以及参将、游击、兵备副使、镇守、守备、操守等武职若干名,在河西地区,仅仅甘州诸卫就有“马步官军三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员”[17],而且吏治较为败坏。并因此在明正德十六年(1521 年)十二月,甘州卫发生了“甘州五卫兵变”,对于明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是明代中叶北方边政的持续败坏、士兵贫困、官员盘剥的一个缩影,[18]所以卫颖、蒙泰也希望更多的官吏能够以“循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五、明代政府及卫所官兵对河西地区民间信仰的引导
洪武五年“岭北之战”的最终失败,使得明朝放弃彻底消灭蒙古的势力,转而依托长城并建立九边重镇来采取防御之策。 明朝对西域的经营止步于沙州和哈密,[19]所以明与蒙古在甘肃近边展开争夺,给甘肃镇带来巨大压力。 而在“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统治者对于经略边地则失去了洪武、永乐时期的奋发激昂,更多转为保守的防御之策。 所以为了凝聚人心、稳固边防则需要实行“文化化边”的策略。[20]而文化化边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对民间信仰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在明代河西地区,尤其是自正统以后,河西地区的宗教信仰有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信仰的主体开始变化,在正统之前,河西地区对于佛教信仰较为推崇,但是正统以后则多与武功、忠义有关的民间信仰崛起。 如天顺二年,蒙泰、卫颖修建了“清源妙道真君庙”,前湖广道监察御史牟伦为之撰写碑文。碑文曰:“圣王之制祭祀也,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其神之灵,岂惟著乎所治之一邦,虽他处亦蒙其休也,盖其聪明正直,无愧天地,故神之在天,下无所往而不在也。 ”[21]明代河西地区对于二郎神信仰的引进, 与武烈大帝的信仰有相同的原因。 另外,蒙泰、卫颖又重新修建了西夏时期的“忠武王庙”,定襄伯郭登为之撰文,碑文载曰:“夫西陲用武之地,历代相沿,分合靡常。 凿凶门者,恺敌而必征;衽金革者,丧元而不悔。 固土风之精强,亦人心之习尚也。 惟神储阳之精,合阴之妙,代天之功,顺帝之则。 昭布显烈,默相幽赞,干机运化,嘘炎吹冷,拯时艰而煦物,佐岁光而流泽。 凡有血气者,举厥痛痒,悉轸神衷,感之于形声,应之于影响,若寒挟纩,若渴饮水。 达俊功于四鄙,而群生殖;导灵命于一方,而诸殃散。 虽建极以表功,尤执元而作宰,好是正直,拂彼回邪,响于德而不响于逆,歆于忠而不歆于凶。 若夫仰之于天,则日月星辰雷雨,可以俪其高;揆之于地,则名山大川岳镇海滨,可以班其秩;稽之于人,则百谷五祀,八蜡三厉,可以齐其功。其护国之称,真君之谥,于义岂不昭矣哉?”[22]护国忠武王,即西夏齐国忠武王李彦宗,按《宋史》载:“西夏有齐国忠武王李彦宗,为元昊之后。 其子遵顼继立之后,尊其父为王”。 之所以推崇西夏土主护国忠武王,因为忠武王可以“掌岳渎,化阴兵,助征战,救生育、水火、刀兵诸厄。 ”另外,如真武庙、关帝庙、武安王祠庙等在明正统以后大肆兴建,这正是明代政府对于河西地区民间信仰的导向作用。 更加重视信仰主体能够“阴翊王度”,可以为在明—蒙古互动格局中,对于明朝政府发挥有利作用。
此外,明朝政府对于河西地区一些在明—蒙古战争中牺牲的将领,为其建立祠庙,对其功业进行歌颂, 希望受到百姓的推崇。 例如成化四年(1468年)八月,伏羌伯毛忠率军镇压满四叛乱,但是不幸中流矢牺牲,其侄毛海、孙毛铠皆战死。 成化帝得知后,赠其伏羌侯,谥号勇武。 弘治十二年,并为其建立祠庙,明代侍讲学士张昇为其撰写碑记,歌颂其功业,碑文载曰:“礼缘人情而设,公生长西陲,奋勇以殄寇侮于斯;懋赏而隆勋业于斯;保障以固我圉于斯;敷惠泽以利人生于斯。 吾知公精神命脉,不能舍此也。 人心思之,不以久暂而间,故祀之斯土,礼也。 况有功于民,以死勤事,允合祀典,敉功属后,为陲之景仰,岂非礼哉? ”[23]芮宁在正德年间担任游击将军,正德丙子(1517 年),吐鲁番速坛儿入寇肃州,芮宁等率军英勇抵抗, 后他与家仆等十余人皆战死。 所以明朝政府“命下赠都指挥同知,同袭指挥使,赐祭葬、立祠,谥襄愍,并敕内阁撰文,一以表上旌忠之义,一以显公尽忠之名,且为边防守臣效忠之劝。”芮宁成为边防守臣的代表,受到景仰。当然,还有在甘州五卫兵变中牺牲的巡抚许铭、嘉靖时期战死于甘浚堡的都指挥使王纲, 他们都代表着正义、忠勇,所以明朝政府建立祠庙,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已经神化的武烈大帝、二郎真君、西夏土主齐国忠武王,还是镇守河西而牺牲的毛忠、芮宁、王纲、许铭等,他们对于河西边防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明朝政府为了达到“阴翊王度的目标”, 对于河西地区的信仰采取了政府引导的行为。
六、结 语
有明一代,甘州地区祠庙林立,神祇繁多,尤其是民间宗教信仰非常兴盛。 这些神祇既有自然神,也有人物神;既有本地神祇,也有外来神祇。 纵观明代甘州地区的神祇, 其功能主要包含了主文教、功名禄位、御灾捍患、救国救民、抗敌御暴等。 武力护边与礼教治边是甘州地区宗教信仰的一个集中体现。 明廷在河西等地设立卫所,建立起强大的防御体系,派遣数量庞大的军队在该地区驻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明——蒙古互动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 所以武力在维护边防稳定中占据重要作用,尤其在“北有蒙古,西有诸番”的甘肃镇,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屡屡犯边,诸番“恃险阻,数出掠”,[24]所以在武力解决蒙古等部落的屡次劫掠之后,如何更加长期地维护以甘州为中心的河西地区的稳定,则需要依靠宗教信仰来构建新的华夷秩序,使得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信众具有相同的神祇信仰,尤其是处在同一地理区域的民众在信仰上具有相同的因素,为重建河西等地的秩序做出贡献。
“文化化边” 也是明朝政府以及卫所官兵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与武力治边密切结合,达到“外武而内文”的积极效果。 武烈帝信仰的引进即是该地区“文治”策略的重要体现。 武烈帝自隋唐时期兴起于江南地区之后,在五代、宋、元时期受到许多统治者的推崇,在江南地区十分流行。 而明代卫所官兵将这种信仰移植于河西地区,[25]体现出当时的统治者及卫所官兵对于“文化化边”这种政策的重视,体现出在明——蒙古互动格局中, 对于循吏、 干吏、猛将、战神等的推崇,与当地所推崇的二郎神、平天仙姑、真武大帝等信仰类型在作用以及意义上有相似之处。
另外, 陕西行都司的官员也比较重视儒学教育,并配合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积极因素,注重“外武内文”的守边之策。 尤其是在甘州地区,书院的修建、庙学、卫学的设立,祠庙、寺院等的兴建,与甘州地区的卫所官兵关系密切。 通过文化上的引导,使得该地区的各个民族能够建立起新的“华夷秩序”,为边防的戍守做出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