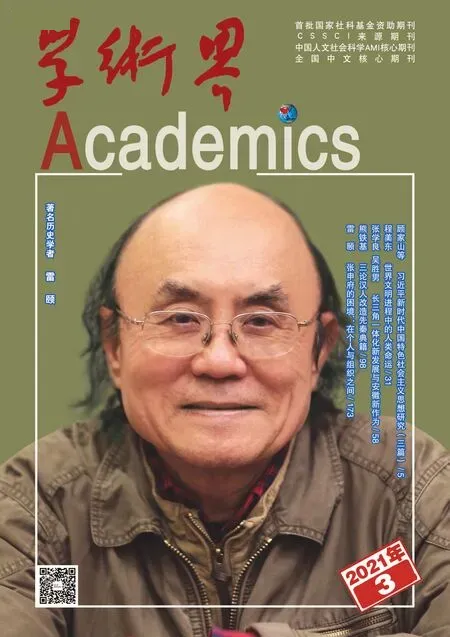人性逻辑与语义逻辑的统一
——有关若干情态助动词的语义分析
刘清平
(1.复旦大学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上海 200433;2.武汉传媒学院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海德格尔说的“语言是存在之家”,〔1〕是目前引用率颇高并且备受称颂的一句哲理名言,专门阐发它的微言大义的论说也屡见不鲜,却似乎很少看到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具体揭示日常语言是如何与人的存在形成关联的。本文试图从人生哲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想要(will)、能够(can)、可以(may)、应当(应该,should或ought to)和必须(必需,must或have to)、敢于(dare)这几个常见“情态助动词(modal verbs)”的核心语义,考察人们是怎样以“我欲故我在”的方式达成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存在,并且由此展现“人性逻辑”和“语义逻辑”的内在统一。〔2〕
一、作为动力性“意欲”的“想要”
部分地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中“情理”精神的深度积淀,〔3〕英文里的“modal verbs”通常被译成了“情态助动词”。不过,它们直接涉及的主要还是人们在“心之所之”层面上的意志心态,只有以此为基础,才会与人们在“喜怒哀乐”层面上的情感心态进一步形成关联。拿在上述情态助动词系列中居于首位的“想要”来说,它的核心语义正是把欲望、志向、企求、希望等都包括在内的“意欲”;而英文“will”作为名词的时候,更是直接指称被视为三大心理机能之一,与“认知”和“情感”截然不同、鼎足而立的“意志”。事实上,康德在谈到人类心理(灵魂)的“知情意”三分结构时,已经把“认知的机能、愉快和不快的情感、欲求的机能”明确区分开来了,特别强调它们“不能再从某个共同的根据那里推出来”。〔4〕就此而言,把“modal verbs”译成“意态助动词”或许更合适一些——虽然本文将依然沿用“情态助动词”这个通行的译法。
“想要”之所以在情态助动词系列里占据榜首的位置,与它指称“意欲”的核心语义直接相关。本来,在所谓的“非推测意思”上,情态助动词的基本功能就是表述“实义动词(主要动词)”指称的行为动作在与主体心理活动特别是意志活动的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情况状态”(这或许是它们被译成“情态助动词”的另一个理据),诸如“你‘想不想’考大学啊”,“他肯定‘能’办好这件事”,“我‘可以’在这里抽烟吗”,“你们‘应当(必须)’遵纪守法”,“他们‘不敢’冒这个险”等。明白了这一点,“想要”的领头羊地位就一目了然了:它指称的“欲求机能”,是人生从事任何自觉行为都不可或缺的心理动机;失去了它,人们就会处在“无欲无求”的绝对寂静状态,以致那些指称实质性行为的实义动词都将失去用武之地,并连带着让其他情态助动词也无从发挥效应了。例如,倘若你压根“不想”考大学,你“能不能”“可不可以”“应当与否”“敢不敢”考大学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了。
从哲理视角看,“想要”在语义逻辑中的这种优先地位,其实是“需要”在人性逻辑中的原点地位的语用学体现:当一个人的“存在”出现“缺失”时,他就会产生弥补缺失的“需要”,并凭借种种机制满足自己的需要,维系自己的存在。〔5〕一方面,许多生理需要(像呼吸的需要等)通常不会进入人们的自觉心理,单凭机体自身的本能运转就可以得到满足了。另一方面,不仅另外许多生理需要(像食色的需要等),而且超出了生理层面的所有需要(像维系人伦关系、求知、艺术创作和信仰的需要等),则会在进入人们的自觉心理后以“意志”的形式呈现出来,再进一步通过日常言谈中“想要”这个助动词表述出来,最终往往还要诉诸人们从事的可以用实义动词表述出来的自觉行为才能得到满足。“需要(need)”在许多情况下也能像“想要(will)”一样,作为具有类似语义的情态助动词发挥作用,就折射出了“需要—想要—意志”在人性逻辑的开端阶段形成的这种直接演化的绵延链条,二者的区别表现在:如果说“想要”突出了主体诉求的积极主动一面,充分展示了黑格尔指出的“意志”固有的“自由”属性的话,〔6〕“需要”则突出了主体诉求的消极被动一面,充分展示了“因果必然”对于“自由意志”的内在制约:人们总是因为自身的存在受到缺失束缚的缘故,才会形成试图摆脱(free from)这种束缚、“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自由意志。〔7〕
这样将“想要”的情态助动词与人性逻辑的实质性链条融为一体后,它就自然而然地涉及善恶好坏方面的价值内容了,集中体现在中外学界都曾给出过的“可欲之谓善”“可厌之谓恶”的概念界定上,〔8〕在此只需补充下面两点。
第一,这两个界定已经潜含着“需要”把“事实”与“价值”联结起来的枢纽作用了:当某个东西有助于满足一个人的需要时,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个“值得意欲”的“好”东西,“想要”得到它;反之,当某个东西有碍于满足一个人的需要时,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个“讨厌反感”的“坏”东西,“想要”避免(“不想”碰上)它。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是合二为一的:想要得到某个好东西(如美食佳肴),也就等于是想要避免与之对应的坏东西(如饥饿干渴)。人性逻辑的第一原则“趋善避恶”(或者说是不限于实用领域的“趋利避害”),正是这样确立起来,对于所有人都适用的:无论是谁,用“我想要”的句式指向的,总是他认为可欲的好东西(有利的东西);用“我不想要”的句式指向的,总是他认为可恶的坏东西(有害的东西)。举例来说,“己所不欲”中的“不欲”,主要就是指“自己觉得讨厌的坏东西”,所以接下来才会通过“将心比心”这种不时也会出错的类推途径,得出“勿施于人(不要给予其他人)”的结论。
第二,“需要—想要—意志”具有的这种赋予“事实”以善恶“价值”的中介功能,最终又会反身性地回归到人的“存在”那里:一个人觉得某个东西好,是因为它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弥补自己的缺失而维系自己的存在;一个人觉得某个东西坏,是因为它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反倒会造成自己的缺失而损害自己的存在。在这个意思上说,西方主流学界依据认知理性精神主张的“我思故我在”,仅仅是人的存在中一个次要从属的方面;只有从意志诉求角度指认的“我欲故我在”,才展现了人的整体存在的动力根源,并且足以为“想要”在情态助动词系列中的独占鳌头奠定哲理的基础:如果没有“想要”发挥的带头作用,其他情态助动词都将因为实义动词在“无欲无求”的绝对寂静中失去用武之地的缘故,无从发挥它们在表述人们基于意志从事行为的“情况状态”方面具有的语用效应了。
二、作为实然性“允许”的“能够”
在情态助动词的系列里,紧跟在“想要”之后的是“能够”,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把“想要”付诸实施的时候,总是首先面对“能不能够”的问题恰相一致。它在语义上与下一节讨论的“可以”有着相通之处,都是泛指“允许”,因此两者在日常言说乃至学术话语里很容易被人们混为一谈,有必要仔细辨析。
从“能够”与“可以”有所差异的视角看,“能够”偏重于表述主体的能力以及相关的非主体因素对于主体从事行为的意欲所产生的影响效应,等于在“想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可操作性”(又叫“可行性”)的问题——这里的“可”字,也是“可以”与“能够”混用的一种表现,因为它们严格说来是指某个行为的“能操作性”或“能行性”:你的能力以及种种相关因素,是不是“允许”你把“想要”从事的那个行为付诸实施,并且如愿以偿地得到你认为“值得意欲”的那个目的善呀?倘若答案是肯定的,这个行为就被认为具有可行性,反之则被认为没有可行性。例如,你“想要”报考一所名牌大学,就得面对有时候很残酷的“能够”问题:一方面,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学习能力和时间,掌握足够的知识,取得足够好的成绩,最终美梦成真呢?另一方面,你想要报考的大学是不是会在你所在的地区招收你感兴趣的那些专业?同届考生的超常发挥是不是会让你在竞争中遭受挫折?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成语,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上述两方面缺一不可的纠结作用。“谋事在人”不仅涉及主体方面的“想要”,而且涉及主体方面的“能够”。主体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允许”他谋划和实施一件事情呢?相比之下,“成事在天”则涉及非主体方面的“能够”:主体之外的种种因素(包括自然界和其他人等),是否“允许”主体凭借能力实施一件事情,并且取得成功?正是两方面的这种纠结作用,让“能够”的问题变得十分残酷,构成了一个人不管多么强烈地以“我欲故我在”的方式“想要”,都无法为所“欲”为的首个制约因素:在他认为是“值得意欲”的好东西中,只有一部分是他“能够意欲”的,另外一部分则是无论他如何“想要”也“不能意欲”的。〔9〕所以有了那句流行的谚语:“天上飞的十只鸟,不如手里的一只鸟”,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由于你无可摆脱的内在有限性,许多让你无比憧憬的好东西,哪怕你心里再“想要”,对你来说也不过是白日梦式的虚幻“想要”。
于是,尽管“想要”和“能够”直接相关,二者却呈现出某些深刻的差异,不可混为一谈,尤其不可误以为“值得意欲”的东西都是“能够意欲”的:作为意志的直接体现,“想要”构成了人们一切诉求的自觉起点;相比之下,“能够”主要位于认知特别是“自知之明”的维度上,涉及人们对于自己能力以及相关因素的如实描述,因此偏重于解答这些能力以及相关因素是不是“实际上”允许主体实现意志诉求的问题。像英语和德语里的“can”和“kann”,就同时具有“能够、有能力、会、知道如何做”的意思,折射出了“能够”与“认知”的特殊关联。
从这里看,混淆“想要”和“能够”,其实就是广义上的“把应然当实然”了:误以为自己“想要”实现的应然性诉求,一定是“能够”达成的实然性状态,所谓“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不错,它们是人们经常发出的美好祝愿,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谁要是不加辨析地轻易相信了,真把“心想”和“事成”看成一回事,却忽视了“能力”在两者间扮演的重要角色,以致按照“只要你想要,一定能做到”“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模式从事行为,十有八九会因为自身有限性的缘故,遭遇挫折甚至失败。说穿了,即便“全能”的上帝“能”以“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的“心想事成”方式,把自己的大多数“想要”变成“能够”,他也无法将“画出圆形之方”的“想要”以“万事如意”的方式变成“能够”。
另一种常见的混淆是,人们往往把“不想”和“不能”搅和在一起,用客观上“不能”的实然性借口掩盖主观上“不想”的应然性诉求。例如,两千年前《墨子·兼爱下》就从这个角度反驳了当时流行的“兼之不可为也,犹挈泰山以超江河”的论调,指出:如果说举起泰山、跨过江河确实不在人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因而属于“不能”的话,那么,“不可害人,兼爱交利”的正义原则却一直是力所能及的实践目标;所以,那些主张“兼之不可为”的人们,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这样做。事实上,一千多年后朱熹依然宣称:“人也只孝得一个父母,哪有七手八脚爱得许多”(《朱子语类》卷五十五),还是拿“能力有限”作为论证“人只能孝父忠君,没办法爱得许多”的理据,没有察觉到这里的要害不在“能不能”,而在“想不想”:要是你原本就“不想”爱得许多,哪怕长出了三头六臂,你照样会找到借口,强调自己“不能”爱得许多。有鉴于此,无论“想要”和“能够”的关联多么直接,我们仍然有必要清醒地意识到,二者分别处于广义的应然性和实然性维度上,不然就会因为忽视了它们的这种深刻差异,造成理论上的扭曲和实践上的误导。
三、作为应然性“允许”的“可以”
第二节提到,“可以”与“能够”都有泛指“允许”的相通语义,因此,“这个可以有”的说法,也就等于承认“这个允许有”。不过,与“能够”偏重于从实然性能力的角度表述主体“想要”从事行为的“能操作性(能行性)”不同,“可以”偏重于从应然性权衡的角度表述主体“想要”从事行为的“可接受性(可从性)”,从而在“想要”和“能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下面的问题:某个好东西你不仅“想要”得到,而且还“能够”得到,但在它与其他好东西发生抵触的“诸善冲突”情况下,你对它们的主次轻重作出的权衡比较,是不是“允许”你把你的“想要”付诸实施,从事“能够”得到这个好东西的行为,并且“可以”接受由于其他好东西在冲突导致的“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结构”中被否定所生成的负面后果呢?于是,一旦嵌入了这样的语境,我们会发现,“想要”以及“能够”与“可以”在情态助动词系列里的语义互动,和人性逻辑链条里“善(好)”与“正当(对)”、“值得意欲”与“可以接受”、“成功学”与“正当论”的哲理关联是根本一致的。〔10〕
举个例子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刚才的抽象论述:我有烟瘾(“想要”),同时收入等也允许(“能够”),但我是不是因此就“可以”随意实现抽烟的“想要”呢?倘若我意识到了我指向抽烟和健康的两种意欲处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中,得到了其中一个好东西就会失去另一个好东西,事情就取决于我对它们的权衡比较以及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结构的具体情况了:要是我觉得健康之善的重要性超过了过瘾之善,我就会认为,尽管抽烟的行为是我既“想要”、也“能够”的,却又是“不可允许”的(因为抽烟之善在悖论性结构中造成的患病之恶在我看来“不可接受”)。相反,要是我觉得抽烟之善的重要性超过了健康之善,我却会认为,抽烟的行为对我来说不仅“想要”和“能够”,而且也是“可以”的(因为抽烟之善在悖论性结构中造成的患病之恶在我看来“可以接受”)。类似的情况同样会出现在人际冲突中: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虽然我既“想要”、也“能够”,但“可不可以”抽烟呢?由此不难看出,人们经常问的“我能不能在此抽烟”,严格说来其实是“我可不可以在此抽烟”的意思。
于是,只要两个值得意欲之善出现了无法兼得的冲突,人们就不得不在“想要”和“能够”的基础上面临“可以不可以”的问题,从而彰显了“可以”不同于“能够”的独特语义。具体说来,它们分别是从善与正当的不同维度出发,对于“是否允许”人们把“想要”付诸实施发挥着不同的效应:“能够”意味着“允许”人们“成功”地实现“想要”的某种善,“可以”意味着“允许”人们“正当”地实现“想要”的某种善;反之,“不能”意味着“不许”人们“成功”地实现“想要”的某种善,“不可”意味着“不许”人们“不正当”地实现“想要”的某种善。所以,尽管在“允许”的语义上彼此相通,两者却时常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能够”的行为“不可”从事,“不能”的行为反倒“可以”从事;“可以”的行为“不能”成功,“不可”的行为反倒“能够”成功。转换成人性逻辑的术语说则是:“成功”的行为可能是“不正当”的,“失败”的行为反倒是“正当”的;“正当”的行为可能会“失败”,“不正当”的行为反倒能“成功”——所以说成功学与正当论深度有别。
人们在日常言说中往往将“能够”与“可以”混为一谈,主要就是因为忽视了两个助动词的上述差异。诚然,如果“想要”—“能够”—“可以”原本是一致的,这类混用倒也无伤大雅,因为它们只是以不自觉的方式,显示了“值得意欲”—“能够意欲”—“可以意欲”的前后一贯。不过,如果由于冲突造成了“能够”与“可以”之间的不一致,这种混用就会陷入“为了追求成功之善却犯下不正当之错”的悖论性结局了。用前面的例子说,假如我仅仅出于自己不仅“想要”、而且“能够”的考虑,便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却忘记了还有一个“可以”的情态助动词在那里,也许有一天就要面对不治之症追悔莫及了。另一个反差更强烈的例子是:即便你“有能力”杀人,你也“不可以”这样做。理由很简单,“可以”和“正当”的直接关联,同时也蕴含着“可以”和“权益”在人伦关系中的直接关联:即便你“有能力”杀人,你也没有杀人的“权益”。〔11〕有鉴于此,不管从人性逻辑的角度看,还是从语义逻辑的角度看,我们都有必要牢记一点:你“能够”做的不见得就是你“可以”做的,因为“能行(能够从事)”的事情也许是“不对(不可接受)”的。
在学术话语里,混用“能够”和“可以”同样会导致荒唐的结果,像语言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就在《逻辑哲学论》里犯下了这方面的失误。首先,他声称“逻辑的先天性在于我们不能非逻辑地思考”,〔12〕就是用“不能”替代了“不可”,没有看到人们是完全“能够”非逻辑地思考的,并且任何人一生中非逻辑地思考的时间,或许还超出了合乎逻辑地思考的时间。说穿了,他的本意是想说:由于所谓“逻辑的先天性”,人们“能够”从事的非逻辑思考从根本上就是“错”的,“不可”接受。其次,他在全书结尾处得出的那个经典结论——“对于不能(nicht…kann,cannot)言说的东西必须(muss,must)保持沉默”,〔13〕也有类似的毛病:“不能”言说的东西明显意味着超出了人们言说的“能力”,亦即“能力不允许”;既然如此,命令人们“必须”对它们保持沉默,岂不等于多此一举?进一步看,要是把这个结论译读成“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似乎还是画蛇添足:“不可”言说的东西原本就是“规则不允许”或“被禁止”的,哪里用得着再要求人们“必须”对它们保持沉默呀?
不过,在强调了两者的区别后,我们也不要忘了“能够”和“可以”在“允许”语义上的彼此相通:一个人的任何“想要”,都会在“能够”和“可以”两个方面受到“是否允许”的限制,以致其中有任何一个方面不允许,他却依然将自己的“想要”付诸实施,结果就是要么失败、要么犯错,并且导致他遭受相应的惩罚。就此而言,从人性逻辑和语义逻辑的统一视角看,像“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样的口号,便属于双重性的无法成立了,因为它们忽视了任何“想要”都会同时受到“能够”和“可以”的双重约束。
四、作为强制性“迫使”的“应当”和“必须”
在情态助动词系列里,“应当”和“必须”的哲理内涵也许最明显了,因为人类行为涉及的肯定性“义务”,不管位于哪个价值领域(道德、认知、实利、信仰或炫美),都只有通过它们特有的强制性“迫使”语义才能表述出来。
从人性逻辑的角度看,“应当”和“必须”如同“可以”一样,也是由于诸善冲突的原因,才在“想要”以及“能够”之后出现的。不过,与“可以”偏重于“允许”从而给予了人们自由选择的空间不同,它们突显了在诸善冲突中形成的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结构的强制性意蕴:对于某个既“想要”、又“能够”、还“可以”的好东西本身,人们是谈不上受强制去追求的,只会按照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心甘情愿地得到它。可是,一旦处在与其他好东西的冲突中(包括要耗费精力时间这些属于能力范畴的好东西的广义冲突),人们就“不得不”根据主次轻重的权衡比较,评判自己是不是“有必要”在悖论性结构中,以忍受某些尚可接受的坏东西为代价,努力得到这个重要的好东西了;倘若答案是肯定的,人们就觉得自己有“义务”采取行动,“应当”甚至“必须”(而不仅仅是“可以”)追求这种好东西。
例如,单就考大学是你既“想要”、又“能够”、还“可以”的好东西来说,你是不会感到受强制去做的;毕竟,谁会被“逼着”去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目的呢?不过,一旦你心甘情愿地将它付诸实施,却会发现,要达到这个朝思暮想的可欲之善,你就“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时间投入到枯燥的学习中,以致你没法再追求其他方面的享受了。正是这样的严峻冲突,迫使你通过权衡比较来评判考大学对你的重要性:如果它对你来说十分重要,你会觉得付出那些代价是“值得”的,自己“应当”甚至“必须”考大学;如果它对你来说不那么重要,你会觉得付出那些代价“不值”,于是就把考大学划归“无可无不可(可考可不考)”的范畴了。人际“应当”的形成机制也与此类似:通过国家机器颁布的法律“义务”,实质上就是诉诸像坐牢蹲监狱这类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严重惩罚,强制性地命令社会成员“必须”遵守它们,以求维系被认为是不仅“值得意欲”、而且“至关紧要”的社会秩序。一言以蔽之,“应当”和“必须”作为“义务”的本质就是:在诸善冲突中,人们哪怕“不得不”忍受某些次要的恶,也“不可不”达成某种重要的善。〔14〕
所以,从语义逻辑的角度看,“应当”和“必须”(以及“应该”和“必需”)的共通语义都是“迫使”,偏重于从应然性权衡的角度表述主体“想要”从事行为的“应强制性”,从而在“想要”“能够”和“可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下面的问题:某个好东西你不仅“想要”和“能够”得到,而且还“可以”得到,但在它与其他好东西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你对它们的主次轻重的权衡比较,是不是会“迫使”或“逼着”你把你的“想要”付诸实施,从事“能够”得到这个好东西的行为,并且“可以”接受由于其他好东西在冲突中被否定所生成的负面后果呢?于是,一旦某种“能够”和“可以”的“想要”是你“应当”或“必须”付诸实施的,它就不再享有“无可无不可”的淡定空间了,而是会受到“不可不”确保重要善和“不得不”忍受次要恶这双重“义务”的严格限定。至于“应当”和“必须”的区别,主要涉及强制性的程度或力度(“必须”比“应当”的强制性更高),并与要确保之善的重要性和要忍受之恶的严重性直接相关。同时,我们不妨对“应该”与“应当”、“必需”与“必须”的区别也作出一点微妙的辨析:尽管都卷入了诸善冲突,“应该”和“必需”主要是在善的维度上提出强制性的要求,逼着你努力克服“能够”方面的阻碍,“成功”地实现目的善;“应当”和“必须”主要是在正当维度上提出强制性的要求,逼着你努力克服“可以”方面的阻碍,“正当”地确保重要善。换言之,“应该”和“必需”是就“成功”说的,“应当”和“必须”是就“正当”说的。另外有必要说明的是,与主要意指认知维度上事实存在的“实然(being)”相对而言的“应然(oughtness)”,并非仅仅意指具有强制性意蕴的“应当”或“应该”,而是在广义上泛指意志维度上涉及所有价值诉求的“想要”“能够”“可以”“应当”和“敢于”,在狭义上特指意志维度上涉及所有非认知价值诉求的“想要”“能够”“可以”“应当”和“敢于”。
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的“可以”“应当”和“必须”在以否定形式表述出来的时候,语义会呈现某些微妙的变化,并且也不是与西方语言里的情态助动词一一对应的:一方面,“不应当”与“应当不”可以说是彼此等价的,都是旨在表述“should not”的强制性禁令:“你不应当在此抽烟”;“对下列情形登记机构应当不予登记”。另一方面,“不可以(may not)”和“必须不(must not)”则是比“不应当”强制性更高的禁令:“你不可以在此抽烟”;“紧要关头必须不退缩”。相比之下,“可以不”和“不必(not have to)”反倒和“不需要(need not)”相似,不再具有强制性,而是进入了“无可无不可”的宽松状态:“你可以不(不需要)考大学”;“弟子不必(无需)不如师”。
按照上面分析的语义逻辑,康德主张“应当意味着能够(Ought Imply Can)”,〔15〕在下面的意思上就可以成立了:如果某个行为完全超出了一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如“挈泰山以超江河”或“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它对这个人就谈不上“应当”。不过,倘若某个行为只是由于难度较大、不易成功,部分超出了一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如“攀登泰山,横渡江河”或“不可害人,兼爱交利”),它对这个人来说还是有理由成为“应当”的。澄清这一点的目的,是防止有人又拿“哪有七手八脚”之类的相对“不能”作借口,免除自己“不想”履行的“应当”义务。至于康德主张“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义务”,〔16〕倒是流露出依据理性主义偏见割断“应当”与“想要”之间联结的苗头,在将“应当”认知化、理性化和形式化而抽空其实质性善恶内涵的同时,不仅会让良善意志沦为只服从理性义务、却无法从心所欲、因而不再自由的抽象逻辑法则,而且还容易生成依据德性制高点实行道德绑架的意向,值得我们反思和批判。〔17〕
五、作为冒险性“决断”的“敢于”
“敢于”处在情态助动词系列的末尾,其核心语义是“冒着风险付诸实施”,偏重于从应然性权衡的角度表述主体“想要”从事行为的“敢决断性”,从而在“想要”“能够”“可以”和“应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下面的问题:某个好东西你不仅“想要”“能够”和“可以”得到,而且还“应当”得到,但在它与其他好东西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你对它们的主次轻重的权衡比较,是不是会让你作出“决断”,不惜冒着种种风险,把你的“想要”付诸实施,从事“能够”和“应当”得到这个好东西的行为,并且“可以”接受由于其他好东西在冲突中被否定所生成的负面后果呢?
在日常言说中,人们往往是在风险较大的语境下,才会运用“敢于”助动词表述自己对某种“想要”的决断。但从人性逻辑的角度看,只要存在诸善冲突及其生成的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结构,这种冒险性的决断对于落实任何“想要”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想要”就会耽于“想入非非”的境地:由于人们在冲突状态下趋于任何值得意欲之善的时候,都必然会在悖论性结构中冒着生成某些反感讨厌之恶的风险,就像白日梦做多了也可能罹患精神病那样,“敢不敢”的问题就将始终萦绕在人们的脑海里,决定着他们是不是迈出关键的一步,把自己心中对于某种好东西的意志性诉求,转变成脚踏实地的实践性行为——只不过在风险不大的情况下,人们通常会对风险忽略不计,直接将“能够”“可以”和“应当”的评判转化成付诸实施的决断罢了。
就此而言,缺少了“敢于”的“最后一跃”,此前讨论的那些情态助动词就将停留在主观心理维度的“帮助”上,不足以让实义动词表述的行为在现实中真正展开了。因此,“敢于”助动词也可以说是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在付诸实施的更高层面回归到了作为起点的“想要”那里:尽管包含了程度不同的种种“不能”“不可”“不应”等因素,主体依然意志坚挺,甘冒交织而来的坏东西对自己造成损害的风险,有胆量作出把指向某个好东西的“想要”付诸实施的坚定决断,如肯定性的“我敢玩蹦极”,否定性的“他不敢按这个题目写博士论文”等。
由于拥有这种将“心里想要”升华成“实践行为”的最后一跃功能,在现实生活中,“敢于”助动词还会影响到人们的品格塑造,发挥“从做事到做人”的重要效应,从而进一步见证了人性逻辑与语义逻辑的两位一体。问题在于,面对“敢不敢”的冒险挑战,由于先天脾性、后天历验、文化积淀、当下境遇等因素的复杂影响,人们总是会作出两类不同的决断:一方面,胆小者在风险不大的情况下,也不敢将“想要”付诸实施,因为他们担心失败或犯错会给自己带来惩罚之恶。“因噎废食”就是这方面的极端例证:尽管确实存在因噎致死的风险,大多数人在做出了“我应当吃饭”的评判后,都会直接将这种“想要”付诸实施,“无需”诉诸“敢于”的助动词,可胆小者却会仅仅因为担心这点风险给自己带来的危害,居然到了放弃决断、拒绝进食的地步。另一方面,胆大者在风险很大的情况下,也敢于将“想要”付诸实施,几乎到了对于任何交织而来的惩罚之恶都无所畏惧的程度,如“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人有多大胆,就有多少钱”等。毋庸讳言,这些不同的冒险取向肯定会促使不同的人在类似境遇下做出不同的选择,最终导致他们的人生轨迹甚至活法也呈现出鲜明的反差,从而清晰地展示了人的存在与日常语言的直接关联。
从孔子和柏拉图起,中外哲学家往往喜欢把“勇敢”当成一把肯定性的德性标尺,用来评判和褒贬人们在现实中具有的不同冒险取向。其实,从人性逻辑的元价值学视角看,这些通过“敢于”助动词的语言表述呈现的冒险取向,只是体现了不同人们在个性品格方面的实然性歧异,还谈不上是否具有勇敢德性的应然性内涵。例如,“拼死吃河豚”的赌它一把,乃至“违反法律滥杀无辜”的铤而走险,尽管都是孤注一掷的“敢于”决断,但我们与其给予“勇敢”的规范性赞誉,不如作出“鲁莽”乃至“凶残”的应然性评判。
六、人是语言家园的主人
情态助动词除了具有前面分析的位于意志维度上的“非推测意思”外,还有位于认知维度上的“推测性意思”,两者的互动关联构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本来是表述人们意欲志向的情况状态的助动词,怎么还能从认知角度推测各种事实(包括自然事实)的情况状态(特别是未来趋势)呢?这些推测性意思究竟来自何处呢?就连维特根斯坦对此也感到困惑,曾在关注日常语言的后期哲学中这样发问:“当某人说‘你将—要这样做(Du wirst das tun,You will do this)’的时候,他或许不是把这句话当成了‘预言’,而是当成了‘命令’。那么,是什么使同一个语句或者成为预言,或者成为命令的呢?”〔18〕虽然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却能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此类现象作一些初步的阐释。
首先,我们可以诉诸人类语言中经常出现的“拟人化”机制:尽管情态助动词原初只是用来表述人们主观意志的情况状态,但如同“山在欢呼海在笑”这类涉及实义动词的现象一样,它们也能通过拟人化的途径扩展到也有主观心理的其他动物那里,甚至扩展到没有主观心理的其他生物乃至无机物那里,用来描述它们的存在状态特别是未来趋势,以致人们常常说,太阳明天“将要”照常升起,电脑“能够”干许多活,这种作物“可以”在南方生长,再过五分钟泥石流就“应当”到达这里了,石头“必定”沉到水底,那颗小陨石居然“敢于”撞击地球等。至于这里的拟人化往往用于推测事实的未来趋势,也与人们的意欲志向主要指向了未来要从事的行为内在相关。
其次,对于维特根斯坦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诉诸由于认知和非认知两类不同需要形成的“诉求语句”与“描述语句”的内在区分:一方面,人们用来表达自己任何需要(包括认知需要)的语句都是“诉求语句”;另一方面,人们基于认知需要指认各种事实(包括价值性事实)存在状态的语句都是“描述语句”。〔19〕因此,如果张三对李四说“你将—要(必—定)这样做”的意图是表达自己的某种需要(希望或要求他考大学、说实话、提高艺术修养等),它就是一个意志维度上的“命令”;但如果张三对李四说“你将—要(必—定)这样做”的意图是从好奇的角度指认张三未来会做些什么(觉得他会考大学、说实话、提高艺术修养等),它就是一个认知维度上的“预言”或“推测”,其理据主要是张三对李四以往拥有这类意欲志向以及将它们付诸实施的情况状态的实然性把握(如根据李四好学的一贯表现推测他“必定”会考大学等)。
值得注意的是,两种解释的视角虽然不同,却有一点彼此相通:都认为情态助动词在认知维度上的推测性意思来自它们在意志维度上的非推测意思——“will”的“想要—将会”和“must”的“必须—必定”特别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虽然“能够”与其他助动词有所区别,不是直接表述人们的意志诉求本身是怎样的(“想要”“可以”“应当”“敢于”做什么),而是偏重于表述人们的能力以及相关因素是否允许他们将意志诉求付诸实施,因而更依赖于有关人们的能力以及相关因素的实然性描述,但我们也能看到非推测意思在此对于推测性意思的根源性:比较一下“他‘能够’干许多活”与“电脑‘能够’干许多活”两个语句,我们会发现,后一个语句其实也潜含着“电脑‘想要’干许多活”的拟人化预设。此外,亚里士多德把“可能(possible)”的事情解释成人们“力所能及做到”的事情也能启发我们,〔20〕将“可能”和“不可能”这对实然性的描述概念看成是“可以”和“能够”这两个表述应然性意志诉求的情态助动词的叠加结晶:既然一个人不仅“能够”、而且“可以”做的事情对他来说就是“可能”的,反之则是“不可能”的,人们自然也可以通过拟人化的途径,用它们指认各种事实(包括自然事实)的两种不同存在状态:“今年夏天可能有几个强台风”,“无中生有是不可能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汉语里,“可能不”的语义接近于“可以不”,“不可能”的语义接近于“不可以”。
通过分析情态助动词系列的语义演变说明了人性逻辑与语义逻辑的统一后,作为本文的结束,我们就能批判性地重新阐释海德格尔的名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了:一方面,这句名言深刻指出了人与语言的“存在论”关联,强调不能只从交流手段或形式符号的角度理解语言对人的意义,从而彰显了语言哲学与“此在存在论”之间的密切关联。〔21〕另一方面,当海德格尔因此把语言从人的存在中剥离出来,赋予语言先于人的存在的决定性地位,甚至主张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通过人自我表达出来,强调“语言才是人的主人”的时候,〔22〕他又落入了反客为主的异化泥潭,在让语言具有神秘的先在性主体地位的同时,反倒让人成了受到语言掌控的被动傀儡,结果不仅自己钻进了说不清楚的牛角尖,而且连带着让不少拿这句名言做文章的论者也经不起魅惑,不知不觉步入了走不出来的理论迷宫。无论如何,否定了人的主体地位,离开了人的存在蕴含的种种价值内容及其遵循的人性逻辑,以主人自居而自顾自地言说自己的语言,只能沦落为没有意思的“说大话”“放空炮”。迄今为止很少见到把语义分析与人的存在具体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流行的大多是一些类似于“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大地上歌声如风”这样看似高深莫测玄乎其玄,其实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美文学华丽辞藻,不能不说是海德格尔这种非理性地故弄玄虚所导致的一个负面后果。
有鉴于此,我们只有将这句名言置于日常现实的基础上,对它展开“去神秘化”的“祛魅”,才能让它的本来含意如其所是地显露出来:人首先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说出了语言,按照自己的存在方式形成了自己的言说方式,遵循着人性的逻辑塑造了语义的逻辑。所以,只有人才是语言的主人,才能运用语言达成种种目的,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澄明”自己的存在这个重要的目的。与此同时,语言又不仅仅是一种单纯为人所用的外在工具,而是始终内在于人的存在之中,发挥着颇为独特的积极效应:它不仅通过言说“澄明”了一旦缺失言说就会处于遮蔽状态的人的存在,让人的存在及其价值内容充分敞开,而且还能让人通过自己的言说改变自己的存在,运用语义的逻辑丰富人性的逻辑。归根结底,人就是因此才在自身存在和日常言说的统一中,作为主体寓居在自己的家园里。最后,也是基于“语言澄明了人的存在”这条理由,我们才有必要通过具体考察人们的日常言说,深入揭示人生在世的生活轨迹,探究人在自己家园中的存在真相,说明人性逻辑与语义逻辑是怎样统一的。
注释:
〔1〕〔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66页。出于行文统一的考虑,本文引用西方译著时,会依据英文本或英译本略有改动,以下不再注明。
〔2〕刘清平:《找寻经济学原理中的“人性逻辑”——米塞斯行为逻辑学批判》,《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3〕刘清平:《“人为”与“情理”——中国哲学传统的基本特征初探》,《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3期。
〔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5〕刘清平:《需要概念在人生哲学中的原点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1页。
〔7〕刘清平:《为自由祛魅——自由意志的悖论解析》,《关东学刊》2018年第5期。
〔8〕刘清平:《怎样界定善恶概念——兼析元价值学与规范价值学的区别》,《人文杂志》2016年第3期。
〔9〕就此而言,“可欲之谓善”的概念界定其实也潜含着双重性的语词误用,因为它先是把“值得意欲”与“能够意欲”混为一谈了,然后又把“能够意欲”与“可以意欲”混为一谈了。严格说来,只有“值得意欲之谓善”才是一个精准的定义;无论在此之上再增加“力所能及”的限定,还是再增加“可以允许”的限定,都会离开“想要”的原初层面造成扭曲。
〔10〕刘清平:《“避恶”对于“趋善”的前提性意义——兼论“成功学”与“正当论”的关系》,《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11〕刘清平:《论正当、权益和人权的关联》,《学术界》2013年第9期。
〔12〕〔13〕〔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69、97页。
〔14〕刘清平:《“应当”强制性的根源》,《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15〕〔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0页;杨松:《“‘应该’蕴含‘能够’”(OIC)原则与义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6〕〔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14页。
〔17〕刘清平:《理性但不自由的良善意志——康德良善意志观的悖论解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18〕〔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16页。
〔19〕刘清平:《合乎事实之“真”与合乎逻辑之“明”——析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悖论》,《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2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9页。
〔21〕王遥、李景娜:《语言何以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语言观浅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22〕〔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