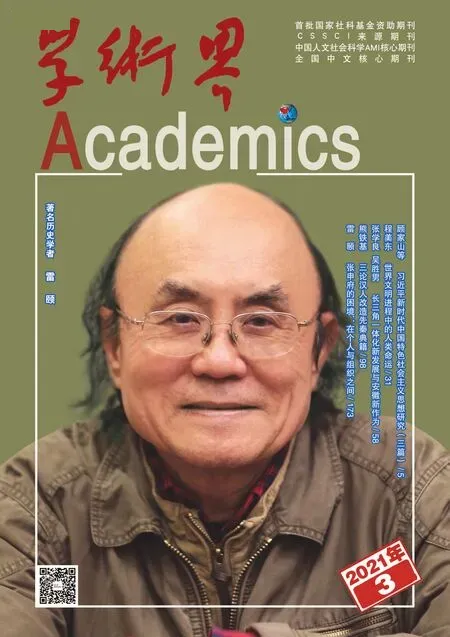柳宗元、韩愈对欧阳修“穷而后工”论影响关系新辨〔*〕
杨再喜
(湖南科技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湖南 永州 425199)
一、问题的缘起
欧阳修(1007—1072)“穷而后工”论主要见于他的《梅圣俞诗集序》〔1〕、《梅圣俞墓志铭》〔2〕和《薛简肃公文集序》〔3〕等文献之中。对于“穷而后工”论的溯源,现普遍认为,唐代韩愈(768—824)的“不平则鸣”〔4〕对其产生了直接影响,是其重要源头。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较为集中在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材和文学理论专著之中,〔5〕通过广泛传播,这也极大提升了“穷而后工”论的历史地位。毫无疑问,这些成果对于追溯“穷而后工”的历史渊源,揭示“不平则鸣”对于“穷而后工”的历史影响,是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欧阳修“穷而后工”论直接承接韩愈“不平则鸣”的论断,大都也只是局限于近现代学者研究中的一些结论性观点,对于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和接受原因还缺乏深层次的分析。同时,还必须看到,有一些学者对于欧阳修“穷而后工”论与韩愈“不平则鸣”直接承接的关系提出了疑问,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甚至是两个不同的范畴。〔6〕
面对上述情况,我们就会思索,在对“穷而后工”论的溯源中,除韩愈“不平则鸣”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对其产生更深刻影响的文学理论呢?实质上,已有学者把与韩愈同时代并与之在文学史上相提并论的柳宗元(773—819)所提出的“感激愤悱”同“不平则鸣”进行了对比,一方面认为两者存在着相通之处,另一方面指出“感激愤悱”在内涵上更加丰富深刻,在现实意义上更为积极进步。〔7〕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推断,柳宗元“感激愤悱”对于欧阳修“穷而后工”论的影响程度是不可能低于甚至有可能高于韩愈“不平则鸣”的。基于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只是偏执于一端只看到韩愈的“不平则鸣”,却不顾柳宗元“感激愤悱”对于欧阳修“穷而后工”论的影响。可目前学界尚没有专文把柳、韩两人在此方面的文学思想对“穷而后工”论的影响关系进行较深入的比较。本文就是基于这些认识,有意进行一些尝试,望以此来说明“感激愤悱”对欧阳修“穷而后工”论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是其重要的源头。
二、柳宗元“感激愤悱”与“穷而后工”论在内在关联程度上更为接近
柳宗元“感激愤悱”的文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文献之中,他在《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说道:“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以(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娄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术未用,故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辞。以余弟同志而偕未达,故为赠诗,以悼时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预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间,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将俟夫木铎以间于金石。大凡编辞于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8〕柳宗元自身与文中的娄二十四秀才(娄图南)有着相似的境况遭遇,故以诗文赠之。该文认为“君子”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是“感激愤悱”之情,进行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在文章、歌咏中得以体现济世之心,以求有益于世。那么,这种积极用世的“感激愤悱”之情来自何处呢?柳宗元在《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中进而指出:“吾观古豪贤士,能知生人艰饥羸寒、蒙难抵暴、捽抑无告,以吁而怜者,皆饱穷厄,恒孤危,訑訑忡忡,东西南北无所归,然后至于此也。今有吕氏子名让……不目小民农夫耕筑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独粹然怜天下之穷氓,坐而言,未尝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积于中,得于诚,往而复,咸在其内者也。彼告而后知,示而后哀,由外以铄己,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积,诚之得,其为贤也莫尚焉……﹙吕让﹚今来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辞以通,然后及乎物也。’”〔9〕认为“志士”们的“感激愤悱”之情来自于对社会人生的深入关切,来自于对百姓苦难遭遇的感同身受,主张把个人的情感和积极用世相统一,创作出“以效于当世”的文学作品。
细加比较,柳宗元“感激愤悱”与欧阳修“穷而后工”论的文学思想在内在关联的程度上基本接近,而在这些方面韩愈的“不平则鸣”很少或者没有较深入的论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本文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10〕将范围和内容进行拓展,现试比较如下:
其一,在创作主体方面,柳、欧两人都强调文学创作是“君子”所为。柳宗元认为由于“感激愤悱”而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大都是“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的“君子”;〔11〕欧阳修也指出“见于文章”是“君子之学”,〔12〕并且特别推崇梅尧臣“可谓君子者也”。〔13〕何谓君子?“天下之有德,通谓之君子。”〔14〕这道出了君子的共性,但柳、欧两人在其文论中所指的“君子”还呈现出特定的涵义。首先,对于他们的人生遭遇,柳宗元称其为“太平之不遇人”,〔15〕欧阳修称其为“失志之人”。〔16〕其次,对于他们的人生志向,柳宗元提出“君子学以植其志,信以笃其道”,〔17〕认为真正的“君子”都是立志笃道之人。对于“志”与“道”的涵义,柳宗元进而指出“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18〕欧阳修是一个“君子”意识很强的人,他认为君子的操守是“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19〕君子的作为是“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20〕君子的性格是“仁厚乐易,未尝仵于物……而不怨怼。”〔21〕两人基于对文学创作主体“君子”之一致的认识,也必将这一理念贯穿于文学实践中,在文学思想上具有更多的共鸣。
其二,在创作动因方面,由柳宗元的“感激愤悱”〔22〕到欧阳修的“感激发愤”〔23〕和“忧思感愤”〔24〕,都强调情感的感愤激发是文学创作的动力。“愤悱”一词最早出自《论语·述尔》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之语,前后句为互文,“启愤”“发悱”也可视为“发愤”“启悱”,因此从字面上看,柳宗元所主张的“感激愤悱”与欧阳修的“感激发愤”是基本一致的。朱熹的《论语集注》解释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从中可以这样理解,“愤”谓思虑不通畅之时烦闷郁积的心理状态,“启愤”即通过启导使憋闷的心理状态得以疏解;“悱”谓心有所思而口不能言的状态,“启悱”即通过恰当的词语为载体以表达出来。总体而言,所谓的“愤悱”或者“发愤”是指“作家创作前情感郁积于心的憋闷的心理状态”。〔25〕进而言之,柳宗元的“感激愤悱”主要是指文人出于对社会的深刻理解和责任担当,而产生出一种愤激的变革现实的情绪和要求。当“贤者不得志于今”,〔26〕这种激愤之情未能实现之时,就要“发其郁积”,〔27〕就会把这种情感寄诸文学作品中,以求得世人了解的言辞。欧阳修的“感激发愤”主要指“失志之人”在经过“忧思感愤之郁积”后,所发出的忧时愤世而不能的深沉感叹。欧阳修的文学作品多忧愤之气,如,他在《读李翱文》的文后所发出的“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的感慨,清人林云铭对此评说道:“是篇虽赞李翱,却是借李翱作个引子,把自己一片忧时热肠血泪,向古人剖露挥洒耳。文之曲折感怆,能令古今来误国庸臣无地生活。”〔28〕我们循着这一启示,对欧阳修的文献进行检索,发现他的作品中共有292处发出了“呜呼”的感叹,而柳宗元更是甚于此,有多达381处的“呜呼”感叹之词。由此可见,柳、欧两人的忧时伤世之情的深沉激切程度之深。
相比较而言,韩愈“不平则鸣”与柳宗元“感激愤悱”在对情感理解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一是产生情感的途径不一样。柳宗元的“感激愤悱”来自于对社会人生的深入了解,因此与积极用世联系起来;韩愈的“不平则鸣”来自于外在事物的触发,更多强调个人情绪的变化。二是包含的内容不一样。韩愈“不平则鸣”中的“不平”之情“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29〕柳宗元“感激愤悱”之情主要是指对社会现实的“忧愤”。三是呈现的状态不一样。韩愈的“不平则鸣”之情多是在“情不能已”的情况下自然产生的,感性色彩较浓。这种因外物而起、率性而为的情绪表达方式,也正是柳宗元所不满的。柳宗元指出:“告而后知,示而后哀,由外以铄己,因物以激志者也。”〔30〕认为那些要别人告诉才知晓,给看了才心动的人,只不过是暂时受到外物的影响刺激而已,最后导致这种情感的产生是被动的和短暂的,而柳宗元主张的情感是“积于中,得于诚,往而复,咸在其内者也”,〔31〕这种情感是由内及外的,具有自觉性和主动性的特征,持续的时间也会更长。宋代李涂在比较柳宗元、韩愈、欧阳修等人在文中所呈现的情绪特征时说:“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慨,子瞻兼愤激感慨而发之以谐谑,读柳、欧、苏文,方知韩文不可及。”〔32〕
其三,在创作手段方面,从柳宗元的“形于文字”〔33〕到欧阳修的“寓于文辞”〔34〕,都强调在有才不被用的情况下,通过文学辞章来寄托自己的情志。《论语》有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古代士人最理想的选择是从政为官,以求建功立业;而当左迁失意、困守穷厄之际,就会退而求其次把人生价值的实现转向文章诗艺,通过文学辞章来言志明道、发愤抒情。对此,柳宗元曾指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35〕无所用于世的君子必然会激发愤悱之情,通过“形于文字”达到“文以求其志”〔36〕的目的。欧阳修认为当“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之时,就会理性地进行“寓于文辞”的写作,实现“文章发于其志”〔37〕的主张。对此,韩愈也曾指出:“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38〕但相比而言,柳、欧两人所指出的文士创作更多的是创作主体的理性选择,作为人生事业有意而为之,韩愈在此方面并没有明确强调。
其四,在创作目的方面,从柳宗元的“效于当世”〔39〕、“施于人世”〔40〕到欧阳修的“施于世”〔41〕、“施之于事”〔42〕。所有这些都是柳、欧两人服务于现实之“文用观”的共同体现。实质上,不管柳宗元的“感激愤悱”之情或是欧阳修的“感激发愤”之情,都是在无法直接“效于当世”“施于世”,即无法“行其道”而“立功”的情况下转身文学创作的。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当然是希望通过自己所著述的文学辞章达到其人生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在于通过文章以“明道”,以达到辅时及物和经世致用的目的。诚如柳宗元所言:“思报国恩,独惟文章。”〔43〕“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辞以通,然后及乎物也。”〔44〕那么柳宗元如何使文章“效于当世”呢?可以从他的《送邠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45〕窥见一斑。他在赠序中对友人独孤宓谈到,即将作为一名书记官,如果把文职人员看成只是做一些“曳裾戎幕之下,专弄文墨,为壮夫捧腹”的事情,那就是“甚未可也”;指出文人的职责可以“发群谋于章奏之笔,上为明天子论列熟计,而导扬威命”,也就是说能在奏章中充分反映将士们的智谋,向天子陈述成熟的计策,借以宣扬朝廷的威严和命令;还应该“赋从军之乐”以鼓舞士气,用“移书飞文”来“谕告”民众和犒劳欢迎朝廷的军队,只有这样才是“真可慕也”。欧阳修反复强调:“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46〕欧阳修所主张的“道”,主要指生活中的“百事”,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47〕对于这种溺于文事而不关心现实的态度是深为不满的。对于柳、欧两人所呈现出的这一共同点,当代散文家和学者孙犁(1913—2002)指出“欧文多从实际出发,富有人生根据,并对事物有准确看法,这一点,他是和柳宗元更为接近的”。〔48〕反观韩愈的文学思想,他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文学主张重在复古,对于社会政治的作用涉及相对较少,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的失意哀怨。对于柳、欧两人“文用观”与韩愈“不平则鸣”的区别,周楚汉在其著作《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中明确指出:“‘感激愤悱’与韩愈《送孟东野序》的‘不平则鸣’有所不同,‘感激愤悱’强调‘效于当世’,与‘有益于世’的文用观联系密切;‘不平则鸣’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要求。”〔49〕
其五,在创作态度方面,从柳宗元的“不苟悦于人”〔50〕到欧阳修的“不求苟说(悦)于世”〔51〕,都秉承不以个人荣辱为念,而为时代社会立言的写作态度。写作动机决定了写作的态度,柳宗元以“利安元元为务”,心中所思所念的是他心中的“道”,所以他的一生“终能毋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52〕绝不会通过媚俗附时来换取一时之誉,而是反复强调为文之要在于“不苟悦于人”“不为流俗所扇动”。〔53〕欧阳修的一生不尚时好,不慕荣利,主张为文要“多论当世利害”,〔54〕坚守着自己的文学标准和创作态度,这与柳宗元的文学思想是非常接近的。他对于梅尧臣“不求苟说(悦)于世”的态度给以赞赏;在《仲氏文集序》中对于作者仲讷“不苟屈以合世”而创作的“抑扬感激,劲正豪迈”之作品,认为“必将伸于后世而不可揜(掩)也”。〔55〕
其六,在创作内容方面,由柳宗元的“能知生人艰饥羸寒、蒙难抵暴、捽抑无告”〔56〕到欧阳修的“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57〕,都强调作家对于社会人生体验的深度和生命情感体验的浓度,决定着文学作品的高度。柳宗元所激所愤的正是百姓遭受之苦,所忧所忡的正是“辅时及物”之道的实现,这才是“感激愤悱”的根源。他主张以“辅时及物”作为创作的主要内容,把眼光投向社会人生,从自己的不幸遭遇和生活体验中去进行深刻的领悟,所以说:“吾观古豪贤士,能知生人艰饥羸寒、蒙难抵暴、捽抑无告,以吁而怜者,皆饱穷厄,恒孤危,訑訑忡忡,东西南北无所归,然后至于此也。”主张文士在遭受穷厄之时,能把个人的情感与社会相联系,把自己的遭遇与民众的苦难相统一。欧阳修主张诗歌应该“刺口论时政”,〔58〕要能够“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相比而言,韩愈的“穷苦之言易好”〔59〕只是一句结论性的话,至于作品中的哪些内容为“穷苦之言”并没有提及。同时韩愈“不平则鸣”所“鸣”的关注点“是从个人的哀怨失意,遭穷困的角度提出问题的,缺乏更广阔的社会内容”。〔60〕
其七,在创作规律方面,柳、欧两人都揭示了文人之“穷”与文学作品之“工”的因果关系。文人在经历“穷”的过程中,会形成苦闷的情绪,并且这种苦闷在一定的条件下能转化为精神的动力,促使作家“穷”而激发感愤,以强烈的情怀使命加深对社会人生、生命真谛的体验感悟,从而达到作品之“工”的程度。童庆炳先生对此曾指出:“正是在‘穷’中,诗人蓄积了最为深刻、饱满、独特的情感,正是这种带着眼泪的情感,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把诗人推上了创作之路。”〔61〕欧阳修“穷而后工”论阐释了作家在遭遇了现实生活的“不幸”之后,如何实现思想情感的深化以及由此向艺术美感转化的过程。他指出不得施于世的穷困之人,往往因不得志而自放,因自放而外见,因外见而感愤郁积,因感愤郁积而兴于怨刺,最后表现为具有一定情感和美感的文学辞章。柳宗元的“感激愤悱”说也指出,“未得行其道”的“古豪贤士”,在“知生人艰饥羸寒、蒙难抵暴、捽抑无告”的感受之后,通过“发其郁积”和“读百家书,上下驰骋”,最后“得知文章利病”,〔62〕达到了文章之“工”。
对此相比较而言,韩愈的“不平则鸣”主要是揭示创作的动因,而“穷而后工”论却更在于“强调诗人之穷与诗之工的因果关系”。〔63〕韩愈的“穷苦之言易好”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作家遭遇与文学成就的关系,但“穷苦之言易好”强调的是作品内容之“穷”,而“穷而后工”强调的是创作主体的人生遭际之“穷”。“穷苦之言易好”只是一个结论性的观点,比较简略,而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却对由“穷”到“工”的过程和原因有着较为深入的论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通过以上的比较就会发现,柳、欧两人在阐述各自的理论主张时,两者除了具有基本一致的内涵意蕴外,在阐述方式上,甚至在所使用的词汇和表达的句式上也非常相似。现试举例如下(见下页表1)。
根据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说,接受者会根据当时所具有的人生经验和审美体验等对接受对象所呈现的形式和内容等产生预测和期望,并转化成为定向性心理结构图式。显然,柳宗元“感激愤悱”的内容和形式对于欧阳修的“期待视野”而言,与其定向性心理结构图式是非常吻合的。读者出于对接受对象的过分熟悉或者喜爱,就会不自觉地化用甚至直接承袭原有的呈现方法,接受其外在的形式,这也是其定向性心理结构图式的实现,是一种最直接的接受行为。这种外在形式上的相似性是以最直观的方式表明,“穷而后工”论与“感激愤悱”具有亲缘性,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话语家族系统。
三、“感激愤悱”比“不平则鸣”有着更适合“穷而后工”论的接受语境
文学史上的晚唐、五代乃至宋代初期,受到“不平则鸣”等诗学观念影响,由于过分强调诗歌对于情绪的宣泄作用,导致了“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64〕等文学表达中伪情绪的泛滥。对此,在时代变革和文风发生根本变化的大背景下,由于“出于诗学内部自身新变的要求,也出于宋代社会政治和道德的要求,宋人对‘诗可以怨’和‘不平则鸣’的流行说法提出了尖锐的挑战”,〔65〕于是对诗歌所承担的功能和所表达的内容进行了规范修正,主张化激情为温情,以作“忧世之言”取代“叹老嗟悲”和“羁愁感叹”。北宋时欧阳修“穷而后工”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就此而言,欧、柳两人的文学主张在对于“穷”的理解和对待“穷”的态度上,比韩愈“不平则鸣”则更趋于一致,这使“感激愤悱”之思想能够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也就有着比“不平则鸣”更适合“穷而后工”论的接受语境。

表1
其一,对于“穷”之涵义的理解。欧阳修所理解的“穷”主要是“失志之人”在“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时的一种遭遇,是指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显然这里的“穷”是相对于“达”而言的,属于政治的范畴。对于“穷而后工”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梅尧臣的人生遭际,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他:“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畜,不得奋见于事业”。对于柳宗元“感激愤悱”说中的代表人物娄图南秀才,他本“志乎道”,却遭遇了“其道宜行,而其术未用”的人生坎坷,乃至柳宗元在文后感慨道:“大凡编辞于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66〕清人宋荦对此指出:“盖尝闻诸孔子曰:‘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凡位不配德,任不展才,是皆所为不得志而穷焉者之事也。”〔67〕可见,欧、柳文论中关于“穷”之涵义的理解大致属于“不得志而穷”这一类的。相比较而言,韩愈在“不平则鸣”中所指的“穷”,其主要内容是指“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68〕的个人困穷生活状态,对于生活困顿的过分强调,显然属于经济的范畴。韩愈在《送孟东野序》文中所描述的“不平则鸣”代表人物孟郊,他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贫寒的生活和苦涩的人生使孟郊常在其作品中“自鸣其不幸”。在宋代,士人群体的经济待遇是相对优渥的,他们所肩负的主要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政治担当。显然,在士人群体洋溢着政治情怀与使命担当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柳宗元“感激愤悱”对于“穷”之涵义的理解与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是一致的,也自然就比“不平则鸣”更加深刻地影响着“穷而后工”论。
其二,对待“穷”的态度。在宋代,性命之学盛行,文士们追求的是一种身达心亦达,即使身穷心亦达的精神境界,所以“无论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还是韩愈的‘不平则鸣’都未能得到宋人的呼应,因为这两个命题都含有发牢骚之意,与宋人的中和诗论相左。”〔69〕以“自持、自适”的心态推崇“穷而后工”成为宋人在这个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于诗歌本质的理性探讨。苏轼说:“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此语信不妄,吾闻诸醉翁。”〔70〕王安石也在其《哭梅圣俞》一诗中评价梅尧臣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成就时,有感而发:“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公窥穷阨以身投,坎轲坐老当谁尤。”〔71〕欧阳修作为这个时代的精神象征,对于外在的得失,他认为应该做到“君子轻去就,随卷舒,富贵不可诱。故其气浩然;勇过乎贲、育,毁誉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见于喜愠”。〔72〕所以,他所郁积的“忧思感愤”,是一种深沉忧患意识,而非穷酸的牢骚不平;所要作的是“忧世之言”,而非“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73〕这种不戚戚于个人进退得失和心忧天下的情怀,正如欧阳修在《梅尧臣墓志铭》中赞叹梅尧臣所言,称其:“不戚其穷,不困其鸣。不踬于艰,不履于倾。养其和平,以发阙声。”欧阳修秉承身穷志亦达的理念,努力化悲怨为旷达,化酸楚以闲暇,把文学创作作为安顿人生精神的家园,真正做到了自己所标榜的“能不戚戚于穷厄,而泰然自以为乐者……所以自乐而忘忧者诗也”。〔74〕
柳宗元的“感激愤悱”对传统的由穷而生怨的观点有所突破,在才不被用,身处穷厄之时,秉持着“贫者士之常,今仆虽羸馁,亦甘如饴矣”〔75〕的态度,认为应该“居易俟命,乐天不忧”,〔76〕要积极入世,能知百姓的“艰饥羸寒”,为他们的苦难而奔走呼喊。在“感激愤悱”之情主导下,柳宗元文章内容充满了进取精神,较之于韩愈的“不平则鸣”在情感基调上色调亮丽。宋人葛立方曾感慨“柳子厚可谓一世穷人矣”,〔77〕然而他始终秉承着“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78〕的信念,在艰难困厄中保持着当初人生的本色。柳宗元的一生成就正如宋徽宗在其《初封文惠侯告词》中所说:“文章在册,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为不朽。”
虽然欧阳修非常尊崇韩愈,但对于韩愈在体验了“不平”遭遇之后的“自鸣其不幸”的狭隘表现也提出了批评。韩愈曾写过《感二鸟赋》,对此欧阳修说道:“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79〕认为韩愈终不能摆脱个人穷通得失的卑微情感,对此指出:“(韩愈)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愈)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80〕显然欧阳修对于韩愈在贬谪之后的“戚戚怨嗟”之表现和所作的“戚戚之文”是不满的。
四、欧阳修把柳宗元列为其“穷而后工”论的典型实践者
欧阳修之所以把柳宗元列为其“穷而后工”论的典型实践者之一,显然是因为认为柳宗元的文学思想较好地印证了他的这一论断,当然也希望借此来惜人叹己。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赞赏柳宗元寄情山水以消解苦闷的生活方式。欧阳修指出“穷而后工”者的生活方式大多是“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梅圣俞诗集序》)。柳宗元在长安政治改革失败后,被贬谪到相距两千余里的永州,以“戴罪”之身寄寓于山水自然中。在此漫长的十年(805—815)里,他的日常生活大都就是在“上高山,入森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81〕中度过的。实质上欧阳修自身的生活也是如此,他认为“荫长松,藉丰草,听山溜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此山林者之乐也”。〔82〕二是同情柳宗元艰难困苦的创作环境。欧阳修在其编撰的《新唐书》中对柳宗元在贬谪之后的创作环境,有着具体的描述:“(柳宗元)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83〕三是感叹柳宗元的忧时虑世之心。欧阳修在其《永州万石亭·寄知永州王顾》一诗对柳宗元的人生遭遇和写作成就发出感慨:“天于生子厚,禀予独艰哉。超凌骤拔擢,过盛辄伤摧。苦其危虑心,常使鸣声哀。……我亦奇子厚,开编每徘徊。”〔84〕欧阳修在晚年的《薛简肃公文集序》一文中还念念不忘地感叹柳宗元等人在艰苦环境中所体现出的“苦心危虑”,并最后实现了“穷而后工”的事业。从“苦其危虑心”到“苦心危虑”,欧阳修一再强调了柳宗元的“危虑”之心。根据辞海的释义,“危虑,犹苦思”。关于这一写作思想,在柳宗元自身的文论《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也得到了印证,他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85〕可见,柳宗元这种“危虑心”是在经常有意识地克服“轻心”和“怠心”中实现的。这种“危虑心”,它“不仅仅是对事物的认识深度的问题,它体现出作家的一种胸襟气度,乃至于对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86〕
反观欧阳修自身,他四岁丧父,“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87〕做官四十年,却三次被贬地方为官长达十余年,可他“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88〕在困难面前他奋不顾身,在逆境之中能够处之泰然。由此可见,欧阳修“穷而后工”论虽然是以柳宗元等人为代表,实质上也是自己人生的缩影。梁启超曾称欧阳修为“‘发愤为雄’的史家”,〔89〕把他与司马迁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欧阳修与柳宗元都有着长期身陷穷厄而文学有成的人生经历,实质上他俩都是“穷而后工”论的典型印证者。这也必然使欧阳修与柳宗元惺惺相惜和神通共感,在心灵上走近并接受柳的“感激愤悱”之思想。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在追溯欧阳修“穷而后工”论的源头时,如果只是强调韩愈“不平则鸣”对其产生的影响,而对柳宗元的“感激愤悱”置之不顾,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本文把柳、韩相关文学思想对欧阳修“穷而后工”论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比较,其中虽也难免存在偏颇之处,但这是一种尝试,我们从中看到了“穷而后工”论与柳宗元“感激愤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由此可以认为,柳宗元的“感激愤悱”无疑对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产生了直接影响,是“穷而后工”论的重要源头。
注释:
〔1〕《梅圣俞诗集序》:“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土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12-613页)。
〔2〕《梅圣俞墓志铭》:“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余尝论其诗曰:‘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97-498页)
〔3〕《薛简肃公文集序》:“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18-619页)
〔4〕《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唐〕韩愈:《韩愈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276页);《荆潭唱和诗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唐〕韩愈:《韩愈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291页)。
〔5〕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18页;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29页;张福勋:《宋代诗话选读》,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5-136页;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霍松林主编,漆绪邦、梅运生等撰著:《中国诗论史(中册)》,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587页;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2-83页;李建中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8页;童庆炳:《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87页。
〔6〕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周裕锴:《自持与自适:宋人论诗的心理功能》,《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李凤英:《“穷而后工”的源起》,《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7〕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姚奠中:《柳宗元的文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23页;可永雪:《史记文学研究》,载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著集成(第9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9页;邓承奇、蔡印明编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导引》,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2页。
〔8〕〔9〕〔11〕〔15〕〔17〕〔18〕〔22〕〔26〕〔27〕〔30〕〔31〕〔33〕〔35〕〔36〕〔39〕〔40〕〔43〕〔44〕〔45〕〔50〕〔53〕〔56〕〔62〕〔66〕〔75〕〔76〕〔78〕〔81〕〔85〕〔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44、638-639、644、644、618、780、644、783、571、639、639、644、783、784、644、30、2、639、590-592、195、884、638、789、644、802、627、841、762、873页。
〔10〕杨再喜:《欧阳修与柳宗元的文学关联及其思想差异》,《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2期。
〔12〕〔13〕〔16〕〔19〕〔20〕〔21〕〔23〕〔24〕〔34〕〔37〕〔41〕〔42〕〔46〕〔47〕〔51〕〔54〕〔55〕〔57〕〔58〕〔72〕〔73〕〔79〕〔80〕〔82〕〔84〕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18、497、618、297、632、497、618、612、618、619、612、978、978、664、612、450、617、612、89、960、999、1050、999、583、75页。
〔14〕〔52〕〔71〕〔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秦克、巩军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07、298、383页。
〔25〕张立兵:《先秦至唐代“发愤说”内涵及源流考索》,《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8〕〔清〕林云铭:《足本古文析义合编(卷七)》,上海:上海锦章图书局,民国11年(1922),第23页。
〔29〕钱锺书:《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第3期。
〔32〕陈骙、李涂:《文则 文章精义》,刘明晖校点,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7年,第63页。
〔38〕〔59〕〔68〕〔唐〕韩愈:《韩愈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276、291、276页。
〔48〕孙犁:《孙犁文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65页。
〔49〕周楚汉:《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61页。
〔60〕邓承奇、蔡印明编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导引》,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2页。
〔61〕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0页。
〔63〕王英志:《“发愤著书”说述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传统研究之一》,《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 第1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8页。
〔64〕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
〔65〕周裕锴:《自持与自适:宋人论诗的心理功能》,《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
〔67〕《梅尧臣集编年校注迻录》十四,见洪本健编:《欧阳修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55页。
〔69〕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
〔70〕〔宋〕苏轼:《苏轼诗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77页。
〔74〕〔宋〕赵湘:《南阳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4页。
〔77〕〔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3页。
〔8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6〕王晶晶:《“穷而后工”三十年研究述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32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6页。
〔87〕〔88〕〔元〕脱脱:《宋史·欧阳修传》,卷三百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