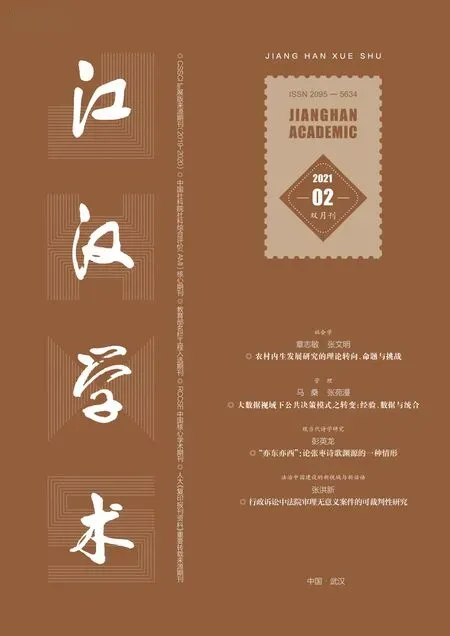行政诉讼中法院审理无意义案件的可裁判性研究
张洪新
(周口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0)
一、问题的提出
逻辑上,任何一种司法权力的运用应该以案件所依赖的争议始终存在为前提条件。即,从可裁判性角度,一个真实的争议(actual controversy)必须在诉讼程序的所有阶段始终存在,无论是初审还是上诉审阶段[1]。然而,诉讼进行过程中某种事由的发生可能使得案件的争议不复存在,特别是案件中的个人利害关系消灭,进而使得案件变得没有审理的必要和意义。例如,刑事被告在上诉过程中死亡,使得案件不再具有进一步审理的价值;如果当事人通过和解解决了系争问题,待解决的争议显然就不复存在;在行政案件的进行过程中,对某种受到挑战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告行政机关可能会做出某种改变,如依据当事人的请求履行法定职责,或者采取补救、补偿措施满足了当事人的诉讼主张,使得行政案件没有进一步审理的价值。
那么,对于这种没有审理必要和意义的案件,法院应该如何处置呢?是严格坚持将案件予以撤销,还是选择继续就案件所涉及的实质问题作出最终裁判?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这要依赖于对诉讼目的和价值的理解。如果诉讼的目的仅仅是解决当事人之间存在的争议,保护当事人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的权利,面对一个没有争议和审理必要的案件,由于司法权力得以运用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显然,法院应该将案件予以撤销。然而,如果诉讼除了解决纠纷和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还存在其他方面的目的和价值,特别是在公法诉讼中,诉讼目的还在于监督政府权力运用的合法性,法院如何处置表面上没有审理必要和价值的案件,或者应该选择何种考量因素来决定先前具有可裁判性的案件是否仍然具有可裁判性,从而规范司法权力行使,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2],就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尽管问题重要,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第62 条(原第51 条)却对此仅仅作了如下规定,即“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①。可见,对这种被告改变受到挑战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从而使行政诉讼案件变得没有审理的必要和意义,我国人民法院是否必须将案件予以撤销,法律本身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而且人民法院应该将何种因素纳入考量范围,法律也没有做出准确指示。只能说无审理必要和意义的案件是否仍然具有可裁判性,要受制于我国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从这个层面分析,一个有理论含义和实践重要性的问题便是:应该如何、以何种标准评估法院这种裁量性权力的行使?或者说,在何种意义上,司法权力之运用是正当、合法的,而不是陷于一种专断和恣意?
二、美国联邦法院的经验
尽管不无问题,但由于美国联邦法院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成熟司法模式及其理念的典型代表,本文将首先通过经验实证的方式,考察美国联邦法院是如何处理所谓没有审理必要和意义的案件的②。
从概念上讲,任何一种司法权力的运用都必须以案件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如果案件存在所必需的争议事项不存在,即通常所说的没有审理的必要和意义(mootness),那么该种事项便不再具有可裁判性,不在司法权力范围之内③。这在强调政治权力合理配置和分工的美国尤其如此。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经常强调的那样,“我们缺乏管辖权审查无意义案件来源于宪法第三条的要求,因为无意义案件没有呈现出案件或争议”④。存在着某种争议的案件是司法权力得以运行的前提条件,具有审理的必要和意义是一种宪定命令,是对司法权力行使的一种要求和限制。
然而,规则总是有例外,即便宪法规则也是如此。虽然案件中的个人利害关系变得没有意义,通常来说不再具有审理的价值和必要,联邦法院必须将其撤销。但是在联邦法院的案例法运作实践中,其仍然创造了一系列所谓的审理无意义之例外,即“能够反复,但规避审查”之例外、“被告自愿放弃”之例外以及“集体诉讼”之例外[3]。在这些“例外”情形下,联邦法院指出即便某种事由的发生使得当事人的个人利害关系在相关的案件中变得没有审理意义,也不当然使得它们不再具有进一步审理的价值,联邦法院仍然能够以各种审议性因素为依据,决定是否进一步对审理无意义的案件所涉及的实质问题作出宪法裁判。
并且,我们还必须回答为什么是这些“例外”,而不是其他类型的例外,构成所谓可裁判性原理的“例外”。显然,这只能通过批判性地分析这三种“例外”情形的内在原因,才能够得出回答。
首先,就“能够反复,但规避审查”之例外而言,其指的是如果(1)受到挑战的行为本身持续时间太短,以至于在行为终止或到期之前,不能够充分完全地进行诉讼;或者(2)存在着一个合理的预期,即同样的当事人将再次经受相同的诉讼。那么,即便是某种事由的发生使得案件当事人的个人利害关系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消失,联邦法院仍然能够就案件所涉及的某种实质问题作出某种最终裁判⑤。这是因为从性质上讲,某些特定类型的诉讼主张本身具有短暂的时限性,例如怀孕和投票,显然它们只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主张才有意义。然而,如果严格地坚持这种具有内在时限性的诉讼主张,必须在诉讼过程中始终存在,否则便以案件无审理意义而驳回的话,可能会使得这些具有时限性约束类型的案件完全豁免于司法审查。更不用说,如果案件所涉实质问题还具有重要的宪法含义。这种结果显然是不合理的。
其次,“被告自愿放弃”之例外指的是被告自愿放弃受到挑战的行为本身并不足以使得案件变得没有意义,即并不当然剥夺联邦法院听审和决定案件的权力,因为被告的这种自愿放弃可能并不是真诚的,或者说理论上没有任何障碍阻止被告在将来再次恢复这种受到挑战的行为[4]。在司法实践中,使得某个案件变得没有审理意义,特别是原告的个人利害关系在其中变得没有审理的意义,经常发生的一种情形是被告自愿停止或者改变了受到挑战的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严格要求联邦法院以案件变得没有审理意义、不再具有可裁判性为由而将案件驳回,实际上就相当于授权被告能够通过单方面的行为排除联邦法院的管辖权,进而起到规避司法审查的效果。不用说,这种结果同样也是不合理的。
换句话说,被告自愿放弃受挑战行为并不构成撤销案件的充分理由,而且受到挑战的政府权力运用的合法性得到解决存在着一种公共利益⑥。当然,联邦法院也承认案件可能会因无意义而被驳回。如果被告能够证明存在着合理的预期,即受到挑战的行为不会被重复,就不会使案件变得没有意义。但是,这种举证负担是沉重的,被告仅仅承诺不会恢复受到挑战的行为并不足以满足这种举证负担。
最后,就“集体诉讼”之例外而言,通过一系列的案例,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已得到确认的集体诉讼仍然是具有可裁判性的,即便代表集体提出诉讼的原告在案件中的个人利害关系变得没有意义,联邦法院仍然能够就该集体诉讼的实质性问题作出宪法裁判[5]。因为依据定义,集体诉讼在性质上不同于个人诉讼,有名的原告个人对于诉讼结果拥有个人利害关系,并不是维持集体诉讼的必要条件⑦。据此,在集体诉讼中,联邦法院通常不会以个人利害关系变得没有审理意义为依据将案件驳回[6]。
总之,面对诉讼进行过程中某种事由的发生使得当前案件没有审理必要和意义,美国联邦法院的案例法实践所存在的以上三种例外,说明即便某种事由的发生使得个人利害关系在某个案件中变得没有审理意义,法院仍然可以选择不以审理无意义为依据而将先前具有可裁判性的案件撤销。从实证的角度确认这一点后,就可以进入到一个规范的层面,即法院应该如何具体区分产生没有审理意义的不同情形,以及在不同的情形下法院作出相关决定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三、审理无意义案件的两种情形及其司法应对
(一)议题无意义与个人利害关系无意义之区分
分析美国联邦法院在案例法实践中树立的仍然具有可裁判性的三种审理无意义之“例外”情形,可以发现诉讼进行过程中某种事由的发生使得案件没有审理的必要和意义,是否仍然具有可裁判性,进而处于法院的司法权力范围之内,主要是在司法审查的语境中产生的⑧。若某个案件当事人所请求的司法救济是就某部法规或者某种政府行为的合宪性做出宣告性判决,如果坚持个人利害关系在诉讼的进行过程中,始终是确保先前具有可裁判性的案件继续具有审理价值的必要条件,那么实践中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大部分案件将豁免于司法审查。显然,这最终可能废止了司法审查制度本身。因此,为了维持司法审查这一重要的具有宪法意义的司法权力,在涉及司法审查的案件中,个人利害关系成了一个不重要、有时甚至不相关的考虑因素。的确,这似乎是无意义原理测试标准的一个“例外”,但这种例外是为保持司法审查权力之存在所必要的。
在司法审查的语境当中,除了案件当事人的个人利害关系所衍生出来的个人诉权以外,司法权威的有效维护以及监督政府权力依法行使这些重要政治价值和法律目的,都在某个案件当中展开和呈现,并且在可裁判性问题上相互竞争。因而,从规范的角度,法院如何处置表面上看没有争议以及没有审理必要和意义的案件,判断当前案件是否仍然具有可裁判性,并非存在着非此即彼的简单回答。相反,法院如何面对没有审理必要或者审理意义的案件,必须在维护司法权威以及审查政府权力依法行使之间取得某种适当平衡。
在这里,本文认为,从维护司法权威的整体性和监督政府权力合法行使的角度,面对诉讼过程中某种事由使得案件没有审理的必要和意义的情形,法院首先需要在个人利害关系变得没有审理意义与议题本身变得没有审理意义之间进行区分,即其中所涉议题不再具有可讨论性的案件,以及原告个人对案件结果不再有法律保护利益的案件。因为根据定义,如果案件所涉议题变得没有审理意义,那么法院也就没有必要就案件所涉实质问题作出裁判。对于议题审理无意义的案件,法院应该简单地予以驳回。就确定某个审理无意义的案件是否仍然具有可裁判性这个问题而言,法院必须从以下这个问题开始分析:受到挑战的行为是否有合理复发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涉及的是法院的任何裁判是否可能会影响现状⑨。这是“议题审理无意义”旨在回答的问题。如果法院确定案件所涉及的议题本身是过时的,这意味着已经起诉的案件不再呈现出宪法所要求的真实“案件或争议”,因此法院必须驳回,案件也不再具有审理的价值。
相反,对于个人利害关系无意义的案件,要以各种审议性因素为依据,决定是否继续就案件所涉实质作出裁判。那么,在议题仍然具有可讨论性、但个人利害关系变得没有审理意义的案件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实际性和审慎性考虑因素,指导着法院决定是否撤销该种案件呢?
本文认为,能够纳入法院审议性考虑范围内的因素,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案件所涉实质问题及时作出裁判的迫切需要;第二,对司法权威的不利影响;第三,现有司法资源有效合理的利用。
(二)个人利害关系无意义的司法应对
1.迅速裁判的迫切需要
在司法审查的语境下,如果某个受到挑战的法规或者政府行为的合宪性存在疑问,无论是在何种意义上,法律或者政府行为的这种持续不确定性都是一种社会成本。因而,从审议的角度,决定因为个人利害关系变得没有审理意义的案件是否依然具有可裁判性,首要考虑因素是作出一个迅速裁判是否是必要的或者可欲的。
概括而言,在因为个人利害关系变得没有审理意义的案件中,如果下述两种情形之一或者同时出现的话,在当前诉讼中听审并决定案件实质可能就是必要的或者可欲的:(1)所提出的诉求影响到缺席的第三方当事人,但第三方当事人有效主张其权利存在着障碍,或者涉及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的含义;(2)本案当事人挑战的法规或者政府行为,具有内在的时限性,如果现在不被审查,可能会存在规避审查的效果。实际上,这些事实情境所存在的共同点是如果宣布个人利害关系审理无意义的案件不再具有可裁判性,会将一系列类似的诉求隔离于司法审查。实际上,使个人利害关系变的没有审理意义的相同事实情境,同样会影响每一个后来提出的个人诉求,使得案件再次变得没有审理意义。
2.司法权威的不利影响
如果某种诉讼能够被重复提起,例如在涉及政府机构或者大型企业为诉讼被告的情形下,为了避免糟糕的先例,诉讼当事人可能会故意采取某种行为使得案件变得没有审理意义,即便是以失掉当前案件为代价。就此而言,如果一味地坚持诉讼过程中某种事由的出现使得案件没有审理意义,法院当然没有权力听审以及决定案件,可能使得诉讼当事人产生强有力的激励,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积极采取某种战略性行为操纵审理无意义之规则,进而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因而,法院在决定是否听审审理无意义的案件,所需要考虑的第二个审议性因素是听审该案对司法权威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在司法审查的语境中,为了避免裁判进而产生对自己有利的局面,经常出现的情形是被告采取某种行为,例如改变受到挑战的行为,或者与寻求禁令性救济的原告达成和解,从而使原告的个人利害关系变得没有意义。然而有时候,特别是相关案件如果涉及对法律原则含义的界定,那么即便是原告采取某种行为使得个人利害关系变得没有审理意义,也并不妨碍法院就案件的实质问题作出裁判⑩。因而,维护司法权威的整体性不受损害,也应该成为法院在做出审理无意义之决定时需要考虑的审议性因素之一。
3.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
决定某个审理无意义的案件是否仍然具有可裁判性,第三个需要考虑的审议性因素是已经投入的司法资源以及仍然需要的司法资源之间的比重,即要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沉没成本”(sunk costs)与“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之间取得某种权衡。尽管案件或争议条款本身没有对此明确规定,但在司法资源有限的约束下,法院总是或者必须关心如何有效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在可裁判性的语境中,在诉讼的早期阶段以可裁判性为理由将某种案件驳回,可以节省司法资源,进而能够将有限的司法资源分配到更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案件中。相反,如果是在诉讼的后期阶段将某些案件驳回,重要的司法资源已经消耗,可能就会浪费司法资源,特别是本案的诉求可能会再次被提起。因此,从有效利用司法资源的角度,决定某个审理无意义的案件是否仍然具有审理的价值,就需要在已经投入的司法资源以及仍然需要的司法资源之间做出某种评估和权衡。那么,法院应该如何做出这种评估和权衡呢?
让我们假设有限的司法资源为单位1,在某个先前具有可裁判性的案件中已经花费的资源为x,显然剩余的司法资源为(1-x),就案件实质问题作出最终裁判仍然需要花费的资源为a,a 在理论上讲应该不超过(1-x)。进一步,我们假定案件所涉议题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为P,那么如果出现下述情形的话,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准确地说,在前述两个审议性考量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法院就应该决定该案件仍然具有可裁判性,即便某种事由的发生使得个人利害关系在先前具有可裁判性的案件中变得没有审理意义,即:(x-a)×P≧(1-x+a)×(1-P)。
应该指出的是,已经花费的司法资源即所谓的沉没成本,在该公式中并不以成本的形式出现。实际上,沉没成本根本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因为覆水难收,而成本始终起源于有所选择。已经花费的资源仅仅是已经消耗掉的资源而已,对于做出何种决策并不会产生必然的影响。重要的是,这种已经消耗的资源能够以租值的形式出现,即如果案件能够再次被提起的话⑪。在受到挑战的行为复发的情况下,决定当前无意义的案件仍然具有可裁判性的价值就表现为租值x 减掉仍然需要花费的成本a 乘以P 所得出的结果。另一方面,公式的右边表示的是将现有司法资源用在受到挑战行为不复发时(1-P)所产生的收益,现有的司法资源除了所剩余的司法资源外,还应该包括司法就无意义案件作出裁判所仍然需要的资源a。因为受到挑战的行为不复发时(1-P),资源a仍然可以用到其他的案件中,这正是机会成本的当然含义。
总之,判断曾经具有可裁判性的案件是否仍然具有进一步审理的价值,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就是要看公式左边的结果是否大于或者等于公式右边的结果。如果公式左边大于或者等于公式右边,从司法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该案件仍然具有进一步审理的价值,是具有可裁判性的案件;如果是公式右边的结果要大,那么法院就应该以案件变得审理无意义、不具有可裁判性为由将案件驳回。
四、审理无意义原理在我国的适用
前述部分指出,在我国行政案件的诉讼过程中,被告改变受到挑战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从而使行政诉讼案件变得没有审理意义,我国人民法院是否必须将案件予以撤销,法律对此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而且就人民法院应该将何种因素纳入考量范围,也没有做出准确指示。
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行政案件都以原告撤诉的形式结案⑫。为了规范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的行使,2008 年1 月10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就人民法院应该如何处理行政案件的撤诉问题作出了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即“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一)申请撤诉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二)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超越或者放弃职权,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三)被告已经改变或者决定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四)第三人无异议”⑬。换言之,对于被告改变行政行为、进而使案件变得没有意义的情形,我国人民法院是否应该将案件予以撤销,所需要考量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原告撤诉权的保障;(2)被告改变行政行为合乎法律的规定;(3)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显然,要想使审理无意义的案件没有进一步审理的价值,被告改变行政行为合法且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最没有争议的考量因素,因为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就在于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而,这三种考量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即原告撤诉的意思必须是真实的。
由前可知,在行政诉讼的过程中,如果被告改变受到挑战的行政行为,且原告申请撤诉的意思真实,那么我国人民法院就必须将审理无意义的案件予以撤销。问题在于,就行政诉讼的目的而言,即人民法院有权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原告申请撤诉这一考量因素,是否是一种可靠的考量因素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有两个方面需要分别考虑:(1)被告改变受到挑战的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的可能性有多大?(2)如果原告不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应该怎么办?
首先,表面上看,在诉讼的过程中被告改变了受到挑战的行政行为,与原告是否申请撤诉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原告是否申请撤诉是诉权行使的重要内容,并不因被告行为的改变就使得行政诉权消失,行政诉权并非纯粹程序意义上的权力[7]。然而在实践中经常真实发生的情形却是,如果被告政府机关改变了受到挑战的行政行为,例如在行政不作为的情形中政府机关积极履行了相应的职责,或者采取了某些补救、补偿措施使得原告的合法利益得到恢复。这样原告在案件中的个人利害关系得到满足,那么继续诉讼对原告来说,显然就已经没有必要。特别是,考虑到高昂的诉讼成本,考量到自己仍然会在将来的某段时间、某种情形受制于行政机关的管理或者服务,除非原告是具有高度公共精神的当事人,那么,选择申请撤诉是必然的。
在这里,重要的是,如果被告行政机关改变受到挑战的行政行为,其原因并非是为了主动满足原告的个人诉求,而是为了避免创造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先例,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要求人民法院以当事人是否申请撤诉为考量因素,将原告当事人在其中的个人利害关系变得没有审理意义的案件予以撤销,将使得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能够规避司法审查。显然,这与行政诉讼的目的相违背。
其次,如果原告是具有公共精神的当事人,坚持就受到挑战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最终裁决,而选择不撤诉,人民法院又应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在我国语境中,尽管人民法院能够依据新《行政诉讼法》第53 条之规定,就规章以外某些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法性进行附带审查,但由于抽象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本身并不具有可裁判性,人民法院仍然仅能够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因而,在诉讼过程中如果被告改变了受到挑战的行政行为,例如“改变被诉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或者“改变被诉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且对定性产生影响”,或者“撤销、部分撤销或者变更被诉行政行为处理结果”⑭,而且这种改变合乎法律的规定、不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案件审理标的不存在,那么人民法院必须将案件予以撤销。此时,如果原告仍然坚持诉讼的话,原告应该就改变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另案提起诉讼。实际上,由于被告改变受到挑战的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原告也必然就丧失了再次提起诉讼的激励。显然,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如果被告已经合法地改变行政行为,原告是否申请撤诉,人民法院是否应该将案件予以撤销,就成为了一个不相关的考量因素。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在行政诉讼案件中不允许被告改变受到挑战的行政行为,也不是说被告改变受到挑战的行政行为时,人民法院必须将案件予以撤销。而是说,在这种情形下,应该像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第62 条所规定那样:“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只不过,人民法院在作出这一决定过程中,所应该考量的因素不应该是,或者不应该仅仅是:(1)原告申请撤诉的意思是否真实;(2)被告改变行政行为是否合乎法律的规定;(3)是否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在这里,本文认为,从维护司法权威和行政诉讼目的得以实现的角度,被告改变受到挑战的行政行为从而使得案件变得没有审理意义,特别是原告的个人利害关系在案件中变得没有审理意义,人民法院是否应该将案件予以撤销,所考虑的因素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被告改变受到挑战的行政行为是否真诚,是否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表明受到挑战的行政行为不会再次适用到原告或者第三人;(2)被告的自愿放弃行为,是否是为了避免对自己不利的先例,而采取的某种策略性行为,以至于最终完全规避司法审查⑮;(3)出于合理利用稀缺司法资源的角度,已经用掉的司法资源以及作出最终裁决仍然需要花费的司法资源两者之间的比重是多少。
五、结 语
实践中,诉讼过程的展开和进行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和作用的一种复杂产物。某种程度上,无审理必要或者审理意义的案件存在于诉讼过程的始终,是诉讼进行过程中的一种常态。但关键的是,从可裁判性进而司法权力运用的角度,是选择将没有审理必要和审理意义的案件一律予以撤销,还是在某种情形下基于某些考量性因素继续坚持对其中没有个人利害关系的案件所涉及的实质问题进行司法裁判,可以说是任何国家的法院都必须要面对和处理的程序性议题。对此类问题的回答,是现代法院走向政治成熟的标志。现代诉讼,特别是审查政府权力运用合法性的公法诉讼,法院不得不处理自身与其他政治机构的相互关系,在这种动态的政治关系中赢得司法所应享有的当然权威。
从方法论角度讲,法院如何面对审议无意义的问题,必须首先理清诉讼过程的目的和价值。特别是就行政诉讼程序而言,除了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司法权威的树立和维护、监督政府行为合法行使,决定了法院在处理审议无意义问题时,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简单态度。为此,法院必须首先区分导致审理无意义的具体情形,是议题无意义还是个人利害关系无意义。如果是后者,那么法院在考虑该案件是否仍然具有可审理的必要和意义、处于司法权力的范围之内,必须将司法权威的维护、行政诉讼目的实现、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等因素纳入考量因素。就此而言,在我国行政诉讼的审理过程之中,如果被告行政机关改变了受到挑战的行政行为,从而使得原告的个人利害关系在其中变得没有审理意义,并不当然剥夺我国人民法院对受到挑战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在深层次的意义上,人民法院必须积极主动地将可裁判性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纳入法院的决策范围。对于可裁判性问题的自我意识,可以不断促进人民法院在政治上趋于成熟,进而某种意义上最终树立人民法院的自治地位。
注释: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 年修正版)第62 条。
② 在美国联邦法院的案例法运作过程中,在管辖权范围内联邦法院为树立其自治地位,孕育、适用以及发展了一系列诸如咨询意见的禁止(ban on advisory opinion)、当事人适格(standing)、时机成熟(ripeness)、审理无意义(mootness)在内的可裁判性原理(doctrine of justicia⁃bility)。在实践中,当公民就某种事由形成诉讼提请联邦法院要求作出裁决时,联邦法院能够诉诸这些可裁判性原理来决定是否受理并作出相应的裁决。对这些可裁判性原理的简要分析,可参见Wayne McCormack著,“The Justiciability Myth and the Concept of Law”,载Hastings Constitutional Law Quarterly ,1987 年第 14 卷第3 期;Robert J Pushaw Jr. 著,“Justiciability and Separa⁃tion of Powers:A Neo-Federalist Approach”,载Cornell Law Review ,1996 年第 81 卷第 2 期;Erwin Chemerinsky著,“Federal Jurisdiction”(第6 版),New York:Wolters Kluwer Law&Business出版社,2012年版。
③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可裁判性原理组成部分的“moot⁃ness”语词本身,是难以准确翻译的。英语“moot”存在着两种词性,即形容词和动词。作形容词时,有两种含义:(1)非实际的,假设的;(2)可争论的,未决的。做动词时,则有三种含义:(1)争论,辩论;(2)使失去实际意义,使成为纯理论的;(3)提供争论。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928 页。因而,“mootness”就可能同时含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含义,可解释为问题的可讨论性、未决状态,也可以解释为诉由消失之事、过时、没有审理的必要和意义。然而,从可裁判性的角度,由于在联邦法院的案例法的运作过程中,经常指的是联邦法院在驳回(dis⁃miss)某种案件时所诉诸的理由(尽管存在着例外),因而本文将“mootness”翻译为“审理无意义”,即某种事由的发生使得案件不再具有进一步审理的价值。
④ Liner v. Jafco,Inc.,375 U.S. 301,306 n. 3(1964).
⑤ 参见Weinstein v. Bradford,423 U. S. 147,149(1975);SEC v.Sloan,436 U.S.103,108-110(1978);Wis.Dept.of Indus. v. Gould,Inc.,475 U. S. 282,285(1986);Ho⁃nig v.Doe,484 U.S.305,317-318&n.5(1988).
⑥ 参见United States v.W.T.Grant Co.,345 U.S.629,632(1953).
⑦ 依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23(a),在下列条件下,集体中一个或数个成员可以作为集体全体成员的代表,代表当事人起诉或应诉:(1)集体人数众多,使得全体成员的合并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2)该集团有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3)代表当事人的请求或抗辩在集体中是有代表性的请求或抗辩;(4)代表当事人能公正和充分地维护集体成员的利益。
⑧ 参见Abbott Laboratories v. Gardner,387 U. S. 136,149(1967);Warth v. Seldin,422 U. S. 490,518(1975)。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可裁判性原理,审理无意义的分析应该主要集中于“案件或者争议”含义中的第一个方面,即某种案件能够通过司法救济解决的特质。即是说,正是在司法救济的语境中,才会产生某个过时、没有意义的案件,是否仍然具有可裁判性的问题。
⑨ 参见U. S. Parole Comm’n v. Geraghty,445 U. S. 388,396(1980);Murphy v.Hunt,455 U.S.478,481(1982).
⑩ 参见City of Erie v. Pap’s A. M.,529 U. S. 277,287-289(2000).
⑪ 在经济学中,有关沉没成本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以租值的形式出现,详细分析参见张五常:《收入与成本》,中信出版社2011 年版,第193 页。
⑫ 以河南省新密市为例,1996 年至 2000 年 5 年间,累计审结各类行政诉讼案件851 件,撤诉结案达279 件,比率为32.8%,几乎占总结案数的三分之一。参见牛保娟:《行政撤诉案件的调查与分析》,载《中州大学学报》2002 年第1 期,第 20 页。2000 年全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的一审行政案件中以撤诉结案的占46.2%,参见李璠、刁乃君:《浅析行政撤诉制度》,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 年第5 期,第36 页。
⑬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由于新《行政诉讼法》将原先的“具体行政行为”一律修改为“行政行为”,因此本文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具体”一词放入括号内。实际上,能够纳入我国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行为,仍然是“具体的”,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⑭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
⑮ 有种观点可能认为,由于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人民法院不存在遵循先例原则,因而这一考量因素并不适用于我国。本文认为,尽管我国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然而在我国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下,人民法院就某种行政行为所做判决可能会被遴选为指导性案例,或者即便没有成为指导性案例,由于同样案件同样对待的司法原则,其也会对相似案件起着指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为了避免产生对自己不利的“指导性案例”进而规避司法审查,完全有可能采取某种策略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