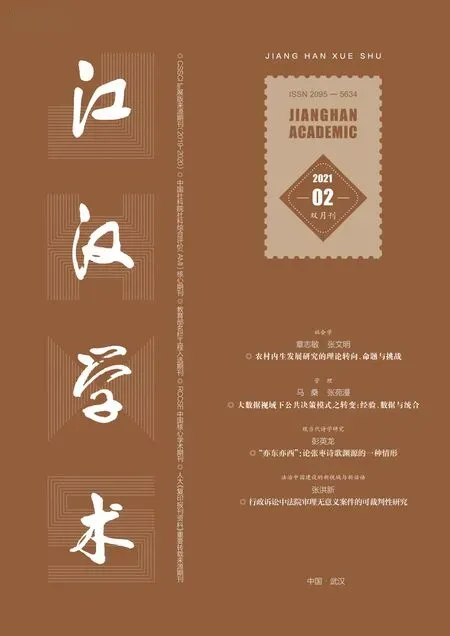浪人形象·女性气质·死亡冥思
——象征派诗人诗歌的“颓废”趋向与读者批评
田 源
(四川美术学院 通识学院,重庆 401331)
就中国现代新诗的“颓废”研究史而言,从1990 年代中期掀起一波热浪,至2010 年代初,有四本颇具影响力的专著涉及象征派诗人诗歌的“颓废”趋向①。它们从史料阐释、思潮影响、中西比较、传播接受等方面,塑造“颓废”的文学研究景观。然而,深究这些著述,它们从概念的界定到阐释的路径,再到结论的断定,仍然存有“模糊化”“矛盾化”“偏激化”的“缺陷”[1]。有关象征派诗人诗歌的“颓废”研究内容相对较少。
近几年来,关于象征派诗人诗歌的“颓废”研究论文变得丰富起来,呈现出宏观与微观的两种研究思路。前者如邓招华的《重构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图景》,作者认为“以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为代表的早期象征主义诗人即以象征主义的形式抒写着一种现代颓废情怀”②;后者如姜玉琴的《叙“颓废之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与李金发诗歌创作关系论》,认为李金发诗歌“不管是在思想观念还是审美基调上都必须要彰显出一种‘颓废之美’”③。
学者们将象征派的“颓废”聚焦于李金发诗歌,其“颓废”的现代诗学内涵“显现为无力感、活力能量的贫乏、健康生命的凋零、倦怠与烦闷的迟缓流动、萎靡不振的漠然、深深的悲伤与抑郁”④。以李金发为中心,辐射至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邵洵美、于赓虞、焦菊隐等象征派诗人⑤,其异质同构的“颓废”趋向,引发了读者的批评,从而呈现出相似的审美质素。
一、落魄无依的浪迹漂泊
象征派诗人在1920—1930 年代读者批评中大多是浪人形象,人生经历与创作背景带有动荡的“颓废”轨迹。以李金发、王独清为代表的诗人前往欧洲留学,离开本土,来到陌生的异域,他们游荡在现代化的大都市,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罪恶耳濡目染,视听的冲击形成心灵的震撼,既有对故国荒园的哀悼,也抒写着自我的孤寂情绪;以穆木天、冯乃超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在邻邦日本留学,尽管一衣带水,却仍摆脱不了漂泊他乡的哀思;以于赓虞、焦菊隐为代表的象征派诗人虽未离开中国大陆,但历经故乡的变乱,迁徙都市,从农村到城市的流亡苦难,体现了世态炎凉的悲情处境。
李金发在法国学习美术的经历颇为坎坷。黄参岛写出李金发到法国后的流浪足迹:“作者到法国后在巴黎南部拿翁行宫所在地……但不久他们到法国西部去了……但在学校一方面腐败的学科,他们不能再事句留,于是一溜烟讬词跑到巴黎去了。”[2]三次迁移令李金发看到法国社会的黑暗,孤身求学的辛酸随着移动的步履不断累积,诗人的处境更显落寞。华林从李金发的游荡“想起英国诗人拜伦,在这种麻木蠢动的畜类中,不得不流于孤寂漂泊的生涯”[3]。李金发像一个拜伦式英雄,无畏地在欧洲的不同城市穿行,他的诗作“大半产生于法国的地雄,百留吉,巴黎,德国柏林等处,所叙之情事,所写之风景以异国为多,所以他的诗也就天然变成异国的了”[4]。脱离本土文明的异域空间点燃了李金发流浪的热情,表现在诗歌里便是赵景深所说的“异国情调的描绘”[5]。
异国漂泊旅程对感官造成强烈的冲击,李金发依靠流浪观察到不同于本国的景象,异域风情的抒写从一个侧面衬托出李金发浪荡的足迹。赵景深列举李金发诗歌中关于异国的描写,例如《给蜂鸣》一诗的第三节:“我愿长睡在骆驼之背,/远游西西利之火山与地上之沙漠;/无计较之阳光将徐行在天际,/我死了多年的心亦必再生而温暖。”诗中的“远游”一词是诗人游历意愿的体现,躺在骆驼的背上,即便是荒芜的沙漠,诗人也宁愿沉醉于夕阳的余晖,沉寂冰冷的心逐渐苏醒,徜徉在酣畅的慵懒里。李金发的“颓废”迷醉在“异国情调”里,折射出游手好闲的浪人形像,他好似被“波德莱尔遗弃在人群里的人”,人的生理机能被物化为商品的贩卖属性,诗人丝毫未能觉察这种日益加深的从属效应,放荡的“麻醉药,极乐地渗透了他的全身”[6]。李金发忘却被都市遗弃的悲哀,他义无反顾地投入自然怀抱,沉迷于美景,获得片刻慰藉,融入骑士游侠的孤傲气质,形成了波德莱尔所言的“浪荡作风”,它仅仅是“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7]501,因为诗人在现代化都市中是极其渺小的存在,或许内心充斥着堂吉诃德式的精神品质,但他根本无力反抗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只能在流浪中放逐自我,在冷漠的精神世界试图获得聊以自慰的满足。
王独清的流浪与李金发类似,但读者批评认为其中的感伤气氛更为浓厚。王独清的第一本诗集《圣母像前》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郑伯奇认为该集是“纯粹的一个诗人的生活记录”,承载着“诗人在法国这七八年度过的波澜坎坷的流浪生活”[8]。郑伯奇列举的《我飘泊在巴黎街上》的四句诗可以作为“流浪生活”的凭证:“我飘泊在巴黎街上,/任风在我的耳旁苦叫;/我迈开我浪人的脚步,/踏过了一条条的石桥。”王独清称自己是“浪人”,诗中凄风惨雨的巴黎无法阻挡诗人的流浪步伐,尽管发出象征哀愁的“苦叫”风声,但留下的足迹如同海浪般翻滚不息。
王独清流浪的情感基调是悲哀的,正如《圣母像前》的序诗所写:“我是个精神不健全的人,/我有时放荡,我有时昏乱……/这儿,就是我那些悲哀底残骸。”也许“悲哀”本身就足以让人感到沉重,而“悲哀底残骸”更是将“悲哀”置于阴森冰凉的角落。王独清在流浪中的悲哀首先表现为故土的沦丧。《我从café 中出来》中的“要失了故国的浪人的哀愁”被许多读者铭记,批评文章里也反复提及,除郑伯奇引用了该句以外,白云认为王独清后来出版的诗集《零乱章》的各诗篇“仍是怀着一付‘我从café 中出来,我的身上如中了酒的疲乏’那样的一个流浪者热中的伤感的心情之悲咽”[9]。咖啡馆的困顿和巴黎街道的冷清衬托出一个在现代都市漫无目的、疲倦不堪的浪人剪影。
王独清悲哀的流浪与中西方历史文化名人的经历颇为相仿。祝秀侠认为《圣母像前》蕴含着王独清两大思想:“漂泊”和“伤逝”。“因为他一个天涯流浪人的原故,他极力追慕但丁,极力追慕屈原,差不多他承认自己的身世和但丁屈原有同样的比拟。”然而,祝秀侠却对王独清摹拟的流浪对象提出了批判:“……他们浪荡的生活,悒郁的感伤,消极的行动,与现实社会是没有一点帮助的。”[10]读者间接否定了王独清的流浪姿态,其中蕴含的颓废情感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
王独清的流浪生涯还伴随着追忆过往的惆怅,读者对《吊罗马》一诗的批评渗透着吟游者的哀思。游生认为王独清的“《吊罗马》一作,有拜伦《哀希腊》的遗韵”[11]。古希腊罗马帝国在历史上拥有璀璨的文明,但其陷落与覆灭的结局令人唏嘘,在流浪者心中激起失落的波澜,满目疮痍的废址将曾经的光芒掩盖,只有借助流浪的足步回忆过去的辉煌。读者林炼认为王独清的流浪“从罗马的近郊,向烟雾中的古都一步步迈进,随时发出感怀来,其曲调亦随之层层回转,如擂鼓行军,又如层峦垒峰,愈行愈深,身入大山之间,有天苍地茫之感”[12]。王独清的步伐似乎唤起了昔日征讨帝国的号角,帝国的倾覆在旦夕之间给人苍茫的毁灭感。穆木天推断王独清的流浪体现了贵族的“没落”,诗人“放浪在欧洲大陆之上,到了古都罗马”,帝国兴衰的感官冲击让王独清站在“罗马的废墟上,想起了在那个‘地中海上的第二长安’的过去,过去的英雄的伟业永远不朽的光荣的历史,在濛迷的恼人的雨中,他凭吊起这荒凉的古城来了”[13]。从李金发到王独清,他们在欧洲的流浪“是一轮落日,有如沉落的星辰,壮丽辉煌,没有热力,充满了忧郁”[7]501-502。
于赓虞、焦菊隐等象征诗人的流浪尽管没有跨越国界,但是颠沛流离的辛酸感触如出一辙。昭园批评赓虞诗集《晨曦之前》,指出诗中“荒”和“无”使用较为频繁:“在那首《花卉无人理》就有十二个荒字,在《野鬼》里就有十二个‘无’字。要一再地表现他是个流落天涯的浪人,所以屡用‘荒’‘无’等字表明他的世界是片旷野,一无所有,只得踉跄他徘徊在荒曼的郊野,凄迷的晦夜,所唯一渴望的醇酒,全是他往昔失去的灵魂的滋味。”[14]正如于赓虞的自剖:“我从民间来到都市,在辗转的流落里,受着为别人所想像不到的苦难。然而我只有含泪的忍受……我常把我比作一个游行的孤星,因为我不容易受到他人的感染,无论到什么环境里,我永远保持着沉默的心情,把眉头皱起,给人家一个不愉快的印象。”[15]荒芜与虚空的诗境流露出“浪人”的寂寞。
于赓虞的流浪始于家乡匪患。赵景深说:“于赓虞初期的诗大半是些乡思。河南是著名的土匪窝子,他的家乡遭了焚掠,因之发出悲愤的歌声来。”[16]诗人目击了一幕幕惨剧,见证了亲人的罹难,赵景深引用诗歌《昨夜入梦》中的诗句:“我的儿呀,……已呈凋零,汝叔已被兵匪戕生。”于赓虞的叔叔被土匪戕害,鲜活的生命瞬间变成冢中枯骨。赵景深还借其诗歌《九女山之麓》中的诗句:“我的亲人,你们在荒坟间知否后代已无宁馨的乐园?”暗示诗人的悲惨身世,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启前往都市的流浪之旅,因此,于赓虞在诗歌中表露“孤独,怪癖地吟哦,徘徊废墟之间”[17]。
焦菊隐的流浪来自家庭变故。于赓虞在为焦菊隐诗集《夜哭》作的序言中说:“他的家庭曾是一个很荣华的乐园,后来几遭不幸,卒至凋零到难于维持。现在流落到江南的也有,流落到京华的也有,在天津的只有他的父亲与妹妹了,更使人哀苦欲绝。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他隐忍含痛的孤零零的往前步着,怀含着已往,梦想着将来,感到不少荒凉的意味。”[18]殷实安逸的“乐园”被苦难冲散,沦落天涯的焦菊隐饱受亲人分离的痛楚,即便如此,他还要向前行走,在孤独的漫游里品味人世间的冰冷。姜公伟曾与焦菊隐有过交往,他记得一天夜里自己在吹奏《阳关三叠》曲,身旁的焦菊隐“默默地听着。最后他的情绪迸发了,‘默默’的结果,写成一首《阳关曲》”[19]。“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流浪浸染着人生的艰辛,暗含着万般的无奈。
读者将李金发、王独清、于赓虞、焦菊隐等象征诗人视作浪人,隐秘传递出两层“颓废”元素。其一,触目惊心的废墟场所。李金发诗中的荒漠、王独清笔下的罗马、于赓虞吟咏的荒野、焦菊隐叹息的阳关,都具有凄凉的“颓废”意味。穆木天回顾留日经历时写道:“东京,在我进大学的那年夏天,发生了大地震……可是,在当时我的眼睛中,反觉得那是千载不遇的美景。就是从那种颓废破烂的遗骸中出去,到了伊东。而从伊东归来后,也是在那种凌乱的废墟中,攻案着我的诗歌。”[20]东京大地震后的废墟竟然令穆木天觉得是“美景”,断壁残垣给予了诗人“颓废”的创作灵感。
其二,抚今追古的绵绵哀情。流浪串联感伤的旅程,废墟演化为孤苦内心的象征。流浪经历不仅仅是漫无边际的游走,更是压抑、彷徨、落魄的心理写照,惊心动魄的见闻引发苍凉悲苦的人世感慨,象征派诗人仿佛背负某种罪孽,被流放在无边的黑夜。正如穆木天的《流亡者的悲哀》所写:“可是,没有人晓得,在这个大都市中,/我一个人在拖着我的流亡者的悲哀。……在阴凄的巷中,渡着虚伪的生活,/人生的途径,在心中被虐杀着……故园的屠杀和烽火,在心中交映着。”[21]
象征派诗人的低徊步履裹挟无奈的迁移足迹,诗歌中的“颓废”趋向在读者批评里“基于肉体的位移”,诗人联想家园故国的衰败,内心遂起“悲哀的颓废之思”[22]。随之而来的是女性柔弱的错位忧思。
二、女性渲染的感伤气质
女性气质的前兆通常表现为现实男女间的追逐。黄参岛解读李金发留学期间的“颓废思想”,伴随女性的追求,李金发当时“被一个他不愿爱的女同学(法国的少年啊)纠缠贪恋着,可是这真不幸,天啊,他所欲爱反失恋了”[2]。恋爱对男性和女性的意义是截然相反的,男人可能把恋爱当作一部分生活阅历,女人则把恋爱当作全部的生活,比例失衡造成恋爱观的偏斜。女性弱点里“诸如平庸、懒惰、琐碎、奴性等——也正好表明了妇女一向被禁闭的事实”[23],这些短板是颓废的分支符号。活泼浪漫的法国少女对李金发的恋爱追求饱含热情,但反复的求爱表白尽显平淡与杂碎,“纠缠”与“贪恋”也丧失了女性平等独立的地位,好像要屈尊乞求男性的同意。李金发根本不喜欢他的这位法国同学,他的拒绝却熄灭了恋爱的火苗,失恋的打击好像女性身上的弱点,沉入庸庸碌碌、浑浑噩噩的生活。
赵景深认为李金发的诗中“爱用‘傲慢的诗人’一类的词,……他所以傲慢的缘故,大约由于他爱一个姑娘,而又不愿自卑地去求爱罢”[5]。李金发对追求心爱之人流露出一丝女性的羞涩,赵景深大略列举了几首含有类似词组的诗歌,揭示李金发强装自傲以掩饰卑微的心理。《Falien与Hélène》一诗出现了“傲慢的诗人”,该诗末尾写道:“假如男人说:你的唇儿给我,那你以/为是最荣幸了呵,追逐成性的生物,/他们可以用一手捏死你在掌里,如/颓墙下之死猫……”,恋爱中男女的追逐可能充满了谎言的陷阱,最后演变为一场死亡的惨剧,李金发担心自己成为女性的猎物,隐藏真实的爱意。然而李金发对于拒绝女同学流露出一副遗憾的神态,他在《憾》中使用“作家的自负”,因为他“不了解”女性“微笑的效力”:“我的懊悔遂结队来了,/因我抛弃了爱余的她。”李金发刻意回绝女性的示好,又不敢踏出追逐的步伐,隐隐传递出怯懦的“颓废”气质。
女性在恋爱中的主动追逐并不多见,象征派诗人大多以男性追求女性的姿态出现在读者批评里。王独清对女性的痴迷追逐与李金发形成鲜明对比,显得大胆和执着。他在文学上钟情缪塞与乔治桑的恋爱佳话,读者游生说:“在近代作家方面,他爱读缪塞(Musset)等人,尤其是缪塞和女作家乔琪桑的恋爱故事……有一次替朋友写扇面,有游威尼市旧作一首,为集中所不录,特记其大意如下:‘此地有佳话:/缪塞乔治桑;/我今独漂泊,/黯然神为伤。’”[11]法国作家缪塞和乔治桑的结合抚慰了王独清浪人的孤独心灵,他肆无忌惮地追逐着不同的女性。王独清对女性的追逐像杂耍小丑出尽洋相,又如地痞流氓蛮不讲理,读者对此或许只是付之一笑,又或许只是报以嘲讽,却忽略了在这般出格追逐中的女性魅惑,王独清在异域与妓女厮混,受尽屈辱[24],回国后又大肆追求国内青年女性,似乎要借此转移漂泊的悲哀情绪。
女性追逐间接沾染异性的气质,其他象征派诗人还有着与生俱来的女性气质。于赓虞尽管自述在苦痛时分“不能如半女性的脆弱的诗人一样想神祇及命运求怜悯”,但他又声称自己是“多愁善感的人”,灵魂深处尽被“幸福与危害常摆手践踏”[15]。前后不一的语调暗含纠结感伤的女性化特征。于赓虞的弟弟因遭到诬陷被打入牢狱,诗人回河南营救,他在“百忙中曾应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之请,赴该校讲演,题为‘妇人与诗’,于氏以夏娃代妇女,闻甚动听云”[25]。于赓虞用《圣经》中的女性原型人物谈诗歌与女性的关系,可见其对女性的青睐,两性起源的宗教传说渗透着于赓虞深沉的女性气质。
邵洵美和焦菊隐的女性气质也许更容易被读者察觉。少白发现邵洵美“是一个有女子的温柔的男子,他是一个有女人的好处的男人”[26]。柔美外貌搭配淫邪笑容,既给人女性化审美认知,又附带男性对女性的窥探。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在编选《新月诗选》时收录邵洵美的五首诗歌,并在《序言》部分评论其诗如阳春三月瑰丽美艳的女子,《洵美的梦》制造了惊艳幽香的梦境,喜剧性的肃穆氛围引出荒诞不经的笑容,精彩绝伦的诗歌高潮“是洵美对于女人的赞美”[27]。春光明媚的慵懒气候烘托出女性的“香艳”魅力。《洵美的梦》开篇即发出了“疑惑”:“从淡红淡绿的荷花里开出了/热温温的梦,她偎紧我的魂灵。/她轻得像云,我奇怪她为什么/不飞上天顶或是深躲在潭心?”温暖的梦里诞生了一个莫名的女子,她仿佛幽灵般将诗人缠绕,轻飘飘的女性形象若隐若现,似乎就是诗人自己,在模糊幽暗的梦境中,诗人幻想“把她们的色彩芬芳编成歌曲,/做成诗,去唱软那春天的早晨”。女性的感召激活了邵洵美的女性气质,诗意地再现了柔美的女性体态。
焦菊隐的女性气质显得更加委婉动人。他曾在一场戏剧表演中饰演女性角色并大获成功,和他同台演出的姜公伟回忆道:“他的身段微高一些,而他温柔的表情,玲珑的姿态,至少我们自己是满意的。他听了这话,两颊呈现出一丝红意,微笑地低下头去。在他周围慢流的空气里,似乎闪出他的慈祥的,稚心的,情挚的诗意。我在那时又认识了菊隐真纯的心情及其女性化的含蓄。”[19]诗人的男性本色似乎被亭亭玉立的少女身姿和羞涩扭捏的女性神情取代,被称赞后红晕的脸颊明显是女性害羞的标志,女性气质同时具备儿童的纯真趣味,没掺进丁点杂质。
姜公伟还用当时焦菊隐写下的一首诗歌证明他是“女性化的孩子”,这首名为《香奁乍启》的诗写道:“香奁乍启,/玲珑姿态;/都使人心迷神醉。……这是谁的绒冠?/把玩——把玩,/舍不得送还。”诗中“香奁”为女子盛装香料的小匣子,同时也是化妆的工具,诗人在香粉弥漫的“香奁”中沉醉,仿佛自己便是对着“香奁”梳妆打扮的女子,“香奁”也成为了古代女子闺房的象征物。诗人对毛绒饰品的“把玩”洋溢着童真的趣味,男性的阳刚气质被可爱的女性光环覆盖,女性气质已经主宰了焦菊隐的身心。
赵景深对焦菊隐的女性气质进行了全方位的概述:“他的诗的情调正如他的为人,懒懒的,像一个多愁多病的少女,带着生的闷脱的气息。倘若他是女子,他准是林黛玉!他自己在万里长城的游记里曾经提起别人戏称他为女孩子,他还扮过女孩子,与姜公伟合照了一张照片,好像夫妇合影一样。”[28]焦菊隐像一个被闲愁和泪水紧紧包裹的女子,如《夜哭》中《慵懒》一诗所写:“终日里烦愁悲苦,没有法儿解除。再看看青葱的远林,迷离,迷离,看看斗艳的花朵儿,又失意,失意……虽然芬香的五月给诗人不少的赞赏的材料,而给一个昏愚的人的,只有慵懒的神气。”受到女性化气质感染,焦菊隐的诗里全是女性的悲苦。
韦丛芜的女性气质与焦菊隐类似。沈从文认为他“以女性的柔和忧郁,对爱作低诉,自剖,梦呓”[29]。韦丛芜在诗集《君山》第三十六章回忆与梦中女郎相见和离别的场景:“江面的阳光晶晶闪耀。/山女只不敢走下吊桥。/我扶着伊慢慢地走去,/我不敢再看伊的微笑。/步步踏上百级的江岸,/岸上的晨风冷冷拂面;/我低低说声:‘再会!’——/我如何能往伊们的家园!”诗人站在女性的视角审视彼此的爱恋,即便陷入飘忽意境,他依然对女性的容貌保有清晰的记忆,正如他在诗集《冰块》中《黑衣的人》一诗反复出现的一节:“她是谁,我似乎还记得清。/看,那乌黑的丝发,/那发亮的云鬓,/那苍白的脸孔,/那紧闭的双唇,/那深黑的衣裙,/看,月光下何等的娉婷!”女性的五官和装束深深烙印在诗人的心上,由此生成女性化的凄美气质。
象征派诗人的浪迹充满昏昏欲睡的懒惰,细腻的感官变幻和抑郁的女性气质,逐渐转变为一种颓废的女性媒介。它们刺激着象征派诗人的神经官能,潜意识里的性兴奋因子骤增,但现实的压抑笼罩着苦闷阴影,女性刺激不是为了获得爱的结合,仅仅是苦闷情绪的宣泄,为了“寻求一种力比多的替代物,获得一种变态的满足”[30]。这种“替代物”非但没解决“颓废”问题,反而加剧“颓废”趋向,酒精和泪水的深层次“替代物”接踵而至。
三、酒泪浸润的死亡奔流
读者批评反映象征派诗人的悲哀感受,将内在的经验与外在的环境共同纳入“颓废”趋向的归宿,酒精、泪水的介入,象征派诗人进入死亡冥思的想象空间,探寻释放、缓解悲哀负担的出口。
王独清借助酒精对神经的刺激获得暂时麻醉,玉芙女士却不以为然。读者以诗歌形式反对王独清的迷醉:“是血,/是泪,/是愁苦,/是悲伤,/啊!/人生那里是这样?!……诗人的笔,/譬如酒醴:/只可刺激心灵,/不能滋养身体。”[31]王独清颓废的人生观让读者既疑惑又惊叹,血泪交织的悲愁似乎只有通过酒的刺激才能得以转移,但沉醉在酒精营造的幻境,诗人只是徒劳地自我催眠,日渐消瘦。王独清幻想在酒的浇灌中发泄悲哀的情绪,这种酒精刺激下的文学创作正是西方颓废派的源头。世纪末的一帮法国青年聚集“在巴黎腊丁街,一个咖啡店地窖里,放歌纵酒,这便是颓废派的创始”[32]。同巴黎颓废派青年一样,酒精驱动王独清,放纵自我情欲,舒缓苦闷情绪。
冯乃超的酒精刺激重构中国传统文人借酒浇愁的颓废情景。邵冠华认为诗集《红纱灯》中的“《酒歌》和《南海去》两篇是近乎旧式腐儒的庸俗的‘牢骚式’的‘词’或‘曲’,不是‘新诗’”[33]。读者用“腐儒”与“庸俗”批判古典用词,但“旧式”的艺术剖析里蕴含现代的颓废思想。《酒歌》的开篇和结尾的四句诗均为:“啊——酒/青色的酒/青色的愁/盈盈的满盅/烧烂我心胸”。酒本无色,诗人却用青色涂抹酒精,产生一种怪状,而青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又是一种不太清晰的颜色,《荀子·劝学》里说“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这种蓝绿混杂的色调似乎成为酒精含混不清的刺激象征。“酒”与“愁”借共同的“青色”等同为一物,诗人的心胸被酒精灼烧,也就等同于被忧愁侵扰。如果说王独清诗歌的酒精刺激是对悲哀的选择性遗忘,那么冯乃超的诗歌利用酒精的刺激令悲哀的程度逐步加深,诗人在迷醉中对悲哀有着更清醒的认识,恰如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本想用酒精熄灭愁苦的火焰,反而助长了悲哀的颓势。部分读者眼中“曾经手刃数人,狎妓酗酒的李白,也有人称他做颓废派的诗人”[32]。冯乃超诗歌的酒精刺激再现了李白放浪形骸的纵酒画面,复原了古典文人愁苦悲凉的颓废图景。
于赓虞的酒精刺激更具传奇色彩。阴冷的诗歌氛围“使他感到神明所赋与他生命之酒杯,乃是满满的斟着一杯绝望的眼泪,既没有那豪气使他在强者的面前一站,又不愿意那聪明的人,或者是糊涂至极的人耻笑他是个懦夫的声音,所以他只得每每拿着酒杯在手,一口酒,一狂笑,做个懵懂的醉人”[14]。于赓虞沉迷酒精的“醉人”姿态,癫狂的笑声又使醉酒的常态显出变态的神情,诗人在逃离世间纷争的“懵懂”里麻痹了自我悲哀的神经。
诗集《晨曦之前》“从《红酒曲》后,趋势却像‘每饭必酒,每饭必醉’的五柳先生”[14]。陶渊明即是“五柳先生”,辞官归隐田园后热衷喝酒,创作了《饮酒二十首》,《小序》曰:“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陶渊明借饮酒打发无尽夜晚,也舒展心中不快,在月光下盯着自己的影子对饮,很快便沉醉不醒。于赓虞对酒的嗜爱与陶渊明毫无二致,他在《红酒曲》中疾呼:“红酒,红酒,我的生命,/在此宇宙你以外我无知心。”高穆认为嗜酒如命的于赓虞从酒精“摄取片刻麻醉”[17]。
象征派诗人的悲哀在酒精刺激后获得暂时的缓解,但现实的黑暗依旧让他们心中填满了无限的悲哀,他们只能以痛哭的方式将之宣泄。苏雪林认为李金发诗歌中有许多“恸哭”的字眼[4],读者还列举几句诗歌为例:“我仗着上帝之灵,人类之疲弱,遂恸哭了……耳后无数雷鸣,一颗心震得何其厉害,我寻到了时代死灰了,遂痛哭其坟墓之旁。”现代人的疲软弱小令诗人感慨,胸中积蓄的压抑随着雷声撕裂,诗人在死寂的夜空放声痛哭,尽情释放内心的悲哀。
夜的意象与哭的发泄完美搭配。象征派诗人“常拿夜象征人世的黑暗,的确是白昼使我们对于事物的感觉是明朗的,夜则使我们模糊”[34]。读者批评涉及“夜”的新诗有李金发的《夜之歌》,冯乃超的《梦》《红纱灯》,于赓虞的《风雨之夜》《昨夜入梦》,邵洵美的《花一般的罪恶》,焦菊隐的《夜哭》《艮夜》《寂月》《深夜》《夜祷》《长夜》,姚蓬子的《云夜》《是葡萄憔悴在藤蔓上的夜了》,韦丛芜的《荒坡上的歌者》,石民的《良夜》《月夜》等。夜晚漆黑的苍穹没有丝毫光线,在封闭沉重的氛围里,悲哀慢慢发酵,难以排遣的苦闷凝固在黑夜里,哭泣成为挣脱悲哀束缚的途径。
焦菊隐诗集《夜哭》汇聚泪水和黑夜。姜公伟在评价焦菊隐的《夜哭》时说:“悲哀只是供自己来向里面寻求甜蜜,此确苦中的甜蜜,才是真的,美的甜蜜。在我们悲哀时,‘背地里饮泣’,那不是怯弱的表现,我以为那是有味的,因为我们一旦‘哭’出,或是‘落泪’,我们的悲哀便有了安慰了。”[19]甜美的愉悦感往往需要经过悲哀的洗涤,悲哀经过“哭”与“泪”的刺激获得同情与慰藉。然而,夜晚撕心裂肺的哭泣难免不让人感到一阵颓废的抽搐。阵阵抽泣化作循环往复的音浪,宋琴心认为《夜哭》“把情绪环包着成就一颗圆珠的哭声的浪的回旋”[35]。圆转的结构在读者的心灵产生强烈的刺激,悲凉的哭泣声把夜晚渲染得格外凄楚,诗中风雨夹杂妇孺哭声,流水仿佛也跟着嚎啕。
酒精与泪水的感官刺激,逐渐演变为死亡冥想,它是悲哀到极点的或畏惧或向往的复杂感觉。程千帆评论于赓虞诗集《世纪的脸》时说:“以诗、酒、剑为生命的装饰,正是‘五四’时期文化的征象,那是带着一点浪漫的姿势的。然而那是已经成为霜透心核的枯草了,诗人惟有出之以想像。”[36]酒精无法抵挡悲哀洪流,冷若冰霜的枯萎诗心亟待死亡解救,获得崭新的生命空间。程千帆用诗集《骷髅上的蔷薇》中《毁灭》的诗句来诠释于赓虞对死亡的向往:“荒途中我冒雾进行,不论有无毒蛇或陷阱,/发飘泪流,我踏着人类的墓茔摸索向死城。”通往死亡的路途虽荆棘密布,诗人依旧毫无畏惧地向死神靠近,黑暗现实依托死亡憧憬变为光明。高穆也指出于赓虞诗集《孤灵》中《归来》“厌世自杀的谶语”般诗句:“曾几次,在万籁死寂的寒夜,因回忆人世之侮辱与悲怆,黯惨与空虚,我想以毒药使生命得其永远的安眠。”惨痛的人世令诗人心灰意冷,也便失去了生存的意志。高穆由此推断于赓虞在诗中“与其丑恶的生,毋宁美丽的死,获取永恒的静息……替死海中挣扎的堕落的现代人,喊出最后的丧歌,该唤起多少失意者同情”[17]。上述诗人向死而生的逆向冥思蕴含现代人普遍的颓废哀思。
象征派诗人对死亡的心驰神往饱含生存的意念。苏雪林评论邵洵美诗歌说:“一切厌世的诗人都是死的赞美者,而患着世纪病的现代人于死更极端表示欢迎。”讴歌死亡是基于悲哀情绪刺激之上的情感转移,世纪末的现代人在感伤的气氛中展现出对死亡拥抱的热情,苏雪林转而又认为“颓废派诗人虽厌世而对于生的执着反较寻常人为甚”[37]。读者以邵洵美诗歌《死了有甚安逸》的诗句为例指出邵洵美在死亡想象里“对于生的执着”:“死了有甚安逸,死了有甚安逸?/睡在地底香闻不到,色看不出;/也听不到琴声与情人的低吟/啊,还要被兽来践踏,虫来噬啮。”惨死的情状隐隐令人恐惧,现世的“安逸”远胜于死后的凄凉,在生死的边缘,诗人依旧留恋苟活的种种美好,不愿面对阴冷的墓地。从于赓虞的死亡憧憬到邵洵美的生存意念,象征派诗人的“颓废”出口位于生死交界带,他们“寻找不到出路的精神状态与趋向死路的肉体行为相结合,并深深地沉浸在这种状态中而获得某种心理的释放、满足乃至享乐感,颓废也就出现了”[38]185-186。
王独清诗集《死前》融合了于赓虞与邵洵美对于死亡的颓废观念。诗集出版后,玉芙女士、巴士顿、龙家汾三位读者以诗歌的形式对王独清的死亡意识嗤之以鼻或大加批判。玉芙女士在《常恨》一诗中说:“常恨良辰虚度,/旧梦依然如故,/理不尽的闲愁,/抛去又回原处/且住,且住,/仍向花儿低诉”[31]。飞逝的光阴与闲散的愁绪不免令人心生悲哀,但读者没有坠入死亡的联想,而是回归原点,制止颓废的念头,向自然诉说苦衷。
王独清对死亡的态度或许不太果决,巴士顿用戏谑与反对的口吻说:“朋友你要死便痛痛快快地死罢!不死呢,可不要诳言又诳言。/躲避在死神的黑色大衣边,/去也徘徊,不去也徘徊……要是死了又死,一次,二次,三次……/那么,你宁可在十丈软红尘里长眠。/呸,在死前,你在死前;/尤迷恋着什末叩墓门,立碑铭,/诗人月桂冠,一堆鲜妍的花圈;/而还要把灵魂埋在情人的深底心坎,/借情人儿的假泪,洗涤一番。”[39]
王独清诗集最末两句诗写道:“我知道我现在的生命,已是不能久留的生命,/唵,这些回忆,我只有预备一齐带进,我底墓坑!”龙家汾批判遗嘱与现实的差别:“你嘱说死后烧掉你的诗稿,/这社会自然给你伟大的应报;/你嘱说死后好在你的墓前追述你前生的疲倦,/便得你的心中感着不安的悔恨;/你嘱说死后不愿听着伤感的哀哭,/这样徒然是空打乱你柔弱的心头;/你嘱说死后你的墓前休要竖着巍峨的碑铭,/最好是将你这一抔的黄土墓顶推平……。”[40]
象征派诗人试图利用酒精和泪水涤除“颓废”的污渍,却因此深陷死亡幻境,既喟叹生命尽头的无奈,又在感官刺激里对死亡感到漠然。读者批评中象征派诗人的死亡冥思“既是精神的自我分裂,又是精神的自我和解”[41],垂死挣扎象征他们内心的矛盾,死亡的颓废表现为一种从感官刺激向心理崩溃过渡的悲哀感受。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漂泊无依的足迹牵动着象征派诗人忧伤的思绪,1920—1930 年代读者批评揭示李金发等旅法学生异域游荡的孤独灵魂,也指认于赓虞等因故土沦陷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仓皇模样。象征派诗人在读者视域里俨然是浪人的凄苦形象,漂泊轨迹受到“颓废”感官的影响,蕴含女性化的诗人气质,衍生出强烈的女性刺激,转化为酒精和泪水的含混产物,进而在灵魂深处烙下死亡想象的印记。
西方现代社会的世纪末情绪刺激着象征派诗人敏感的官能,令他们接受颓废思潮的影响。李金发留法期间“受了种种压迫,所以是厌世的,远人的,思想是颓废的,神奇的,以是鲍特莱的恶之华,他亦手不释卷,同情地歌咏起来”[2]。异域的孤苦让李金发在接触波德莱尔的颓废思想时产生了天然的共鸣。王独清在欧洲的流浪之旅中“领受了缪塞的Dandysme,同时,他更遇到了象征派颓废派诗人的诗歌”,结合他自身没落贵族忧伤的情绪,生成的“那种感伤主义,不是卢梭的伤感主义,而是世纪末的感伤主义了”[13]。中国象征诗人在西方社会的落寞感,与法国贵族的伤感相似,面对工业革命后机械化生产与商品化经济的都市景观,丧失了“原有的高贵、精致的精英意识的优势,于是悲观厌世、消极颓废的思想倾向也就成为贵族及部分上流人物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38]35。一无所有的象征派诗人深感疲乏,在失落的世纪之交产生“烦闷苦痛的结果,他们的神经,受了过度的刺激,陷于神经过敏。那寻常一样的刺激,此刻便不觉得刺激了”[32]。
中国社会尽管没有历经西方世纪末的感伤浪潮,但在青年中依然弥漫着悲哀的情绪。姜公伟在对焦菊隐诗歌的批评中说:“人生脱不了悲哀,而悲哀也脱不了人生,尤其是一般的青年——现代一般的青年。他们处在这样诡诈而黑黝的社会里,一方面要应付虚伪的人情,一方面还要寻求内心的要求。”[19]虚与委蛇的人际关系与尔虞我诈的社会风气,让中国青年倍感哀愁,浅薄的社会经验几乎无法支撑他们在大染缸中存活的勇气,于是转而以悲哀的人生观装扮身心。王独清等象征派诗人诗歌迎合了青年颓唐衰微的情绪,梁新桥认为当时“文学上的伤感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是王先生的个人色彩”,梁新桥从反面提出假设否定王独清诗歌感伤的个性色彩:“那时中国的新文学,如过没有感伤主义的趋向,纵使王先生再伤感,在读者中间,是不能引起多数的共鸣的。”[42]
象征派诗人的人生悲哀在读者批评中表现为外界的刺激与压迫,李金发、王独清、冯乃超、于赓虞、焦菊隐等人“当外感之刺激过深时,易陷感情于郁抑,其乏制裁之力旷观之思,一往不拔终且精神堕落!彼厌世派抱消极悲观主义;非不肇因于此”[43]。除了诗人们的个人经验,他们的人生悲哀实则是社会的悲哀。“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现代思潮,“颓废”的诗学因子被置于庞杂的“政治生活、经济基础、文化潮流、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共同决定的历史场域”[44],象征派诗人诗歌隐秘纷繁的“颓废”趋向,从传播接受的层面引发读者的批评话语与审美意识。
注释:
① 四本关于文学的“颓废”研究专著按照出版时间先后顺序,依次为:一、解志熙的《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二、肖同庆的《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三、张器友等的《20 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四、薛雯的《颓废主义文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② 参见邓招华:《重构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图景》,《江西社会科学》2017 年第8 期,第112-118页。作者将李金发等象征派诗人称作“颓废的象征主义者”。
③ 参见姜玉琴:《叙“颓废之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与李金发诗歌创作关系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3 期,第145-153 页。作者由此引出“忧郁的审美风格问题”。
④ 参见米家路:《狂荡的颓废:李金发诗中的身体症候学与洞穴图景》,《江汉学术》2019 年第4 期,第91-106 页。就“颓废”的所指而言,作者将之概括为:“狂荡的颓废”(une turbulente décadence)。
⑤ 本文的象征派诗人群体不是单纯从文学流派的角度限定,而是从象征风格和意识方面汇集不同文学社团相似的新诗人。正如陆耀东先生在《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里写道:“比如各主要文学社团中都有象征主义诗人……新月社成员于赓虞明显倾向象征派。”(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