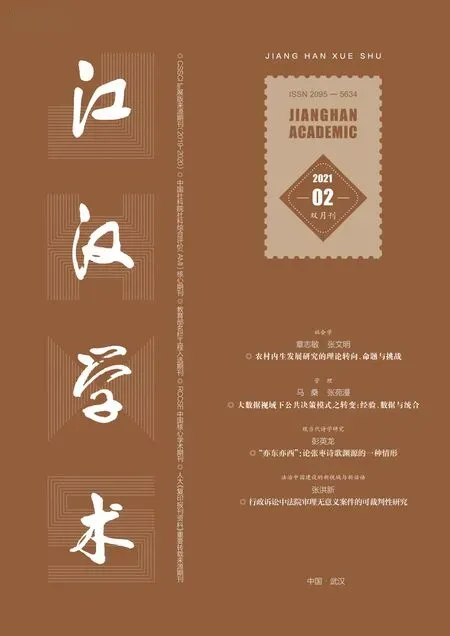从训诂到义理:《老子》“自然”之基本问题辨析
宋德刚
(广州美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006)
从训诂出发求得义理,是人们颇为熟悉的中国哲学诠释方法。在这一方法中,训诂是基础,其意义在于:“训诂不仅有益于我们深化现成的思想范畴的哲学内涵,而且有助于发现某些常用字被日常用法所掩盖的内在意义,即从中发现未被揭示的义理问题。”[1]如果与西方相比照,最接近以训诂求义理的当是哲学语义学。洛夫乔伊说:“哲学语义学也就是对一个时期或一种运动中的神圣语词和短语的一种研究,用某种观点去清除它们的模糊性,列举出它们各种各样的含意,考察在其中由模糊性所产生的混乱结合的方式,这些模糊性曾影响到各种学说的发展,或者加速某一流行的思想由一个向另一个,或许正好是向其反面不知不觉地转化。由于其模糊性,单纯的语词很有可能作为历史的力量而产生某种独立的活动。”[2]以训诂求义理与哲学语义学的关系不是本文所要关注的,笔者只是想指出,注重由解释字词以通达思想乃是中西学者的某种共识。
就中国哲学而言,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许多从事经典解释的学者都在运用训诂阐发出哲理。然而,如何妥善运用训诂,如何将字词解释、语境、文本、思辨有机结合,是颇为紧要和困难的问题。本文正是由此出发,围绕《老子》之“自然”的三个基本问题展开辨析:首先是对“自然”之“自”作“始”义的辨析;其次是对“自然”释为“自己如此”的辨析;最后是对五例“自然”指向对象的辨析。一定意义上讲,本文是通过运用训诂、对某些训诂进行辨析,并结合语境、文本而阐发义理。
一、“自然”之“自”难作“始”
“自”的“始”义十分特殊,从哲学的视角看,这涉及本根、起源、本然、本质等话题。对于哲学研究者来说,“自”的这一层含义无疑具有吸引力,有论者便从此处入手分析《老子》之“自”“自然”。论者的思辨从哲学上讲是一种深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先秦时“自”作“始”义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就需要对相关解释和论述进行辨析了。
(一)许慎与段玉裁的解释
《说文解字》曰:“自,鼻也,象鼻形。”段玉裁注曰:“此以鼻训自,而又曰象鼻形。《王部》曰:‘自,读若鼻。今俗以作始生子为鼻子是。’然则许谓自与鼻义同音同,而用自为鼻者绝少也。凡从自之字如《尸部》‘㞒,卧息也’,《言部》‘詯,胆气满身在人上也’,亦皆于鼻息会意。今义从也、己也、自然也,皆引申之义。”段玉裁所引《王部》的内容乃是指《说文》中的“皇”字,《说文》曰:“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自,读若鼻,今俗以作始生子为鼻子是。”段玉裁就“皇”字注曰:“扬氏雄《方言》曰:‘鼻,始也。兽之初生谓之鼻,人之初生谓之首。’许谓始生子为鼻子。字本作鼻。今俗乃以自字为之,径作自子。此可知自与鼻不但义同,而且音同,相假借也。今俗,谓汉时也。”[3]136,9,10
许慎和段玉裁给出的“自”的含义主要有五个,本义为“鼻”,引申义为“从”“己”“自然”,以及与“鼻”“皇”有关联的“始”义。需要注意的是,引申义“自然”并非《老子》的“自然”。
(二)当代学者的论述
萧无陂、许建良、李晓英、叶树勋等学者都认为“自”有“始”义。萧无陂认为:“‘自’还有一种建立在其本义基础上的重要引申义,鼻子有‘始’的意思。‘鼻’为‘始’义古文很常见,《汉书·扬雄传》:‘或鼻祖于汾隅。’鼻祖亦即始祖。‘鼻’训为‘始’在经文中亦常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后世俗说谓人之胚胎,鼻先受形。’总之‘自’有‘始’‘初’等义,引申开即‘初始(的)’‘原初(的)’的意涵,作名词或形容词,这是‘自’的第一层引申义。这层含义对于‘自然’一词的理解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自然”之“然”引申为“如此”“这样”“样子”等意,他也没有抛弃“自”作为“己”的这层含义,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自然”这个概念就具有两层内涵:“根源性状态”“原初性状态”;“自己如此”“自己这样或那样”。“自然”就是“一切事物自身皆有其初始状态或原初性状”[4]142-143。与萧无陂略有不同的是,许建良将“始”作为“自”的原义或本义。他说:“在本义上,‘自’象‘鼻’,‘读若鼻’,扬雄《方言》认为,‘鼻’是‘始’。……‘自’的原意为原始、开始、初始、始发,引申为自己、自然。”[5]李晓英采纳许建良对“自”的本义为“始”、引申义为“自己”的研究,认为“自”的“开始”“初始”之义“已经蕴含了一种发动力,潜藏了一种根源,否则就无法开始”[6]。叶树勋也认为:“具体到‘自然’一词的使用,在无外力的情况下,‘自’强调‘自己’的意思,而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自’主要体现‘原初’之义。”[7]相较而言,萧氏、许氏的论说更为细密。因此,笔者将主要围绕许慎、段玉裁、萧无陂、许建良的观点,并结合今人在文字学、语言学方面的相关举例和研究展开辨析。
(三)辨析
第一,许慎从“皇”字引出“自”之“始”义实乃误判。李瑾说:“从殷周古文看,皇字并不从自,只有秦、汉篆、隶才从自之省体。”[8]106刘瑞明说:“金文‘皇’字中部是圆圈内有一横,上部是三或四条斜光线,下部是‘土’字。《汉语大字典》引吴大澂《古籀补》:‘皇,大也。日出土则光大,日为君象,故三皇称皇。’又引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皇即煌之本字。’另有按语:‘皇象王著冠冕形。’就是说,到篆体才变成‘皇’的字形。可见许慎‘从自、王。自始也’的分析不确。”[9]一言以蔽之,许慎是根据秦汉时期的书写文字来作出的解释,从而忽视了“皇”字在殷周时期其实与“自”并没有关联。
第二,段玉裁与许慎不同的一点是他引用了扬雄《方言》“鼻”有“始”义的内容,以证“自”有“始”义,许建良正是从此处入手。萧无陂引用的例证主要是《汉书·扬雄传》中的“或鼻祖于汾隅”,以及将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对“自”的解释中的“后世俗说谓人之胚胎,鼻先受形”作为佐证。扬雄提出了“鼻”有“始”义,但很难判断“鼻”有“始”义是从何时开始的,因为从现有文献上看,扬雄是第一个说“鼻”有“始”义之人,许慎说“今俗以作始生子为鼻子是”,段玉裁明确说“今俗”即为“汉时”,而“鼻祖”一词也是在汉代文献中出现的,则汉时“鼻”有“始”义是肯定的。
尽管《方言》乃是对周秦方言的研究著作,但语言、文字具有时代性,扬雄之时为西汉末期,距春秋战国之际约四百年,此四百年间语言、文字乃至人的思想意识都会发生许多变化。“鼻”或许在先秦时有“始”义,但就笔者所见,先秦文献中还没有找到“鼻”字有用作“始”义的。殷周时期“自”与“鼻”基本已各有所指,“自”作“鼻”的用例十分罕见。李瑾指出:“即使在多如牛毛的殷墟甲骨卜辞、记事刻辞中也很少见,目前只在一块龟腹甲上发现两条正、反卜问的辞例‘自’用为‘鼻’。”[8]103不仅甲骨卜辞、刻辞中难见单独的“自”作“鼻”义来用,在传世文献中也几无有力的例证。从仅有的一点关联出发,也不能确定“自”有“始”义。因为“自”象鼻形,就是指鼻子这种器官,即便是“鼻”有“始”义,也是一种引申义,萧无陂注意到了这一点,而许建良用一种引申义再来转指为“自”的本义,这就不太符合逻辑。总之,仅从《方言》和《汉书·扬雄传》中实难判断先秦时“鼻”具有“始”义,乃至“自”(尤其是本义)具有“始”义,而许慎的误判也不支持先秦时“自”有“始”义,朱骏声的“后世俗说”的“后世”也没有具体的时代界限。不过,由于《说文解字》的影响极为广泛,那么此后“自”有“始”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今人的研究中,杨树达《词诠》、杨伯峻《古汉语虚词》、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在解释“自”时均未列出“自”有“始”义。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王叔岷《古籍虚字广义》列出了“自”有“始”义。其中,《古书虚字集释》有两个例证,皆出自《尚书》;《汉语大词典》有两个例证,出自《韩非子》和《南史》;《古籍虚字广义》有一个例证,出自《论衡》。《南史》为《说文》之后的著作,可暂且不论,其余皆先于《说文》,需详察。
刘瑞明对《尚书》和《韩非子》中的例证作出了分析:“《尚书·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实际是说:当儿子从远处经商回来孝敬父母,父母高兴时,自然可以饮食丰盛而用酒。孔传:‘子乃自絮厚致,用酒养也。’解释成‘自己’,也可。《尚书·多方》:‘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而孔传:‘小大多正自为不和。’可见,与‘尔’对比的‘自’只能是‘自己’。”[9]刘瑞明解释“自洗腆”之“自”时给出了两个含义,即“自然”和“自己”,但是“自”之“自然”义实为晚出,因此只能作“自己”。刘瑞明接着说:“《韩非子·心度》:‘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心度》开篇即说:‘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可证‘爱之自’即‘爱之由’:刑,是由爱(而设的)。如果理解成刑是爱的开始,就会推导出没有刑就没有爱,便是大大不合理的了。”[9]可见,《尚书》《韩非子》中的例证并不能支持先秦时“自”有“始”义①。
王叔岷说:“论衡讲瑞篇:‘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上两‘自’字,乃‘自己’之‘自’。末‘自’字义与‘始’同,谓‘三年始知不及孔子’也。刘子心瘾篇作‘三年方知不及’,‘方’亦‘始’也。”[10]首先,“自知”一词在《老子》中就已出现,可从未见人说过《老子》之“自知”乃为“始知”,《淮南子》中有五例“自知”,亦不作“始知”讲。其次,前两句中的“自谓”之“自”作“己”,第三句“自知”之“自”按常理作“己”更加合适。再次,《刘子·心瘾》与之相对应的原文为:“若子贡始事孔子,一年自谓胜之,二年以为同德,三年方知不及。”[11]其遣词造句与《讲瑞》篇并不相同,不能以此来断定“自知”为“始知”。最后,即便“自”为“始”,也并不表示先秦之时“自”有此义,因为“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始出自《论衡》,“三年方知不及”始出自《刘子》,《论衡》《刘子》都不是先秦文献。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至少没有充分的例证可以证明先秦时期的“自”字具有“始”义,更遑论本义为“始”了。当然,笔者并非主张先秦时的“自”就一定不具有“始”义,所谓“说有易说无难”,应当谨慎地对待文献,通过一定的分梳,至少《老子》中的“自”不具有“始”义的可能性极大。
此外,笔者还想指出两点,供研究者思考。其一,我们应该注意到先秦时一字(一词)多义是常见的,但在组词时要将一字(一词)并无直接关联的两种或多种含义都融入其中就属于反常了。因此,退一万步讲,即使《老子》之时的“自”真有“始”义,《老子》中的“自然”之“自”也很难说兼具“自己”“始”两义。其二,一旦“自然”理解为“始然”,那么我们还要问:《老子》的其他“自”类语词(即以“自”为结构原型的复合词、短语等)中的“自”是否也要从“始”义理解(上文已有论及)?又或者,哪些该从“始”义,哪些不该从“始”义理解,其判定标准是什么?如果只有“自然”之“自”才具有“始”义的“资格”,其依据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提倡“自然”之“自”为“始”的学者应当直面的。
二、“自然”:作为正面价值性的“自己如此”
其实,学界的主流观点是释“自”为“自己”,“然”为“如此”,“自然”的含义是“自己如此”,代表者如张岱年、卢育三、陈鼓应、涂又光、刘笑敢等人②。“自己如此”是将“自”作代词,“然”也作“代词”。
“自己如此”在训诂学、语义学上是说得通的,而且“自”指“自己(自身)”可以从《老子》中其他“自”类语词得到佐证,如“自知”“自爱”“自胜”“自化”“自朴”“自定”“自富”“自均”等等,这些“自”皆指称对象自身。关于“然”,《说文》曰:“然,烧也。从火肰声。”段玉裁曰:“烧也。……训为如此。尔之转语也。”段玉裁在注“尔”字时说:“又凡训如此、训此者皆当作尒。乃皆用尔。尔行而尒废矣。”[3]128《玉篇》曰:“然,如旋切,烧也,许也,如是也,应言也。”[12]“如是”“如此”乃是代词,可作谓语或状语。《说文》曰:“如,从随也。”段玉裁曰:“从随即随从也。随从必以口。从女者,女子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白虎通曰:‘女者,如也。’引申之,凡相似曰如,凡有所往曰如。皆从随之引申也。”[3]620可见,“如”是随从某一对象的,“如是”“如此”便是“随是”“随此”,“是”与“此”是中心,“如是”之“是”乃是代词,也就是“此”的意思。《庄子·齐物论》曰:“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13]“彼是”正是“彼此”。
不过,将“自然”释为“自己如此”仍需要深入探讨。“自然”具有正面价值性,“自己如此”则具有开放性。“自己如此”只是一个单纯的语义分析的结果,将这一含义超出语境、文本,就会造成一定的问题。譬如《老子》中具有负面色彩的“自见 ”“ 自是 ”“ 自 伐”“自 矜”“自 贵 ”“自生 ”“ 自为大”也可以从“自己如此”的角度去理解。一个作恶的人在为他的恶行辩护时,也会说这是他的“自己如此”。而《老子》乃至道家显然是在正面意义上使用“自然”一词的,贡华南认为“自然”是一“正价值”[14]66。王博进一步指出:“我们仍然要从‘然’字入手。在存在的意义之外,‘然’的另外一个主要含义是价值领域的‘许’也。‘许’代表的是一种认可和肯定,即我们如何理解事物如此存在的意义。事物的存在是一回事,如何理解事物存在的意义是另一回事,后者必然牵涉到价值的问题。”[15]48将“如此”义、“许”义结合起来,“然”便具有“存在和价值两个方向的意义”[15]53,而这也表示“自然”的两个方向。
那么,从“许”义理解“自然”之“然”可行吗?我们来看《庄子》中的一个例子。《秋水》篇曰:“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16]引文中的“然”意指与“非”相对的“是”。杨伯峻说:“‘然’可以当‘是’‘对(正确)’讲。可以作谓语,也可以作应对之词。”[17]这样的“是”也就是“许”。但这里的“自然”显然不是《老子》《庄子》所要言说的“自然”,其大意是“自以为是”。可见,“许”义的“然”与正面价值之间并不能划等号。此外,“如此(如是)”义、“许(是)”义的结合,也属于前文所说的反常,应当谨慎对待。
如果不从“许”义出发,“自然”的正面价值性何以体现?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是应当返回语境、文本之中,考察《老子》是怎样言说“自然”的。在《老子》的五例“自然”中,有三例具有明显的正面价值性,分别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功成事遂”泛指事情的成功,“法”具有遵循之意,“常”指恒常(《老子》中有“常德”“知常”“常足”等词),这些语汇都具有正面价值性,并与“自然”关系密切,特别是“法自然”“常自然”,“自然”被正面价值所“环绕”。依此,便可顺理成章地从正面价值去思考“希言自然”(《二十三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18]166(《六十四章》)。
要之,“自然”的字面意思是“自己如此”,正如陈鼓应所言:“‘自然’并不是指具体存在的东西,而是形容‘自己如此’的一种状态。”[19]30“自己如此”实际上是正面价值性的“自己如此”。《老子》运用“自然”一词不是指一切存在状态。因此,陈鼓应认为老子提出“自然”,“来说明不加一毫勉强作为的成分而任其自由伸展的状态”[20],涂又光认为“每个存在的状态和变化,都是‘自然’”[21],便显得不够严谨,“任其自由伸展”和“每个存在的状态和变化”是将负面的、消极的内容包含在内,而这就与“自然”相悖了。
三、五例“自然”何所指向
当我们面对《老子》的“自然”时,特别关切的一个问题是谁“自然”?也就是说“自然”的指向对象(也即“自然”之“自”的指称对象)是什么?它之所以基本和重要,是因为在分析指向对象的过程中,“自然”的观念意涵和重要性会逐渐清晰起来。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两类较有特色和代表性的观点:其一,“自然”的指向对象被规定为万物和百姓,代表者如池田知久、王中江、王博、曹峰、叶树勋等;其二,“自然”的指向对象是多元的,其可以指向道、德、天地、万物、圣人、百姓等,代表者如贡华南、罗安宪。针对第一种观点,笔者这里只简要介绍王中江和池田知久的研究。王中江重点分析了“道法自然”,而他的方法是对其他四例“自然”的梳理,他认为五例“自然”具有某种一致性,指出:“‘自然’是同‘万物’和‘百姓’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言以蔽之,就是道、圣人的“无为”,万物、百姓的“自然”。因此,“‘道法自然’的准确意思是:‘道遵循万物的自然’。”[22]39池田知久认为:“所谓‘自然’,就是‘万物’、‘百姓’通过其自身内在力量而自律、自发性地存在、变化。”[23]可是,既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而且“自然”可以指向万物、百姓,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指向道、天地、圣人等?贡华南就认为五例“自然”的指向对象是不同的:“‘百姓皆谓我自然’指百姓之自然;‘希言自然’指天地圣人等希言者之自然;‘道法自然’指道之自然;‘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指玄德之圣人之自然;‘辅万物之自然’指圣人和万物之自然的关系。”[14]64罗安宪针对《六十四章》和《五十一章》的“自然”,指出“‘圣人’治国,不是要‘无为’,而是要‘自然’”,“‘道’‘德’生养万物,则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此正是‘道’‘德’的‘自然’”[24]。
几位学者都是基于文本作出的分析,结果却大相径庭。造成分歧的原因主要是五例“自然”在语境、文本中的清晰程度是不同的,这就加大了论者的研究难度和结论的偶然性。在宏观层面,笔者认同贡华南、罗安宪的研究进路。而在微观层面,指向对象仍需进一步探讨。
在五例“自然”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表述较为清晰、信息较为充分的当属《六十四章》的“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和《十七章》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8]40。王中江也指出这两章“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其所属关系”[22]40。“自然”依附于“万物”“我”。“我”指何人有两种看法,通常的看法是“我”指百姓,也有人认为“我”指圣人。刘笑敢说:“‘百姓皆谓我自然’一句,历来的解释都是百姓皆谓‘我自然’。(蒋锡昌、陈鼓应、古棣)这种理解以‘谓’为‘曰’字,因而‘我自然’就是‘曰’引起的直接引语。河上公似乎是这种理解的先河。……笔者认为,河上公所代表的通行的理解未必符合《老子》全文中‘自然’的基本思想。按照这样理解,自然只是百姓自认为如此的一种陈述。但事实上,‘自然’在《老子》中有很高地位,不是一般性的描述性词语。”他又指出本章的叙事的主体是圣人,而按照竹简本、帛书本的动宾句式来看,“成事遂功”或“功成遂事”应当与下句的内容贯穿起来,则“我”就是指“圣人”而不是指“百姓”,并分析了“谓”在先秦时有“评论”“认为”的意思,应当句读为“百姓谓我,‘自然也’”,尽管竹简本作“曰”,但是“竹简本此处没有用‘谓’字是因为那时‘曰’与‘谓’的分工还不明确,‘谓’的使用还不普遍,而帛书本的编者已经意识到了二者的区别,所以用‘谓’而不用‘曰’字”[25]235-237。即使“谓”作“评论”或“认为”,仍并不一定是针对他人的,因为还有“自我评论”“自我认识”之说,况且“曰”字比“谓”字更能体现“我自然”是百姓之言,而以“‘曰’与‘谓’的分工还不明确”来强调作为“评论”的“谓”更准确则显得较为牵强。刘笑敢句读的“百姓谓我,‘自然也’”是经过改造的,竹简本作“而百姓曰我自然也”,帛书本作“而百姓谓我自然”,王弼本作“百姓皆谓我自然”[25]233,刘笑敢将“而”删去,又在“自然”之后加上“也”。“而”字删去之后,失去了转折的意味,加上之后,语势有所变化,它可以意味着主语的转换,那么后面的主语是“百姓”也是顺理成章的。加上“也”字除了有竹简本的依据,还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句读为“百姓谓我,‘自然’”,则语气、语势上不够顺畅,“自然也”则平缓、顺畅,但是竹简本的“而百姓曰我自然也”句读为“而百姓曰:‘我自然也’”较之刘笑敢的整合版更加顺畅,且本身不用进行丝毫修改,即使去掉“也”,也不影响语气、语势。因此,笔者主张“自然”在这里是指向百姓的,“我”即是百姓的自称。《五章》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8]13尽管这一章强调的是天地与万物、圣人与百姓的关系,但从类比的角度看,《老子》是将圣人类比于天地,百姓类比于万物。因此,针对《六十四章》和《十七章》的“自然”,我们可将其划为一类,称之为“万物—百姓之自然”。顺此理路,我们不禁要问:天地、圣人是否也是“自然”的?对这一问题,《老子》是以隐喻的方式来回答的。
《二十三章》曰:“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18]57在“希言自然”中,“希言”是用来解释“自然”的。什么是“希言”?蒋锡昌说:“老子‘言’字,多指声教法令而言……‘希言’与‘不言’,‘贵言’同谊,而与‘多言’相反。‘多言’者,多声教法令之治;‘希言’者,少声教法令之治;故一即有为,一即无为也。”[26]陈鼓应说:“希言:按字面解释是:少说话。深一层的意思是:不施加政令。”[19]153这都是从政治治理的角度来解释“希言”。笔者认为,“希言”中“希”是形容词,指少,“言”是动词,指说话。但在语境中,“希言”并不是指“少说话”,而是指涉了两层隐喻。在第一层隐喻中,“希”隐喻时间上的不持久,“言”隐喻刮大风、下暴雨(它们都属于天地的一种比较强烈的运作),“希言”隐喻的就是“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其意为天地的强烈运作是不持久的。在第二层隐喻中,“希”隐喻数量上的少,“言”隐喻发布政令(发布法令是一种比较外显的治理方式)。由于天地与圣人相类比,我们有理由认为“希言”隐喻的就是作为优秀统治者的圣人少发布政令。值得注意的是,“飘风”“骤雨”并非像王淮所说的“‘飘风’以喻暴政之号令天下,宪令法禁是也”“‘骤雨’以喻暴政之鞭策百姓,赋税劳逸是也”[19]154。“飘风”“骤雨”是天地本身就有的,而《老子》中讲天地的其他地方都不涉及负面内容。因此,笔者不主张从负面意义去理解“飘风”“骤雨”。换言之,无论是哪一种隐喻,《老子》都不是要彻底取消“言”。一个没有“飘风”“骤雨”的现象世界是不存在的,而一个有统治者却又没有任何政令的社会也是不可思议的。基于此,“希言自然”意指呈现出“希言”的状态便是“自然”的,它同样涉及两层隐喻:其一,“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便是天地的“自然”;其二,做到少发布政令,便是圣人的“自然”。第一层隐喻是第二层隐喻的基石,或者说天地的“希言自然”是圣人的“希言自然”的一种合理性根据。“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一设问便体现出两者的关系。要之,《二十三章》的“自然”首先指向的便是天地,其次指向的是圣人,可称之为“天地—圣人之自然”。
虽然万物与百姓相类比、天地与圣人相类比,但当我们跳出这种类比,会发现百姓与圣人作为人,其实都属于万物这一范畴。这就是说,实际上万物的“自然”是一大前提。《六十四章》中圣人的诸种存在状态并非万物“自然”的原因,其连同百姓的“自然”都应当是万物“自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除了“希言”,圣人的“自然”还应当有其他类似的内容,而百姓的“自然”也应当有更加具体的内容:“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七十二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二十二章》),“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8]150(《五十七章》),等等。圣人的“自然”,一言蔽之就是自制(如果用《老子》中的语词概括,则应为“自胜”);百姓的“自然”,一言蔽之就是自化③。
这三例“自然”所要表达的就是天地、万物的“自然”,其意味着现象世界中的存在者展开并呈现着合理的自身。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现象世界中的存在者④何以能够“自然”?这一追问涉及现象世界中存在者的本质问题,即它们的这种“自己如此”还有没有更为深层和本质的原因。而这就必然要从宇宙生成论、本根论、本性论等方面去思考。《老子》曾探讨过宇宙生成的序列,即《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8]117笔者曾指出,“道生一”是“‘道’展开了自身。在展开中,孕育出‘二’”,“二”指“天地”,“天和地的共同运作也即天地展开自身可谓之为‘三’,在这种运作之下便产生了万物”[27]。道是本原、本根,属于形上世界,道生成天地,天地生成万物,天地与万物又都属于现象世界。《老子》本身言简意赅,因此在谈论形上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关系时,会省略掉一些内容。《五十一章》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18]137将道、德、万物放在一起,而省略了天地。笔者认为,这里的“万物”应当隐喻着现象世界中的存在者,而道、德并举并不是说在道之外还有一个叫作“德”的存在者。罗安宪认为“德”就是“性”[28]。笔者认为:“对于天地、万物而言,‘道’是外在的,但同时,‘道’以‘德’的形式内贯于天地、万物,天地、万物便以‘德’体现着‘道’。‘德’是天地、万物的本性,而‘德畜’就是本性的发动。”[27]“尊道贵德”中的“尊”“贵”是动词,“尊道贵德”并非指现象世界中的存在者有意去“尊—贵”道和德,而是指它们本于道、依于德而能够展开自身,是一种存在层面的去“尊—贵”。基于这种“尊—贵”,《老子》进而提出“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⑤。“道之尊,德之贵”中的“尊”“贵”是形容词,形容道和德处于至高的地位。“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在马王堆帛书本为“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25]529。“命”与“爵”相通,“爵”表示给予尊位,象征一种世俗价值,“莫”表示否定。那么,“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实是说道和德的至高地位并非世俗所给予,而是通过“自然”实现的。因此,此例“自然”是指向道和德的,可称之为“道—德之自然”。“道—德之自然”具体说就是“道生德畜”,由此,才有现象世界中的存在者之“自然”。
将上述四例“自然”结合起来看,以“自然”为中心,世界构成为了一个有机的系统:道展开自身,生成现象世界便是道的“自然”,在这个过程中,德(本性)的发动便是德的“自然”,天地、万物依本性展开自身便是天地、万物的“自然”,万物中的圣人与百姓各有各的“自然”。
在以上分梳的基础上,再来看最后一例“自然”。《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8]64人、地、天、道,通过顶针的修辞方式和作为中介的“法”,层层递进,至“道法自然”结句。从顶针式的言说序列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一序列讲了两种关系。一种是人、地、天、道之间的单向关系,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⑥;一种是人、地、天、道这些存在者与“自然”的关系,即“道法自然”。前一种是以具体存在者面目出现的,非常直观。后一种关系是将“道”作为一种表征存在者整体的隐喻⑦,将“自然”作为一种表征整体性存在状态的隐喻,也就是说“道法自然”的“道”实际上包含着道、天、地、人,“自然”实际上包含着道、天、地、人的合理性存在状态。那么言说序列的意涵为:道、天、地、人各自“法”自身的“自然”。“自然”的正面价值性显露无遗,或者说,“自然”成为了一种关于存在者的合理存在状态的价值性概念。其次,言说序列中的头与尾常常具有某种密切关系。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更强调“道—生—万物”。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更强调“人—法—自然”。尽管《老子》中论及了道、天地、自然物这些非人的存在者,但《老子》的目的始终是如何安顿人,价值的最终归宿都要落实到人身上。可以说,“人—法—自然”是《老子》在宏观视域下对人自身的存在、人与他者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结晶。基于上述两点,笔者将这一例“自然”称之为“人与世界之自然”⑧。
由以上辨析,我们发现训诂以及妥善运用训诂十分重要,但训诂还需同语境、文本分析相结合。应当说,搞清“自然”的基本含义和五例“自然”的指向对象,是理解《老子》乃至道家“自然”观念的基石。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并非所有的内容都能获得一个准确无误的解释,有些甚至很难解释。王弼曰:“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18]64王弼对“自然”的解释多少体现出这种困难。不过,面对种种困难,尽己所能,将经典中的思想有理有据地阐发出来,当是哲学研究者的共业。
注释:
① 叶树勋也举了《韩非子》的例子,此外他还举了《礼记·中庸》的“知风之自”为例。但是这里的“自”是“从”或“由”之义。郑玄注曰:“自,谓所从来也。”可知“自”非“始”。参见叶树勋:《早期道家“自然”观念的两种形态》,《哲学研究》,2017 年第 8 期,第 19 页。
② 也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将“自然”解释为“自然而然”。萧无陂对这一解释进行了批驳:“被解释的名词又重新出现在解释用语之中,属于同义反复。此外,如果我们要进一步追问‘自然而然’中的‘自然’,就会面临上文谈到的同样困境。”因此,本文不讨论“自然而然”这一解释。参见萧无陂:《论早期道家“自然”概念的双重意蕴》,《中州学刊》,2010 年第 5 期,第 145 页。
③ 关于“民自化”,笔者曾指出:“它统领‘自正’‘自富’‘自朴’。作为一种观念,‘民自化’主要指的是民众的社会伦理生活之‘化’,是民众在社会伦理生活之中合理地、主动地变化、发展。”参见宋德刚:《〈老子〉“民自化”观念研究》,《江汉学术》,2018 年第 2 期,第 119 页。
④ 本文所论及的现象世界中的存在者是指在现象世界中具有主动性的存在者。而人造器物属于被动性的存在者,不在讨论之列。在《老子》中,被“自”指称的存在者都是主动存在者。
⑤ 王中江指出:“对于这句话,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说道和德受到万物的尊重,没有谁下命令或作安排,它从来就是那样的;二是说道和德受到尊重,是因为它们对万物不加干涉,使万物顺任自然。”王中江支持第二种解释。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有各自的问题,故皆不取。参见王中江:《道与事物的自然:老子“道法自然”实义考论》,《哲学研究》,2010 年第8 期,第40-41 页。
⑥ 天与地虽为同一类存在者,但《老子》在这里似乎进行了区分。这可能与当时的知识背景有关,“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地位要高于“地”。
⑦ 作为世界之本根、本原的道有“资格”成为这样的隐喻。
⑧ “道法自然”或“人与世界之自然”与儒家的“万物一体”观在思想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具有着丰富的当代意义,都可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底蕴。限于篇幅,笔者对此一问题将另撰专文探讨。关于儒家“万物一体”观及其当代意义,可参见刘海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儒家伦理底蕴》,《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第 38-4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