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窟第2窟正壁普贤行愿图像定名考
——兼论榆林窟第2窟营建背景①
袁 頔(浙江大学 艺术与考古学院暨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8)
榆林窟第2窟位于今甘肃省瓜州县,是一座具有代表性的西夏佛教石窟,窟内壁画清新典雅,艺术水平极高并呈现出独特造像思想。不少前辈学者的研究都曾涉及该窟:刘玉权先生认为,榆林窟第2窟属于西夏在榆林窟营建的最晚一批洞窟,在断代过程中列入敦煌西夏石窟第三期洞窟;[1]沙武田先生在论及敦煌石窟分期时也持此意见;[2]关友惠先生提到,以榆林窟第2窟为代表的西夏晚期洞窟,具有别样色彩,壁画作品中的细节精致华丽,观之犹如置身于殿堂彩画,是敦煌地区焕然一新的风格;[3]赵晓星先生则重点关注窟内正壁骑狮文殊图像,并利用佛教经典对该图像相关问题作出新解释;[4]16—25王胜泽先生综合两宋山水画风格,对榆林窟第2窟部分壁画创作技法进行了分析。[5]但至今该窟正壁即东壁仍有部分图像未曾准确定名,且壁面题材组合缺乏整体解读,由造像延伸出的信仰状况、营建背景等方面尚无人进行较为详细的探讨,故笔者不揣冒昧,对上述问题略作分析,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校正。
一、榆林窟第2窟概况及正壁普贤行愿图像的定名
榆林窟第2窟现存有甬道及主室,主室为覆斗型顶,地面中央建有中心佛坛(图1)。甬道顶绘制有一尊触地印坐佛,南北壁内容有所残损,但依然保留了梵天赴会的画面。主室藻井为团龙井心,龙身绘制十分细腻,周边饰以青、白云纹(图2)。四披有精美的璎珞垂幔,其下为千佛。

图2 窟内藻井
根据《安西榆林窟内容总录》,榆林窟第2窟主室四壁的主要内容为:正壁中央画文殊变(图3),并在正上方配有金棺自举、涅槃图两小幅画面;文殊变左右有观音救难条幅画。正壁南、北两侧各画说法图,南、北两端绘条幅故事画;南北壁上方皆画垂幔,下方三幅说法图并列绘制;西壁上画垂幔,门南、北均为水月观音,门南下部女供养人四身、侍女五身,门北下部男供养人七身(图 4、5)。[6]

图3 窟内正壁文殊变
以上为内容总录中对榆林窟第2窟内容的梳理与记录,由此可以发现,总录对于正壁图像的解读还不甚清晰,仅以说法图、故事画等一言代之。随着进一步研究,相关探讨又有了新进展。学者赵晓星认为,榆林窟第2窟正壁文殊变十分特殊,该图像与上方小图呼应,突出五台山文殊地位,是结合《文殊师利般涅槃经》和《文殊真实名经》的内容创作而成。[4]16另外,小幅涅槃图中出现的跪姿比丘代表《文殊涅槃经》中的文殊,他与图示中右侧四名比丘象征五百仙人,于佛灭度之后示现比丘形继续弘扬佛法,所以此幅涅槃图像表达的观念是文殊菩萨即为佛祖之继承者。[4]20
榆林窟第2窟特点鲜明,窟内绘画题材、组合方式都堪称独一无二。与敦煌石窟群中同时期西夏洞窟相比较,该洞窟仍彰显出与众不同的风格,故在营建过程中,其壁画创作一定有着新鲜血液的灌输,并受到西夏佛教发展大背景与艺术水平飞速提升的影响。通过图像情节与构图等方面对比,笔者认为,洞窟正壁文殊变南、北两铺壁画应是以西夏刊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可思议境界普贤行愿品》卷首版画为蓝本所绘,正壁南、北两端条幅故事画则为普贤行愿的具体细节内容。
1.洞窟正壁南、北铺壁画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现留有《普贤行愿品》卷首版画三处,分别位于TK61、72、98《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文本开端。从宏观绘画结构来看,三者大致相同。TK61版画以一佛二菩萨为中心,展现出说法场景。空中有十方佛赴会、不鼓自鸣的天乐等细节体现。佛菩萨旁围绕着诸多听法众,有几处榜题如“十大弟子”“八金刚”等等。在版画左下角绘有一头小象,右下角绘一只狮子,以作为普贤居左、文殊居右的象征,构图十分巧妙;TK72版画顶端榜题“教主大毗卢遮那佛”,华严三圣居于画面正中,均坐于莲台上(图6)。主尊毗卢遮那佛左右上方为前来赴会的十方佛,身两侧为文殊与普贤,左下方立有威光太子,右下方立善财童子。画面左右为听法弟子、菩萨与天龙八部等等;TK98版画顶端有榜题“教主毗卢遮那佛”,画面中央为华严三圣,一佛二菩萨的布局(图7)。根据榜题,文殊居右,手中持如意;普贤居左,手中持梵夹。三圣周围依旧绘制大量菩萨、弟子、天人众等听法、护法者。其中,TK98版画绘制精美,在佛说法场景旁,还详细绘制有普贤行愿的情节画面(图8)。

图4 窟内女供养人画像

图5 窟内男供养人画像

图6 俄藏黑水城文献TK72版画

图7 俄藏黑水城文献TK98版画

图8 普贤行愿画局部

图9 正壁北侧局部
再将视角转向榆林窟第2窟内正壁,该壁文殊变两侧两铺说法图同版画布局差别不大,均以佛说法为中心,天人众与天龙八部等分布于四周,佛身前有合掌听法的僧人与菩萨。特别的是,两图中佛说法的正前方均有一身跪拜者直面佛身,在北铺图像里跪拜者旁边的两身人物还留有榜题框,这一点与TK72卷首版画完全相同。佛经版画中跪拜者左右人物有清晰的榜题标注,分别为“善财童子”与“威光太子”,第2窟正壁北铺图像榜题框中的字迹虽已漫漶,但从其在说法图中的位置以及跪拜者的出现来看,框中内容与版画应属一致。总的来看,这两铺壁画中的佛说法场景、龙天诸部、跪拜者直面于佛等等细部与黑水城《普贤行愿品》经文前印的毗卢遮那说法画面,尤其是TK72卷首之画几乎没有差别。因而,我们也基本可以确定正壁南、北侧壁画是依据西夏佛经版画为粉本制作的,其所表达的内容为毗卢遮那法会。
2.正壁两端条幅画
在正壁南、北法会图像的外侧,绘制有诸多小画面组成的条幅画,部分画面细节尚可观察,有佛菩萨形象、人物活动、楼台建筑等等,画面之间以不规则的曲线分隔。从图像位置上看,这些小画面是附属于两铺说法图的。而俄藏黑水城文献TK98卷首版画中除有毗卢遮那佛说法之外,还留有保存完好、细节翔实的故事画。除去已经漫漶部分,现北铺壁画外侧自上而下可辨识出三幅场景,现将其与版画中的内容进行比对:

图10 TK98行愿经变画局部
(1)正壁北侧自上而下第一部分,画面右部可见一佛趺坐于莲座之上,身旁伴有侍从(图9)。左下部一身较小的童子形象,正伏地向佛施礼。TK98行愿故事画中,榜题为“一礼敬诸佛”“二称赞如来”两场景均为佛趺坐莲台,童子于佛前礼拜(图10)。画面构图、主要人物等细节基本统一。
(2)正壁北侧自上而下第二部分(图11),可以看到,画面正中有一塔,塔左下方有俗装人物,右下方有僧侣数身,皆合掌礼敬。还有一人于塔正前方伏地跪拜,其身上所着衣物似乎为田相袈裟。TK98版画中,榜题为“随喜及般涅槃,分布舍利善根”的画面里有一佛塔,左右为僧人与世俗装人,正前方一身着袈裟僧人向塔跪拜(图12)。
(3)正壁北侧自上而下第三部分(图13),画面左侧有一身立佛,佛手伸出,侧身向前。一人向佛跪拜行礼,身后有两身鬼怪相貌人物。这一图像同TK98版画中题为“极重苦果,我甘代受”的情节相仿,该情节画面内容为在烈焰地狱门前,有一合掌礼拜的童子与两身鬼怪形人物(图14)。
正壁北侧条幅画余下画面漫漶严重,已无法判断其完整的构图。正壁南铺壁画外侧条幅画也仅有三处较清晰,尚可供比对:

图11 正壁北侧局部

图12 TK98行愿经变画局部

图13 正壁北侧局部

图14 行愿经变画局部

图15 正壁南侧局部

图16 正壁南侧局部

图17 TK98行愿经变画局部
(1)正壁南侧自上而下第一部分(图15),画面中有骑象普贤立于云气之上,在重峦叠嶂中穿行。此部分画面保存比较完好,普贤菩萨、白衣老人、佛陀波利等人物刻画细腻,远处的山峰以墨线勾勒,立体生动。行愿经版画中没有具体描绘普贤的形象,而壁画中则特地画出骑乘六牙白象而来的普贤菩萨,既强调了行愿主题,也同壁面中央的文殊形成呼应。另外,笔者以为此处普贤形象出现,当同五台山信仰有密切联系,将于下文叙述中提及。
(2)正壁南侧自上而下第二部分(图16),图中右侧可见佛并侍从数身,佛侧身向下俯视作宣讲法门之状,周边有云气环绕。佛身前有一身俗装长须男子形象,似在向佛祈请。左下部可见几身女性信众朝佛方向礼拜。俗装男子旁尚有人物,但漫漶不清,无法判断数量与细节。俗装信众礼佛听法、恭请佛身在TK98行愿版画“请佛住世”情节中有出现(图17)。
(3)正壁南侧自上而下第三部分唯有一高塔清晰可见,底座为六角形,塔旁有树木、植被等等。其余部分剥落严重,塔周边是否有礼拜人众不得而知。
经过比对不难发现,榆林窟第2窟正壁南、北两侧条幅画的画面内容与整体结构基本取材于“行愿经变相”版画中的具体情节。同时,绘画者将行愿图像与佛向众菩萨、天众说法场景结合,将其绘制于毗卢遮那法会之侧,这样的格局与TK98等卷首版画几无二致。另一方面,就敦煌地区悠久的壁画制作传统来看,以中央法会场面辅以小幅故事画的图像组合是一种经典绘画模式。总览各类大型经变画,无论是配置以“十六观”“未生怨”连环小图的观无量寿经变,还是出现有“一种七收”“树上生衣”场面的弥勒经变,大部分均遵循这一构图方式。同样,榆林窟第2窟正壁南、北两侧法会图像并条幅画也符合此类风格,以毗卢遮那说法为中心,绘普贤行愿故事细节于侧面,两者结合形成完备的经变画格局。综上,通过图像粉本对比、壁画所依托经典断定以及构图方式传承,笔者以为榆林窟第2窟南、北两侧毗卢遮那法会并行愿故事是西夏时期以佛经版画为粉本,根据《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可思议境界普贤行愿品》内容所创制的新题材经变画,应定名为“普贤行愿经变相”。
二、正壁图像组合的思想内核
在对壁画进行题材分析与定名后,我们可以发现,榆林窟第2窟正壁整体呈现出文殊与普贤相关内容的呼应。而在佛教造像中,常借助经典中的上首菩萨彰显主尊佛像身份,如以观世音和大势至界定阿弥陀佛、以日光和月光菩萨界定药师佛等等。[7]故该窟正壁以文殊、普贤二者成一真法界,凸显毗卢遮那佛尊格的意味不言而喻。华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极为久远,早在汉末,一些华严系经典已被高僧译出。而自唐代始,借助“三圣圆融思想”的诞生与完善,华严三圣成为佛教造像领域备受青睐的题材,留存数量也非常可观。三圣的标准组合为毗卢遮那佛居中,文殊、普贤对称分列主尊两侧。敦煌作为丝路佛教交流的咽喉枢纽,与华严三圣相关的造像必然为数不少。例如莫高窟盛唐第44窟内中心柱东向龛顶部绘有敦煌最早的华严经变;中唐时期敦煌石窟内的华严经变日趋精美、宏大,著名的莫高窟“阴嘉政窟”主室北壁便有大幅华严经变,画面中七处九会的榜题依旧清晰可见;莫高窟曹氏归义军第454窟中则将的华严经变绘制于窟顶北披。
华严理论体系的柱础便是唐代李通玄所阐释的三圣圆融之说,“文殊为法身妙慧,普贤为万行威德故,体用自在名之为佛”,[8]745此理论基于经典,将毗卢遮那佛、文殊、普贤三圣合为一体,更重要的是把文殊与普贤的地位大大提高,至与佛平齐。针对文殊、普贤两位上首菩萨,李通玄阐释了“文殊以理会行,普贤以行会理,二人体用相彻”[8]740的观点,认为在功能上两位菩萨异同不一,但实质上是不可分割的紧密组合。华严四祖澄观则进一步补充了“二圣法门既相融者,则普贤因满,离相绝言,没因果海,是名毗卢遮那”。[9]在这三圣当中,两位大菩萨为因,主尊为果,普贤代表所信法界、所起万行和所证法界,文殊代表能信之心、能起之解和能证大智。可以说,文殊普贤这对经典组合是以华严信仰为基本依据和绝对支持的,通过经典以及历代高僧大德的阐释、注疏,民众心目中“文殊主智,普贤主理,二圣合而为毗卢遮那”[10]的基本形象也随之确立起来。
华严三圣相关理论使人们对于菩萨的崇拜意识空前加强,文殊、普贤的结合即可等同于佛。[11]透过整个华严信仰体系,可以体会到文殊菩萨拥有无上法身妙慧,并具象成为般若智慧的代表;而普贤菩萨则是僧众们学法修行、力行实践的榜样,其同法身完美契合,直达法身之境。因华严经典中描述文殊菩萨为众菩萨之首,负责提出问题与讲述教义,具有代佛宣言的身份,法藏甚至认为,《华严经》乃是由“文殊所结”。[12]故在榆林窟第2窟内,我们可以看到文殊变居于正壁中央,并借助涅槃小图、参拜者等元素体现“文殊师利为法宝”的重要地位。而正壁南北两侧说法图,则以普贤行愿变相为点睛之笔,反映广大信众希望“修习普贤圆满行”的理念。二者在同一壁面上的契合,正是“二圣合而为毗卢遮那”的完美图像表达。
除此之外,榆林窟第2窟正壁图像也极有可能是西夏五台山信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上文已述,该壁同时出现有文殊变与普贤行愿变相。值得注意的是,中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第144窟、第361窟内均出现《文殊并万菩萨化现图》与《普贤并万菩萨化现图》的组合;莫高窟第237窟西壁还有《五台山图》与《普贤行愿图》的对应。这无疑反映出唐代时期的普贤化现以及行愿故事情节已经同文殊信仰与五台山图像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乃至被纳入五台山图像体系。有学者认为,第144窟主室西壁龛外南、北侧图中“善首菩萨来会”“净戒菩萨来会”榜题,表明二图展现的是文殊、普贤为众菩萨说法的法会,普贤下方“五台山”榜题亦说明法会地点,因此144窟二图实际可合为一图,即《五台山化现图》。[13]由此可见,以“文殊+普贤”为核心的相关题材组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五台山图的衍生图像。
从构图上看,榆林窟第2窟正壁中央的文殊像庄严神圣,绘制者将涅槃图置于文殊上方,并在下方添加参拜者形象,力图把文殊塑造为佛法的继承弘扬者与现实苦难的救度者。[4]25这同五台山图中数不胜数的神迹化现情节有异曲同工之妙,均着重凸显出文殊的神通广大与对信众现实利益的关注。同时,壁面南、北两端的普贤行愿故事画及其中乘象而来的普贤亦是五台山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前所述,普贤行愿早在唐代即同五台山图共同绘制,二者之间的联系渊源已久,而西夏时期普贤信仰与相关图像创作又有了新发展,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可以看出,《普贤行愿品》留存数量颇多,TK98卷首更是出现内容完备的行愿情节画。应给予重视的是,TK98卷中发愿文明确提及仁宗皇帝逝世于乾祐二十四年(1193)九月二十日,而此经典刊印于天庆二年(1195)九月二十日即仁宗两周年忌辰,是为纪念这一特殊日期所印。据学者统计,在仁宗及其皇后罗氏统治时期,《普贤行愿品》在皇室施经中占比极大,可称之为“西夏最流行的经”。[14]史料记载乾祐二十年西夏官方于大度民寺“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品》《观音经》各五万卷”。[15]由此可见,《普贤行愿品》于西夏社会流传之广。在这样的氛围之中,作为佛教修行实践及礼忏活动的主要引导者,普贤得到了包括西夏皇室在内各阶层信众的推崇。就佛教经典中内容看,以普贤行愿为中心的大乘菩萨修行体系贯穿了《华严经》,经书中所描述的普贤菩萨是一位集护持、传播大乘佛法并引导大乘信众成就佛果于一身的大菩萨,而华严信仰是西夏佛教中历史最悠久的传统信仰,且普贤仪轨在西夏非常流行。[16]因此榆林窟第2窟中出现普贤行愿图像是顺应此期西夏佛教信仰风潮的,并直观反映出西夏人重视佛教实践的特性。如此一来,在以五台山文殊为中心的壁面布局中,有计划的绘制普贤行愿相关内容并将其扩大化,既继承了自唐代沿袭下来的题材组合,又以普贤强大的实践色彩促进了五台山信仰对于信众修行过程中的帮助,既符合西夏人对于佛教的个性化理解,亦为这一时期的五台山信仰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图18 莫高窟第172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
三、榆林窟第2窟文殊造像功能分析
通过对榆林窟第2窟正壁图像的辨识和定名,我们可以直观看出,此壁面上的图像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即“尊像(文殊菩萨、普贤行愿变相中的佛菩萨等)加故事情节(文殊救八难、普贤行愿细节图)”的组合。这样的构图方式不仅是艺术创作,且从多方位满足了信众多样化的需要。经典前代案例如莫高窟第172窟,其主室南、北壁大铺观无量寿经变壁画采取“三分构图”(图18),将具有不同宗教含义的三种绘画模式融为一体,以尊像居于中心作为礼拜主体,一旁借助故事绘画阐释未生怨等经文内容,另一旁所绘的王后韦提希“十六观”则可作为“观想”礼仪的视觉向导,尊像与两旁场景的艺术表现有着显著差异,故运用不同的视觉逻辑以服务于不同的宗教功能。[17]前文已述,榆林窟第2窟正壁文殊同该壁面其他题材结合,一定程度上是五台山图的再现,以礼拜者视角来看,文殊圣像被绘制于正壁中央这一特殊位置,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方位相同,因此也具有神圣导引图像的特征:不仅有助于观想修行,还可以通过图像的视觉导向,逐步带领信众进入到清凉圣境。[18]而文殊图像两侧的普贤行愿变相尤其是条幅故事画则增添了实践色彩,常在法事活动中以忏悔主身份出现的普贤菩萨在这里依旧能够承担引领礼拜者诚心发愿、完成忏仪的角色。整壁图像既在义理上相辅相成,又贴合实际信仰需求,是服务于信众观想主尊、礼敬神佛乃至践行佛教仪轨的完美融合。
同时,营建者在榆林窟2窟形制的架构上也别具匠心,中心佛坛文殊塑像与正壁文殊变的对应,形成了一条中轴线,进一步强化了窟室的空间主题。榆林窟第2窟中心佛坛现存塑像为清代重修作品,针对敦煌西夏石窟中大量的清修塑像,李志军博士曾对此系统梳理并总结出清修塑像的几种模式,提出敦煌西夏重修洞窟中所谓清修塑像或是在原作塑像上重新彩绘、修复细节,或是按照原有题材尽可能复制原塑内容。①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梳理见陕西师范大学李志军博士《末法选择与神系重构——莫高窟第353窟西夏重修新样三世佛的思想内涵》一文,原文待刊。因此文殊及随从眷属的组合应是榆林窟第2窟佛坛造像的原有配置。自晚唐以来,瓜沙地区兴建中心佛坛窟的风气日盛。如莫高窟第61、98、100窟、榆林窟第31窟等由归义军官僚世族主持下完成的诸多大窟。到西夏时期,作为西平监军司驻地的瓜州又迎来一波修窟热潮,榆林窟第2、3、4、29窟等艺术水准极高的窟室均设有中心佛坛(图19)。这些洞窟的诞生一方面是贵族阶级显示雄厚财力与地位的手段,具有一定世俗意义,同时也是设坛作法、践行信仰的宝殿。[19]历史记载表明,西夏很早就已盛行“菩萨—道场”模式的文殊信仰。[20]就榆林窟第2窟来看,佛坛上群组塑像的设置不仅再次宣示了文殊统摄全窟的尊格,其作为圣像崇拜的载体也更加便于供养活动与佛教仪式举行,仿佛文殊师利真身降临于此,为入窟者消除恶业,助其修行精进,未来得以往生净土。在佛教语境中,“示现”是信众在特殊情形下直接接触佛菩萨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佛教传播策略中比较重要且行之有效的方式。[21]因此,“文殊图像——文殊塑像”的中轴线无疑拉近了主尊与信众的距离,“文殊菩萨五台山,遍化神通在世间”,[22]入窟者即得见文殊并受其护佑。在此氛围之下,信众开始诚心发愿,礼佛赞叹,依照自身的需求逐步完成不同类型的佛教实践仪式。
四、佛王传统与武官开窟——榆林窟第2窟营建背景讨论
作为少有的以文殊图像居于正壁中央的洞窟,榆林窟第2窟着力彰显文殊及五台山主题的意图已不言而喻。敦煌地区源远流长的文殊信仰使得僧俗各界对于参拜圣地五台山有着极为强烈的热忱。受制于遥远路途及频繁战乱等各种因素,仅有少数人能够真正抵达五台山,因此无法亲自前往的敦煌人只得于本地营建属于自己的朝圣地,莫高窟“文殊堂”——第61窟即是明证。而西夏时期,其疆域内文殊信仰依旧极为盛行,且统治者对于文殊的崇拜更是抵达一座新高峰。西夏自立国之初便是极为崇佛的政权,统治者以佛王身份推行对国家的统治。曾参与大量译经活动的高僧拶也阿难捺在《入中论颂注疏》藏译本中谈到,西夏法王世系延续不断,历代西夏皇帝都为法王或转轮王。[23]92更为重要的是,《夏圣根赞歌》记载,李继迁身有“十种吉祥皆主集,七乘伴导来为帝”[24]等多种祥瑞,十种吉祥正是文殊菩萨出生时的吉兆,《赞歌》中的内容显然是暗喻李继迁为文殊菩萨下生。[23]93古正美先生依据《华严经·入法界品》中“尔时,智慧转轮王者,岂异人乎?文殊师利童子是也;绍继转轮王姓,诸如来种,使不断绝”的内容,认为,《华严经·入法界品》视文殊菩萨等佛教神祇与转轮王同身,所谓佛王信仰,就是佛教转轮王能以佛或菩萨的面貌治世的信仰,因此一位帝王也能以文殊等神祇的面貌统治天下。[25]李继迁的后继者元昊更是与文殊有着密切联系,明代朱旃所撰《宁夏志》载:

图19 榆林窟第4窟中心佛坛(现存坛上造像为清代重修)
文殊殿,在贺兰山中二十余里,闻之老僧。相传元昊僭居此土之时,梦文殊菩萨乘狮子现于山中,因见殿宇,绘塑其像,画工屡为之,皆莫能得其仿佛……忽见一老者鬓皤然,径至殿中,聚诸彩色于一器中泼之,壁间金碧辉焕,俨然文殊乘狮子相。元昊睹之甚喜,恭敬作礼,真梦中所见之相也。于是,人皆崇敬。[26]
透过这些的记载能够发现,西夏帝王在推行统治过程中善于运用佛教力量,且常常借助文殊菩萨的神圣身份加强王权。与此同时,榆林窟第2窟作为西夏高水平佛教艺术的代表性洞窟,以文殊造像为中心,构建出一座五台山信仰色彩极为浓厚的圣殿,可称之为西夏人自主营建的“文殊堂”,那么此窟的落成是否同西夏统治阶级乃至王权相关呢?笔者注意到,在榆林窟第2窟西壁门两侧下部,尚留有西夏供养人画像。由于题记漫漶较为严重,现无法对该窟功德主的具体身份、官阶等信息进行辨识,但据残存图像来看,绘于西壁门北下部的男供养人皆头戴黑色冠帽并穿窄袖长衫、腰系腰袱(图20、21),其衣着冠饰与同属西夏晚期窟室的榆林窟第29窟、东千佛洞第2窟内的武官供养人极为相似(图22、23),这无疑为我们探究榆林窟第2窟的营建背景提供了绝佳的参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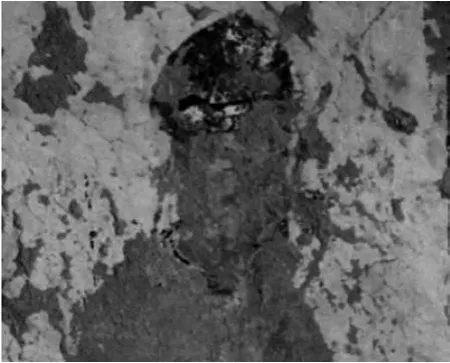
图20 榆林窟第2窟男供养人冠帽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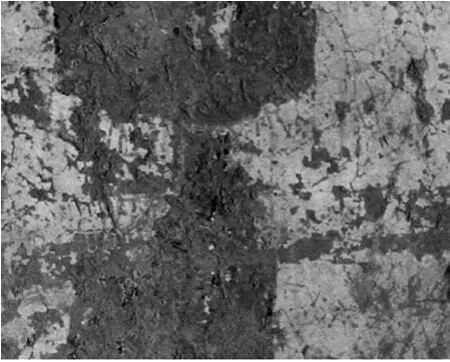
图21 榆林窟第2窟男供养人服饰细部

图22 榆林窟第29窟武官供养人

图23 东千佛洞第2窟武官供养人
由供养人题记可知,榆林窟第29窟是由“沙州监军摄受”赵麻玉、“瓜州监军司通判纳命”赵祖玉等瓜、沙武官资助修建的,东千佛洞第2窟功德主则身居“边检校”职位,属于边地中级武官。据史料载,西夏官员“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涂银束带,垂蹀躞”。[27]透过文本与史料的对应,可以发现,榆林窟第29窟赵氏家族的衣着基本还原了西夏武官服饰风貌。而借助黑色装饰冠帽、两侧腰袱等细节的辨识,可以确定榆林窟第2窟供养人身份与29窟功德主相近,其官阶或许低于赵氏家族,但同属于镇守边地的武官群体这一点应该无疑,因此榆林窟第2窟的营建必然同官方信仰状况产生息息相关的联系,这也顺应了自晚唐以来瓜沙大族利用中心佛坛窟标榜身份品阶的风气。再结合西夏历代帝王极力强调文殊崇高地位,借文殊神格巩固统治的政治传统,笔者认为,榆林窟第2窟应是地方官员在皇室的授意与支持下,结合五台山文殊信仰以及西夏佛王治世传统而修建的瓜州文殊堂。此窟的落成既能够满足瓜州信众渴望参拜五台山的宗教需求,也意图向统治者展示自身的忠诚与服从。
在历史上,西夏皇室也确实对榆林窟这一佛教圣地非常重视。榆林窟第15窟内现留有题记:“南方阇普梅那番天子戒国□、大臣,睹菩萨□山,当为修福”,陈炳应先生认为,“阇普梅那国番天子”即是西夏皇帝,此题记说明最高统治者极为看重莫高、榆林二窟,指示臣下为之修福。[28]经由现存题记内容可知,榆林窟第29窟为瓜、沙赵氏武官家族所资助修建的功德窟,且郑重其事的将真义国师鲜卑智海绘在诸功德主前(图24)。从绘制位置上看,官居功德司司正的鲜卑智海像位于窟门旁重要位置,在该窟中的地位比实际功德主赵麻玉家族更高,表现出建窟者对于国师的无限尊崇。据前辈学者研究,在举办法事之时,西夏皇室常常延请著名高僧来主持印经、施经、行道等活动,唯有地位至高无上的皇室可请国师,其余高官宰辅只得延请法师、禅师,并无邀请国师的资格。[29]故鲜卑智海的出现为榆林窟第29窟营建活动添加了浓重的王家色彩,此窟之完成或许与皇室重大事件相关。[30]从这一例证不难看出,西夏皇室对榆林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有学者还认为,崇佛的仁宗皇帝甚至有可能亲临榆林窟。[31]而通过观察榆林窟第2窟的壁画粉本——西夏佛经版画,笔者还发现一处重要细节:在俄藏TK98版画的佛会场景中,出现有两身十分特殊的人物,一身为头戴冕旒的男性形象,其身后则有一女子,应为贵族女性身份(图25),两人跟随于善财童子身后合掌向佛礼拜。不同于戴通天冠的帝释、梵天等天众,此身男子能够在童子的引领下直接礼佛,已然凸显出与众不同的地位,而得以穿戴冕旒,毫无疑问是帝王的专属特权。在敦煌壁画中,我们也看到许多头顶冕旒的王者形象,如维摩诘经变中前来闻法的中原皇帝,莫高窟第98窟中有明确身份榜题的“大圣大明天子”于阗王李圣天(图26)等等,可见,华服冕旒的配置是壁画中用以表现世俗帝王的经典图像符号。应当重视的是,作为榆林窟第2窟普贤行愿变相的图像粉本与依托经典,TK98版画并后续经文是为纪念夏仁宗逝世而大规模刊印的,且画面中直接添加了帝王礼佛细节,因此其流行、传播与应用显然带有强烈政治意义,以如此特殊的题材作为石窟营建的粉本,榆林窟第2窟必然符合西夏皇室所主导的信仰思潮,顺应了西夏佛教发展的官方趋势,是完全遵循着上层统治阶级信仰的佛教石窟作品。
五、结语
通过对窟内正壁图像进行新的辨识,可以发现,榆林窟第2窟在营建时大量运用了西夏佛经版画的内容,并以之为粉本绘制出颇具创意的普贤行愿经变相。此题材同文殊变结合,成为西夏五台山图一种新的表现方式,也丰富了此期文殊及五台山信仰。基于正壁文殊图像对应佛坛塑像所形成的窟室中轴,再考虑到洞窟供养人同榆林窟第29窟功德主身份的相似性、榆林窟整体受到皇家重视以及第2窟壁画粉本中帝王因素等多方面背景,笔者认为榆林窟第2窟的落成不仅可作“文殊堂”服务于本地信众朝圣瞻仰、礼佛发愿等宗教活动,亦呼应了西夏代代相承的“帝王即佛王”观念,其修建活动蕴含有浓重皇室色彩,具有重要政治意义。
经过几代帝王的大力支持与各阶层信众的虔诚笃信,西夏佛教逐渐迎来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其石窟营建理念渐趋成熟、造像水平日益精进,榆林窟第2窟便是西夏佛教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的现实反映。透过此窟案例研究,我们能感受到敦煌西夏石窟营建过程中的思想之深与包容之美,这是一片佛教实践的沃土,亦为西北原野上的艺术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