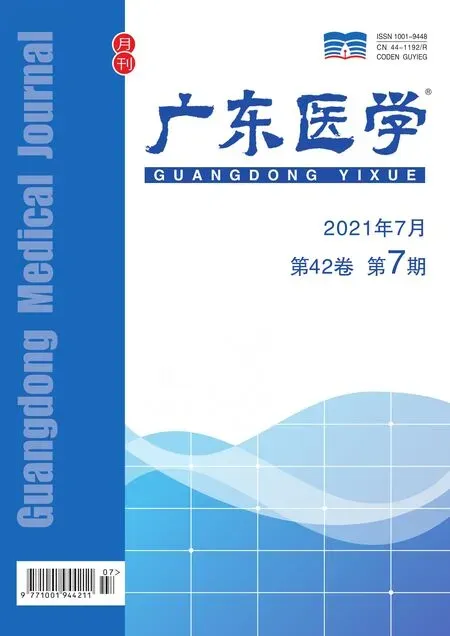CYP3A4和CYP2D6基因多态性对阿片类药物术后镇痛效应影响的研究进展
陈佳慧,赵雷
1暨南大学第二临床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2深圳市人民医院麻醉科(广东深圳 518020)
术后疼痛是一种强烈的急性疼痛,是影响患者术后康复的重要因素之一。有效的术后镇痛可以加快患者术后康复,是当今精准医疗时代下实现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的关键环节之一[1-2]。阿片类药物是目前常用的镇痛药物之一,然而,这类药物用于缓解术后疼痛呈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导致镇痛效果不佳及阿片类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增加[3]。因此,如何个体化应用阿片类药物,给“正确的患者”以“正确的剂量”提供“正确的药物”,以加强镇痛效果,减少阿片类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是精准医疗时代的一个主要目标。国内外多个研究发现,基因多态性是影响阿片类药物术后镇痛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4]。常用的镇痛药物有吗啡、羟考酮、芬太尼、舒芬太尼、曲马多和可待因等。细胞色素P450(CYP)是体内参与药物生物转化的主要酶系,在某些内源性、外源性物质代谢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6],CYP3A4和CYP2D6作为CYP450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对多种镇痛药的代谢有关键性作用,CYP3A4和CYP2D6基因多态性影响阿片类镇痛药物的代谢速率和活性药物的血药浓度而影响其镇痛效果甚至毒副作用,本文就CYP3A4、CYP2D6基因多态性对常用阿片类药物术后镇痛效应的影响进行综述。
1 CYP3A4的基因多态性及其对芬太尼、舒芬太尼的影响
CYP3A4是CYP的亚型之一,是参与药物代谢的单加氧酶超家族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7],负责目前处方药物中60%的代谢[8]。然而,CYP3A4蛋白在肝脏中的表达差异可达40倍,引起药物代谢的变化,并导致个体对药物的反应差异。研究表明,CYP3A4蛋白活性中约90%的个体间变异性主要归因于遗传因素,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是CYP3A4最常见的遗传变异形式[9]。CYP3A4基因位于第7号染色体长臂2区1带1亚带至2区2带1亚带,包括13个外显子及12个内含子,CYP3A4 基因已被证实有40个等位基因[10]。
Fukushima-Uesaka等[11]发现CYP3A4*1G是现在CYP3A4 SNP中突变频率较高的一个位点。目前研究发现CYP3A4*1G(20230G>A)是亚洲人的高频等位基因,其突变在中国汉族人群中的频率为18.8%~22.7%[12],是中国汉族人群中CYP3A4的最高SNP。CYP3A4*1G等位基因在第10号外显子中具有同义的G-A突变,是影响CYP3A4活性及蛋白的表达和CYP3A4代谢药物的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13],因此CYP3A4*1G基因多样性对于预测药物血浆水平和患者对治疗的反应是至关重要的。
芬太尼和舒芬太尼代谢途径相一致,都是由肝脏CYP3A4酶N-脱烷基化代谢而失去药理作用[14]。因此,CYP3A4酶作为芬太尼及舒芬太尼的重要代谢酶之一,其酶活性的变化将影响芬太尼及舒芬太尼的血药浓度,从而影响药物的镇痛效能。
1.1 芬太尼 Kharasch等[15]发现肝CYP3A4活性的改变与芬太尼的代谢、消除和作用持续时间有显著相关性,而芬太尼主要在肝脏中被CYP3A4代谢为几乎没有活性的去甲芬太尼[16]。因此,当肝脏CYP3A4酶活性增强时,芬太尼在体内代谢速度增快,导致其更快地失去药理活性,镇痛效能降低,从而导致个体需求量增加才能满足镇痛效果。由于CYP3A4*1G基因多样性引起个体肝CYP3A4酶活性的差异,芬太尼用于疼痛控制的有效剂量也因个体而异。有研究表明,腹部手术患者平均每小时芬太尼剂量有5倍的个体差异[17]。学者Yuan等[18]通过测定人肝微粒体中芬太尼浓度,发现肝微粒体中芬太尼代谢速率与CYP3A4 mRNA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而不同CYP3A4*1G变异等位基因CYP3A4 mRNA差异显著,携带突变型纯合基因*1G/*1G的患者其芬太尼的代谢率显著低于携带野生型等位基因和突变型杂合基因*1/*1G者。Zhang等[19]对143例妇科手术后行芬太尼静脉自控镇痛患者进行了PCA治疗期间休息时的疼痛程度评估及CYP3A4酶的活性测定,发现突变型纯合基因*1G/*1G的CYP3A4酶的活性显著低于野生型等位基因*1/*1和突变型杂合基因*1/*1G,并且CYP3A4*1G/*1G基因型患者用于控制术后24 h疼痛的芬太尼需求量更少,可见CYP3A4*1G基因多态性降低CYP3A4酶活性和芬太尼用于控制术后疼痛的用量。CYP3A4*1G基因多态性对中国受试者术后芬太尼的用量具有明显的相关性[20],但是否可以作为芬太尼的个体需求量预测因子之一,仍需要更多大样本的研究证实。
1.2 舒芬太尼 舒芬太尼在肝内被生物转化代谢形成N-去烃基和O-去甲基的代谢物,与芬太尼不同的是,舒芬太尼代谢物去甲舒芬太尼仍有药理活性,效价约为舒芬太尼的1/10,与芬太尼相当,因此舒芬太尼的镇痛效果和持续时间都大大优于芬太尼。但CYP3A4酶作为舒芬太尼的肝代谢酶,其基因多态性对舒芬太尼个体镇痛用量仍有一定的相关性。Zhang等[12]对191例行肺切除术的汉族患者比较了术中全麻舒芬太尼用量,发现CYP3A4*1G/*1G基因型患者对舒芬太尼的需求明显较少,并且这种差异与性别无关。有学者[21]根据CYP3A4*1G不同基因分型比较了143例剖宫产产妇术后每个时间点(0、8、24和48 h)舒芬太尼的消耗量,发现CYP3A4*1G/*1G组在手术后8、24和48 h内与其他两组相比,舒芬太尼的消耗显著降低。关于CYP3A4*1G基因多态性对舒芬太尼镇痛的影响研究尚少,CYP3A4*1G基因分型是否有助于为舒芬太尼的使用提供指导,需要大量大规模的研究以验证。
2 CYP2D6基因多态性及其对可待因、曲马多和羟考酮的影响
CYP2D6是CYP450家族中的重要成员,主要分布在肝脏、小肠和脑组织中。CYP2D6虽然仅占肝脏CYP450酶蛋白总量的4%,但可代谢约30%临床常用药物[22]。可待因、曲马多等常用阿片类镇痛药都是作为前体药物通过CYP2D6酶脱甲基化成活性代谢物才具有药理作用,其活性代谢物比母体药物具有更强的μ受体亲和力[23-24],羟考酮虽然本身具有药理活性,但其经CYP2D6酶代谢后产生的活性代谢物镇痛效果更强。因此CYP2D6酶活性对这些阿片类药物发挥临床疗效具有关键性作用,而CYP2D6基因多态性对酶的活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影响药物对不同个体的疗效及不良反应。
在CYP2D6基因中已经发现了80多个基因多态性,不同CYP2D6等位基因的组合可导致一系列的CYP2D6活性,产生不同的代谢型,通常分为4个不同的活性范围,称为表型[25]:超快代谢型(ultrarapid metabolizer,UM)、强代谢型(extensive metabolizer,EM)、中代谢型(intermediate metabolizer,IM)和弱代谢型(poor metabolizer,PM)。基因用药指导相关指南[26]指出弱代谢型患者其CYP2D6酶完全没有功能或其体内不存在CYP2D6酶;中代谢型的CYP2D6酶功能有限;强代谢型具有全活性酶功能,因为其CYP2D6酶具有两个功能基因拷贝;超快代谢型CYP2D6酶活性升高,这是由于功能基因拷贝数量的增加导致CYP2D6酶蛋白数量的增加(即大于2个CYP2D6的功能拷贝)。不同种族中代谢型比例不同,其中,东亚人群中超速代谢型的比例为1.4%,弱代谢型的比例为0.4%[27]。CYP2D6存在三类等位基因:正常功能等位基因(主要是CYP2D6*1、*2和*35)、功能减退等位基因(主要是CYP2D6*9、*10、*17、*29和*41)和非功能等位基因(主要是CYP2D6*3、*4、*5、*6、*7、*8、*11和*15)[28]。据报道,CYP2D6*10(100C>T)是亚洲人最常见的功能改变,是东亚人酶活性降低的主要变异等位基因,在中国人中变异频率为56.2%,日本人中变异频率为38.8%[29-30]。CYP2D6*10有一个重要的序列变异,外显子1(100C>T)发生单核苷酸改变,导致Pro34Ser氨基酸取代,从而产生代谢活性较低的不稳定酶[31]。
2.1 可待因 可待因是一种有效的镇痛药,广泛用于治疗咳嗽和各种类型的疼痛[32]。可待因在肝脏中通过葡萄糖醛酸化代谢,主要是由UGT2B7酶转化为可待因-葡萄糖醛酸结合物C6G(60%~80%),由CYP3A4酶通过N-脱甲基转化为去甲可待因(2%~10%),是可待因体内代谢的主要途径(超过80%)。可待因另一条次要代谢途径是由CYP2D6酶通过O-脱甲基转化为吗啡(0.5%~10%),吗啡进一步代谢为吗啡-3-葡萄糖醛酸结合物(M3G)和吗啡-6-葡萄糖醛酸结合物(M6G),吗啡和M6G具有阿片活性,是可待因产生镇痛、止咳作用的基本方式[9]。可待因作为前体药物,本身不具有药理活性,必须由CYP2D6酶进行O-脱甲基转化生成具有阿片活性的吗啡和M6G才能发挥疗效。由此可见,CYP2D6酶活性的大小是影响可待因疗效和不良反应的关键因素,可待因的镇痛效果与CYP2D6基因多样性密切相关。CYP2D6酶活性增强时(如UM),可待因O-脱甲基化作用增强,血清中吗啡和M6G浓度增加,可能引起镇痛效果增强,甚至毒性增加危及生命;相反,PM中由于CYP2D6酶活性减弱甚至失活,可待因转化为吗啡和M6G的量微乎其微,因而PMs中可待因镇痛效果不佳[9]。Wu等[33]探讨了CYP2D6*10等位基因对血浆可待因及其代谢物吗啡、M6G和M3G浓度的影响,发现CYP2D6*10等位基因在口服可待因的O-去甲基化代谢产物的药代动力学中起重要作用,CYP2D6*10等位基因显著降低吗啡、M3G和M6G水平,但不降低可待因水平。而在UM中,其可待因O-去甲基化代谢物的浓度比PM高45倍[34]。
Kirchheiner等[35]通过研究发现与CYP2D6 EM 相比,CYP2D6 UM 患者可产生50%~75%的吗啡,CYP2D6基因重复引起可待因超速代谢,导致吗啡暴露量是EM 的1.5倍。多个病例报告[36-37]详细报道了在UM中使用标准剂量可待因后发生的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药物不良反应。具有CYP2D6 UM表型的儿童更容易出现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和呼吸暂停[37],Lauren等[38]报道了3例儿童扁桃体术后使用正常剂量可待因镇痛后死亡的病例,事后发现这些儿童均是UM表型,这些儿童CYP2D6酶活性活跃,导致可待因超速代谢、血清中吗啡增加,导致呼吸停止。另外,具有UM表型的哺乳期妇女服用可待因后,血清吗啡浓度增高而导致母乳存在高含量的吗啡,曾有报道婴儿死亡的病例[39]。相关临床指南[26]建议,CYP2D6 PM个体不应接受可待因来缓解疼痛,而不需要CYP2D6激活的镇痛药如吗啡是合适的选择;同样,CYP2D6 UM个体也应避免使用可待因来缓解疼痛,而使用不产生CYP2D6强效代谢物的止痛药作为替代药物。
2.2 曲马多 曲马多是一种合成的中枢作用的镇痛药,其疗效低于吗啡。曲马多和可待因一样,其代谢依赖于CYP2D6酶,曲马多经CYP2D6酶主要代谢为两种代谢物:N-去甲基曲马多和O-去甲基曲马多(M1),其中只有后者具有药理活性,且具有较强的镇痛作用[23,40]。
Dong等[41]评估了不同的CYP2D6*10基因型对汉族肾切除术患者曲马多术后镇痛的影响,发现CYP2D6*10/*10组在2、4 h时曲马多用量均显著高于CYP2D6*1/*1或CYP2D6*1/*10组。Li等[42]比较了CYP2D6*2和CYP2D6*10两种不同的基因型组合与曲马多药代动力学的关系,发现CYP2D6*10基因携带者曲马多清除率显著降低,而CYP2D6*2基因携带者中曲马多的主要药动学参数和其代谢产物M1与野生型CYP2D6*1/*1相比没有明显差异。最近一项研究CYP2D6*10C188T多态性与曲马多的药代动力学和临床结果相关性的荟萃分析表明,CYP2D6*10C188T多态性对曲马多的药代动力学和镇痛效果有显著影响,即CYP2D6*10C188T突变者曲马多血清半衰期延长且清除率减慢,其镇痛作用减弱,需要更高的曲马多消耗量以达到相同的镇痛效果[43]。
CYP2D6基因多态性与曲马多的不良反应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Arafa等[44]根据CYP2D6的基因多态性对60例接受长期曲马多治疗门诊患者进行研究,发现EM和UM长期暴露于曲马多可导致肝毒性的发生,这可能是由于EM和UM增强了曲马多生物活性代谢物M1的积累并因此增加氧化应激。可见,临床上识别CYP2D6代谢表型有利于曲马多个体化指导用药,为患者提供良好的镇痛效果的同时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2.3 羟考酮 羟考酮是一种强效的半合成类阿片激动剂镇痛药,其对μ-阿片受体的亲和力低于吗啡受体[45],但研究发现羟考酮比吗啡的镇痛功效更强[46]。羟考酮在肝脏通过4种途径进行代谢:N-去甲基化、O-去甲基化、6-酮还原和葡萄糖醛酸结合[47]。通过CYP3A4酶进行N-去甲基化为去甲羟考酮是羟考酮的主要代谢途径(80%),但其镇痛作用很弱;CYP2D6酶催化羟考酮O-去甲基化为羟吗啡酮(11%)[47],羟吗啡酮具有镇痛作用且其镇痛效力是羟考酮的14倍[48],但其血药浓度低。羟考酮通过CYP2D6酶对羟吗啡酮的代谢促进了羟考酮的镇痛作用,但并不是其主要作用的原因[48]。CYP2D6酶和CYP3A4酶活性的调节对羟考酮的药效学有明显影响,且这些依赖于CYP2D6基因多态性,PM组的羟吗啡酮最大浓度明显低于UM组及EM组,其药物效能也较其他组低[49]。关于CYP3A4和CYP2D6介导的羟考酮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作用的重要性的研究尚少,需要更多研究探究基因多样性影响羟考酮疗效中的地位。
3 总结
综上所述,CYP3A4和CYP2D6酶活性是影响阿片类镇痛药物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的重要因素,CYP3A4和CYP2D6的基因多态性产生了不同代谢表型,是导致阿片类镇痛药疗效产生个体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基因多态性与种族相关,CYP3A4*1G和CYP2D6*10是中国人群中的高频等位基因[29-30]。CYP3A4*1G基因多态性主要影响芬太尼及舒芬太尼的镇痛用量,携带CYP3A4*1G基因的人群的芬太尼及舒芬太尼用量减少;CYP2D6*10的基因多态性主要与可待因、曲马多及羟考酮的用量及镇痛效果相关,携带CYP2D6*10基因的人群CYP2D6酶活性下降,对可待因、曲马多及羟考酮的需求量增加且镇痛效果不佳,并且这种影响可能与等位基因的数量呈正相关[35]。
在精准医疗时代,基因多态性指导下的麻醉镇痛可以将镇痛方案个体化,减少患者因镇痛不足导致的生理应激及心理消极等负作用,加快术后康复,实现术后快速康复目标。基于基因多态性的麻醉镇痛最大的益处体现在PM和UM中。对于PM,可以预见性地避免使用其代谢不良的药物,选择其他合适的镇痛药,从而满足个体镇痛需求,加快康复;对于UM,同样地,要避免使用其超速代谢的药物,防止因代谢过速引起的危及生命的不良反应,选择其他代谢途径的镇痛药物,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满足个体镇痛需求。
然而,目前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基因多态性可以明确地进行镇痛药物指导,目前关于CYP3A4和CYP2D6基因多态性与镇痛药物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且样本量不足,同时许多临床结果不相一致。此外,除了文中提到的CYP3A4和CYP2D6,细胞色素P450家族中CYP3A5及CYP2C19也参与了阿片类药物的代谢过程,但相关的文献报道较少。未来的研究应扩大样本量,大规模、前瞻性地探索基因多态性对术后镇痛用药的指导意义。此外,更多的研究应该注重联合多种基因多样性对镇痛药物的影响,进行更大样本量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