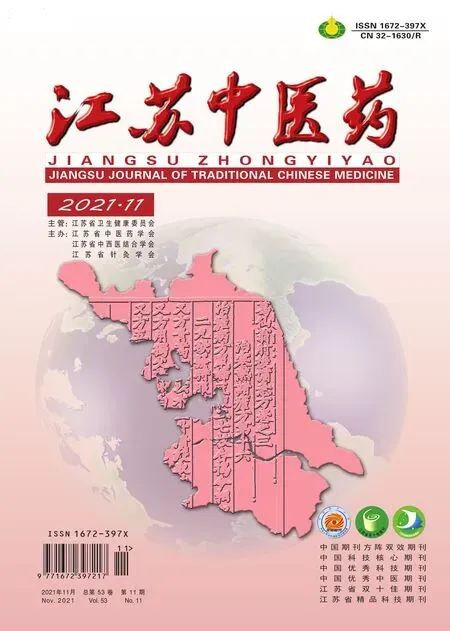《普济方·水病门》证治探析
姚佳音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上海 201203)
明代《普济方》[1]海纳百川,集15世纪以前方书之大成,同时兼收了传记、杂说、道藏、佛书中的相关内容,载方六万余首,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普济方》中的《水病门》篇涵盖了多种与水肿相关的病证,除风水、皮水、石水外,还有十水、涌水、水癥、水气、水饮、诸肿、湿肿、卒浮肿、膜外气、水蛊、蛊病等。此外还罗列了许多与水病相关的症状,如心腹鼓胀、脚膝浮肿、大腹水肿、遍身肿满、胸满气急、咳逆上气、小便涩等,并分别载方。笔者将《普济方·水病门》中的医论与方药进行了梳理,对其特点作如下归纳。
1 治疗原则
1.1 祛邪为先,汗下并举 《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2]168指出:“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脉沉绝者,有水,可下之”,乃水气病的治标之法。水病采用发汗、利小便、攻下逐水等法可快速去除体内水气,即《黄帝内经》中“开鬼门”“洁净府”“去宛陈莝”。《金匮要略》所列治水诸方,或以麻黄剂开腠理,或以防己剂利下窍,偏于一端。《普济方·水病门》则多汗下并举:常以麻黄、羌活、细辛、葱白等辛温发汗,茯苓、泽泻、木通、椒目、猪苓、滑石等利水渗湿,甘遂、牵牛子、大戟、芫花、巴豆、商陆等峻下逐水。或发汗配以利水,或利水佐以攻逐,或汗法辅以下法,双管齐下。水肿较甚的病证,还会将发汗、利小便、攻下逐水三法合用,以去除水邪为要。方如“风水”部分所用方大豆散,治“风气通身大肿,眼合不得闭”[1]2582,即以辛温之麻黄、防风,渗利之防己、泽泻,峻下之甘遂,配以大豆、乌头等药而成。又如“卒浮肿”部分之甘遂麻黄散,治“卒身面目肿,喘急气卒,大小便涩”[1]2620,以甘遂、麻黄、桑白皮三味,汗下并举,表里分消,给邪以出路。
1.2 以利为度,时时护正 《普济方·水病门·总论》[1]2552云:“证虽可下,又当推其重轻,不可过用芫花、大戟、甘遂猛烈之剂,一发不收,吾恐峻决者易,固闭者难,水气复来,而无以治之也。”罗知悌在《卫生宝鉴·胃气为本》[3]中也强调:“人知服牵牛、大黄,为一时之快,不知其为终身之害也。”汗下之后水肿得消,《水病门》中多谓之“取转”。治标虽能逞一时之快,然汗下不当,往往后患无穷。攻逐之后,大小便情况是最为重要的提示,小便利、大小便利或大便微溏均为停药指征,《普济方》中曰“以利为度”或“以知为度”。给予患者峻猛之剂可采用少量频服或逐量递增的方法,可防攻逐太过。方如麻黄煎“煮取六升,分六七服。一日一夜合尽,当小便极利为度”[1]2583,又如槟榔丸“每服米饮下十丸,日三,稍加至十五丸,未知,加至二十五丸,得小便利为度”[1]2553。《普济方·水病门·水气》[1]2597曰:“大凡治水,只可徐徐轻取,不要暴使过峻之药,以残伐人之肾气。”证情所需,用药须峻,少量频服,逐量递增,以知为度,徐徐轻取,则攻不伤正。
1.3 攻补兼施,正邪兼顾 治标可一时解决水肿的问题,然“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标本同治,方能绝水气之源。因此,于峻药中配入黄芪、附子、干姜等药物,可达攻补兼施之效。如“水肿胸满气急”部分的黄芪丸,在大戟、甘遂中加入益气之黄芪,和胃消食之神曲、麦(即麦芽),祛邪而不伤正。又如“水气遍身肿满”部分的大戟散,以大戟配干姜,辛热之干姜可缓和大戟寒凉之性,又可防其利下无度之弊。此外,峻药中加入食疗之品如鲤鱼、牛羊肉等,亦可使水邪去而正不伤,奏补泻兼施之功。如商陆根与羊肉同煮可治“卒肿身面皆洪大”[1]2621,且肿瘥后亦可食之。
1.4 调补善后,以人为本 峻药之后,正气受损。因此《水病门》在一些峻下的方药之后,会紧跟一两剂平和调补的方剂,称之为“补药”或“补方”。如服桃红散(含甘遂)后需以温通之平胃散(附子、白术、丁香)调补,又如“心内受水气,吃药取转”[1]2599后需服远志散(人参、远志、藿香、肉豆蔻、川芎)以补之。从这些“补方”来看,用药多为温中行气之品,如补药方(肉桂、青皮、干姜、莪术等)、荜茇汤(荜茇、荜澄茄、红豆蔻等)、四君子汤、胃苓汤等,总以温通行散、调整胃气为要。许多方后还需用米饮或粥饮调下,保护胃气,生津滋液。即使不用米粥调服,药后也常需食糜粥自养,以助正气恢复,缓解副作用。体虚者还需加用温补下元之品,如鹿茸丸(鹿茸、肉苁蓉、干地黄、菟丝子等)可治“水气已愈,体瘦”[1]2592,又如复元丹(附子、茴香、吴茱萸、槟榔等)可“助真火,以养真土,运动枢机”[1]2553。
“水肿”部分还记载有先用第一退水丸(莪术、三棱、桂心、青皮、益智仁、巴豆)温通为主,仅一味巴豆逐水退肿;服药未效,改用第二退水饼(甘遂、大戟),直接攻逐水饮;服后水肿得退,再用第三大腹子散(大腹子、桂心、茴香、陈皮),温中行气、调整胃气。方药进退之间,体现了医家以人为本,时时护正的思想。
攻逐是消除水肿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像西医使用各种利尿剂,看似效捷,但简单粗暴,后患无穷。利尿剂的使用会导致电解质紊乱、肝肾功能损伤,肿退之后,还会再次复发。因此,逐水虽然简单,但水退之后的善后更为重要。瘥后大体有两种情况:一为胃气受损,需以温中行气之品如木香、陈皮等,使胃气得复;二为正气虚弱,下元不足,需用补益之品如牛羊肉、鹿茸等,使元气得充。
2 方药特色
2.1 理气活血,通利津液 《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言:“大气一转,其气乃散”[2]165,“血不利则为水,名曰血分”[2]166。《景岳全书·杂症谟·肿胀》[4]指出:“凡治肿者必先治水,治水者必先治气,若气不能化则水必不利。”《血证论·阴阳水火气血论》[5]云:“瘀血化水,亦发水肿,是血病而兼水也。”
这些水气病治从气血的理论,在《普济方·水病门》中有很好的体现。气药多用陈皮、槟榔、木香、青皮、枳壳、大腹皮,气行则水行。血药则多用川芎、三棱、莪术、丹参,血活则水利,甚则以硇砂、鳖甲消积软坚。方如“水肿”部分大戟汤以逐水之大戟、调气之橘皮,配理血之当归,气、血、水完美结合,可疗“水病无问年月深浅”[1]2563。又如鳖甲饮,以吴茱萸、槟榔温中行气,鳖甲软坚散结,配茯苓、郁李仁前后分消,可“专治水气,心下痞紧,喘息气急,大肠秘涩”[1]2594。
“水饮”部分还专列了治血分的桂苓汤、调荣饮,治气分的枳术汤、桂术汤。虽言血分,仍伍入气药如槟榔、青陈皮等,盖气停则血停。虽言气分,亦配少量血药,如加味枳术汤中有五灵脂一分,血行则气行,二者不可截然分开。
2.2 香药走窜,开窍透络 “十水”部分有一张方名为“集香汤”,方中集沉香、丁香、木香、藿香、乳香、麝香等香药,方后云“凡虚肿,先用诸香,以透其关络,然后审查证疗”。可见,香药以其辛香走窜之功,有透络之能,可在药前行开路之功,且不燥不烈,可用于虚肿。《水病门》中用木香75次,麝香15次,沉香9次,藿香7次,香附5次,石菖蒲4次,乳香4次,香薷2次,冰片2次,苏合香1次。
麝香还常在方后出现,如葶苈丸以麝香酒下,沉香琥珀丸以麝香为衣,玉并散以麝香汤调下等。《本草纲目》言麝香“通诸窍,开经络,透肌骨”[6],可治二便不通、小便淋沥等证。《仁斋直指方》言其“能引药透达”[7]。清代《叶案存真类编·肿胀》用琥珀麝香方治疗水肿,以琥珀、麝香宣通利窍,大黑豆皮补肾固阴,言“今之所苦,愈结,宣通宜以利窍润剂”[8]。其他诸香药亦有开窍宣通之能,如:《本草再新》云丁香“开九窍,舒郁气,去风,行水”[9];《药品化义》言藿香“其气芳香……辛能通利九窍”[10]24,言沉香“纯阳而升,体重而沉,味辛走散,气雄横行,故有通天彻地之功……总之,流通经络,血随气行,痰随气转”[10]31;《名医别录》沉香条云“熏陆香、鸡舌香、藿香、詹糖香、枫香并微温,悉治风水毒肿”[11];《医学衷中参西录》言乳香、没药“二药并用,为宣通脏腑,流通经络之要药”[12]。水病多为前后二窍或汗窍闭塞不通,经络为水气所壅滞,以香药之走窜,恰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壅遏。
香药祛邪避秽、醒脾开胃、行气活血、宣透通络、开窍醒神,可用于疫病防治、变应性鼻炎、心脑血管病、外科疾病、骨伤疾病、口腔黏膜病等[13-16]。然而,以香药治疗水肿的临床报道却未见。《普济方·水病门》中香药的运用虽然不多,但有一定的启示。从其运用来看,虽然不单用香药来退肿,但将其配入利水行气活血的方药之中,却有引经透络之能,达事半功倍之效。正如集香汤,香药虽多,却依旧与茯苓、川芎、槟榔、枳壳等品相配,且强调“先用诸香,以透其关络,其后依旧需审证治之”。又如麝香丸,于芫花、甘遂之中加入半分麝香,既可增逐水之功,又不致峻烈太过。“水气,已服药,未平除”者,不可再行峻猛之药,亦可用麝香细研,奶汁调服以收尾[1]2594。
2.3 风药为助,辛散宣通 “风药”一词最早见于金代张元素《医学启源·药类法象》,以防风、羌活、升麻、柴胡、葛根、威灵仙、细辛、独活、白芷、牛蒡子、桔梗、藁本、川芎、蔓荆子、秦艽、天麻、麻黄、荆芥、薄荷、前胡为风药。明代贾九如的《药品化义》又将紫苏叶、香薷、生姜、葱头归入风药的范畴。张真全[17]指出风药“味薄气淡,质轻性浮,具灵动风性”。罗再琼等[18]认为风药具有“升、散、行、透、窜、动等多种特性”。
《水病门》中运用较多的风药依次为:羌活、生姜、麻黄、防风、细辛、葱白、紫苏、白芷、牛蒡子等。祛风类风药如麻黄、防风、羌活、柴胡、葛根等可宣散透邪,水病初期兼表者尤宜,方如“风水”部分麻黄散(麻黄、石膏、白术、附子、防己、桑白皮),麻黄与石膏相配,还有发越水气之功。紫苏、前胡、牛蒡子等入肺之风药,可调肺之宣发肃降。肺为水之上源,肺之宣肃正常,则水道得以通调,肿满得以俱消,还可缓解水饮射肺的相关症状如胸满气急、咳逆上气等。“风水”部分以单味牛蒡子二两为细末,每服暖水调下二钱,每日三、四服,即可治“风水,脐腹俱肿,腰不可转动”[1]2585,盖取其“提壶揭盖”之功。祛风湿类风药如羌活、独活、威灵仙等可宣畅气机、祛风除湿。水湿痰饮同源而异流,往往合并出现,如《金匮要略》中风湿及风水表虚证皆用防己黄芪汤治疗。且一些水病会出现“骨节酸疼”,当是水湿犯及关节所致,祛风湿药正好药至病所。“治风肿,皮肤麻木不仁,或时疼痛”之防风散中就有风药麻黄、防风、羌活、独活[1]2605,其中防风、羌活、独活还可祛风胜湿止痛。
风药辛散宣通,还有行气散瘀疏滞之功。清代张锡纯治癃闭、水肿之宣阳汤、温通汤、加味苓术汤,方中皆用威灵仙,谓其温窜之力能化三焦之凝滞,且能“行参之滞”。《本草正义》云威灵仙“善逐诸气,行气血,走经络……性利善走”[19]。“水肿”部分杨子建护命方,使用羌活、独活、细辛、荆芥等多种风药,并配以木香、川芎、半夏等理气活血化痰之品,治“肝脏实热,相刑于脾,遂生浮肿,渐欲成水病”[1]2568。
高红旗等[20]认为风药有宣肺疏风、祛风活血、行气利水、引经报使等功效,在肾性水肿的治疗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见,风药以其辛散、走窜、宣通、轻灵活泼之性,不仅能开表之毛孔,调肺之宣肃,祛风湿止痛,还可上行下达,内透外散,贯穿周身骨节毛窍,使气血周流、津液畅达,治疗水病不可或缺。
3 外治方法
早在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就总结有针、灸、温、烙、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人工呼吸等外治方法。
中药外治直接作用于患处,同样对患者具有发汗、利尿、泻下逐水等作用。徐维诚等[21]对中药外治法治疗水肿的现状进行了综述,发现外治水肿的方剂多以大黄、芒硝、牵牛子、甘遂等泻下药,黄柏、山栀等清热药,冰片、麝香等开窍药组合为主。这些中药通过缓解局部炎症、促进局部循环等,从而达到减少组织间隙中过多的液体、消除水肿的目的。认为中药外治法可以应用于人体多个部位的水肿,具有很好的临床疗效,可以促进水肿的消除,改善预后,同时还具有成本低廉、操作简便等诸多优点。
3.1 外洗 《水病门》中“水病肿满,腹大气急,大小便不利”,内宜依证服诸利小便药,外则以蒺藜汤(蒺藜子、赤小豆、葱心、青皮、菘菜子、蒴藋、巴豆)洗四肢,淋洗肿处[1]2607。以猪蹄汤(猪蹄、蒴藋、蒺藜、葶苈、黄柏)冷浴,每日3次,可“治服石发热,因劳损热盛,当风露卧肿”[1]2608。有仅以一味陆英煎汤洗浴“治水气虚肿,风瘙肌肤恶痒”[1]2600,及以杜蒺藜煎汤外洗治四肢浮肿的记载。《药性论》言陆英“主水气虚肿……煎取汤入酒可浴之,妙”[22]。《神农本草经》云蒺藜“主恶血,破癥结积聚”[23]33,盖取其活血利水之功。
《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记载,百合病变渴者,内服百合地黄汤,外用百合洗方,清热生津,洗其外,所以通其内。外洗与内服在病因病机、辨证用药上相同,只是给药方法、吸收途径不同而已。内服配合外洗,更可全方位地使药物功效得到充分发挥。
此外,还有用外洗法缓解药物副作用的记载,如治“膜外水气”用甘遂、大麦面制饼食用,药后如出现下利,“以冷水洗手面即止”[1]2624。
3.2 摩熨 外摩法、熨法、熏法等也属于外治法。《灵枢·刺节真邪》[24]云:“治厥者,必先熨,调和其经,掌与腋、肘与脚、项与脊以调之,火气已通,血脉乃行。”可见熨法可借火气以温通经脉、调和气血。《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头风摩散即是以附子为散外摩以散风寒、通血脉。
《水病门》中载有:以生商陆一斤“水煎摩肿上,并涂以纸覆上,干辄敷之”治“肤表久肿”的外摩法;服拓肿神应丸后,用椒目六两、白萝卜子半斤炒香熟,用手帕盛药熨病患身上肿处的熨法;“治水气,坐卧不得,面目身体悉浮肿,先以炭火烧一处净地令赤,以葱白七斤置于地上,令病人脱袜,蹲坐于葱上,围裹衣被,令汗出小便利”的熏法。葱白发表通阳,《神农本草经》谓其“主伤寒寒热,出汗,中风,面目肿”[23]121,借火之热势,更能宣散透达,亦可获开鬼门、洁净腑之效,且较内服更为安全简便。药后水肿未尽除者,还可以灸法善后,如:服十全汤十日后,可针灸三里、绝骨下气;服桃红散后以平胃散调补,若肿未退,还可灸三阴交、命门扶正以退肿。
3.3 脐疗 《水病门》中以商陆根杵烂后贴脐心治疗水蛊,可使病从小便而去。现代以脐疗治疗腹水的研究也多有报道,如代倩兰等[25]发现近20年来,医者多以甘遂、冰片、牵牛子、大黄等攻逐类药物敷脐,治疗肝硬化腹水。
对于全身水肿,脐疗亦有辅助之功。如《水病门》中服大戟散后,若肿不能全去,则于腹脐旁涂甘遂末、甘草水少许,可使其肿尽去。又有涂脐膏,以地龙、猪苓、针砂为末,和葱汁为膏,敷脐中,约一寸高,可治“水肿,小便绝少”。清代吴谦亦以贴脐琥珀丹治疗水肿。
神阙穴是经络的总枢,是经气汇聚之处,因此脐疗可补虚泻实、调和阴阳、通达气机,是调治三焦疾病的要穴,用治腹水更可使药物快速到达病所。
3.4 导引 《素问·汤液醪醴论》指出,治疗水肿需“平治于权衡,去宛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26]22。《普济方·水病门》中记载有“虾蟆行气,正坐,动摇两臂,不息十二通。以治五劳,水肿之病”的导引法[1]2569,即是对内经“微动四极”的具体做法。脾主四肢,微动四极有助于阳气展布、脾气健运。《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湿肿满,皆属于脾”[26]153,脾阳得运则水湿阴霾得散,水肿得消。
4 结语
《普济方·水病门》记载了各类水肿,其病因不一,然当务之急皆为去除水邪。汗下之法虽立竿见影,却要时刻谨记汗之得法,下之得当,以利为度,时时护正。理气活血,可使气行血活,津液通利;香药加入,可开窍宣通,走窜透络,引经报使;风药辛散,可透邪通调,祛湿止痛,行气散瘀,疏滞畅津液。洗摩熨敷,脐疗导引等外治法,可治外而通内,为内治法之佐助。期待古人朴素的智慧能为今日临床治疗各类以水肿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病证提供一定的经验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