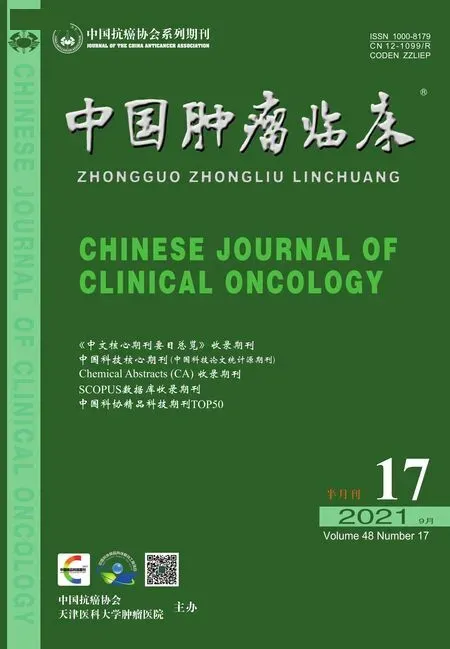BRCA突变乳腺癌的临床研究进展*
王斌 杨艳芳 姜战胜
BRCA1 和BRCA2 是乳腺癌的主要遗传性相关基因,携带BRCA 突变(BRCA mutation,BRCAm)的健康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会显著增加[1-2]。BRCAm 分为两种类型:1)胚系突变(germline mutation,gBRCAm),是指来源于精子或卵母细胞的生殖细胞突变,导致机体所有细胞都带有突变,可遗传给后代;2)体细胞突变(somatic mutation,sBRCAm),是指发生于肿瘤细胞中的BRCA 基因突变,为非遗传性突变。大多数临床研究中的BRCAm 多是指gBRCAm。
BRCA1 突变常见于三阴性乳腺癌,而BRCA2 突变则多发生在激素受体阳性亚型中。研究显示,BRCA1 和BRCA2 突变健康携带者,70 岁时单侧乳腺癌的累积发病风险分别为67.2% 和76.8%;BRCAm乳腺癌患者的对侧乳腺癌10年和20年的累积发病率分别为19.4%和50.3%[3]。除与遗传因素和发病率相关以外,BRCAm 也成为乳腺癌的治疗靶点之一。针对BRCAm 晚期乳腺癌,NCCN 指南(2021年)推荐使用talazoparib 和奥拉帕利两种PARP 抑制剂。本文就BRCAm 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及相关治疗进行综述。
1 BRCAm 乳腺癌的临床特征
研究显示,835 例乳腺癌患者进行BRCAm 检测,其突变率为16.6%(139/835),BRCA1 突变率为7.3%(61/835),BRCA2 突变率为8.3%(70/835)[4]。该研究还发现,在三阴性乳腺癌(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中,BRCA1 的突变率(44.3%)明显高于BRCA2(17.1%);在激素受体阳性患者中,BRCA2 的突变率(54.2%)明显高于BRCA1(27.9%)。该研究的预后分析显示,行新辅助治疗或辅助治疗的早期患者,BRCAm 和BRCA 野生型(BRCA wild type,BRCAwt)组的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相似;晚期患者一线治疗后无疾病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在两组中也非常相似。另有研究对999 例TNBC 患者使用二代DNA 测序进行BRCAm 检测发现突变率为13.1%,BRCA1 突变率为9.7%(97/999),BRCA2突变率为3.5%(35/999)[5]。该研究还证实BRCAm 患者的平均诊断年龄明显低于BRCAwt 患者(45.6 岁vs. 50.1 岁),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 1);中位随访53.6 个月,BRCAm 和BRCAwt 之间的DFS、OS 和乳腺癌特异性生存(breast cancer-specific survival,BCSS)均无显著性差异(P=0.799、0.092 和0.124)。另外一项大样本研究显示,7 361 例未经选择的乳腺癌患者中,BRCAm 突变率为5.4%(BRCA1和BRCA2 分别为1.9%和3.5%)[6]。该研究也发现TNBC 亚型中BRCAm 检出率最高(11.2%),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receptor-2,HER-2)阳性亚型中的BRCAm 检出率最低(1.8%)。
2 BRCA 突变的早期乳腺癌治疗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的一项研究纳入肿瘤直径≥1 cm 的BRCAm 乳腺癌患者给予单药talazoparib(1 mg/d)新辅助治疗6 个月,主要观察终点是残余肿瘤负荷(residual cancer burden,RCB)[7]。该研究纳入的20 例患者中16 例BRCA1 阳性、4 例BRCA2 阳性,15 例为TNBC、5 例为激素受体阳性,结果发现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率为53%。该研究第一次在BRCAm 乳腺癌患者中证明了单药PARP 抑制剂新辅助疗效,pCR 率和既往化疗或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结果相近;同时在乳腺癌激素受体阳性患者中也有显著的疗效,pCR 为60%(3/5),通常这类乳腺癌患者被认为属于新辅助治疗不敏感人群。
除单药外,对PARP 抑制剂联合化疗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在BrighTNess 新辅助治疗研究中,将Veliparib 联合紫杉醇+卡铂与紫杉醇+卡铂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总体患者的pCR 率(53%vs. 58%)并未提高,在BRCAm 亚群中也无明显区别(57%vs. 50%);因此不推荐Veliparib 联合紫杉醇+卡铂方案用于新辅助治疗[8]。GeparOLA 研究纳入同源重组缺陷(homologous recombinant deficiency,HRD)的乳腺癌(临床分期为T1~3N0~3),对奥拉帕利(100 mg、bid)+紫杉醇(80 mg/m2/周)组与卡铂(AUC 2/周)+紫杉醇(80 mg/m2/周)的新辅助治疗方案进行比较,12 周治疗后两组均序贯4 个疗程的阿霉素+环磷酰胺(EC)化疗方案再手术,结果发现奥拉帕利组的pCR 为55.1%,高于卡铂组的48.6%,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该研究根据BRCA基因进行亚组分析发现,BRCAm 患者的两组pCR 相当(60%vs. 60%),而奥拉帕利在BRCAwt 中有更高的pCR 率(50%vs. 37.5%),提示在HRD 乳腺癌患者中,奥拉帕利在BRCAwt 患者也起作用。该研究虽未达到预设的pCR,但从耐受性上,作者认为奥拉帕利代替卡铂值得尝试。
BRCAm 乳腺癌患者是否可从铂类新辅助治疗方案中获益一直无定论。一项纳入5 项研究、共363例BRCAm 乳腺癌患者的Meta 分析发现,含铂组和对照组的pCR 率无显著性差异(43.4%vs. 33.9%,P=0.400)[10]。另外一项纳入7 项研究、共808 例患者Meta 分析发现,BRCAm 组患者的pCR 率为58.4%(93/159),BRCAwt 组患者的pCR 率为50.7%(410/80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1]。INFORM 研究是一项随机、对照、多中心的Ⅱ期临床试验,在BRCAm 乳腺癌患者中,比较单药顺铂组与阿霉素+环磷酰胺(AC)组4 个周期治疗后的pCR 率(ypT0/is,N0)[12]。该研究对117 例患者分析发现,顺铂组pCR 率仅为18%,低于AC 组的26%。
GeparQuinto 研究[13]显示,贝伐珠单抗可增加TNBC 新辅助治疗的pCR 率。该研究中493 例患者行基因检测,BRCAm 发生率为18.3%(90/493)。在全部人群中,BRCAm 组的pCR 率为50%,BRCAwt组的pCR 率仅为31.5%(P=0.001)。在贝伐珠单抗治疗亚组中,BRCAm 组的pCR 率为61.5%,BRCAwt组的pCR 率为35.6%(P=0.004)。进一步分析发现,BRCAm 组中的pCR 和non-pCR 患者的DFS 无显著性差异(HR=0.74,P=0.472),BRCAwt 组中的pCR患 者 的DFS 明 显优 于non-pCR 者(HR=0.18,P<0.001)[14]。由此可以发现,虽然BRCAm 会增加治疗的敏感性,但是并未改善患者的长期生存,因此对这部分患者是否在术后给予PAPR 抑制剂的强化辅助治疗,以进一步改善长期生存值得深入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一项有关辅助治疗的临床研究,就是在BRCAm的高危乳腺癌患者中观察奥拉帕利是否可以改善生存(NCT02032823)。
总之,通过以上对于BRCAm 的早期乳腺癌研究可得出,单药talazoparib 新辅助治疗后的pCR 率为53%,奥拉帕利替换卡铂联合紫杉醇后序贯EC 方案的pCR 率为55.1%(高于卡铂组的48.6%),且这两种方案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Veliparib 联合紫杉醇/卡铂方案并未提高pCR,而且增加不良反应,单药顺铂或联合铂类方案在BRCAm 早期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中并无价值。BRCAm 患者的pCR 并未转换成DFS 延长,因此对于BRCAm 的高危乳腺癌是否需要PARP 抑制剂强化辅助治疗需后续的临床研究来证实。
3 BRCA 突变的晚期乳腺癌治疗
基于OlympiAD 研究[15],2018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了第一个PARP 抑制剂奥拉帕利用于携带gBRCAm 的HER-2 阴性的转移性乳腺癌治疗。该研究将奥拉帕利组与医生选择的卡培他滨、艾日布林或长春瑞滨(TPC)组进行对比发现,奥拉帕利组的中位PFS 明显长于TPC 组(7.0 个月vs. 4.2 个月,HR=0.58,P<0.001),奥拉帕利组和TPC 组的客观有效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分别为59.9%和28.8%,奥拉帕利组3 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发生率为36.6%,TPC 组为50.5%,因不良反应停药率分别为4.9%和7.7%;亚洲患者的疗效、安全性和耐受性与全球数据基本一致[16];2019年公布的OS 结果显示,奥拉帕利组的OS 为19.3 个月,TPC 组为17.1 个月,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0.90,P=0.513),但部分初治的晚期患者,一线使用奥拉帕利的OS 有明显获益(22.6 个月vs. 14.7 个月,HR=0.51,P=0.02)[17]。
EMBRACA 研究[18]与OlympiAD 研究设计类似,431 例晚期乳腺癌患者按照2∶1 的比例,分为talazoparib 组和医生选择的卡培他滨、艾日布林、吉西他滨或长春瑞滨(TPC)组。该研究结果显示,talazoparib 组的中位PFS 明显长于TPC 组(8.6 个月vs.5.6 个月,HR=0.54,P<0.001),talazoparib 组的ORR同样高于TPC 组(62.6%vs. 27.2%,P<0.001),血液学3~4 级不良事件(主要是贫血)在talazoparib 组和TPC 组分别为55%和38%。后续的安全性报告提示,talazoparib 相对于医生的治疗选择可显著提高疗效、改善患者预后、降低医疗成本和不良反应发生率[19]。将OlympiAD 研究和EMBRACA 研究进行荟萃分析显示,与TPC 方案相比,PARP 抑制剂会显著增加贫血和任何级别头痛的风险,但中性粒细胞减少和手足综合征的风险会降低;接受PARP 抑制剂治疗患者的生存质量恶化的时间明显延迟;单药PARP 抑制剂是治疗BRCAm 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首选[20]。
研究显示,PARP 抑制剂联合免疫治疗(尼拉帕利+帕博利珠单抗)在47 例可评价疗效的患者中的ORR 为21%(5 例CR、5 例PR),3 例患者持续缓解已超过1年。另有研究显示,在BRCA 突变患者中,联合治疗获益更为显著,ORR 为47%(7/15),中位PFS 为8.3 个月;而在BRCA 野生型患者中,ORR 仅为11%(3/27),中位PFS 为2.1 个月[21]。MEDIOLA研究在34 例BRCAm 患者中,将奥拉帕利联合德瓦鲁单抗治疗结果发现,中位PFS 为8.2 个月,中位OS为21.5 个月;治疗≤2 线患者的中位OS 为23.4 个月,治疗>2 线的中位OS 为16.9 个月[22]。因此,对于BRCAm 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PARP 抑制剂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值得进一步研究。
4 结语
在BRCAm 的早期乳腺癌患者中,PARP 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化疗均显示出较高的pCR 率。对于BRCAm 的高危乳腺癌是否需要PARP 抑制剂强化辅助治疗需要相关的研究结果来证实。在BRCAm 的晚期乳腺癌患者中,PARP 抑制剂一线治疗的地位尚未确定;在二线及后线的患者中,talazoparib 和奥拉帕利已成为BRCA 突变乳腺癌患者治疗的标准选择。另外,对于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患者也有一部分伴有BRCA 突变,特别是BRCA2 突变比例较高,这部分患者在新辅助治疗和晚期内分泌治疗耐药后,可考虑PARP 抑制剂作为治疗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