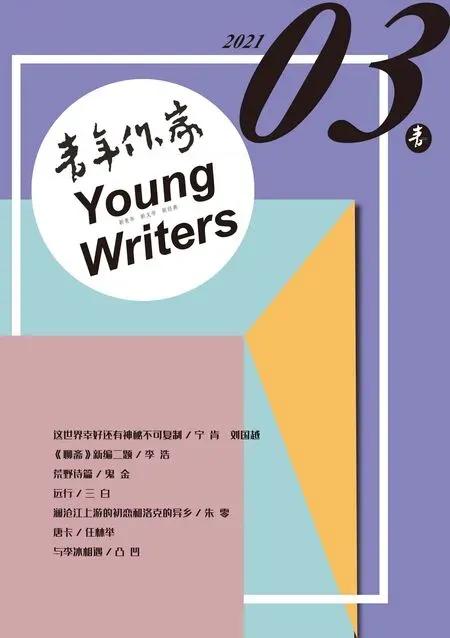唐 卡
任林举
一
沙来左手托着一只酒盅大的颜料碗,右手擎着一支笔尖细细的画笔,高挺的鼻尖险些贴上了面前的画布,而手上那些微小的动作幅度却小得如同静止。下午的阳光透过传习所的窗子从侧面照进来,有一道明亮的弧线从头顶至后背描绘出她凝然不动的轮廓。远远看过去,仿佛那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块石头或一尊雕像。
光线终于映射在画布上时,才看清那是一幅已经近于完成的唐卡。一点点金黄色的颜料正从沙来的笔尖儿落在深暗的画面上,宛若浩瀚的时间和无限的光明正从背后照进沙来的身体和生命,再由她的身体或内心注入她手中的笔,最后从笔端溢出,凝成画面上的色彩和线条。
这幅臻于完美的唐卡名为“财宝天王”。画中本尊全身呈金质,色泽金黄,一面二臂,头戴五佛宝冠,身穿黄金铠甲,佩诸种珍宝璎珞,右手持宝幢,左手持口吐各种珍宝的宝鼠,以菩萨如意坐姿态,坐于伏地白狮子背上,身上放射出十万旭日之光……依经典所记,在释迦牟尼佛住世之时,天王在佛前立下誓愿,愿护持佛法,并予众生以财资,令其成就世间法。虽然其外在显现为财宝天王之貌,但实质上仍是佛陀之所化现。这是藏地一尊既可佛心又遂人愿,将佛性和人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护法之神。
沙来的唐卡尚未完成,早已被人以高价订购。如今的沙来不仅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物质上获得报偿,最重要的是,在心性和境界上得到了提升。整整十年的精修和参悟,整整一年多的潜心绘制,在这个秋天到来之际,她终于欣喜地看到唐卡这棵生长了两千年的艺术之树上结出了自己的心愿之果。十年间,她通过这种纸上的修行,已经由一个心性蒙昧、不谙世事的牧女,变成了对艺术、宗教和生命都有了独到理解和把握的画师。难道真如人们所说,唐卡是可以卷起来的佛,对所有走进它的凡俗生命都有着度化之功?
十年前,已经25 岁的沙来,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此生能够有今天。在平均海拔3200 米以上的壤塘,她作为一个11口牧民之家的第八女,从小到大还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教育。她就像一朵无人赏识也无人采摘的野花,在高原的阳光下自由绽放。从不到十岁开始,她就赶着她家的牦牛群,随着寒来暑往的风,随着飘动不定的云,去西山,去东山,去南山,也去北山,在风霜雨雪中悄然长高、长大。在牧牛的间隙,为了贴补家用,她也会随身带着挖掘工具,挖一些贝母、虫草等可以到市场出售的藏药,但更多的时间她还是习惯于独自发呆或对着空空的山和空空的远天唱歌。
起初,她只是用高亢、清丽的调子唱六字箴言,据说这样可以为自己积下功德,也可以为家人和牛群祈得平安。但是唱着唱着,她就忘记了内容,歌声如流水、如岩浆,带着内心的灼热和波动,日日不停地流淌、喷涌,让她感觉到了莫名的畅快和愉悦。不管心中有多少哀愁、凄苦或块垒,只要那么一唱,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她是一个极具艺术天分的女子,唱歌让她发现了一种不借助任何对象就可以自由交流和倾诉的方式。可是,唱着唱着,她却发现有什么东西常常会跟着自己的歌声飞向远方,内心里就会有一些清晰的空落和朦胧的期盼。
渐渐的,沙来发现自己更适合放牧那些顺随自己心意的歌声,而那些歌声又总像无形的鸟儿,飞越只知道低头吃草的牦牛群,飞越寂静的山谷,甚至也飞越穿着破旧衣衫的自己,飞向高处,飞向云端。她开始渴望追逐自己的歌声去一个干净、吉祥如云的地方。
二
从来没有离开过牛群和山谷的沙来并不知道大山之外究竟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世上除了上山的小路还有许许多多的路可供选择。但是住在县城里的上师嘉阳乐住知道,他不但知道,而且正在整合各方善缘为她以及和她一样的年轻人搭建一条条从山地、高原通往大千世界的道路。
2009 年,是嘉阳乐住以藏传佛教觉囊派第四十七代法王的身份灌顶传法、收授弟子、开示法要的第十个年头。那是一宗善缘的发端。十年来,他走遍壤塘的山川和乡镇,体察了6800 平方公里县境内的民情。在总体上游牧多于农耕的藏区,很多家庭子女众多,少则三四个,多则十来个。有限的家财、众多的人口,均摊之后,不但人均资财很少,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会出现人口过剩和相对闲置。由于放牧所需劳力少,劳动强度低,只要一个女孩子就可以应付,很多适龄男青年只能在春夏之际到山上挖一些虫草和贝母为庞大的家庭增加些收入。冬天来临,大地被冻成了“铁”,待在家里的年轻人体内过剩的精力无处宣泄,便聚在一起滋生事端。酗酒者有之,赌博者有之,打架斗殴和盗窃者亦有之,失去家庭或组织约束、管教的年轻人有相当一部分成了派出所高度关注的对象。当嘉阳乐住上师发现这些现象之后,突然慈悲心动,深深地为这些年轻人感到惋惜。想一个个、一代代鲜活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本应该更多地呈现出他们的芬芳、光明、美好和意义,就这样一味毫无追求、漫无目标地游荡颓废下去,不仅是生命的巨大浪费,也会给社会和芸芸众生带来搅扰。
从这一年起,嘉阳乐住开始四处奔波,找各种机构、组织和朋友,祈求大家向那些一时丢失了心性的年轻人伸出援手,帮助他们从歧途上回归正轨。然而,这些民间机构或个人,毕竟经验和精力有限,解决这样的问题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初步尝试失败后,他决定自己亲自出手,通过开办唐卡、藏香、藏药、雕刻、堆绣等具有民族特色的传习所,将这些年轻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然后再用慈爱和艺术之火将他们的心灵一点点温暖、照亮。当有人怀疑或质疑嘉阳乐住的发心,认为他不懂世俗、异想天开时,嘉阳乐住总是回以自信一笑。他坚信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不会是黑暗寒冷的永夜,不管那些年轻人年龄多大,是男是女,有没有受过教育,出生于怎样的家庭,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存有一个善根,只要唤醒,只要呵护,只要施以阳光雨露,那颗小小的种子就会发芽生长,放大成无量光明。“尽管佛店里的灯火如豆,你也不要怀疑它能照亮整座大殿。”只要善根在,希望就在,就没有理由放弃。
最初的传习所,是因陋就简,零星分散的。学员少的专业可以在师傅家里开班,学员多的专业就根据实际需要租用面积稍大的民居作为课堂。费用,当然是由嘉阳乐住个人承担。不但传习所的场租费,就连学员的食宿和外出学习的费用都是由他一个人出。为了更多地吸引农牧民子女特别是贫困家庭的青年,他还承诺为每一个来传习所学习的学员提供每月300 元的资助费。为了打通人才培养以及与外界的沟通渠道,开阔学员的艺术视野,博采众长,嘉阳乐住上师又求助、联络壤塘县在上海市青浦区金泽古镇建立了传习基地,聘请著名高校的教授和专家为传习所的学员授课。夏秋季节学员在壤塘学习,冬季就去上海基地接受高校老师的培训或到有关艺术机构进行深造、实践、交流。经过近十年的坚持和探索,传习所为藏区青年的成长和走出经济困境积累了成熟的经验,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最初参加传习所的60 名学员如今都已经成为壤塘县县级艺术大师,其中有6 人已经成为县级非遗传承人,学员们独立创作的艺术作品被全国各地订购,特别是唐卡,在市场上一幅最高可卖到400 万元的高价,而且还一画难求。
2018 年,壤塘县进一步重视和发扬传统文化优势,抓住“脱贫攻坚战”的历史机遇,确立文化扶贫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渠道,在原来传习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投入,扩大了规模。不但通过招商的方式在中壤塘镇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壤巴拉非遗传习创业园,将唐卡、堆绣、刺绣、藏纸、藏药、藏香、陶瓷等传习所都集中到一个园区之内,而且将“文化+旅游+扶贫”的模式推广到壤塘县全境,共建立各类传习所47 个和18 个飞地传习基地,带动3000 余名青年以文创产品实现了脱贫致富和人生境遇的改变。
三
对沙来而言,2010 年的天是充满了慈悲的天,仿佛特意为她开了一道缝隙,有一道奇异的光透进来,照在了她的脚前,让她一抬眼就看见了自己一生的道路。
那一年,出家多年的哥哥咔隆作为得力助手去了上师嘉阳乐住的传习所,负责传习所的管理工作。咔隆无意间向家人透露的各种工作信息被沙来捕捉到之后,经过酝酿、加工,变成了越来越清晰的指引和越来越迫切的愿望。
有一天,沙来居然向父母和哥哥提出要去传习所学习技艺。这想法让所有的家人感到意外和震惊。父母和哥哥的第一反应就是强烈反对。简直是异想天开嘛!一个25 岁的女人,没上过一天学,想离开放牧了十多年的牦牛群,能干成什么呢?沙来说,我能唱歌。哥哥说,没有唱歌的传习所。沙来说,我要画唐卡。哥哥说,女孩子不能画唐卡。这是藏族民间的规矩。父母也异口同声地附和:“别说你画不来,就是画出来了,谁会要一个女人画的唐卡呀?”
“不管是什么,我就是要去!”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沙来充分发挥了她性格里的坚韧不拔。提一次要求不答应,再提一次。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提,最后父母和哥哥都屈服了。“那就让她试试吧!”传习所里教授的技艺,哪一样不比放牧复杂千倍万倍!没准儿,她去那里看看就知难而退了。哥哥决定带沙来去传习所,让她自己选一种最感兴趣的来学习,或哪个也不感兴趣,死了那颗不安的心。
那些天,咔隆领着妹妹在县城里分散在各处的传习所转来转去,以为妹妹会性味索然,没想到沙来却每天都处于兴奋之中。每到一处,她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藏药的神秘、藏香的芬芳、刺绣的精致以及藏纸的神奇,每一样都会令沙来驻足许久,但需要在内心做出决断时,她又轻轻摇头,选择放弃。然而,一到唐卡传习所,沙来的目光就直了,炯炯然,灼灼然,凝固在那些栩栩如生的画面上。仿佛冥冥中向她发出呼唤,推动她向着一个陌生领域前行的正是这些图画。在高原,很多人是相信缘分的,沙来说不清自己的前世与这些画有什么缘分,只是一见到这些画中的色彩和法相,就感觉到了自己的怦然心动,往那里一站,就不想再走开。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唐卡。这似乎合理也出乎意料的选择,再一次让哥哥咔隆感到为难,他仍然认为,在所有的选择中,沙来的这个选择是最错误的。她的错不仅在于有违风俗,更在于这是一项对沙来来说难度太大的技艺,几乎没什么成功的可能。关于唐卡,虽然事先也曾经提及,但哥哥还是把自己心中的顾虑和看法又对沙来强调了一次。本以为沙来会因为这郑重的劝告而另行考虑,没想到她的态度会越发坚决。哥哥既不能有效说服沙来,心又总是不能落地,最后只好带着妹妹去请教上师嘉阳乐住。
不得不说,在上师的眼中,沙来是一个极其独特的藏女。他能判断出来,眼前的沙来在物质条件和生活基础方面并不及其他学员,但她一定是一个聪慧、勤奋、刻苦的人。她个子高高,身材笔挺,但看她的脸色,深暗、红紫,足以证明她在过去的岁月里曾承受过旷日持久的风吹日晒;看她的手,大而粗糙,显然干过数不胜数的粗活儿;再看她的眼睛,虽目光羞还有些许卑微,却是清澈、纯净而坚定。她并不美丽,却天生一段清雅、沉静的气息,正是这气息让上师看到了她的潜力和未来。
上师听完咔隆的陈述之后,把目光转向沙来,微笑着对她说:“孩子,你的选择是对的。”虽然当时的沙来已经25岁,早已经不再是孩子,并且从面相上看,她的年龄也远远大于25 岁。这是上师一贯的姿态或心态,对所有来传习所的学员,他一律称呼为“我的孩子”。
上师深深知道自己开办这些传习所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他虽然并不知道具有魔法的时间,终将他的“孩子”塑造成什么样,但他坚信,任何技艺,只要有恒久不变的愿力和信念,只要付出足够的时间和耐性,都一定能被掌握,至于能达到什么程度,最终要看个人的慧根和愿力。关于世俗对女孩子的规约和偏见,他的态度十分明朗,在他这片佛家净土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上师看来,人是不应该有分别心的,无论男女,不分贵贱,都是一个生命,而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尊贵的,都有成长和升华的权利。技艺及其高度、价值、价格等都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塑造生命,使其成就,使其圆满。除此,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是手段,一切都是渠道。
四
只有坐在教室里面对老师的授课,沙来才意识到自己的粗糙、无知和心浮气躁,当然也感到无助。最初的课程几乎让沙来失去信心和坚持下去的勇气。老师的声音像天边的雷声,轰隆隆响个不停,她却听不懂那声音所表达的意思;也像一阵紧似一阵拂面而过的风,从左耳进入,又从右耳溢出,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沙来发现,自从来到传习所之后,每天需要做的主要事情,并不是学习什么本领,只是要把几乎全部精力都用在抵御课堂上难以抵御的困倦和平息随时都可以袭来的烦躁上。正在她暗暗地盘算自己要不要向哥哥和父母承认自己选择的失误,要不要知难而退选择放弃时,上师嘉阳乐住来了。
上师说,我知道你们遇到了困难,这并不奇怪。大家不要气馁,更不要失望,反而应该高兴才对。我们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自己变得完美的过程。这就像一场战斗,敌人没有出现,我们去和谁打仗?连个打仗的对象都找不到,我们如何取得胜利?现在很好,我们已经发现了隐藏在我们生命里的敌人,我们就有了目标,只要克服它、战胜它,我们就离成功和完美更进一步。这是第一关,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咬紧牙关挺过去,就能感受到胜利的喜悦。对你们,我有十分的信心,也坚决不会放弃,我也希望你们知道,我会一直和你们在一起,你们自己也不可以放弃。
上师的话,像阳光一样带着巨大的温暖和能量照耀着沙来的心灵。很快,她的情绪就稳定下来,曾一度浑浊、昏暗的内心仿佛雨过天晴,云开雾散,困倦消失了,烦躁消失了,困惑、迷惘也消失了,继之而来的是对新知识、新事物的好奇和渴望。
靠坚强的意志度过理论学习关之后,沙来开始跟着师傅按照唐卡的绘制程序一道道向下进展。制作画布、学习打稿、熟悉颜料的特性和研磨制作、着色、勾线、拉金……
刚刚拿起画笔,沙来的信心又一次遭到了沉重打击。这一双拿了十多年鞭子和镐头的手,突然攥住一支细小的画笔,竟如擎起千钧重物,不由自主地瑟瑟颤抖起来。也许是年龄稍大的关系,比起其他学员,沙来似乎显得更加复杂一些,一方面她更有主见,更会把握机遇;另一方面心理压力也更大,能够预见和感受到的困难也更多,所以她表现得更加胆怯和自卑。她万万没有想到,当初凭借直觉做出的一个选择,竟然让自己进入如此艰难的境地,几乎步步是坎,坎坎连环。
此时的沙来,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已经对觉囊派唐卡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历史上曾有“唐卡始于松赞干布,成于多罗那他”的评价。这里提到的多罗那他就是明代觉囊派第二十八代传承人。他在世时曾以大量的艺术作品和绘画艺术论述将唐卡艺术推向了一个巅峰,也为觉囊派留下了一门“看家”技艺。在壤塘,选择唐卡,就算摸到了唐卡艺术的正源,攀上了唐卡艺术的最高枝。凭沙来要强的心性,她并不会质疑自己那定得高高的目标,只是每每反观自己薄弱的基础和空空的底子,就觉得心里发虚、焦躁、忧虑。
这个阶段,嘉阳乐住上师会常常来到唐卡传习所,一改公共场所的威严,尽量放低姿态,平和如自家父兄,耳提面命,叮嘱沙来要放下包袱,要坚定信念,要相信自己,要坚持,要加油,并几次单独为她摩顶加持。上师得知沙来有一副清亮的嗓子,能唱好听的山歌,为了增强她的自信心,便鼓励她发挥自己的长处,展现自己的才华,想唱歌时就放声歌唱,并在每次传习所表演节目时,都为她做了特殊安排,由她领唱或以她的歌声开场。
于是,沙来开始放开嗓子大声歌唱,随着音量的放大和歌声的飞扬,沙来仿佛挣脱了一层无形的禁锢,原来那个畏缩的自我渐渐地伸展开了蜷曲的腰身。嘹亮的歌声让沙来的灵魂超越了自己平平的相貌和拙重的肉身,看到了潜隐其后的另一个更加年轻、轻灵、激情、美丽和充满了创造活力的自我。歌声虽已渐渐停息,但有一种透射着力量和信念的光芒却永久地驻留在沙来的眼眸之中。
很快,她的绘画便进入着色阶段,涉及到色彩所出的颜料。这是唐卡甚至一切绘画的入口。特别对于唐卡的绘制,颜料还有着特殊的意义。一般来说,唐卡的基本颜料都来源于自然。由于天然矿物颜料具有稳定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所以有色彩鲜艳耐久、可保持千年而不褪色的特点。矿石颜料通常用于绘制唐卡的底色。植物颜料主要从罕见的花、草、树叶、树皮中提取,这些植物颜料都耐光、耐热,具有极佳的色彩寿命,通常用于色彩的过渡。此外,还有一些出自动物身体的原料,如虫子皮、贝壳、鹿角粉等,这些颜料大部分用于唐卡的勾线。因天然矿物的稀缺、昂贵、耐久,如金、银、绿松石等,加之神佛的绘画主题,使得唐卡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先天的永恒指向。
作为一个优秀的唐卡绘制大师,必须对每一种颜料的特性都有一个深入的认识和理解,颜料的基本颜色、兼容性、持久性、随着时间推移所表现出来的变化等等都要做到了如指掌,运用合理、准确,恰到好处。因为对于一幅画来说,色彩就是主体的衣饰、发肤和气血,甚至是灵魂,必须在时间的浅表和深处都表现出始终如一的和谐,那是确保主尊具有不竭“生命力”的先决条件。对沙来来说,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大坎。如果把唐卡绘画艺术比作一座大山,这一坎,就是登顶前最后一道陡坡。沙来虽然已经断续画过几幅习作,但这次似乎又陷入了另一种困惑。
一幅正在着色的唐卡,静静地摆在那里,已经有几天时间了。沙来基本是一直枯坐在画布前一笔未动,她不知道如何完美处理唐卡中那尊金刚的手腕与护腕之间的过渡线,不知道那道线应该是金色的还是银色的,她也不知道自己的唐卡在整体感觉上要与以往大师的基调一致,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处理。
这时,嘉阳乐住上师刚好到画室来巡查,他站在沙来身后看了许久,猜出了沙来的困惑。上师像是针对沙来一个人说,也像是对画室中所有人说:“艺术是对生命和美的理解与表达,本身就是善、爱和慈悲。当你发现自己画不好的时候,一定是自己的情绪或心性出了问题,或者自己还不够完美。这个时候就不要一味纠结下去,要反观自身,看看是什么成为你的障碍,发现了障碍,然后消除障碍,你就通达了,画画就是修行。这时,你应该离开画室,去调整自己的情绪或生命状态,唱唱歌,跳跳舞,甩一甩袖子,或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让自己的情绪和心境变得美好起来。只要你自己变得美好了,你就能理解你的画,就能与那些线条和色彩产生共鸣,你就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于是,你的色彩和线条也就变得流畅、洁净、和谐、美好起来了,你的画也就圆满了……”
五
沙来终于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了哪里。原来,她是需要一种想象中的色彩来完成自己的创造。由于传习所内或市场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颜色,尽管煞费苦心在各种颜料谱系里搜寻,还是没有自己想要的结果,她正是为此事焦虑,一筹莫展。现在,她已经知道自己要什么了,也知道必须怎样做。经过再三咨询、斟酌和考虑,他决定在矿物颜料库里选择一种金黄色的砒石再加上一定比例的孔雀石混合研磨。她要的就是那种明黄里透着些许蓝绿的奇异色彩。因为没有先例和现成的配方,她需要亲自动手并根据研磨后的混合效果判断,之后还需要添加哪种矿石,添加多少。边磨,边摸索、调配,经过数次调适,最终得到自己理想的颜色。通常,研磨出一种单一的颜色,需要一个星期或半个月的时间,如果制造这种复合颜色,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一个坐在地上的石臼,含住一个从天棚上吊下来的石杵,中间是经过漂洗和浸泡过的小块矿石。沙来就端坐在石臼旁手扶石杵上的木柄,一圈圈用力研磨。一圈圈,旋转复旋转,重复再重复,像诵经,像念咒。在节奏单调的动作和声音中,一种恒定的力量和信心靠恒定的时间向前推动着,如魔法均匀地施加于矿物之上。十日之后,石块变成了齑粉,齑粉化作了岩浆,岩浆中那些成分不同的微小颗粒通过一系列物理的或化学的方式融合到一起,终于成为一种鲜艳的颜料。当日常生活中的不可能变成了艺术追求之中的可能,沙来似乎终有所觉悟,大约这既是愿力之功,也是时间的造化。
有一天,沙来在工作间隙路过刺绣传习所,远远看见戈登特聚精会神工作的背影,突然心有所动,决定转到他的工作台上去看一看。
这个比沙来小10 岁的大男孩,是沙来在传习所演出时认识的,因为他生得魁伟英俊,被选出来饰演藏戏里的格萨尔王。沙来站在戈登特身后一米多远的距离,并没有打扰他,静静地看他一双粗壮的大手在那里飞针走线。说是飞针走线,其实很难看到他两手间那条细细的彩线,只能看到他的手在空中上下翻飞,只是在“舞”。奇妙的是,一幅美丽的鸢尾兰在他的“空”舞中已经生动地显现于他面前的画布之上。
眼前的情景让沙来感慨万千,时间果然能够塑造出很多奇迹。谁能想到当年那个顶着一头红发、烈马般桀骜不驯的男孩会有如今这般光景呢?仅仅十年的时间,那个骑着摩托车在草山上挖药、横逛的男孩,那个抽烟、酗酒、打架斗殴的男孩,一次赌博就输掉家里两头牦牛的男孩竟然神奇地消失了,呈现于人们眼前的竟然是一个俊美儒雅的“格萨尔王”,也是县级刺绣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不但野性尽收,全身心地投入到刺绣技艺,而且还戒烟、戒酒、戒荤,成为一个严格的素食者。
沙来似乎又悟出了某种人生的真谛,她悄悄回到了自己的画位上,开始用舌尖洇开蘸笔尖上的颜料,一笔笔将颜色点到画布上。一点点,一点点,摒除杂念,凝神静气,一丝不苟……仿佛时间、身心和整个世界都随着那洇开的颜料一点点化开、消散,只有色彩在画布上堆积、显化,只有浩瀚如海的大愉悦在无边际地漫延——
沙来发现,当一个画师真正如上师要求的那样,让心灵“归零”时,时间便失去了方向和边际。似乎刚刚坐下,一天就过去了;似乎刚刚画出个轮廓,一个季节就过去了;似乎刚刚有了一个完整的表达,一年就过去了。有时,几年时光就如短暂一瞬,有时,短暂一瞬竟然漫长如永恒。
多年后,沙来的一幅“财宝天王”宣告完成。上师嘉阳乐住闻讯带人前往欣赏、评鉴。
“这幅唐卡是同一个主题中极其独特的一幅,构思巧妙,气韵通透,特别是对线条的理解以及金线的运用,充分体现了画师心性的成熟和技艺的高超……”当沙来的唐卡出现在众人面前,就有专家忍不住抢先发言。
嘉阳乐住上师却突然在两米之外止步,静观,站在唐卡前良久无言。几年来,他一直不太敢相信一个从山谷里走来的大龄女学员竟能把一幅唐卡画得如此完美,更没敢实实在在地指望有一天她能够成为一位优秀的画师。如今,这幅唐卡完美告成,俨然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带给他的不仅是一个意外惊喜,还是一个深深的感动。
那天,他并没有对那幅唐卡做任何评价,可是当他转身离开时,人们却从他眼中看到了闪动的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