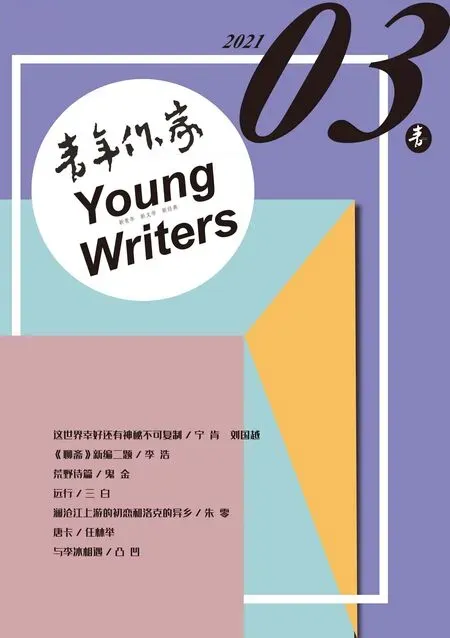《聊斋》新编二题
李 浩

李浩, 1971 年生于河北省海兴县;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将军的部队》《变形魔术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等20 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等;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现居石家庄。
耳中人
我要告诉你,我讲的这个故事,可是真的。
我没有讲假故事的习惯——虽然有人说我们的小说本质上就是“弄虚作假”,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能比“真实”的力量更能打动人,更有趣味和魅力了:尽管有些故事,从表面上看仿佛就是弄虚作假,就是说谎。这没办法,因为有些事情的发生就是超出了我们习惯的理解范围,我们不知道的、不能理解的还有很多呢!难道我们不知道的、不理解的,就都是假的吗?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此我必须保证故事的主人公有名有姓,有据可查——谭晋玄,淄青有名的谭先生你总该知道吧?他的家距离我的家很近,大约有四十里地的路程,门前有一棵硕大的老槐树,本来之前还有另一棵的,但在谭晋玄出生后不久即遭到雷击,大火烧了两天两夜,瓢泼的雨水也无法将它浇灭。后来谭家人在原来的旧址上又种植过槐树、榆树、柏树或银杏树,但都没能栽活,于是只好作罢。这件事儿,方圆七十里,甚至整个淄川都知道,你尽可随便打听。再说这位谭晋玄谭先生,他曾在肥丘做过一个小官儿,三五年,后来回到淄川,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诗人,而更为有名的是他特别特别迷恋于……痴迷于……热衷于……这么说吧,这些词都可以用到他的身上但都不及他迷恋的、痴迷的、热衷的半分,他实在是太过痴迷啦!他痴迷什么?你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道家方术,修仙炼丹之道。在他的房间里充塞着《太清导引养生经》《飞羽化鳞经》《炼神化虚归元经》《散魄纳精术》这类的书籍——不,这些书他没有存放在书房里,而是在自己的卧房里,出于怎样的原因我也并不清楚。
谭晋玄做小官儿的时候并不有名,他的诗文似乎也并不那么有名,至于教书……有几个学生私底下和自己的父母谈,谭先生的书教得不怎么好,他们总会在他讲着讲着的时候瞌睡,而他一停下他们就会醒来——不过那几个学生在别的老师那里也是瞌睡虫,不足为凭。真正有名的是他的修仙,据说他学得很深很透,颇有道行,有人说他精通《奇门遁甲》,能够召唤神仙鬼怪为自己所用,也能驱使当地的狐仙、蛇仙和鬼魂……我说过我要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些“据说”我也并不能相信,但我还是愿意将它列举在这儿,信还是不信,全凭你的判断——对于我们无法亲眼看到的事儿,我的处理办法是先存疑,但不会一下子否决:毕竟,我们无法亲眼看到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们知道谭先生是一个痴迷的修仙之人,知道他或多或少会有点儿“异术”就可以啦,接下来的故事与他的修仙修道有关,马上,我就要讲到它啦。
这一日,谭晋玄正在自己的房间中修炼……即使那些并不懂得修仙修道的人也知道,这样的修炼需要平心静气,放空杂念,物我两忘,耳朵的边上响起的是水声、风声和淡淡的鸟鸣声,水声潺潺,带着一股清凉意,风声缥缈,带给人的同样是清凉——然而入定的谭晋玄却感受不到清凉,他感受到的依然是酷热:仿佛一团火焰盘踞在他的头顶,而且还散发出哔哔啪啪的响声,一团火辣辣的气从他的后背那里不断地冒出来,让他似乎汗流如雨: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闭着眼睛努力让自己入定的谭晋玄正在汗流如雨,窗外火热的阳光早已晒透了他的屋子,一大团乳白色的热气从门缝外面飘进来,把谭晋玄和他身上的汗一起笼罩在下面。
谭晋玄感觉自己心生愤怒。似乎还有些委屈,还有些小小的恶意——“我是一个修道的人,我不能如此,我不能任由这种情绪蔓延,它会毁掉我的修仙之路的。”谭晋玄暗暗地提示自己,物我两忘,施受两忘,恩怨而忘,无欲无为,五蕴皆空,此时此刻,我不是我,我不再是我,我是……但那股炎热还是无法让他获得宁静,他感觉,有一团雾紧紧地包围着他,让他无法真正地走到他想要的清凉的对岸去。窗外。蝉在聒噪,它的出现更让人心烦。谭晋玄想如果有根细针,从蝉的背部悄悄地插进去,它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疼痛就从树上重重地摔下来,啪啪啪地拍几下翅膀——但那份毫无节奏、让人烦闷的聒噪就会止住。窗外,一个孩子的哭声,他很可能是踩进了水塘,跑过来的女仆在低声呵斥,有两声沉闷的声响,之后,哭声轻了下去。谭晋玄想,这个名叫王兰女仆也许乘着周围没人推搡了自己的小主人,这样的行为着实可恶,她应该……在想到剥去衣物用桑枝打屁股的时候谭晋玄止住了联想,罪过罪过,我应当物我两忘施受两忘恩怨两忘无欲无为五蕴皆空才对,怎么会……
像往常一样,谭晋玄用掉了近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让自己安静下来,这时窗外的炎热也并不像刚才,西边的墙上晚霞如血,干燥的树影在细细的风中晃动。就在这时,谭晋玄突然听到自己的耳朵里有一个模糊的、几乎像苍蝇只扇动了一下翅膀那样的细小声音:“我可以出来吗?”谭晋玄愣了一下,身上的汗水似乎骤然变凉——什么?
当他仔细去听的时候,那个声音已经消失了,就像根本没存在过、没有出现过一样。他晃动自己的头、耳朵、脖子,毫无异样。“是不是我听错了?是不是由于炎热的缘故、情绪不稳的缘故,才让自己产生了这样的幻觉?”谭晋玄将信将疑。
晚餐的时候,谭晋玄把自己的儿子叫到身边,“过来,下午踩水了没有?湿了鞋子没有?”摇晃着拨浪鼓的儿子颇有些不耐烦,但不得不按照规矩认认真真地回答:“没有,父亲。”谭晋玄看得出儿子满脸的不耐烦,他伸出手去拧了一把不耐烦,“看你不老实,不说实话。”在收拾桌椅的间歇,谭晋玄叫住女仆王兰,“少爷是不是又调皮了,又惹你了?”“怎么会。”王兰笑起来,她笑得像一朵才绽放不久的花儿,“少爷可听话啦,比我的小弟弟强不止十倍百倍,他乖得让人心疼。”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谭晋玄的夫人转过脸来,用一种异样的表情盯着王兰的脸。“没事,”谭晋玄半闭着眼睛,“你家那孩子,我怕他太顽皮。”
“老爷,”打发走儿子和女仆,夫人一边将香点起一边对谭晋玄说,“上午去衙门打听过了,咱们在荆川买的那十二亩六分官田……”
正午。谭晋玄再次进入他的清修中,当然炎热也在同一时间里再次火辣辣地袭来,这一次甚至较之前几日更甚。他身上不断地渗出有异味的汗,而腋下,则更早地湿透了,还有些微微的刺疼。他忽然想起在肥丘时的某些故事,这些事多数令人不愉快,本来他早就忘却了,然而在这个寂静的只有蝉声喧哗的正午却又想了起来。他想象,等他法术精通之后,把那个打过他两记耳光、喜欢在河湾中游泳的主计仆使用法术按进水里,等他挣扎到无力的时候再把他放出来,让他受些惊吓却不至于淹死,让他一生再也不敢下到河湾里去;他想象,等他法术精通之后,让那个嘲笑他不知躲闪而被马尾携带的粪便甩了半身的车夫把自己的车赶进沟里去,要断一根马腿,让它再也……谭晋玄被自己突然冒出来的想象惊到了,他急忙将它们驱赶出去:物我两忘,施受两忘,恩怨两忘,无欲无为,五蕴皆空,此时此刻,我不是我,我不再是我,我是……
再次,他听到了那个声音。那个藏在耳朵里微小的、仿佛是苍蝇的嗡嗡声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我可以出来吗?”这一次,比上一次更清晰些,也更有节奏。然而当谭晋玄真正去注意它的时候,它又消失了。谭晋玄晃动自己的头、耳朵、脖子,甚至在心中默念,暗暗呼唤那个声音,然而它没有再次出现。“它是什么呢?”谭晋玄想不明白,他搜索记忆,在那些讲述清修、养生、炼神化虚的书籍中,似乎没有一处提到过在修炼过程中会在耳朵里有声音出现,它出现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后果……“它,是不是在问我?如果我回答说可以出来,它又会怎样?”谭晋玄仅仅想了一下,他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也许,问话的那个就是他的灵,是他的魂魄,而一旦将它放出来……
然而一日又一日,每次打坐清修的时候,谭晋玄都会先进入心神不定之中,甚至胡思乱想之中,只有过上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好一些;而在他进入充满清凉的水声、风声和淡淡的鸟鸣声之前,耳朵里那个奇怪的声音就会再次响起:“我可以出来吗?”
一日一日,日复一日,从初夏到仲夏。谭晋玄渐渐习惯了耳朵里的声音,他甚至在修炼的时候早早地会期盼它的出现,甚至连偶尔飞进屋子里的苍蝇也变得有些亲切起来。日复一日,谭晋玄也渐渐习惯了夏日炎炎,习惯了在最初的时候难以入定,习惯了自己的胡思和乱想,习惯了在这胡思乱想中释放某些……谭晋玄在那种释放中小有快乐,这一点他不想否认,尽管这个小有的快乐并不是修炼的部分,需要在修炼中努力抵御的部分。一日,谭晋玄随意地翻看着一本购得不久的旧版书,《扪虱谈仙闲录》,随意翻看着,里面的记载让他陌生也让他兴奋:原来,仙也可以这样来修,竟然会有这个样子的仙……读着读着,已经过了他平日开始修仙的时间,然而他浑然不觉。
他读到,南宋时淄青有一姓王的书生,排行第七,从小仰慕道家方术,于是前往崂山访仙学道……大约过了四十几年他才回来,面容未改,竟然看上去比自己的侄子还年轻许多。这位归来的年轻王道士,善于医术,竟然可以使死掉的人复活,而使人复活的方法,竟然是利用从他耳朵里取出的仙丹——妙!妙极了!谭晋玄有种天灵盖被什么力量骤然地掀开、一股灿烂的光透过身体的感觉,他想,“原来,我耳朵里藏着的竟是仙丹!是它已经炼成啦!它嚷着想出来,原来是……”谭晋玄兴奋不已,他在房间里不停地转着圈儿,完全没有注意到水杯里已经变凉的茶水在光影中变成了绿色。“如果它再次问我‘我可以出来吗’,那我就回答它‘可以出来啦’……”
“它会是仙丹么?它会是怎样的仙丹呢?”谭晋玄并不得其解。
那一日,那个声音并没有出现。谭晋玄并不在意:毕竟,他在读书的时候忘记了时间,是天快要黑的时候才开始修炼的,仙丹大约有些挑剔,所有有灵性有才华的人或物都有些挑剔,这,他当然理解。第二日,那个声音也没有出现。第三日,第四日。
第五日。谭晋玄再次在床上坐好,让自己的身子冒出有味道的汗,一边默念平心、静气、放空杂念、物我两忘,一边让自己再次沉浸于胡思乱想中,在想象中想象……“我可以出来吗?”终于,谭晋玄再次听到了来自耳朵里面的声音,他的心砰地跳了一下、两下,那句回答便脱口而出:“可以出来啦。”
不一会儿,他感觉自己的左耳又疼又痒,仿佛它出现了小小的囊肿,而这囊肿在迅速地扩大,里面有一个怎样的活物儿在其中挣扎——终于,它钻出了耳朵,顺着他的肩膀、衣襟,慢慢地滑到了床边,然后又慢慢地顺着床角滑到地上。
是什么?
谭晋玄也想知道,他比我们更心急,只是,他不敢动作太快——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怕什么。谭晋玄屏住呼吸,硬着脖颈和自己的身体,转动的只有自己的眼珠——呀!他被自己吓了一跳,几乎要喊出声来!
他看到了什么?
我说过,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是真的,我没有讲假故事的习惯,所以,我必须要按照真实的情况去讲,而不是添油加醋、弄虚作假,将真实改变得面目全非;如果我要讲述一个假故事,在这里我一定会按照假故事的方式给谭晋玄送来一颗玲珑剔透的仙丹——但我不能。我只好实事求是地把事情的真相讲出来。
他看到的是,一个三寸左右的小人儿。它是灰黑色的,而且面目狰狞,就像一些图书中的“夜叉”那样——只见他有着尖利的牙,牙齿上还垂着暗红色的涎,眼睛里尽是恶狠狠的神态……“哦,终于出来了。我先熟悉一下这里再说。”
说实话,他的出现着实让谭晋玄意外,他身上的汗毛立刻变得粗大而坚硬,一股股凉风从他后背的汗毛孔里飞快地钻进去,它们如果能聚在一起似乎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这样的小人儿……“这,这……”谭晋玄呆得就像一块木头做成的鸡,窗外的蝉声,小孩子奔跑的脚步声,奶妈的呼喊和女仆的应答都无法传入他的耳朵。他的耳朵里,第一次那么让人疼痛地充满了静寂。
他甚至没有听到邻居到来时的脚步声,没有听见他和王兰的对话,他是来借什么东西的。他听到的是突然响亮起来的敲门声——“谭先生,你在吧?我是来……”突然响亮起来的敲门声简单是炸雷,谭晋玄耳朵里的静寂一下子被撕开了,许多只蝉一下子放进了他的耳朵。
“啊……”
只见那刚刚从耳朵里钻出的小人儿也无比慌张,他,简直就像一只受到了惊吓的老鼠,一只找不到自己洞口的老鼠——在谭晋玄房门被推开的瞬间,这只慌乱的“老鼠”撞到了床角,然后又以最快的速度消失于床的下面。
“谭先生,你的脸……怎么这个颜色?你是不舒服吗?是不是发烧?”
谭晋玄昏昏沉沉,他感觉自己的灵魂脱离了身躯,晃晃悠悠地不知道飘向了哪里。在昏昏沉沉中,他似乎知道夫人来过,孩子的奶妈和孩子来过,邻居来过,另外的邻居和邻居的邻居来过,王兰来过,她请来了大夫,在昏昏沉沉中谭晋玄未能看清他的脸也根本记不得自己都有怎样的应答。黄昏,黄昏散去,黑夜,黑夜已深。
谭晋玄一个人躺在床上,不断跳跃的蜡烛只有微弱的光,而他的身侧则全是黑暗和空旷,孩子和夫人、奶妈和女仆都已歇息,谭晋玄恍惚中看到床边的木桌上放着一个小碗和两个茶杯,而茶杯里的水竟然是暗绿色的。三更天了。他听到打更人的梆子。然后听到的则是嚓嚓嚓嚓,似乎是老鼠试图顺着什么爬上床来的声音。“帮帮我。我要回去。”
是那个细小的、仿佛苍蝇的嗡嗡声的小人儿发出的。但谭晋玄昏昏沉沉,根本无法移动自己的身子。
小人儿只得自己努力,继续努力。嚓嚓嚓嚓,嚓嚓嚓嚓。谭晋玄好像听见了它的喘气声,也听见了它的叹气声。“帮帮我。我要回去。”过一会儿,小人儿的嗡嗡声又再次开始:“帮帮我。我要回去。”“我是我。我是你啊。”小人儿的声音里似有哀求,似有怨恨。谭晋玄昏昏沉沉,根本无法移动自己的身子,他的眼皮却越来越沉,慢慢地进入梦乡。
在梦里,那个小人儿终于要爬到床上来了;谭晋玄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翻了个身,把他的左耳压到了身下。这时,又是一阵嗦嗦嗦的响动,屋顶上,出现了一条白色的蛇,它吐出的信子也是白色的,谭晋玄看得很清楚。它将自己的大半个身子吊在拔步床的木榻上,张开它的大口,一口将浑然不觉、正在全身心向上爬着的小人儿吞了下去。在梦中,谭晋玄啊了一声,他的左耳一阵疼痛,随后便再无知觉。
许多时日之后,谭晋玄才从他的昏昏沉沉中醒来。他醒过来的时候,夫人正在晾晒他的被子,她抱怨,一条新被子,刚给谭晋玄盖上,不知怎的就被莫名其妙的东西给染上了莫名其妙的污渍,灰的红的,怎么洗也洗不掉。她拿给谭晋玄看,谭晋玄忽然想起自己耳朵里钻出的那个小人儿:“咱家房上有条蛇……”
据说,谭晋玄在那之后患上了癫痫,服药医治总不见好,还是一个游方道士送给他两粒看不出颜色的丸药,服下去后才有好转,这,大半年的光景已经过了。我说过,我要讲的这个故事是真的,我没有讲假故事的习惯,所以谭晋玄是否得过癫痫、是不是从那时才得的我不得而知,我知道他的故事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年,我难以说清把故事讲给我听的那些人会在讲述的过程中添加什么、减少什么。在淄川的集市上我曾见过谭晋玄两次,在我去济南参加府考的时候见过一次:那年府考,正赶上春节,按照风俗,立春的前一天商栈店铺都要扎起牌楼,敲锣打鼓地到藩司衙门“春演”,真是热闹极了,我也就跟着几个朋友去看。拥挤中,朋友孔雪笠指给我:“看,那个站在红灯下面、戴着皮帽的矮个子就是谭晋玄,你应当听说过他的事吧,在我们曲阜也极其有名,说他是半个圣人、半个仙人……”
孔雪笠对我说,自从谭晋玄耳朵里的小人儿被房梁上下来的白蛇吃掉之后,谭晋玄的性情大变,原来他尽管修仙修道,可心胸狭小,总爱睚眦必报,更见不得别人的好。然而性格变化之后,他凡事都不再争再抢,凡事都心平气和,宽容忍让,也变得乐善好施起来……“也不知道他耳朵里钻出的究竟是什么,大概,不应当是夜叉吧?那条蛇出现得也够奇怪……”
孔雪笠说道。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考城隍
我要告诉你,我讲的这个故事,可是真的。
我没有讲假故事的习惯——假故事有什么好讲的?哦,我想到一个“劝诫”,劝人向善,劝人不偷不盗不淫,劝人爱父母爱妻儿,然后根据这个劝诫之词开始弄虚作假,繁衍出一个故事来……天底下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而那所谓的道理也实在清浅、无趣,再由我来讲一个,新的,似乎也没太大的意思。所以,我要讲的必须是真实的,我向你发誓。我也不想在其中塞入什么寓意和劝诫,至于你读出来的那些,大约也并不是我的本意——不过我的本意是什么在这里也没那么重要,我一向这么认为。
我讲的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它发生在我家亲戚身上,是由我的姐夫宋之解告诉我的。他向我保证,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故事的主人公是他的祖父宋焘,他不可能把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安插在自己祖父身上,他说自己可没那样的胆量——我相信他。的确如此。
“我的祖上曾经阔过……”姐夫宋之解递给我一把陈旧的黑紫檀折扇,告诉我说,上面的题诗即是他祖父手迹,而另一面的画,则是王渔洋所绘,画的是山水,元林、渐江一路,“你也知道,王渔洋偶尔会为朋友们题字题诗,画,却是难得一见……”姐夫伸长脖子,在听我称赞了几句之后才缩回他的身子,“我的祖父,和王渔洋年轻时候过往甚密,只是后来——他不是一个喜欢显摆的人,几乎从来不提他与渔洋山人的关系……不过,我要和你讲的这个故事,与王渔洋也确实没什么关系。”
下面,即是我姐夫宋之解讲的,他祖父宋焘的故事。
他的故事从病中开始——我不知道姐夫宋之解忽略掉了什么,或许他觉得忽略掉的故事都无关紧要——宋焘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茶不思,饭不想,整日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却总有晕眩,仿佛天地时有突然翻转,仿佛他马上就会从床上掉下去,掉进一个不可名状的深渊里去,而那深渊一片雪白,闪烁而明亮。病居住在他的身体里,并不噬咬他,并不让他疼痛,却不断地让他晕眩,使他从一个奇怪的梦里跌入另一个奇怪的梦里,有时它们是连续的,有时则完全没有联系,他不得不适应新的梦境中的环境、人物和自己……
这一日,宋焘从一个令人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感觉那种晕眩感似乎较往日减轻了许多,只是幢幢的人影变得更为模糊。他看到窗外的阳光、树影,心里竟然有一点点心酸,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努力地直直身子——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已不像以往那样沉重,他已经能够移动,甚至可以坐起来了:床几边有一盏新泡的茶,淡淡的白色气息还在飘散。他喝了一口,有点苦,这种苦是他之前似乎从未尝到过的,但随后又是一种他从未尝过的清香浸润进他的味蕾……他放下茶杯,体味着刚刚的茶味儿,而茶杯中的茶水似乎没有多大减少,还是那么多那么清澈。
他听到房门吱呀一声。然后是第二声,第二声更长一些。阳光瞬间罩满了整个屋子,那种轻微的晕眩又重新回到了宋焘的身上。进来的是一名四十余岁的中年人,官差打扮,胡须稀疏,但看得出经历过细心整理。进到屋里,他先皱了皱鼻子:满屋子的药味儿和一些其他的杂味让他感觉不适。
“宋先生,我这次前来是奉命请您参加考试的,请您勿要推辞勿要耽搁,马上和我上路吧。”
宋焘本能地应了一声,探着身子用脚踩上自己的鞋,然后又端起茶杯——“且慢,这位官差,我也是不明白……”
“您不明白什么?”
“我记得今年的府试刚过,不足两个月,而殿试还要等两年……对吧?负责主考的学政老爷还没有来,怎么能突然地要考试?您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吗?”
“哎,我也说不清楚,毕竟我只是一般差役,听从上边的命令就是了……我们差役,要司其职尽其责,该知道的必须知道,该听到的必须听到,该做到的必须做到,但不该问的绝不问,不该听的不能听,不能知道的还就真不能知道。我奉命过来请您,我也就只负责请您,至于您提到的为什么,最好是到了考场再问,或许您不问也就明白了也说不定……”
“可是……”
“我说宋先生啊,您怎么有那么多可是,我也不能回答您呐,您到了,参加了考试,一切也就明白啦。先生啊,你收拾收拾就跟我走吧,院子外面,马也给您备好啦……”
“好好好。”宋焘再次端起茶杯,一饮而尽,“那我收拾一下……”
“您也别多带什么东西,一是那边有,二是您也不能把您的物品都带进考场,放在外面也是累赘……”
“是是是。”宋焘拿了拿扳指,然后又放下,拿了拿折扇,然后又放下,拿了拿笔和砚台,将它们放在背搭,然后又端起水杯,一饮而尽。“官差大人,你略略再等我一下,我可能还要,还要……”
“宋先生,已经够了,那边儿还等着您呐。”
“嗯。”宋焘点点头,他又一次感觉口渴——也许是病得太久的缘故,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他又一次感觉到口渴。他转过身子,意外地发现水杯里的茶水还是满的,淡淡的白色气息还在飘散。宋焘端起水杯,脑子里一片恍惚,他记不起自己刚刚是否又新冲了茶,又朝着水杯里倒进了水。
宋焘跟着这位官差一起走到门外。阳光真好,比以往显得稠密很多,它明亮得都有些不真实,甚至能够直接穿过树叶和墙壁的阴影。宋焘看到自己的妻子正在穿越门廊,邻居家的小孩则径直跑着朝他撞过来,仿佛没有看到他的出现——宋焘避开疯跑的孩子,而自己的妻子已经转过回廊走到后院去了。
马在门外拴着,宋焘从没见过这样高、有着这样一身漂亮长毛的马,它的额上生有一簇更长的白毛,滑顺、柔软,让久病在床的宋焘更是心生欢喜。他伸了伸腰——虽然,那种僵硬疲乏还在,但较之之前的那些日子要好太多了,宋焘心想,自己真应该感谢官府安排的这场考试,使自己的情绪和身体都变得好起来了。
骑在马上,宋焘感觉自己的活力正一点点恢复,而那些一点点他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只是,晕眩还在,当然这种晕眩与以往的那种晕眩略有不同……怎么说呢?以往的晕眩是发生在他的大脑内部,他会倾斜、旋转——事实上那种倾斜和旋转并没有发生,他躺在平坦的床上,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与他同时感受到倾斜与旋转;此时的晕眩则是,他骑在马上,马在颠簸,而他感觉不到马的速度有多快,它的一步跨出了多远。周围的风景纷纷后退,从它们后退的速度来看,这匹马应当是在以最快的速度疾驶,然而从马的动作和它的长毛的飘动来看,应当是悠闲散步的样子,而且身侧的那个官差也同样悠闲,并不需要紧紧地追赶。宋焘想自己或许是病得太久了,以至于错觉连连,完全分不清哪是真实的哪是幻觉的……他想,“我也许不必关心这些,到了考场,也许真的会像这位差爷说的那样,一切都明白了。再说,我也没什么损失,身体都已恢复正常,病也好了大半儿。有些事儿,不明白就不明白吧,自己这大半生,不明白的事儿还少吗?”宋焘漫无目的地想着,直到一根树枝划到他的脸——他一惊,伸出手去摸摸自己的脸,庆幸的是,并没有划破也没有划出痕迹来。一惊过后,宋焘意识到马奔跑的方向并不是他所熟悉的方向,它不是奔向淄川也不是奔向济南,而是一条全然陌生的大道,路边的树木高大茂密却几乎看不出是什么树,层层叠叠,几乎遥无尽头;而空中的云也是别样的白,每片云拖拽着一条蓝色的尾巴,一动不动,这匹马的奔跑也不能拉近和它的距离。“这是去哪儿……”宋焘嘟嚷了半句,他知道他根本从官差的嘴里得不到答案,索性就不再问他。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们来到一座城的外面,城墙高大庄严,飘动的旗帜在辉映中闪着金光——“我们是到了都城?”宋焘自言自语,他知道那位跑得面色红润的官差是不会回答他的。
他看到了车水与马龙、人来与人往,或许是仍有晕眩的缘故,他没有记下任何一张脸。
“宋先生,宋先生”,刚才接他进门的另一个官差凑到他的身侧,“诺,您的位置在那儿。宋先生啊,您可真是有福之人啊,日后飞黄了腾达了可别忘了我们几个,我们可是细心地照应着您呐。”宋焘用力地点点头,然后朝他指点的位置坐下来——坐下来,他才稳住心神,可以细细地观察周围的环境了。
大殿恢宏壮丽,似乎还有祥云围绕——宋焘想,这又是自己的错觉,即使这座高耸的大殿矗立在山上,也不会有发亮的云朵从脚下升起,伸过手去就能抓住——宋焘心里生出一点小小的顽皮,他真的想去抓一把白云:这当然不可,他觉得大殿里那些面容严肃的官员、进进出出送水送纸送看不清什么东西的小僮和立在一边的官差很可能因此心生鄙夷,觉得他没经过世面,也不够稳重,那,这场考试还未开考自己已经输了大半。在他左侧,已经坐下了一个秀才模样的人,较之自己要年轻一些,面目倒是清秀,然而却显得有些柔弱、苍白,他朝着自己点点头,然后指指飘到桌角处的白云——秀才的这个动作,立刻让宋焘生出了几分亲近,宋焘朝他笑了笑,算是回答。
只有两张桌、两个坐墩,笔墨纸砚是早已准备好的,宋焘想起自己的背搭和里面的那些器物,似乎比面前的这些要精致些。“考试开始……”有官差从大殿里面喊,宋焘恍惚中发现,自己的面前已经多出了有考题的试卷,试卷的上面写着八个字:一人二人,有心无心。
——只有我们两个人考?
——宋先生,您需要更多的人一起参加么?我建议您还是专心答题吧,笔墨已经为您准备好啦,我们也会精心地伺候您,只要您的要求与答题并不相关。
——好好好,我马上答。
虽然宋焘之前并未做过类似的题目,但他依然感觉轻松。他想起自己的阅读、经历和经验,想起自己在病中的时日和病中的怀想,想起自己在乡试、府试时与诗友们的相聚和争辩,想起……宋焘觉得,自己的笔下一下子就涌出千言万言,它们相互推拥着、相互铺垫着、相互勾连着、相互补衬和相互争斗着;宋焘觉得,他把自己的理想、梦想和种种感悟都写在了这篇文字中,有时甚至忽略了文法的严谨,但积在胸中的那些块垒则被一一推开。
他从未如此迅捷,从未如此愉悦,从未如此感觉意气风发,仿佛那些可怕可恶的疾病从未缠绕过他的身体,仿佛他年轻了十岁,身体里充满着这样那样的冲劲和活力……答完试卷,宋焘利用空暇时间观察着大殿上的人——中间坐着的,慈眉善目,年纪看上去不大,脸上仿佛涂有一层金粉,宋焘将它再次当做是自己的错觉,毕竟大殿里一直金光闪烁,也许是光影的缘故也说不定。右侧第一位,肤色黝黑,额上仿佛有一个月牙般的白色印迹,因为距离较远,看不太清;第二位,留着长长的花白胡子,笑呵呵的,一副和蔼像,他正在精心地阅读宋焘递上去的试卷;第五位,则正在阅读旁边那位书生的试卷,不住地点头——或许是视力不佳的缘故,他的脸和纸张凑得很近。左侧,第二位,是一个身高很高的大个儿,留有长长的黑色胡须,面色黑红,略有上吊的丹凤眼微微闭着……关,关公?!宋焘吃了一惊,仔细再看,那一位的确与戏台上的关羽有几分相像,而且越看越像……“我,我这怎么啦?难道,是我在病中梦见了这场考试?我为什么要梦见考试而不是别的什么?是不是,我的功名心还在作祟,即使在病着的时候也不能完全放下?这,又是一出怎样的戏呢?”宋焘情急中忽然想起有人说过,验证一件事是不是真实发生,只要狠狠地掐一下自己的腿就可以明白,如果有痛感,说明它是真的;如果没有痛感,则说明就是在梦中。
宋焘悄悄地把手指伸向自己的大腿——
“宋先生,里面传下话来,请您上殿呐。您的文章……”刚才和他搭讪的官差悄悄地朝他竖起拇指,“里面的爷,都在传您的文章呢,说是选对人啦。恭喜您呐!”
宋焘来到殿上,和他一起的那位秀才也跟在后面一起跪倒在殿上。“宋焘啊,好文章,好文章——当然张勒学的文章也好,只是和宋焘的‘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相比,还是略略逊色了一点……”中间那个脸色金黄、似是帝王的人冲着他们说道。他看了一眼周围,端起面前的水杯然后放下:“宋焘,此次招你考试,是因为河南商丘某处缺一位城隍,为了保险和有效,我们找来你与这位张秀才一起……而你去,我们认为是最合适的。”
——城隍?宋焘咀嚼着这个词,感觉自己的胸口受到了重重一击,突然意识到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一路行来的那些错觉和晕眩也就有了来由。哦,我已经死了。来此参加考试的是我的灵魂。我见到的金脸帝王不是戏剧里的,我见到的关帝爷也不是在演戏……宋焘一阵心酸,他想起自己的一生,想起自己未尽的那些事儿。他哭泣起来。
“诸位大人,仙人……我,一个小小的书生,能够得到这样的信任这样的重任,自然不敢有什么推辞……只是,只是,我的母亲……她已经近七十岁了,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在我病着的时候她总拖着自己的病躯来探望我,您知道她的腿……”宋焘脸上的泪水变得更多了,“如果我这样离开……别的事儿,倒是可以放下,可是我的母亲……我能不能,能不能……我知道,这个要求是有些过分,可是,我很怕我即使做了城隍也不能安心……”
宋焘听到一阵窃窃私语,尽管他的大半心思都在自己的哭泣中。“这样,你……这样,你查一查,宋母还有多长时间的阳寿?”
“九年。”
又是一阵窃窃私语,但在宋焘听来,那足够喧哗。
“不如这样。”那个很像戏台上关公关帝爷的长胡须高个子男人说道,“我们一共考了两位,而那位张秀才答得也不错,如果不是宋焘那句‘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我想我也许更倾向张勒学一些。不如这样,我们先请张勒学代理,等宋焘送走了母亲再来接任……”
“也是个办法。”黄金脸色的人点点头,然后转向宋焘,“无论做人做官,仁孝之心当然是不能丢的,我们无法信任一个缺乏仁孝、无情无义的人,而你的这点儿,也是我们所看重的。本来,你应当立即上任才是,要知道在这个大殿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的规定一向细密严格……但,我们可以给你开一个下不为例的口子。这样,就按关羽的建议,你先回去,等你母亲过世之后再把你召回来。”
“感谢感谢,万分……”宋焘激动的嘴唇都在抖动。他的内心里,有着一种百感交集。
时间:考试之后,傍晚。地点:芸溪街,一家叫“苍芜”的小酒馆,二楼。人物:宋焘,张勒学。几碟小菜,几杯烧酒。
“今日得遇宋先生,竟有种特别的亲切感,就是在考试的时候也没有觉得你是对手……当然,这可能和只有我们两个是新来的,同时又同是读书人有关。”张秀才的眼睛里有一种迫切,正是这种迫切也让宋焘产生着亲近。一杯,两杯。两杯过后,两个人越聊越近,相谈甚欢,不知不觉谈及自己的试卷内容。
张勒学:宋兄,你说“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是想避免让人们把做善事、行善行看成是表演,避免人们为了获得某些好处才做善事。它当然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因为我们多年来都看惯了那种表演善事的行为,他们有时的确让人作呕。可是“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我觉得似乎也有失公允。它很可能会破坏掉人们做善事行善行的愿望,如果那样的话……
宋焘:张兄,你也讨厌做善事、行善行的表演性,他们四处标榜自己的所谓善举,无非是想讨一个赏赐,现世的也好,后世的也好……如果我们不管他们的用心而见善举就赏,势必会导致民众的普遍虚伪,他们本没那种美德却要宣说自己有那种美德,本没有那份善意却反复表现有那份善意,久而久之,我们的民众就会失去本心本性,而成为道貌岸然、虚伪无比的伪君子之国。只有断绝他们的这份有心,不让他们想着善行而为善行,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真实质朴,有仁有义。
张勒学:我倒不那么觉得。宋兄,你想想,我们为具有良好德行的人树碑立传,在阳间阴间都建立一个分明、严格的赏罚制度,反复劝导读圣人书、学圣人行,知书明理,这不正是有心吗?不正是劝诫吗?不正是让他们能够努力为善、克制作恶吗?所以,我觉得有心为善还是无心为善,都不能作为我们赏罚的主要条件。
宋焘:读圣人书、学圣人行,在我看来是对人本心本性的唤醒,它与有心和刻意不是同一……迷失本心本性的善,不只是表演性一种危害,也不只是他们希望获得赏赐的欲念过强的危害,更重要的是,它会导致有些人掩盖自己的失误和恶,他们会让自己所做的恶也涂上善的油脂,让你一时分辨不清……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的人会为此丧命,甚至是许多人。我愿意给你举一个我们淄博的例证——
张勒学:宋兄,我明白。我当然明白。只是,我们该如何判断一个人的善行善举是有心为之还是出于本性本能?如果我们的判断是错的呢?是不是会导致一种示范——他们看不到善行得到表彰和赏赐,慢慢地,就丧失了善的兴趣而转向恶或者麻木呢?
宋焘: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判断能力也需要判断方法,否则,张兄,我们要知府知州,要判官城隍和仵作做什么?他们就要做这样的判断,当然这个判断必须慎之又慎。是的,它大约不能保证所有的判断都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因为不能保证所有就放弃这一判断和判断的可能。就像我们考试,任何一篇文章都不太可能获得所有考官和天下学子的一致好评,但评和判还必须存在,勉力为之也要分一个一二三。对不对?
张勒学:判断文字,是因为文字已经呈现在那里;而判断一个人做事有心无心,则可能完全没有条理,没有踪迹,除了那些极少让人一眼能够看穿的事件。它很容易因为个人的好恶,做事的人面容的美丑而妄下断言……相由心生,以貌取人也不完全没有道理,但绝非完全准确,不然文曲星君、钟馗、天王都可能因为相貌问题而被……
宋焘:我们当然不能根据相貌判断,即使它有一定的道理。
张勒学 :好的,即使我们可以有判断的方法,只奖励那些不刻意求善的善,只惩罚那些故意为恶的恶,久而久之,我依然觉得它很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民众失去敬畏心,他们会变得浑浑噩噩……宋兄,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奶奶病着,而我需要从厨房里将刚煎好的药给她送过去。路上,我洒了些药,当然这是无心,我没有想把它洒出去的意愿;路上,我在上台阶的时候摔倒了,药碗摔碎,我依然是无心,绝没半点儿故意。母亲还是因为我的无心之失责罚了我,而正是这个责罚让我明白,做任何事都必须小心谨慎,不可大意。宋兄,如果一个人无心的过错不被施以惩罚,那太多的人就会变成无心人,他们就能变得粗枝大叶……
宋焘:张兄说得有道理,极有道理。我的确未从这个方面去考虑——但我也要向你声明,我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和你说的不同。我说的“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本质上是想制止人们的机巧之心,不使人在标榜自己的善行而假装,不使人在假装中获得好处而让世人纷纷效仿。张兄,你也看到,太多的人都称自己善良质朴本分,在外面也尽量做到他所宣称的样子,可一转身,一旦进入内部,他就完全不是那样子了。我觉得这样的伪善是不能得到赏赐,我们其实给予伪善太多机会,以至于真的善良善心被掩盖了起来。
张勒学:我在想,我们为什么要那样追问动机呢?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
宋焘:兄弟,如果我们不根据个人的出发点来判断,而只根据结果来判断,那样很可能一个一生善良、做了不少好事的人因为一个偶然的无心的过错而受到重重惩罚,没有一点儿改错的机会。你觉得那样合理吗?
张勒学:……
两个人一言一语地争辩着,这个过程如果都写出来——据我姐夫说,他的祖父宋焘的确将两个人的争辩细致地写下来过,然而那个手稿在后来的战乱中不慎遗失,我姐夫宋之解只记住了一小部分,很小的一段。“我的祖父很在意他的这个手稿,甚至想过勘印——后来出于种种犹豫而放下了,结果这一放下……也许是天意吧,我父亲也觉得手稿的遗失应是天意——那些匪贼,竟然没有抢掠我们太多的东西,容易带的歙砚、折扇和一些玉器都没动,结果唯独丢了这件手稿……”
两个人一言一语地争辩着,整个过程令人愉悦,宋焘感觉自己与张勒学的关系又近了一步,宋焘感觉这争辩是一种享受,一种强烈的棋逢对手感。酒,当然也没少喝。这时,宋焘听到门外的马嘶,他知道,自己应该离开了。
宋焘从那个奇怪的却又清晰无比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处在一片黑暗里,这黑暗让他恐惧、窒息——我这是在哪儿?
尽管我承诺我讲的这个故事是真的,我没有讲假故事的习惯,但那些熟悉《聊斋》故事的人应当会猜到,宋焘是处在哪里——你们猜得没错儿。他是在棺材里面,已经整整三天……“是我,是我啊。”宋焘在里面喊,外面正在吹吹打打,哭声一片,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呼喊。
宋焘用力地踢打,用力地敲打——这时,终于有人发现了异样,他们停止了吹吹打打,也停住了哭泣,有声音传递进来:“你是?你是谁?”“是我,宋焘。我活过来了。”“是是是,似乎是宋老爷的声音……真的是你吗?”“是我。真是我。”“你,真的还是你吗?你怎么证明……”
略过那个对话的过程,外面的人终于确认棺材里面确实是宋焘,宋焘的确又活了过来,而活过来的宋焘也依然是宋焘,而不是被什么附了体,这才将棺材的盖子打开——我也不准备更多地描述宋焘再和家人重聚的那一刻,聪明的读者完全可以自己想象,它将会多么多么动人,多么多么具有戏剧性。
刚刚从棺材里出来的宋焘身子有些僵硬,甚至又一次感觉有些晕眩——医生来了,邻居、亲戚和那些好事之徒当然更是络绎不绝,宋家为此可是繁忙了好一阵子,以至于终于恢复宁静之后仆人们还有些不太适应: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工作被不同的人观看、被不同的人打断。最高兴的当然是宋焘的母亲,“我的儿啊,你可是把我给吓死了啊,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啦!”
“怎么会,娘。我也是牵挂你啊。”
宋焘并没有把自己的所有“遇见”都告诉自己的母亲和家人,但他讲了自己是如何跟着一匹高大的、额上长有一缕白色长毛的马进入那座大城,遇见了金色面孔的人、白色面孔的人和红色面孔的人,其中他最能认得清的便是关帝爷,他和戏台上的模样几乎一模一样;他怎样参加了考试,考的是什么,而他又是如何回答的,考官们对他的回答基本满意,而最满意的又是什么……他们本来准备派他去河南某处做城隍的,说要“吏竭其力,神祐以灵,各供其职,无愧斯民”,然而宋焘牵挂自己的母亲,毕竟她年老多病,腿脚也不利索,即使妻子儿子都很孝顺,他也放心不下,故向上求请,然后竟然得到了应允,于是他又回到了这个人世间。宋焘没有说自己和张秀才张勒学的饮酒和争辩,他觉得家人未必对此感兴趣;他也没有说考官们查到的母亲的寿限和留给他的时间,那是他的秘密,不应轻易地说破。
三天之后,宋焘备下礼物和祭祀的用品,按照记忆中张秀才给定的地址前往吊唁。地址是明确的,只是略远了些,宋焘走了四日才走到长山,这时已是深秋,路边的层层落叶别有一番萧瑟感。到达张勒学说的村镇,宋焘叫仆从询问,仆人回来告诉他说:的确有一个张秀才在前几日去世,现在已经入葬,葬在村西的祖坟那里;他的家住在……“不,我们不去家中了。我们直接到张先生坟上吧。”
在张勒学的坟前,宋焘按照礼仪摆放好礼物和用品,燃烧了纸钱,然后对着坟中的张勒学说出这几天来他的思考:你的提醒更有道理,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一直在反复地想,我也觉得仅仅“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是不够的,我们当然更需要律法规则的规约和保障,它可以是一种有效补充;不过我也依然以为我们必须有方法和条件制约有心之善,避免大家都成为伪君子,避免伪君子的伪反复地获得奖赏而成为示范性的……
突然一阵细细的风吹过来。它将纸钱的灰烬卷起,几乎直直地吹上了高处。宋焘看见,一条细细的、赤色的蛇,绕过祭品,钻入墓碑后面的草丛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