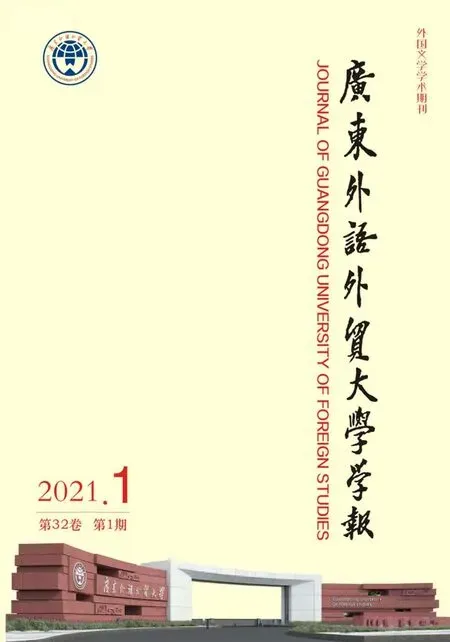儿童图画书的双重读者与戏仿策略:以当代英国图画书为例
周静
引 言
儿童图画书,又称绘本,是当代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主要面向尚不能独立阅读的幼儿读者。20世纪下半叶以来,儿童图画书的创作和传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图画书在当代儿童的文化生活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儿童图画书的研究不断深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儿童图画书的叙事,包括其中图画与文字的动态关系,以及反讽、元小说、跨层叙述(metalepsis)等手法的运用;另一个则是图画书对儿童语言习得、认知情感以及道德规训等方面的教育作用,这个领域的研究同样取得了不少成果。在现实中,儿童图画书的审美与教育是一起进行的,因此越来越多研究指向上面两个领域之间的交叉和跨学科研究(Colomer,et al,2010:2)。
与儿童文学其他文类相比,儿童图画书特别之处在于:一是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媒介——图画和文字,且图画和文字之间具有特殊的关系;二是它同时面向儿童和成人读者,后者包括出版商、批评家、教师、图书馆员以及作为购买者和共读者的父母们。因此,正如Egoff(1981:248)所言,儿童图画书是“看起来似乎最简单,实际上却最复杂的一种文体,它使用图画和文字两种艺术形式来吸引两类读者(儿童和成人)的兴趣”。为此,当代儿童图画书在叙事策略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包括使用反讽(irony)、跨层叙述(metalepsis)、元小说(metafiction)和戏仿(parody)等手法。有学者认为,这些手法在当代儿童图画书中的出现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由此生成了多面性的文本,既好玩,又有颠覆性(Allan,2012: 171)。还有不少学者对这些叙事手法在儿童图画书中的具体表现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但很少有人把它们和双重读者联系起来。Beckett(2001:193)提到,图画书中对经典画作的戏仿为成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得以引导儿童去了解伟大的原作。虽然贝克特的讨论仅限于对图画的戏仿,但它启发了笔者全面思考图画书中的各种戏仿与双重读者之间的联系。因此,本文拟以当代优秀的英国儿童图画书为例,探讨它们如何通过戏仿来吸引两类截然不同的读者,以及怎样才能使儿童图画书中的戏仿实现最大的审美和教育功效。
儿童图画书与双重读者
现代意义上的儿童图画书是西方近代“儿童的发现”的产物。因为只有儿童被视为独立的群体与成人区别开来,针对儿童的特定文学读物才能够出现。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和批评家Townsend(1977:14)指出,“在儿童书籍存在之前,儿童必须先被视为有其独特需求的人,而非仅仅是缩小版的男人和女人。”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确切的文化领域出现在18世纪。当时儿童主要被视为在学习和信仰上需要规训的对象,因此儿童文学从根本上依附于教育系统,有别于一般文学。受制于图画印刷技术的原因,儿童图画书的兴起在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常立,等,2016:145)。图画书的初衷,是为了愉悦和方便还不能阅读文字的幼儿,让他们能够通过图画来了解故事的内容。此外,图画书还用来帮助儿童发展其文字阅读能力和技巧,以便他们最终能过渡到纯语言的读物。与其他类型的儿童文学一样,图画书与教育密不可分。
20世纪70年代,新西兰教育家赫达维(Don Holdaway,1930-2004)提出“共读”(shared reading)这一理念,主张成人和儿童以一种互动的方式进行早期阅读。此后,美国等众多发达国家的研究者们从心理学和教育学等角度论证了亲子共读对于儿童情感、认知以及读写能力发展的重要价值,并对这一方法进行了引进和推广。儿童图画书尤其被视为学前亲子共读的最佳材料:图画书中的大量图画能够吸引儿童,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父母对文字的朗读、对图画的指称、评论和提问等则把不识字的儿童带到语言的世界,从而在图与文、视与听、(父母)亲与子等之间形成多元的互动。
20世纪以来,儿童图画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图与文的复合媒介为图画书的表达提供了极大的潜能,而家长对儿童阅读和教育的高度重视也催生出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利益。由于成人在儿童图画书创作、出版、评论、购买,甚至阅读方面占主导地位,不少儿童图画书都不仅指向儿童读者,还同时考虑到成人读者。当代美国儿童文学研究者杰克·齐普斯(2010:228)曾说过,“纯正的儿童文学并不存在。那些为青少年读者创作的作品,往往是为作者本人或为编辑们而写的”。在亲子共读被广为接受的情况下,儿童图画书尤其还需要为幼儿的家长而写。越来越多的儿童图画书作者在创作时就考虑到幼儿和成人这双重的读者,以期为孩子和共读的成人各自提供不同的乐趣和教益。
不可否认,由于幼儿和成人无论在兴趣、经验、认知,还是在社会角色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要同时满足他们并不容易。Wall(1991:9)提出“双重讲述”(dual address)这一概念,指儿童文学作品在讲故事时兼顾儿童和成人读者。她认为,早期儿童文学的叙述者通常进行 “两面讲述”(double address), 它看似为儿童讲故事,实际却“显示出对成人读者的在场的强烈意识”,往往忽视了儿童读者。随着平等意识的崛起和对儿童利益的关注,20世纪逐渐出现了完全关注儿童读者的叙述声音,即“单一讲述”(single address)。双重讲述则是单一讲述和两面讲述的融合,指叙述者同时对儿童和成人说话,它对写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事实上,双重讲述是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指那些被批评家们认为最有价值、经久不衰的儿童文学文本。由于儿童文学的经典化最终是由成人决定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不仅要吸引儿童,而且还必须具有一种隐含的深刻意义,以满足成人的鉴赏力”(Kümmerling-Merbauer,1999:14)。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9世纪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为孩子们创作的《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sAdventuresinWonderland,1865),它不仅深受儿童喜爱,还得到了成人读者的认可。这部作品“允许多层解读,为各种年龄的读者提供某种理解”(Scott,1999:101),甚至在主流文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20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家和批评家刘易斯(C.S. Lewis, 1898-1963)有一句名言:“只被儿童喜欢的儿童故事不是好的儿童故事”(Beckett,1999:xvii),即好的儿童文学必须能够同时吸引儿童和成人。20世纪后期,随着儿童图画书创作和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双重讲述”越来越成为作者努力的方向。
当代英国图画书继承了英国优良的儿童文学传统,诞生了不少享誉世界的作品,既受到儿童读者的喜爱,也得到了成人读者和专业人士的肯定。戏仿是这些图画书进行双重讲述的重要策略,它为儿童和成人同时提供不同层次的文本意义和阐释空间。
当代英国图画书的戏仿与双重讲述
有研究者曾说,“为儿童写作的文学也是完全互文的,因为它没有自己特殊的文本”(Stephens,1992:86)。虽然很多儿童文学作者和研究者并不会同意如此绝对的论断,但它无疑道出了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一般文学相比,儿童文学具有更多的程式性和互文性。在当代儿童文学中,互文尤其表现为一种游戏的方式,“使儿童文学成为一个天然的游乐场”(Nikolajeva,2005:37)。这种游戏式互文的突出体现就是戏仿,即为了滑稽效果而刻意地模仿某一作品、作家或文类风格。
戏仿是“互文性”的一种独特形式——“超文性”,是对源文本的复制、模仿,是一种带批判性姿态的、带有差异性距离的重复(陈彦华, 2018: 51)。戏仿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对其他艺术作品进行有差异的模仿,由于这种差异具有游戏的因素,从而形成了滑稽的效果。正如玛格丽特·罗斯(2013:31)所说,“大多数戏仿以刻意的滑稽形式利用了被戏仿文本与戏仿之间的不调和,这种不调和产生出滑稽效果,提醒读者或观众滑稽戏仿的存在”。过去,无论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还是昆体良(Quintilian,35 AD-100 AD),都把戏仿作品视为较低级的文学形式,只是经典作品的寄生品和派生物。当代学者则对戏仿的性质和功能有了不同的看法。Hutcheon(1985)考察了20世纪的各种艺术实践,指出戏仿是对“过去的艺术作品进行修改、重演、反转和转换语境的一种结构整合的模仿过程”。她认为这种广义上的戏仿是后现代艺术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现代自反性的一种主要形式”。因此,戏仿不再是一种低级的文学形式,而是现代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她还指出,当代艺术中戏仿的意图很广泛,“从反讽和戏谑到嘲弄和讽刺”都有。在当代英国图画书中,有一些戏仿作品对原作具有一定的批判态度,如《顽皮公主不出嫁》(PrincessSmartypants,1985)对传统童话中公主和女性刻板印象的颠覆和批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戏谑和玩乐的态度。
戏仿对读者有着较高的要求。Beckett(2001:175)指出,“要欣赏戏仿,读者必须首先能察觉戏仿另一作品的意图,然后有能力识别被戏仿的作品并解释它在新语境中的意义”。这种对认知水平和文化经验的要求,显然超出了许多儿童读者的能力。因此,当代英国图画书中的戏仿——主要包括对经典童话故事的戏仿和对经典绘画作品的戏仿,绝不仅针对知识有限的幼儿,而是同时指向与其共读的成人读者,形成一种“双重讲述”。
(一)戏仿经典童话故事
经典童话故事是儿童最为熟悉的文学形式之一,儿童较容易识别对它们的戏仿,并意识到其中的游戏和颠覆因素,因此,当代不少图画书都以经典童话故事作为戏仿对象。对经典童话故事的戏仿可以采取三种方式,分别是戏仿某一童话故事、戏仿多个童话故事,以及戏仿某一童话题材或文类,它们在当代英国图画书中都有所体现。
曾多次荣获各项大奖的英国图画书大师安东尼·布朗(Anthony Browne,1946-)是戏仿的高手,通过对戏仿的巧妙使用,他创造了许多有趣而深刻的作品。其中,《我和你》(MeandYou)戏仿了经典童话故事《金发姑娘和三只熊》(GoldilocksandTheThreeBears)。在原故事中,当熊爸爸、熊妈妈和熊宝宝出门散步时,一个金发小姑娘随意闯入了他们的家,弄坏他们的椅子、吃他们的食物,还在他们的床上睡觉。原故事以重复的情节告诫儿童应该遵守规矩和懂礼貌,对熊一家三口以及金发女孩都没有太多的交待。安东尼·布朗的戏仿则加入了不少细节,采取一种并行的双线叙事:左页的图画主要是黑白色的,叙述了金发女孩的一连串经历,没有文字;右页温暖的彩色图画则呈现熊一家三口的场景,文字采用小熊的口吻叙述,基本上沿用了原来的故事框架,但加入了更多细节使其具有现实感(安东尼·布朗,2012)。金发女孩的饥饿、窘迫以及她与妈妈之间的温情,与熊一家的富足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冷漠隔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金发姑娘和三只熊》是西方幼儿从小就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因此,《我和你》的大多数幼儿读者应该很轻易就能识别出被戏仿的文本。由于故事的场景被转换为当代儿童熟悉的生活,例如三只熊散步的公园、三只熊家里的摆设等,儿童读者甚至能更切身地理解和认同熊宝宝的叙述,并对与自身不同的事物——例如故事里的小女孩产生好奇和同情。另一方面,安东尼·布朗巧妙地设置了一些只有成人读者才能明白的讽刺,例如,熊爸爸与熊妈妈之间的疏离和隔阂、熊宝宝作为独生子女的孤独无奈、熊爸爸熊妈妈遇到问题时夫妻间的互相指责以及熊爸爸在发现危险时的退缩,等等。这些当代家庭生活中常见的问题无疑主要是指给成人看的。
安东尼·布朗(2016)的另一作品《走进森林》(IntotheForest)则在戏仿《小红帽》(LittleRedRidingHood)的同时,植入了多个经典童话。《走进森林》的主人公是一个小男孩,他独自一人去给住在森林里的奶奶送蛋糕。与小红帽一样,他没听妈妈的嘱咐,走了一条小路,遇到了一系列来自经典童话故事中的人物和场景,例如《杰克与魔豆》(JackandtheBeanstalk)中正牵着奶牛叫卖的杰克、《金发女孩和三只熊》中还未闯入小熊家的金发女孩、格林童话《汉塞尔和格莱特》(HanselandGretel)中被遗弃在森林里的兄妹俩,还有穿靴子的猫、《长发姑娘》(Rapunzel)中骑着白马的王子、灰姑娘的水晶鞋和南瓜等。最后,当穿着红外套的小男孩在极度惊恐中推开奶奶家的房门时,却看到了笑容满面的奶奶和他极度思念的爸爸。温暖美好的大团圆结局与此前一直营造的恐怖和不安氛围,构成了一种大反转,不仅让读者觉得有趣,也安慰了儿童读者幼小的心灵——他们正像《走进森林》中那个小男孩一样,日常需要面对无数来自未知世界形形色色的恐惧和疑虑。因此,即使是对书中所指涉的经典童话一无所知的幼儿读者,也能从这个故事本身获得意义。而熟悉经典童话的读者,更是能够通过这部作品丰富的影射建立与以往阅读的关联,从而积极地参与故事和意义的建构。经验更丰富的读者则或许能够进一步领会到,男孩在森林里的一系列奇遇其实只是他内心思想的幻化,是他在恐惧和不安中对以往阅读的经典童话故事的创造性想象。可见,《走进森林》至少提供了三种不同层次的意义:故事本身、对经典童话的戏仿和影射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整个故事的重新解释和思考,分别为不同阶段的读者提供不同的乐趣。
对经典童话故事的戏仿除了指向具体的经典童话故事,还常常指向某一特定的经典童话类型。英国著名插画家芭贝·柯尔(2011)的《顽皮公主不出嫁》(PrincessSmartypants)就戏仿了传统的公主童话,后者的情节通常是富有而漂亮的公主为了在众多求爱者选出最佳配偶而进行一系列的任务测试,最后终于找到意中的白马王子。但柯尔笔下的公主一出现就不同寻常:她没有穿长裙而穿着裤子,心爱的宠物是一头“怪兽”。这位公主不想嫁人,于是给前来求婚的王子们设置了各种匪夷所思的任务。然而,还是有一个王子顺利完成了所有任务。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公主给他来了个“魔法亲亲”后,王子变成了又大又丑的癞蛤蟆。因此,故事的结尾不是“公主与王子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是公主如愿以偿地过着自己喜欢的单身生活。这个故事离奇搞怪,天马行空,即使没有被戏仿文本的参照,对于幼儿读者来说也是幽默好玩的。而那些能够对这里的戏仿进行解码的读者,还能够看到它对传统童话中公主及女性刻板印象的颠覆和批评。
结构主义心理学家 Bettelheim(1976:5)认为,童话不仅为儿童提供乐趣,还直指他们潜意识中的压力和冲突,对儿童的心理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以上图画书通过戏仿和改写经典童话使它们更加符合当代儿童的成长环境以及当代社会的价值观,从而更易为当代的儿童读者所接受。同时,这些图画书的作者们“还注视着儿童听众头顶之上另外一些聪明人的脸”(Tolkien,1997:136),后者往往是成人,他们能够对更深层的信息进行解码,获得不一样的乐趣。戏仿经典童话因而成为儿童图画书满足双重读者的重要策略。
(二)戏仿经典绘画作品
由于图画在图画书中的主导地位,戏仿经典绘画作品是当代许多儿童图画书常用的手法。图画书中被戏仿得最多的绘画作品,往往是那些广为人知、已经成为西方文化标志的杰作,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还有毕加索、莫奈、凡高等知名画家的作品(Beckett,2001:177)。同时,图画书绘者在选择被戏仿作品时也有自己的偏好。众所周知,安东尼·布朗就对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情有独钟,他在其处女作《穿越魔镜》(ThroughtheMagicMirror)中就多次戏仿了马格利特的名作《禁止复制》,此后布朗在其创作生涯中继续戏仿了后者的不少作品。然而,对经典绘画的戏仿尽管受绘者个人偏好的影响,却绝不是随意的。
对经典绘画的戏仿常常大量出现在涉及美术和美术馆主题的图画书中。由梅雷迪思·胡珀(Meredith Hooper)撰文、比·威利(Bee Willey)绘图的英国图画书《藏在名画里的猫》(CelebrityCat:WithPaintingsfromArtGalleriesAroundtheWorld)(2010)讲述了猫画家菲莉西玛的故事。猫咪们在画展上看到没有一幅名画上有猫的形象,都很生气。于是猫画家菲莉西玛重画了这些画,添上了在猫们看来“本来就该在那儿的”猫。为此她受到了所有猫的尊重,成了最著名的猫画家。但菲莉西玛逐渐厌倦了聚光灯下的生活,并醒悟到:并不是画家们忘了把猫画上去,而是天性热爱自由的猫自己不愿意待在画上。随后,菲莉西玛也选择了自由,她从此不再往名画上添加猫,而是画自己想画的东西。由于情节的巧妙设置,《藏在名画里的猫》戏仿了一系列经典画作如《梵高的椅子》《庭院中的女人和小孩》《热带雨林之虎》《收割季节中的一餐》《侍女》《蒙娜丽莎的微笑》等。尽管幼儿读者可能并不熟悉这些原作,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们识别出戏仿的存在,并积极地辨认出戏仿作品与原作的区别——这里或那里多了一只或几只形态各异的猫。因此,这本图画书中的戏仿事实上能够让儿童了解更多的世界名画。另一方面,成人读者在这些戏仿中还能领会作者的反讽,看到书中的角色——猫对名画的解读的局限性。例如,在猫们看来,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全然是因为原画中漏掉的猫。这种在儿童身上同样常见的自我中心主义,无疑会让共读的成人读者会心一笑。猫画家菲莉西玛最后的醒悟和自由宣言恐怕也只有对名利及其相关束缚有所了解的成人读者才能心领神会。因此,《藏在名画里的猫》虽然以象征和代表着儿童的动物作为主角,但在其对经典名画的戏仿中却同时蕴涵了大量面向成人读者的内容。
在与美术和美术馆主题无关的图画书中,绘者也往往通过戏仿某些经典绘画作品来突出主题。例如,在安东尼·布朗(2009)的图画书《朱家故事》(Piggybook)中,妈妈离家之前的客厅里挂着荷兰画家佛朗斯·哈尔斯的著名画作《笑容骑士》,影射着爸爸和两个儿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快活得意的生活。当任劳任怨的妈妈愤而出走之后,与墙上的壁纸、开关及门把手等相对应,《笑容骑士》上的人物也变成了猪的形象,突出了父子三人的行为本质,也呼应了他们变成猪这一故事情节。由于前面的铺垫,幼儿读者能够轻易地识别出这里戏仿的存在,尽管可能只有某些具备更多绘画知识和文化资本的成人读者才能认出原作。布朗在这部图画书中还运用了一些更隐秘的戏仿,例如父子三人在餐桌边坐着,催促妈妈快点把早餐端上来那一幕,爸爸手中报纸上几张呐喊的嘴以及桌两边张着大口的儿子的形象,就巧妙地戏仿了爱德华·蒙克的名作《呐喊》。但是,由于这一戏仿没有任何文本提示,甚至没有画框,就连成人读者也很难察觉。虽然它不影响读者对故事的理解和享受,但能够识别出这种戏仿的成人读者,无疑会对此书获得更完整的领会和更多的乐趣。
对经典绘画的戏仿除了向具备一定文化资本的成人读者提供乐趣,同时还能够让儿童经由戏仿了解伟大的艺术作品,使经典艺术对儿童更有亲和性,因此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有学者以法国画家修拉的新印象主义名作《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在儿童图画书中的呈现为例,调研它如何影响了儿童对美术馆原作的体验(Yohlin,2012)。研究显示,那些从图画书中认识了这幅画作的儿童在美术馆参观中更充满热情。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儿童图画书通过戏仿、再创作等方式为儿童提供了经典绘画的一些基本知识,使他们在真正接触到原作时具有一定的自信,因而是让儿童“与艺术产生反思性、想象性体验的有效工具”。
儿童图画书的戏仿与儿童读者的优先权
由于儿童读者对戏仿的充分理解往往存在困难,戏仿在儿童文学中的使用有时会引起争议。正如Allan(2012:32)所说,“由于戏仿要完全发挥作用,依赖于读者对前文本的知识,戏仿在儿童文学中可能会产生问题”。即便如此,戏仿仍然是儿童图画书中盛行的手法,因为戏仿一方面是取悦成人读者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也与儿童的游戏精神契合,其滑稽的效果对儿童有着天然的吸引力。还有研究者指出,在电子时代,儿童习惯了多层次、多渠道的信息接收方式,利用戏仿来吸引不同年龄的读者是图画书应对这一时代背景的重要策略(Lamb,1998:171-172)。戏仿能够使读者积极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中,就像在电子游戏中那样。此外,戏仿对经典作品的改写具有解放的力量,它往往打破固化的文化传统和习俗,以幽默的形式表达严肃而重要的内容,如《顽皮公主不出嫁》对传统公主和女性刻板印象的挑战就是很好的例子。可见,“戏仿是对成人和儿童都方便的一种形式,它具有一种拉平一切的力量”(McGillis,1999:114)。
在儿童图画书中,戏仿的适当使用能够为不同年龄的读者提供不同层次的丰富意义,从而增加作品的吸引力和市场潜力。然而,在儿童和成人这双重读者中,孰轻孰重仍然是个问题。事实上,儿童文学批评中一直都有重“儿童”还是重“文学”的争论。有批评家(如Townsend,1977)认为,好的儿童文学“不仅必须取悦儿童,还必须在其自身意义上是一本好书”(Hunt,1984:55)。由于“好书”的评判标准是由成人制定的,于是儿童文学必须服从成人对“好”文学的普遍要求。但当代越来越多评论者(如上文提到的Wall、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朱自强等)指出,儿童文学应该把儿童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在儿童和成人这双重读者中,儿童才应该是儿童文学的主体读者和裁判。据此,在儿童图画书的戏仿中,儿童读者同样应该是第一位的,不能为了讨好成人而牺牲儿童读者的权益。
为了避免儿童图画书中的戏仿忽视儿童读者,沦为仅仅是对成人的献媚,无论是图画书作者还是共读的成人读者都可以采取一些策略,使儿童也能够参与到戏仿的解码中来。虽然无法识别戏仿的儿童读者也能享受阅读,但对戏仿的解码无疑会使他们对作品获得更多的乐趣和更完整的理解。同时,对戏仿的识别和欣赏还能够使儿童从中获得一种力量和权力感(Beckett,2001:192),不仅有利于他们的心理发展,也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
对图画书作者来说,适当使用一些文本策略能够使儿童读者更容易识别戏仿的使用。对同一作品的反复影射即是一种方法,在图画书中尤其可以运用图/文双重媒介进行影射。比如,在前文提到的《走进森林》这本图画书中,布朗不仅一开始从故事情节上戏仿《小红帽》,在故事快结束时,图画中的小男孩还穿上了暗示小红帽的红色外套。图/文的双重影射使戏仿的意图更加明显。另外,在戏仿经典绘画时,用动物替换原画中的人物是一种极为方便的手法,这样儿童读者“即使不能在更高深的层面解码戏仿,至少能够识别出戏仿的意图,并且欣赏对原艺术作品的幽默和戏谑处理”(Beckett,2001:191)。此外,Beckett(2001:191)还提到,使用博物馆或美术馆作为故事背景,或把戏仿的图画置于相框里挂在墙上,也更能让儿童产生文本之外的联想,进而对戏仿进行解释和理解。事实上,当戏仿的图画没有被加上画框出现在图画书中时,即使是成人读者也可能很难识别出来。
为了使儿童读者识别和欣赏戏仿,共读的成人也应发挥重要作用。成人读者比儿童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因此在图画书共读中,他们应该作为图画书和儿童之间的中介,引导儿童了解戏仿和被戏仿的原作,鼓励儿童积极参与到戏仿的解释中来。这就要求一种谈话式的阅读(dialogic reading)。谈话式阅读是由Grover J.Whitehurst等人首先倡导的一种图画书共读方法,主张成人和孩子用互动的方式一起完成故事的讲述。在谈话式阅读中,成人是提问者、引导者、倾听者和回应者,使儿童积极地参与到故事讲述之中。不少研究者(如Whitehurst,et al,1994)发现,谈话式阅读对提高儿童的口头叙述能力、读写能力有很大帮助。在对戏仿图画书的谈话式阅读中,成人可以提示儿童戏仿的存在,并针对戏仿进行交流,鼓励儿童对戏仿和被戏仿的原作进行对比,探讨戏仿的意图和意义等等。这样,儿童读者才能够从戏仿中获得更多的乐趣,并对作品产生更完整的理解。
结 语
佩里·诺德曼等(2008:155)指出,“最好的儿童文本既可以用简单的字眼来理解,又不会像许多童书那样过于简单。这些文本允许读者以更复杂的方式回应文学,从而产生更复杂的理解,并常常通过独特的构建方式鼓励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发展出更复杂的回应”。就此而言,戏仿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戏仿带有对经典的致敬、戏谑或嘲讽,引导读者在新的语境中以新的视角看待后者,并展开对话。上述研究中,儿童图画书通过戏仿建立起多层次的意义,为双重读者提供不同的乐趣,也为成人和幼儿读者在共读中进行知识交流和传递创造机会,使他们都积极参与到作品的阐释和解码中来。作为图画书主要也是最重要的读者,儿童对图画书的阅读往往是多次的、反复的,戏仿的丰富内涵能够鼓励他们不断在文本内外探索,并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获得更充分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戏仿策略的图画书作者(通常是成人)没有在智识上俯就儿童读者,而是把他们放在和成人平等的地位上,引导他们走上知识和智慧之路。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