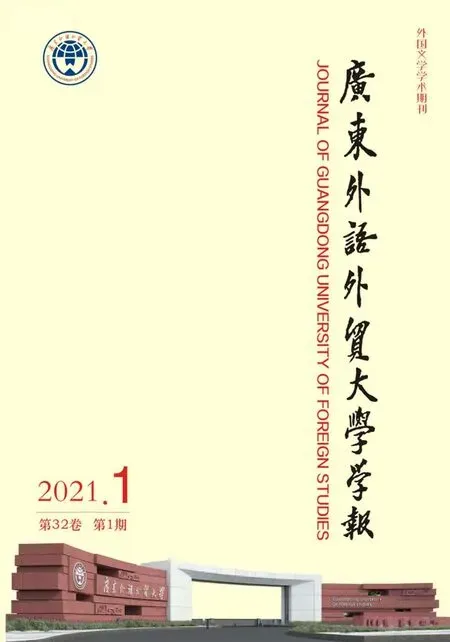孤独抗争还是道德虚无:麦金太尔社群主义视阈下的《秀拉》
辛珏如 王羽青
引 言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秀拉》(Sula)发表于1973年,该小说一经出版就在美国文学评论界引起轰动。在莫里森冷静客观的笔触下,小说同名主人公秀拉的放荡不羁和桀骜不驯跃然纸上,成为非裔文学史上一个鲜活的艺术形象。读者们对秀拉这个极富艺术张力的人物形象一直众说纷纭,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秀拉。如简·弗曼(Jan Furman)(1996:23)认为《秀拉》是对“自我的庆祝”;约翰·N·杜瓦尔(John N. Duvall)(2000:49)认为《秀拉》探讨“那些无法恰当表达自己声音之人的痛苦”;蒂莫西·B·鲍威尔(Timothy B. Powell)(2015:53)却认为“秀拉和佩科拉(《最蓝的眼睛》中的主人公)对身份的追求具有讽刺意味,在她们的行为中没有英雄,没有胜利,没有救赎”;中国学界李喜芬(2005:80-83)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赞扬秀拉对自我的执着追求,但也指出她割断与本民族文化联系的弊端;郭棲庆和郝运慧(2011:56-62)从尼采哲学的角度解读《秀拉》,认为秀拉对男权和黑人社区传统的颠覆中蕴含着重建的力量,但她因颠覆得过于猛烈而付出惨重的代价;荆兴梅(2013:102-107)把秀拉解读为美国的存在主义者,并把秀拉的为所欲为与美国的反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李贺青(2016:59-67)把秀拉解读为黑人女性的奥德修斯,分析秀拉追寻自我的探索旅程,指出莫里森在女性成长小说情节模式方面的新突破。在有些学者眼中,秀拉俨然成为时代的女勇士。这种解读一方面是由于受到黑人对邪恶的辩证态度的影响,“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看,非洲人对于善恶的判断自有一套高度复杂的体系,更准确地说,他们对善恶并不做区分”(Lippmann, 2009:3)。比之于其他文化,非洲文化更加强烈地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善恶并存的两面性。另一方面,这种解读方式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它源于现代社会方兴未艾地对自我的探索和尊重以及对多元价值观的肯定。无可否认,秀拉的反叛言行有摧枯拉朽的气势,孕育着积极的重建力量。然而,在秀拉猛烈的颠覆下,伦理美德的价值何在?秀拉式的反叛造成的效果是否会事与愿违?这些问题学界迄今未做充分探讨,值得读者进一步深思。因此,文章将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以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在《追寻美德》(AfterVirtue)中的社群主义思想为理论参照,从德性、社群归属、人生叙事统一性三个视角来分析小说主人公秀拉,并尝试回答以上问题。
作为黑人女作家,莫里森尤为关注黑人女性在种族歧视与男权社会中的双重边缘地位,在多数作品中诠释黑人女性对自我主体意识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在秀拉身上表现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全然否决,引人深思。作家“非人格化”的客观叙述使《秀拉》的读者面临积极主动进行道德评价的任务:传统伦理道德与个人权利,孰轻孰重?莫里森借小说引发的这个道德评判,颇为先知先觉,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政治哲学领域的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峙,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早在17世纪,自由、生命和财产权就被洛克(John Locke)视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被置于神圣的位置,洛克也因此被公认为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奠基者。在现代性的过程中,道德等一切传统权威均遭到质疑和解构,自由主义几经沉浮后终于成为现代西方世界的主流思想,它以多元价值观的共存为基础,坚持权利本位,倡导人们对各种善观念和生活方式兼容并蓄。在自由主义被普遍认同的现代社会,这种对个人权利正当性和优越性的肯定体现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推崇。但无可否认,与此相随的则是善与道德这些概念的日益模糊和相对主义趋势。此种趋势可追溯到启蒙时期的休谟(David Hume),他认为在道德判断中发挥作用的是人的主观情感,道德判断的标准至此走向相对主义。虽然人们在启蒙精神的引导下对前景充满乐观,现代自由主义精神也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孕育而生,但战争纷争犯罪等丑陋却让人们无法回避现代社会道德缺失的状况。在此背景下,对自由主义持批评态度的社群主义应运而生。它的代表人物之一麦金太尔对现代性语境中的道德危机倍感担忧,在他影响深远的代表作《追寻美德》中,麦金太尔认为现代社会的道德语言正处于混沌无序状态,这也造成现代个体在道德上缺乏选择标准。面对当代道德语言的相对主义趋势,麦金太尔极力主张回归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伦理传统,回归到传统美德以及所属社群的共同善,强调社群以及传统的积极价值,以求摆脱当代人们道德观的混乱和虚无,走出当代道德的困境。
德性的缺失与自我迷失
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中以德性为切入点反思现代社会的道德颓废,德性、社群归属、人生叙事统一性是个体认同与行为评判的基石,德性在其中处于核心位置。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人的德性是既让人变得良善又让人更出色地完成活动的高贵精神品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1992:3)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的真正区别在于人拥有感知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等等的能力”。正是人的德性让人与禽兽相区别,这和荀子所说的“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的道理不谋而合。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行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出于个人的意愿。当情感和欲望等灵魂的非理性部分服从理性的指导时,德性就产生了,否则,“失去自控的人就会出于欲望而行为”(Aristotle, 2013:32)。有了德性,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时就能明智地选择,既无过度也无不及,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还是个人实现至善/幸福的首要条件。可以说,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是伦理生活的中心。但在规则主导着道德哲学的现代,德性却被人们忽视。麦金太尔继承并倡导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他认为现代的规范伦理学所设立的诸多外在伦理规则对缺乏内在德性的人没有实质的约束力量,要走出当代道德规范苍白无力的困境,必须拯救已被边缘化的德性,重建德性的权威。
然而,忽视传统伦理道德,甚至以反道德的态度对待道德,这是现代主义思潮的特征之一。在此思潮中,文学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被有意无意地抹杀,这意味着文学道德教诲功能的边缘化,在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为我们解读秀拉这一人物提供了另一独特路径。在德性论的观照下,秀拉种种行为中隐藏的极端个人主义特征昭然若揭。小说中,莫里森的寥寥数笔生动地刻画出秀拉的性格:“她信马由缰地听任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暴露无遗……她甘心体验痛苦,她也甘心让别人痛苦”(莫里森,2005:218)。“她没有中心,没有一个支点可以支撑其成长”(莫里森,2005:219)。秀拉所缺的这个中心和支点,正是亚里士多德笔下“灵魂中具有理性原则的部分”(Aristotle, 2013:19),它能帮助个体遵从理性,对欲求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应。秀拉的灵魂中缺乏理性的部分,她的内在德性也就相应地缺失。这个缺陷人格的形成与匹斯家的单亲背景以及母亲汉娜对秀拉的忽略不无关系。少年秀拉在缺少爱的环境下成长,又缺乏对她实施正面教导的长辈,她天性中任性顽劣的一面如野草般毫无节制地蔓延。秀拉放纵的性格早在其童年时代失手溺死“小鸡”的细节中就初露端倪。一心追求快乐的秀拉在此场景中把“小鸡”“抡起来转了一圈又一圈”(莫里森,2005:178),意外发生后,年幼的秀拉懦弱地选择沉默来掩盖事实,这个飞来横祸也成为秀拉成长道路上的标志性事件,令其进一步失去道德上的支点,阻碍其形成健全的人格。后来秀拉无动于衷地观看母亲被火烧死,这也正是她内在德性缺失的表现。成年后秀拉把此种漫无矩度、一味标榜自我的放纵发挥到极致。她的极端方式使人联想起希腊神话里的阿喀琉斯(Achilles),他虽抱着为挚友复仇的初衷,但在仇恨中他对特洛伊人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连河神也忍不住怒斥他丧心病狂。与此相似,秀拉在手段方式的选择上陷入非理性状态,她虽自我定位为反抗白人和黑人男性双重压迫的女斗士,不愿滑入黑人女性传统生活的窠臼,但她实际上缺乏对黑人女性同胞弱势处境的感同身受,急于摧毁旧世界的迫切渴望让她无法自觉地培养德性,实践智慧的缺失导致她对实现目标应采取何种恰当手段更加缺乏明智的选择。在外的求学经历让秀拉比社区同龄人更为视野开阔,本该有助于她睿智与审慎性格的培养,却反而助长她的目空一切与放纵。她将精力空耗在极端的宣泄中,她亵渎上帝,去教堂不穿内衣,毫无愧疚地将祖母送入养老院;她追随性解放潮流,和“底层”几乎所有男性有染,甚至连好友耐尔的丈夫也不放过。她在性爱中赤裸裸的欲壑难填令她成为麦金太尔笔下的“精神紊乱者”。精神紊乱在麦金太尔看来“就是追求各种生理欲望的满足并为了这种满足而追求各种激情的满足,而不是受节制、勇敢、正义这些美德的规导,以使生理欲望和激情得到合理的转化”(麦金太尔,1996:105)。然而,秀拉在放纵的性爱中并没有如期而至的幸福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幸福就是完满自足的至善,正是灵魂的德性让我们得以实现这种美好的生活。没有合乎美德的灵魂,秀拉也就失去达到幸福/至善的首要条件。
德性的缺失让秀拉与耐尔的友谊不可避免地走向破裂。在秀拉身上,甚至连友善这种德性的“影像”也踪影难寻。当她扬言要把镇子撕成两半时,她实质上是把对黑人群体弱势困境的无奈错误地转化为对同胞手足的仇恨。怀着这股恨意,秀拉沦为兽性的存在,伤害周围人甚至好友却不怀一丝愧疚。莫里森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她在小说创作时特意描述“耐尔外婆是妓女”这个家庭背景,她认为,她如此描述的目的是为了指出耐尔身上具有外婆叛逆的基因,从而阐明秀拉与耐尔这两个表面截然相反的女性之间建立友谊的合理性 (Taylor-Guthrie, 1994:13)。虽然少年时的友谊令秀拉和耐尔相互温暖,也因此有了河边挖洞这幕“极具象征意义的‘结拜’仪式”(王守仁、吴新云,1999:57)。虽然十年后秀拉的回归让耐尔的心情也跟着明快起来,但两人的友谊最终还是破裂。她俩友谊的破裂在表象上似乎是多年不同生活经历所铸就的迥异价值观碰撞的结果,但深究起来,不难发现两人友谊破裂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其一,秀拉的友谊观以自我为中心,她已丧失关爱他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年少时秀拉和耐尔曾遭遇白人男孩的欺负,虽然秀拉为保护耐尔挺身而出,不惜割破自己的手指,但总的来说秀拉只在乎自身的存在感。实际上,秀拉极端的性格早在少年时代的割指事件中就现出端倪,所以她一厢情愿地寻找“符合她概念的朋友”(莫里森,2005:220),没有意识到“友谊更在于去爱”(Aristotle, 2013:106);“她把耐尔看成另一个版本的自己,在她满足自己的冷酷无情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中,勾引好友丈夫,因而失去了好友”(Powell, 2015:52)。其二,两人的友谊中并没有共同信奉和追求的善。在麦金太尔看来,真正友谊必须有共同追求的善(麦金太尔,2008:178),而秀拉的狂野令她无法奉行任何特定的善。秀拉无异于尼采式的狂人,视传统伦理为虚伪,抨击人道主义道德为软弱,宁愿以藐视和破坏来表明自己与传统的黑人女性划清界限,看似超脱,实则不仁。临死前,她居高临下地嘲讽耐尔的凡俗,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负,德性的缺失导致她的善恶观念混淆,也让她终其一生无法协调理性与感性欲望,迷失在自我追求的幻象中。可以想象,在一个充斥着秀拉式狂人的社会,个体将自己的价值观奉为圭臬,只从社会攫取个人利益,人与人之间缺乏共识和共善,社会将由母体沦为麦金太尔所指的冰冷的“竞技场”(麦金太尔,2008:220)。
现代社会物质的极大繁荣并没有伴随着道德的进步,自由主义者主张的道德中立更是令道德不得不为个人权利让路,也意味着美德概念趋于模糊。在《追寻美德》中,麦金太尔把利益分为内在利益与外在利益。外在利益指有利于个体的财富、名声、地位等,而内在利益指有利于参加实践的共同体的利益。无可否认,当今人们的实践活动更注重追求外在利益,而非麦金太尔所强调的内在利益,德性也就似乎变得无足轻重,善恶的评断已由外部的客观力量转变为个人心灵和喜好的产物。秀拉固然拥有选择自己钟爱生活方式的自主权利,秀拉特有的我行我素的孤傲也不因面对死亡而有半分消减,但这种个人自由和权利不过是根植于人的自利性。当利己的合理性被秀拉式的自由主义者夸大并发展到极端时,在此情形下的自由更接近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的最基本的自由观:物体不受阻碍地自由运动,自由人也随心所欲做自己欲求的事。在放任的自由中,个体过分自主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人们之间的相互疑惧,或许“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霍布斯,1996:93)。秀拉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可称是现代性道德危机的缩影,危机的原因之一在于外在道德规范越来越形同虚设,对内心具有约束力的德性的回归正是对这种道德困境的回应。
自我身份的模糊与自我迷失
在《追寻美德》一书中,麦金太尔以古希腊英雄时代为例证来阐明个体与社群的关系,作为社群主义者,麦金太尔维护社群在个体自我认同中的优先性,强调个体的社群成员身份。社群也即共同体,社群的范围可大可小,既可以是家庭村落也可以是种族阶级国家等。不同的社群主义者对于社群与自我的关系尽管理论表述略有不同,但他们都认为社群决定着个体的自我理解。例如,另一代表人物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提出“构成性的自我”概念,即自我的本质由所在的共同体属性构成,自我从属于所在的共同体。麦金太尔则在《追寻美德》中十分推崇荷马史诗中的英雄社会高度明确的角色分配,他认为,英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角色,人们对自己被分配的角色和责任义务非常清晰,个体通过在各种团体中的种种角色界定自己(麦金太尔,2008:136-139)。在其笔下,“角色”是指在某个社会或团体中的位置以及与这个位置相随而来的职责。也就是说,个体领会自己在各种团体中的种种特定位置,并自觉履行相关的职责,自我和各种社会角色相统一。因此,在所属社群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个体通过明确自己在其中的独特位置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并在履行应尽的职责中实践德性,促进社群的共同善。
黑人的都市生存空间与种族偏见的氛围成反比,种族歧视越严重,黑人的生存空间就会越狭窄(庞好农、刘敏杰, 2019: 70)。童年时期接受的黑人传统文化教育滋养着莫里森的精神世界,她也肯定黑人社区在黑人个体身份认同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点与社群主义者对社群的看法相似。莫里森曾指出,秀拉的缺陷在于“割断和社区他人的联系,把自己引入危险的地带”(Taylor-Guthrie, 1994:67)。黑人社区在莫里森的小说中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它是《秀拉》中黑人被白人忽悠而得到的山上那块贫瘠的土地,是《所罗门之歌》中房屋东倒西歪的城南黑人居住区,是《爱》中频遭自然灾害侵袭的“上滩”。无论是哪里,它们都是黑人历史上受到白人压迫排挤的产物,具有居住条件恶劣、居民饱受贫困与失业困扰的共同特点。在莫里森看来,黑人社区犹如黑人的母体,大家在此抱团取暖,这里某一家人的孩子就是社区所有人的孩子,因此她在《秀拉》中描绘社区人在夏娃的艰难时期对她一家人的救济。但同时她也敏锐地捕捉到黑人社区的缺陷,这种缺陷更多地源于人性固有的恶,具有普适的意义。例如,她在《最蓝的眼睛》中无情地揭露社区人对佩科拉悲惨遭遇的漠然,在《宠儿》中隐晦地暗示赛丝的弑婴悲剧源于社区人对她们一家好运的妒忌心理,在《天堂》中痛心地叙述鲁比小镇的男黑人由于心胸狭隘而酿成的屠杀。对黑人社区她可谓爱之愈深责之愈严。总的来说,莫里森仍然认为黑人个体身份的建构离不开对个体有哺育之恩的社区,在访谈中她曾说:“有成千上万的小城,那儿是大部分黑人的居住地,是黑人的精神源泉,就是在那里我们构建了自己的身份”(Taylor-Guthrie, 1994:12)。
在自我身份的确认中,秀拉片面地认为黑人社区的传统价值扼杀自我个性,以为脱离社群才能找到自我,把黑人社群的成员身份视为个人认同的羁绊。可以说,其个人认同中缺乏社群认同这个维度。《秀拉》中的几位女性人物,最能体现麦金太尔的社群主义自我身份观的,非夏娃莫属。虽然夏娃不忍心看儿子在毒品中消耗生命而将他烧死的行为该受谴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夏娃身上仍洋溢着浓浓的母爱。当她被丈夫抛弃、处于生活绝境时,为养大孩子,她不惜让火车压断一条腿以换取保险金。正是这种母爱和责任感,造就她顽强的生存意志,让她能克服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坚强地履行自己作为黑人母亲的义务,对生活中的善进行探索。作为黑人社区的成员,夏娃在生活好转后,收养孤儿,为流浪汉提供栖身之处,这种博大无私的爱来源于夏娃对黑人社区关爱他人传统的恪守,同时她对家庭和社区所赋予她的角色和义务有着高度责任感。秀拉极力摒弃的,恰好是夏娃用心承载的传统。秀拉畏惧黑人女性庸碌俗套的生活,她很早就意识到黑人女性身上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双重枷锁——“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自由和胜利都没有她们的份”(莫里森,2005:49)。秀拉在如此残酷的生存境况下对革新的追求和对自我身份的诉求无可非议,但她的致命之处在于她完全抛弃黑人群体关爱互助的传统,抛弃养育她的黑人社区,以没有任何社群价值归属的我行我素来否定自己的种族身份。在小说中,秀拉把处于闭塞生活中的黑人女性比作囿于蜘蛛网的蜘蛛,却没意识到她本人也走向以破坏母体来突显自身的另一个极端。但是,秀拉没能清醒地看到,一旦她否认黑人社群的养育之情,否认自己的种族身份,她连自己是谁都无法清晰界定,她脱离母体式的自我追求注定无果而终。
一方面,从个人的层面上讲,个体的幸福和尊严与个体作为某个文化群体的成员这一身份息息相关。在缺乏稳定归属感的社会中,个体因内心的动荡不安而难以获得真正的幸福感。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甚至认为,归属于某个特定的群体也是人类众多基本需求中的一种(Berlin, 1980:257)。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认为,文化成员身份作为一种基本善(primary good)在个体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个体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决定才有意义,因为这是某个文化所认可的生活方式(威尔·金里卡,2005)。秀拉因惧怕个人会被社群湮没而意欲凌驾于黑人文化群体之上,她因成为社区人眼中的异类而一度促进社区人团结的事实昭示着她注定是黑人社区里孤独的被放逐者。另一方面,从黑人族群的层面上看,秀拉式的自由主义者们在张扬个性的过程中拒斥本民族世代沿袭的传统文化并过分追求凌驾于黑人族群集体价值之上的普遍化权利,这在无形中淡化黑人族裔的文化特殊性,甚至消解本族群文化身份,使黑人群体更进一步陷入文化生存困境。
人生叙事的矛盾与自我迷失
在阐明理解自我必须先理解自我所处文化背景的同时,麦金太尔提出他的人生叙事统一性理论,作为理解个体行为的依据。人生叙事的统一与可理解性,离不开对行为主体意图或目的的考察。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传统带有很浓的目的论色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事物内在的目的规定着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在社会领域,人的每一种实践都以特定的善为目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TheNicomacheanEthics)开卷之首,亚里士多德说,“每一种艺术,每一种探索,每一种行动,每一种追求,都被认为是指向某种善”(Aristotle, 2013:7)。麦金太尔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体系中,人通过接受道德箴言的指导,发扬德性并使自己从自然的未受教化状态转变为能认识自己的本性并达到真正目的的人。而现代社会伦理学已然抛弃亚里士多德目的论,也就是说,把“能认识自己本性并达到真正目的的人”这个目的因素排除了,其后果就是道德箴言与戒律对未受教化之人缺乏权威性,麦金太尔于是倡导继承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人生在麦金太尔眼中具有目的性,虽然未来总是充满种种可能性,但同时我们总在生活中探索寻求着某种“善”,在对这个终极目的的追寻中人生所经历的不同事件被视为具有整体的意义。他在《追寻美德》中说:“所有的现在都渗透着对某个未来的某种想象,并且这种未来的想象总是以一种目的(telos)——或多种多样的目的或目标——的形式呈现自身,而现在的我们要么正向这个目的运动,要么没有……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可是,我们的生活具有某种朝着我们的未来策划自身的形式”(麦金太尔,2008:244)。麦金太尔又把人生看作文学故事,他说:“人不仅在他的小说中而且在他的行为与实践中,本质上都是一种讲故事的动物。他不是天生地而是通过他的历史逐渐变成了渴望真实的讲故事者”(麦金太尔,2008:244)。这些不同的人生故事构成一个叙事整体,指向某个终极目的,形成麦金太尔所强调的人生叙事统一性。在麦金太尔看来,这种统一性体现为个体被要求要为他的人生的种种行为提供某种可理解的解释,使他人能够理解为何个体在不同的情景中、在不同的行为描述中仍是同一个人(麦金太尔,2008:246)。也就是说,人生叙事统一性的关键在于可解释性,个体不仅对自己来说是可以解释的,对他人来说也是可以解释的。
如果把秀拉人生的种种不同事件视为一个叙事系列:割破手指吓跑白人男孩、失手溺死小鸡、外出到大城市求学、和不同男人发生关系、强行送外婆进养老院、和好友丈夫有染、爱上阿杰克斯并意欲占有他、临死前的倔强倨傲,这些不同事件因其意图的前后矛盾而无法形成麦金太尔所强调的人生叙事统一性。叙事系列中的前六个和最后一个事件都显示出秀拉颠覆传统道义、自由主义式的个性,也符合秀拉意欲挣脱种族和性别桎梏的人生意图。但第七个叙事事件“爱上阿杰克斯并意欲占有他”在此叙事系列中显得突兀,像链条上脱节的一环。在第七个叙事事件中,秀拉似乎走上回归传统女性的道路,对阿杰克斯的专一和痴迷犹如初坠情网的女子。在没有遇见阿杰克斯之前,秀拉的世界中并没有两性情感上的爱,只有放纵的性爱生活。当她情不自禁坠入情网时,她才体会到传统两性之爱的忠贞和占有,妄想以柔情来拴住同样放浪形骸的恋人,这时的她与社区中其他黑人女性并无二致。一直以来,秀拉以放荡不羁的行为展现她颠覆男权与社群传统价值观的意图,但在“爱上阿杰克斯并意欲占有他”这个叙事事件中,秀拉的言行明显迥异于她颠覆的意图。或许阿杰克斯的出现,正是秀拉在追求自我的旅途中无法战胜的诱惑。如果阿杰克斯愿意接受秀拉浓烈的爱并安顿下来,秀拉所谓的追寻自我之旅会否戛然而止?秀拉是否也会变成她所藐视的芸芸黑人女性中的某个个体?抑或因彼时秀拉已遭到社区人的集体排斥而倍感孤独,因而把擒获恋人的心当作重被社区接纳的狡黠手段。因此,综观秀拉的整个人生叙事系列,“秀拉爱上阿杰克斯并意欲占有他”这个叙事事件所体现出的意图与她颠覆的意图产生抵牾,这个叙事事件放在其人生叙事整体中也变得无法理解,造成秀拉人生叙事系列的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说,秀拉意欲颠覆男权价值以及突破禁锢黑人女性的牢笼这个看似确定的信念也就变得摇摇欲坠。
黑格尔(G. W. F. Hegel)曾说,“人就是他的一串行为所构成的”(黑格尔,1979:14)。一方面,具体的行为内容虽各不相同,但透过不同情境下种种不同行为显现出来的,应是个体人格的同一性,在这人人相异的人格中彰显个体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人生的种种不同行为能否构成麦金太尔笔下可理解的人生叙事整体,其先决条件也正是这种人格的同一性。人生既被麦金太尔视为叙事整体,在他看来必有对某个终极目的“善”的追寻。诚如麦金太尔所言,个人要理解并探寻“善”,只有在他所继承的传统中。反观秀拉的人生,在抛弃社群及传统的状态中,她追求自我的旅途中透过种种行为体现出的价值观念实质上前后矛盾,造成其人生叙事的矛盾性。缺乏坚执的人生信念,秀拉实质上陷入游移不定的人格矛盾中,她所追寻的自我必然也前后抵牾。
在莫里森的作品中,众多黑人女性人物处于白人强势文化的冲击以及男权的压迫下,或是心灵扭曲,或是命运多舛。宝琳爱雇主家的女儿远胜于爱自己的女儿;维奥莱特跟随大迁徙的人潮来到大都会谋生,却遭丈夫背叛;派拉特因身体构造异于常人,遭到同族人的孤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着旺盛原始生命力的秀拉无疑给看惯黑人女性不幸遭际的读者带来一丝慰藉,正如《她们眼望上苍》(TheirEyesWereWatchingGod)中勇于反抗传统习俗束缚、不断尝试寻找幸福的珍妮,她们的故事都彰显黑人女性自我觉醒、尝试打破成规的顽强精神。这种敢作敢为的精神恰似李有成(2015:23)在《逾越》一书中对逾越的描述:“逾越意味着跨界……挑战既有的规范,改变原先建立的秩序。换句话说,逾越也意味着否定——否定现状,尤其是不公不义或充满偏见的现状”。 但正如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只能为珍妮安排孤身一人回到伊顿维尔这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结局,莫里森或许也预感到秀拉缺乏引领黑人女性群体走向解放的特质,因而无奈地为她安排早逝的命运。抛弃社群,轻视“姐妹情谊”,意味着秀拉抛弃基本的伦理道德,也意味着她无法为黑人女性群体树立起值得效仿的榜样。
结 语
秀拉的果敢与自主让人耳目一新,但从麦金太尔社群主义理论的角度剖析秀拉,秀拉的种种缺陷也促人警醒。德性缺失让秀拉失去内省与自律,导致她把放纵狂野的生活视为追寻自我,把社群归属视为对自我的束缚。在割裂与社群的纽带后,她无法领略黑人社群共同生活中才能发现的共同善,无从发现自己的道德身份,从而造成其人生叙事整体中行为方式的前后矛盾。自由并不意味着责任的匮乏,在背离传统伦理道德的自由中,秀拉虽力图建构自我身份,但其脱离所属社群的无根状态让她失去约束,从而肆意践踏黑人社群的传统与美德,其所追寻的目标也沦为空洞的自我。20世纪7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逐步在全球发展成为势不可挡的主导思潮。《秀拉》恰好发表于自由主义兴盛的前夕,莫里森似乎借小说隐隐预示,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对传统道德的过分否定,对价值中立、包容异己以及权利本位的过分宣扬,人的精神沦落将不可避免。秀拉的故事虽具有黑人族裔的独特性,但莫里森似乎借秀拉的故事来影射普遍性的道德沉沦。在道德世界里,古老的德性失去往日的高贵,道德语言不可避免地趋于含混,走向道德相对主义的路途上,现代人在精神上似乎左右摇摆、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