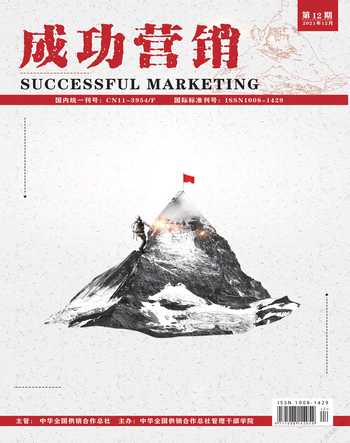智能合约的法律性质分析
摘要:智能合约则是区块链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全新合约样态,其自动执行的方式能够大大提高交易的效率。而对于智能合约性质的争论在学界也开始兴起。本文希望通过对智能合约概念、特性以及适用场景等内容的介绍,来辅助分析智能合约的法律性质,并且将其与传统合同制度中的内容进行简要对比,以此加深对智能合约的理解。
关键词:智能合约;法律行为;合同
1 智能合约的含义及其原理
2008年,一位名为中本聪的学者发表了一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的论文,提出了支持比特币运转的技术——区块链。区块链技术是基于密码学、计算机科学以及数学等学科的一门综合性的技术,而本文所要研究的智能合约正是基于这一技术所产生的一个新事物。在相关机构制定的《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2016)》中指出,“区块链1.0”阶段,呈现为整个区块链围绕着数字货币运作。而发展至“区块链2.0”阶段时,区块链技术的适用范围将被扩大至数字货币外的领域。在2018年发布的白皮书中还强调,要不断拓展区块链的适用范围,就需要不断创新演进和优化共识机制、智能合约、跨链技术等核心技术。[1]由此可见,智能合约的应用价值在被不断强化。
1.1 智能合约的含义
1.1.1 最初的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的概念由尼克·萨博提出,他将其定义为“一套以数字形式定义的承诺,包括合约参与方可以在上面执行这些承诺的协议。”[2]他用自动售货机为典型的例子,与最简单的计算机语言逻辑“if……then”相类似,如果有消费者将代表着承诺的硬币投入自动售货机中,机器就开始了不可逆的合同履行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智能合约就是一份或者数份可以自动履行的协议。但根据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自动售货机仅实现了卖方的自动履行,只有实现了对于双方的自动履行,才能够称得上是“智能合约”。[3]在这个阶段,由于技术的限制,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合约的实现难度很大。
1.1.2 区块链背景下的智能合约
借由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自动履行的合约”成为现实。以以太坊(Ethereum)为代表的技术平台,给智能合约的开发者们提供了各种图灵完备的编程语言。开发者们编写的代码通过链上节点的共识程序嵌合入链,用户能够在应用层面审视并使用智能合约技术。智能合约也因区块链技术的固有属性而具有了匿名性、自动性、确定性和不可撤銷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能够极大程度上提高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因此广泛应用于金融交易甚至是慈善事业。在区块链应用中,智能合约被归结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合同型智能合约、执行型智能合约以及单向型智能合约。[4]不同类型的智能合约有着不同的使用场景和订立流程。合同型智能合约,是具备传统合同要素的智能合约,一般由专业机构作出或提供,由相对方进行选用的合同,如果满足合同预先设定的必要条件,则合同执行。执行型智能合约,通常是当事人在编写智能合约之前已经约定并达成合意,此时合约充当的更多是工具性的作用。而单向型智能合约多用于遗嘱设立、公共治理等一方意志能够决定法律后果的情形中。
2 智能合约是否是法律行为
随着智能合约的普及,学界就智能合约是否是能够被民法典合同编体系所覆盖的问题开展了许多研究。但根据体系来看,合同的上位概念是法律行为,如果跳过对智能合约是否是法律行为的分析,径直讨论其是否适用合同编的相关内容是不合理的。因此这一部分主要就智能合约是否属于法律行为展开论证。
2.1 智能合约与法律行为的本质
弗卢梅在《法律行为论》中对“法律行为的概念”的定义是,所有在法律秩序中形成的行为类型的抽象,就法律秩序针对这些行为类型所规定的内容而言,其目的在于使个体能够以意思自治的方式通过制定规则来形成、变更或者消灭法律关系,也即旨在实现私法自治原则。[5]笔者将这段话总结为三个要件,一是以在法律秩序中为前提,二是意思自治,三是制定规则。本文分析判断智能合约这一新形式是否属于法律行为的范畴,就将先从上述三方面进行论述。
2.1.1 区块链仍需法律束缚
从最初的设想来看,区块链技术所对应的是去中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即区块链的支持者们认为未来的社会发展将舍弃国家、政府、教会等中心节点,此时的状态就可以被称为去中心化。这种去中心化状态能否适用法律进行监管?落实监管后其还是否是原本意义上的去中心化?这些对于智能合约乃至区块链来说都是关键问题。区块链的拥趸们认为在链上,法律即代码,代码即法律,在这样的环境中技术完全可以取代法律,以作为链上主体之间构建信任的手段。其实不然,区块链技术虽然能够使全球的各个节点相链接,但是作为互联网技术来说,还是无法摆脱其固有缺陷。以The DAO事件为例,黑客就是利用了以太坊代码中的递归漏洞转移资产,最后导致以太坊社区作出了硬分叉的决定。另外,区块链的匿名特性,也会被不法分子当作非法交易的避风港。区块链的设计者们认为代码能够绝对公正公平,但是他们忽略了代码的创造者——人。人为因素的介入就无法百分之百保证代码的绝对正义。因此,在尊重区块链去中心化运行的基础上,需要将其纳入法律秩序的框架之下,尽管区块链技术反复强调其去中心化的特征,但是从其共识机制的设置可以看出,要完全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去中心化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形成有限制的去中心化存在可行性。但是对于在区块链里面的交易等行为来说,是更加偏向私法领域的行为,是将这些行为认定为现实法律体系中的法律关系,还是所谓的纯粹不产生法律效果的关系,这对于智能合约的性质认定具有重要意义。私法领域中,所谓法律关系,是与普通民事关系相对应之概念,调整的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财产关系。将这些权利义务关系抽象出其上位概念,可以将其本质定义为人格关系。虽然由于区块链的匿名性,导致区块链中的节点人格关系没有现实中一目了然,但是在区块链内部构建时,各个节点之间或多或少形成了契约关系,例如对于框架及共识的协议。这种各个节点间复杂的契约关系就学者将其总结为“准组织”的特性。[6]因此,区块链中并非不存在人格关系,而是被隐藏在一串随机生成的密钥之下,密钥与合约主体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追溯到当事人。人格关系的存在为法律关系的适用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智能合约的法律性质分析提供了路径方向。
2.1.2 智能合约的意思自治
智能合约的自动性并不能否认智能合约中的意思自治要素。虽然在合约效力判断、执行以及违约责任等依赖智能合约底层代码等内容受制于区块链的底层运行逻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智能合约在生成的时候,关于合约的内容是充分尊重合约参与方的意思表示而一致达成的,以上文所提到的三种智能合约为例,执行型智能合约和单向型智能合约本身就是有现实合意或是自我意志为基础,智能合约在此是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实现方式而存在。对于合同型智能合约来说,合约的参与者也已经了解了这些智能合约的特性,并且这经过商议最终同意这样的运行方式,这与传统合同中的格式合同有着类似的原理,因此也就不能否认这类合约的意思自治。
2.1.3 智能合约所产生的规则
从法律行为的目的来看,参与法律行为的当事人所欲达到的目的就是在单方、双方甚至是多方之间形成产生法律效力的规则,该规则是参与人之间约束力的来源。由此可见,法律行为在私主体之间起到了法律规范的作用。从这一方面看,智能合约与传统法律行为的差别并不大,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智能合约,目的都旨在形成、变更或者消灭合约参与方之间的某些关系。并且在智能合约所在的区块中进行的交易,都需要根据智能合约中的内容执行,合约内容已然成为智能合约所涉主体所要遵循的规则,这也符合这一要素的表现。
2.2 智能合约的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意思表示就等同于法律行为,它是对法律行为参与者内心意思的宣告,只有将设定法律效果的意志表示于外,才能构成法律交往行为。因此,判断智能合约是否构成法律行为就需要判断智能合约参与方有无作出其意思表示,以及意思表示的内容如何。意思表示的要素通常被分解为行为意思、表示意思以及法效意思等三个方面。对于智能合约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意思表示,本文也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2.2.1 行为意思
行为意思是指表意人有意作出表示的意思要素,该要素表明表意人的外在行动是在其自主意志支配下所作出的。从定义来看,智能合约的参与者所存在的行为意思可以说是毋庸置疑。因为目前的智能合约明显是为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或是提高效率而制定的,参与者有着强烈的意图。而那些没有真正参与订立智能合约规则的用户也在受到全网广播后,对智能合约的内容达成了共識,在应用时会主动输入自己的签名信息以确认交易,希望利用智能合约的优势提升效率和安全性。因此,可以认定参与者存在行为意思。
2.2.2 表示意思
表示意思是指引起事实构成的人是否希望起行为构成表示,也即当事人是否意识到自己作出了“表示”。在采用智能合约的情况当中,就需要联系到智能合约之原理。在智能合约以代码的形式发布,并覆盖有区块链技术的数字签名和时间戳之后,任何一个合约方都能够通过一定的交互方式来了解合约的具体内容,在此区块链中的用户都会对其进行签名验证并进行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在区块链中的任一用户都可能是智能合约的潜在参与者,而且在参与之前,他们都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了该合约所设定的状态。进言之,在他们改变自己账户里的资产或其他内容时,就已经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被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某人在实施行为时明知法律关系将基于自己的行为而形成,这就构成了以推定行为作出的意思表示,即默认。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其他主动参与智能合约的参与者的表示意思可以认定为表示方式明确或是依据先前之交往惯例可以得到的明确的表示意思,属于明示。并且这些意思是由计算机代码所表现,不太可能存在误解的情况。
2.2.3 效果意思
法效意思是指表意人欲依其表示发生特定法律效果的意思。该要素与表示意思的区别是前者要求表意人存在更加具体的法律效果意思。如果将智能合约参与人的表示意思解释为“参与智能合约”这一行为的话,那么法效意思则更加聚焦于该智能合约所欲达成之目的。在目前智能合约应用的场景之中,参与者都带有明确的目的性。以区块链上的艺术品交易为例,智能合约参与人所欲达到的法律效果就是移转艺术家对于该该艺术品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而表示意思的内容则是购买者或艺术家一方表示同意用智能合约形式成立契约。
综上,智能合约参与方的表示存在行为意思、表示意思以及法效意思三个要素,可以构成完整的意思表示。前一部分也阐述了智能合约的原理和运行逻辑符合对法律行为的基本定义,智能合约可以法律行为的框架之中,可以适用法律行为的体系对其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3 智能合约是否是合同
在论述了智能合约可以纳入法律行为的框架之后,在此框架内最类似于智能合约这一表现形式的,应属合同。根据上文对于智能合约的分类来看,其订立的情形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双方已经商定了具体的合约内容,再通过技术手段部署上链,这种情况应属合同,其只是采用了智能合约的表现形式。另一种是一方自行拟定合约内容并部署上链,其他主体通过区块链应用或其他方式参与合约。根据传统法学体系,合同的订立应当符合“要约-承诺”的构造。因此这个部分将主要分析第二种情况,并以要约和承诺的角度判断这类智能合约是否可以归入合同体系。
3.1 要约
《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要约的构成,一是内容具体确定,二是向受要约人表明一经承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首先,智能合约都是由计算机代码所呈现的,其有着明确的语法和语义。而对于受要约人来说,可以通过计算机运行代码或调用相应的语义表来理解智能合约的内容。在目前的应用场景中,智能合约的内容都能够精准反映合约所具备的条款,这使得合约内容在现在的发展阶段来说能够较为明确、具体地呈现给参与者。其次,从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机制可以推断,发布者具备受智能合约内容约束的意思,因为一旦智能合约成立,发布者所持账户就会进行相应的交易。如果没有受智能合约内容约束的意思,那么其就会遭受不可逆转的财产损失。智能合约一旦在区块中发布,就开始了不可逆转的自动执行,只要合约相对人的账户达到某一状态,则进行预先设定的行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智能合约的发布可以被认定为要约。
3.2 承诺
承诺需要满足以下的构成要件,一是必须是受要约人作出且只能对要约人作出,二是承诺表示的内容必须与要约相符。当智能合约发布人将智能合约部署上链并全网广播后,智能合约的调用人在接收到合约内容,并且作出调用行为时,就认定其完全同意了智能合约中所约定之条款,无法进行修改,其所承诺的内容必然与要约之内容一致。由于智能合约的“承诺”展现出事前承诺和事后承诺的双重特性,因此对于智能合约的“承诺”可以界定为一种意思实现。意思实现是指,根据交易习惯承诺无需向要约人表示,或者要约人预先声明无需表示的,即使没有向要约人表示承诺,承诺一经作出,合同即告成立。[7]由此可以将智能合约的承诺认定为意思实现。智能合约的参与者在进行共识的阶段,已经同意了合约中可能发生的内容,而随后智能合约接受方输入签名触发智能合约的行为,则属于以意思实现进行承诺,这样的构造并不违背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
因此,在现有的合同体系中,可以认为智能合约具备“要约——承诺”的构造。
3.3 智能合约之合同属性
從智能合约的表现形式来看,其应归属于广义电子合同的范畴。根据《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之规定,订立合同的形式包括书面、口头和其他形式。而书面形式其中就包括以电子数据交换等方式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另外根据《电子签名法》第二条之规定,数据电文是通过电子、光学等手段生成、发送、接收和储存的信息。智能合约以可编译的计算机代码呈现在合约参与人面前,并且其订立的过程满足传统合同“要约-承诺”的构造。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特性让其与传统的电子合同产生了一定的差别,智能合约的状态能被计算机识别、判定并执行,而传统的电子合同只能在相对方点击“同意”按钮或是输入电子签名后才能继续履行。[8]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智能合约与电子合同的形式有所类似,但是其特性又超出了目前对于电子合同之定义,以将其视为电子合同的升级样态。
4 总结
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智能合约这一技术的普及,但是就目前不同学科的讨论来看,对于区块链这一去中心化的结构是否应该通过法律来进行规制还存在着争议。笔者通过本文的论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去中心化并不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法律仍然应当介入这一新兴结构,以防其因为缺少监管而危害社会。而从智能合约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可以将其纳入法律行为体系的框架,并在传统合同的体系下对于其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智能合约中有很多问题可以通过对现有法律的解释予以解决,但是还有一些底层逻辑的问题,需要静待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提供新的解决路径。
参考文献
[1] 中国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论坛.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研究报告[EB/OL].http://www.cbdforum.cn/bcweb/resources/upload/ueditor/jsp/upload/file/20201110/1604997218359058044.pdf,2018-12-18.
[2] Nick Szabo.Smart Contracts: Building Blocks for Digital Markets[EB/OL].https://www.fon.hum.uva.nl/rob/Courses/InformationInSpeech/CDROM/Literature/LOTwinterschool2006/szabo.best.vwh.net/smart_contracts_2.html,1996.
[3] Alexander Savelyev.Contract Law 2.0: Smart Contracts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Classic Contract Law[EB/OL].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885241,2016-12-14.
[4] 谭佐财.智能合约的法律属性与民事法律关系论[J].科技与法律,2020(06):65-75.
[5] 弗卢梅,迟颖译,米健校.法律行为论[M].法律出版社:北京,2013:27.
[6] 汪青松.区块链系统内部关系的性质界定与归责路径[J].法学,2019(05):130-142.
[7] 韩世远.默示的承诺与意思实现——我国《合同法》第22条与第26条的解释论[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01):80-85.
[8] 刘薇.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法律性质[J].法治论坛,2020(02):69-81.
作者简介:杨奇,(1998.09-),男,汉族,浙江省温州市,研究生,澳门科技大学,民商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