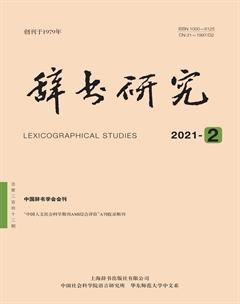当代三大科技与21世纪语言学
摘 要 20世纪下半叶,世界科技进入新的飞跃时期,先后出现计算机科技、分子生物学、现代脑科学。现代科技促进了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计算机科技孕育了计算语言学,现代脑科学提升了神经语言学,现代生物学推进了生物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分子人类学与亲缘比较语言学相互验证,由此呈现当代语言学和当代科技的互动。当代语言学的交叉性、实验性和精密化趋势,促使其成为 “语言科技”——此为21世纪语言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三大科技 语言学 促进 互动 语言科技
回顾19世纪,西方语言学先后受到生物学(Lamarck1809; Darwin1859)、心理学(Herbart1816; Steinthal1850; Lazarus1851)、社会学(Comte1839; Tarde1890; Durkheim1893)的影响,由此形成第一代生物语言学(Becker1827; Müller1861/1866; Schleicher1863)、心理语言学(Lazarus1851; Steinthal1855; Lazarus & Steinthal1860; Steinthal1871; Hecht1888)、社会语言学(Sayce1875; Paris1887; Meillet1905),集中体现为基于社会心理的现代语言学理论(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1871, 1889)。20世纪上半叶,西方语言学主要受人类学(Boas1911; Malinowsiki1923)和格式塔心理学(Ipsen1924)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Chomsky1957)生成语法的蓝本则来自希尔伯特(Hilbert1920)的形式系统方法和波斯特(Post1936)的数理语言学。20世纪下半叶,世界科技进入新的飞跃时期,先后出现计算机科技(1950)、分子生物学(1953)、现代脑科学(1987)。三大现代科技促进了当代语言学的发展,并彼此互动。
通过对20世纪语言学的沉思,我在2000年提出“语言科技新思维”。2001年创办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学及技术系及语言信息处理本科专业(即所谓“新文科”教育),主持建设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理论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方向,2008年增实验语音学方向),并发表《论语言科学与语言技术》(李葆嘉2001/2003)。世纪之交“瞻望新世纪语言学发展”的众多会议我皆未参加,也许我的瞻望与之有别。至于要细论21世纪语言学的走向,有必要等待前十年的发展。本文是近年来的思考——21世纪的语言学必然与当代三大科技交会,21世纪语言学的主流就是计算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和生物语言学。
一、 计算机科技孕育了计算语言学
虽然计算机研制的初衷缘于数值计算,但是图灵(A.M.Turing, 1912—1954)在《计算机和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1950)中已经提出,检验计算机智能的最好方法就是对语言信息处理能力的测试。1954年,赫尔德(C.C.Hurd, 1911—1996)主持世界首次机器翻译试验,标志着计算机科技与语言学结合的起步。1977年,费根鲍姆(E.A.Feigenbaum)提出“知识工程”,表明计算机信息处理出现从“数据世界”向“知识世界”转移。1990年,第13届国际计算语言学大会提出处理大规模真实文本的战略目标。语言信息处理的核心是语言的自动理解和生成,其最终目标是仿真人类语能的“人工语言脑”。
(一) 计算语言学的界定和研究内容
在语言学与计算机科技结合的领域,立足于不同学科视角或知识结构,出现过一系列名称,如数理语言学、语言工程、自然语言处理、语言信息处理等。“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这一名称,是由语言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海斯(D.G.Hays, 1928—1995)提出的。他著有该学科的第一本教科书《计算语言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67),遗憾的是该书没有中文译本。
“计算语言学”的定义可归纳为四种: (1) 以计算机为工具研究语言;(2) 把语言学成果应用于计算机;(3) 研究语言中的可计算问题;(4) 建立基于计算机科技的语言学理论。前两种流行于欧洲,把计算机当成语言研究的工具;后两种盛行于美国,强调计算机科技对语言学的影响。综上,计算语言学可定义为: 利用计算机作为工具研究语言、研究自然语言机用系统、研究语言系统或语言能力的可计算性,建构基于计算机应用、数学模型、认知科学的语言学理论。
计算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包括: (1) 应用基础研究,即语言处理技术研究,如: 自动分词、词语特征标注或语句篇章分析、语料库或语言知识库建设等。(2) 应用研究,主要是工具和系统的开发,如: 机译工具、自动文摘工具、信息检索和抽取工具、言语识别和合成系统、人机对话系统等。(3) 理论研究,包括人工智能理论和语言学理论,如: 计算机如何或是否可以仿真人脑功能和语言能力,如何寻找合适的语言计算模型等。此外,还有对自然语言的本质属性是语义性的认定、面向信息处理的机用语法学理论、语言系统与数学模型的关系、语言结构和数理逻辑的关系、语言符号的数字化可能性及其局限性、语言的异质性和受限理论、元语言理论方法等。
(二) 语言研究工具和语言研究资源
计算语言学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便捷工具: (1) 语音研究工具;(2) 词汇研究工具;(3) 词性、句法研究工具;(4) 语义(词汇、句子、语篇语义)研究工具。语言研究资源包括语料庫和语言知识库。除了一般性语料库,专门性语料库更有针对性。李葆嘉主持研制的“现代汉语语域语料库”(2002—2005),包括法律、商务、体育竞技、新闻热点等子库。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资助的Child Language Data Exchange System语料库,包括若干语种的儿童语料。李葆嘉主持研制的“汉语幼儿(2—6岁)日常会话跟踪自然语料库”(2005—2015),盖为目前最大的汉语幼儿自然语料库。
属于应用基础研究的语言知识库建设,涉及语言知识的整理、发现和形式化,以便为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系统提供知识支撑。(1) 美国宾州大学中文树库的目标是建立100万词的句法标注数据库。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中文句结构树数据库包括61087个树图。(2)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密勒(G.A.Miller)和费尔鲍姆主持研制的词网(Wordnet, 1985),是基于同义词集和语义关系描述的词汇知识库。(3) 美国百科全书公司雷纳特(D.Lenat)主持研制的CYC知识库(1984)包含概念、概念关系、推理规则三部分,其应用领域涵盖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语义网、知识表示等。(4) 美国微软公司理查德森(S.D.Richardson)主持开发的智网(Mindnet, 1993)基于三元组自动获取语义关系,反映了从自然语言文本中自动获取、组织、访问和挖掘语义信息的方法。(5) 美国语言学家菲尔墨(C.J.Fillmore)主持研制的框网(Framenet, 1998),对英语义项的语义句法组合进行细致描述,通过对手工标注例句的自动整理得到配价模式。(6)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语言信息中心董振东等基于义原系统和概念关系研制了知网(How-Net, 1998),台北“中央研究院”中文词库小组拓展成“概念网”(Concept-Net, 2003)。此外,李葆嘉主持研制的“深度语义分析信息库”(2008—2011),对“九年制语文课本”加以标注,包括语义词类范畴10大类32种,语义句法框架117种(VP结构核84种,NP结构核33种),配有字词句检索与统计工具、语义词类范畴检索和统计工具、语义句法范畴检索和统计工具、语义词类语义句法范畴对应检索工具等。
近年来成为热点的知识图谱,也属于语言知识库建设的一部分。图书情报界称为“知识域映像地图”,即用可视化技术展示语言知识资源,以挖掘、分析和图标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动态知识图谱需要很强的数据、算法和计算基础支撑。构建知识图谱的目的,也就是试图把人脑认知的知识关系通过可视化技术移植到计算机中去,其质量的高低受限于研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设计匠心。
(三) 广义人工智能和人类语能模拟
作为广义概念,人工智能研究集中在人工体能(肢体活动)、人工技能(行业技术)、人工算能(最典型的是阿尔法狗,经过几百万次训练,职业棋手不可能)、人工感能(图像识别、音质识别)等方面,而与“人工语能”距离尚远。所谓人工语能,即人类语言能力的计算机仿真(机器翻译、文—语转换、人—机会话等)。
机译系统研究的起步(1954),比一般的“人工智能”(1956年夏,麦卡赛、明斯基、罗切斯特和申农等首次提出)要早两年。1964年11月,美国科学院语言自动处理咨询委员会在《语言与机器》报告中指出: 机器翻译遇到了难以克服的semantic barrier(义障)。这一警告,致使机译研究热暂时消退。1982年,日本制订面向AI的“第五代计算机”研制计划,其中包括自然语言处理装置。1992年结束时,只有部分达到预定目标。随后又公布“真实世界计算机计划”,不久暂停,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穿过语言(语义)的“瓶颈”。
2006年,辛顿(G.E.Hinton)将多层神经网络方法应用于图像识别。2009 年,微软实现基于多层神经网络的语音识别系统。2014 年,赵景贤(Kyunghyun Cho)和本吉奥(Yoshua Bengio)等提出基于注意機制的编码器—译码器框架,建立了基于神经网络的机译系统。2017 年,Google翻译提出完全基于注意机制的转换器模型,实现了神经翻译引擎。这些努力促使机译系统取得明显进展,甚至已经有人尝试翻译成本著作。据我使用,英—汉、俄—汉机译比较成熟,德—汉、法—汉机译次之。一般规范性文本的机译基本通顺(约70%—90%),语言学文献的机译能知大意(约40%—70%),需要凭借专业知识修正和调整润饰。2005年李葆嘉曾提出,就翻译的内容而言,机译系统依靠语言规则(理性主义)可解决约35%,依靠大规模语料(经验主义+连结主义)可解决约35%,还有约30%就是语义的、语境的、知识背景的(就是翻译家也难免出错)。神经网络只是处理语料的连结主义模型,虽有所改善,但关键的“义障”仍然没有跨越,机译系统研究仍然任重道远。尽管近几年人工智能沸沸扬扬,然而人工语能的实现,依然“路漫漫其修远兮”。李葆嘉(2003/2012)在《人工语言脑: 自然语言处理装置的研制思路》中,设计了语言基因图谱分析工程→认知语义网络建构工程→受限语言能力仿真工程。此后,陆续完成现代汉语元语言系统研究、典型动作词的认知语义网络建构、话题语说明语范畴系统及其匹配框架、话语行为效能范畴系统等。
二、 现代脑科技提升了神经语言学
脑科学(Brain Sciences)研究脑的结构和功能。狭义的脑科学即神经科学,了解神经系统内分子水平、细胞水平、细胞之间的变化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在中枢功能控制系统内的整合作用。1989 年美国国会通过“脑的十年”计划议案。1991年欧共体成立欧洲脑十年委员会及脑研究联盟。1995年国际脑研究组织在日本京都第四届世界神经科学大会上,提议把21世纪称为“脑的世纪”。1996年日本制定“脑科学时代: 脑科学研究推进计划”。1997年美国启动“人类脑计划”。2013年美国公布“脑活动绘图计划”。2015年中国发布“中国脑计划——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总体而言,现代脑科学的主要任务: (1) 了解脑——阐明产生感知、情感和意识的脑区结构和功能,阐明脑的信息加工功能(语言信息的脑神经网络表达机制,人类获得语言能力的过程,语言、思维和智力的关系)。(2) 保护脑——控制大脑的发育和衰老过程;神经性精神病的康复和预防。(3) 创造脑——研制类脑型构件和仪器(具有学习和记忆能力的神经元芯片,具有智力、情感和意识的脑型计算机);类脑型信息产生和处理系统设计(支持机器人系统)。目前的研究热点有: 类脑认知计算模型;人工神经网络;神经接口、脑机接口;神经形态芯片、类脑计算机。
(一) 现代脑科学的技术手段
人类对大脑的研究,始于解剖尸体大脑和研究大脑局部损伤者,由此获取相关知识。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人脑的主要途径是脑组织损伤、电生理学、成像及切片。现代脑科学的无损伤性技术设备和神经影像学研究方法都是近二十年内的发明,并且最近十年才广泛应用。
20世纪50 年代末,出现脑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通过记录刺激事件诱发的脑电变化研究大脑活动。70 年代,出现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显像技术(PET)或计算机断层显像技术(CT),通过多次投影获得人脑局部的葡萄糖利用、血流、氧耗或受体密度的影像,以对启动脑区定位。80 年代,出现大脑自发电活动所伴随的脑磁成像技术(MEG)。90 年代,出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检测局部脑血流内脱氧血红蛋白变化的水平。在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上,fMRI和ERP具有互补性,已成为研究人脑机制(或神经语言学)的重要手段。
(二) 从失语症研究到神经语言学
16—17世纪,欧洲医生开始研究语言障碍与特定部位脑损伤的关系,已能区分语言障碍和一般认知障碍、语言表达障碍和语言理解障碍、词法缺失和发音障碍、句法缺失和词形障碍等。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解剖学家加尔(F.J.Gall, 1758—1828)创立大脑神经学,与施普尔茨海姆(J.G.Spurzheim, 1776—1832)出版《一般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Anatomie et physiologie du système nerveux en général, et du cerveau en particulier)和《关于大脑功能及其分区功能》(Sur les functions du cerveau et sur celles de chacune de ses parties),推测脑区有掌控说话和储存词语的神经中心。1848年,法国巴黎医学院院长波伊劳德(J.B.Bouillaud, 1796—1881)推定语言功能定位于大脑额叶区。
第一位为大脑额叶区控制语言提供证据的是法国医生布罗卡(P.P.Broca, 1824—1880)。1861年他相继发表《失语症: 慢性软化和左额叶的局部损伤》(Perte de la parole, ramollissement chronique et destruction partielle du lobe antérieur gauch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2)235-238和《基于所观察语障(失语症)论语言能力的脑区》(Remarques sur le siège de la faculté du langage articulé, suivies dune observation daphémie [perte de la parol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natomique de Paris 6)330-357。1874年,德国医生韦尼克(C.Wernicke, 1848—1905)刊行《失语症状的复杂性: 基于解剖学的心理研究》(Der aphasische Symptomencomplex, Eine psychologische Studie auf anatomischer Basis, M.Crohn und Weigert)。1885年,德国医生利奇海姆(L.Lichteim, 1845—1928)通过临床证实了韦尼克推测的传导性失语症。1909年,德国神经学家布罗德曼(K.Brodmann, 1868—1918)出版《基于细胞结构原理描述大脑皮层比较定位理论》(Vergleichende Lokalisationslehre der Grohirnrinde in ihren Prinzipien dargestellt auf Grund des Zellenbaues, J.A.Barth)。1885年,波俄語言学家博杜恩(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5—1929)基于失语症个案研究,撰有《病理语言学和胚胎语言学》(Из патологии и эмбриологии языка)。1926年,英国神经学家黑德(H.Head, 1861—1940)在《失语症和言语障碍》(Aphasia and Kindred Ddisorders of Speech)中划分了命名性、句法性和语义性失语症。受博杜恩影响,俄裔语言学家雅柯布逊(R.Jakobson, 1896—1982)从事儿童语言和失语症研究,1941年出版《儿童语言、失语症和一般语音法则》(Kindersprache, Aphasie und Allgemeine Lautgesetze)。从布洛卡到雅柯布逊的研究,可统称“失语症和语障研究”。
作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创始者,博杜恩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关注语言科学和神经科学的联系。他在1870年提出: “我对语言定义如下——语言是肌肉和神经的合适行为的可听结果(语言是最广义上的人体功能之一)。”(Бодуэн1963)Т.I: 78[1]他在1889年提出: “语言的基础是纯粹心理的、大脑中枢的,因此语言学属于心理科学。生理学与微观解剖学或大脑组织学相结合,如果可以取代心理学,如果可以研究并将大脑组织系统化,如果可以展示这些组织伴随说话和语言思维的物理运动和化学变化,那么就可能帮助理解语言的精神本质。”(Бодуэн1963)Т.I: 217-218他在1903年预言: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发现神经元(神经细胞)的动态变化与化学变化,或与物理能量变化之间的联系——太妙啦!到那时,这两个领域的成果将会结合成一个共同的科学体系。”(Бодуэн1963)Т.II: 65在语言学文献中,博杜恩关于语言学、大脑组织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协同研究的论述为最早,并预言大脑神经元的动态变化与化学变化或物理能量的联系如被发现,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会结合成一个共同科学体系——可谓“神经语言学的先声”。
20世纪60年代,语言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交叉催生了神经语言学(Neurolinguistics)。1974年,美国惠特克(H.A.Whitaker)创办《脑与语言》(Brain and Language)杂志。1975年,苏联卢利亚(А.Р.Лурия, 1902—1977)出版《神经语言学的基本问题》(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нейролинrвистики)。卢利亚192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其父为该校生理学教授),书中有三处赞扬喀山语言学派创始人博杜恩。
20世纪80年代,国外神经语言学研究进入发展期,中国学界开始译介这门学科。1987年,赵吉生、卫志强翻译的卢利亚著的《神经语言学》出版。1997年,王德春等编著的《神经语言学》出版。1996年,徐州师范大学杨亦鸣开辟以汉语语料研究为主的神经语言学方向并招收硕士生;2001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专设神经语言学方向,特邀杨亦鸣教授培养神经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生及博士后人员。 2018年6月,中国神经语言学研究会成立。
(三) 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对象
毫无疑问,现代脑科学技术提升了神经语言学。除了传统的行为学和临床失语症测查,当代神经语言学的关键是利用神经影像学和神经电生理学等无创伤技术研究人脑的语言加工机制。
人脑不断产生EEG(脑的自发电位),但从中观察不到特定心理认知活动产生的脑电信号,需要采用计算机叠加技术,从EEG中提取脑电信号ERP(实时波形)。比如N400,就是研究大脑语言加工时常见的ERP 成分。以视觉逐词显示句子,如有语义上不适合的词出现在句末,那么这个词就会诱发N400的产生。人脑神经活动兴奋水平增强,则局部腦组织血流及血氧消耗增加,由此导致脑启动区静脉中的血氧浓度增高,脱氧血红蛋白减少。脱氧血红蛋白是顺磁物质,氧合血红蛋白是逆磁物质,磁性物质的增减反映了相关脑区的启动状态。fMRI可直接用于被试,所记录图像最小可达1mm 范围,空间分辨率最高,但时间分辨率存在局限。接受刺激后,脑细胞的启动需8秒钟才达到最大值,fMRI不能做到实时记录。由此,需要将事件相关电位、功能磁共振等仪器结合使用,才能对语言神经机制进行实验和数据分析。(梁丹丹,顾介鑫2003)
一般而言,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包括: (1) 言语生成或理解的神经生物学机制;(2) 言语交际的神经生物学机制;(3) 语言能力获得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具体而言,其研究专题包括: 语言习得和运用、言语生成和理解的神经机制,人脑如何接收、存储、加工和提取言语信息,正常言语的神经生理机制或言语障碍的神经病理机制。此外还有神经语用学研究,涉及儿童的语用能力发展、获得性语用障碍和语用失语症、脑损伤病人的语用能力评估和治疗。除了儿童语言神经机制,近年老人语言神经机制研究兴起。如要全面探讨个体语言的发生和发展神经机制,需要长年累月的追踪。
近二十年来,神经语言学已经取得许多成就。现代脑科学家在不同层次探索脑的工作原理为: 整个脑神经通路脑区神经回路神经元细胞分子。在微观层面上对大脑探索的不断深入,可以增强对语言神经机制的认识。神经科学、遗传学、心理学的最新进展,仍然是推动神经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四) 神经语言学面临的相关问题
目前,神经语言学大都基于脑功能成像建立理论——“它不仅能够解释听者如何通过感知把语音转化为意义,以及如何在言语产出过程中把意义转化为声音,而且必须通过神经生理学和大脑成像技术手段得到验证”(Grimaldi2012)307。不过,崔刚、王海燕(2014)提出神经语言学研究面临三大问题。
第一,语言处理内在机制与语言形式规则的矛盾。首先,语言处理内在机制是顺序性还是交迭性。模块主义认为不同层次之间的处理相互独立并按序进行;互动主义认为在不同层次或阶段之间的处理存在交迭。神经语言学更多地采用模块主义。其次,语言处理内在机制是规则性还是概括性。语言处理模式中运用的转换生成语法规则,是否具有神经现实性?此外,联结主义否定纯粹基于规则的语言处理模式,而认为信息处理更多地基于对输入数据的概括。
第二,语言学与神经科学的兼容性矛盾。虽然语言学和神经科学力图结合,但尚未形成兼容性平台。(Grimaldi2012)首先,学科模式不同。转换生成语法把语言视为先天“装置”,认为可通过理论假设及实验验证对语言的物质特征(即大脑)做出推论。而通过本族人言语验证理论的方法,往往带有主观色彩。神经科学的基本理念是心理体现在神经系统上,神经生理过程与正在进行的心理过程等同。(Grimaldi2012)尽管神经科学需要理论推测,但更看重通过控制性实验得到的数据。与语言学研究沿着从理论到验证的方向进行相反,神经科学则是通过实证观察与研究并基于数据建立相应理论。神经科学积累的大量数据,很难与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
此外,坡佩尔和恩比克(Poeppel & Embick2005)指出,把语言学术语直接用于语言的神经生物基础研究会产生颗粒度失调和本体不可比问题。前者指各自学科对语言单位的划分不同。语言学中有许多细微区分,心理语言学有较细描述,但神经科学更多地基于概念框架。后者指语言学和神经科学的计算单位难以比较。转换生成语法提出句子=NP+VP(通过日常话语归纳的语言知识),但并不意味大脑中就有与之对应的神经机制。句法树可描述句子结构,但在语言神经机制研究中未必有用。实际上,大脑中的句法处理是神经细胞的同步活动,几百毫秒之内即完成。(Fuster2003; Schnelle2010)究其根源,语言学家研究的是一般语言知识,而神经科学家探索的是语言神经机制,两者难免龃龉。
第三,大脑功能反射说和内在说的矛盾。谢灵顿(C.S.Sherrington, 1857—1952)在《神经系统的综合性行为》(The Integrative Ac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06)中指出,大脑功能基本上是反射性的。布朗(T.G.Brown, 1882—1965)在《论神经中枢基本活动的本质》(On the Nature of the Fundamental Activity of the Nervous Centres, 1914)中认为,大脑功能(包括信息处理过程)首先是内在的;即使在无外部刺激的情况下,大脑也在进行各种认知活动。成年人的大脑重量只占体重的2%左右,但却消耗总能量的20%,其中事件触发状态所耗仅占5%。(Clarke & Sokoloff1999)这意味着绝大部分能量消耗在内在神经信号处理中。仅靠外部事件诱发活动的实验,反映的只是大脑实际功能活动的小部分。(Raichele2010)180
最近看到《五年过去了,美国脑计划进展如何?》(原刊2019年4月27日Psychology Today,作者是加州圣地亚哥大学神经学教授 P.S.Churchland)一文,美国脑指委提议促进神经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工程学、物理学、遗传学、数学和化学等学科的真正跨领域合作。遗憾的是没有语言学,美国脑科学家的态度略见一斑。
三、 现代生物学推进了生物语言学、演化语言学
(一) 语言学和生物学的姻缘
1863年,施莱歇尔(A.Schleicher, 1821—1868)发表《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Die Darwinsche Theorie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 offenes Sendschreiben an Herrn Dr. Ernst Haeckel.),今人认为这反映了进化论对语言学的重大影响。然而,早在18世纪70年代,历史比较语言学先驱蒙博多(Lord J.B.Monboddo, 1714—1799)在《语言的起源和进化》(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Language, 1773—1792)中已经首创语言进化论,并进一步推导和论证了“人类体质进化论”和“人类心智进化论”,形成了作为科学理论的进化模式。其后的学者基于这一模式,在地质学(Hutton1788; Smith1816; Lyell1830)、生物学(Hutton1788; E.Darwin1794; Lamarck1809; Mathew1831; Chambers1844; Wallace1855; C.Darwin1859)、人類学(Wells1813; C.Darwin1871)领域,利用所搜集的数据使其丰富化,从而形成了各自学科的个别进化论。(李葆嘉2014)
18世纪下半叶,欧洲生物学界流行有机体学说。1805年,德国学者本哈迪(A.F.Bernhardi, 1769—1820)在《语言科学原理》(Anfangsgründe der Sprachwissenschaft)中提出,“语言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把语言有机体刻画清楚。19世纪上半叶,主张“语言有机体学说”的德国学者及其论著主要有: (1) 洪堡特(W.von Humboldt, 1767—1835)的《论与语言发展不同时期有关的比较语言研究》(eber das vergleichende Sprachstudium in Beziehung auf die verschiedenen Epochen der Sprachentwicklung, 1820/1822);(2) 贝克尔(K.F.Becker, 1775—1849)的《语言有机体: 德语语法引论》(Organism der Sprache als Einleitung zur deutschen Grammatik, 1827);(3) 葆朴(F.Bopp, 1791—1867)在《元音系统或语言比较综述》(Vocalismus order Sprachvergleichende Kritiken, 1836)中提出: 语言应视为有机的自然主体,按照一定规律的形式,以其内在生命原则主导自身的演变并逐渐消亡。19世纪中叶,主张“语言自然主义”的学者及其论著主要有: (1) 比法学者查维(H.J.Chavée, 1815—1877)在《印欧语词汇学》(Lexiologie indo-européenne, 1849)中提出语言的“自然家族”,在《印欧语词汇观念学》(Idéologie lexiologique d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1878)中把语言学定义为“有关思想的音节生物体的科学,并且这些音节生物体,彼此之间就像种族一样自发地创造自己”;(2) 德英学者缪勒(F.M.Müller, 1823—1900)在《语言科学讲座》(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in April, May, & June 1861, 1866)中提出: “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与地质学家研究矿石和化石、天文学家研究天体、生物学家研究花朵毫无差别。”
在达尔文《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1859)出版四年后,施莱歇尔(Schleicher1863)7在《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中写道: “语言是自然有机体,在不受人类意志决定的情况下,会按照确定的规律产生、生长和发展,进而衰老和死亡。他们也独特地具有通常被理解为‘生命的一系列表现。语音隶属于语言科学,因此是一门自然科学。一般而言,其研究方法与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并且提出,“我希望能证明,达尔文学说的主要观点适用于语言生命,甚至可以说,这些观点已经被人不声不响地运用过”。看上去,似乎达尔文学说影响了施莱歇尔,其实施莱歇尔是基于“语言有机体学说”与达尔文学说共鸣。施莱歇尔宣称: I was a Darwinian before Darwin,就是要表明——在达尔文学说之前,他已经具有语言进化观,并用生物学概念解释语言生命。 “这归功于施莱登(M.J.Schleiden, 1804—1881)的《科学植物学》(Grundzüge der wissenschaftlichen Botanik nebst einer methodologischen)和卡尔·福格特(Karl Vogt, 1817—1895)的《生理学信札》(Physiologische Briefe)此类著作,使我认识到语言的本质和生命。正是从这些书中,我首次了解到什么是发展史。”(Schleicher1863)7
18世纪70年代,青年语法学派反对施莱歇尔的语言自然主义,用心理类推机制解释语言变化。早在1855年,心理语言家斯坦塔尔(Heymann Steinthal, 1823—1899)在《语法学、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原理及其相互关系》(Grammatik, Logik und Psychologie: Ihre Prinzipien und ihr Verhltnis zueinander)中就批评过贝克尔的《语言有机体》。随着心理取向和社会取向的兴起,第一代生物语言学销声匿迹。
(二) 当今的两种生物语言学
1950年,美国科学家米德和梅斯肯(C.L.Meader & J.H.Muyskens)在《生物语言学手册》(Handbook of Biolinguistics)中首次使用术语“生物语言学”。此后,分子遗传学成为生物学的巨大变革,种群遗传学、协同进化论以及生态学促进新一代生物语言学蓬勃发展。1967 年,美国神经生物学家雷纳伯格(E.Lenneberg, 1921—1975)出版《语言的生物基础》(Biological Foundation of Language)。1974 年,生物语言学国际学术会议指出生物语言学是生物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1980 年,哈佛大学“生物语言学”小组成立,其研究涉及分子生物学、动物交际神经学、语言学习障碍、神经语言学、语言的起源和儿童语言发展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等。2007 年,博尔克斯(C.Boeckx)创办《生物语言学》(Biolinguistics)杂志。
生物语言学把语言看成一种自然现象,寻求人类语言知识的本质、来源和运用。广义的生物语言学包括运用进化生物学、基因科学、神经科学以及心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语言;狭义的生物语言学指以乔姆斯基(20 世纪70年代)为代表的生成语法学派对语法属性的相关研究。据统计,百科全书或词典中的“生物语言学”多指前者,而一些语言学家研究的“生物语言学”基本指后者。生物语言学旨在回答: (1) 语言知识如何组成?(2) 语言知识如何习得?(3) 语言知识如何使用?(4) 相关的人脑机制为何?(5) 语言知识在种族中如何进化?前三个问题参见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1975),后两个问题参见雷纳伯格(Leneberg)《语言的生物基础》(Biological Foundation of Language, 1967)。2000年,詹金斯(L.Jenkins)在《生物语言学: 探索语言的生物性》(Biolinguistics: Exploring the Biology of Language)中分別阐述了这些问题。(吴文2012)
进入21 世纪以来,生物语言学开始关注语言的递归性。生物语言学朝着物种语言演化、个体语言发展和语言认知演化三个向度推进。主要探讨: (1) 关于“生物语言学”概念及其研究范围的界定;(2) 关于生物语言学的缘起及盛行的动因;(3) 关于语言学者对生物语言学背景下的语言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2002 年起,国内学者引介西方生物语言学研究,近年来的研究以推测性居多。(丁凯莉等2017)
(三) 基因FOXP2并非“语法基因”
20世纪90 年代初,媒体曾广泛报道KE 家族患病成员的所谓“语法特异障碍”。这些报道源自《自然》的一则短讯[M.Gopnik.Feature-blind Grammar and Dysphasia. Nature1990(6268)]715: “该家族患病成员不能判断、理解和运用语法(‘语法表征盲缺陷),此缺陷在患者自发性言语、书写和复述中都有表现,而根源可能在于潜在的语法程序发生错误,且表现出单基因遗传模式。”尽管当时尚未鉴定造成这一障碍的基因,但一些专家通过媒体高呼发现了“语法基因”,似乎“普遍语法”这一概念已获得生物学实证。
研究发现,“KE 家族成员所患的言语失用症(Developmental Verbal Dyspraxia),是由于言语肌肉运动的位置、范围、协调性和运动序列的编程能力受损,而产生的运动性言语障碍。除此,KE家族患病成员还有表达理解混合型语障,某些病例还有书写缺陷及非言语性认知损伤”(Watkins & Vargha-Khadem2002)458。2010年,纽伯里等(Newbury & Monaco2010)310-311回溯了FOXP2 的鉴定及功能研究的过程: 费希尔(S.E.Fisher)通过全基因组连锁分析将该基因初步定位于7q31处,拉伊(C.S.Lai)等通过基因精确定位发现所有KE家族患病成员的FOXP2基因都有突变,而未患病成员则无。接着发现一位患有类似障碍的非KE家族儿童,其染色体重排导致FOXP2基因的断裂。由此,FOXP2基因和言语失用症的相关性得到支持。此后,又有一些独立的FOXP2基因筛查研究,鉴定出另外几例FOXP2断裂的病例,他们都有言语失用症状。KE家族携带FOXP2的杂合性错义突变,改变了FOXP2蛋白的DNA结合区域。另有研究表明,FOXP2的另一处杂合性无义突变也和言语障碍有关,这种无义突变严重截短了蛋白,剪除了必需的功能模序。虽然FOXP2在言语失用症中的真正作用有待明确,但可以确定——该基因对负责精细动作控制的大脑区域发育非常重要,如果断裂将对言语发育造成严重后果。
然而,FOXP2基因是否就是“语法基因”或“语言基因”?费希尔(Fisher2006)288对此进行了驳斥。第一,FOXP2基因并非人类特有,在哺乳动物世系中它以高度保守的形式存在。FOXP2仅为人类言语和语言能力服务的观点与之不符。第二,对FOXP2的表达研究还发现,其功能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而且体现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对肺、心脏、肠的发育也发挥重要调控作用。第三,FOXP2在脑发育中的表达极为复杂。在人类和啮齿类动物的早期发育中,FOXP2在脑区(包括皮质、丘脑、下丘脑、纹状体、小脑和髓质)广泛表达,并一直持续到成年期。因此人类的FOXP2基因,不仅影响传统认为与语言相关的皮层区域,也影响其他皮层区域的发育和功能,FOXP2并非仅局限于布罗卡区。(李慧2013)
由此可见,一些学者急于把对言语发育会产生严重后果的FOXP2(对除大脑以外的人类其他组织的发育也是必需的)贴上“语言基因”的卷标,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所谓“普遍语法”的误导。可以推定,人类应有促使语言器官(基于一般发音器官)和语言能力(基于一般认知能力)发育的基因,但是不可能有所谓“普遍语法基因”。
(四) 综合性的演化语言学
演化语言学(Evolutionary Linguistics)是基于演化生物学理论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学科。20 世纪50年代以来,动物行为学家通过人与猿猴各自沟通系统的对比,来研究人类语言产生和演化的生理、认知和社会基础。1972年,第一届语言起源和演化北美会议在多伦多召开。20世纪90 年代以后,演化生物学、遗传学、分子人类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考古学、人类学等更多学科的学者加入其中。1996年,在“第一届语言演化国际会议”(爱丁堡)上,诸多领域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探讨语言的演化机制等,语言起源与演化的研究全面展开。
2005年,阿特金森和格雷(Atkinson & Gray)在《惊人平行和惊人关联: 生物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系统发育思路》(Curious Parallels and Curious Connections: Phylogenetic Thinking in Biology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一文中列出生物学和语言学的平行概念表。2009 年,王士元教授发起“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迄今已举办10 届。王士元(2011)21指出: “而语言的演化却是双重的——它是一种生物功能,也是一种社交行为。我相信研究这样双重的演化,一定会对演化论提出新的刺激、挑战,产生一些关于演化理论的新看法。”
麦克马洪等(April Mcmahon & Robert Mcmahon)在《演化语言学》(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2013)中指出,演化语言学是运用进化论研究语言相关问题的交叉学科。根据研究现状,可分为两个分支。其一是研究人类如何获得语言能力。该分支的“演化”是生物进化论意义上的“进化”。主要问题是: 人类的语言能力是怎样、为何以及从何更早系统中产生的;它又是怎样从何时、为何经过一系列的修正之后,成为我们可以习得运用的现代语言的。费希尔(Fisher2006)270指出: “人类语言的出现一定经历了漫长的灵长类动物祖先形态上的量變和质变,如脑容量的改变、神经关联强度的改变、新的神经通路的产生,以及声音感觉机制的形态改变,而形成这些改变的分子机制有基因型改变、基因表达时空改变和基因表达量改变。”然而,基因表达产物为调控因子、信号分子、受体、酶等,它们之间形成高度复杂的作用网络且受环境调节以构建和维系大脑功能,由此基因和语言的关系是间接而复杂的。该分支的主要成果有: 艾奇逊(J.Aitchison)《言语的种子: 语言的起源和演化》(The Seeds of Speech: Language Origin and Evolution, 1996)、菲奇(W.T.Fitch)《语言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2010)、迈克尔(C.C.Michael)《递归的心智: 人类语言、思想和文明的起源》(The Recursive Mind: the Origins of Human Language, Thought and Civilization, 2011)等。其二是研究人类语言的演变。麦克马洪认为这里的“进化”是隐喻的,但克罗夫特(W.Croft)、穆夫温(S.S.Mufwene)等认为,语言演化现象本身可用进化论解释,不一定非要与生物物种模拟。该分支借用生物进化论模式和方法,把语言演变过程视为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过程”的缩影,以之解释语言演变的各个环节。其主要成果有: 塞缪尔斯(M.L.Samuels)《语言的演化: 专门参考英语现象》(Linguistic 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ish, 1972)、克罗夫特《语言变化解说: 一种演化分析法》(Explaining Language Chan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2000)、穆夫温《语言演化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volution, 2001)和《语言演化: 接触、竞争和改变》(Language Evolution: Contact, Competion and Change, 2008)等。
显然,演化语言学可视为广义生物语言学的一部分,特别是第一个分支与生物语言学研究多有交迭。两个分支发展至今,较成熟的理论是语言演化生态学。豪根(E.Haugen, 1906—1994)在《语言生态学》(The Ecology of Language, 1972)中提出“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语言演化生态学的目标在于探寻语言演化的动因、机制、过程和特点,以及语言演化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穆夫温(2008)指出,语言演化生态学的理论基础: 一是语言演化的动力存在于说话者的个体交际行为之中,就像生物学中的种群或物种由其个体活动所发生的影响一样;二是引起语言演化的累积行为,基本取决于说话者所处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其研究对象包括: 结构变化、语种形成、语言产生、语言消亡。总之,语言演化生态学认为语言就像生物种群,其中的每个有机体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有机体的特性,单个有机体的特性是由个体基因特征和种群基因特征结合构成的。语言演化生态学主张,不存在非接触性的语言演化现象,一切语言演化现象都是由语言生态环境的变迁而促发,在“竞争选择”机制作用下,沿着同样的演化模式展开。(朱敏霞2014)
四、 分子人类学与比较语言学的互动
1962年,萨里奇(V.M.Sarich)和威尔逊(A.C.Wilson)用不同结构的生物分子研究人类进化时提出“分子人类学”(Molecular anthropology)这一概念。20世纪80年代,引入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才使分子人类学接触到带有生物遗传信息的DNA水平。近年来,随着遗传学和人类基因组研究的迅速发展,能在分子水平上研究人群的遗传学特征,分子人類学得到进一步发展。(陈文婷2014)
达尔文(Darwin1859)350在《物种起源》中曾设想: “如果我们拥有一份完美的人类谱系,那么人类种族的谱系排列就可为目前世界上使用的各种语言提供最完善的分类;并且,如果把所有消亡的语言,以及所有处于中间状态的和缓慢变化的方言也包括在内,那么这种排列,我以为才是唯一合理的分类。”达尔文的论点未免简单化(仅有分化)。同时代的赫胥黎(T.H.Huxley, 1825—1895,1865)257在《论人种学的方法和成果》(On the Methods and Results of Ethnology)中写道: “显然,语言的一致性或许能提供某种假设支持这种说法,即不同民族如果在语言上具有一致性,那么在人种上也就趋于一致。但是此论并不能证实这种人种的一致性,即使目前尚未找到反例。除非语文学家准备证明——任何民族在丧失本族语并采用异族语之后,都会随着语言的改变而出现血统的相应改变。”换而言之,语言的演变除了纵向传递还有横向传递,除了分化还有接触。除此,更为复杂的语言运动,还有不同语言在某个历史阶段的混合(其典型是克里奥尔语,包括底层语和混入语)、不同语言在多个历史阶段的层垒性融合(形成语言的底层、中层、表层等)。(李葆嘉,张璇1999)
(一) 人口基因与语言谱系
分子人类学家在研究人类起源的同时,注意到语言演变与生物遗传演变有着类同关系。通过对现代人群的线粒体DNA 和Y染色体的大面积调查,根据Y染色体的分化类别把人类定为20个主干单倍群。20世纪80年代起,卡瓦利斯福札(Cavalli-Sforza)就呼吁基因研究应当和语言学、考古学结合起来,并绘制过一幅世界人口基因与语言谱系的对照图(Cavalli-Sforza, Piazza, Menozzi et al.1988)。结果表明,遗传谱系和语言分类大致是平行演化关系,不甚完美之处必有其历史、地理、文化等原因。分子生物学家已经发表多篇论文,就全球范围而言,绝大部分地区的语言和基因是匹配的。遗传谱系的枝叉层次丰富,各组距离一目了然,但卡瓦利斯福札给出语言学分类发生树则相当笼统(列出的仅是语系,没有语族、语支等)。此外,伦弗鲁(Renfrew1999,2000),贝尔伍德(Bellwood2011),德迪乌和拉德(Dediu & Ladd2007),李辉(2008),鲍韦恩(Bowern2010),阿特金森(Atkinson2011),西苏、德迪乌和莫兰(Cysouw, Dediu, Moran2012),布尔拉克(Burlak2013),戴蒙德和贝尔伍德(Diamond & Bellwood2013)等,努力将语言学、生物学与考古学的成果结合起来探索人类演变的历史。他们利用语言学家提供的一些资料,试图提出人类基因遗传和语言平行演变的假说。
(二) 印欧语言与分子生物学
对印欧人和印欧语的起源和迁徙问题,西方学者已关注了几百年。立陶宛裔美国考古学家金布塔斯(Gimbutas1970)提出“库尔干假说”,认为印欧人起源于南俄黑海草原的德涅伯河伏尔加河地区。与此相对,英国考古学家伦福儒(Renfrew1987)却认为印欧人起源于安纳托里亚,早期农耕者在不断扩张中把古印欧语带到欧洲。
近年的DNA研究表明,此安纳托里亚的“农业先导”对欧洲人的基因库影响很小,似乎只限于毗邻中东的地区。另一项成果表明,如今的欧洲人几乎没有遗留来自“新月地带”的古代居民基因,很可能远古的农耕迁徙者已被后来的游牧居民所代替。此前的研究也证明,从捷克到阿尔泰地区,一直向南贯穿中亚,M17 这个标记出现的频率都很高。“微卫星定位”的多样性显示,它最早起源于南俄和乌克兰。所有这些基因资料和考古发现,都指向印欧语源于南俄黑海草原。2002 年,芬兰学者佩尔托宁(L.Peltonen)对“耐乳基因”进行研究,采集了4 大洲37 个族群的1611 份DNA 样本,其结论是,对牛奶具有适应性的基因来自乌拉尔山与伏尔加河流域之间,产生于距今约4800 至6600 年以前,然后传播到欧洲、中东和印度次大陆。该研究引起卡瓦利斯福札的兴趣,他推测印欧人进入欧洲可能有两批: 较早的来自安纳托里亚地区,第二批来自乌拉尔和亚洲草原。
西班牙西北部和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人,其语言与现存其他语言没有亲属关系。1944年,西班牙裔墨西哥考古学家吉姆佩拉(P.B.Gimpera, 1891—1974)在《古老的定居点和西班牙人的形成》(El poblamiento antiguo y la formación de los pueblos de Espaa)中,提出巴斯克人是西欧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居民的后代。在对Rh血型的地理分布研究中,证实巴斯克人的Rh阴性频率非常高,由此推测巴斯克人是欧洲最早居民的后裔,而欧洲其他人群则是此后新移民和最早居民的混合。近年对其线粒体和Y染色体DNA多态性的研究支持这一结论。
据奥本海默(S.Oppenheimer)的《英国人的起源: 基因侦探记》(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A Genetic Detective Story, 2006),就英伦三岛居民及其语言,大体情况如下。距今15000—7500年,一批狩猎采集者(与巴斯克人最接近)来到英伦(当时尚未形成三岛),所说可能为古巴斯克语。这股基因流在现代英国人基因库中占3/4(在英格兰占2/3)。距今约6000—4400年,掌握冶炼技术的凯尔特人从伊比利亚来到英伦三岛,扩散到爱尔兰和威尔士,所说即古凯尔特语。这股基因流在威尔士北部地区的现代男性基因库中占1/3,在英格兰南部沿海占10%,在爱尔兰占4%。距今4400年左右,一股更加强大的基因文化潮(与维京人最接近)从现今德国西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登陆英伦,影响了其东部和东南部,所说可能为古斯堪的纳维亚语。这股基因流在现代英国人基因库中占10%—19%。公元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从现今德国北部和日德兰半岛南端入侵英伦。这股基因流在现代英国人基因库的男性基因型中约占5%。就英伦三岛的语言来说,底层古巴斯克语(基因流占3/4)早已了无踪迹(估计被古凯尔特语取代),中层古凯尔特语(威尔士北部占1/3)分化为威尔士语、盖尔语、爱尔兰语等,中层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基因流占10%—19%)为古日耳曼语,表层盎格鲁撒克逊语(基因流占5%)为日耳曼语,最终演变为中古英语。由此可见,早起基因流的比例虽然大,也不决定现今所说语言,反之,后来征服者的语言必然取代早期原居民的语言。
7. 李葆嘉.超越譜系树模式: 语言关系类型学.∥李葆嘉主编.引玉集——语言学与文献学研究论集.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0.
8. 李葆嘉.论语言科学与语言技术.中国语言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扬州大学,2001;又中国语言学报,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9. 李葆嘉.人工语言脑: 自然语言处理装置研制的新思路.第四届汉语词汇语义学研讨会论文,香港城市大学,2003.∥李葆嘉.一叶集.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10. 李葆嘉.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转折: 从同源论到亲缘度.∥王士元主编.汉语的祖先.李葆嘉主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5.
11. 李葆嘉.亲缘比较语言学: 超级语系建构中的华夏汉语位置.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讲座,2008.∥潘悟云,沈钟伟主编.研究之乐: 庆祝王士元先生七十五寿辰学术论文集.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12. 李葆嘉.爱丁堡之谜: 蒙博多的语言进化论和进化模式.第十五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主题报告,黑龙江大学,2014.
13. 李葆嘉,张璇.中国混合语的研究现状和理论探索.语言研究,1999(1).
14. 李辉.人类语言基本元音体系的多样性分析.现代人类学通报,2008(2).
15. 李慧.后基因组时代的生物语言学研究.外语学刊,2013(1).
16. 梁丹丹,顾介鑫.神经语言学研究方法与展望.外语研究,2003(1).
17. 潘悟云.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stics. Monograph Series 8,1995(8).
18. 王士元.演化语言学的演化.当代语言学,2011(1).
19. 吴文.“生物语言学”及术语考究.中国科技术语,2012(2).
20. 吴文.生物语言学研究综述.外国语言文学,2013(2).
21. 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民族语文,1991(3).
22. 徐文堪.分子人类学与当代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东方语言学》编委会编.东方语言学(第四辑).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23. 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stics. Monograph Series 8,1995(8).
24. 朱敏霞.论生物学对语言学的影响.理论界,2014(8).
25. 宗成庆.人类语言技术展望.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通讯,2020(1).
26. Aitchison J. The Seeds of Speech: Language Origin and Evolution.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7. Atkinson Q D. Phonemic Diversity Supports a Serial Founder Effect Model of Language Expansion from Africa. Science, 2011(332).
28. Atkinson Q D, Gray R D. Curious Parallels and Curious Connections: Phylogenetic Thinking in Biology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ystematic Biology, 2005(54): 4.
29. Becker K F. Organism der Sprache als Einleitung zur Deutschen Sprachlehre. Fankrfurt: Reinherz, 1827.
30. Bernhardi A F. Anfangsgründ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Berlin: Heinrich Frllich, 1805.
31. Bellwood P. Early Agriculturalist Population Diasporas? Farming, Languages, and Gen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1(30).
32. Su Bing et al. Polynesian Origins: Insights from the Y Chromosome.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2000(97): 15.
33. Boas F. 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Bulletin, 1911(40): 1-1069.
34.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Baudouin de Courtenay).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знанию.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ъство Академни Hаук СССР, 1963.
35. Bopp F. Vocalismus, Order Sprachvergleichende Kritiken. Berlin: Akademische Buchdruckerei, 1836.
36. Bowern C.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n Australia: Trees, Network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iological Sciences, 2010(12).
37. Brown T G. On the Nature of the Fundamental Activity of the Nervous Centres. Journal of Physiology, 1914(48).
38. Burlak S A. Languages, DNA, Relationship and Contacts. Journal of Language Relationship, 2013(9).
39. Cavalli-Sforza L L, Piazza A, Menozzi P. et al.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Evolution: Bringing Together Genetic, Archeological and Linguistic Data. PNAS, 1988(85).
40. Chavée H. Lexiologie Indoeuropéenne. Paris: Franck, 1849.
41. Chavée H. Idéologie Lexiologique d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Paris: Maisonneuve, 1878.
42. Chambers R.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Published Anonymously). London: John Spriggs Morss Churchill, 1844.
43. Chomsky N.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Hague: Mouton, 1957.
44. Chomsky N. The Logical St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45. Clarke D D, Sokoloff L. Circulation and Energy Metabolism of the Brain. ∥Agranoff B W, Siegel G J. (eds.) Basic Neurochemistry: Molecular, Cellular and Medical Aspects(6th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Raven, 1999.
46. Comte M A.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Vol. Ⅳ). Paris: Bachelier, Imprimeur-Libraire, 1839.
47. Croft W. Explaining Language Chan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London: Longman, 2000.
48. Cysouw M, Dediu D, Moran S. Comment on “Phonemic Diversity Supports a Serial Founder Effect Model of Language Expansion from Africa”. Science, 2012(335).
49. Darwin C R.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John Murray, 1859.
50. Darwin C R. The Descent of Man. London: John Murray, 1871.
51. Darwin E. Zoonomia; or, the Laws of Organic Life Part Ⅰ. London: J. Johnson, 1794.
52. Dediu D, Ladd D R. Linguistic Tone is Related to the Population Frequency of the Adaptive Haplogroups of Two Brain Size Genes, ASPM and Microcephalin. PNAS, 2007(104).
53. Diamond J, Bellwood P. Farmers and Their Languages: The First Expansions. Science, 2013(300).
54. Durkheim D . 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 Paris: Félix Alcan, 1895.
55. Fisher S E. Tangled Webs: Trac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Genes and Cognition. Cognition, 2006(101): 2.
56. Fitch W T.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7. Fuster J M. Cortex and Mind-Unifying Cogn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58. Gall F J, Spurzheim J G. Anatomie et Physiologie du Système Nerveux en Général, et du Cerveau en Particulier(4 vols.). Paris: F. Schoell, 1810—1819.
59. Gall F J, Spurzheim J G. Sur les Functions du Cerveau et sur Celles de Chacune de ses Parties(6Vols.). Paris: J.-B. Baillière, 1822—1825.
60. Gimbutas M. Proto-Indo-European Culture: The Kurgan Culture during the Fifth, Fourth, and Third Millennia B. C.∥Cardona G, Hoenigswald H M, Senn A.(eds.) Indo-European and Indo-Europea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0.
61. Gimpera P B. El poblamiento antiguo y la formación de los pueblos de Espaa. México: Imprenta Universitaria, 1944.
62. Grimaldi M. Toward a Neural Theory of Language: Old Issues and New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 2012(25).
63. 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Haugen E. Language Scienc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1972.
64. Hays D G. Introduction to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New York: American Elsevier, 1967.
65. Head H. Aphasia and Kindred Ddisorders of Speech.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6.
66. Hecht M. Die griechische Bedeutungslehre. Eine Aufgabe der klassischen Philologie. Leipzig: Teubner, 1888.
67. Herbart J F. Lehrbuch zur Psychologie. Knigsberg: August Wilhelm Unzer, 1816.
68. Humboldt W. ber das Vergleichende Sprachstudium in Beziehung auf die Verschiedenen Epochen der Sprachentwicklung. Abhandlungen der K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aus den Jahren 1820—1821. Berlin: Georg Reimer, 1820/1822.
69. Hutton J. Theory of the Earth; or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ws Observable in the Composition, Dissolution, and Restoration of Land upon the Glob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1785/1788(1): 2.
70. Huxley T H. On the Methods and Results of Ethnology. Fortnightly Review, 1865(1).
71. Ipsen G. Der alte Orient und die Indogermanen. ∥Friedrich J, Hofmann J B. et al. (ed.) Stand und Aufgaben der Sprachwissenschaft — Festschrift für Wilhelm Streitberg. Heidelberg: Winter, 1924.
72. Jakobson R. Kindersprache, Aphasie und Allgemeine Lautgesetze. Uppsala: Universitets Arsskrif, 1941.
73. Jenkins L. Biolinguistics: Exploring the Biology of Language.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74. Lamarck J-B. Philosophie zoologique. Paris: Detu, 1809.
75. Lazarus M. ber den Begriff und die Mglichkeit einer Vlkerpsychologie. Deutsches Museum: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 Kunst und ffentliches Leben, 1851(1).
76. Lazarus M, Steinthal H. Einleitende Gedanken über Vlkerpsychologie, als Einla-dung zu einer Zeitschrift für Vlkerpsychologie und Sprachwissenschaft. Zeitschrift für Vlkerpsy-chologie und Sprachwissenschaft, 1860(1).
77. Lenneberg E. Biological Foundation of Languag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7.
78. Lyell C. Principles of Geology. London: John Murray, 1830—1833.
79. Malinowski B.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Ogden C K, Richard I A. The Meaning of Mean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3.
80. Mathew P. On Naval Timber and Arboriculture; with Critical Notes on Authors Who Have Recently Treated the Subject of Planting. Edinburgh & London: Black, 1831.
81. Mcmahon A, Mcmahon R.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82. Meader C L, Muyskens J H. Handbook of Biolinguistics. Toledo: H. C. Weller, 1950.
83. Meillet A. Comment les Mots Changent de Sens. Année Sociologique, 1905(9).
84. Michael C C. The Recursive Mind: The Origins of Human Langu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85. Monboddo L J B.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Language. Edinburgh: J. Balfour ; London: T. Cadell, 1773, 1774, 1786, 1787, 1789, 1792.
86. Mufwene S S.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volution.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87. Mufwene S S. Language Evolution: Contact, Competion and Change.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8.
88. Müller F M. 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in April, May, & June 1861. London: Longmans, Green, 1861/1866.
89. Newbury D F, Monaco A P. Genetic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Speech and Language Disorders. Neuron, 2010(68): 2.
90. Oppenheimer S.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A Genetic Detective Story. New York: Constable & Robinson, 2006.
91. Paris G. La vie des mots tudiée dans Leurs significations, par Arsène Darmestcter. Journal des savants, 1887.
92. Poeppel D, Embick D. The Relation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Neuroscience. ∥Cutler A (ed). Twenty First Century Psycholinguistics: Four Cornerstones.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2005.
93. Post E. Finite Combinatory Processes-Formulation 1. The Journal or Symbolic Logic, 1936(1): 3.
94. Raichele M E. Two Views of Brain Func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0(14): 4.
95. Renfrew C.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London: Pimlico, 1987.
96. Renfrew C. Reflections on the Archaeology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Sykes B. (ed.) The Human Inheritance, Genes, Language, and 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97. Renfrew C. At the Edge of Knowability: Towards a Prehistory of Language.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2000(10).
98. Samuels M L. Linguistic 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ish.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99. Sayce A H. The 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Philology. London: Trübner, 1875.
100. Schleicher A. Die Darwinsche Theorie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 offenes Sendschreiben an Herrn Dr. Ernst Haeckel. Weimar: H. Bhlau, 1863.
101. Schnelle H. Language in the Br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2. Smith W. Strata Identified by Organized Fossils. London: William Smith, 1816—1819.
103. Steinthal H. Der heutige Zustand der Sprachwissenschaft. ∥Steinthal H. Kleine sprachtheoretische Schriften. Hildesheim/New York: Georg Olms, 1850/1970.
104. Steinthal H. Grammatik, Logik und Psychologie; Ihre PrinZipien und Ihr Verhltnis zueinander. Berlin: Ferd Dümmlers Verlagsbuchhandlung, 1855.
105. Steinthal H. Ueber den Wandel der Laute und des Begriffe. Zeitschrift für Vlkerpsy-chologie und Sprachwissenschaft, 1860.
106. Steinthal H. Einleitung in die Psychology und Sprachwissenschaft. Berlin: Ferd Dümmlers Verlagsbuchhandlung, 1871.
107. Tarde G. Las Leyes de la Imitación y La Sociología. Madrid: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Agencia Estata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1890.
108. Turing A M.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1950(New Series, 59): 236.
109. Qian Yaping et al. Multiple Origins of Tibetan Y Chromosomes. Human Genetics, 2000(106).
110. van Driem G. Sino-Austronesian VS. Sino-Caucasian, Sino-Bodic VS. Sino-Tibetan, and Tibeto-Burman as Default Theory. ∥Yadava Y P, Bhattarai G, Lohani R R, et al.(ed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Nepalese Linguistics, Kathmandu: linguistic society of Nepal. 2005.
111. Wallace A R. On the Law Which Has Regul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Species. The Annals and 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 Including Zoology, Botany, and Geology(XVI), 1855.
112. Watkins K E, Dronkers, Vargha-Khadem F. Behavioural Analysis of an Inherited Speech and Language Disorder: Comparison with Acquired Aphasia. Brain, 2002(125): 3.
113. Wells W C. An Account of a Female of the White Race of Mankind, Part of Whose Skin Resembles That of a Negro, with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Colour and Form between the White and Negro Races of Man. ∥Wells W C. Two Essays: Upon a Single Vision with Two Eyes, the Other on Dew. London: A. Constable & Co. Edinburgh, 1813/1818.
(黑龍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210023)
(责任编辑 刘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