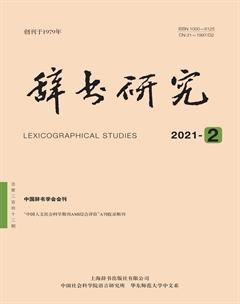是旧词重启还是新词新用
摘 要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是中国社会新旧更替、急剧动荡的时代,社会生活的变化会引起人们观念和认知方式的变化,这一变化在语言特别是词汇层面得到了生动反映。“动物”作为一个双音黏合式组合,最早出现于先秦文献,最后定型为一个承载现代科学概念含义的复音词进入现代汉语。这一衍化过程既有其内因,如双音节黏合式组合单位词汇化的趋势,语言使用者接受、表达新观念的需要,也有外部的影响因素,如日语“回归词”的影响。通过一个语言单位词汇地位的变化及其进入通用语全过程的描述,文章展示了“动物”一词被现代汉语接纳的细节,为认识、说明一个时期社会发展以及观念之变对语言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一个例证。
关键词 动物 类书 新词 外来词
社会生活的变化会引起人们观念和认知方式的变化,这一变化往往与语言现象密切关联。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是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在这种情形下,汉语的词汇层面首先做出了积极反应。有学者指出,这一时期的新词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当时创造的、代表新概念的词或短语;另一种是旧词增添新义的词。前者是词汇性新词,后者是语义性新词。(姚德怀2001)我们认为,“动物”一词不是新词,考察结果表明,它经过了一个词汇化的长期演变过程。此外,词义层面上它所反映的现象也不宜归为一般的词义扩大。按传统用法,“动物”因具有“能活动”这一外部特征,一直用来指称“鸟兽虫鱼”一类生物,进入19世纪以后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它获得了现代生物科学的概念内容,但这一任务的承担一开始并非是由“动物”一词接手的,早期外汉词典的对译可以说明这一点。(仇志群1996)在词汇化定型和语义内容刷新的任务完成后,“动物”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并成为高频用词。因此,我们认为“动物”这类词汇单位可称为语用性新词,区别于上述词汇性新词和语义性新词。
我们可通过“动物”一词词汇地位的变化以及进入现代汉语全过程的描述,展示“动物”这一语用性“新词”被接纳的细节,以展示说明社会观念的变化是如何通过词汇层面对语言的发展变化产生影响的。
一、 “动物”一词的来源和本义
“动物”作为一个双音节黏合式组合单位,很早就见于先秦文献。
《周易》:本乎天者,谓动物,本乎地者,谓植物。“动物”和“植物”的组合,在《周礼· 地官·大司徒》中也多次出现。如: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鳞。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羸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
不过这里的“动物”可能还不是一个词。《周礼》中“~物”的组合形式很多,除了“动物、植物”,以及上面的“毛物、鳞物、膏物、羽物、核物、介物、羸物、丛物”外,还有“米物、灰物、炭物、兽物、鱼物、旗物、腊物、狸(埋)物、互物、蜃物”等。例如:
舂人掌共米物︱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征令︱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春献王鲔,辨鱼物,为鲜薨,以共王膳羞︱以旗物辨乡邑,而挛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后之屯,而戮其犯命者︱凡祭祀,共豆脯,荐脯、膴、胖,凡腊物︱鳖人掌取互物,以时簎鱼鳖龟蜃,凡埋物︱掌蜃掌敛互物、蜃物
从《周礼》中“~物”格式的习惯用法来看,“动物”“植物”应是一个临时组合。“动物”即能自行运动、活动的东西。《史记·五帝本纪》: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张守节《史记正义》:动物谓鸟兽之类,静物谓草木之类。此处,“动物”是与“静物”相对的。至于这一时期的“植物”,如同“动物”,也是一个黏合式组合。“植物”即“直立之物”。《说文解字》段注:“植当为直立之木。……植之引申为凡植物,植立之植。”关于“动物”“植物”的取名,来自古人对“动物”“植物”所指称事物的外部特征的直接观察。
南宋王应麟编撰的大型类书《玉海》200卷,分天文、地理、官制、车服、器用、食货、郊祀、祥瑞、音乐、宫室等21门。毎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每部之下,又分为若干类目,祥瑞部下有植物、动物等类目。清代曹昌言撰《多识类编》二卷(雍正丁未年,1727),也分动物、植物二门。我们认为,这里的“动物”“植物”还是本乎《周礼》中的意义,作为一个语言单位仍未词汇化,更非现代学科意义的“动物、植物”。《朱子语类》卷四:“‘本乎天者亲上,凡动物首向上,是亲乎上,人类是也。”“心本是个动物,怎教它不动。”“动物”就是能动、善动的东西。
“动物”还可以名之为“动类”。《文选束皙〈补亡诗六首〉》:“动类斯大。”“动类”张铣注“禽兽也”。唐刘禹锡《伤亡赋》:“何动类之万殊,必雄雌而与俱。物莫失俪以孤处,我方踽踽而焉如!”南北朝谢灵运《山居赋》:“植物既载,动类亦繁。飞泳骋透,胡可根源。”此处“动类”与“植物”对举。不但有“动类”也有“植类”。晋戴凯之《竹谱》:“植类之中,有物曰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明陈耀文所撰类书《天中记·交州记》还用“植类”的说法:“竹非草非木,植类之中有物曰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 清初姚止庵撰《素问经注节解》:“木为植类,萎则仆,强则挺直而立也。”到近代严复的《天演论》(1896),仍称动类、植类:“地球本为流质,动植类胚胎萌芽,分官最简。”(导言二·广义)或作“动植之伦”“动植庶品”。[1]
二、 传统生物学的认知——类书的分类:草木鸟兽虫鱼
中国古代提倡“博物多识”“博物洽闻”,提倡读书人要做到学问广博、见多识广。这种“多识之学”主要是遵循孔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训导进行培养、传播的。古代最早的分类辞书《尔雅》,即是“鸟兽草木”等名物的解释,列有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类,成为古人学习动植物常识的一种教科书。《诗经》是一个“多识之学”依附的中轴。魏晋南北朝时期陆机所著的“诗经学”著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一部专门针对《诗经》中提到的动植物进行注解的著作,被看作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动植物的专著”。该书共记载草本植物80种、木本植物34种、鸟类23种、兽类9种、鱼类10种、虫类18种,动植物共计174种。对每种动物或植物不仅记其名称(包括各地方的异名),而且描述其形状、生态和使用价值。该书注释《诗经》名物的体例和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其“草木鸟兽鱼虫”的分类,被历来的类书相关部分的分类所沿用。宋郑樵所著《通志》(包括二十略)列在史部别史类,其中《昆虫草木略》是作者有感于“大抵儒家多不识四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便“会同”《诗经》《尔雅》注疏有关鸟兽草木的内容而编纂的。宋韩境的《全芳备祖》是专门的植物类书,其编纂理念即来自“昔孔门学诗之训有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现存最大的集成式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设立了“博物汇编”的名目,之下包括“多识之学”的禽虫典、草木典。
据统计,现存类书尚有两百种左右。在综合型类书中,完整保存至今,比较重要者有七世纪前期隋末唐初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唐欧阳询等的《艺文类聚》(624)、唐徐坚等的《初学记》(727)、唐白居易的《白氏六帖》(八世纪前期)、宋李昉等的《太平御览》(984)、宋王钦若和杨亿等的《册府元龟》(1013)、宋高承的《事物纪原》(1085年前后)、明王圻和王思义的《三才图会》(十六世纪后期)、清张英和王士禛等的《渊鉴类函》(1710)、清陈梦雷(蒋廷锡)等的《古今图书集成》(1726)等。上下千年,这些类书都不以“动物”和“植物”来分类。
如唐徐坚撰《初学记》,其中列有兽部、鸟部、鳞介部、虫部。宋吴淑编撰的《事类赋》,全书三十卷,其中有禽部两卷、兽部四卷、草木部、果部、鳞介部各两卷、虫部一卷。宋《太平御览》为:兽部、羽族部、鳞介部、虫豸部。宋《太平广记》分类较细,为:龙、虎、禽鳥、水族、昆虫部。清《渊鉴类函》为:鸟部、兽部、鳞介部、虫豸部。清《格致镜原》事物分三十类,相应部分为鸟、兽、水族、昆虫四类。明末编成后又经清人增补注释的蒙书《幼学琼林》,凡四卷,按内容分成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花木等30多类。第四卷32章为“鸟兽”。
唐《艺文类聚》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官修类书,全书共分为四十六“部”,“部”下有“类”,即基本知识单元,总共227个。按现在的认知应该归入“动植物”的品种,在该书分别归入百谷、果、木、鸟、兽、鳞介、虫豸等部。以动物而言,该书九十三卷到九十五卷的兽部有马、牛、驴、象 犀、兕、貔、熊、鹿、獐、兔、狐、猿等。龙、蛟、蛇、龟、鳖、鱼等归在鳞介部。而凤皇、鸾、比翼鸟、雀、 燕、鸠、雉、马、白鹿、狐、兔、白狼、比肩兽、龟、鱼等却不在“兽部”或“鸟部”,它们都归在“祥瑞部”。
《艺文类聚》的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宋人的《事文类聚》、清代官修的《渊鉴类函》都模仿它;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也都采用了这个体例。如《渊鉴类函》相应的部类有食物部、五谷部、药部、菜蔬部、果部、花部、草部、木部、鸟部、兽部、鳞介部、虫部等。对照《艺文类聚》,可以看出它们在分类上的相承关系。不仅是类书,传统的图书分类也皆遵循之,《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谱录类”就分列“草木鸟兽虫鱼之属”,凡21部。
《本草纲目》这样的专业著作也依循了类书的分类体例。该书卷五至五十二为各论,收药1892种,附图1109种。按其“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的体例,以部为纲,以类为目,计分16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60类。其中第三十九卷至第四十二卷为虫部,第四十三卷至第四十四卷为鳞部,第四十五卷至第四十六卷为介部,第四十七卷至第四十九卷为禽部,第五十卷至第五十一卷为兽部。
传统分类模式反映了古人对事物的认知特征。类书,作为“类事之书”(王应麟语)是古代的资料汇编,其分类名目和基本框架则反映了中国古代围绕“博物多识”建立的知识结构和观念。[2]以上例子说明中国传统书目中没有分出“博物”专类,说明中国古代还没有建立起“博物学”概念,具体而言,所谓“多识”之学只是依附《诗经》文本而发展起来的动植物知识。(于翠玲2006)
我们赞同现代学者的这一认识:中国传统分类模式的特征,是以“人”而不以自然作为基本出发点的,即以事物相对于人的关系作为区分它们的主要依据。许多类书中,蝗虫不放在虫类,而是放在“灾异”类。因为蝗虫给人带来灾害,灾害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动乱。对事物的认识分类偏重于其直观性,即以事物外在的,可以被人所直接感知的形态作为区分的依据。例如将天文与气象知识作为一类,因为直观上它们都发生在“天”上。所以“兽、鸟、鱼、虫和木、草、果、卉等始终没有被归纳为动物、植物这样的大类”,是因为它们的外在形态相异,凭人的直观印象就可判断异同,所得的分类正是人直观判断的结果。(梁从诫1986)
三、 现代汉语前期阶段“动物”一词的词汇地位
从一些个案可以看到,进入近现代社会的前夕,从与“人”的关系角度观察格物,也逐渐产生了接近现代动植物学意义的分类概念。17世纪末,清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专门论述“动植物”与人类的关系:施于动物而不施于植物,正是知类。此正释氏不容泯之天理,自然须得如此。恰好引入理一分殊去,何反以此讥之?植物之于人,其视动物之亲疏,此当人心所自喻,不容欺者。故圣人之于动物,或施以帷盖之恩,而其杀之也必有故,且远庖厨以全恩。若于植物,则虽为之厉禁,不过蕃息之以备国用,而薪蒸之,斫削之,芟柞之,蕰火之,君子虽亲履其侧而不以动其恻怛,安得以一类类之耶?王夫之在这里用“动物”不用“禽兽”,也与他的思想观念有关。在他的思想体系里,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事物和行为,都被他称为“禽兽”。“禽兽”被他赋予了特定意义。
但是直到19世纪,如果把这一时期看作是现代汉语的前期阶段,当时的种种迹象明确显示,“动物”的词汇化仍未最后完成,而这一过程基本与汉语社会为接受现代生物科学的理念而寻求一个表达形式的过程同步。
根据马西尼(1997),1864年由丁韪良译成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把英语的personal property 初译为“动物”,后来才改为“动产”。来自日语的“动产”对应的英文原文似应是movables或movable properties,《万国公法》也许据此译为“动物”,即可移动的东西。 显然,如果“动物”像现在一样是个常用词或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译者绝不会用“动物”来对译英语中的“动产”一词。[3]
我们还可以从早期的外汉和汉外词典中得到验证。外汉词典的释文总是要尽可能地找出等价形式,如果是词与词的对释,目的语的选词应该是当时语言社会通行的或被认可的。也可以这样说,出现于现今同类词典同一条目下的必选词项,在早期外汉词典中如果不出现,那么可以认为这个词当时还不通行,还没有被认可。按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利用早期外汉词典的释文对“动物”的词汇地位进行考察。
例如:罗存德(D.W.Lobscheid, 1866)《英华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animal 一词的释文为:生物、生灵、畜生、牲口。1903年T.Theodor Wang《商务书馆华英词典》(Commercial Press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初版将animal释为:生物、生灵、禽兽(该词典1913年第十版仍同此)。1905年司登德(G.C.Stent)主编的《英汉官话口语词典》(From English to Colloquial Mandarin Chinese)将animal一词释为:生灵、活物、生物。我们还可以把《英汉官话口语词典》同以这部词典为基础编成的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标准英汉官话词典》)(1916)做一比较。后者的主编赫墨龄(K.Hemeling)也曾参加过《英汉官话口语词典》的编写。赫氏1916年本animal条释为:动物(新)、甡动物(新)、胜(新)。“新”即“新词”,是当时教育部组织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审订词语时所加的标注。参加审订工作的学者不会不知道“动物”一词早已见于先秦典籍,仍标注“动物”为新词,想来是从该词的使用情况和词汇地位来考虑的。除了用“动物(新)”为animal做释,词典还拟定了一个让人很难理解的“甡动物”和“胜”(非“勝”字的简体)。这也反映当时在用什么形式对释animal一词时所表现出的犹豫。(仇志群1996)
从“动物”组成的复合词上,也可以看出“动物”一词的现代概念,一开始在人们的认知领域内并不是很清晰。
据《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动物园”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曾先后有过以下名称(按开始见于文献的时间):“生灵院”(1854)、“生灵苑”(1866)、“万兽园、万牲园”(1868)、“野獸园”(1870)、“牲灵园、万牲园”(1871)、“生物园、琐卧拉治戈加登”(1876)、“禽兽园”(1880)、“生灵囿”(1881)、“动物园”(1887)、“动物院”(1894)、“兽园”(1901)、“动物园、生物院”(1901—1902)、“动物园”(1921)。有些记述性文章,一篇之内也有用名不定的现象。
生灵院 伦敦乃京都也……宫殿书院文儒所萃,博物院、施医院、养济院、生灵院,皆景象繁华。(慕维廉《地理全志》,1854)
生物囿 生物囿中,藏印本三万五千册。伤老病院中,藏印本三万册。(墨海书馆《六合丛谈》,1857—1858)
生灵苑 往生灵苑。虎豹狮象蛇龙之族,无不具备。(斌椿《乘槎笔记》,1866)
万兽园 其地有万兽园,为众所同游之胜景,……其中珍禽奇兽不可胜计。(志刚《出使泰西记》,1872)
野兽园 往观其野兽园。泰西各国,皆有聚草木鸟兽之所,借资多识,故不顺述。(志刚《出使泰西记》,1872)
牲灵园 牲灵园禽惊兽骇,诚为未有之浩劫也。(张德彝《随使法国记》,1873)
万牲园 午后随志、孙两钦宪游万牲园,有管园官巴克尔者引游各处。所畜鸟兽倍于前年,中有所未见者,如玄豹、玄狼、双角犀……(张德彝《欧美环游记》,1875)
生物园 旁边有生物园(西语称琐卧拉治戈加登)一区,鸟兽鳞虫,无所不有。(李圭《环游地球新录》,1876)
生灵院 伦敦等大城中有生灵院,内畜各国各种之兽类,无论野者熟者,俱可察其孕字之期,不至有误。(傅兰雅《格致汇编》,1877)
兽园 午后,同张、荫两侍郎,李提督希德等往观柏林兽园。园方广不止一方英里,走兽如虎、豹、犀……斑马等。(李凤苞《使德日记》,1878)
禽兽园 初九日,在汉倍克游禽兽园。(徐建寅《欧游杂录》,1880)
禽兽囿 二点钟,游禽兽囿。(徐建寅《欧游杂录》,1880)
动物园 动物园在教育博物馆南,入门有小鱼池数方。(陈家麟《东槎闻见录》,1887)
动物公园 游浅草之动物公园。有鸟名“拔立根”,产自美利加。有虎一。(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9)
动物场 午后进樱田门,过万世桥,亦名目镜桥,游上野公园,观动物场。(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9)
生灵院 分院共计十五:一农工院,一种植院,一生灵院,一渔务院,一矿务院,一机器院,一运务院,一工艺院,一电务院……(郑观应《盛世危言》,1894)
动物院 游动物院,有虎,有熊,有豹,有象,有鹤。(黄庆澄《东游日记》)
生物院 自生物院而外,无复有猛兽者矣,只有驯兽耳,盖至是全地皆为人治之地矣。(康有为《大同书》,1901—1902)
动物院 (各地政府)则必有金行、公园、博物院、植物院、动物院、美术院、讲道院、大商店、邮电局、飞船铁道局。(康有为《大同书》,1901—1902)
动植物园 乐曹掌人间进化极乐之事,凡音乐馆、博物院、动植物园、其施舍人伦之事、奖励之张掌焉。(康有为《大同书》,1901—1902)
动物园地方自治之属—— 植物园、动物园 (康有为《大同书》,1901—1902)
我们看到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在“动物园”之前,出现了众多相当于英语zoological gardens 的丰富的汉语“曾用名”。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人同一著述中出现了用名不定的现象。清志刚《出使泰西记》(1872)兼用“万兽园”“野兽园”;清徐建寅《欧游杂录》(1880)用“禽兽园”,又用“禽兽囿”;清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既用“动物公园”,又用“动物场”。清康有为的《大同书》前后分别使用三个名称:“生物院”“动物院”“动物园”,还用了“动植物园”这样的简缩形式。同治五年(1866),张德彝随蒲安臣、志刚出使欧美,写下《再述奇(欧美环游记)》,其中相关部分称“动物园”为“万牲园”。四年后(1870)他又随访法国,在法国待了一年,用日记形式写了《三述奇(随使法国记)》,其中描述法国的动物园篇章中,用的是“牲灵园”。
“动物园”一名称的定型过程,与社会对“动物”一词的熟悉、接受过程基本同步。
四、 “动物”一词进入通用语一段路程的回望
根据文献反映,“动物”一词的引进或者说“启用”,最大可能是受日语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渠道需要细节的展示。清黄遵宪1879年《日本杂事诗》中已见“动物”一词。我们注意到,最早使用“动物×”称说方式的大都出于记述者的赴日游记,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如“动物园”见于清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1887),“动物公园”“动物场”见于清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9),“动物院”见于清黄庆澄《东游日记》(1893)。
日本文化很多是通过书籍翻译影响到中国的。日本明治维新后掀起西学高潮,翻译了大量生物学书籍,编译了大量近代生物学教科书,中国也随之兴起“翻译东书热”。这些译著为中国学习普及西方科学知识提供了途径。据谭汝谦主编(1980)《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1816年至1911年的15年间,日文中译本达988种,其中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占172种。由于日本使用的译名基本符合汉语构词习惯,很大一部分日译生物学名词被中国接受。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动物学大辞典》,编纂工作前后历时十几年,编写工作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该词典附录日本假名的词语6000多条,如此重视日语的名词形式,自然也多有采撷。德国汉学家米列娜和瓦格纳(2015)37-47也曾研究指出:在清末“新政”早期,我们可以看到前一阶段出版的一系列百科全书大量再版的状况,但对于新编百科全书而言,由于懂日文的人数迅速增加,使得较为发达的日文百科全书成为重要和现成的信息来源。因此这一时期快速增长的中文百科全书,往往与日文文本直接相关……1903年问世的中文百科全书,几乎都是借鉴与模仿了日文百科全书(直到民国时期,英文百科全书才成为主要的模仿对象)。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编写的外汉词典,也采取拿来主义,大量吸收日语译词。一些英华词典利用日本编的英日词典作为主要参考书,如《英华合解辞汇》(翁良、唐澂等编,1915)的例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吾国通行之英汉字书非由英文本直譯、即由和文本改纂。”外汉词典在当时也成为日语新词流播的一个来源。
教育也是接受来自日语文化影响的重要渠道,学校学科的设置、教材的引进或编写,直接影响广大的受教育者,进而扩散至整个社会。清政府于1904年开始颁行《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把这个学制与1900年日本实施的学制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基本上是依样画葫芦的。”(樊洪业1998)按“癸卯学制”中的系科设置,高等小学堂“格致”一门规定,要使学生了解“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形象质性,并使知物与物之关系,及物与人相对之关系”。中学堂设“博物”课,“其植物当讲形体构造,生理分类功用;其动物当讲形体构造,生理习性特质,分类功用”(樊洪业1998)。大学堂下设置的格致科大学,分为六门,其中一是动植物学门。
与博物学科的引入相配合,博物学教科书随之出现,推动“动物”“植物”等一批新词进入通用语。其中,西方的一些科技译著,以东西相配合的节奏,对汉语新词语的创制推广做出贡献。来华的英国传教士艾约瑟,于19世纪末编译了《植物学启蒙》和《动物学启蒙》两部书,后者译自法国动物学家爱德华的Zoology Primer。这两部书被京师大学堂颁布的《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和江苏省的《高等小学堂暂用课本之书目》收入。杜亚泉(1873—1933)的《博物学初步讲义》作为“师范讲习社师范讲义”,在第一章绪言中关于“博物学之范围”,明确说明“鸟兽之类谓之动物,草木之类谓之植物,至土石等无生物,大都存于地内采诸矿中,故又称为矿物”,“博物学者,即合动植矿物而研究之学问也”。[4]
除了教科书,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日文化交流的潮流影响下还编纂出版了为数可观的词典和新型类书,对新词的推介和规范化起到重要作用。1903年,曾留学日本的汪荣宝和叶澜编纂了《新尔雅》,该书借用《尔雅》的名目和形式,以“释”为类目,每一类目关联某一学科,介绍了十四个领域的核心概念,其中包括释地、释生理、释格致、释动物、释植物等类。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以辞书形式介绍西方新学科门类知识的读物,同时推广、普及了新学科的名词术语。百科性辞书中影响最大的是黄摩西(1911)于20世纪初编撰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这是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辞书。“本书之特色”定为“动植物生理与生理科互参”。词典附有“科学记号”表,其中“动物学”标为“动”,“植物学”标为“植”。“动物”和“植物”已经被作为学术名词确定下来。德国汉学家米列娜和瓦格纳(2015)对这部词典的内容、编辑特色、历史地位等做了评介,并指出这本词典所受的日本的影响。 从时间上看,宣统三年是出版时间,完成这样一部一百几十万字的大词典的编辑任务,估计要几年的时间。词典反映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对新学新知接受的状况。
当时所编纂的词典,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与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相配合,这样也通过教学活动把新词语的推介、规范推向社会。例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上海宏文馆出版的曾朴、徐念慈合编的《博物大词典》,主要是对动植物的术语提供各种解释,凡例中称:“我国通行学界者,只有字典而无辞典。自译籍风行,始有注意于撰普通辞书以便读者诸君之检查。本书为教师、学生读书参考之用。”[5]新式辞书与新式教科书配套编辑和出版,成为当时的一种编纂思路和推销方式。1921年出版的一本《博物词典》(彭世芳等编著,中华书局),其“编辑大意”仍然坚持未变:“本书包括中学教育上博物教材之全部,与本局新式理化词典相辅而行。”
“动物”“植物”的“旧词重启”或者说“新词新用”,见证了那一时期国人在新学新知的冲击下观念和认知方式的变化。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教育丛著第五十种《中学校之博物学教学法》(1925)总结道:博闻广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十八世纪以前研究动植物学底一个态度,中国从前教授动植物学也不过如是而已。再看20世纪初徐珂(1984)在《清稗类钞》中对动植物的描述:“植物为有机物之一,与动物同称为生物,其体由细胞构成,摄取无机物以为营养。”“动物为有机物之一,与植物同称生物,有知觉、运动、营养、生殖之机能。下等者,由单细胞构成,与下等植物不能显别。高等者,由种种细胞构成,复杂特甚。种类繁伙,在世界中之总数,达三十余万种。”而动植物的研究属于“理学”门类:“理学有化学、气学、重学、数学、矿学、画学、天文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机器学。”显然,这已经不是“动物,禽兽也”的简单认识。“动物”“植物”等名词在国人语文生活中逐渐活跃起来的状态反映,语言背后是国人认知上从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到现代科学高度的巨大飞跃。
进入通用语的“动物”“植物”这类新名词(“新”,主要是从语义内涵来说),对其来源可能有不同意见,不管怎么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一阶段,中日文化交流的热潮所起的巨大的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五、 结语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是中国社会新旧因素加速更替,急剧动荡的时代。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从四面八方如潮涌来。社会的、生存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语言的呼应。特别是语言的词汇层面,大量新词语的进入产生,视觉上给人万花筒般的印象。一方面,社会的交流、表达需要新的概念工具,另一方面,新的词语带来新知新见的同时,也影响、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传统的思维模式。这一时期,社会语言活动中对词语的选择、整理、定型、扬弃、规范,折射社会的万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本文对“动物”一词的“考今”,从“社会—观念—语言”的宏观视角尽量展现语言变化的细节,提供了一个有完整故事可讲的语言成长的案例。
在此,我们联想到有的学者论述的“睡美人”现象。所谓“睡美人”现象,指的是某一论文发表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乏人关注,之后近乎突然地就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和征引。有学者就用“睡美人”现象解释某些词语的历史演变。[6]有的词语产生的时间不短,但此后很长时间一直处于沉睡状态,到后来的某一时期“近乎突然地被唤醒”,踊跃地进入语文生活中。研究者认为:“这类‘睡美人词汇在汉语及其他语言中想必还有不少,其沉睡时长和深度、唤醒的强度和动因等问题,都值得今后的研究予以重视和关注。”我们认为,“动物”一词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汉语词汇史上的一位“睡美人”。
诞生于先秦时代的“动物”一词,一路走来,道阻且长,随着人们认知的变化,带着现代科学理念色彩的“动物”一词一步步进入到现代汉语通用语。针对本文开头的题目之问“动物”一词是旧词重启还是新词新用,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回答:在词的形态体貌上可看作是旧词(一位“睡美人”),在词语的语义内涵的重构以及唤醒的状态上不妨视之为旧词新用(“睡美人”的被突然唤醒)。
附 注
[1]关于“动类”“植类”的用例引自北京语言大学BCC现代汉语语料库。
[2]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类事之书始于《皇览》。”
[3]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的高柏先生(Koos Kuiper)也给笔者提供了这个例子。
[4]据杜亚泉、杜就田《博物学初步讲义》1917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师范学校及中小学教科书全文库。
[5]据曾朴、徐念慈《博物大词典》,上海弘文馆,1907。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图书全文库。
[6]史文磊(2019)在《“鉴”“鉴于”“有鉴于”异同考辨——兼论跨层结构词汇化问题与词汇史上的“睡美人现象”》一文中分析了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一种“睡美人”现象。原来指的是某篇论文在长期被冷落后突然受到密集的关注,史文磊认为“可以化用这个美丽的名字来形容”一个词的历史演变过程。
参考文献
1. 樊洪业.从科举到科学:中国本世纪初的教育革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1).
2.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
3. 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
4. 教育杂志社编.中学校之博物学教学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5. 梁从诫.不重合的圈——从百科全书看中西文化.走向未来,1986(4).
6. 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7. 米列娜,瓦格纳.思维方式的转型与新知识的普及——清末民初中国百科全书的发展历程.复旦学报,2015(2).
8. 仇志群.从早期外汉词典看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中国语文,1996(6).
9.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 史文磊.“鉴”“鉴于”“有鉴于”异同考辨——兼论跨层结构词汇化问题与词汇史上的“睡美人现象”.辞书研究,2019(5).
11.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长沙:岳麓书社,1991.
12.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北京:中华书局,2009.
13. 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15. 徐珂.清稗类钞·植物类/动物类.北京:中华书局,1984.
16. 姚德怀.近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序.∥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近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17. 于翠玲.从“博物”观念到“博物”学科.華中科技大学学报,2006(3).
(聊城大学文学院 山东 252059/鲁东大学汉语辞书研究中心 烟台 264025)
(责任编辑 马 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