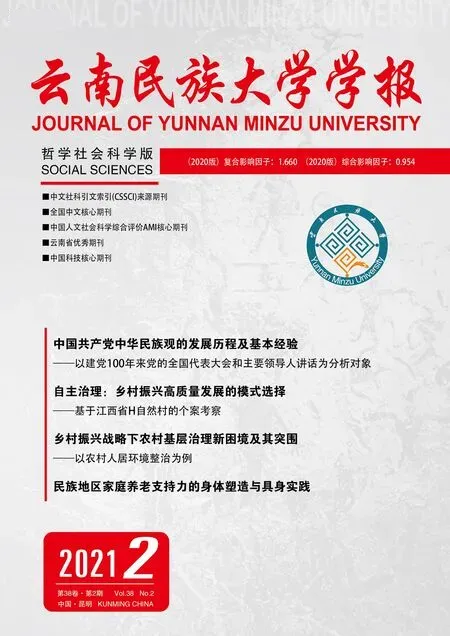公众舆论对清政府应对边疆危机的冲击与挑战
——以片马事件为中心的讨论
曾黎梅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文献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34)
近代以来报刊媒介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大规模公众舆论的形成,对清政府应对边疆危机的传统方式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从认识报纸对边疆危机事件的影响,到出台相应法律、采取应对措施,反映了在现代传播媒介发展初期,清政府提升边疆危机应对能力的艰难历程。本文试图梳理清政府限制报刊参与边疆危机事件的过程,分析在这一背景下,报刊媒介如何构建片马事件的报道要素,使其发展成为全国民众关注和重视的边疆危机事件,进而探讨清政府如何应对公众舆论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及其取得的成效。
一、管控舆论:清政府对报刊媒介的规范
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针对报纸的“专律”。1901年颁布的《大清律例》中,仅有“造妖书妖言”这一条款。条例中的“妖书妖言”包括“邪言”“淫词小说”“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等内容。(1)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有关出版的各种法令”,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311~312页。具体规定如:“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千里,合依量情分坐)。若(他人造传)似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斩,监候。若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人,不及众者,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至狂妄之徒,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亵嫚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即时察拿,審非妖言惑群者,坐以不应重罪。”“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由此可见清政府对民间言论管控的措施极为严酷,从创作者、传播媒介到传播者都有相应的惩罚规定。在严苛的惩罚制度下,本土报刊几乎不敢涉及禁载内容。一些本土报纸以假借西方人的名义,或寻找西方人为报刊庇护人等方式,逃避清政府的监管。
自现代报刊传入后,清政府对待报刊的认识和态度不断变化,从戊戌变法时期的支持,到戊戌政变后的查禁,再到清末新政时期的广设官报。在这期间,华文报刊从百余种增加至500种,连同陆续停刊者,共计有700-800种之多。(2)桑兵:《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报刊的繁荣局面促进了报界团体的建立,“报业人员除以报馆为单位开展活动外,还运用团体组织形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3)赵建国:《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页。报界团体的建立,使报刊界的力量得以联合,社会影响进一步增强。由于清政府对“妖言邪书”并没有严格的限定,使地方官员缺乏对报刊的具体评判标准,增加了报刊的监管难度。重新制定相关法规,细化规则条例,成为清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自1906年起,清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与新闻出版相关的法律法令。1906年7月,清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传媒管理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以下简称《专律》),对相关条例进行细化,但《专律》的规定并不具体,没有很强的针对性,无法满足形势的要求,虽制定但并未颁行。同年10月,清政府又颁布《报章应守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但《规则》只规定了禁载内容,没有相关处罚措施,且该规则由清廷京师巡警总厅公布施行,“在京师及以外地区缺乏法律效力,所以对遏制上海、广东等沿海地区报刊的反清言论几无效果。”(4)倪延年主编:《中国新闻法制通史·史料卷》(第5卷),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页。1908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新闻法《大清报律》诞生。“《大清报律》实脱胎于日本报纸法。由商部拟具草案,巡警部略加修改。”“但各报馆延不遵行,外人所设者尤甚。宣统二年,由民政部再加修改,交资政院议复后,请旨颁布。”(5)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有关出版的各种法令”,第319页。
对于对外交涉,清政府一直采取保密策略,并不轻易对外公布信息。西方传播媒介传入后,清政府更加注重外交信息的保密。如清政府颁布的《通饬中外交涉事件宜加慎密案》,其中就有“案查各国通商以来凡中外交涉事件理宜慎密,叠经本衙门奏请谕旨通饬各省钦遵办理在案,诚以事关重大有可与各国咸知之事,亦即有慎密筹商不可宣露之件,不独各省来往文移书札宜防泄漏”等内容。(6)孙学雷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5页。中日甲午战争后,革命党日益重视边疆危机事件在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将其作为满清“恶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攻击政府辱国丧权”(7)[日]小岛淑男:《中国国民会与辛亥革命》,丁日出译,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2年第8期。。孙中山指导云南留日学生创办革命报刊时,指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8)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云南杂志选辑》“序”,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鉴于内政、外交和军事内容的敏感和重要性,清政府逐步将相关内容特别纳入报律中,具体规定参见表1。

续表1
资料来源:1.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有关出版的各种法令”,第319~324页。2.郭锡龙主编:《图书馆暨有关书刊管理法规汇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3.倪延年主编:《中国新闻法制通史·史料卷》(第5卷),第110~111、122~123页。
从表1可以看出几部报律的特点与变化。第一,从惩罚的力度来看,相较于《大清律例》中对“造妖书妖言”的严酷规定,其余的法律法规更为宽松,有的只有禁止事项,并无具体的惩罚规定。第二,从内容来看,清政府关于报刊的规定逐渐细化、规范,可操作性不断增强。第三,从时间来看,报律的制定远远落后于国内报刊发展的速度,加之由于外国势力的影响、干涉和制约,报律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第四,从相关条例明确规定报刊对关于外交、军事、内政问题禁止刊载的内容及其处罚规定来看,反映了清政府对上述方面舆论影响的认识存在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民政部修订《大清报律》改为颁行《钦定报律》时,《钦定报律》删除了原《大清报律》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的内容。修改《大清报律》第“十二条”为“外交、海陆军事件及其他政务,经该管官署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登载。”并将惩罚条款修改为“违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者,处该编辑人员以二百元以下、二十元以上之罚金。”对于这一修改,军机处曾表达强烈的反对意见。军机大臣认为,“政务之秘密为国家安危所系,故中外刑律,均严定科条,所以预防机务之漏泄,与外交、军事同一重视,并无轩轾于其间也。”如果是“事涉机密,当然不得登载”,不需要再由官署去禁止。(9)《会奏资政院复议报律第十二条施行窒碍照章分别具奏折》,倪延年主编:《中国新闻法制通史·史料卷》(第5卷),第119~120页。最终,军机处的意见并未被采纳。《钦定报律》的颁行,给了报刊登载既涉及内政、外交,又涉及军事信息的边疆危机事件以很大的自由空间,“至于报道和评论,只要不是直接号召暴力革命,即使是对清廷内政外交和皇室的尖锐批评,报律也都不加以限禁。”(10)陈钢:《晚清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官员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对报刊进行监管,如汉口《楚报》以宣布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被封,主笔被判监禁10年;《重庆日报》以揭载知府鄂芳劣迹被查封,“主笔卞小吾下狱死”;《济南报》、上海《中外日报》《时报》《警钟日报》等“屡载德国在山东有不利于中国”,德国领事请各地当道“禁止登载”等。(1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60~161页。
总的来看,尽管清政府不断出台和修订针对报刊的法律法规,但具体措施往往参照欧美国家和日本,一些规定脱离中国实际。而“经该管官署禁止登载者”的规定,使报律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受地方官员的主观意识影响较大,各地执行宽严不一,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并没有实现对报刊实行规范、切实有效的管理。报刊在边疆危机事件中的作用及影响,以及清政府在报刊管理和运用上的不足和缺陷,在片马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制造、引导舆论:《申报》《大公报》对片马事件的叙事逻辑
任何事件的发生,都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新闻报道对事件的“追根溯源或刨根问底”,能够使事件本身得以放大,以获得民众的关注,使一件“小事”成为一个重大事件。1900年,英兵就曾过界烧毁腾越厅属茨竹、派赖各寨,枪杀土守备、土练、土民110余名,(12)台湾“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六册《西南卷》(一),2005年,第105页。这次事件被称为“左孝臣事件”。由于茨竹、派赖与片马、古浪、岗房同属于小江流域,学界往往将“左孝臣事件”视为“片马事件”的前奏。“左孝臣事件”几乎未在国内产生任何波澜,但“片马事件”却在国内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在“片马事件”的传播和影响扩大的过程中,报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1910年5月20日前,云贵总督李经羲就向清政府奏报片马地区发生冲突的情况。(13)《片马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馆藏号:02—17—002—03—002。1910年10月10日,李经羲致电外务部,说明“本年片马夷民与登埂土司交哄,英领竟指为缅地出头干涉”“近谣传有英兵将实行驻守片马各处,已饬西道密为防探”,提请外部与英国驻华公使沟通与英国政府勘办滇缅界务的问题。(14)《滇督李经羲致外部请与英使提议滇缅界务以便勘办电》,王彦威,王亮辑编:《清季外交史料》(8),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97~4398页。此后,李经羲又陆续向外部致电说明“缅边腾龙界桩被英人去标削字请趁机查勘”(15)《滇督李经羲致外部缅边腾龙界桩被英人去标削字请趁机查勘更正电》,王彦威,王亮辑编:《清季外交史料》(8),第4406页。。1911年1月19日,李经羲再次致电清政府,报告“英兵抵片马并胁各夷降附”的消息。对于李经羲多次致电报告英兵侵占片马的进展和分析事件对西南区域安全的影响,提议要“筹防备战”不能“以一隅而误大局”,清政府均不作积极回应。军机处认为,李经羲的看法是“就滇言滇”“现在我国情形彼所洞悉,若声言设备,转恐彼籍为迎战之据,不独患中一隅并将牵动全局”(16)《致云贵总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8页。,多次劝诫他要“审时度势,究未便轻启兵端”。在此期间,关于片马问题的信息只在清政府、云贵总督以及驻英公使间传递往来,并未公诸于报端。
1911年2月6日,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份报纸《申报》和《大公报》同时登载了有关片马事件的消息,打破了清政府垄断片马事件消息的局面。辛亥革命爆发前,《申报》及《大公报》关于“片马事件”报道数据统计见表2。

表2 1911年《大公报》《申报》报道“片马事件”数据统计表(17)报纸所载“要闻”“专电”时,往往登载全国范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在《申报》和《大公报》的要闻和专电报道中会同时列举几条信息独立的、有关“片马”的新闻动态,此处统计时将专电消息按条数统计在内。由于在其他事件中提及“片马”同样能够增加片马事件的影响,因此尽管不是专论片马问题,也计入统计数据中。但报刊中与片马问题相关的信息体量较大,本表只是初步的统计数据。
根据统计,自1911年2月至11月,《大公报》刊载关于片马事件相关新闻和评论达229篇,《申报》除11月无相关数据外,总数也达217篇之多,还不包括两份报纸中其余关于中缅界务交涉的相关文章。
由图1可见,1911年,《大公报》与《申报》对片马事件的报道有两个高峰期,其中3月份两份报纸的数值都达到了顶峰,此后数值不断下降,在7、8月又出现短暂的回升。第一个报道高峰处于片马事件发生后的前两个月,是舆论发酵的高峰时期,随着英兵将撤出片马的消息逐渐回落。第二个高峰期出现在6月英国将永租片马的消息传出后,此后又逐渐回落。刊载文章数量的变化虽然代表着事件热度的起伏,但《大公报》和《申报》所刊载文章中对清政府的不满却在不断上升,这在报纸所刊载评论的标题和内容上都能够有所反映。

图1 1911年《大公报》与《申报》关于“片马事件”报道趋势比较图(据表2统计数据绘制)
片马地处滇西北一隅,两份报纸如何在事件发生后约10个月的时间内,登载了至少450余份新闻报导的呢?分析所刊载的内容,可以发现除了对事件发生情况以及解决的具体进展的追踪报道外,《大公报》和《申报》对“片马事件”的叙事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时空维度对事件的追溯与分析
对“片马事件”发生根源的追溯、背景的介绍,以及片马对于西南乃至中国影响的论证,在《申报》和《大公报》刊载的文章中占较大比重。这两类文章,主要分布在4月份以前。如《申报》刊载的文章中就有《滇缅界务问题》《永昌府属历史上之遗迹》《舆地之重要》《云南省谘议局为中缅界务与片马交涉上滇督书》《片马事件尚无结果》《滇边今昔之观感》《危哉四面楚歌之中国》《滇缅划界小史》《片马交涉聚讼而已》《片马问题》《片马交涉之首祸》《西南边界交涉片片谈》《片马界务之近状》等近30余篇,约占《申报》刊文总数的15%。通过对所刊载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报刊对“片马事件”相关信息的获取、选择、阐释和评论,被放置于中缅界务交涉和片马与整个西南乃至中国关系的时、空脉络中,以此论证片马事件关系到我国西南边疆的领土安全,事关国家统一乃至国家存亡。
(二)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歧的追踪报道
围绕如何应对英兵侵占片马,李经羲与清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事件发生之初,李经羲向清政府力争要进行军事筹备,与英国进行积极的交涉,并将勘界提上议程,但清政府的态度是国力不能相抗衡,加之国内交涉事件众多,不应与英国轻启衅端。这一分歧的存在,为报刊介入后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埋下了伏笔。1911年2月19日,《大公报》报道李经羲向政府请求“速派得力陆军若干来省以资保护”(18)《李督请兵之急电》,载《大公报》1911年2月19日。。1911年2月24日,《大公报》报道“外部诸公对于此事为保全滇边大局起见,已颇有退让之意,所有英人要求开筑通商口岸两处已将认可。”(19)《片马交涉已有退让之意》,载《大公报》1911年2月24日。1911年2月26日,又报道滇督李经羲请求外交部速派精于英法语言交涉人员到云南。(20)《滇督电调交涉人员》,载《大公报》1911年2月26日。在未得到清政府积极回应的情况下,李经羲致电全国各地督抚“咨商”片马问题和中缅界务交涉问题,这封电文被刊载于《申报》和《大公报》等报纸上。(21)分别见《滇督因英兵入界事致各督抚电》,载《申报》1911年2月17日;《滇督关于界务咨商各督抚电》,载《大公报》1911年2月27日。上述报道扩大了片马事件的影响,与清政府保持秘密交涉的宗旨相悖,激化了李经羲与清政府高层之间的矛盾。这些信息为报刊所捕捉,并刊载诸如《滇督有将被排挤之耗》《李经羲竟不容于政府耶》《滇督办理片马交涉之苦心》《外部不满意于滇督》《既不见好于外部,复不见原于政府》《各省报纸所登载滇督函电均系忧国忧民之语》等评论文章。(22)分别载《大公报》1911年4月19日、《申报》1911年5月1日、《申报》1911年7月8日、《大公报》1911年7月12日、《大公报》1911年8月4日、《大公报》1911年9月4日不仅如此,李经羲发出的电文内容常被公布在报刊上。对于如何处理片马事件以及滇缅边界交涉,李经羲与清政府高层的分歧一直存在,相关报道几乎贯穿了1911年2月至10月的《大公报》。
在上述分歧的基础上,《大公报》和《申报》还刊载了诸多批评文章,指责清政府应对边疆危机事件采取保密主义,“得报既不宣布又无抵制之策”(23)如:《又秘密川滇边防外交》,载《大公报》1911年2月13日;《外部但知秘密二字》,载《申报》1911年5月11日;《请看政府对付片马之交涉》,载《大公报》1911年2月26日。,外务部“失机误国”“只知劝民勿滋事”(24)《非失机误国而何》,载《申报》1911年3月12日;《外部只知劝民勿滋事》,载《申报》1911年3月15日。,历数政府“筹边之拙劣”“昏庸之罪状”(25)《论吾国筹边之拙劣》,载《大公报》1911年3月31日;《中国危亡警告书》,载《大公报》1911年3月25日。,明确指出“政府对滇事冷淡”“今日之危急政府不得辞其咎”“外部之独行独断”(26)《政府对滇事冷淡》,载《申报》1911年6月20日;《论今日之危急政府不得辞其咎》,载《申报》1911年4月29日;《外部之独行独断》,载《大公报》1911年7月4日。,讽刺驻英公使“只怕强硬国不收他这个弱软人”(27)《闲评一》,载《大公报》1911年3月19日。等等。这些文章围绕李经羲的积极应对政策与清政府的消极应对乃至对李经羲的劝诫、指责、批评,塑造出李经羲积极抗英保卫边疆、努力经营边疆的爱国形象,而清政府军机处、外务部、外交官员则是一味敷衍了事,遇事推诿、妥协退让、软弱无能、丧权误国的“卖国”形象,二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同时,清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冲突,成为吸引读者眼球的要素,对维持事件的热度产生了一定作用。
(三)对民众抗争行动的报道和声援
在《大公报》《申报》所刊载的文章中,国内民众的抗争是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众抗争本身就是片马事件社会影响的一种体现,而报刊对这一内容的广泛报道,对于片马事件舆论环境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以《大公报》为例,这一类报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云南民众抗争活动的相关报道。《大公报》报道片马事件的第一篇稿件就来自于云南谘议局,且报道中提及是发给“帝国日报转各报”,强调英国派兵侵占片马“势将北进扼蜀藏咽喉,馋长江流域”,影响国家大局,向全国提倡“拟先文明抵制,不买英货,请转各商协力实行。”(28)《要闻》,载《大公报》1911年2月6日。1911年3月17日《大公报》刊登留日云南同乡特派代表王九龄和杨大铸联名发出的通告书,文中历数英法日俄在当时对中国北方和西南的侵略举动,强调英国侵占片马与国家存亡之间的重要关联。(29)《滇代表通告书》,载《大公报》1911年3月17日。3月22日又报道云南留日学生为“英占片马窥伺川藏”“特开大会议,决举办民兵(即团练)以备不虞”,公推王九龄、杨大铸回省提倡团练。(30)《云南代表已抵沪上》,载《大公报》1911年3月22日。此外,还有诸如《滇客详述英占片马之状况》《滇人组织民团之露布》《滇人关心界务》《谘议局联合会宣告全国书》《五代表痛哭滇省》等报道。(31)分别载《大公报》1911年4月16日、《大公报》1911年4月23日、《大公报》1911年6月15日、《大公报》1911年7月17日、《大公报》1911年9月4日。
另一方面是全国各地民众对云南民众的回应。1911年3月24日,《大公报》报道上海成立“中国保界大会”,以更好地呼应“云南保界会”,并确定“先从云南做起如文明抵制”“发电于枢府凡关于云南划界事当会同资政院办理,资政院须听命于各省谘议局,并请如未明晰界务情形不必贸然签字。”(32)《中国保界大会纪事》,载《大公报》1911年3月24日。1911年5月13日,黑龙江省谘议局接云南省谘议局“实行就地请办团练以为文明抵制”的函电后“即电复深表同情”(33)《谘议局之救亡策》,载《大公报》1911年5月13日。1911年6月30日,江西谘议局对云南省谘议局的倡议表示支持。(34)《赣省协助联合会之要电》,载《大公报》1911年6月30日。陕西、江西、四川、广东、广西、福建等省谘议局均致电内阁“力争片马交涉”(35)《各省对于片马之电争》,载《大公报》1911年7月5日。。在报道全国各地对云南民众抗争行动的过程中,《大公报》还激烈批评其他漠视或无视的行为和举动。1911年4月15日,《大公报》刊载上海报界公会质问上海商务总会的函件,函件中介绍云南商会致电上海商务总会:“英兵进据片马,意在进窥藏蜀,拟用文明抵制,不买英货。各省埠已复电赞成,请组合团体实行。” “沪商会以镇静为主,拟将滇中各电束置不复。”(36)《上海日报公会质问上海商务总会函》,载《大公报》1911年4月15日。对于这一态度,上海日报公会刊载长文批判沪商会的态度。云南谘议局组织保界会并电邀各省约以不买英货为抵制的呼吁,劝业道为此照会云南商会“片马之得失与商人毫无关系”“仍可照常买卖勿庸抵制”,1911年4月24日的《大公报》因此声讨劝业道“太无心肝”(37)《请看劝业道太无心肝之照会》,载《大公报》1911年4月24日。。
除以上几点外,《大公报》《申报》也重视政府对民众抗争的态度、(38)如外务部对各省谘议局的力争“充耳不闻”(《闲评二》,载《大公报》1911年7月6日);“滇人士拟组织民团以自卫,近日该省谘议局广发传单”“本局已四次上书督院立请练团,迄今两月尚无允准批答。”(《滇人组织民团之露布》,载《大公报》1911年4月23日)等。英国对片马的企图及交涉态度(39)如驻英公使“始而抵赖继而推诿,毫无实际答复”(《片马交涉拟请各国公判》,载《大公报》1911年2月22日);“外交界近息英人此次进兵片马,其原因系为本年中英商约亦须改订,所有约外要求增入之款甚多,恐我政府不肯允准,故欲籍重兵威以为恫吓之计。”(《英兵进占片马之用意》,载《大公报》1911年3月11日)等等。等内容的报道,并将片马事件纳入全国各地的边疆危机,分析与其他交涉事务的关联。上述内容共同构成了报刊对片马事件较为完整的叙事体系,助推片马事件成为影响重大的边疆危机事件。
三、消解舆情:清政府的应对及其成效
外务部档案资料显示,最迟在1910年5月20日之前,李经羲就向清政府奏报了片马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40)《片马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馆藏号:02—17—002—03—002。1910年6月3日,外务部收到英国署公使的照会回复。(41)回复内容为:“本月初二日接准来照,以片马一案及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滇缅未划定之交界一事,将滇督所电各语抄送前来,均已阅悉。查本年正月缅政府接阅新闻,知登埂土司,将片马各寨焚烧,并恫吓朗澎暨他村舍,当时英领事奉札照会腾越道台,旋于三月间娄领事奉本国政府所嘱,亲赴前提各处,详细查明实在情形,本署大臣亦奉本国政府嘱向贵部声明,须俟娄领事所查各节详报之后方可照复。”见《复片马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馆藏号:02—17—002—03—005。此后,对于如何处理片马问题,李经羲与清政府的分歧愈发严重。清廷不断向李经羲要求“密饬地方文武妥慎防维,勿任鲁莽偾事”(42)《滇督李经羲致枢垣英兵抵片马并胁各夷降附请饬商英使退兵妥议电》,王彦威,王亮辑编:《清季外交史料》(8),第4437页。。1911年1月24日,李经羲向清政府提议“预行布告各国,声明其曲在彼,用兵在先”(43)《滇督李经羲致枢垣英占片马拟督军备战誓以身殉乞示电》,王彦威,王亮辑编:《清季外交史料》(9),第4441页。,以在国际舆论上争取支持。在此期间,李经羲又致电其他各省督抚“有请旨备战、设法援救之语”,使事件扩散到全国其他省份。这一举动引起清政府的极度不满,指责李经羲:“现在人心浮动,万一消息流传,内讧外侮因之而起,后患何可胜言。”(44)《致云贵总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册),第508页。与此同时,云南省谘议局也向全国各地以及国内主要报刊发出“文明抵制,不买英货”的倡议。这一倡议被刊载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报刊上,引起更多民众的关注。李经羲以及云南省谘议局的行为,是事件自爆发以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国内舆论的发酵,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去应对。
(一)贯彻秘密外交,防止信息泄漏
片马事件经过报刊广泛报道后,政府的应对措施成为报界关注的重要内容,而一旦出现消极的信息就将引起民众的不满。为防止这一状况的发生,清政府继续向各部门强调事件的机密性,“各枢臣仍抱定秘密宗旨,所有与川滇两督及川滇边务大臣往返电报,均由那、徐两军机亲自译缮,故其中情形外间无从探悉,并闻日昨由那相国谕交枢垣各员,以此次滇边各处交涉,现正严密调防,如有轻易泄漏者,一经查出即按泄漏军秘之罪从严惩办。”(45)《又秘密川滇边防交涉》,载《大公报》2月13日。“川滇边交涉案件宜严守秘密,如有泄漏定予严惩。”(46)《专电》,载《申报》1911年2月15日。在两国会谈时“颇为秘密,一切仆从尽行摈退,即译员亦不令在侧。”(47)《外部会晤英使之述闻》,载《大公报》1911年3月22日。内阁对于重要机密事件,“各项电报无论紧要、普通,统责成该阁丞亲自译出呈堂查阅,不可稍有泄漏,惟关于军事之要电,概不交译,以重权限。”(48)《内阁慎重机密之政策》,载《大公报》1911年7月3日。通过这些措施,清政府试图严密管控片马交涉信息的外泄。
(二)加强报刊管控,禁止刊载相关信息
加强对报刊的管控,是防止关于片马事件的舆论进一步发酵的重要措施。为此,外务部命民政部“转饬内外城厅,严禁报馆登载各边省交涉,否则照章惩办决不稍宽。”(49)《外部又拟取缔报馆》,载《大公报》1911年3月9日。谕令各报“凡关于中俄与片马交涉事件暂禁登载。”(50)《直隶交涉使又禁载交涉事件》,载《申报》1911年3月16日。1911年3月24日,《大公报》报道“政府前曾提议,凡属交涉事项未决以前,各报不准登载,既决之后,由官报刊布,各报仅许转录,以便国人皆知,免之滋生谣诼。”(51)《交涉事项仍拟秘密》,载《大公报》1911年3月24日。1911年5月5日,《大公报》刊载消息:“枢府又严行取缔报馆矣”“枢府于日前(即初三日)曾密交民政部交片一道,探其内容确为取缔报馆之手续,并闻不但禁登借款与片马等交涉且尚有他项密要事件,非外间所能探悉。”(52)《枢府又严行取缔报馆矣》,载《大公报》1911年5月5日。在事发的云南省,主管部门对报刊的管控更加严格,“《云南日报》于宣统三年四五月间批评清政府对英军入侵片马的妥协退让,提学使叶尔恺即将该报总编辑撤职。”(53)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志·报业志》(卷77),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三)取缔民众抵制英货,防控事件影响扩大
在事件传播和舆论发酵过程中,各省谘议局尤其是云南省谘议局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对于云南省谘议局“抵制英货”的倡议,清政府分别命令工商部、劝业道等部门及两江总督,对这一行为要严厉禁止。(54)如《交饬禁止抵制英货》,载《大公报》1911年2月19日;《电禁抵制英货》,载《大公报》1911年3月9日;《饬查有无抵制英货之举动》,载《大公报》1911年4月12日。对于云南省谘议局举办团练以抵御英兵侵略的提议,清政府更是坚决予以拒绝:“兹准电称滇省谘议局屡请指拨饷械团练民军,并电恳资政院开临时会各节,在滇人痛切剥肤或有急不暇择之势,殊不知资政院并无干预兵政处决国际交涉之权,况当战衅未开,只宜密筹对待,讵可自相惊扰,肆意沸腾。”(5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册),第554页。督办粤川汉铁路端方认为“各省谘议局于外交政策往往不悉,当事为难,辄复横加訾议,而民情浮动时或受其影响。”(56)《督办粤川汉铁路端方奏滇边界务请于片马交涉未定之际与英使商撤片马》,王彦威,王亮辑编:《清季外交史料》(9),第4514~4515页。1911年7月1日,《大公报》更是报导消息,说清廷“严电滇督”“谓办理交涉,朝廷自有权衡,讵容人民之妄行干预此事,应由贵督设法缔禁,勿得推卸责任。”(57)《严电滇督缔禁干预界务》,载《大公报》1911年7月1日。1911年7月又传出清政府将对谘议局章呈进行修改的消息,“政府为预防本年资政院开议时冲突起见,故将院章赶即修改入奏以为将来钳制议员之地步。兹又得一消息,内阁总协理大臣日昨提议以各省谘议局自上年以来屡启纷争,若不赶筹办法于宪政前途大有关碍,俟法制院各事就绪后即行将谘议局章大加修改以期完善。”(58)《谘议局章亦有修改之耗》,载《大公报》1911年7月7日。
从报纸对清政府上述应对措施的披露来看,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尽管清政府决策层的信息控制取得一定成效,但云贵总督李经羲的相关电文以及其他蛛丝马迹,仍不断出现在各报报端。(59)一些电文还被西方报刊关注和译载,如《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1911年3月14日、1911年6月8日的报道。云南提学使叶尔恺指责李经羲发表相关言论,“不过欲沽名而已,各报登载即彼意也。”他甚至认为《云南日报》登载“丑诋外部”的文章“皆彼为之耳。”(6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2289页。同盟会会员马叙伦也认为,在片马交涉中李经羲的表现,是“阴图去滇,而阳示为国宣力,致电外务部,谓将躬赴边方,与敌冲折,久不得复。一日盛气语僚属,深咎外部,延不咨答。”(61)马叙伦:《石屋馀瀋 石屋续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从李经羲力争片马的应对策略和具体措施来看,不能否认其在捍卫边疆领土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同时,国内对片马事件的传播和舆论发酵,李经羲确实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其他官员也是报刊信息的来源渠道,如云南提学使叶尔恺也一直在向著名报人汪康年提供片马事件的消息。(62)叶尔恺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写道:“前闻各报载滇事翔实,知必出自尊处,但须极秘密,且要将情节略改,不可说出十分真相。缘报馆访事人每多道听途说,半真半假,方合体裁。若过于实在,则彼必以为局中人泄漏,反有不利。又虑以后格外慎密,峻其防范,则将来访件反多妨碍也。千难万难,另纸一张,皆去年随笔所录,久欲奉寄,因冗碌未暇,兹仍寄阅。后如欲宣诸报纸,尚须摘其大要,斟酌改窜。其中颇有为官场所悉者,若全行泄之,恐或不妙,只可隐约其辞为是。”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2287页。由上述事例可知,清政府在地方政府的信息管控方面失去了效力。其他如管控报纸、取缔民众抵制英货等活动的措施,被作为新闻刊登在报纸上,使清政府在应对片马危机不力的罪状下,又增加了新的引起民众不满的因素。
结 论
进入近代,现代报刊媒介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引起中国社会变革的因素之一。边疆危机的不断加剧,得到了报刊媒介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为清政府应对边疆危机的传统方式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为此,清政府出台了针对报刊媒介的法律法规,规定了涉及清政府内政、外交和军事等方面的禁载内容。但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西方报刊、租界的特权,以及报刊创办的灵活性等因素,清政府并没有实现对报刊的有效管理。且对报刊“揭载”内政、外交和军事内容的惩罚规定较轻,表明清政府对报纸刊载这些内容带来的公众舆论压力缺乏足够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此前普通民众对国家大事的影响微弱。因此,在应对边疆危机时,清政府采取一味封堵的做法,不注重信息的通达和民情的疏导。在公众舆论发酵过程中,在各种信息交汇、真假难辨的复杂环境下,清政府在边疆危机问题上处于话语权缺失,舆情应对能力低下的状态。
以片马事件为例,报刊媒介对事件的参与,使围绕该事件的公众舆论的形成成为可能,暴露了清政府在边疆危机的舆情应对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1910年英兵侵占片马的事件发生后,清廷与云贵总督李经羲就事件的解决方式上产生了严重分歧。1911年2月,事件信息开始出现在报端。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申报》《大公报》等报刊,将发生在滇西一隅之地的冲突,通过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深入发掘和阐释,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事件解决的分歧追踪,以及民众的抗争活动等问题的报道,使英兵侵占片马放大成为影响遍及全国的重大边疆危机事件。为消解报刊媒介介入片马事件后带来的舆论压力,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诸如严密控制信息源的外泄,限制报刊对边疆危机事件内容的报道,以及取缔民众的抵制活动等措施,但并未取得积极效果。报刊对政府采取秘密主义,试图严格禁止报刊报道事件内容等行为的披露,反而增加了民众对清政府应对边疆危机不力的严重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