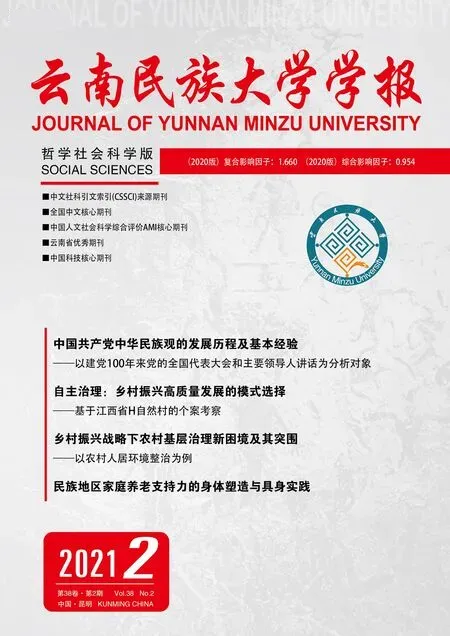知行合一: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认知与践行(1921—1949)
刘训茜
(上海交通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0)
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始恪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目标,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
回顾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取得革命斗争最后胜利的光辉历史,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和革命实践进程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科学地洞察中国社会结构之性状,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问题,与时俱进地调整目标和任务,在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同时,以发展的理念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其中,对民族及其结构、民族问题等的认识渐渐明晰,在革命征程中不断发展完善民族政策,建立起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拟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认识的变化,探讨党的民族政策形成及践行过程,以更加坚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信念。
一、建党初期对国内民族及民族问题的理解
对于刚刚创立不久力量尚属薄弱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当时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行革命。中共一大纲领提出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的主张,(1)《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主要以资产阶级为对手。1922年,“中共二大”进一步提出了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目标。1924 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在《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中提出“对内解除我人加于殖民地弱小民族(如蒙古西藏)之压迫”(2)《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的号召。无论是“殖民地”还是“弱小民族”的表述,都是为了体现这些民族所受到的压迫,其目的依然在于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共初创时期的指导,当时主要受到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理论政策方面长期以俄为师。中国共产党主张解放一切“弱小民族”,赞同中华民族内部各少数民族对于汉族的自决,亦即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在当时中国,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认识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系统全面的认识。孙中山于1920年11月《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言说》指出,光是汉满蒙回藏五族仍然不够,要把各民族都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最终“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3)《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言说》,载《孙中山全集》第5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4页。直至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对“民族主义”进行了新的解释,将其定义为“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4)《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119页。重新解释后的民族主义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境内各民族自决”,受到了共产国际决议的直接影响。(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343页。自此,“五族共和”之外,对国内民族的处理,又增加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扶植弱小民族自决自治两种口号。
1934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称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内部只是“宗族”的大小分支而已。甚至“民族”概念也遭到刻意回避,只能代之以“边疆”。相比孙中山提出的“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反而进行了大幅度地收缩,因而无法给予国民以完全平等的地位。
综言之,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对国内民族问题未加注意,虽然在共产国际影响下提出过“民族自决”,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的思想;但更为符合中国国情的对民族问题的认知,以及更为成熟的理解要下逮长征与抗战时期。
二、长征时期关于民族及民族问题认知的转变与深化
(一)红军长征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与因应
历时两年的长征是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接触最为广泛深远的时期。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先后转战中国西南、西北广大省区,途经中国民族走廊区域,穿越黔、滇、康、川的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其中又以在西南地区历时最久,里程最长,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最为频繁。
1935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在针对贵州白军的工作指示中首次提及注重苗、瑶士兵的“民族意识”这一概念。(6)《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就四川省而言,红军发现其五千多万人口中,除汉族外还有“藏人、回人、番人、苗人等各种民族”。红军因其人数少于汉族而称为“少数民族”,表达了族别统计人口数量少的涵义。红军于四川深山腹地亲历多民族散杂居,及其村落、饮食、服饰、住屋、婚姻、宗教状况,观察到诸如“藏人中男女大概是同样工作,不像汉人轻视女子,藏人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番人“主要也靠畜牧为生,同时兼种植包谷,挖野药卖与汉人,番人也迷信佛教,但没有喇嘛”“熟苗生活习惯与汉人差不多……生苗在永宁一带居深山老林石洞或小棚中与汉人少交通”等等,(7)《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少数民族工作须知》,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282页。堪称详尽的民族志调查。可以说,党和红军对于生活在西南的族体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已经产生了极为深切的体认。
中国共产党基于长征中的切身体认和实践所得,从坐言而起行;相对于国民政府“不尊重少数民族”和“大汉族中心主义”,立刻提出了“各民族平等”“少数民族自治”等口号作为民族政策宗旨,不但承认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高度尊重民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除了风俗文化方面的认识,还有经济社会状况的认识。参与长征的陈云托名一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在中共创办于巴黎的《全民月刊》连载《随军西行见闻录》,记录了沿途所见贵州东部苗家、云南与四川彝家的统治格局、社会结构、地理环境等。据他观察,贵州苗民不时面对来自军阀的苛捐杂税、勒种烟苗、军队抽丁,担负着沉重的劳役,贫苦程度难以想象。云南的情况有所不同,包括龙云在内的军队与政府中上级官员都属于“彝家”,汉人属于下层社会而受到压迫。(8)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6、42页。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贵州进入云南,随即制定了与之相适宜的民族政策——针对云南汉回苗民提出“民族解放”口号,对于彝民则使用“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进行宣传。
1934年11月,长征刚刚开始时,中央红军政治部发布了针对瑶民和苗民的工作指示,“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主张民族平等,给予彻底的民族自决权。(9)《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然而,直至红军长征途中与少数民族进行深入广泛的接触和交往,才意识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并非以往所认为的、单纯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渡过嘉陵江,进入到川西高原,观察到当地居民鲜少,以藏族为主,亦有少量回族、羌族、彝族、汉人,社会经济落后,“少数民族群众只好居住在高山贫苦地方,平川和较富庶地方为汉族的地主所有。”(10)李中权:《难忘的川康少数民族》,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2册,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31页。中共领导人意识到,过去诸如汉族压迫“弱小民族”的二元对立的表述是不准确的,笼统的汉族整体并不等同于个别的统治军阀,少数民族内部的阶层划分也是错综复杂的,有必要重新建构关于少数民族的阶级革命话语。
1935年5月,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为度过大渡河而决定穿越彝族聚居区。其时负责民族问题宣传的何克全,对四川建昌大小凉山彝民展开实地调查,发现其内部等级制度森严,人身依附关系严重,“黑彝是统治阶级、压迫者,白彝是被压迫者”。土司制度已经衰败,头人兴起。彝民遭军阀压迫而被驱赶上山,失去了发展农业的机会,只能劫掠平地平民,造成了彝汉关系的紧张,也导致整个凉山地区硝烟四起,民生凋敝。大乱虽然没有,小乱却不曾停止。职是之故,何克全提出发动彝族中的白夷,白夷是基本群众,但不能过早分裂黑夷的统战策略。(11)凯丰(何克全):《关于夷民众的工作》,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页。同时,红军以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布告,提出了“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12)《中共工农红军布告》,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的口号,将彝族平民纳入到了与自己相同的阶级范畴。红军随后通过“彝海结盟”得以安然通过凉山彝民区域。
(二)少数民族的平等联合与民族意见的容纳
由于面对来自日本军事入侵和国民政府的双重压力,争取各少数民族成为长征时期民族工作重心所在。在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感受到了“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斗争的高涨”(13)《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页。和其中所蕴藏的“丰富的革命力量”(14)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3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也体会到了少数民族对民族民主革命的支持和拥护。长征临近结束时,红二、四方面军会师进入的甘、陕、青地区,属于西北地区人口物产稠密丰富的区域,包含有“回番民族”,红军进入当地感受到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群众的抗日热情。(15)《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扩大红军运动的指示》,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
基于此种情况,少数民族被纳入革命主体的表述,并在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扎根。1936年初,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红六军团转战到达川滇黔边区,号召边区“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16)《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革命根据地纲领》,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在这一表述中,边区根据地为红军与当地少数民族人民所共有,并无“土客矛盾”引发的纠缠与争夺,取而代之的是一起建设家园的共同体意涵。
随着中共根据地范围的扩大,少数民族在整个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平等联合的对象。为了消除和化解历史上的民族矛盾与隔阂,中国共产党力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彻底平等。首先是对于参与红军的少数民族战士的平等。例如对于回民新战士,将其单独组成连排,允许单独饮食,以鼓舞回民展示抗日为主,开始时不应禁止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习俗。(17)《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扩大红军运动的指示》,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页。绝对严禁对回民的风俗习惯进行嘲笑。(18)《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关于进入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页。
其次是平等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组织原则。长征后期已将长征中所亲见的少数民族聚居、散居相结合的复杂特点纳入政策考虑,试图多层次、多地方地设立民族自治。1936年5月,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始总结长征途中民族聚居区的经验,探索建立西北回民的政权区域自治方案,其细则包括:其一,“在回汉人杂居的乡或区”其委员人数“以该乡或区的回人与汉人数量多少为比例决定”;其二,“完全是回人集居的乡或村,则组织回人单独的回民政府。”(19)《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页。
再次是少数民族人民政治权利的平等。自1935年5月开始,已有“回、番、藏、蒙、苗、夷”民族的代表出席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大会,(2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通电》,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页。不同民族共商大计的参与模式开始萌芽。1936年初,由贺龙担任主席的川滇黔革命根据地,明确了“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一切劳苦群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不分民族(汉、回、苗、彝、瑶……)”(21)《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行动纲领》,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在政治上享受平等待遇。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在无产阶级的划分中,除了早期的工人、农民、参与革命的红军等不同职业和阶层;还可以被划分为汉、回、苗、彝、瑶等不同的民族。少数民族被纳入到无产阶级的组成元素当中,泛化了“阶级”语义的内涵,(22)王奇生: 《从“泛阶级化”到“去阶级化”: 阶级话语在中国的兴衰》,载《苏区研究》2017年第4 期。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群构成的社会认知。由原本二元对立的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细化成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族体等多个维度和层次。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把握有了质的飞跃,启发了少数民族的阶级意识,也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和动员力量。
综上所言,1934年10月开始的长征,使党和红军深入民族地区,了解到的少数民族的风俗语言、历史渊源、聚居情况,对中国多民族社会的现实产生了直观的感知。党和红军对西南、西北人群结构的分类和认识,是促成其民族理论政策转变的重要原因。
三、抗战时期民族统一战线表述的生成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将少数民族联合到民族统一战线当中,防止日本挑唆少数民族分离,成为了当时中共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
少数民族作为抗战的重要力量,频频出现在中共有关抵抗日本侵略的一系列声明和决议当中。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23)毛泽东: 《论新阶段》,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1页。。张闻天在大会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争取少数民族,在平等的原则下同少数民族联合,共同抗日”的方针。(24)洛甫:《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698页。这里的“民族统一战线”代替了之前的“阶级”概念的运用,少数民族被纳入民族统一战线主体,成为了民族革命话语的一部分。章汉夫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而抗日战争正是“中华民族以血和肉来争取民族自决。”(25)汉夫: 《抗战时期的国内少数民族问题》,载《时论丛刊》1939年第4期,第127~135页。“中华民族”和“多民族国家”概念的明确,极大地揭示了各民族之间团结抗战、相互依存、共御外敌的意涵。
1942年4月,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可以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刊载了《云南少数民族问题》。该文写道,“在国内少数民族问题上,素来一般人所注意的,大体只是汉、满、蒙、回、藏五族”,无非因为五族在历史上影响深远,“而对于散布西南各省,特别是云南底复杂的少数民族,则极少重视。”然而无论历史影响之大小,民族都是客观存在的。随着缅甸、印度战事的爆发,云南在抗战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云南民族的团结,是国内各民族团结的一部分,而团结国内各民族抗战,则是争取反攻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26)刘健(刘浩):《云南少数民族问题》(原载《群众》第7卷第7期,1942年4月),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92~93页。“少数民族”在中共抗战话语体系中得到了极大的彰显。
在主张上,中国共产党在在各个根据地下达了一系列文件,以践行民族平等的承诺。例如,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提出“在民主选举中,应予少数民族以优待,各民族亲密团结,共同抗日”(27)《中共中央对“晋西北施政纲领草案”的修改意见》,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在晋冀鲁豫边区也规定民主选举“应予少数民族以优待,反对看不起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28)《中共中央北方局对晋冀豫边区目前建设的主张》,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对于在选举中特别关照少数民族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也有明确的解释。比如陕甘宁边区的回民和蒙民人数就相对较少,因而需要单独的民族选举,“如果照一般居民选举,很难选出其代表来”(29)《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选举条例的解释及其实施》,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01页。。
在实际中,在关中、三边、陇东三个回民乡镇的选举中,“照条例要有五十个回民居民才能选出一个乡议员。但现在只要有五分之一,即十个以上的回民就可选出一个回民乡议员;县只要有七分之一,即一百个以上的回民居民,就可选出一个回民县议员;边区只要有八分之一,即一千个以上的回民居民,就可选出一个回民边区参议员”(30)《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选举条例的解释及其实施》,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01页。。可见延安时期少数民族的选举制度已十分周全妥帖,把握其人口相对较少、居住范围分散的特征,完全站在了少数民族的立场上设想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平等的文件精神落实到实际当中,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即知即行”。
综言之,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团结少数民族抗战,同时以民族平等宗旨巩固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中国革命的走向胜利,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四、建国初期多元共治的民族参与政策的确立
解放战争后期是广泛容纳民族意见的时期。1947年3月,乌兰夫致书中央提出了“使各少数民族有适当数目的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与中央政府”的意见,(31)《云泽对宪法中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意见》,载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4页。体现了少数民族代表共同筹划建国大事的积极意愿。与此同时,乌兰夫在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上,号召“团结各个阶层、充分发扬民主”,而非仅限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乌兰夫尤其指出:“‘蒙古人民要当家’,是什么样的人民来当家?首先是农民、牧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占着全国人口中的百分之八九十,一向受着压迫,如果不使他们翻过身来,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政治,则自治政府的存在就失去了广大的基础。”(32)乌兰夫:《在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提纲(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载《党的文献》1997年第2期。
1949年9月,《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为国家的基本政策,把新中国确立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人民共和国。(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首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应了中国交错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保证了少数民族在自己的聚居区内实现当家作主,并依据自身的习惯、传统、风俗管理自身事务。其次,《共同纲领》保障了少数民族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此基础上产生代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这一代表选举制度并非西方意义上资本博弈式的竞争普选,而是能够兼顾包括弱势者在内的各个阶层,在取得最大限度的共识后所进行的选举,意在“使劳动人民真能选举他们所乐意选举的人去代表自己”(34)《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载《刘少奇选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使社会所有阶层都能参与到政权建设当中,从而形成了更具有普遍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再次,少数民族通过政治参与,向国家政治体系表达自己的诉求、利益、愿望,传达实际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使之成为国家决策的依据。对少数民族意见的兼听广纳,也更有利于国家政治决策的合理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权力为全国各族人民所真正共同分享,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缔造了新的政权。
《共同纲领》的制定本身就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35)《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3 页。集思广益、共同商议,最终达成共识的结果。《共同纲领》中初步的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则是对长征时期与延安时期根据地施行的少数民族选举政策的延续,维护了各民族真正的“民族意识”,关照了各民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共同纲领》确立的精神原则也为195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奠定了基础。
质言之,新中国建立之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国家大事的筹划和管理,既包括本民族内部的政治和社会事务,也包括国家层面的政治事务。各族体通过共同分享权力,从而意识到国家是由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奠定了广大而深厚的新中国国家认同的社会基础,也为少数民族群体融入广阔的政治舞台提供了通道。新中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与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选举制度,并不是朝夕之间形成的,而是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和发展。事实上,一个政策的落地也往往先基于对现实环境的深切体认,历经长时期的调适,在实践中反复校准,从而呈现清晰、丰富的意涵,并最终获得广泛而深远的认同。
五、结语
中国应该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一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从长征接触少数民族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了少数民族对革命的支持和拥护,并将其纳入革命的主体力量。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革命时期共同参与民族民主革命,共御外敌;在政权建设时期又以与汉族同等的地位,参与国家和各级地方事务的管理筹划,共定国是。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理论政策,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危急关头,都始终立足现实,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指引下,团结各民族共同奋斗,共享发展成果,最终探索出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