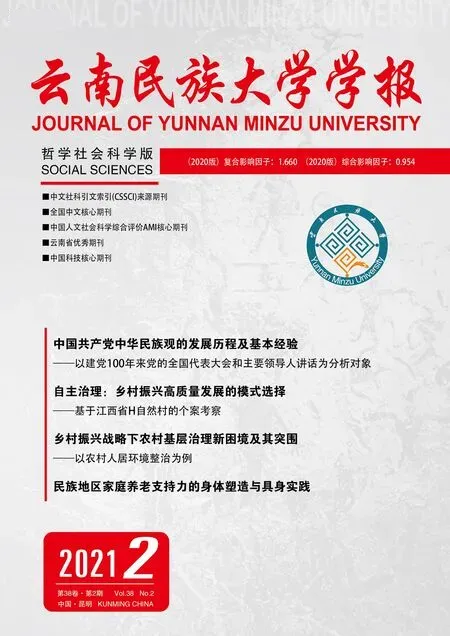作为一种武器的“正统”论:太平军、湘军合法性叙事话语评析
曹威伟
(1.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2.湖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正统”是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命题,是历代封建王朝建构其统治合法性以及政治、文化威权的思想支柱和工具。哈贝马斯指出,“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住政治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在古代中国,只有被人们视为正统,政治权力、军事权力才拥有合法性并转化为真正的权威。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既是军事战争,也是一场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战争,双方在这场战争中不约而同地利用了正统的话语资源来建构自己行动的合法性。这二者如何依据正统论建构起“反清”和“护清”两种行动的“正义性”?他们的合法性叙事建构反映出何种民族观?其民族观如何影响到满汉关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走向?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厘清这些问题的关系,既能为分析太平军与清军的胜负提供新的解释视角,还有助于促进对中国历史上正统论、民族观发展趋势的深入考察,进而为我国当代民族政治叙事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辨华夷”与“护纲常”:正统的知识谱系
“正统”论滥觞于春秋公羊学“大一统”义,“昉于晋而盛于宋”。从最初《春秋》中以宗周为正、强调血统上的嫡长子继承制以及文化上的华夷之辨,再到秦汉时的大一统说、五德终始说,“正统”论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之后,于宋代初步定型。宋以后,分两大主脉——“辨华夷”与“护纲常”向前演进。其中,“辨华夷”以“华夷”群体及其空间位置之分作为正统与否的划分依据,强调“天下”以“华夏”(既是空间位置,也是群体划分)为中心,只有“华夏”方具有统治的正当性,由此形成了以华夷为中心的差序结构以及“华夷正闰”的正统观。“护纲常”强调维护“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秩序,依据道义正当性规则以建构优良的秩序体制安排,注重社会自上而下的秩序统一,将“纲常”之维系作为正统与否的依据。这两条主脉在历史演进中相互批驳,相互渗透,或分流,或合流,影响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利用这种资源的价值取向。
宋时,民族主义兴起,以华夏论正统的倾向得到凸显。北宋王钦若在划分三国正闰时称:“魏文受山阳之禅,都天地之中”,可称为正统,而“刘先主僻处梁益,孙大帝远据江吴,自窃尊名,靡有神器,诚非共工之匹,然亦异于正统,故同为闰焉”(2)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00页。。北宋陈师道重视“夷夏”之防,主张只能以夏变夷,“夷而变,虽未纯乎夏,君子进之也”,但不可以夷变夏,“夏而变,犹未纯乎夷,君子斥之也”(3)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7页。。到了南宋时期,由于担忧“以夷变夏”的危险,“华”正“夷”闰的论调更为盛行。南宋理学家张栻旗帜鲜明地提出“夷狄不可为正统”的思想,认为在南北朝中“元魏北齐后周”都是夷狄,正统应当“独系于江南”(4)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38页。。宋末郑思肖更为激进,认为“臣行君事”是为逆、“夷狄行中国事”是为僭,彼时君臣颠倒、华夷颠倒,为古今天下之大不祥,“天理必诛”(5)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46页。。与华夷说同时盛行的还有“纲常说”,这种观点将执政阶层是否能够建立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接受维护纲常礼义作为评判标准。欧阳修将北魏黜为非正统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北魏未能兼并晋、宋一统天下,主张正统即“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6)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2》,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3页。。苏轼《后正统论》指出,“天下无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汤武既没,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当时之正而已”(7)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0页。,认为正统与否在于能否使天下有法有制可循,使现有秩序得以维护,使历史和文化得以存在和发展。张方平则认为纲常礼义的维系是正统评判的重要依据,提出晋在渡江之初,“遗中服之雅俗,据吴人之旧土”,然齐梁之后“风教荡然,危弱相承,礼刑不立”,虽欲“正之”,已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了。
到了金、元时期,人们更倾向于从大一统和纲常礼教的层面对政权进行合法性论证。金朝赵秉文在《蜀汉正名论》中提出,“《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8)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96页。,并认为西蜀虽然是僻陋之国,但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应当称为“汉”。元世祖忽必烈发布的《中统建元诏》提出,“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9)陆学艺,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宋元明清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4页。。刘整认为,“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10)宋濂:《元史》卷161,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86页。杨奂建议“舍刘宋取元魏”,将北魏立为正统,指出明朝“荒淫残忍抑甚矣”,因此夷夏之分没有意义,只要能够遵循中国的纲常礼教,“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11)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52页。。
明朝时期,北方边防的现实危机加剧了夷夏之防的观念,民族关系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纲常纲纪的宋明理学往纵深发展,正统论出现了新的面向:学者士大夫们既强调夷夏之防,又强调纲常纲纪之维系,正统论与民族关系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出现了直接将华夷秩序视为纲常秩序的倾向。正如有学者所言,“以华夷论正统的民族正统观在南宋灭亡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元明清三朝乃至近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郑炜:《略论欧阳修正统观中的民族因素》,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朱元璋在北伐时颁布《谕中原檄》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13)王雅轩,王晓岩,周文英:《中国历史文选》,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1981年油印本,第367页。,将驱逐胡虏和立纲陈纪联系在了一起。明初胡翰将华夷之辨作为“正纪”的重要标准,万民之众“有纪焉而后持之”,并提出中国与夷狄是内外区分的关系,应当“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14)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86页。。方孝儒则将华夷之辨与君臣、君后等纲常关系相比附,提出“有天下而不可比于正统者三:篡臣也,贼后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恶其乱华,篡臣贼后,恶其乱伦也”(15)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89页。。他的这一说法得到丘濬的响应,丘濬也把华夷关系比喻为君臣关系,提出“华夷之分,其界限在疆域”,以华为华、以夷为夷则为正,如同以君为君,以臣为臣为正一样。(16)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05页。万历时期章潢的《论历代正统》完整地体现了“辨华夷”和“护纲常”的合一:“正统明而后纲常纲纪一,法守严;正统定而后中国尊,夷狄惧”“天下固不可一日无统之者,无统则散乱;亦不可一日而无纲常纲纪,无纲常纲纪则邪慝”“以纲常纲纪为正统,夫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圣贤之所授受,民物之所趋向者也”(17)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05页。。明末,清军入关并在南下征服中大规模使用暴力,激起了汉族士大夫的强烈反感,黄宗羲在《留书》中谈到,“中国之与夷狄”是“内外之辨”,因此“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不失中国之人,“宋之亡于蒙古”,则是千古之痛也,极力主张“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的秩序观。王夫之同样如此,将作为“天子之位”的治统和“圣人之教”的道统视为“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18)王夫之:《读通鉴论》,上海:世界书局, 1936年版,第242页。,尤其君主是维系天下秩序的核心,“天下之治,统于天子者也,以天子下统乎天下,则天下乱”(19)王夫之:《读通鉴论》,上海:世界书局, 1936年版,第313页。。又把“中国-夷狄”的关系比附为“君子-小人”的关系,“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则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为。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两者秩序绝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20)王夫之:《读通鉴论》,上海:世界书局, 1936年版,第256页。。
作为少数民族执政的清王朝时期,正统论又发生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一方面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融进一步深入、认同感增强,另一方面,清军入关前后的民族压迫政策推动了反清思潮在民间发酵,使正统论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中呈现出认知偏差。在知识精英阶层和大多数地区的百姓阶层中,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策略,并引以理学的君臣、父子之伦和“有德者据天下”为依据,清朝正统说受到广泛宣扬且被认可。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说道,“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清朝“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强调清朝承继正统,维护中外一体、满汉一家的政权性质。顺康年间邵廷采主张将辽、金少数民族政权纳入正统,认为辽金“设官养民,创制立度”,乃至其亡国之时,亦有“忠义之士,与之同毙”,岂能“以其史为载纪而夷于十六国”呢?(21)邵廷采:《思复堂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2页。清末李慈铭批驳宋儒“重中原,轻诸国”的倾向,认为他们于五代之中“帝梁而寇河东”“尊石晋汉周而伪南唐”是不合理的,提出“与其帝石氏,不若帝契丹也”的观点。(22)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23页。而在一部分底层社会如华南地区的民间社会中,受朱明王朝复兴活动影响,秘密组织“天地会”自乾隆二十六年开始一直活跃于此,将汉族统治视为正统,利用“华夷之辨”的话语资源开展反清复明活动,获得了一部分下层民众的支持。
发生于清中后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正处于这种内涵丰富且争议不休的“正统”话语之下,为湘军和太平军各取所需、开展各自的合法性叙事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合法性叙事话语体系,也是基于“正统”论的不同指向建构起来的。
二、“辨华夷”:太平军起义合法性叙事
一般情况下,政治叙事在反映或记录“事件”时必然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自觉,展示出某种政治社会秩序建构的需要。在太平军的动员话语中,借助了正统话语中的华夷之辨,将“华”作为正统,“胡”作为异端,同时,又与宗教世界《启示录》的“神魔二元”话语、中国传统中的反压迫话语相对接,用攘夷驱魔的话语范式建构起一整套“起义”合法性的叙事体系,影响着太平军将士对战争正义和政权正义的认知。
(一)话语框架:“辨华夷”
两广地区是天地会长期活跃的地区,洪秀全的家乡广东花县的花山一带是南明抗清的最后基地之一。洪秀全曾对韩山文说:“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23)杨家骆主编:《太平天国文献汇编》第 5 册,台北: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版,第872页。天地会素有将清朝“胡夷化”、妖魔化的传统,在其广为散布的传单中,有“大哉中华……妖胡窃篡,此恨难消”“整军经武,誓灭满妖”之语。(24)徐建竹:《太平天国初期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2页。太平军承继了这一话语传统,在合法性叙事中以“辨华夷”为话语框架,用动物譬喻满人,论证了“攘夷”的必然性。
太平军在诏令文告中“妖魔”化清朝的叙事普遍存在,对清朝的称呼有魔鬼、邪魔、邪神、妖魔、老蛇、蛇魔、阎罗妖、东海龙妖、东海老蛇、鞑靼妖胡、满洲妖魔等近40多种。(25)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7页。这些称号或来自于圣经,如魔鬼、邪魔、邪神、妖魔、老蛇、蛇魔等;或来自于佛教神祇,如阎罗、龙王等;或来自于太平军自创。关于清朝的“妖魔”说,太平军还有一套完整的叙事体系。包括渊源说,如清之“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然后“种类日滋”“并无人伦风化”,他们“乘中国之无人,盗据中夏”,致使中夏境内“妖座之设,野狐升据;蛇窝之内,沐猴而冠”(26)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6页。。还有罪行说,如在衣冠服饰形象方面,令“中国”之人“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其服“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在人伦方面,统治者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满清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竞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在制度方面,满清王朝“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在语言方面,“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总之,“胡虏”以“蛇魔阎罗妖邪鬼”之身,“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致使“中国”“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其恶“罄南山之竹简”“决东海之波涛”(27)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6页。难以写尽、洗净。太平军话语中“辨华夷”二分叙事框架,实际上为人们建构起一个话语“洞穴”,“不仅使个人看到了某些东西而不是另外一些东西,还使个人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看那些被看的东西。”(28)[美]艾尔东·莫里斯:《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通过上述叙事,太平军对敌我对峙的认知因之而清晰、情感因之而强化,建构起了征伐清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二)叙事对接:“辨华夷”与“归上帝”“反压迫”
“辨华夷”为太平军建构起一套消解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话语框架。为争取获得民众的支持,太平天国还建构起树立“天国权威”和“反压迫”的话语体系,并使二者融会于“辨华夷”的话语框架中,实现了话语对接和逻辑自洽。
一是树立天国权威,为己正名,通过正当性和异质性两个向度的话语生产,实现“辨华夷”与“归上帝” 的叙事对接。他们将皇上帝、天王列入正统之中,通过正当性论证的话语生产建构“皇上帝”的合法性,称“中国所称为华夏者,谓上帝之声名在此也”“又号为天朝者,为神国之京都于兹也”,弘扬一种“上帝之纲常”。而天王是皇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乃皇上帝“命我主天王治之”,因此,要“遵中国、攘北狄”,必须“归上帝、扶天王”,以此恢复“久沦之境土”“以洗二百载之蒙羞”“复十八省之故土”(29)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57页。。太平军受命于“天国”,在其中承担着“扫除妖孽,廓清华夏”的神圣使命,是一支受到“皇上帝”护佑的队伍。他们还利用异质性的话语对违逆“皇上帝”的行为进行批判,提出天下、衣食、子女民人本是上帝之天下、之衣食、之子女民人,痛斥“胡虏”对之强取强占,(30)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106页。且“率民拜邪神而弃真神”,在宗教信仰上“叛逆上帝”,使中国“文武衣冠异于往古”“父母毛发强为毁伤”等,必将遭受“天罚”。
二是回应百姓痛楚,树己正义,实现“辨华夷”与“反压迫”的叙事对接。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时期,满汉矛盾已得到极大缓和,然而官贪吏蠹也在明显滋长,贫富对立冲突加剧,乾嘉年间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事等基本上都属于“官逼民反”。呤唎发现,“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全部叛离了他们的统治者,除太平运动外,中国十八省的每个省份中都有起义活动在进行着”(31)[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01页。。太平军的合法性叙事极力纳入对现实问题的关照,通过建立反对清王朝昏庸独断统治和压迫的话语,丰富和支撑着“辨华夏”的话语框架。他们宣称清王朝在水旱时“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要使“中国之人稀少也”;纵容贪官污吏,“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使我中国之人贫穷”; “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的阶级固化,“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32)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6页。。此外,还控诉清王朝在满汉资源分配中的不公,“每岁剥中国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以卫花粉之费”“每岁耗费鸦片烟土银几千万”(33)罗悙曧:《太平天国战纪·外十一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致使汉族人民受尽苦难。面对张家祥匪徒等“闻风而兴,招集匪人,凌暴黎庶,沿江取税,到处抢掠”“逞其虎狼之性,鱼肉生民”的暴行,清朝官方不予“究诘”,反“肆其狐狸之淫,闾里受害”,加剧了百姓的痛楚。(34)罗悙曧:《太平天国战纪·外十一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太平军通过对满人的污名化建立起华夷对立、满汉对立话语框架,有选择地对客体、情势、行为序列和经验进行强调和编码,并以树立天国权威、反对阶级压迫和满人统治的多重叙事话语进行填充,从而在一定群体范围内成功地建构起“起义”的合法性。太平军全盛之时所动员的军队达百余万众,势力波及中国十八个行省,影响波及全国,其话语效力可见一斑。
三、“护纲常”:湘军讨逆合法性叙事
作为讨伐太平军的主要力量,面对太平军反满、反儒、反压迫的三重叙事,湘军抓住正统论中“护纲常”“大一统”话语,创制了一套有理有据的“讨逆”合法性叙事体系,对太平军的话语叙事予以了清晰有力的应对。
(一)话语框架:“护纲常”
曾国藩本人是大一统秩序和纲常名教的坚定维护者,其思想深受老师唐鉴、倭仁的影响。唐鉴拥有开明的民族观念。他两次深入瑶疆,出任“瑶、僮多于汉人十倍”的广西平乐府知府,提出“猺亦人也,异视之则异,同视之则同”“猺亦人也,以人视猺,则猺易治;以猺视猺,则猺难驯”(35)李陵:《论唐鉴“猺亦人也”的民族观》,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9期。的观点。而倭仁则力倡程朱理学,一生致力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是一个典型的卫道主义者。受此影响,曾国藩高度推崇三纲五常,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3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36页。。对于人主他寄予厚望,认为“国之富不足恃,独恃有人主兢兢业业之一心耳”(37)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王启原校编,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页。;为臣者应恪守纲常,尽力保君佐君,因为“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督抚将帅,犹东家以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3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 2》,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881页。。他在行为上也恪守礼教,受命帮办团练时,初因母丧不肯出来,经朋友劝解再三才出来,后遭父丧又回家守了几个月服制。因此,在他拟草的《讨粤匪檄》中,强调大一统的社会秩序,将清朝视为维系大一统的力量(而非异族统治),匡扶了儒家纲常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一整套“讨逆”的合法性叙事体系。
湘军利用传统儒家的纲常观抨击太平军摧锄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做法,对其破坏大一统秩序,颠倒人伦,毁坏诗书典则和民间信仰等行为进行了集中批判。一是对太平军颠倒人伦秩序的行为进行痛斥。《讨粤匪檄》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然而“粤匪”却对之进行了破坏,他们“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主张“凡民之父”皆兄弟,“凡民之母”皆姊妹,上至“其伪君伪相”,下至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39)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社会亲亲、尊尊、长长的人伦秩序,危害极大。这样的话语得到了士人群体的普遍拥护。据史料记载,太平军咸丰二年十二月在猎马场筑台“讲道理”,招来马姓生员的反驳:“尔才所说之言,一派伤天害理,犬吠之声,何道理之有?试问自有人即有五伦,尔贼头于群丑皆称兄弟,是无君臣;父子亦称兄弟,姑媳亦称姊妹,是无父子;男女分馆不准见面,是无夫妇;朋友兄弟离散,是无朋友兄弟,可谓五伦俱绝。即依尔所述亦只有兄弟一伦,况舍亲兄弟不认而别呼他人为兄弟乎?如此悖谬,是真无用之狂贼也。”(40)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二是对太平军破坏诗书典则进行批判。称在太平军的治下,“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4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修订版)》,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32页。士人群体对此纷纷响应,将太平军焚毁经书之举讽喻为焚书坑儒,或作乐府曰:“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42)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5页。或作诗曰:“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灭绝圣贤心枉用,祖龙前鉴正非遥”(4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6页。,表达了强烈的愤慨。三是对其破坏日常祟拜的行径给予了指责。指责太平军“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佛寺、道院、城隍、社坛等“无朝不焚,无像不灭”(4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3页。。又“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致使“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即使是同为“乱臣贼子”的李自成和张献忠,也能做到“至曲阜不犯圣庙”“至梓潼亦祭文昌”(4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反衬出太平军行为的极端恶劣性。
儒学到晚清时期业已发展到巅峰,儒家的观念、信仰、情感、思维、态度、精神、道德、文艺和儒教等观念深入人心,三纲五常、礼义忠信等儒学精髓融入到了中国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湘军动员话语列举太平军对于人伦秩序,儒家经典、庙宇、社坛、城隍等“纲常”载体的破坏,成功地实现了对士人和乡农群体的动员。正如1854年一位西方传教士所言:“士大夫阶层构成整个中国社会体系的中坚,是大众舆论的领袖,民众一向乐意和信任地团结在其周围。对于他们,叛军不是用心地争取其归顺,而是宣布他们的荣誉头衔无效和非法,抨击他们所珍爱的古代书籍,焚毁他们的公共藏书地,使他们变成了自己的敌人。”(46)罗尔纲,王庆成:《太平天国》(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54 页。
在叙述了太平军对名教的种种破坏行为后,曾国藩在檄文中写道“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47)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在潜在的逻辑中将清朝确立为“名教”“大一统”秩序维护者。清政府自入关后就开始了一系列儒化活动,崇德元年皇太极受“尊号”时遵循了诸多繁文缛节,对各级官吏服式、冠饰、仪仗、名号制定了等级森严的规制。皇太极还遣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祭孔子,称孔子“惟至圣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谨备牺牲玉帛等致祭”。清王朝作为名教继承者的形象既已建构,那么捍卫“大一统”秩序、捍卫纲常伦理,也就与捍卫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浑然一体了。
(二)叙事对接:“护纲常”与“化万民”
曾国藩认为“三纲之道”十分重要,“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不可倒置”,甚至将纲常伦理提升到“性”与“命”的高度,提出“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的观点。(4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 文集》上卷.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在纲常之下,为臣为子当尽敬尽忠,为君为父则当尽仁尽慈。尤其是为人君者,当以仁义“化万民”,实行仁政、泽民和物。因此,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合法性叙事话语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以保民爱民话语为填充,与“护纲常”话语框架形成呼应,建构起“讨逆”合法性叙事的丰富性。
一是斥“虐民”以护纲常。湘军动员话语以二元分类图式将太平军斥之为“匪”,强调其“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之恶行。称其“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49)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因为动员对象以湘勇为主,湘军叙事话语对太平军破坏湖湘地区的行为予以着重强调,指出“粤匪”“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以此推动话语对象形成对自身角色和应有社会行动的认识,唤醒“读书识字者”“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5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
二是安“惊民”以护纲常。咸丰二年,曾国藩守制在籍,面对太平军攻入湖南引起人心惶惶的局面,创作《保守平安歌》三首,安抚受惊的百姓,鼓励和发动他们团结抗敌。《莫逃走》动员百姓“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本乡本土总不离,立走主意不改移”(5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22~423页。;《操武艺》主张“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学些好武艺”“各有义胆与忠肝,家家户户保平安”;《要齐心》提出“百家合成一条件,千人合做一双手”“邻境土匪不怕他,恶龙难斗地头蛇”“个个齐心约伙伴,关帝庙前立誓愿”(5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326页。。对于湘军将士,极力勉励他们“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5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批牍》,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13页。,“行军以不扰民为本”(5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62页。,阐明“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的道理,赋予其战争的正义和道德的责任,要求他们“扎营不贪懒”“行路要端详”“号令要声明”,不可取人门板,搬民砖石,毁人禾苗,扯道边菜,讹人钱文,调人妇人等。(5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29~430页。
三是化“叛民”以护纲常。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在安徽祁门大营作《解散歌》,“于难民之久困贼中者曲达其苦衷”,对太平军施以心理攻防,“士民读之,莫不感泣,因此而自拔来归者颇多”(56)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附事略 荣哀录》,长沙: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116页。。其诗站在太平军士兵的立场上,对其被掳当兵表示同情和理解。歌曰:“如今贼多有缘故,大半都是掳进去”,“初掳进去就挑担,板子打得皮肉烂。又要煮饭又搬柴,上无衣服下无鞋。看看头发一寸长,就要逼他上战场。初上战场眼哭肿,又羞又恨又懵懂。向前又怕官兵砍,退后又怕长毛斩”“半夜偷逃想回家,层层贼卡有盘查。又怕官军盘得紧,跪求饶命也不准。又怕团勇来讹钱,抢去衣服并盘缠”。士兵们在太平军营“种种苦情说不完,说起阎王也心酸”(57)李瀚章编撰:《曾文正公全集》第7卷,李鸿章校刊,北京:中国书店,2011年版,第429页。。为宣示皇天浩恩,表达拳拳爱民之心,曾国藩就势提出对待太平军俘虏“八不杀”原则,以此促使“叛民”归顺。(5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31~432页。
湘军动员话语以护纲常为话语框架,通过痛斥太平军的恶行,多方面回应民生疾苦,抚慰不同百姓群体,建构起“讨逆”正当性,以及湘军作为正义之师、仁德之师的形象。其叙事话语不仅吻合士绅和乡农群体的心理需要,也吻合清朝统治阶层的心理需要,达到“团结到了所有能团结的人”的效果,为最终战胜太平军奠定了基础。
四、两者合法性叙事的历史启示
为了粉饰自己行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更为了赢得双方交锋的胜利,太平军和湘军分别利用正统论中“辨华夷”和“护纲常”话语,应用选择、强调、排除、凸显等叙事机制,分别建构起“反清”和“护清”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从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知合法性叙事的内在规律:叙事的生产、接受、阐释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的,合法性叙事能否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提供支撑、起到应有的效果,与其是否契合社会历史语境密切相关。推进叙事话语与叙事接受群体、与叙事语境、与话语传统、与历史发展大势的相适应,是提升叙事有效度的重要条件。
首先,叙事话语应当与接受群体相适应。从叙事的接受群体来看,太平军和湘军的合法性叙事之所以能够生效,与“辨华夷”“护纲常”各自拥有一定的支持群体相关。太平军的组成多以会党、煤工、矿工、船户等脱离了土地的流民群体为主,人称“游荡之子、刁滑之徒,皆其羽翼也”“爆竹之铺、铁冶之匠,皆其辅佐也”“游手之夫、饮博之场,皆其耳目也”“星卜之流、乞丐之辈,皆其侦伺也”“塘铺之兵,担力之人,皆其邮递也”“深山之中,大泽之阻,皆其巢穴也”,“吏胥之首、弓兵之精,皆其朋党也”(59)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卷2,清抄本,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这些靠出卖劳力为生、四处流亡、没有稳定生活来源的无产者,反叛意识和冒险精神较为突出,“纲常”意识相对淡薄。尤其在广西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灾害频仍,租赋沉重,吏治腐败,各类反清运动如广西壮、汉各族的反清起义,贵州苗、教、号军起义,云南回民起义,陕、甘、宁、青回民起义此起彼伏,与民族压迫有关的话语更容易得到响应。而以士人领乡农的湘军队伍则恰恰相反,大一统和纲常话语更容易得到这一群体的接受。清廷一直有意识地处理满汉关系,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大胆起用汉族士大夫,士人群体对清廷的认同感增强,加之咸同时代理学复兴,唐鉴进京讲学培养形成了一批理学骨干中坚,正统、纲常秩序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在湘军内部,汇聚了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等在内的理学家群体,他们享有共同的符号、信念和话语,相近的意识形态信仰和一致的行动,形成了话语联盟及话语能量场域,这是“护纲常”话语能够在湘军内部得到普遍认同的原因之一。在乡农群体中,因士人领乡农的体制和持续不断的说教机制,促成了其对于湘军意识形态的认同。曾国藩时常用儒学之理开导士兵,每次“至一时数刻之久”,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6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08页。,“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6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46页。。将领们“常教士卒作字读书,书声朗朗,如家塾然”,“又时以义理反复训谕,若慈父之训爱子,听者潸然泪下”(62)王诗正:《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王壮武公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纲常意识在乡农群体中原本就根深蒂固,这种苦口婆心的说教更起到了强化的效果。
其次,话语叙事应当与叙事语境相适应。正统中的“辨华夷”和“护纲常”在历史演变中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哪一个能够成为主流、占据上风,与当时的时势紧密相关。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展开激烈战争之际,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外国势力由门户深入堂奥,《天津天约》《北京条约》相继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作为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苦难和危机进一步加深。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最重大的冲突已不再是中华民族内部的冲突,而是外来侵略与中华民族整体之间的冲突。科塞认为,外群体冲突有利于群体内部的整合,因为外群体冲突可以把“其他方面毫无联系或对立的个人或群体相互联系起来,并把他们带进一个公共的社会活动领域”(63)侯均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动员起群体成员的活力,进而增强群体团结。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单方面强调华夷之辨,而不把矛头一致对外,已经不再符合时势的需要,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共鸣。因此,《清史稿》中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将“严种族之见,人心不属”(64)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66页。列进其中。
再次,叙事话语应当与话语传统相适应。太平军与湘军的合法性叙事,虽然都借用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传承的“正统”话语,但是两者与传统话语的亲和度仍有差别。中国文化一直以来有着自觉的整体观和大一统的秩序意识,湘军“护纲常”“保民生”等关键话语皆脱胎于此,内在于文化工具箱之中。而太平军的“辨华夷”话语与“皇上帝”等基督教的语汇捆绑在一起,依附于“天国”信仰,在中国缺乏文化根基和感召动员力,无法使其内化为民众文化的组成部分。置于认知场中的文化工具箱,体现了思想工具和文明演化的历史,行动主体在界定自身的利益、目标和策略时,越是能够娴熟地从文化工具箱中寻找、应用资源,越是容易创造出为人们所认同所接受的话语方式。这也就湘军和太平军话语在动员力上形成差距的原因。青年毛泽东因此说到,“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65)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李锐则认为,“在这样一场大战争中,显出曾国藩过人之处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动员口号”(66)李锐:《为什么“独服曾文正”》,载《读书》1992年第9期。。
最后,叙事话语应当与历史发展大势相适应。总体来看,太平军和湘军合法性叙事既有与历史大势相吻合的一面,也有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消极一面。太平军通过“辨华夷”的合法性叙事,动员起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使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根基发生动摇,为最终将人民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拯救出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湘军在合法性叙事中将大一统和纲常秩序的维护作为最高追求目标,明确了清王朝在历史序列和现实格局中的正统地位,使满清入关后为了巩固统治基础而推行的消弭满汉矛盾的进程得以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大一统格局的持续发展,从而使得中国大一统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不因近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型而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产生着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两者的合法性叙事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如太平军在地域上将“中国”局限于十八省,与“满洲三省”截然对立,忽视中华民族交流和融合大势,煽动民族情绪,体现出违背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事实的固执和短见。湘军则一味强调大一统和纲常秩序,不对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施行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事实给予回应,不对当时清王朝崇满抑汉,满、汉畛域甚明的政策予以反思,表现出忽视民族问题、社会问题复杂性的历史局限。两者在构造多民族共融共存局面上均没有提出真正有效的方案,不能为民族问题的真正解决提供助益,最终无法动员和团结全国力量给予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势力以坚决、强力回击,导致中华民族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重灾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