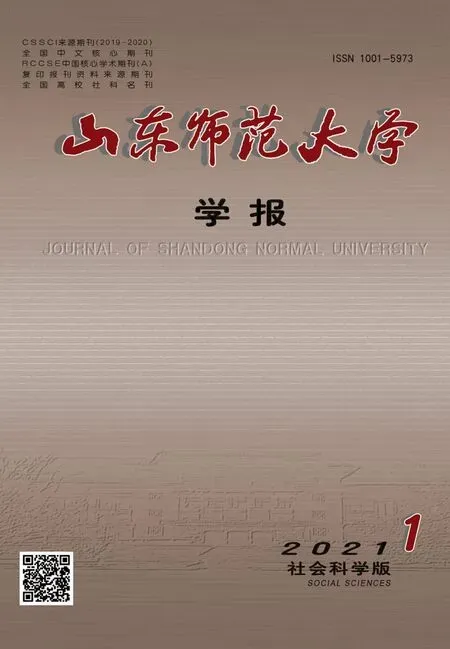被动中的抉择
——清政府同意中韩建交的原因探析*①
张礼恒
(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252000 )
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到1899年12月《中韩通商条约》签订、徐寿朋驻派韩国公使前,中韩两国政府层面间的交往是阙如的。学术界对于中韩两国何以在4年之后重建邦交这一问题多有涉及(1)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陈尚胜:《徐寿朋与近代中韩关系转型》,《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尤淑君:《甲午战争后的中朝关系》,《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李晓光、陶常梅:《晚清中韩关系走向近代外交的历程》,《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但现有研究成果存在过于空泛的缺憾,未能将大趋势与具体实务进行有机整合,给人一种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错觉。笔者认为,中韩重建邦交是合力促成的结果,既有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也有中韩两国各自需求的内在驱动。但就整体而论,清政府同意中韩建交基本上是一种被动中的抉择。
一、化被动为主动,彰显大国风范
中韩建立邦交是由韩国发起的。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第一款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2)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95页。中朝之间数百年的宗藩关系至此划上了休止符。李承纯、闵泳哲成为朝鲜派往中国的最后一任进贺谢恩使。(3)《致北洋大臣李鸿章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3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3页。此后,朝鲜为彰显独立自主之国的形态,极力抹煞属国痕迹。继1894年8月拆毁迎接清朝敕使的“迎恩门”之后,1896年11月,朝鲜又在原址上建造“独立门”“独立园”,“以彰自主之据”。(4)《北洋大臣王文韶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4869页。1897年5月,朝鲜将接待清朝敕使的“慕华馆”改为“独立馆”。同年10月,朝鲜再将“昔年敕使驻节之南别宫,现已改筑天坛,似属再为声明自主独立之意”。(5)《驻扎朝鲜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50页。

朝鲜国王李熙在向欧美派驻公使的同时,又出于以下三种考量,极力推动与中国建立邦交。其一,缓和中朝关系。中朝两国山水相连,两国人民往来不断,边境贸易、朝民越境开垦等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对于朝鲜而言,独立固然可喜,但独立的过程则让朝鲜背负上了沉重的道义亏欠。甲午年间,中国出兵朝鲜,原本是应朝鲜国王求请,帮助镇压国内叛乱,维持李氏王朝的统治。孰料,中日战端一开,朝鲜竟与日本缔结军事同盟,为日本提供军需粮草、情报(10)《致北洋大臣李鸿章电》,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3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5页:“韩廷犒赏日兵米、肉甚多,韩喜日,殊不可解。”,伏击中国军队。战争结束后,朝鲜虽然获得了独立,但其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终究是一种出卖盟友、见利忘义的卑劣行为,绝非东方国家传统之君子所为。自忖理亏的朝鲜国王为修补中朝裂痕,缓和中朝关系,遂决定主动示好,建立邦交。其二,借中朝建交,彰显独立国家形象。朝鲜国王李熙曾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试探性活动,借以观测欧美各国的反应。遗憾的是,除日俄美之外,英法德意奥等欧洲强国均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反对意见。为此,与中国建交就显得尤为迫切。按照近代国际公法,缔结邦交必须是在两个独立国家之间进行。一旦中朝建立邦交,就意味着中国对朝鲜独立身份在事实上的认可。而中朝存在数百年的宗藩关系举世尽知,中朝建交的国际影响力绝非他国可比。其三,引进中国,遏制日俄瓜分。在大韩帝国成立之前,朝鲜执行了一条由亲日到亲俄的外交战略,虽也有所收获,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极为昂贵的。无论是日本,还是俄国,皆在利用朝鲜的依附心理,在保护朝鲜的名义下,大行侵吞或瓜分朝鲜之实,致使朝鲜深陷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危险境地。1896年2月11日,国王李熙向各国驻朝使领大诉其苦:“自八月二十六日以来迄未用印,并未曾见此印,朝中颁发政令余亦全不知也。”(11)《同文馆学生朱敬彝译〈字林西报〉》,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7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740页。尤其是当日俄为缓和矛盾、避免冲突,签订系列协定以来,朝鲜成为日俄两国利益的牺牲品。此种情势如不改变,朝鲜势必沦为日俄一国或两国的殖民地,独立平等之梦终将化为泡影。为此,朝鲜决定大打“中国牌”,利用中国地缘与历史传统上的先天优势,借用中国力量,实施朝鲜版的“以夷制夷”策略(12)赵润生、张礼恒:《论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以夷制夷策略》,《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遏制日俄对朝鲜的瓜分或占领,试图在多边力量的博弈中保全朝鲜。朝鲜重臣闵种默对此曾有过清晰的表露。他说:“华弃韩,置之不理,恐非良策,将求中朝允速立约,自可防外人叵测之患。”(13)《唐绍仪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41页。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与长远的考虑,朝鲜在宣布独立后不久,就发起与中国建交攻势。1896年6月17日,朝鲜国王委任卞元圭为缔约专使,拟赴华“订立约章”,并于次日指派翻译朴台荣拜见中国“委办朝鲜商务总董”唐绍仪,打探中国意向。(14)《收北洋大臣王文韶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856-4857页。8月,朝鲜国王再派赵秉稷与唐绍仪举行会谈,表达与中国建立邦交之诚意。(15)《北洋大臣王文韶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899-4901页。
面对韩国发起的建交攻势,清政府走过了一条由拒绝到同意、由被动到主动的路径。中朝(韩)进入无邦交状态,是从代理“驻扎朝鲜总理交涉事宜”唐绍仪撤离汉城开始的,并非始于《马关条约》的签订。1894年7月28日,唐绍仪离开汉城,“赴仁川登英兵船”回国(16)《禀北洋大臣李鸿章文》,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3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0页。,中朝(韩)邦交由此中断。到1899年《中韩通商条约》签订前,中朝(韩)两国处于无邦交状态。《马关条约》签订后,朝鲜成为清政府的伤心地,既为失去朝鲜而痛心,又为朝鲜的背盟弃义而愤怒。心理学原理揭示,当木已成舟之时,治疗心理创伤的最好办法就是选择性忘却,暂且不去提及、触碰勾起回忆的人和事。在此期间,仅仅出于保护、管理在朝华商的需要,于1895年12月设立了“总商董”(17)《北洋大臣王文韶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7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563-4564页。,1896年11月委任了驻朝总领事(18)《总理衙门奏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68页。。但无论是“总商董”,还是总领事,都不具有政府层面的意义,因为前者归北洋大臣王文韶驱使,后者供总理衙门调遣,清政府据此与朝鲜保持着民间或半官方的联系,追踪着半岛局势的动向。
当朝鲜初次表达建交意向时,清政府的答复是拒绝。1896年6月,卞元圭受命为订约大臣,拟赴北京修约,临行前指派翻译朴台荣拜访“总商董”唐绍仪,试探清政府的态度。唐绍仪先答以位卑言轻,“我国大事焉能知之”?继称朝鲜先后得日俄庇护,“今国王仍驻俄馆,究系俄宾。既假宫于他国使馆,何能称为独立国主”?按照国际公法之规定,无独立之权的国王,是无权派遣使臣的;靠外国军队保护的国家,与藩属无异。唐绍仪警告道:“若王迳行派使中国,恐不以礼相待,似宜缓行为好。”(19)《收北洋大臣王文韶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856-4857页。事后,唐绍仪专门向北洋大臣作了禀报,并委婉地提醒,既然朝鲜欲与中国建交态度坚决,中国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求变,执掌中韩建交的主动权,引领中朝建交的走向。7月12日,总理衙门收到北洋大臣王文韶转呈,接受了唐绍仪的提议,又几经斟酌、研讨,最后确定了中朝建交的“三不原则”:“拟准商订通商章程,准设领事,不立条约,不遣使臣,不递国书,中国派总领事一员驻扎朝鲜都城,代办使事。”(20)《总理衙门奏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68页。
与曾经的藩属建立近代邦交毕竟是前所未有,总理衙门为此特向“外交智囊”李鸿章征询意见。7月19日,远在圣彼得堡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的李鸿章回电,完全同意总理衙门的决议。其电文称:“查英法德驻韩,皆系总领事。南美如秘鲁、伯理微亚等小国,俄奥德亦派总领事。按公法,应由总署寄信凭于彼外署,不递国书。尊拟准订通商章程,设总领事,正合。”并提议由唐绍仪出任驻朝总领事。(21)《复译署》,戴逸、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2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63页。
总理衙门的决策、李鸿章的回电均已表明,为了扭转中朝建交的被动局面,化被动为主动,清政府的外交中枢机构经慎重考虑,决定在不缔结邦交的前提下,以派驻总领事的形式,与朝鲜建立官方联系,借此阻止朝鲜的建交纠缠。按照近代国际交往惯例,两国建立邦交的标志就是互派驻外公使。而总领事可以在两国断交或不建交的情况下保持存在。由于派出机构的不同、承担职责的不同、权限的不同、归属管理权的不同,总领事与公使存在着根本性差异。而在这种差异的背后,透露出清政府对朝外交的真实意图,即以设立驻朝鲜总领事的方式,拒绝承认朝鲜的独立国地位,用一种变相的“宗藩关系”,继续保持与朝鲜交往的优越性。总理衙门对此曾有过明确的表述。它在奏折中坦言,派驻朝鲜总领事的用意,既是为了“存属国之体”,又是为了“可息朝鲜派使之心”。(22)《总理衙门奏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68页。
客观地说,总理衙门的决定的确存有不合时宜的虚枉性,但其果断求变的外交决策,取得了明显的外交成效,阻止了朝鲜单方面遣使入京缔约的建交企图,重新掌握了中朝建交的主动权。1896年11月20日,清廷朱批总理衙门奏请,同意唐绍仪为中国驻朝总领事,归总理衙门与北洋大臣双重管理。(23)《总理衙门奏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68页。1897年1月30日,唐绍仪入驻汉城。唐绍仪履职驻朝总领事,打乱了朝鲜国王李熙的盘算,延缓了中朝建交的进程。1896年11月,朝鲜国王李熙“特派前驻津督理成歧运”,准备携带拟定好的条约文本,“去京请订约章”,但随着唐绍仪的到来,只得被迫取消,“故行亦不果”。(24)《驻扎朝鲜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88-4989页。
此后,清政府派驻韩公使的过程,简直就是派驻朝总领事的翻版,依旧是被动在前、主动在后。建元称帝是朝鲜显示独立平等夙愿的一种表现。自1896年改元“建阳”之后,朝鲜就在帝制自为的道路上加速前行。据史料记载,1897年9月至10月间,议领政沈舜泽、特进官赵秉世等朝廷重臣,九次上书国王,“请加尊号”。在上书中,沈舜泽等人先是依照东方传统,追溯朝鲜肇始于檀君、箕子,历史悠久;称颂国王李熙敬天爱民,德侔天地,堪与三皇五帝比肩。次是套用西方的主权独立观念,将建元称帝视为“建独立之基,行自主之权”,《万国公法》明确写有“各国自主者可随意自立尊号”。(25)《驻扎朝鲜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51页。开化派人士徐载弼则以《独立新闻》为载体,以“独立协会”为阵地,呼吁朝鲜独立,鼓吹欲提高国家与庶民之地位,“其国君主必须与他国君主比肩而立”。10月12日,朝鲜国王李熙举行登基大典。13日,宣布建元“光武”,国号初为“大华”,后称“大韩”。至此,“大韩帝国”宣告成立。
然而,国际社会对于韩王称帝一事反映不一,赞同者有之,如日本、俄国;而日俄的赞同也不过是为了获取韩王的好感,赢得侵朝先机的廉价“投名状”,并非真正拥护。反对者有之,如英法德等国。英国驻韩总领事朱尔典认为:“我国主亦是君主之称,何须更改?”法国驻韩公使葛林德称,“我是民主之邦,不重皇王字样,安南系我属地,曾封其国主为皇”。德国驻韩总领事口麟则扬言,“欧洲五大国主倘称我帝,政府自然认受,其他小国若加尊号,事恐难成。然朝鲜非大国,无端改无主名目,未识我政府之意以为然否”。(26)《唐绍仪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39-5040页。欧洲列强的反对、质疑之声,自然令“大韩帝国”处境尴尬。1897年10月16日,韩国外署督办闵种默发布通告:“我大君主陛下于本月十二日勉膺大皇帝尊号。”各国驻韩使领反应冷淡,例行公事式地回称,“将转禀政府而已,并无提及认受与否字样”。唐绍仪事后禀报:“驻汉法德美英各员,均以韩王加尊号一节,系在其境内自有之权。至于各政府允否认受,彼等未能深悉。”俄国驻韩公使士贝邪则称:“日前接其政府来电云:韩王称皇,我视之如韩铜钱,只可销行于韩境,若到我国,虽以百万文亦不能糊一朝之口。”(27)《驻扎朝鲜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56、5050页。可以说,闵种默的话语概括了世界各国对韩王称帝的基本态度:“倭助我,俄阻我,德法戏我,英欺我”。(28)《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40页。
为摆脱尴尬,争取国际社会广泛的承认,韩王李熙再次发起对中国的外交攻势,试图在建立邦交的旗号下,获得中国对韩国改元称帝的认可。1898年6月,韩国授意朝鲜海关税务司与中国海关税务司暗通款曲,撮合中韩建交。7月,韩国宣布任命沈相薰为驻华公使,进驻北京。(29)《朝鲜总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145-5148页。韩国在中韩建交问题上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意。
面对韩国政府发起的建交攻势,清政府改变策略,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史料显示,清政府初闻韩国欲遣使入京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阻止。1898年3月23日,总理衙门电告唐绍仪:“韩派使坚拒为妥。”(30)《发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21页。5月,总理衙门获悉韩国欲派使臣来华的消息,电询唐绍仪:“韩拟派使系几等?是否欲议商约?现认韩国自主者几国?现住韩京各使内,有几国系总领事、参赞、代办?希详查电复。再筹办法。”(31)《发电档》,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6月2日,唐绍仪电复,“韩拟派二等使赴京订约”。按照国际惯例,二等公使奉有国书,须觐见该国君主或元首。(32)[美]惠顿:《万国公法》,张剑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81页:“第十二节 延见之规:第一等国使,可在公朝觐见。前此多设仪仗款接,今则私觌公见,率从简便,概以内朝延见,与二、三等国使同例。”唐绍仪深知,让昔日行三跪九叩之礼的藩属之臣,以平等礼节觐见清朝皇帝,实是对天朝尊威的亵渎。为此,他提议:“似应由华先行派使来韩,以示昔年主仆之别。若任韩先派,似系为彼所索,恐有碍体制。”(33)《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35页。唐绍仪的提议可谓是深孚清政府心意。6月12日,总理衙门电令唐绍仪:“韩本属邦,派使不便接待”,“韩愿订商约,尽可就近与议”,韩国须“止派使”。(34)《发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36页。但是,总理衙门的如意算盘,遭到了韩国政府的抵制。6月16日,唐绍仪禀报,韩国自恃有日俄英等国的支持,指斥清政府的外交构想违背国际惯例,坚持遣使建交在前,订立通商章程在后。由于中韩立场分歧严重,虽经多次斡旋,韩国拒不通融。无奈之下,唐绍仪只得据实禀报,请求“电示”。(35)《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37页。
为破解中韩外交的僵局,总理衙门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有条件地采纳韩国的议案。7月8日,总理衙门电示唐绍仪,“韩若再坚求派使,可与商明遣四等公使,国书由署代递,无庸觐见。其通商约章,本署当与会议。”(36)《发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40页。该电文内容透露出了总理衙门的双重目的,即援引近代国际公法四等公使无需向派驻国君主或元首递交国书之规定,拒绝韩国公使觐见清朝皇帝;由驻韩总领事签订中韩通商章程。孰料,唐绍仪对此提出质疑,力主中国派出四等公使,进驻汉城。(37)《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1页。
就在总理衙门举棋不定之时,7月上旬,韩国政府任命沈相薰为二等驻华公使,并委托时任朝鲜总税务司柏卓安草拟国书。(38)《朝鲜总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146页。
韩国发起的建交攻势,迫使清政府再度求新求变。1898年8月5日,锐意变法的光绪皇帝发布谕旨:“所有派使、递国书、议约,韩使来京、递国书、觐见,均准行。”(39)《军机处电寄唐绍仪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3页。从此,中韩建交快速推进。8月13日,清政府发布上谕,任命徐寿朋为驻扎朝鲜国钦差大臣,后改为出使朝鲜国大臣。(40)《军机处交出本日上谕》,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135页。1899年1月25日,徐寿朋抵达汉城。1月31日,向大韩帝国皇帝李熙递交国书。(41)《徐寿朋抄折》,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200页。9月11日,《中韩通商章程》正式签字盖印。(42)《出使韩国大臣徐寿朋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245-5246页。1900年1月21日,徐寿朋成为中国首任驻韩公使。(43)《徐寿朋抄折》,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306页。至此,中朝(韩)两国历经5年终于缔结邦交。
二、迫于列强压力,顺势而为
随着近代东亚的整体沦陷,域外力量几近成为该地区变动的主宰。在中日朝(韩)三国的历史进程中,欧美列强的身影处处可见。发生在19世纪末期的中韩建交事件同样也是如此。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除老牌列强外,日本这个新崛起的列强也参与其中,横加影响。
在中韩建交启动之初,韩国就挟洋自重,每每以“如不重修新约,维(惟)恐各国必有诘问”(44)《唐绍仪原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873页。为借口,试图迫使中国就范。史料显示,介于中韩建交的国家主要有日本、俄国、英国。这三个国家可谓是各怀鬼胎,各有盘算,或出于眼前的利益,或出于长远的考虑,纷纷搀入其间,联合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迫中国就范。地处瓜分狂潮中的清政府出于对新老列强的忌惮,被迫改弦更张,顺势而为。可以说,列强的联合施压成为助推中韩建交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
具体来说,日本助推中韩建交是为了缓和日韩矛盾,意在日俄争霸韩国中占据有利态势。日本凭借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实现了驱逐中国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构想,但战后急切冒进的侵朝行动,却触犯了欲速则不达的兵家大忌。以1895年10月“乙未事变”为转折,以1896年2月朝王“俄馆播迁”为标志,日朝关系急剧恶化,朝鲜迅速由亲日转向了亲俄。俄国成为甲午战争后的最大获利者,几乎掌控了朝鲜的军事、财政、外交大权。日本在与俄国的争夺中明显处于下风。史称:“倭之国人恃当华事之后,愤俄收渔人之利,矜骄之心日益坚固,急拟兴兵问韩之罪,将与俄战,独伊藤博文深悉其非俄敌,因请倭主将上下两议院关闭十日,俾息国人奢愤之议。”(45)《委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05页。为挽回颓势,实现侵吞朝鲜的夙愿,日本除对俄国妥协退让外,还极力讨好韩国。1897年10月,大韩帝国成立时,日本是首批承认的国家之一。时人曾一针见血地揭披了日本的心机:“乙未秋间倭杀闵妃,韩之恨倭已极,乃倭颇谙韩性,屡以谀词奉承于王,欲藉此以释韩疑,并可消其杀闵妃之憾也。”(46)《驻扎朝鲜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50页。韩国政府深谙日本之心理,遂在提请中韩建交屡次受挫之后,施展以夷制华之术,达到建立邦交之目的。而日本的考虑显然更胜一筹,敦促中国与韩国建交,一则显示对韩国的支持,借此缓和日韩关系,扭转在日俄角逐中的不利局面;二则引进中国,遏制俄国,改变俄国在韩一家独大的格局,实施日本版的“以夷制夷”之策。因此,当韩国政府发出求援时,日本政府痛快答应。1898年6月12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致函总理衙门,内称:“兹准外务大臣电开:因现在韩国之清国人民其数不少,韩国政府愿与清国订立条约,请我政府居间玉成,未知清国政府于意云何等因。务希示复,以便电复本国为望。”(47)《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118页。
俄国作为中日甲午战争的既得利益者,利用朝鲜政府急于寻求庇护的时机,疯狂拓展权益空间,赚得盆满钵满。巩固扩大在韩国的势力范围,自然成为俄国的首选。为此,俄国处处以韩国的支持者、保护者的姿态出现。1897年10月,韩王称帝,俄国是首批拥护国之一。唐绍仪曾对此有过深入剖析。他说,俄国原本并不赞成韩王称帝,“乃近来韩王僭加尊号之意已决,俄之不欲强止此举,或恐韩近倭远俄,虑失其权利起见”(48)《驻扎朝鲜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50页。。当韩国为中韩建交相求助时,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驻韩公使士贝邪、驻华代理公使巴布罗福,纷纷以劝说的名义,联袂向中国施加影响。1898年3月31日,俄国驻华公使巴布罗福照会总理衙门,劝说中韩订约建交。照会内称:“兹奉外部大臣咨称,高丽政府以贵国高丽彼此派往常驻之使,诚愿从速接续,迳行往来,故请驻汉城俄使转托本国政府于贵国政府,派往高丽之使,亦接高丽派往贵国之使之事,相助为理。复念中国高丽二邻邦接续迳行,睦谊往来,于中国商务有益,且固信中国政府甘愿成此高丽美意,故公爵穆兹嘱本署大臣将此奉达贵国,并候如何定夺。以上所列奉达贵署,并以公爵穆之意中国高丽从速彼此派往驻扎之使,于贵国利益尤所欲之举,烦请贵署将贵国政府何时、何等人员定派出使高丽之处示知可也。”(49)《俄国署公使巴布罗福照会》,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83页。
英国是利益至上的典型。从19世纪70年代起,随着整体国力的下降、俄美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英国的全球战略由攻转守,维持现有国际秩序成为其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在东亚地区,英国最初的外交构想是扶植中国,打压日本,稳定东亚国际局势。为此,自1882年英朝条约缔结后,英国在朝鲜只设有驻华公使领导下的总领事,变相地承认了中朝宗藩关系的客观存在。日本外务卿陆奥宗光曾说过:“当时英、俄两国都在暗中默认了中朝之间的宗属关系,在交涉有关朝鲜的重大事件时,只是将中国置于中心位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50)[日]陆奥宗光:《蹇蹇录——甲午战争秘录》,徐静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0-81页。但甲午战争的爆发,颠覆了东亚地区的原有秩序,引发了世界格局的震荡。基于现实的考虑,更基于长远的打算,英国开始调整其远东政策,逐渐由扶植中国变为亲近日本,推行以日制俄的外交战略。与此相应,英国的对朝政策也随之而变。史料显示,早在韩国改元称帝之初,英国的态度是暧昧的。但当韩国为中韩建交而向其求援时,英国转而给予了明确的支持。1898年6月,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访问韩国,“韩王及外部臣工曾经苦恳转求”游说中国,促成中韩建交。(51)《委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函》,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021页。7月4日,韩国外署大臣李道宰求请英国驻韩总领事朱尔典,托其致电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请韩与华订约,并拟按照英韩约,想窦使日间必诣钧署请议约事”。(52)《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39页。
清政府确定的中韩建交的既定国策因东西方列强的介入而改变,发生了由拒绝建交到同意建交的历史性转变。其实,早在中韩建交的初始阶段,唐绍仪作为中韩建交事实上的推动者,就预判到了东西方列强介入的可能性。1896年6月,唐绍仪在驳阻韩国试探性建交之余,致函总理衙门:“韩王派使意切,此次虽经绍仪暂为驳阻,仍恐俄使韦贝及各国使员劝解王疑,竟备国书,派使前赴京师,请修约款”,提请未雨绸缪,以免被动。(53)《唐绍仪原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873页。11月,唐绍仪在致函中称:“今则韩臣鸷骜者多,又有他国之人唆使”,暗示总理衙门绝不能一味地拒绝韩国的建交之请。(54)《知府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71页。总理衙门对于唐绍仪的提醒是高度重视的。7月16日,在致李鸿章的函电中称,虽不愿与韩国建交,“然虑各国怂恿,宜预筹办法”。(55)《总理衙门发李鸿章电》,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874页。从后来的进程看,总理衙门正是出于对列强介入的忌惮,才于同年11月同意设立驻朝总领事,迈出了中韩邦交正常化的第一步。在奏请设立驻韩总领事的奏折中,总理衙门坦承,“派领事分驻各口,庶可息朝鲜派使之心,并可免他国煽惑之议”。(56)《总理衙门奏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68页。
1898年3月后,俄日英等国相继游说中韩建交。此时深陷瓜分狂潮中的清政府,国际地位急剧下降,自然不敢无视列强的表态。在论及中韩建交时,驻韩总领事唐绍仪、总理衙门和清政府有关官员,无不把东西方列强的介入当作重要的变量考虑在内,大有谈虎色变之惧。1898年7月5日,唐绍仪致电总理衙门,内称:“俄、倭、英先后代韩请约,非为保护中韩交涉商务起见,殊有关各西国在亚洲争强之患。倘华不与韩订约,恐日后另生枝节。”(57)《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第39页。8月10日,总理衙门在奏折中集中回应了俄日英等国的要求,公开承认是外部压力促成了中国对韩政策的改变。在奏折中,总理衙门开宗明义,将“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款中国认明朝鲜国独立自主”和“英俄德法美义奥日本诸国均认朝鲜自主,或派三等使臣驻扎汉城,或派领事兼理使事”,视为中国决定选派出使韩国大臣的两条重要因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出于对列强意向的重视,总理衙门高度重视驻韩大臣的派出,向朝廷递交了一份17人的大名单,以供挑选。(58)1898年8月10日,总理衙门提供的人选名单:徐建寅、黄遵宪、徐寿朋、杨兆鉴、志锐、蔡钧、曾广钧、江标、王同愈、陈宝琛、梁诚、傅龙云、孙宝琦、袁昶、黄绍箕、张亨嘉、寿富。——《总理衙门奏折》,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133-5134页。备选人员众多,堪称自1875年清政府选派郭嵩焘出使英国以来的首次,开创了近代中国遣派驻外使节的历史记录。在驻韩大臣人员的选定上,同样体现了清政府对列强意向的重视。8月11日,清廷颁布上谕,委派张亨嘉为驻韩国公使。13日,清廷变更圣谕,改派徐寿朋为驻韩国公使。(59)《上谕》,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135页。人员及称谓的变化,表征了清政府的良苦用心。一则,公使人员级别的提升。张亨嘉本为翰林院编修,官秩介于正五品至正七品之间;徐寿朋原为安徽按察使,官秩为正三品。在官秩上,徐寿朋不仅远居张亨嘉之上,实际上也成为自清政府派出驻外使节以来,级别最高的外交官员。二则,驻韩公使级别的提高。在8月11日的上谕中,宣布张亨嘉为“驻扎朝鲜国四等公使”。8月13日的上谕则任命徐寿朋为“驻扎朝鲜国钦差大臣”。按照清代官制,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的徐寿朋直等于国际公法下的“全权公使”,拥有自主裁决一切外交事宜的权力,而“四等公使”则难望其项背。史料显示,东西方列强的联合施压明显加快了中韩建交的进程。清政府一改两年前的拒绝、延宕作派,迅速钦派了以徐寿朋为首的高级别外交使团,于1899年2月向韩国皇帝递交国书,入驻汉城。
三、内在驱动力,保护在韩华商与追讨韩国欠款
清政府在中韩建交过程中总体上是呈被动态势,却也不乏积极主动的要因,那就是在韩华商与韩国欠款。换言之,保护在韩华商利益与追讨韩国欠款,是清政府接受中韩建交提议的两大内在驱动力。
在韩华商经济的腾飞始于袁世凯担任驻朝商务委员期间(1885—1894年)。袁世凯秉承“以商驭属”的经济战略,坚持“在属之商务日盛,即驭属之事权日增”(60)《禀北洋大臣李鸿章文》,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1页。的理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在韩华商的保护与管理,保证了华商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经商区域上,华商实现了由沿海通商口岸向内地的延伸;在营销品种上,华商由传统的生活用品,发展到金砂、牛皮等贵重物品;在运输手段上,完成了由原始的肩挑手提到近代化的机器轮船的跨越;在组织方式上,华商不再是锱铢必较、独来独往的商人,而是与中朝官府密切合作的商帮,涌现出了以“韩国首富”广东巨商谭以时为代表的大批华商巨贾;在国际地位上,实现了由弱变强的转变,打破了日商对朝鲜市场的垄断,成为与日商并驾齐驱的两大力量之一,大有弯道超越的趋势。(61)张礼恒:《袁世凯对在朝华商的保护与管理》,《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被逐出朝鲜半岛,驻各口岸商务委员相继内撤,在朝华商处境艰难。按照战前中英两国政府商定,在朝华商暂由英国驻朝总领事及海关税务司人员代为管辖、保护。(62)1899年12月22日,徐寿朋向总理衙门提请嘉奖保护在韩华商人员名单,因英国政府规定驻外使领不得接受他国嘉奖,故只有时任朝鲜海关税务司人员: 柏卓安、欧森、阿滋布、湛玛斯、何文德、罗保德、普尔来、阿莫尔。——《出使大臣徐寿朋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292页。尽管如此,华商被日韩商人殴打、欺诈之事时有发生,日本租界巡捕可擅入华商宅室搜查、捕人。
后虽委任唐绍仪为商务总董、驻韩总领事,但因中韩尚未建交,韩国政府拒不承认其外交官身份,无权介入中外官司,“凡遇交涉及争讼事件,无人保护”,华商只能任人宰割。(63)《总理衙门奏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68页。难能可贵的是,华商身处逆境,不仅生存下来,且商务有了振兴的迹象。到1896年底,“华商之在韩者,已有四千余人,迩来进口货物日增月盛,较之日本商人,加增不啻倍蓰,是商务渐有起色”。(64)《收委办朝鲜商务总董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59页。汉城、仁川两地华商,“比之日本商人一年之中犹多数十万元生意”。(65)《委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88页。可以断言,只要有妥善的保护,凭借着勤劳与智慧,假以时日,华商必定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打破日商的垄断,形成与日商平分秋色的局面。正因为如此,从韩国提出建交请求起,有识之士就委婉地批评了清政府拒绝建交的决定,呼吁重视对在韩华商的保护。1895年11月5日,北洋大臣王文韶在致总理衙门函中,力主将“仁川港口华商租界与各国租界联合为一”,借此遏制日本的侵吞。他说道:只因中韩尚未建交,“在韩华商共计四千余人,无所依恃,以亚洲商务大局而论,朝鲜一隅,终未能从此隔绝。现虽暂托英员保护,究于我民情俗例有所隔膜。遇有我商待理各事,不无仍多窒碍”。时任浙江温处道的袁世凯则提议,在中韩建交之前,以商董的名义,派人驻朝保护华商。(66)《收北洋大臣王文韶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7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516-4517页。1896年11月5日,唐绍仪向总理衙门陈情:“自驻韩各口委员撤回后,华商皆生觖望,日人肆其强横,韩人频加藐视,虽曾托英总领事代为照料华商事件,而情词隔阂,措置终难。”“商情无人保护,实于国体有碍。倘蒙派员驻韩,当可止其来使,兼酌议税则,保卫商民,有裨大局,实非浅鲜”。(67)《收委办朝鲜商务总董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59页。1897年3月,唐绍仪向总理衙门婉转表达了中韩建交的迫切性。他说,年初驻韩各国公使及驻仁川领事,在仁川工部局专门讨论各国租界事务。日本驻仁川领事石井菊次郎公开提议,中国尚为无约之国,其在韩的元山松亭租界、仁川三里寨租界、釜山租界理应没收。他说:“中国与朝鲜无条约,华租界应即充公,归还朝鲜,华人何得擅踞?又何得入工部局会议事件?”美国驻韩公使斯露士附和道:“华韩无约,华人竟有租界。此诚公法所未见。”会议虽未形成决议,但商定续议,华商租界岌岌可危。(68)《驻扎朝鲜领事唐绍仪禀》,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89-4990页。史料显示,唐绍仪等人的建议成为撬动中韩建交的杠杆,逐渐改变了清政府的对韩政策,使甲午战后的中韩关系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折。从“商务总董”“驻韩总领事”,到“驻韩公使”,囊括了中韩关系由民间到官方、由低层次官方关系到高层次政府关系确立的全部过程。而清政府每一次对韩政策的改变,无不与华商利益紧密相关。1895年11月5日,总理衙门明确规定了“商务总董”的职责,“名系充当商董,隐以维持商务”。(69)《收北洋大臣王文韶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7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517页。1896年11月20日,总理衙门坦承,设立驻韩总领事的目的之一,是“保华民通商之利”。(70)《总理衙门奏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968页。1898年8月10日,总理衙门在奏折中称,派遣出使韩国大臣是因为“朝鲜国土与我奉吉两省水陆毗连,商民来往交涉甚繁,既经准令自主,自应按照公法遣使订约,以广怀柔之量,而联车辅之情”。(71)《总理衙门奏折》,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133页。据此完全可以说,保护在韩华商的利益,是清政府最终接受韩国提议,同意中韩建交的内在驱动力之一。
向韩国追讨欠款,是清政府同意中韩建交的另一内在驱动力。从19世纪80年代起,朝鲜为缓解财政困难,多次向清政府借款。据史料记载,大型的借款共有5笔:1882年10月1日,朝鲜向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借款50万两,实到20万两,分12年还清。(72)朝鲜内阁编:《度支部来去案》(奎17766)第4册,隆熙三年十一月三十日(1909年1月30日)“照会 第七○○号”:“光绪八年由唐道廷枢用招商矿务两局出名与朝鲜政府订立合同,原借足色纹银五十万两,后来开平矿局有无拨款未能知悉,而招商局共借出曹平纹银二十万两。”1885年7月,朝鲜向电报总局借款10万两,分25年还清。(73)权赫秀编著:《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36页。1892年、1893年,朝鲜两次与华商“同顺泰”签订借款合同,共借款20万两,分80—100个月还清。(74)[韩]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第9卷《清案2》,韩国:高丽大学出版部,1965年,第304页。1893年,朝鲜政府向清政府借款35000两。(75)戴逸、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23)《电报》(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91页。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朝鲜共向清政府借款53.5万两白银。甲午战争之后,中韩两国处于隔绝状态,韩国欠款遥遥无期。1895年10月,袁世凯首次提议,为防欠款化为乌有,必须重新建立政府间的联系,委派专人入韩,“坐催各项债款”。北洋大臣王文韶对此表示赞同,称“该道所陈尚属可采”。(76)《收北洋大臣王文韶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4517页。从此以后,追讨韩国欠款就成为清政府同意中韩建交的重要考量之一,也成为出使韩国大臣、驻韩公使的重要职责之一。1898年11月18日,总理衙门指令北洋大臣彻查韩国欠款数额,以便追讨。由于时隔已久,且经战乱,出使大臣徐寿朋遂于1899年3月22日向北洋大臣裕禄求援。3月29日,裕禄致函总理衙门,要求贷款经手人唐绍仪核实韩国欠款本息总数,一并向韩国追讨。(77)《北洋大臣裕禄文》,郭廷以、黎育澍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8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2年,第5204-5205页。然而,追讨欠款实属不易,直到1908年中韩两国才达成协议,韩国一次性支付“日金三十五万圆作为全数偿还”。(78)朝鲜内阁编:《度支部来去案》(奎17766)第4册,隆熙三年十一月三十日(1909年1月30日)“照会 第七○○号”。至此,韩国政府基本结清了招商局、电报局的欠款。
四、结语
从表面上看,清政府在与韩国的这场建交博弈中取得了胜利,改变了韩国建交在前、订立通商章程在后的建交方略,将中韩建交的进程纳入中方的设计轨道,实现了《中韩通商章程》签订在前,中韩建交在后的大逆转。但清政府在局部环节上的主动,却无法掩饰其在中韩建交全局中的被动。中韩建交的全部过程显示,面对韩国发起的一次次建交攻势,清政府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境地。它在每一个重要节点上的反击,究其实质,不过是对韩国建交攻势的消极回应而已。韩国政府在甲午战后东亚格局分化调整的关键期,利用中国身陷被瓜分狂潮的有利时机,充分施展纵横捭阖外交之术,将域内域外力量纠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由韩国为主角、英日俄等国为配角的强大阵营,主动出击,联合施压,逼迫清政府就范。尽管在这其中,韩国政府多有妥协、退让,但就最终的结果而论,韩国毕竟实现了中韩建交的夙愿。因此,完全可以说韩国才是中韩建交博弈的大赢家,韩国才是中韩建交节奏的真正操控者。
中韩建交开创两国关系的新纪元,宣告了东方外交体制的寿终正寝。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始终是东亚文化的创造者与输出者,由宗法伦理推衍而成的“宗藩体制”成为东亚地区国家交往的外交准则,构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相环绕的天下谱系。中国皇帝作为万国之“宗主”,对体制内的各藩属拥有册封之权、保护之责。藩属国则有向中国皇帝“勤修职贡”之职。尽管宗藩体制的运行规则为“有道则来,无道则去”,但发轫于儒家文化的宗藩体制毕竟是一种不平等的国家关系,藩属国不仅在大义名分上无法与宗主国相提并论,且要定期遣使来华,行三跪九叩之礼,借以映衬宗主国的隆尊。当时光进入19世纪90年代之时,早已跌落神坛的清政府依旧残存着天朝上国的梦幻,拒绝在平等的基础上与韩国缔结邦交,借此延续宗藩体制的余脉。为此,不惜在甲午战争之后4年多的时间内,中断与韩国的官方联系,置4000多名在韩华商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将本应承担的国家职责交由外国代管。当韩国主动提出建交之请时,清政府考虑最多的不是民族利益,而是一家一姓的王朝利益;关注的不是数千名在韩华商的生命安危,而是大清皇帝在平等礼仪下的那点可怜尊威。由此不难看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数十年的改革探索,清政府仍然没有走出王朝国家的窠臼,依旧是一个视王朝利益高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封建王朝。可悲可叹的是,尽管清政府在中韩建交问题上设置了若干障碍,却未能阻止中韩建交的前进步伐,最终在外力的裹挟下极不情愿地走向了建交的终点。1900年1月21日,随着徐寿朋向大韩帝国皇帝递交国书、就任驻韩公使,拥有上千年之久的东方外交体制——宗藩体制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中韩建交的实现,标志着国际公法在与宗藩体制的博弈中取得了完胜。从起源的角度看,无论是国际公法,还是宗藩体制,皆是人类相互隔绝状态下的产物,而其辐射的区域自然也就是有限的,而非无限的。因此,所谓的国际公法,更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欧洲洲际公法。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并不存在一个“通天下皆一式”的交往准则,各种文明或文化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价值。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人类社会由分散走向集中,世界呈现出一体化端倪。欧美国家在对全球展开殖民征服的同时,还强行兜售其价值伦理、行为准则。欧洲洲际公法遂以国际公法的名义被推向了全世界,文明间的冲突随之爆发。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是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的冲突,也是东西方两种外交体制的对抗。而由朝鲜问题引发的东西方两种外交体制的抗争,折射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渐加深的历史。截止到19世纪80年代前,清政府以双重标准应对时局的变化,一方面按照国际公法的准则,向欧美国家遣派驻外使领,加速融入国际社会;一方面在东方尤其是朝鲜问题上恪守传统,奉行宗藩体制。欧美国家尽管对此多有抗议,却又无可奈何。1882年之后,在朝鲜按照国际公法原则与欧美缔结条约的新形势下,清政府依旧以宗主国的身份,视朝鲜为天然的藩属国。对朝政策的这种结构性矛盾,致使清政府在涉朝问题上捉襟见肘。清政府既要应对朝鲜追求独立自主的挑战,又要遏制日美等国对宗藩体制的抨击与肢解,捍卫东方外交体制的正当性。然而,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苦心经营,随着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均化为泡影。衰落期的封建王朝最终惨败给了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制度。1900年中韩建交的实现,宣告了东方宗藩体制与西方国际公法持续60年抗争历史的终结。1901年,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则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体制完全被纳入到了国际公法主导下的国际条约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