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正直受难者诗篇》的主题思想探析
赵彬宇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00871,北京)
古代先民大多以超现实的方式对世界产生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他们以神话解读世界,以仪式践行信仰,由此形成的宗教观念蕴含着先民对整个宇宙秩序和人类自身的理解。宗教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中占有核心地位,流传下来的楔形文字文学作品也基本都带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在众多文学文献中,有一些被现代学者归类为智慧文学(wisdom literature)或称教谕文学(didactic literature)的作品,着重探讨了人类与神灵的关系,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宗教神学方面的思考。《正直受难者诗篇》(ThePoemoftheRighteousSufferer)是这类作品中尤为引人关注的一篇,但由于作品文本使用了大量罕见词汇和极为繁复的创作技巧,语言较为晦涩难懂,在理解作品内容时各个学者的见解不尽相同,特别是关于作品的创作背景及其所反映的宗教思想仍然存在诸多争议。
1 信仰与受难的主题
人类历史上有关信仰的合理性、神明的公正、人类的苦难等方面的困惑催生了众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其中就包括古代两河流域的经典长诗《正直受难者诗篇》。这篇作品成文于加喜特王朝(约公元前1595—1155)晚期,其古代题目取自作品第一行的开头,即《我愿赞颂智慧之主》(ludlulbēlnēmeqi)。文本开篇是一段对巴比伦主神马尔杜克(Marduk)的赞颂,描述了马尔杜克既暴虐又仁爱的双重特性。作品接着叙述了一位名为舒布什- 梅西乐- 沙干(ubši-mešrê-akkan)的主人公先遭受苦难而后得到救赎的经过。主人公本是一直敬畏神明、不断祷告和献祭的虔诚信徒,但却相继遭受一系列厄运:先是社会人际关系恶化,被家人驱逐,受众人责骂;紧接着是身体健康状况恶化,罹患多种疾病,饱受折磨。在文本的后半部分,马尔杜克又逐一消除了主人公的病痛,恢复了他的人际关系,让其享受安乐富足。
除《正直受难者诗篇》以外,还有不少两河流域的古代作品或多或少表达了对信仰、虔诚、受难、怀疑等有关问题的思考,但多数文献并非是全文专门探讨此类问题的作品。就目前已解读的文献而言,至少还有三篇智慧文学作品专门表现类似的主题,分别是用苏美尔语创作的《人与其神》(AManandHisGod)和用阿卡德语写成的《人与其神的对话》(TheDialogueBetweenaManandHisGod)以及《巴比伦神正论》(TheBabylonianTheodicy)。虽然表面上这四篇作品的主要内容十分近似,然而《正直受难者诗篇》的叙述内容相较其他三篇作品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
首先,在《人与其神》和《人与其神的对话》中虽然都只有一位神出现,但文中没有具体指出神的名字,神明的形象接近于祈祷者个人的保护神。《巴比伦神正论》则是广泛地探讨众神对人世的影响,也没有出现具体的神名。这三篇作品可看作是没有具体所指的、任何人与任何神之间都可能发生的故事。而《正直受难者诗篇》与此不同,不仅明确提及马尔杜克神,把受难和救赎都归因于马尔杜克,甚至在开篇和结尾都用较大的篇幅赞颂马尔杜克。
此外,在叙述从受难到救赎的这一过程中,《人与其神》和《人与其神的对话》都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信徒遭受的苦难,而对于救赎的过程着墨不多。而《巴比伦神正论》只在最后一节表达了对获得神明救赎的渴求,实际上没有关于受难者处境好转的叙述内容。《正直受难者诗篇》则与此不同,描述主人公遭受苦难的部分不足全诗的一半,文本详细叙述了获得救赎的过程,并且在救赎之后还有前往神庙礼拜和献祭的情节,这在其他三篇作品中都没有出现。
由此可见,虽然《正直受难者诗篇》的主题在古代近东的文学传统中并非独有,但仍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说明该诗篇很可能与其他同类作品有着不同的创作背景,而其中反映的宗教思想也有可能存在差别。况且就虔诚信徒遭受苦难的这一文学主题而言,《人与其神》和《人与其神的对话》均成文于古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1880—1595),《巴比伦神正论》则可能是伊辛第二王朝(约公元前1157—1026)甚至更晚时期的作品。所以《正直受难者诗篇》应该处于这一文学传统的发展过程当中,但与此前后的作品都有很高的相似性,反而是处在中间的这一诗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更显出该作品的独特。
2 作品思想的研究概况
《正直受难者诗篇》所探讨的“受难”主题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总能占有一席之地,透露出一种人类基于共同的生活体验而感受到的悲观无奈,加之该作品与《圣经·约伯记》的情节高度相近,因而历来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而各位学者对该作品的宗教思想提出了多种看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第一种观点认为作品含有对于人不得不服从于神的悲观无奈情绪,表达出对虔诚敬神这一主流宗教观念的怀疑,控诉着神明的不公。持这一观点的包括卡雷尔·范德托恩(Karel van der Toorn)和多罗特娅·西茨勒(Dorothea Sitzler)。范德托恩认为这篇作品是在“悲苦的呼喊”中表达“对神的控诉”,“暗示了神的专横武断和反复无常”,含有“悲观愤世”的意味。[1]西茨勒则在其专著《“谴责神明”:一个古代近东的宗教主题》中对《正直受难者诗篇》以及上文提到的同类题材的另外三篇作品作了系统研究,从著作的书名即可看出,她把这一类作品的主题都概括为“谴责神明(Vorwurf gegen Gott)”,而受难者的角色被认定为“控诉者(Ankläger)”。[2]
表面看来,这类作品的确描述了虔诚的人受苦受难、渎神的人反而得意顺遂的情况,与当时主流文化所信奉的虔敬带来福祉的观念相左。但细读文本即可看出,《正直受难者诗篇》中没有提及因为陷入苦难而停止敬畏神明或疏忽宗教义务的内容,反倒是赞颂神的内容占有不小的篇幅,甚至在I 37出现“我将称颂他的愤怒(lušāpiuggassu)”这样的表达。可见,即使是神发怒而施加惩罚,也应服从和称颂,认为作品的思想是怀疑神的公正、控诉神的惩罚的观点值得商榷。
第二种观点指出作品慨叹神明的意志不可理解,饱含对芸芸众生难以知晓神意的无奈。托基尔·雅各布森(Thorkild Jacobsen)和大岛孝义(Takayoshi Oshima)就主张这一观点。雅各布森认为《正直受难者诗篇》和《巴比伦神正论》两篇作品代表着当时的宗教自觉,探讨了对神的信仰问题,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受难时对自身产生怀疑,开始反思自己的判断力和理解力。[3]而大岛孝义也从《巴比伦神正论》和一些祷文中引证,说明人类智识有限、神意莫测是两河流域普遍的宗教观念,所以作品中的悲观情绪不应视为对神的控诉,而是对人类自身的抱怨。[4]
这一观点符合两河流域的主流宗教观,也可以较好地解释作品中受难部分的思想内涵。但正如上文所述,该诗篇与同类作品存在明显差异,重点在于救赎的部分。且不同于《巴比伦神正论》以辩论的形式讨论人神关系和受难缘由,《正直受难者诗篇》只是一个受难者自身经历的独白,并没有把对神的信仰作为核心问题加以探讨。所以作品中确实含有对神明意志不可理解的感慨,但这不是全部的思想内涵。
第三种观点指出该诗篇奉马尔杜克为唯一的至高神,从中体现了一神崇拜的思想。这是让·博泰罗(Jean Bottéro)提出的主张,他认为这篇作品的思想“完全是一神崇拜(résolument monoltrique)”,作品旨在赞颂独一的马尔杜克,从头至尾都将马尔杜克视作唯一的创造神和唯一决定命运的神。[5]也就是说,不论是遭受苦难还是获得救赎,主人公都坚信马尔杜克信仰。
第四种观点认为诗篇中的受难和救赎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宗教,作品的目的在于宣扬以马尔杜克为主的新宗教,强调信仰马尔杜克才可获得救赎。威廉·莫兰(William Moran)曾在一次讲座中谈论了他的这一看法。基于对文本的研读,他注意到作品前半部分的受难和后半部分的救赎形成明显的对比,在前半部分除去开篇I 1~40行对马尔杜克的赞颂以外,剩下二百行的内容没有再提及马尔杜克,而这部分文本反复出现“ilī(我的神)”“ištarī(我的女神)”一类的表述,代表着一种信仰个人守护神的宗教观念。这种传统的宗教观念没能让主人公脱离苦难,直到他转而信仰马尔杜克才得以救赎。[6]
这一观点很好地解释了这篇作品有别于同类型作品的原因。因为其他作品都是在信仰自己守护神的传统宗教思想下创作的,反映的是受难者与其个人的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没有出现具体的神名。而《正直受难者诗篇》是在信仰以马尔杜克为主神的新宗教观念下创作的,自然需要明确提及马尔杜克的名字。但需注意的是,全诗反复提到马尔杜克具有仁慈和狂暴的双重性,且文中I 15~16点明守护神的行为受到马尔杜克的影响,所以不论受难还是救赎应该都是由马尔杜克所掌控的,作品前后两部分是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宗教观仍需进一步论证。不过宣扬对马尔杜克的信仰应该是作品的主旨。
上述讨论说明了该作品思想内涵的复杂性,各位学者的观点不一,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就此分析出的作品内涵仍然不够清晰。这些对作品宗教思想的研究多局限于文本内部,或通过比较同类文本的方法加以阐释,较少关注其创作的时代背景。为了更准确而清楚地理解作品所宣扬的宗教思想,还需回归到加喜特时期的历史背景下,发掘作品的创作动机。对此,下文将在细读作品、从文本内部分析作品思想的基础上,参照同类作品相互印证,并回归作品创作时期的历史背景,结合文本之外的其他材料,探讨《正直受难者诗篇》的创作动机,分析作品中蕴含的宗教观念。
3 诗篇对人类信仰与神明公正的思辨
通观全诗可以发现,《正直受难者诗篇》的思想内涵是深深植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传统中的,虽然该作品传达出的观念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但这并未脱离两河流域总体的宗教环境,也没有对整个信仰体系的否定或反叛。全诗的宗教思想归纳起来大致包括:宣扬对神明的敬畏,倡导虔诚地履行宗教义务;慨叹凡人的智识有限,不可揣测神明的意志;凸显马尔杜克在众神中的至高地位及其掌控人生命运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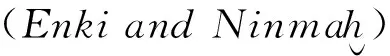

祈求和祷告,铭记在我心①;
tés-li-tumta-ši-matni-qu-usak-ku-ú-a
祷告(于我)是明智,献祭是我(常行的)祀仪。
……
教导国家,遵守男神的仪式;
规训子民,敬重女神的名字。
可见主人公描述的自身形象是一个敬畏神明、不断祷告和献祭的信徒,并且也注重向他人宣扬这样的敬神观念。同样,苏美尔语版的《人与其神》在开篇也如此强调:

人应当虔敬称颂神的伟大,
青年要真诚赞美神说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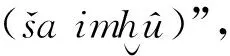
在这种虔敬侍奉神明便可享受幸福安康、不敬神则招致厄运的观念之下,主人公作为一个自认为虔诚的宗教信徒,本应生活顺遂,然而实际却是陷入困境、遭受苦难,不仅身份地位降低、被亲友抛弃,还染上各种恶性疾病。对此,主人公慨叹道:
šadam-qatra-ma-nu-uša-naDINGIRgul-lul-/tum
自认作美妙,对神(或许)是亵渎;
šaina-bi-šúmu-us-su-ktUGU DINGIR-šúdam-qat
私以为鄙陋,于神(可能)正美好。

谁能知悉,天上诸神的旨意?

冥世众神的决议,有谁明了?
e-ka-a-mail-ma-daa-lak-tiDINGIR.MEa-pa-a-ti[10]
众生何从得知神灵的行径?
范德托恩和西茨勒等人正是基于诗篇中主人公的这种感慨而认为作品有着控诉神明不公、质疑敬神能带来福祉的意味。与此类似,以“受难者”和“友人”之间对话的形式写成的《巴比伦神正论》也讲述了不敬神者飞黄腾达、敬神者反而穷途潦倒的情况(如70~71行),这两篇作品也就常被引用来证明两河流域的文学中存在一定的疑神思想。然而这两部作品在叙述内容上实际存有不少差异。《巴比伦神正论》中明确提到了受难的主人公萌生不再敬畏神明和履行宗教义务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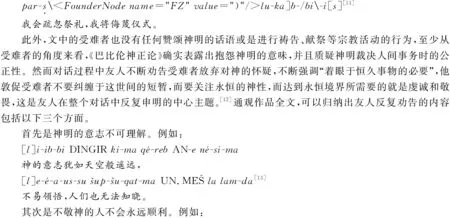
无赖(虽)享有你所渴求的优待,

(但就像粘在)腿上的草,很快便会丢失。
最后是履行宗教义务才能获得神的保佑,对神应当绝对相信。例如:
sa-ba-saqd-miinasu-up-pe-e
祷告中,暴怒的神灵回心转意;
sa-lit-túdiš-tari-ta-riinaba-a-lu
祈求时,和善的女神将会返归。
sa-am-kulašu-te-šu-rui-rem-mua-nai[k-ri-bi]
被埋没的人、误入歧途的人,他们祈祷时,(众神)将仁慈相待。

始终寻求……正义!
受难者每一次抱怨不公或者质疑神明之后,友人都以信神、敬神、服从神明为核心思想来回答,即使认可确实存在不公平的现象,但那也绝不是由于神明不公,而是因为凡人不能揣测出神明的意志,不能理解这些看似不公的情况。到了全文最后的第27节,受难者发出的祈求说明其观念中已经毫无疑神的成分:

愿抛下我的众神助佑(我)!
re-mali-ir-š-adiš-tarši[z-ba-an-ni]
愿遗[弃]我的女神怜悯(我)!
愿牧人,我的太阳,引[导]民众皈依神明!
因此,《巴比伦神正论》可以视为劝诫并最终说服一个信仰动摇的人坚定敬神的对话过程,而受难者最后向神的求助正表明作品主旨仍是虔诚敬神,绝非抱怨和怀疑。更为直接的信息是,该作品是一首藏头诗,摘取每个诗节的第一个符号可凑成:“我是萨吉尔-基纳穆-乌比布,驱魔师,赞颂神与王的人(a-na-kusa-ag-gi-il-ki-[i-na-a]m-ub-bi-ibma-áš-ma-šuka-ri-bušai-liú šar-ri)”。[17]可见作者明确了自己“赞颂神的人”这一定位,作品中的哲理性思考并没有背离传统的主流宗教观念。
与《巴比伦神正论》不同的是,《正直受难者诗篇》根本没有明确提及因为陷入苦难境地而停止敬畏神明或疏忽宗教义务的内容,主人公甚至在I 37宣称“我将称颂他的愤怒”,也就是说,主人公并不认为自己承受的苦难是由于神明的不公而导致的。相反,神的裁决都是公平正义的,即使是神的愤怒也一定基于合理的原因,应该称颂,并绝对恭顺服从。至于II 34~38的慨叹,要表达的意思应该与《巴比伦神正论》中友人劝告的“神的意志犹如天空般遥远,不易领悟,人们也无法知晓”相同,正如雅各布森所说的,是对自身产生怀疑,是对自己判断力和理解力的反思。[18]
必须承认,两河流域涉及人神关系的文学作品中的确常常弥漫着消极情绪,有不少抱怨和质疑,但比起神的不公,人类自身理解力的有限才是抱怨的对象。凡人智力有限、神明的意志不可理解这样的观念反映在各类作品中,一个看似虔诚的人却遭受神的惩罚,受苦受难,应该是由于自己没有意识到犯下的罪过,而非神明的错判,正如一篇向马尔杜克的祈祷文中所说的:
a-me-lu-tuma-lašu-mana-bat
人类,不论其名为何,
an-nara-ma-ni-šman-nui-lam-mad
有谁明知自己的罪过?

谁不曾有过疏忽?谁不曾犯下过错?
a-lak-tiDINGIR [man]-nui-lam-mad[19]
谁能懂得神灵的行径?
实际上,《正直受难者诗篇》的主人公也只认为自己是虔诚的信徒,却并不认定自己就是无罪的,文中数次出现“arnī(我的过错)”“šērtī(我的罪责)”等表达(如Ⅲ 58~61),甚至认为自己在宗教义务上是有疏忽的(如Ⅲ p),在诗篇结尾处也提到希望马尔杜克免除受难之人的罪过:

经受磨[难之人],愿其罪过消除。
类似的,这种即使虔敬也仍然有罪的思想在苏美尔语版的《人与其神》当中也有明确表述,在主人公向神诉说自己遭遇的苦难之后,他请求神明指出其罪过,并且感叹道:
u4na-me dumu nam-tag nu-tuku ama-a-ni nu-tu-ud
从来没有母亲生下无罪的婴孩。
……
我是一名青年,向你坦白罪过。
由此可见,《正直受难者诗篇》与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就思想内涵而言总体上是一致的,都包括“应当敬畏神明”和“人类理解力有限”这两点。这些作品宣扬虔诚履行宗教义务的重要性,强调人类有着自己意识不到的罪过,而神的意志不可捉摸,所以受难时不应质疑神明,而更应向神祷告和献祭,祈求神宽恕自己无意中犯下的过错。
然而该诗篇除上述两点内容以外,还有不同于其他同类作品的第三点主要内容,也就是极力凸显“马尔杜克的至高神地位”。首先是全诗开篇长达四十行的对马尔杜克的赞美,多处体现马尔杜克在众神中享有最高地位,不仅提到马尔杜克直接影响个人守护神的去留(I 15~16),也指明马尔杜克能够洞察众神的所思所想(I 29~32)。而主人公在获得救赎之后前往马尔杜克的神庙埃萨吉(Esagil)礼拜献祭,此后的内容也几乎全是对马尔杜克的赞颂:

若非马尔杜克,谁可起死回生?
e-ladE4.RU6diš-tar-tuma-a-i-tumi-qí-šánap-šat-su
除却萨尔帕妮图,孰能赐予生息?
……
[a-pa]-a-tumma-laba-š-adAMAR.UTUdul-la
一切众生,赞颂马尔杜克!
……
…k]alUN.MEli-bel-ma[22]
……愿他统治万民。
可见,该作品所秉持的神学传统奉马尔杜克为主宰,强调只有马尔杜克及其配偶才决定着生死,掌控着人生命运,而这一点正是该诗篇有别于同类作品的独特之处。究其原因,则很可能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这就需要考察加喜特统治时期巴比伦尼亚地区的宗教信仰状况。
4 加喜特时期王室与民间的信仰冲突

到中巴比伦时期,对马尔杜克的崇奉进一步发展。佐默费尔德指出,据其所掌握的中巴比伦时期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马尔杜克在各个城市的人名中都有很高的出现频率。[24]此外,在恩利尔(Enlil)的主要崇拜地尼普尔(Nippur),马尔杜克原本在古巴比伦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地位。但到中巴比伦时期,尼普尔却建起了马尔杜克的神庙,向马尔杜克礼拜献祭的行为在文献中也时有提及,可见此时马尔杜克在当地的信仰中已经占有了稳固的位置。[25]而更加明显的证据是,在中巴比伦时期的滚印上刻写的祷文里,向马尔杜克祷告的显然占多数。大岛孝义在统计了亨利·利梅(Henri Limet)等人辑录的这一时期的祷文后发现,179篇祷文中有58篇是献给马尔杜克的,占比近三分之一。[26]其次是向沙玛什(amaš)、伊什塔尔(Ištar)、古拉(Gula)和辛(Sn)等神祇的祷告,而献给两河流域传统宗教信仰中的最高神恩利尔的仅有两篇。可以说,中巴比伦时期的马尔杜克在人们的信仰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位置,信徒对马尔杜克的崇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恩利尔。
然而,加喜特王朝的统治者却似乎与这一信仰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从加喜特统治时期的王室铭文以及当时的经济管理文书等官方文献中可以看出,加喜特王室虽是外族统治者,但却接纳了两河流域的传统宗教信仰,尤其是复兴了对恩利尔的崇拜。[27]在加喜特王室的宗教信仰中,马尔杜克并未被奉为至高神,而是排在安努(Anu)、恩利尔和埃亚之后,与辛、沙玛什、阿达德(Adad)等同属于第二等级的神。[28]加喜特王朝的第17任国王库里加尔祖一世(Kurigalzu I)在建造新的都城杜尔-库里加尔祖(Dūr-Kurigalzu)时,为恩利尔修建了神庙“é.u.gal(伟大主上之庙)”,为恩利尔的配偶宁利尔(Ninlil)修建了“é.gašan.an.ta.ál(至高女主之庙)”,也有为恩利尔和宁利尔之子宁乌尔塔(Ninurta)修建的神庙,但却没有为马尔杜克建造神庙。[29]此外,佐默费尔德还发现加喜特时期的王室铭文对马尔杜克鲜有提及,仅有一篇来自波尔西帕(Borsippa)的加喜特第34任国王马尔杜克-阿普拉-伊迪纳一世(Marduk-apla-iddina I)的铭文是献给马尔杜克的,而该铭文的背面却讲到王权是由恩利尔所赋予的:

为马尔杜克——崇高的君主,权威的统领,富足和丰饶的保障者……埃萨吉神庙和埃兹达神庙的主人,他的主……当恩利尔提拔他治理宽广的国土,将正义的权杖交予他统领万民……
这篇王室铭文给马尔杜克冠以“崇高的君主”等称号,可见马尔杜克在加喜特王室的官方信仰中也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但其地位显然排在恩利尔之后。即使这是一篇名义上献给马尔杜克的铭文,且来自一位以马尔杜克命名的国王,文中依然声称是恩利尔赋予了国王统治的权力。显然,加喜特王室把对恩利尔的崇拜置于对马尔杜克的崇拜之上。
《正直受难者诗篇》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作的,由此推断,诗篇中极力推崇对马尔杜克的崇奉,很可能是出于对加喜特王室宗教信仰的不满情绪。实际上,文本中也有一些细节透露出这一创作动机。在作品的评注中有这样一句:
[ša]a-naÉ.SA.Le-gu-uinaU-iali-mur[31]
疏于(供奉)埃萨吉神庙[之人],当以我为鉴。
文中的主人公很可能认为自己遭受苦难的原因在于疏忽了向马尔杜克的神庙供奉献祭,而加喜特王室崇拜恩利尔的宗教信仰倾向正符合了作品隐隐指出的受难缘由。因此,《正直受难者诗篇》可以看作是在马尔杜克的信仰日渐盛行而官方却崇奉恩利尔的背景下创作的,意在推崇马尔杜克,宣扬马尔杜克的至高地位。
5 结论
《正直受难者诗篇》是借用古代近东常见的虔诚信徒遭受苦难的主题而创作的一篇赞美诗,在感叹人类智识有限、神意不可揣摩的同时,强调在苦难中应坚信马尔杜克的救赎,宣扬对马尔杜克绝对的服从和信奉。作品创作于加喜特王朝晚期,马尔杜克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民间信仰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加喜特王室主导的官方信仰却并未凸显马尔杜克的重要性,二者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就是这篇长诗创作的动机,因此该作品才会极力推崇马尔杜克的至高神地位。除此以外,作品反映的敬神观念与同类作品差异不大,并没有表现出质疑神明的意味,而坚信神的救赎和对神的礼赞才是作品的主旨。
注释:
① 文中所引诗歌的汉译皆由本文作者根据阿卡德语或苏美尔语原文译出,下文不再另行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