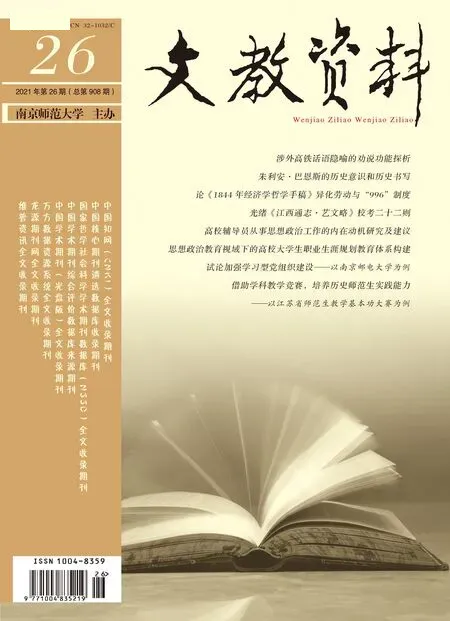朱利安·巴恩斯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
李 贺
(北方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00)
一、巴恩斯的作品及研究现状
朱利安·巴恩斯是战后英国文坛的代表人物,他与同时期的伊恩·麦克尤恩、马丁·艾米斯一起被奉为英国当代文坛的“三剑客”。长期以来他一直笔耕不辍,为英国文坛献上了一系列脍炙人口、引人深思的作品。他的著作《福楼拜的鹦鹉》(1984)、《英格兰,英格兰》(1998)和《亚瑟与乔治》(2005)分别三次提名布克奖;《终结的感觉》最终为他斩获2011年布克奖的桂冠。其他重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她在遇见我之前》《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豪猪》及《时代的噪音》,侦探小说《达菲》《乱弹之都》及短篇小说集《脉搏》《柠檬桌》等。巴恩斯的作品蕴含着丰富广泛的社会生活和经验,以深刻细腻的人性烛照、思想洞见及前卫大胆、高度实验的写作风格为读者所称道。
巴恩斯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直试图通过文体创新不断实现创作突破。他的文本实验和多样性主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他的作品。目前,巴恩斯的多部作品中只有《福楼拜的鹦鹉》《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终结的感觉》和《亚瑟与乔治》几部长篇小说和《脉搏》《柠檬桌》被译成了中文。阮伟教授在《巴恩斯和他的〈福楼拜的鹦鹉〉》一文中最早探讨了小说的内容、主旨及小说所反映的作者的审美意趣,叙述视角的转变,文体的杂糅。罗媛的《追寻真实——解读朱丽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一文探讨了小说中体现的对于传统历史的质疑与再认识。徐颖颖的《从〈福楼拜的鹦鹉〉看人物传记的真实戏仿》关注后现代的特殊写作手法对于历史真实的消解与重构。张和龙教授的《鹦鹉、梅杜萨之筏与画像师的画——朱丽安·巴恩斯的后现代小说艺术》一文着重从元小说的角度探讨巴恩斯的系列历史主题小说。杨金才和王育平的《诘问历史,探寻真实——从〈10 1/2章人的历史〉看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真实性的隐遁》一文同样侧重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历史真实的再现可能。王一平的《〈10 1/2章世界史〉中的反讽艺术》关注反讽手法在小说中的应用。赵胜杰在《边缘叙事策略及其表征的历史——朱丽安·巴恩斯〈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之新解》一文中考察了小说中透现的非理性的历史观念及边缘叙事声音。曾联谊在《从〈终结的感觉〉看朱丽安·巴恩斯的历史观》一文中通过记忆与真实、记忆与历史的联系探讨了历史不可靠性。毛卫强的《小说范式与道德批判:评朱丽安·巴恩斯的〈结局的意义〉》,借用弗兰克·柯默德在《结局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中提出的虚构分析了小说对于传统史观和现代技术道德的颠覆性认识。刘成科在《虚妄与觉醒——巴恩斯小说〈终结的感觉〉中的自我解构》一文中认为,巴恩斯通过小说叙事者托尼对个人记忆、形象及历史的自我结构,揭示其背后虚妄与觉醒的博弈,并且探索个体乃至于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自我发现之路。[1]
国外研究巴恩斯专著相继问世。Merritt Moseley于1997年出版的Understanding Julian Barnes;Breuce Sesto于2001年出版的Language,History,and Metanarrativein 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Cornelia Stott于2005年出版的The Sound of Truth:Constructed and Reconstructed Livesin English NovelsSinceJulian Barnes’sFlaubert’s Parrot及S.Guppy于2009年推出的Julian Barnes:The Art of FictionCLXV;Vanessa Guignery编辑的Conversations With Julian Barnes(2009);Sebastian Groes and Peter Child所编的Julian Barns(2011)。此外,还有Mattew Hattman的Julian Barnes:Writers and Their Work(2002),Vanessa Guignery的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AReader’s Guideto Essential Criticism(2006)和Frederic M.Holmes的Julian Barnes,New British Fiction(2008)。可见,国外对巴恩斯的研究更综合全面,对巴恩斯的小说包括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乃至于散文写作都有相对成熟、角度多样的研究,涵盖从文化身份建构到叙事学乃至道德伦理批评等视角。
目前巴恩斯小说的研究在国内随着创作的继续不断发展。巴恩斯通过系列历史主题小说的写作充分表达了他对英国人民的历史认识和英国社会的未来走向的深切关怀及民众在后现代语境下的生存焦虑和身份困惑。对于巴恩斯小说的研究,对我们了解从撒切尔执政时代到今天的英国社会与文化及文学创作和英国人民的生存状态的有重要的意义。
二、巴恩斯作品的历史意识
综观巴恩斯的小说,他的人文思考延伸到了爱情、婚恋、性别、身份、宗教、历史、哲学等几乎当下英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类别繁杂,包罗万象。然而,在多样化的兴趣中,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强烈的对于历史的热切关注和深入思考。早在《伦敦郊区》中,巴恩斯就体现出对所谓历史宏大叙事的回避和怀疑。在名为“1968年”的标题下,巴恩斯非但没有像读者所期待的那样习惯性地回溯轰轰烈烈、席卷整个法国的学生运动和思想运动,将个人命运置于不可逆转的社会大潮中观察思考,相反,作者似乎满足于用个人小历史、个人的经历和精神史、心灵史代替宣扬高蹈的革命理想的传统史家或作家着力塑造的所谓的家国正史,转而只注重记叙克里斯托弗的恋爱轶事与日常生活。历史不再是小说关注的背景,或者人物命运的塑造因素,转而湮灭成为突出个人经验和成长的注脚,可有可无。在后续的作品中,巴恩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对历史与真实、历史与虚构、历史的线性时间、进步神话乃至于记忆对于历史的支撑等传统历史观进行了质疑、消解和颠覆。
《福楼拜的鹦鹉》以医生杰夫里·布拉韦斯特追踪福楼拜在创作《一颗质朴的心》时从鲁昂博物馆借来的鹦鹉标本的下落为开端,却将大幅笔墨花费在为福楼拜生平做传上面,又交织叙事者与妻子艾伦的故事。在层层叠叠的叙事里,作者将故事、年表、文学评论、随笔、回忆录、词典、问卷等文体恣意杂糅,借用元小说、戏仿、拼贴等手段制造一个个有关福楼拜的伪传记。角度不同、版本迥异的福楼拜的生平故事使历史真相扑朔迷离,不由令人疑窦丛生,充满对于历史认知的强烈的不确定感,正如同繁多的鹦鹉标本,令人眼花缭乱,真假难辨。同时,多重文本并置对历史传记的戏仿,巧妙地凸显了历史书写的文本性和建构性,历史真相的相对性、历史借由文本得以再现的可能性、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多样性等有关历史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历史书写的叙事本质等问题一一浮出水面。
《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借用圣经故事,却颠覆了诺亚方舟“救赎者”的传统形象,并以此为线索煞有介事地打造了一本所谓的世界史。除了每个故事中都有程度不同的方舟变形之外,小说的各个章节的历史故事无论从情节内容、叙事角度、手法还是思想意趣都毫无关联,相互独立。作品中“多种叙事声音和叙事聚焦”混合,各种文体杂糅并置,构成巴恩斯自称的“爱的散文”的多声部叙事。这部纯粹主观臆造,胡乱拼凑,既没有重点,又毫无章法可言的虚拟世界历史缺乏历史书写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及叙事时间和事件的线性联系,更无关传统历史书写的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宏旨。作者或者结合《梅杜萨之筏》这幅名画的创作背景和成因讽刺调侃历史的艺术化过程,或者通过虚构寻找诺亚方舟的阿勒计划恶搞所谓的历史证据,或者考察泰坦尼克号异装癖的幸存者的逃生故事质疑历史发展的正义性,相继探讨有关“真实与虚构、现象与本质、物质与精神、灾难与拯救、爱情与死亡”等多样主题,完全抛弃历史书写的目的性和整体性。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拼贴组合宗教传说、“寓言、动物故事、书信体、散文、旅行日志、法律文书、艺术分析等文本题材”[2],打破历史书写的因果规律和线性叙事,以零散和碎片化的个人历史代替连贯整体的宏大历史叙事,通过历史边缘人物诸如“偷渡者”中的木蠹之口反思所谓的历史真实,消解叙事权威,使传统的历史书写规范和历史真相一样变得面目全非。正如丹尼尔·拜德古德所言:“……似乎对于某些形式的历史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并未导致历史的终结……非但没有死亡,历史的重要性发生了改变;如果文学中的历史表征有任何值得借鉴的意义的话,单一的历史增殖成为了多样的历史。后现代历史编纂元小说与后现代文学技巧的结合促使诸如斯威夫特和巴恩斯这样的作家对于历史事件的文本记录和阐释的偶然性更关注,让他们更注重历史作为文本或者话语的建构性,将历史开放,用多样化的视角看待,承认不同种类的记录都有历史相关性,同时也意识到回溯历史从来都不是如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公正而客观的行为。”[3]
《终结的感觉》“用小叙事的手段解构记忆这个‘个人历史’或是‘小历史’的真实性”[4]。小说中,叙事者托尼童年时有几个玩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年届退休,昔日女友母亲的遗嘱使他回望过往的年轻岁月及他和好友艾德里安之间的纠葛。通过他对年轻时代情爱往事和友谊的回忆性叙事,作者解构由个人回忆构成的自我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并质疑回忆作为建构历史的手段的心理学本质和可靠性。随着历史材料的增加和变化,重新检视历史,作者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自我意识和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凸显了记忆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主观性对于叙事主体“我”的稳定性的颠覆性的破坏。作为对于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本人的追忆和对其批评著作《终结的意义:小说理论研究》的回应,《终结的感觉》如同后者所认为的那样:“道出了记忆与记忆主体及记忆主体的道德责任意识之间的关系,即记忆与其他虚构物一样,它们是能指所构成的幻象,其功能是为了掩盖可怖的不可能性的‘实在界’。”[4]
三、巴恩斯的历史书写
巴恩斯的系列小说创作,包括《伦敦郊区》《福楼拜的鹦鹉》《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及《终结的感觉》,体现了巴恩斯的深入历史意识,即巴恩斯对历史的本质与历史再现的认识,并对其进行多样化的表达,多部作品都体现了对历史不同侧面的探索和相互迥异的技巧运用。瞿世镜曾经这样评价巴恩斯:“当代英国青年作家还是继承了另一种传统,那就是由伍尔夫和乔伊斯等现代派经典作家所开创的实验主义传统。朱利安·巴恩斯无疑是这种传统的代表……他拒绝遵守正统的小说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规则。他编织寓言、讲述笑话、连缀故事、聚集观念,进行各种形式实验。”[6]
巴恩斯的系列作品对已知的各类文体变形、拼贴、仿写,不断进行花样繁多的技巧尝试。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巴恩斯以寻找一只子虚乌有的鹦鹉为契机,将各类文体包括相互冲突、主调各异的福楼拜生平年表,福楼拜对批评家的文学批评,他对社会历史进步的探讨的思考随笔,他所憧憬而未能实现的理想人生的伪传,乃至作者为福楼拜作品所进行的辩护杂糅并置,随意拼贴,试图打破传统文学批评关于小说形式和文类的单一、固定、僵化的界定,以一种更混杂、灵活甚至相互矛盾的方式拓展文学类的边界,为文学读者引入全新的文学期待视域。
除此之外,《福楼拜的鹦鹉》作为一部元小说,显示了强烈的自反性特征。所谓元小说,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作为反传统的文类,元小说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有意识地系统地炫耀自身的人工建构本质来质疑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7]。“对于自身的建构本质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元小说“与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更广泛的文化运动保持一致”[8]。自我指涉或者自反性是历史小说元叙事的重要特征。哈琴认为:“今天我们常说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就有强烈的自我指涉特征和明显的戏仿式的互文性。”[9]自我指涉指的是基于对文本中所应用和体现的文学传统、常规、方法和手段的了解而对其进行自我揭示、自我暴露的行为。叙事者频繁地提醒读者自己的叙事行为,这种强烈的带有自我意识的叙事就反映出这种自反性。元小说中的自反性特征通常体现为:小说暴露“自身与一个人正在写小说相关”;小说“与一个人阅读小说相关”;故事本身“与处理诸如题目,段落成型,情节等特定的故事传统有关”;小说是“非线性的,可以按照某种方式阅读而非必须按照从头到尾的顺序依次阅读”;小说“叙事注解既对故事评论又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小说中“作者是小说的人物”;小说“预见了读者对于小说的反应”;小说中的人物“按照小说的期待做出相应的行为”;小说中的人物“意识到自己身处小说之中”。[9]
在《福楼拜的鹦鹉》中,作者通过不断自我暴露创作痕迹,打破文学评论和小说创作的界限,实现大胆的跨界叙事。无论是小说中三份福楼拜生平年表的并列,叙事者布莱斯维特对路易斯·科莱的评论相关的自我暴露式的自问自答,还是对他自己和妻子关系的不无矛盾的自白式描述中的闯入式叙事,抑或是作者借叙事者之口对评论家关于《包法利夫人》的文学评论做出的不无讽刺的文学批评,都在提醒读者注意作者故意揭示自己介入叙事的行为,以使读者对其叙事保持批评的距离,凸显小说的虚构本质。小说中,巴恩斯借叙事者之口进行了一段非常有名的关于文学批评的批评。爱玛·包法利的眼睛的颜色忽而是蓝色,忽而是黑色,引起了批评家的诟病:“福楼拜并不像巴尔扎克那样用客观的外部描写来塑造人物;事实上,他对于人物的外貌非常粗心大意……”[10]在列举了亨利·戈丁的《蝇王》里近视镜聚光错误和丁尼生写作《轻骑兵进击》诗歌时的将骑兵人数弄错的“外在错误”及文学史中的其他明显的作家谬误之后,巴恩斯质问:“它重要吗?”“如果要问作家自相矛盾是否重要,那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她的眼睛究竟是何种颜色这一点是否重要?当小说家不得不提及女人的眼睛时,我替他们感到可悲:他们几乎别无选择,不管决定用哪种颜色,都不可避免带来一些陈词滥调的含义……”[10]。随后,作者指出,福楼拜对于爱玛的眼睛颜色在小说原文中进行了六次注释,足见福楼拜并非斯塔基博士所批评的那样在写作时粗制滥造;相反,他非常重视艾玛的眼睛的颜色,即写作时细节的精准性:她的眼睛“在阴影中是黑色的,在阳光下却变成了深蓝……”[10]。作者用有力的文本证据不无讽刺地悉数揭露所谓文学批评家的陋见、无知、傲慢及充满妒忌的不良居心。最后,他反问:“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批评家了吧?”[10]在这章中,他直接现身,以创作者的视角和经验,通过第一人称与读者直接对话,批评文学批评。根据马克·库里的观点,元小说这种“将自己置于小说和批评之间的写作”是一种“跨界叙事”[9]。
在小说第二章中,作者罗列了三个以不同的视角写就的福楼拜的生平年表,梳理了福楼拜一生的重要事件。第一份年表关注福楼拜生平的成就,口吻充满了赞誉,将其描绘成为一个文学新星、有志青年和“荣誉等身”“备受爱戴”的著名作家。他才华横溢,“写作对他来说很容易”,即使他的“抱怨”都“流利得让人吃惊”;在年轻时他对女性“很有吸引力”,即使“在生命后半段,由于智识和名望,女性依然对其颇为关注”[11]。第二份年表却以极负面的眼光着重记录了福楼拜生平遭受的重大挫折和打击,包括福楼拜幼年兄弟姐妹的早逝,后来父母,姐姐卡罗琳,他的“接生婆”路易斯·布依莱特及路易斯·科莱的逝世,他对艾丽莎·史莱辛格“无望而充满占有欲的爱”,癫痫发作时似乎要将他的灵魂揪出身体”般“极为痛苦”的折磨,罹患梅毒的惨状,以及对《包法利夫人》创作的艰辛的自述:“写作这本书时我就像一个在指关节上系了铅球的弹钢琴的人”;后来他对“这部杰作给他带来的持续的声名”感到的“懊悔”,他本人被评价为反应极“迟缓”,脸上总带着“近乎痴呆的表情”,他死时“贫困潦倒,孤单而疲惫”[11]。第三份年表是福楼拜以第一人称的自传形式对自己心情、感受和思想进行的自白,包括他对个性、创作及生活的认知和评价:“有的人内心温柔而意志坚强。而我则相反:我一直温柔而内心坚强。我就像一个椰子,将椰奶藏在厚厚的木质层里……”“我只不过是一只沐浴在伟大的美的太阳之下的一只文学变色龙。”“生活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难道不是吗?它就像表面飘满了发丝的一道汤。”[11]这三份年表互相矛盾又互为补充,同一作家的生平因为写作者的视角不同因而材料的选取乃至于作者的结论也大相径庭。这种毫不客观、互相拆台的自我暴露式叙事充分揭露了传记叙事过程的人为操控手法,表明了历史书写的文本性和人工建构本质。小说中,叙事者在传记的表象之下,对于事实真相的追寻就如同福楼拜桌前的两只鹦鹉,逐渐淹没在各种众说纷纭,不明所以的年表、试卷、随笔、字典之中,不知所踪。
上述三个版本的年表实际上也是对传统传记的戏仿。戏仿是对原始文本本身,它的描述对象,作者或者其他一些目标进行嘲弄、评论或者揶揄的一种技巧。它通常是通过幽默、讽刺性或者反讽的模仿原文实现的。哈琴在肯定了戏仿对原文的重复的同时,强调了戏仿与它所模仿的对象之间所保持的批评的距离。戏仿本身对原文本既肯定又否定的双重特性暴露了原文的人工建构和叙述本质,对所谓历史传记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传记写作应该以时间为线索,以事实为基础,客观真实地构建人物形象,前后要有一贯的观点、逻辑和结论。三篇自相矛盾的年表表明,《福楼拜的鹦鹉》背离传统传记的写作手法,也偏离历史写作的纪实常规。[12]它抛弃了以时间主导的人物生平叙事策略,没有统一的叙事文体、风格,也没有一贯的叙事主题。正如莫斯利所说的,这是一部没有主要人物,没有统一的叙事声音、没有紧密关联的叙事进展,没有单线或者双线情节的历史。[13]在小说中作者用不无揶揄的比喻描绘了出于不同目的漏洞百出的传记材料的主观选取、安排和加工过程:“拖网装满了,然后传记作家将它拉起来,分门别类,扔掉一些,储存一些,切成鱼块,然后卖掉。但是你想想那些他没捕获的:这样的东西总是远远多于捞起来的。”[10]所谓历史,不过是作者打捞上来的历史遗迹,破碎凌乱,毫无秩序,亦无逻辑,与事实真相相去甚远,作者所能做的不过是发挥想象去尽力拼凑。历史书写的无奈和漏洞在这个比喻中昭然若揭。
在《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中,木蠹对《圣经》故事的自反性叙述,以个人小叙事的多样性打破宏大叙事对于所谓真相的垄断,粉碎读者对无缝叙事的幻觉,凸显历史叙事的人工操纵痕迹,使读者对传统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产生怀疑。木蠹以自己的视角重述圣经中的洪水故事:“雨下了四十天四十夜?好吧,自然不是……那段时长也不过相当于一个常规的英国夏天。不,按照我的想法,它下了四年半。洪水在陆地表面持续了一百五十天?把它增加到四年……”[14]在它眼中,诺亚并不是《圣经》中描绘的既虔诚又充满智慧的动物的保护者和拯救者:“你们一直以为诺亚是个智者……”[14]相反,他是个专横跋扈又无知可笑的酒鬼:诺亚“是一个恶魔,一个趾高气扬的父权式人物。他每天一半的时间用于跪舔上帝,一半的时间用于拿其他物种撒气”[14]。木蠹对圣经故事的重述和对诺亚的控诉完全颠覆我们对《圣经》故事的认知。它的边缘性叙事和《圣经》文本构成互文,亦是对《圣经》故事的戏仿。这种充满矛盾的历史版本对照凸显历史书写的虚构性、多样性和开放性,消解传统历史文本的权威性、封闭性和单一性。
《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这部既无情节又不连贯、杂乱无序的世界史,从一开始便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创作游戏。正如它的非同寻常的题目“二分之一”所暗示的那样,这并不是一部循规蹈矩、完整有序的历史。理查德·洛克曾经评论说:“小说的题目野心勃勃,令人感到滑稽的宏伟体制溢于言表。一部历史,而非小说被自信地切分成章节,尽管我们也会注意到那精确到的十又二分之一既幽默又搞笑。这个题目暗示了这部书会公然炫耀文类,交流形式的分类及数字,这些都并未精准地符合我们对于十的秩序的追求。这种自我推销式的题目就是自吹自擂,通过让人注意自身文学和认知形式进行自我嘲讽。”[15]在《洛杉矶时报》的书评访谈中,巴恩斯承认:“我对(文学)形式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我很想看看当你将传统叙事规则弯曲,弄折,然后伸展到类似口香糖即将拉断之时的程度会发生什么。”[2]这部貌似目标宏大的世界史却完全没有遵循线性叙事的历史传统,整个叙事破碎分散、颠倒错乱、前后割裂、毫无逻辑。作者时而以20世纪为背景,时而跳回16世纪,时而追溯史前,时而进入19世纪;一会儿谈到对核污染的恐怖,一会儿又讲述轮船巡游,一会儿探讨艺术创作,一会儿又虚构朝圣者的故事。一部堂而皇之的世界史里充满各类边缘叙事者的边缘故事,每个章节的叙述主体身份各异,叙事视角和文体也飘忽不定。从木蠹到异装癖患者,从朝圣女子到森林里的传教士,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任意转换,间杂意识流独白、圣经故事改写、书信和电报、庭审辩词。
在《海滩》中,作者对比海难幸存者的作品《塞内加尔远征记》中的历史事件和画家席里科据此创作的《梅杜萨之筏》的画作,展开独具特色的艺术批评。非但没有认真讨论画作本身所呈现的历史,相反,作者剑走偏锋,通过细节比对着重探讨画作者所遗失的历史真相:“但是为何每个人/即使是尸体?也看起来如此浑身肌肉而强健?……为何他们看起来似乎都刚刚结束了健身课?”[14]作者认为,如果说按照历史真实绘画而如实反映满身伤疤、憔悴不堪、奄奄一息的船员的话,“这种画面对我们的冲击过于直接”,“画作本身应该不仅止于同情和愤怒”。对于受难船员们形象的违反常识的塑造,作者争辩说:“船上的人物就像波涛:他们身体下面和身体里都涌动着海洋……”“这些人物足够强健来传递画布所释放的那种深刻而涌动的情感……”由此可见,画作不再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模仿和重复,而是寄寓了画作创作者的艺术表现意图的工具。接下来的问题基本上回答了历史转化为艺术的创作机制:“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的情感遇到与之相配的事物是多么难能可贵?我们发出的信号有是多么无力?天空有多么黑暗?波涛有多么惊骇?我们都迷失在海上,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动荡摇摆,朝向也许永远不可能来营救我们的东西呼救。灾难已经变成了艺术。”[14]
由此可见,画作的目的不是再现历史事件的真相,而是将历史事件转化为艺术创作的背景,借以渲染创作者的情感、意志或者趣味。这样的艺术化的历史基于历史却不同于历史,虽与历史事件相互呼应,却因经由技法的渲染而更富于艺术魅力,最终服务于特定的艺术创作目的。[14]借由对艺术作品的创作的反思,巴恩斯试图向读者揭示:“历史并非发生过的事情。历史是历史学家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坚持认为历史如同一系列沙龙装饰画,对话片段,其中的人物我们可以凭借想象就使其重新栩栩如生。它始终更像是一个多媒体拼贴,它的颜料是由装饰者的滚筒而非骆驼毛制成的画笔涂上去的。”[14]历史书写与艺术创作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创造的,需要想象力的参与,因此很可能大胆放肆,或者随意拼凑,并非总会对历史的真相亦步亦趋、小心翼翼。总而言之,席里科的作品里“没有画触礁、没有画叛乱、没有画吃人肉、没有画带来希望的白蝴蝶、没有画实际的解救”,画的是人们看见其他帆船时候的欢天喜地。换言之,这部作品不要带:1)政治性;2)象征性;3)戏剧性;4)震惊效果;5)刺激性;6)伤感性;7)记录性;或者8)非歧义性。[16]《梅杜萨之筏》的艺术创作过程暗示了历史书写中作者出于各种因素对历史真相的加工,包括历史材料的选择、夸大、忽略、重组、演绎、变形。换言之,这篇艺术批评还原了历史被篡改的过程,除了对《圣经》故事进行戏仿外,亦有对历史创作过程的戏仿。历史书写的客观、严谨、真实及非目的性的科学迷思被全盘推翻,历史书写作为文本建构的虚构本质水落石出。
《终结的感觉》中,主人公托尼以记忆为线索,站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分别回忆了自己青年时代的过往,并对过往历史及自我进行了重新挖掘、纠正和理解。该小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年届不惑的叙事者托尼着重回忆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他与好友艾德里安的友谊及二人与托尼的大学女友维罗妮卡之间的情爱纠葛。第二部分中,业已退休的托尼,以维罗妮卡的母亲福特夫人的遗赠为契机,对曾经自以为是的历史记忆进行了纠正,并对历史遗留的认知空白进行了补充。托尼一直对自己和维罗妮卡的分手怀恨在心,以为维罗妮卡一家高高在上,自己是被维罗妮卡的傲慢所折磨而最终抛弃的受害者。他对艾德里安和维罗妮卡交往的恶毒祝福信件最终重现,彻底颠覆了他对自己作为一个温良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认知,并由此开启了一系列对往事真相的追寻。
小说的第一部分是“历时性记忆”,“按照事件安排事件”,叙述了回忆的节点以前所发生的事件。第二部分是“共时记忆”[17],叙事者站在当下的时间轴解读、修正和重建过去。整篇小说以记忆驱动叙事,两个部分围绕着托尼的自我身份认定主题展开,既相互抵消激荡又紧密关联。作品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不可靠叙事,审视比对个人记忆与历史真实,体现了巴恩斯对于历史本质的持续追问思考及对作为构建个人历史的重要手段记忆的可靠性怀疑。事实上,作者在开篇就毫不隐瞒地暴露自己作为叙事者的不可靠:在列举他记忆中影响重大的六个片段时,他承认,“我记得,虽然次序不定……”在谈到最后一个片段即有可能是艾德里安的自杀场景时,他说:“这最后一幕我没有真正见过,但是,你最后所记得的,并不总是与你曾经目睹的完全一样。”[18]此外,他还不断在后来的叙述中暗示自己的叙事可能夹杂猜测而推翻其权威性和可信度:“假如我对实际发生的事件不能确信,我至少可以对那些事实所留下的印象有十足的把握。”在随后的叙事中,托尼通过对过往的事实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加工、扭曲、重构,给读者塑造一个受害者形象。正如小说中所说:“历史不仅仅是成功者的谎言”,更是“失败者的自欺欺人。”[18]这种“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19]的历史,在随后的叙事中遭遇了反转。他作为叙事者“先报道一些信息,然后又对之进行否定”;这种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消解叙事”[19],割裂了历史叙事的内在因果逻辑,颠覆了历史叙事的求真传统,打破了历史叙事的确定性,彻底消解了记忆作为叙事手段的可信性和叙事者的叙事权威,使读者对作者叙事背后的动机尤其是价值道德有所怀疑。
随着证据的重现,其极具误导性的碎片化、零散的记忆拼凑的叙事背后所隐藏的事实真相和心理动机,逐渐展露出来。托尼作为爱情的失败者,出于对自己的保护本能,将维罗妮卡恶意描绘成富于心计的坏姑娘。他认为由于维罗妮卡一家社会地位、教养学识都高于自己,因此受到女方家的鄙夷和审视。同时,他一直以为艾德里安的自杀是因为他自身的原因,从来不知道自己写的那封恶毒的祝福信对好友的自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根据詹姆斯费伦的定义,无论是从事实/事件轴、价值/判断轴,还是知识/感知轴上判断,托尼的叙事都不可靠。[19]在整个叙事中,托尼把记忆与想象不断拼接组合,做出了有利于弥补自己内心创伤和自卑心理的再创造,凸显了记忆对历史的改造:“回忆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它与过去所经历的时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个人的‘内心故事’是建立在现实需求之上,并经历持续不断的改写与校订。”[5]小说主人公托尼通过不断追寻历史真实,逐渐弥补记忆的缺失,对其进行矫正;其个人认知获得突破和成长,最终理解自己的道德责任。正如巴恩斯所说:《终结的感觉》“是一部关乎记忆和时间,并探讨时间对记忆产生的影响和记忆又如何作用于时间的小说,同时探讨时隔多年之后,当一个人发现他所一以赖之的种种确定信条如釜底抽薪般轰然倒塌后,在他的身上将会发生的变化”[20]。
巴恩斯在创作中大胆实验各种技巧文类。“巴恩斯大部分的小说……有混杂的倾向,提倡多元化和打破封闭界限。他的书模糊了业已存在的类型、文本、艺术和语言的边界,对其提出挑战。这种颠覆既定文类常规的做法与对于文学传统的张扬和尊奉此起彼伏,相互交织,两种策略都是对文学遗产的有益补充”。
总之,朱利安·巴恩斯作为战后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依然处在创作高峰,他的作品蕴含的丰富主题和采用的多变技巧为学者们研究英国社会战后文化的发展动向乃至于文学创作的发展潮流提供了广泛而可观的研究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