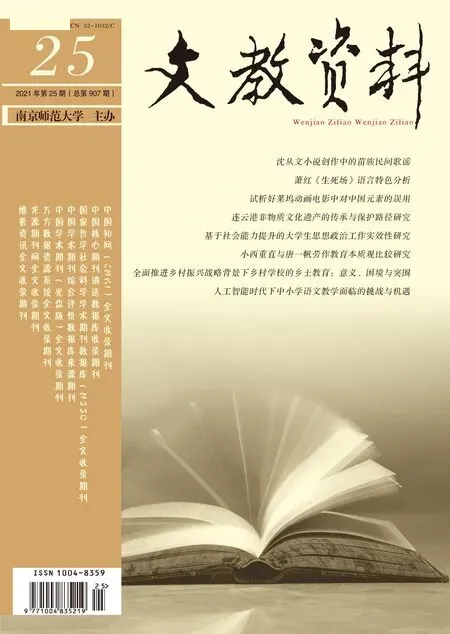小西重直与唐一帆劳作教育本质观比较研究
张思伟 叶哲铭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 311121)
小西重直(1875—1948),日本战前教育家,山形县人。190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学部,后留学德国和英国。1905年,小西重直回国,先后任教于广岛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帝国大学等学校。[1]1927年12月26日,小西重直任成城小学法人理事长,翌年2月9日至1933年担任成城学园总长。[2]1933年3月至6月,小西重直出任京都大学总长。[3]他提倡“敬、爱、信”的教育精神,重视教育实践,强调劳作教育是教育的本质,著有《劳作教育》等作品,对劳作教育在日本的兴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唐一帆(1914—2007),福建仙游人,1933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艺术教育系。[4]毕业后,他先后在仙游县立文贤小学、县立中学等地担任教员。1939年8月至1941年7月,唐一帆在福建省立师范学校担任劳作科教员、工场主任、级任导师和级任教员等职位。[5]1941年8月,唐一帆进入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担任工艺科教师。[6]民国时期,唐一帆积极投身劳作教育,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先后出版了《师范劳作教学新论》《劳作教学研究》两本专著,并发表了《中国劳作教育的本质》等20余篇文章,是民国时期名副其实的劳作教育专家。
小西重直与唐一帆均对劳作教育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见解,相似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的劳作教育本质观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然而,由于教育背景、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他们的劳作教育本质观又各具特色。
一、劳作教育本质观的共识
小西重直与唐一帆所处的社会与时期虽然不同,但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1905年小西重直回国,日本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对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唐一帆出生后,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获得了较好的发展环境,对人才的要求逐步提高。20世纪初,公民教育思想、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等教育思想不仅在日本广为流行,在中国也是风靡一时,二人均受到了强烈的影响。相似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对于劳作教育的本质有着相似的理解,都认为劳作教育是身体与精神相统一的教育,是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的教育,是对道德培养起重要作用的教育,是注重提升创造力的教育。
(一)劳作教育的本质是身体与精神的统一
在古代,劳作教育被看成是对儿童身体进行机械训练的教育。教育近代化开始后,人们发现劳作教育不仅对儿童身体的发展具有影响,而且对儿童精神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小西重直认为劳作教育是灵与肉的交涉,唐一帆主张将劳心与劳力结合在一起,他们都认为劳作教育是身体与精神相统一的教育。
小西重直认为“灵为发生劳作之泉,筋肉则是劳作之流。劳作实为把灵与肉一元的结合之教育原理”。在劳作时,灵与筋肉是不可分割的,“离开了灵的作用,没有劳作。离了精神的劳作之筋肉运动,乃是机械的运动,而不是真正的劳作。依借筋肉的劳作,而内面的修炼,更为确实,但没有内面的修炼,则筋肉的劳作之发展,势不可能”[7]。他提出在乳儿时代,婴儿的运动侧重于肉的方面;当婴儿稍长,进入自由游戏时代,灵与肉在游戏中相互促进,逐渐朴素地成为一元;当儿童继续成长,经过自由游戏时代,灵与肉逐渐产生距离,形成对立姿态,灵支配筋肉进行劳作活动不再像游戏那样简单,“不能圆滑地安易地进行”,儿童只有经历劳作的苦楚,才能发挥其教育意义,实现灵与肉的最终统一。[7]
唐一帆认识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教育主张在我国社会盛行,“劳力”的教育长期被人们所忽视;“刻苦耐劳”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人们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只有劳力的精神,没有劳心的习惯,在劳作的过程中缺乏思考,这样的教育不是真正的劳作教育。因此,唐一帆接受了陶行知“从劳力上劳心”的观点,认为劳作教育包括“劳力”与“劳心”两个方面。他认为一般的劳动人民已经有了“劳力”的训练,不必再在“劳力”上下工夫,只需加强“劳心”的培养;而知识分子虽然接受了教育,但传统的教育并非真正的“劳心”的教育,因此知识分子应接受“劳心”与“劳力”两方面的教育。[8]
(二)劳作教育的本质是实践
劳作教育追求身体与精神的统一,最终都需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因此,小西重直与唐一帆都十分强调实践在劳作教育中的地位。
小西重直指出:“教育在人之生活上,应以精神生活为中心,而将其多样丰富之可能性,尽量地求其发展。然今日的教育,则仅注意于一方面之偏倚地发展。从而儿童青年,均不以学校为他们自身的生活,而时欲求其满足于学校以外。”[7]学校教育只将知识灌输给儿童,忽视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割裂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导致儿童虽有丰富的知识却依旧无法适应社会。小西重直认为:“今后的学校,必须将仅为观念的教材之教授时数,尽量减少,而置重勤劳的劳作或各种构成的劳作以及其他实验实习实演表现等上面,即在各学科的教授方面,亦非依据劳作的教育法不可。”[7]
唐一帆认为劳作教育是一种“手脑并用”的教育,关键在于“做”,要“从做上去发现理论,从做上去印证理论,从做上去获得一切知识、技能、习惯”[8]。唐一帆对劳作实践的强调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对待劳作教师的选择,他强调劳作教师必须具有劳动的身手、敏捷的行动和实际的技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儿童开展劳作活动。[9]其次,他认为劳作是一种技术的学科,教学方法不同于一般学科,因此格外强调“实习”在劳作教学中的作用。再次,对于劳作科成绩的考查,他将考查内容分为“知识、技能、态度和结果”四个方面,知识和态度分别占20%,技能和结果分别占30%,可见相比于理论知识的学习,唐一帆更加注重儿童动手能力的训练。
(三)劳作教育的本质是道德的培养
小西重直与唐一帆认为劳作教育不仅有助于儿童丰富劳作知识、熟悉劳作技能,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儿童的优良品质、提升儿童的道德水平,使儿童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小西重直认为,“凡百劳作,均预想着道德”。在劳作开始前,人们会事先确定目的、制定计划;在劳作过程中,总会有不少困难出现,需要人们尽力克服;劳作结束后,人们通常会进行总结反思,这一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人们的道德品质。“无论个人的道德或社会的道德,在凡百劳作之中,皆得直接间接的修炼。”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存在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仅仅依靠精神的锻炼是不够的,也需要依靠筋肉之力实行各种劳作来培养。他把学校当作一个劳作社会,在这个劳作社会中既可以实行个人的或小群的劳作,也可以实行共同的劳作。在共同的劳作中,个人的意见与全体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儿童可以体验到对立,也可以体验到共鸣。这不仅使儿童的个性得到发展,社会性亦得到发展,“社会连带心、相互扶助心、协同合作、容忍、宽大、友爱、秩序、规律遵循等诸德,均能由此教养之”[7]。
唐一帆也十分重视劳作教育对儿童道德培养的作用,他认为劳作教育是一种道德教育的实践。然而,过去学校中的劳作教育不能使儿童体会到劳动的辛苦与趣味,无法使儿童真正明白“劳动神圣”的含义,也就无法培养出真正的热爱劳动的儿童。因此,唐一帆主张在选择劳作教育教材、实施劳作教育时应避免选择引诱儿童堕落、养成儿童奢华习惯与自私自利的劳作内容,而应该选择大众化、民族化、科学化和时代化的劳作内容,从而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大众化的内容有助于儿童形成人人平等的价值观,消除封建阶级观念;民族化的内容有助于儿童了解民族文化,提升民族自豪感;科学化的内容有助于儿童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时代化的内容有助于儿童明了当前社会的问题与需求,紧跟当前时代的潮流。[9]
(四)劳作教育的本质是创造
劳作教育不是技能的机械训练,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灌输,它是一种培养创造力的教育。小西重直与唐一帆都十分重视儿童在劳作活动过程中创造能力的提升。
小西重直认同小原国芳对“劳作”的阐释,认为“劳是勤劳,作非作业之作而是创作之作,‘劳作’即是勤劳而加以自己之力以从事于创造创作与构成之意味”[7]。可见小西重直将劳作当作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而非呆板机械的活动。他认同自然的教育方法,认为劳作是自然的语言,儿童通过劳作来表现自己,并在劳作的过程中反省自己,明了自身的不足,进而对自身的认识更为完善,这不是机械重复的过程,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儿童在其自己教育中,依从自然的教育法,自行实验而充实的、劳作的、创造的从事发展”。他批判了当时的学校教育,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是一种仅仅依靠“眼耳口”的教育,是一种注入式的教育,忽视儿童个性的发展,使儿童受到了严重的压迫。[7]
唐一帆认为人们的生活是在不断改造的,劳作教育作为一种生活的教育,自然也应特别注意改良与创造。[8]为此,他格外注重废物利用的教学,将无用的事物进行加工组合,变为在实际生活中供儿童玩耍、使用的事物,这种教学活动极易引起儿童的兴趣,他认为废物利用的教学是最容易培养儿童创造的兴趣与能力的方式。[9]然而,改良与创造的实现也并非易事。改良与创造需要立足实际,一方面应符合当下的实际,绝不能超脱现实进行改良与创造;另一方面应符合中国传统的实际,绝不能一味效仿国外。此外,改良与创造也绝非易事,其前提是模仿,越精细的模仿意味着对事物的了解越透彻,基础知识才能越扎实,最终才能实现改良与创造。改良与创造也是有前后的,创造虽好但并非人人都能进行创造,在大部分情况下能做到改良已是不易。[8]
二、劳作教育本质观的差异
小西重直与唐一帆身处的时代与社会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差异性也十分明显的。小西重直信奉“敬、爱、信”的教育理念,他的劳作教育本质观充满了宗教的色彩;他更倾向劳作教育对精神方面产生的作用,强调劳作教育对“美”的重要作用。而唐一帆的劳作教育本质观立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强调劳作教育对“生产”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色彩。
(一)宗教的劳作与唯物的劳作
小西重直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他的劳作教育本质观建立在“动物是肉的,神是灵的,人不仅是肉,亦不仅是灵,他须依借肉与灵的交涉,始能尽其人之所以为人的使命”的人的本质观之上,他把人类的劳作看作“与神之圣的劳作交流而发生于灵肉交涉世界之劳作”。[7]在他看来,宗教生活是一切文化的泉源,宗教的虔敬是教育的出发点,是教育的过程,也是教育的目标。一方面,“宗教上之行”是宗教方面的劳作活动,有助于扫除人们心灵上的污物,实现心灵的净化,有助于达到宗教中所说的虔敬生活,学习这类劳作是实施劳作教育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世间所有事物都蕴含着神的精神与人的努力,只有真正明了这其中的内涵才能生出虔敬的态度,“接受材料的儿童,若能知道此事,那么,将先对人与神佛,而自然低下其小头,其天真无邪的瞳中,亦将表现出真面目的态度”[7]。
唐一帆的劳作教育本质观则与小西重直不同,他在人们实际生活与生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劳作教育本质的看法,并深入分析了劳作教育实施的心理基础与生理基础,蕴含着唯物主义的观念。首先,唐一帆看到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国情上的区别,中国社会正在遭受列强的入侵、社会动荡不安、生产落后、人民生活痛苦,在这种认识下,他提出要实施劳作教育,劳作教育是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和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其次,唐一帆为了更好地进行劳作教育教学,对儿童的心理与生理进行了观察,发现儿童的年龄、性别、智力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对儿童进行劳作活动产生不同的影响。[9]
(二)美的劳作与生产的劳作
小西重直不仅认为劳作的过程中处处充满了美,而且劳作的美也能进一步推动劳作的发展。首先,小西重直认为人们在劳作的过程中处处存在美,人在创作过程中身体呈现出的统一调和的姿态是一种美的劳作,创作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鉴赏也和美的劳作不可分割。而从教育方面来讲,其范围就远远超乎艺术的创作,“在借身体的运动而行之一般广义之构成的活动上,亦能使其达于某种程度之美的构成,故美的劳作,在一般的构成作用上,是能多分的实现的”。其次,劳作多辛苦费力,受人轻视,“要是能对其美化,那么,嫌恶之情自念不起,而能能动的进而从事工作了。凡在能动的自发的从事时,工作与自己已是一致而调和了,故其心境,总是美的。而因心境是美的,故工作又易成为自发的”[7]。
唐一帆也看到了美在劳作教育中的作用,要求实施劳作教育的教师拥有美术的知能,然而相较于小西重直,唐一帆显得更为务实,更强调劳作教育在生产方面的重要性。他认为“劳作教育的作用,一方面是在于改良人类的生活,一方面是在增进社会的生产,故劳作教育的主张‘以劳作为生活的基础,以生产为生活的表现’”,“我们站在教育的立场上,应该设法改良其生产的技术,使其具有‘工业化’的倾向,换言之,即‘使一般纯旧式手工生产转变为进步的手工制造,最后再转变为器械的生产’”。[8]人们在长年累月接受劳作教育后,将获取丰富的劳作知识、实用的劳作技能、正确的劳作价值观,对未来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将产生巨大影响,这不仅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将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生产素质,引导产业的前进与升级。
小西重直与唐一帆对劳作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都认同劳作教育是一种手脑并用的教育,在劳作教育实施的过程中应重视实践的作用、重视道德的培养、重视创造能力的提升。同时,他们对于劳作教育的本质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劳作教育与美的关系、劳作教育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这两种观点也是今天我们教师在实施劳动教学时容易忽视的。此外,小西重直关于劳作与宗教关系的论述,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封建因素,不如唐一帆的劳作教育本质观符合当前的思想潮流,但小西重直思想中蕴含的对大自然的敬畏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对二者的劳作教育本质观展开研究与比较,有助于加深今天我们对劳动教育的认识,加强对劳动教育本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