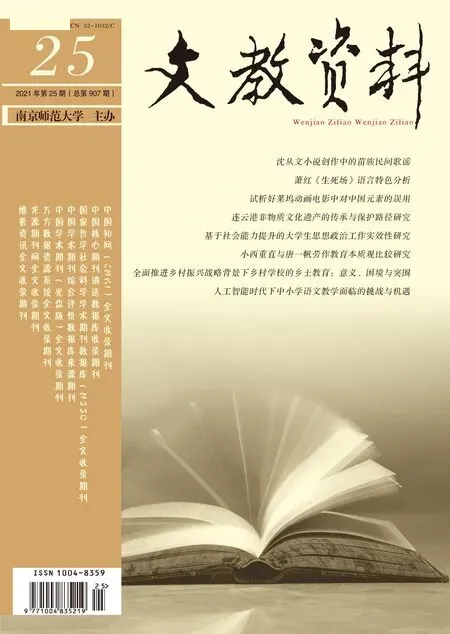《中华教育界》与近代语文教科书的变革
余少琛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20世纪初,由于交通和信息的闭塞,杂志期刊逐渐成为大众传媒的主流方式之一。以研究教育和促进教育发展为宗旨的教育期刊,“作为教育传播的重要信息发布平台,积极引导教育改革的深入,促进着教育的发展”[1]。1912年,中华书局横空出世,作为教科书出版界的巨擘,它以极高的敏锐度参与并引导了语文①教科书的变革,这一点在其出版的教育期刊《中华教育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就期刊内容上看,发布了大量有关教科书的文章和相关专号进行讨论,是促进教科书发展的重要交流平台。就发表文章的作者上看,从著名教育家到一线教员,他们的批评与建议是教科书革新发展的主要推力。而《中华教育界》与教科书的密切关系,也为该期刊在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
一、启发教材编写,助力教材宣传
(一)明确学科性质与问题,奠定教材编写的前提
一直以来,国家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方针始终是教科书编写的总指挥棒,但对学科特性和实际教学问题的把握也是各科教科书编写不可忽略的重要前提。《中华教育界》于第19卷第4期上刊登了宋文瀚《一个改良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意见》一文,他指出国文教科书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是因为编者对国文科的性质和国文教学的目的没有正确认识。他强调国文科的性质“不是叫学生明了及记忆其内容”,而是重在“传授知识的、文字的、运用的训练”。在国文教学上,他反对穆济波将国文教学的目的等同于整个教育目的的观念,并表示国文科的目标并非教育的总目标,而国文教学只有两个目的,即阅读和发表的目的。[2]其观点明确了语文学科的特殊性,为编辑等人员编写语文教科书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
金兆梓从实际运用的角度对国语科性质和教学目的进行了阐述。国语科是营“人的生活”的基本工具。国语的教学,在采用口语文之后,“更应由文字的训练尽量究其复杂变化的运用,去促进语言的进展,补助语言的不足,而作一切保存经验发展新知,陶冶身心,增进生活能力的基本工具的基本”[3]。金兆梓秉着教科书“工具”性的观点,为教材的编纂提出了建议。
(二)热议教材编写,推动教材革新
近代中国时局动荡,课程嬗变,各种教育思潮争相涌入,语文教科书如何编写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就成了编者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中华教育界》积极组织并发表了相关文章,收集了从教育家到一线教学工作者对语文教材提出的问题与建议,推动了教科书的变革。就其内容上看,主要呈现出两种趋势。
1.倡导语体文的编纂
在改用白话文教科书的法令发布之前,中华书局于1915年12月曾出版过一套编有四篇白话文课文的语文教科书——《新式国文教科书》,《中华教育界》对此进行了宣传。如果说此次对白话文的宣传只是期刊为教科书所做的营销手段,那么1916年陈懋治《国民学校改设国语科意见书》一文的刊登便是对采用白话文编纂语文教科书的认可与支持。《中华教育界》于第10卷第8期和第11卷第2期为国语研究特别设置了专栏,并接二连三地发表了许多相关文章,为语体文编纂语文教科书提供了重要思路。
冷香在1917年就提出了改用白话文的观点,他考虑到从文言文骤改口语文,恐教师教授时多有不便,就此对教材编纂提出了几点“渐进之法”。他表示国文教科书可以用口语文作副本,也可按照各地方情形各自选择采用,并行不悖。[4]为正式改用语体教科书提供了几点编写意见。陆费逵从白话文的功用入手,认为口语文易学易懂,可以“先从口语入手,渐渐地学文言”。并对当时口语文没有一定规则的问题也进行了探讨,提出可以先制定标准语和标准音的建议。[5]
还有学者从实际教学情况出发,指出学生国文成绩不佳的原因并非因为教授法的不当,而“实在是国文本身的问题”。艰涩难懂的文言文并不符合学生实际掌握程度,“嘴里说的和纸上写的,绝不一样。什么字该当写出来,什么字不许写出来,必得一个一个的硬记”[6]。因此,语体教科书的选用势在必行。
在国家政令和众多学者的提倡与宣传下,白话文在教育领域逐渐站稳脚跟,“五四运动以来,汉语文学科废除读经、倡导国语、加大白话比重、丰富学科内容的基本格局已经定型”[7],白话文在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中已然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2.提倡以学生为主的编写理念
自小学国文科率先改为国语科后,白话文凭借其浅显易懂,与儿童生活相贴合的优势成为小学语文教科书的主要语言形式。但“在如何引起和保持儿童的学习动机和兴趣方面,刚开始的白话文教材还不够重视”[8]。五四运动后,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与国内自动主义学习观的影响下,儿童中心主义在教育界掀起热潮。语文教科书如何顺应儿童发展成为讨论的焦点,也成为《中华教育界》助推语文教科书编写的一个着力点,特别组织了“儿童用书研究号”“小学爱国教材号”“教科书专号”等专栏进行讨论,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教材编写应该注重学生的兴趣和程度。兴趣是学习的前提,语文教材如何唤起学生的趣味,是编者必须考虑的因素。余家菊认为,丰富的教材内容是激发学生兴味的关键。他表示“今日教育之无成绩,教育者固不能辞其责,而教科书取材不合则是以致命之因”“圈套太多,意义太少”,致使教材没有内容,而“材料的内容愈丰富,学生就愈感兴味而愈为兴奋”[9]。一线教员韦息予也表明现行小学教科书的最大缺点就是枯燥,枯燥的原因就包括教材的内容不充实,国语教科书“只有精读材料,不足以供训练增进读书速率之用”[10]。
编纂学生感兴趣的语文教科书,还要贴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谬文功批评当时的语文教科书“深浅高下不分,黼黻青黄杂施”,并指出以文字长短、文体等来配合年级进行编制的方式并不合适,编者应该统筹始终,“自初等小学以至中学之将终,何者宜先,何者宜后,何者宜缓,何者宜急”并合以教育学理、心理发达程序等由浅入深地对语文知识进行合理的安排。[11]宋文瀚也提到了国文教科书与学生程度不符,如初高中教材重复,有时竟出现高中反不如初中艰深的现象,还指明批评了中华书局的《初级国语读本》,“本书的编次和分配,全凭编者个人的经验酌定”[2]。这些问题都是由编者在学生学习程度上考虑不周所造成。如何统筹教材内容?阮真认为首先要考虑所编教材年龄学段的学生程度,同时还要兼顾之前学段的学生情况,如“编高中国文教科书,也要从初中教科书和初中毕业生的程度上去研究”[12]。沈颐结合学生的言语经验和阅读经验对声音、词类、语法三种语言知识的编排进行了说明。如词类在排列时“应该把词性的虚实做一个大体的标准”,表示实物以及动作状况的词排在前,代词、副词、介词等排在后。相比于抽象的代词、介词来说,表示实物的词更易于学生的理解。形式和篇章上不能受形式的限制,当长就长,当短就短。[13]一线教员王书麟则依据自己的教学经验,从学生的遗忘规律出发,针对生字在教科书中的复见次数提出了建议,“每字其第一次与第二次之距离宜近,盖以忘记之速度,于刚学习后进行最快。故宜于最短时间内,使其有机复见;其后忘记之速度渐减,而该字复见之次数可以渐少,每次之距离,亦可以渐远”[14]。为教材中语文知识的编排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其次,教材编写要贴合实际需要,助力学生融入社会。教科书的功用不仅在于传递人类的知识经验,还需立足学生未来,助力学生融入社会。黄玉笙曾提到,教材的价值,不在儿童记忆它的内容;是在它能够帮助儿童扩展经验,组织经验,改造经验。使儿童能由它而变化其实际行为,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动静。[15]但在实际教学中,却存在“蹈空驾虚”,有空论而无实质的现象。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依靠教学方法的改善是不够的,编者在语文教科书的编纂上也必得下些功夫。其中,有学者将目光放在了应用之文的选用上。黄炎培从“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的角度出发对小学国文提出建议,“读本材料全取应用的作文,多令作记事、记物、记言等体,由多作书函或拟电报”[16]。顾树森在谈及普通教育对职业的陶冶时表示,国文材料“虽不能尽以职业为主体,然其中以宜兼授以关于产业经济之资料,及日常应用必需之文件。俾将来得以应用于社会,无扞格之虞者”[17]。另一方面,“共同生活之习惯”也是融入社会必备之因素,如职业道德、民族精神等社会观念在语文教材中也不可忽略。如养成学生“勤劳作业之习及爱好职业之感情,此等职业上之陶冶,无一不可施于普通教育范围之中”,其中修身、国文、算术等科应该特别注重对职业之道德的增进。[18]关于语文教材中民族精神的培养,《中华教育界》于第16卷第1期发布了“小学爱国教材号”的专栏,对于国语科的爱国教材进行了讨论,如语文教材中应该选择能够发扬国光、表彰国化的,足以说明国势、提醒国耻的内容,反映了社会环境诉诸语文教材的培养学生民族精神的要求。
(三)积极推广,促进营销
有学者研究过,《中华教育界》上“刊登过的教科书广告合订起来,就几乎等同于中华书局历年教科书出版的总名单”[19]。在众多的教科书广告中有专门针对语文教科书的内容。如第2卷第10期和第9卷第3期上分别刊登了《新制中学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和《新教材国语读本》的广告,从编纂旨趣、编纂特色等方面对教材进行宣传。而对教科书的宣传不仅仅是打广告,还组织学校教员填写调查表,以此来获得教科书的实际使用信息,以便有的放矢地进行教科书的推销。
二、丰富期刊内容,促进期刊发展
(一)教科书是教育期刊诞生的重要前提
中华书局以教科书出版为主,在这种经营模式下的《中华教育界》必然与教科书有着密切关系。民国时期,教育政策嬗变,各种教育理念此起彼伏,不断对教科书提出新的要求,教育期刊是不可或缺的沟通桥梁。而教科书的发行同样也需要期刊进行宣传。因此,教科书编纂与发行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华教育界》的创办动机之一。
(二)教育期刊以教科书为内容支撑
《中华教育界》共发行了29卷305期,刊行时间近30年,是中国近代为数不多的刊行时间较长的教育期刊之一。这与它服务教育的价值定位和中华书局的全力支持脱不开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参与和引导教材革新的同时,也丰富了期刊的内容。
从所创设的栏目看,早期《中华教育界》“附录”一栏中,包含了大量有关教科书的信息。有教育部和地方教育会对中华书局教科书的审批意见,如1913年第2期至第5期连续刊登了教育部对中华书局教科书的审定批语。有对教科书的编纂说明,如第5卷第1期上刊登的《新式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编纂说明书》一文,对教科书的宗旨、全书编法、文字文章的选择和编排标准等都进行了详细说明。还收录了各周报对教科书的介绍与批评,如《神州日报》新刊对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介绍,“每册依时代顺序甄录,由近及远,由浅入深”,教材内容“足以涵养学者之性情,启发学者之心志”[20]。不仅如此,期刊还设置了“调查”一栏,虽然中途几经变更,但整体内容逐渐从最初介绍国外的教育状况转向对国内学校教育实际情况的调查,为促进教科书革新和发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另外,针对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与争议等,《中华教育界》还组织刊发了专门的研究专号,如“国语研究号”“儿童用书研究号”“小学爱国教材号”“教科书专号”等,内容涵盖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多个方面,对新环境下语文教科书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经验与教训提供了借鉴和解决的方案,极大地丰富了期刊的内容。
在近代教科书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教育期刊也在不断进行调整与创新,增进教育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在一众教育工作者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同时,又凭借着自身不断增强的关注度和专业度进一步影响了教科书的编写与发行,语文教科书的转型与发展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得以实现。
注 释:
① 我国近代称为“国文”“国语”,为与现代语文学科的名称呼应,故称为“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