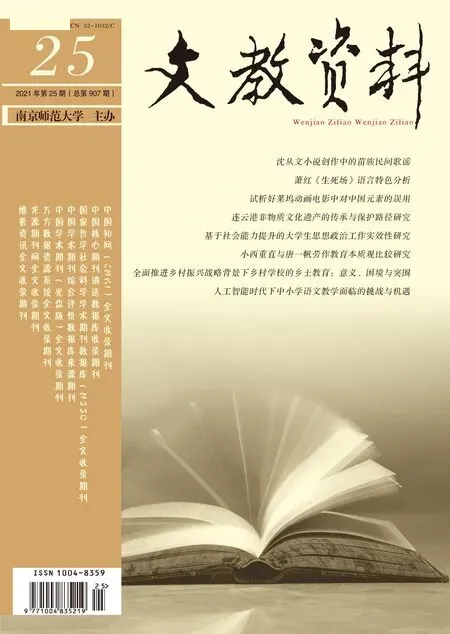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苗族民间歌谣
弓皓然 赵洪奕 雷 霖
(怀化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常常会利用苗族民间歌谣作为叙事的辅助,赋予作品张力,歌谣作为作者建构湘西世界的文化符号之一,具有结构与内容上的双重意义。以往学术界对沈从文作品中歌谣的研究,往往着重于对文本的探讨,如歌谣对小说人物性格的彰显,对情节的影响,歌谣本身的修辞艺术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挖掘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但存在某些不足:一是忽视沈从文小说中的苗族民间歌谣与湘西传统民间歌谣之间的精神关联;二是偏重于苗族民间文化的研究角度,忽视沈从文游移于苗族民间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动态立场,无法深入挖掘其小说中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德国艺术家格罗塞(Ernst Grosse)在《艺术的起源》中曾说:“在歌谣与舞蹈等活动里获得的是一种统一社会感应力的文化功能,社会的一致性得以完成,民族群体的聚合与认同得以实现。”[1]民间歌谣本身带有跨文本性与跨时空性,静态或者孤立地在作品内部研究歌谣的价值意义是不够的。本文旨在将苗族传统民间歌谣与沈从文的具体作品相结合,通过分析作品中所引用民歌的特征,探讨沈从文小说中歌谣人的主题的生成,进一步论证苗族民间歌谣的运用对小说的悲剧性起到的作用。
一、沈从文小说创作中民歌的性爱倾向
情歌作为苗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歌谣数量最多,据初步统计,沈从文小说作品中的民间歌谣共有89首,其中情歌64首,占了七成有余。[2]
作品中所引用的情歌,对于男女两性的情欲表达比较直露,如在《阿黑小史》中阿黑唱的:“娇妹生得白又白,情哥生得黑又黑;黑墨写在白纸上,你看合色不合色?”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里,壮年水手成天在船上唱着:“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在《雨后》中,男主人公四狗直接对阿姐做出“揉胸”这一动作,并唱起:“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翘翘底。心想用手摩一摩,心子只是跳跳底。”在《萧萧》中,花狗教小丈夫唱给萧萧的情歌:“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媚金虽然身为小姑娘,却毫不避讳对豹子的爱意:“红叶过冈是任那九秋八月的风,把我成为妇人的只有你。”男子汉豹子真心地回应:“纵天空中到时落的雨是刀,我也将不避一切来到你身边与你亲嘴。”诸如此类的情歌还有很多,《山鬼》《巫神之爱》《凤子》等小说作品里都有直接体现。
上述情歌中的男女双方不避讳对爱情的渴求,并几乎都会通过“身体”这一媒介进行爱的传递。这在传统湘西苗族情歌中可以窥探到本源。在石启贵整理的《情歌杂唱》中,随处都能找到类似的句子:“手摸乖姣眼看色,似玉如花舍不得。若是是个红桃子,一口吞吃免欠缺。”“面团体正又贤德,越看颜容心越热。若是得伙同屋坐,早死夜埋也值得。”[3]同样是通过大胆直露地描写肉体触碰,表达对情人的爱意;在龙秀海编著的《松桃苗族情歌选》中,无论是“赠物相约篇”里:“和心爱的人儿常来常往,迷恋到齿落发白不分开。”还是“野外幽会”中:“想你我的嘴唇少了血色,嘴皮薄得就像随风摆动的箬叶。”[4]都通过身体大胆抒发男女之间深厚的爱情。
哲学家尼采说过:“如果我们站到这个阴森叵测的进程的终点……我们就会发现在社群之树上最成熟的果实是主权个体,他重又逸出礼俗道教之外,是自律且超伦理的,简言之,就是有自己独立而长久的意志的人,可以许诺的人,——其中有一种自豪的,在所有肌肉中颤动的意识,对那个于此最终赢得的、在自己内部化为肉身的那个东西的意识,一种真正的权力意识和自由意识,一种根本上的人类完满感。”[5]
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喜欢引用带有肉体或者器官意象的民歌,甚至是迷恋,主要原因是其中包含个体的存在,意象、场景、心理最终都指向青年男女的性与爱,它建构起沈从文以“原欲”为核心的生命动力学,这种动力学生产的是“自然人”,即自在自由的个体。这种个体与尼采上面所说的“主权个体”相类似,因为二者都“逸出礼俗道教之外”,而且是一种“自律且超伦理”的存在。在沈从文笔下,角色的“自律”与“超伦理”是不矛盾的,因为他们遵循的不是社会规则,而是情爱原则。“自由的个体”(主权个体)存在的标志首先是对自己身体比较自由地处置,这些都构成他作品中特有的身体叙事现象。
这种身体叙事最鲜明地体现在《雨后》中,四狗与阿姐的爱情过程,沈从文主要通过“肉体”与“野趣”两个关键词展现,小说情节的推进呈现为一种典型的性爱言说。身体、性与爱等诸如此类在苗族传统民歌中被广泛歌唱的因素,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得到传承。这种对于爱意最单纯直接的表露,反映出“性本能”在苗民身上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被弗洛伊德概括为“力比多”(即“性力”),心理学家荣格告诉我们:“力比多在生命过程当中表现自身,并被主观地认知为斗争与欲望。”[6]
荣格的话可帮助我们归纳出沈从文笔下苗族情歌“性欲→爱→自然”的逻辑线,这正好照应沈从文所追求的自然之美:“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7]这种自然之美存在的最高境界就是沈从文小说中的“疯癫”现象。
“癫子”在沈从文的很多小说中都有出现,如《阿黑小史》中的五明、《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的号兵、《医生》中的医生,《山鬼》中的癫子,这些人物形象为追求爱情而变得“疯癫”,变得好动欢乐、大胆直露,它带来的不是病症,而是人生本质。爱欲破开社会道德的束缚,归于自然本真。由此可观,沈从文不仅对苗族传统情歌进行收集与利用,他还将自己自然人性之美的观点与之进行有机结合,塑造出其作品中独有的人性观,即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7]。
二、沈从文小说创作中民歌的自贬倾向
民歌的“自贬倾向”在沈从文的创作中第一个表现是:主人公常常会通过歌谣(以情歌和生活歌为主)贬低自己。
在《丈夫》中男主人公与水保会面后,感到自己与尊贵的人物谈过话,进而想到妻子老七得了许多钱,便唱道:“水涨了,鲤鱼上梁,大的有大草鞋那么大,小的有小草鞋那么小。”男人想到“大鱼”“小鱼”两个对比意象,并在潜意识里将自己的身份归于“小鱼”这类,体现男主人公贬低身份意识的自觉性;同样是在《丈夫》中,当水保离开,男主人公想起他脚上“闪闪发光”的靴子,手上“黄而发沉”的戒指,便唱起:“山坳里团总烧炭,山脚里地保爬灰;爬灰红薯才肥,烧炭脸庞发黑。”这里的山坳和山脚分别对应二人居住地:黄庄和码头。在丈夫眼里,自己作为农民在黄庄只能靠烧炭维持生计,水保作为地方统治者却可以靠“爬灰”这种不正当手段得到财富。虽然体现丈夫对水保某种意义上的戏谑,但丈夫对于财富与地位的仰慕在歌谣中仍然不经意地表露出来。
在《月下小景》中,小寨主见到姑娘后,为表达爱意,唱起情歌:“我不愿做帝称王,却愿为你做奴当差。”男主消解“寨主”这一象征权力地位的身份,更愿为心上人做奴隶,体现一种身份的错位倒置。在《边城》中,翠翠见到戴着“麻花绞的银手镯”的小女孩后,轻声唱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在这里翠翠以首饰为媒介,用豆芽菜与小女孩的贵重手镯做对比,同样体现对自己身份贬低的自觉。
类似的情况在苗族传统民歌中也存在不少,如石启贵所编著《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中的“男女合唱”部分,男青年沦陷在姑娘的美貌中无法自拔,可女主却唱自己:“蟠桃大会在天涯,姣是凡人若比它。姣如瘦地青辣子,瘟猪浪狗都嫌它。”通过鲜明的反差式夸张表达姑娘的有意自贬;在《唱佛歌》中,歌者先为人民祈福,又说自己“为愚不才初学手,言语粗糙莫记仇”,表达对于自身专业知识的谦卑与低调;在椎猪歌《你的大名四海扬》中,男主唱到自己的歌技时说:“今听你唱口难开,甘拜下风投降你。”[3]这也是抬高他人贬低自己,为另一种贬低自身身份的方式。
除了身份自贬的意识自觉外,苗族民间歌谣还有一种对未来境况的自贬倾向,即对未来美好生活表示怀疑或否定。如龙秀海整理的苗族民歌《邂逅相逢》中,男女二人在相互迷恋的高潮时,女方却疑心唱起了:“你对雪白淡香的花簇,激不起丝毫的兴趣,你只是用甜言蜜语,故意把我的心儿灌醉。”使男方一再做出解释;在《渴望牵手》中,女方迫切希望与男子结交婚恋,但又否定结交带来的幸福:“结交担心山水阻隔,爱恋又怕路程遥远。野外相会让你受累,你我最后不要交连。”[4]到歌谣最后甚至否定二人相爱的合理性。
沈从文作品中引用的民歌也有如此特征。如在《凤子》中,男女主人公情投意合,可男人却唱道:“我不问乌巢河有多少长,我不问萤火虫能放多少光。要去你莫骑流星去,你有热你永远是太阳。你莫问我将向那儿飞,天上的宕鹰雅雀都各有巢归。是太阳到时候也应回山后,你只问月亮明夜里你来不来?”以怀疑忠贞的口吻向女主表达另一种相互离散的可能性;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媚金在与豹子定下婚约后向他唱到:“莫让人笑凤凰族美男子无信,你要我做的事自己也莫忘记。”显示出对男子品行的一种假设性否定,为后文媚金的误会埋下伏笔。这两类在苗族民歌中经常出现的自贬倾向是苗族悲剧性文化心理的体现。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丈夫》《凤子》等文本都因为主人公的犹豫徘徊带来一种“人为的悲情结局”。这种悲情结局与民歌中的自贬倾向交相辉映,打造属于苗族本身的身份隐喻。苗族的俗语:“好花长在深山林,美人生在有鬼家”“强是人家的骏马,富是人家的伙伴”[8]等都体现苗族人对美貌、财富的自觉疏离。这种疏离最后导致的是一种文化上对幸福生活与生俱来的远离,“远离”这个词不仅体现在幸福感上,更体现在地域选择上。
自古以来苗族都是一个在不断迁徙的民族,没有稳固的居住地与物质保障,所以一再远离熟悉的事物,对先进的文化思想产生一种“滞后性”,形成僵硬的发展定式。这不可避免地加固苗民对生活的悲剧性体验,即沈从文所说:“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7]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沈从文对这类情歌的引用不仅是对苗族人的书写,还是有关苗族文化身份的寓言,折射出一定情景下自然人面对种种“不凑巧”所产生的精神困境。
三、沈从文小说创作中民歌的泛神倾向
从苗族的发展史中不难看出,湘西苗族民歌中无处不体现神性。“老天有意把我们下放人间,天公将我俩的头发梳成一绺,雷公愿意让我们成为一对”的神赋式;“假若落空就是命中注定,只怪老天瞎了一只眼睛。忧愤不惜年轻的性命,恨不得挖了天公的祖坟”的控诉式;诸如“等待天公为我报信”“不辜负天公的一片好意”[9]的祈求式。可见,从传统湘西苗族民歌看来,神的旨意与命运的安排一切的因果,即神支配人民的生活,支配人民的命运。
正因为民歌中包含一种对于神的崇拜,沈从文得以借民歌的方式,将神在生命中的地位明显地表露出来。《龙朱》有这样的表达:“这个人,美丽强壮象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令无数人向往神性的美并没有使龙朱获得想要的爱情,反而将他陷入无尽的孤独中。要想摆脱这样的困境,必须向心爱及逆行情感的倾诉——民歌对唱。沈从文虽然没有具体写出龙朱所唱的情歌内容,但从极具赞美性的评价中不难看出,龙朱在情歌中倾注自己四年最真挚最原始的感受——情爱。“龙朱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需求的补足及回归原始人性的过程。”要想较完美地通过这一过程,无可避免地要进行神性的表达。
这一点与《神巫之爱》的情感表达相类似,两者所不同的是,《神巫之爱》显然更深入生活,不同女子对神巫的态度及愿望不一。文中从五羊、哑巴女子及神巫等多种视角展现神巫爱情。最后成就神巫与哑子寡妇爱情的,正是泛神倾向的民歌:“天堂门在一个蠢人面前开时,徘徊在门外这蠢人心实不甘。若歌声是启辟这爱情的钥匙,他愿意立定在星光下唱歌一年。”天堂门本是西方基督教中高尚的人得以进入的地方,沈从文在这里加以运用,将传统意义上的苗族情歌披上一层西方神话的色彩,既显示神性的变体,又是神性在苗族中的真实写照。
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面对媚金大胆热烈的表达,豹子直接说出“放心,我心中的最大的神。豹子的美丽你眼睛曾为证明”,将自己的恋人当作神,与神的爱能超越死亡,战胜所有的困难。正因为这样的泛神倾向,豹子才会因寻找白羊,误了与媚金相约的时程,导致两人恋爱的悲剧。他们以爱情悲剧的代价回归最原始的人神共存,不仅引发对如今爱情现状的思考,还寄托沈从文对于神性爱情与泛神性人格的向往。
情歌中隐含的泛神倾向,在仪式歌中同样也存在。“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他们既诚实,又年轻,又身无疾病。他们大人会喝酒,会做事,会睡觉;他们孩子能长大,能耐饥,能耐冷;他们牯牛肯耕田,山羊肯生仔,鸡鸭肯孵卵;他们女人会养儿子,会唱歌,会找她心中欢喜的情人!你大神,你大仙,排驾前来站两边。关夫子身跨赤兔马,尉迟公手拿大铁鞭!你大仙,你大神,云端下降慢慢行!张果老驴得坐稳,铁拐李脚下要小心!福禄绵绵是神恩,和风和雨神好心,好酒好饭当前阵,肥猪肥羊火上烹!洪秀全,李鸿章,你们在生是霸王,人放火尽节全忠各有道,今来坐席又何妨!慢慢吃,慢慢喝,月白风清好过河。醉时携手同归去,我当为你再唱歌!”诸多因素中,不乏有图腾意识与神性意识的表达。燕宝译注的《苗族古歌》中与人类祖先姜央并提的有水牛:“蝴蝶妈妈与水泡谈情说爱,后来生下十二个蛋,孵化出人类的祖先姜央与雷公、老虎、水牛、大象、龙等动物。”[10]雷公、水牛、龙等对应相应的神性图腾崇拜,如湘西的“椎牛”(俗称吃牛)“剖果”(旧译“吃棒棒猪”)、接龙等。[11]将关羽、尉迟敬德、张果老、铁拐李诸如此类的人物神化,表达湘西苗族最原始传统的观念理想——崇尚武力和祈求祥瑞。《神巫之爱》中神巫受族总嘱托进行献牲、祈福,借泛神倾向的仪式表达苗族人民对于族群生存的向往与展望。《边城》中,作者让翠翠唱这首迎神歌,目的在于赋予翠翠敏感而脆弱的内心世界中的神性,让她的爱情前景与生命意识,通过在迎神歌中对神的祈祷表达出来。
由此观之,沈从文借助民歌中神性的表达,不仅说明神是赋予生命价值的存在,还在潜意识上构建一种以生命原欲为核心的人性理念,既使神性充满人性的道德价值,又将人性赋予神性的特征,以一种人神共在的方式阐述理想的生命形态,完成沈从文更高意义上的“人”的内核表达,达到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与生命价值重建的目的。
四、结语
无论是沈从文小说创作中歌谣所体现的性爱倾向、自贬倾向还是泛神倾向,沈从文皆以一种反现代性的视角书写苗族歌谣给其民族带来的深远影响,并将其扩展到更普遍意义上的人类书写中,这本身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写作”。追溯本源,在苗族传统歌谣中能找到相对应的文化心理与性格特征。一个民族的文化永远是动态的,展现文化的媒介在不断变动中。随着改革开放后一大批新锐苗族作家的涌现(如向本贵、蒲玉等),通过苗族文化所引申的对人的书写将越来越全面、具体与深刻,借助文学作品中的苗族歌谣研究苗族文化的趋势将越来越多元化与动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