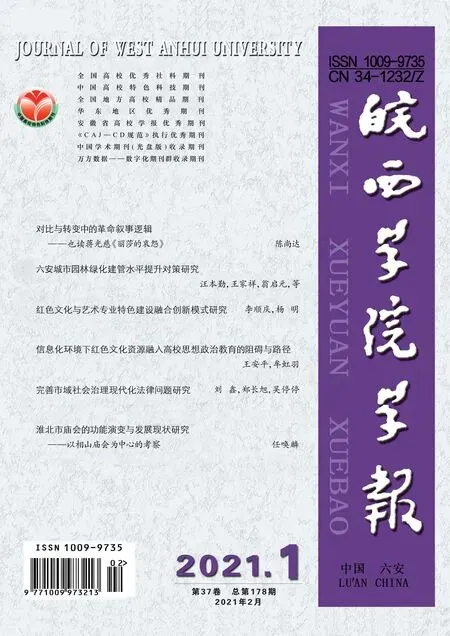对比与转变中的革命叙事逻辑:也读蒋光慈《丽莎的哀怨》
陈尚达
(皖西学院 教师能力发展中心,安徽 六安 237012)
蒋光慈《丽莎的哀怨》自1929年问世后,有过短暂的赞誉,便遭猛烈的批评,且争讼不断。有学者将“丽莎的哀怨”作为“革命的哀怨”来看待,并从丽莎受侮辱与受损害者的下层妓女身份,其关于“俄罗斯并没有灭亡,灭亡的是贵族阶级自己”的“自我检讨”,为丽莎设置众多革命性的参照系,以实现作者极力想要完成的正面革命叙事,表明作者的主观意图确实是通过丽莎的人生悲剧,揭示俄罗斯贵族阶级必然灭亡;但又将其归结为一种粗糙的革命叙事的独特性,“因为缺乏对情感的合理控制而流于脆弱和感伤”,“根源于蒋光慈缺乏对革命动力以及革命结构的深入思考”[1],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哀怨,从而陷入对蒋光慈作品批评的主流话语同构之中。
应该看到,丽莎曾是俄罗斯贵族妇女中的娇艳白花,其身份坠落是流亡困顿生活中的被迫无奈选择,也与丈夫白根的无能无耻有关,沦落为妓女身份也成为丽莎自我鄙视的主要心结。本文在对《丽莎的哀怨》负面评价进行梳理和反思基础上,探讨作品文本的对比叙事和丽莎“哀怨”中的思想观念转变,透视作品对比与转变中的革命叙事逻辑。
一、对蒋光慈《丽莎的哀怨》诸多批评的反思
对蒋光慈的小资产阶级身份及其作品《丽莎的哀怨》批评,因他不愿与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合流,在当时受左倾路线影响的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日报》曾刊登有《蒋光慈被共产党开除党籍》[2],主要内容包括:原是小资产阶级学生;存在拈轻怕重害怕牺牲的可耻行为;擅自脱离组织;入党后对支部生活不重视,经党督促与教育,仍然保留小资产阶级浪漫性;曾写过《丽莎的哀怨》,从小资产阶级意识出发,反映白俄腐朽没落的悲哀,贪图版税,“给读者的印象是同情白俄反革命后的哀怨,代白俄诉苦,诬蔑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党叫他停止出版却延不执行;他的生活是资产阶级化的,已经成了一个没落的小资产阶级。蒋光慈因在张家口不适应苏联顾问的翻译工作,并影响自己的文学创作,不经组织同意而私自离职回到上海,表现出比较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但私自逃到日本是因身体状况恶化而去治病,并非惧怕牺牲、投机取巧和动摇怯懦等所形容的错误革命态度。[3]其对《丽莎的哀怨》创作“小资产阶级意识”出发点的批评,给人的感觉是因作者的小资产阶级身份衍生出的作品创作连带责任。不过,对其因热衷革命文学创作而不从事实际革命工作,也有政治理解上的积极变化,“蒋之疏远群众无论在当年或目前看来都有失共产党人的身份,但是毛泽东也不喜欢其时共产党领导者鼓吹的奇特群众路线——发动示威、罢工和武装暴动来促成‘革命高潮’而全然不顾‘客观环境’。”[4]
“浪漫”也是指刺蒋光慈小资产阶级属性的一个重要证据,过浪漫优裕生活,对革命进行诗意审美,却回避革命实践的艰巨性和残酷性。蒋光慈注重革命文学创作而不愿参加革命实际工作,在当时是无法得到组织理解并被认同的,他本人也并非意识不到不参加革命实际工作的错误和严重性。蒋光慈曾在193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那天上街参加游行,回家后疲惫不堪,女友吴似鸿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指他的党团同志)以为一道跟着去打玻璃窗,去暴行才算是革命,可我是个文人哪!我只能在文字上努力,只有文字是我的革命工具。’‘那你为什么要去呢!要是我,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就不去!’我说。‘这个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你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时整个脸好似要炸了。”[4]南帆教授提到,人们可以从20世纪上半段“察觉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颠倒:国民性改造已经变成了改造知识分子。文学不再赋予知识分子启蒙者的角色;相反,新型的文学主题是知识分子如何置身于工农大众脱胎换骨,赢得新生”;小资产阶级先后作为启蒙者、被教育者和被贬为革命的对象,“这一系列的身份转换无不体现出革命话语或阶级话语与启蒙话语的交汇、纠缠和冲突”[5]。虽然蒋光慈指出革命文学要以被压迫的群众做出发点,李初梨强调革命文学的无产阶级性质;然而就当时革命文学作家而言,并无真正的无产阶级出身,郭沫若就认为,文艺青年们的意识都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即偏重主观唯心的个人主义[5]。因此,蒋光慈的小资产阶级身份也是当时文艺青年的普遍阶级属性,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对工农大众生活疏远与隔膜,自然违背了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受到批判不难理解。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多部《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沿袭了上述对《丽莎的哀怨》政治性错误的批评取向。如认定作品不是憎恶而是怜惜反动俄罗斯贵族阶级,表现出作者的消极思想倾向[6](P200);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不批判反而同情俄罗斯贵族妇女反动派,这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7](P374);“从理智上说,我们相信作者憎恨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白俄。但是,从感情上说,他对丽莎的流浪处境产生了同情,潜在的人性论冲开了理智的堤坝,泛滥了出来,这就改变了作者原来的创作意图,表现出错误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不好的影响。”[8](P168)这里借理智与情感的错位,表明作者创作意图发生始料未及的变化。从“给读者的印象”到“作品给予读者的”再到“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与“错误的政治倾向”,可以发现其中的批评连续性与一体化。对此,柯可先生曾发出质疑:“《丽莎的哀怨》果真是一部替白俄鸣冤叫屈,诬蔑苏联无产阶级统治,有严重政治错误倾向的坏书吗?”[9]在他看来,“我们绝不能将《丽莎的哀怨》和作者的立场问题混为一谈。将丽莎的‘哀怨’中次要的表面的反十月革命的无力呻吟,和主要的实质性的对白俄贵族腐朽本质的深刻揭露,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镜子——大上海的种种人世罪恶的沉痛控诉相互抵消,进而彻底否定作家基于革命人道主义的审美观照立场以及广大读者从这部作品的审美欣赏中领悟人生真谛的可能性。”[9]的确,对《丽莎的哀怨》政治性错误的指责本身导致对蒋光慈创作意图的某种曲解,这或许正是作者“延不执行”停止出版命令的真正原因。
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形式上反十月革命和实质性控诉贵族腐朽结合来形容丽莎的“哀怨”,那样,她思想认识上的发展变化脉络就被遮蔽掉了。有人将满怀爱国之情的贵族少妇丽莎“流亡、沦落、受苦、最终得病自杀”归于为革命所迫,这种不人道的人间悲剧毕竟是布尔什维克与十月革命造成的,从而背离了作者的创作动机,形成了错误思想倾向,产生了消极社会效果,并将其归结为当时白色恐怖环境促成的蒋光慈苦闷彷徨消极思想情绪所致[10]。这就又回归到前述政治性批评语境和框架之中,和上述理智与情感的错位说如出一辙。
夏济安先生提到:“《丽莎的哀怨》情节的弱点在于人物的动机写得不够充分。这可怜的女子操践业已颇有时日了;眼前并没有适切的理由自杀。我倒认为像丽莎这样经过历练的娼妇其处境的真正可怖之处是她可能耽于享乐,对别的事情漠不关心。她可能会有某种不正常的快感,把自己和世界的命运置之度外。这样一个女人的故事如果能作为灵魂的死亡来探讨处理,该会让读者觉得更加恐怖。”[4]丽莎虽同处于白俄贵族反革命阵营,但在流亡生活困顿处境中仍然抱有爱国情怀和道义良知,和丈夫白根与米海诺夫伯爵夫人等是断然不同的。其中值得反省的疑点有四:一是“操贱业已颇有时日”并不意味着被迫无奈的内心痛苦得到缓解以至消除,反而会变本加厉的。当然,小说作品中确实写到丽莎在跳舞场缓步曼舞时曾有寻欢作乐的短暂自我陶醉,但她感伤身世恰如梅雨天气,时断时续,没完没了;二是如果“作灵魂的死亡来探讨处理”,那么丽莎和白根、米海诺夫伯爵夫人等就沦落为一类了,共同体现出白俄贵族的腐朽本质,自然也就无作为“革命的哀怨”可言的,这显然与作者的创作意图不符;三是没有看到作者将丽莎和白根、米海诺夫伯爵夫人等进行对比叙事,鲜明呈现出十月革命导致反革命阵营内部白俄贵族流亡生活中的深刻裂变,以及对比叙事所折射出的革命性意义;四是丽莎的“哀怨”有着极其复杂的内涵,随着流亡生活困顿处境中丈夫白根的日渐消沉卑微,同样落难的朋友米海诺夫伯爵夫人日益堕落疯狂,丽莎思想观念中既有坚守,即爱国情怀和道义良知,也有转变,即对波尔雪委克从简单否定到内心认同的积极变化。有论者认为,丽莎自杀是对白根和米海诺夫伯爵夫人式道路的最后反抗,最终获得阿贵等人身上的革命气质,并和清末登陆中国文坛的俄国虚无党女杰索菲亚相联系[11]。这就有些拔高丽莎形象了,她和过着同样羞辱生活的伯爵夫人同病相怜,不过思想认知有别而已,她是带着羞辱和导致羞辱生活真相的清醒认知走向死亡的,有一种认命色彩。
二、《丽莎的哀怨》作品文本中的对比叙事
《丽莎的哀怨》采取反革命视角的独特叙事方式,无疑是蒋光慈革命文学创作大胆而又创新的一次尝试。他曾说过:“将一个革命党人的英勇表现出来,固然是革命文学,就是将一个反革命派的卑鄙龌龊描写出来,也何尝不是革命文学呢?问题不在于题材的种类,而在于作者用什么态度,用什么眼光,以及会因做立足点,来描写这些种类不同的题材。”[12](P84)《丽莎的哀怨》借鉴了谢廖也夫《都霞》的写作技巧,共产党人的崇高在白色圈中所悟到的,跟都霞在“红”的环境中觉悟到的相比,会显得更有价值。这种从侧面而非从正面来表现的方法感动人的地方,无疑要深刻得多[1]。
红色和白色的不同环境,正面与侧面的不同写法,带来不同的作品审美效果和读者接受心理。丽莎、白根和伯爵夫人是流亡上海生活期间的三个俄罗斯贵族阶级反动人物,旧俄罗斯贵族的卑鄙龌龊和波尔雪委克的伟大光荣都是借丽莎的见闻和感受表现出来的。十月革命让他们陷入流亡生活境地,昔日高贵的丽莎变为令人鄙弃的卖淫妇,英俊傲慢的白根变为消沉卑微的可怜虫,曾同样高贵的伯爵夫人变为不可理喻的疯女人。他们都怨恨革命,并曾对任何一个与波尔雪委克为敌的人怀抱热烈的希望,但结果都是失望。虽然都对波尔雪委克充满怨恨并诅咒,但差异也是存在的,并在流亡生活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可以说,对比叙事是作品反革命视角叙事之外的又一大特色。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比,反革命内部的多种对比,包括不同人物形象性格在流亡生活前后发生巨大变化的对比、不同人物在流亡生活前后对待革命不同态度的对比、丽莎在流亡生活前后对待丈夫白根不同态度的对比等。并且,革命和反革命的对比是由反革命内部的多种对比得到不断强化的。
白根和伯爵夫人都极端仇视革命,前者曾屠杀革命群众,流亡期间时刻不忘自己的团长和贵族身份,“如猪一般睡在家中”,无力养家糊口,竟靠老婆卖淫苟且偷生,最终沦陷为只是一具“活的死尸”;后者的丈夫被革命镇压了,流亡期间陷入生活困顿后,跳裸体舞、卖淫、酗酒等,将肉体当作生活的出路,被哥德曼抛弃后又吸食鸦片等。两者都已灵魂死亡,集中体现出俄罗斯贵族反革命派腐朽没落的反动本质,从而侧面烘托出苏联无产阶级统治的正当性。
丽莎开始并不明白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只是因革命与反革命对立中的暴力和杀戮让丽莎感到不愉快。她出卖肉体前后都有强烈自责且恨极了白根,对祖国的良知从未泯灭,因而才有对自身命运的哀怨。虽然丽莎作为反革命阵营中的人物,对于波尔雪委克存在关于“野蛮”“黑虫”“恶徒”“刽子手”的诅咒,怨恨革命葬送了她舒适安逸的美好生活;即使是在自杀前夕,她也将自己沦落为身患梅毒的卖淫妇羞辱生活结局归结为拜波尔雪委克所赐。不过,她知道诅咒是毫无裨益的事情,波尔雪委克是骂不死打不倒的,反而日见强固起来。丽莎在米海尔表兄等组织力量负隅顽抗失败后,就意识到波尔雪委克的巨大力量了,如同自天而降的万丈瀑布般势不可挡,又如熊熊烈火的广袤森林般无法扑灭,白根与哥恰克乃至整个旧俄罗斯于是被这狂澜与烈火所葬送。就是在流亡上海期间活受罪时,丽莎提出宁愿回到俄罗斯为波尔雪委克当女仆,甚至表示不如痛痛快快地被波尔雪委克捉去杀掉。这在白根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为了不向波尔雪委克屈服而可以抛弃俄罗斯。丽莎曾对白根不相信日本人却希望他们拯救俄罗斯看作是巨大的耻辱,对白根说的情愿让日本人来管理俄罗斯感到惊异且生气。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伯爵夫人邀白根和丽莎夫妇一同到苏联领事馆门前示威,去看那些反波尔雪委克者取下红旗并捣碎领事馆的计划能否得逞,丽莎反而相信波尔雪委克的伟大力量,不仅不去,且认为没有必要,毫无意义。事实也证明了她的判断,她对伯爵夫人的急忙撞门而入报告少年被杀一事心情平静,毫无怜悯,觉得就应该被波尔雪委克杀掉似的,并从伯爵夫人绝望的眼光中,感觉被波尔雪委克所枪杀的,不是那个少年,而是她们自己,是整个的旧俄罗斯。
如此说来,“丽莎对革命的诅咒,就是因为革命使其失去了与原生故乡的血肉联系,从而失去了量度自身的所有维度”[13],只是显现出对丽莎诅咒革命的单方面理解,却缺失了她对波尔雪委克统治力量强大而意识到诅咒于事无补的另一面体认。诚然,让一个反革命阵营的俄罗斯贵族妇女丽莎自述其悲惨经历,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一种自伤自怜的味道,让人对丽莎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情不得已油然而生怜悯之心;但读者如果能够仔细体味到丽莎自述悲惨经历中悲剧的不可抗拒性,并明白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时,就不至于将其视为一种危险情感,进而草率地认定作者同情俄罗斯贵族阶级而反对革命,以致据此推断出:作者内心隐秘的错误阶级立场得以暴露,作品文本整体的叙事指向因此被颠覆了[14]。如果说作者对白根和伯爵夫人取否定与憎恨字眼,那么对待丽莎虽有批评,但同情中又有肯定的。这种肯定,就缘于丽莎对波尔雪委克的强大和俄罗斯贵族阶级的渺小有精准判断;不像白根和伯爵夫人,对打败波尔雪维克一直都心存幻想的。
三、丽莎“哀怨”中的思想观念转变
对《丽莎的哀怨》的批评是同丽莎“哀怨”的解读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或者说,对丽莎“哀怨”的解读直接影响到作品评价。诚如杨慧教授所言:“哀怨缺乏金刚怒目式的斗争精神,它的道德合法性在于无辜,它的人生观在于无可奈何宿命感,它所要倾诉的也只是人被命运所裹挟、所抛弃的哀伤……流亡生活中的流离之苦、思乡之痛是丽莎最大的‘哀怨’。而深入的问题则是,如果说丽莎是因为流亡而哀怨的话,那么这种流亡的痛苦则是缘于对故乡的思念、对祖国的眷怀,而不是政治上的抱负。换言之,丽莎爱的是那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们、青春记忆和俄罗斯文化,而不是政权。”[1]将丽莎最大的“哀怨”理解为流亡生活中的流离之苦和思乡之痛,她爱的是思想精神意义上的俄罗斯,而非政权统治意义上的,固然不错,但是将伴随着流离之苦和思乡之痛的丽莎思想变化线索消解掉了。离开海参崴的前夜,丽莎无论如何不愿离开俄罗斯,“生为俄罗斯人,死为俄罗斯鬼”。白根将她劝离俄罗斯,让丽莎意料不到的是:看不到波尔雪委克失败的白根没有精神,没有尊严,没有信仰,满足于老婆卖淫来养活他,这么卑微的白根就是她当年的理想!可以说,正是白根的可怜、可耻、可笑、可恨让她遭受了她无法承受的羞辱。不过说到底,丽莎认为这不算白根的过错,而是注定了的悲哀的命运。
伯爵夫人的生存境遇并不比丽莎好,甚至更糟糕。他们共同表现了旧俄罗斯贵族阶级的末路。正是这种生不如死的生活,激起有一定良知的丽莎对俄罗斯故土的深情眷恋,她内心宁愿当波尔雪委克的女仆,甚至觉得被波尔雪委克痛痛快快地杀掉也好,这恰恰是丽莎不同于白根和伯爵夫人的独特内心世界。小说还写了洛白珂夫妇,一开始洛白珂夫人丈夫给中国有钱人当保镖补贴家用,积蓄点资本后夫妻俩开鸦片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丽莎受了伯爵夫人的诱导打算吸食鸦片来麻醉自己,结果鸦片馆被查封,洛白珂夫妇被捕。因此,小说通过流亡生活中俄罗斯贵族阶级内部不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对比与变化,映照出丽莎“哀怨”中的思想发展变化脉络。这就从更深层次上揭示出俄罗斯贵族特权阶级整体的腐朽没落,与苏维埃波尔雪委克取代俄罗斯贵族特权阶级的必然性与合法性。
有论者将丽莎的“哀怨”分解为三个层次:“首先哀怨苏联十月革命的暴力革命让她没有了舒适安逸的生活,然后哀怨自己背井离乡被迫漂泊的屈辱生活,最后哀怨自己回国无望、客死他乡的命运以及生不如死的心情。”[15]这三层哀怨鲜明体现出丽莎在流亡上海期间不断加剧的困顿生存处境,这样罗列似乎只是表层意义上的梳理,却没有触及对丽莎“哀怨”的深层认知:第一层“哀怨”隐含有对苏联十月革命力量强大的体认;第二层“哀怨”交织着对白根无能的痛恨与无奈;第三层“哀怨”流露出对腐朽没落的贵族特权阶级统治必然灭亡的认同。这三层“哀怨”并非简单并列,而是整体关联的,体现出丽莎思想认识上的发展变化。其中的意味深长处在于,正是波尔雪委克的强大和光荣,以及贵族特权阶级的渺小和耻辱,才是导致流亡生活悲剧成为丽莎们无法抗拒的人生命运的根本原因。
小说后半部写到丽莎对丈夫白根的绝望:白根为了面包可以放弃尊严和人格;为着让丽莎在家接客,白根竟静悄悄让开;到后来不仅不因丽莎接客陪睡而烦恼,竟还会因丽莎没生意挣不到钱而失望。丽莎甚至愿意将白根让给当初的竞争对手莲嘉而情愿做木匠伊万的妻,记得他唱过的深印在她心灵里的情歌,过劳苦的然而是纯洁而独立的生活,可以避免被人玩弄而羞辱地苟活。在丽莎的心中,伊万昔日地位低微,但现在地位高贵了,她请高贵的伊万原谅自己的堕落。丽莎内心深处的这种移情别恋,意味着她与丈夫白根代表的腐朽贵族阶级精神脱离,转而与新兴的苏维埃无产阶级思想接轨。丽莎还联想到两年前观看的美国西席地密耳导演的影片伏尔加的舟子,少年舟子和林娜的牵手引起她对自己身世的感慨。现场中国观众遇着革命军胜利或少年舟子占上风时兴奋鼓掌,富于同情,让她感到震惊。这暗示了波尔雪委克在中国的同频共振!小说最后写道:丽莎赴死前梦到久被忘却的姐姐,那个抛弃家庭投身革命的薇娜,也许是波尔雪委克的要角了;丽莎当初听从爸妈的教诲,如今过着自行作践的羞辱生活;丽莎请姐姐原谅不幸的自己,让他们得意不已,自己则悄悄死去。这个情节安排同样具有一种暗示,表明丽莎的“哀怨”中饱含着对姐姐所代表的波尔雪委克统治的积极认同,和对自身代表的俄罗斯贵族统治灭亡的消极体认。丽莎“哀怨”中出现的这种思想观念转变表明,虽然她爱的并不是政权统治意义上的俄罗斯,但她对苏联无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统治俄罗斯是有着明显的内心认同的。
“光慈晚年每引以为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从事文艺工作的同时代者,都不能对他有相当的尊敬……此外则党和他的分裂,也是一件使他遗恨无穷的大事,到了病笃的时候,偶一谈及,他还在短叹长吁,诉说大家的不了解他。”[1]一个让人难以消除的困惑在于,对于蒋光慈《丽莎的哀怨》,一方面是对其政治性错误的严重批评,另一方面是作者本人被误解而陷入深重的内心痛苦之中,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对立和矛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前已述及,作者因缺失革命实践经验而使得革命文学创作陷入一种不切实际、难被认同的主观想象之中,无疑是一个主要因素。笔者以为,撇开作者小资产阶级身份与缺乏革命实践经验,单就小说作品本身而言,丽莎因十月革命风暴促成的悲惨命运而诅咒波尔雪委克被放大,其“哀怨”中对波尔雪委克新生和贵族阶级腐朽从而导致悲剧的不可避免这种内心认同被缩小,甚至被忽略,从而导致作品对比叙事和丽莎“哀怨”中思想观念转变所体现出的革命叙事逻辑被遮蔽,甚至被遗忘了,这才是作品不被认同而致光慈先生遗恨无穷的真正深刻原因。当然,反革命视角叙事本身的确存在着一种风险,丽莎对十月革命的诸多诅咒本身难以让革命者接受,它易被理解为对十月革命的控诉,并对革命群众产生不利影响,构成对蒋光慈《丽莎的哀怨》政治性错误倾向批评的强大支持性语境,就并不奇怪。从这个意义上讲,有论者将《丽莎的哀怨》理解为“个人革命话语的无力抗争”[16],也就具有某种可理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