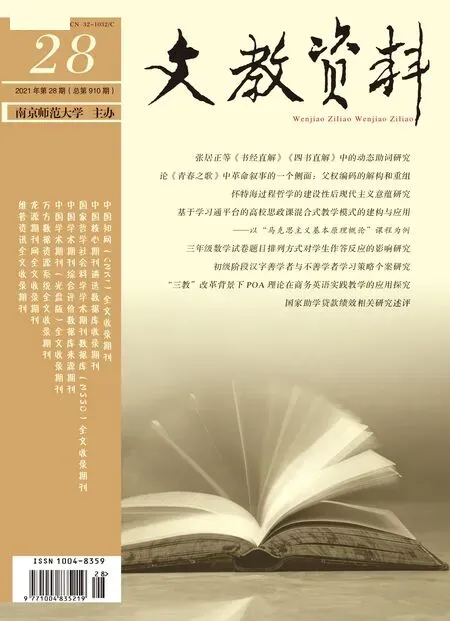论《青春之歌》中革命叙事的一个侧面:父权编码的解构和重组
赵怡然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0)
《青春之歌》中的父权因素是被广泛承认的,却很少有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解读,其中一个原因是,无论弑父也好,救父[9]也好,最终围绕的话语中心都是革命,革命既是子一辈的反抗实践,也是构建“新父”的唯一正当合理的力量,这种“新父”的力量以不同的青年革命者为能指,一次次地指向革命中女性作为性别群体的能指化身——主角林道静。革命叙事交织着父与子以及父权叙事的双重话语表达,因此很容易成为解读《青春之歌》的聚焦点。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在革命叙事的解读中,仅仅涉及情感元素或成长元素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父与子之间颠覆与重构的关系梳理清楚,我们才能够看到《青春之歌》所使用的革命叙事的原貌。
一、革命叙事、父与子母题及《青春之歌》中父权社会的解构方式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父亲”语义的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其最终都指向了权威、严正、不容侵犯或忤逆。主流儒家文化对“父亲”的约束极为有限,相对于背负着恩情与罪责的“子”们的“子子”而言,“父父”仅仅以一种建议和感召的形式存在,与其说是儒学纲常中“父亲们”必须执行的条件,不如说其仅仅是出于思想架构的完整性而设置的表象性的权力软化和内倾的体现。子犯父是大逆不道;父犯子,则早有舜之于瞽叟的榜样。儒学中父与子在“家”中的话语场域是对政治的直接映射,是君与臣在“国”中关系的母命题。因此在封建时代末期,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父与子的关系及其阐释有着对立化和激化的倾向。但在封建政权没有被推翻之前,对这一关系的反思和指控必然是有限的。直到清末民初,父与子的命题才产生萌芽,但仍然“脱离不出孝的话语”[10]。
“五四运动”不仅是20世纪中国政治的重大转折点,在社会文化层面也成了文化解放的代名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个性、自由的张扬真正开启了中国文学的启蒙时代。在这一时期,随着西方现代理论的大量翻译和介绍,父与子命题中的矛盾似乎因为弗洛伊德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引入而有了科学的阐释。弗洛伊德超越了一切国别和文化与全人类产生对话的生物学视角,让这一命题处于朴素、本原、难以超脱的生物性的统摄之下:所有的“子”都有自觉或不自觉的恋母情结,出于这种恋母情结,儿子潜意识中总会抗拒、颠覆父亲的权威,甚至有颠覆式的“弑父”倾向[11],父与子的母题受到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传统话语建构下的父与子关系对“子”的压抑正处于“五四”所张扬的个性解放内核及其主导群体——青年学生、学者——的对立面,所以对这个命题的关注和其自身的发展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议程设置的发展是一致的。在西方现代理论的载体《新青年》《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等刊物中,现代性文本里父与子的母题是时代整体文学解放所产生的新视角中的一个分支。具体作品中,胡适的《我的儿子》、萧军的《第三代》以及30年代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张天翼的《包氏父子》都有颠覆传统父子关系的倾向。40年代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作品也是对这一主题的继续发展。
革命叙事的产生比父与子母题的讨论略晚。“所谓‘革命叙事’产生于20—40年代,即左翼革命主义的史学”[12],“第一次引入了苏联革命理论的基本观念”。在经济层面,强调生产关系对经济社会的决定性作用;在政治层面,突出革命组织带领底层民众反抗来自国内外的压迫势力的必要性,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基础及其在苏联的实践密切相关。“五四”之后的文学经历了一个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型过程,从早期的白话文运动被郭沫若以“破絮袄上打补绽”“污粉壁上涂白垩”但内里资产阶级仍然植根其中的评价否定和批判开始[13],至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中国共产党站上主流政治舞台,早期共产党人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14],革命叙事在主流文学中呈上升趋势。随着1928年国共两党合作破灭,无产阶级文学声势凸现,一些文学杂志和“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甚至对文坛的引领者们发动攻击。[15]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革命文学”的理论和创作都不断发展,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手法逐渐风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后,众多“精英作家”都进行了自我反省,以现实革命和工农群众日常生活为主的叙事逐渐形成压倒性的趋势。解放区文学的要求让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相较于“五四”启蒙时期都呈现出单一化趋势,父与子母题作为一种隐藏文本几乎以常态性的姿态出现在革命叙事中。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文学”延续了这一倾向,“子”一辈作为革命的引领者或是第一接受者,决定着“父”一辈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以政治标准为唯一标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必然被“子”一辈“弑杀”,而底层的、持有落后观念的工农群众往往与同时作为革命主角和文本主角的“子”一辈具有某种血缘瓜葛,因此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被拯救”“被开化”的受教育对象。
革命叙事及其文学作品载体中从来没有强调过父与子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与将封建地主阶级的反面能指无意识地定位成衰老、颓朽、迂腐等特征并存的父辈形象相类似,作家们对父与子母题的运用几乎是一种无意识的运用,比如《家》中高老太爷和觉慧的冲突暗暗交织着父与子的权力争夺;《雷雨》中大骂周朴园的鲁大海是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子”一辈的代表;《包氏父子》中父权的覆灭以老包寄生在小包“往上爬”的梦想破灭和儿子小包在老包身上的经济寄生贯穿始终这一对极具张力的矛盾境况呈现,等等。在《青春之歌》所处的“十七年文学”语境中,这一母题表现模式的主体性发生了偏移,父与子更多是以政治隐喻的面貌出现。与“五四”时期相比,作家们以对父与子关系的叙述和表现推动革命叙事的发展,却没有将其作为主题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而言,革命叙事似乎代替了一切文本含义,在同一文本中的其他叙事元素统统变成了“他者”,以一种被驱使的姿态载负着阐释、凸显革命叙事的任务。《青春之歌》因其叙事元素的丰富性和女性叙事而尤其彰显了这一矛盾。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构建下,作者不得不“牺牲一些女性化的东西”,直接的表现就是林道静虽然以“准主体”的形象出现在文本中,却不是“精神的核心”,而某种意义上只起到了叙事联络作用,成为一种“结构的核心”[16]。
这一点在小说刚刚出版所引发的五六十年代的讨论中也可见一斑。《青春之歌》在出版之后引起巨大反响,引发了文化界的广泛讨论,但讨论的重心围绕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和“知识分子的革命成长道路”展开,分立两派。性别叙事的问题、革命叙事如何构建的问题根本没有提及。可以说,这一时期,也就是关于《青春之歌》的第一阶段的解读,是处于政治话语统摄之下的解读,以政治视角为唯一视角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其在社会泛文本化中的表现恰恰与这一时期作品中革命叙事对其他叙事方式、革命主题对其他主题的主导姿态相印证。
“新三板”市场原指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入代办股份系统进行转让试点,因挂牌企业均为高科技企业而不同于原转让系统内的退市企业及原STAQ、NET系统挂牌公司,故形象地称为“新三板”。
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探索这一时期作品的革命叙事时,反而应该从其统摄之下的子命题入手,这些子命题共同构成了革命叙事的基本内容。
在革命叙事对传统父权编码的解构中,父与子的关系围绕其政治立场呈现出多种形式。本文选取林伯唐、王鸿宾为典型代表,探讨两种截然不同的“父”一辈的命运及其中隐含的各类子命题。
二、弑杀
在明确阶级立场的情况下,被弑杀的“父”以对立阶级的面貌出现。《青春之歌》中出现的这一类典型主要有林道静的父亲林伯唐、余敬唐、罗大方父亲、胡梦安等人,他们是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国民党军阀官僚势力的化身,是这两种势力的核心人物,某种意义上具有精神象征作用,而他们的结局也直接地对应着政治性的隐喻。
“子”一辈对于女性而言的父权重建是文章的主体,为了突出林道静在革命感召下的成长、凸显“子”一辈革命者的光明面貌和引领作用,从而揭示革命正确性及必然走向成功的终极主题,旧的父权编码的解构在小说中处于次要地位,在篇幅和叙事手法上都要为革命的新父权重构让位。因此我们看到的这几种革命对立面的代表,常常以碎片化的面貌,或仅仅在主角的描述中作为陪衬的角色出现。
林伯唐作为林道静的生父,在文本中主要对应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势力,是旧的父权社会编码中的重要因子。他在文中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具象的、具有主体性的人物(大部分源于林道静的回忆),一种作为主角林道静身上的“黑骨头”阶级象征而存在。杨沫对林伯唐的具体塑造集中在文章开头第二章林道静对于自己身世的回忆中,主要情节则为玩弄林道静生母秀妮、听从徐凤英的意见送林道静上学两节,紧接着“1931年的一天”,林道静“高中毕业只有两个多月”的时候,作者就从林道静的视角道出了他的结局:“家里破产啦——我父亲因为地权的事打了官司,身败名裂,就把口外的地一股脑儿瞒着母亲全卖光,带着姨太太偷跑掉了。”[17]在这之后,林伯唐作为小说人物的形式,在文本中几乎销声匿迹,但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象征却在林道静身上得到延伸。对于这种阶级精神的弑杀过程正是林道静在“子”一辈革命人的引领下不断走向革命的成长过程。在《青春之歌》的第二章中,林伯唐作为一个人物“已死”,他的旧父权以“出身”的方式在林道静身上留下痕迹,成为小说革命叙事的起点,当林道静彻底消磨掉自己身上的“黑骨头”,成长为共产党员,并顺利领导了北大的学生运动的时候,林伯唐及其象征物才被彻底弑杀,而这也意味着小说的完结及革命叙事的完成。
在林伯唐一隐一显的两种叙事埋藏中,其实蕴含着另一个命题:显性的地主阶级主体终将走向灭亡,这是浅显而容易的任务,但“地主阶级出身”则更为复杂。从这个角度而言,林道静在革命道路上不断犯错,同时带着强烈的羞耻感和惭愧感对自己进行全盘否定式反省的成长经历,展示了作品所处的五六十年代地主阶级出身者的生存状态。有人将她的成长解读为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笔者认为这一身份并非林道静处境形成的主要原因。“十七年文学”所处的时代背景正是“一化三改”,社会主义改造不断深化的过渡时期,各行各业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剔除和改造显然仍然是主流话题。地主虽然因土地被没收而从旧的父权宝座上跌落,但积重难返的阶级矛盾并没有立刻得到缓解。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阶级印记明显清晰于知识分子的群体印记。林道静的成长过程就是与林伯唐一次又一次地割裂、分离、划清界限,直至将其完全剔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林伯唐作为“父”的角色在文中不断被放逐和悬置,而林道静对青年男性革命者的追随,则向我们展示:“黑骨头”的出身印记只有通过“认父”于革命及其能指,只有通过自我放逐的痛苦过程,才能完全弑去,获得纯洁无瑕的新生,与此同时,主体也将在革命事业的新起点上为自己重新命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林道静与父亲的决裂不仅仅是与具象能指的决裂,还是一种自我决裂。在精神象征的层面,她的“成长”过程不仅是对“父”的弑杀,也是一种“自杀”。这里用的是“自杀”,而不是“自我改造”,这是因为我们还应当看到,林道静身上所谓的“资产阶级的”“黑骨头”的元素恰恰是她有别于常人的性格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合了浓烈的个人印记,甚至能起到指代主体的效果。小说的叙事起点,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学生是这样一副形貌。
不久人们的实现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贩卖乐器的吗,旅客们注意其这行李的主人来。不是商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艺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旅客们的注意,尤其男子们开始了交头接耳的议论。可是女学生却像什么人也没看见,什么也不觉得,她长久地沉入在一种麻木状态的冥想中。[18]
场景中人物的独特表现,不仅让车中人印象深刻,也很容易给阅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乐器、表情寂寞,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都是无产阶级工农子弟们难以触及的元素,却极具个人色彩。而与之相对的,在文章末尾林道静成功领导北大学生游行的高光时刻,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描述。
道静、侯瑞、刘丽、韩林福、吴禹平掺杂在许多男女同学中间,接二连三地抢夺水龙、打碎消防器,向拦阻他们、毒打他们的军警肉搏。道静、晓燕、李槐英她们都几次三番地被打倒在地上,头发蓬乱了,脸青肿了,鼻孔淌着鲜血,但是她们和许多被打倒的同学一样,立刻又昂然地立起来,不顾一切地继续向前冲去。[19]
对于林道静的描写被对革命者集体群像的描写所替代,个人化特征的踪影荡然无存。在主体将自我舍弃而投身集体的过程中,与地主阶级出身标志的决裂使林道静不以个体化的面貌存在,而成为革命集体的能指,或者说,泛指的概念化构成。
另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林伯唐的“被弑”以破产和流亡为文本中的直接表现形式,其他“父”一辈的“被弑”也并不单一表现为肉体的消亡。由于旧父权被解构的次要和他者地位,这些父亲的“被弑”更多是叙事意义上的,比如罗大方的父亲,在上卷第十九章罗大方与卢嘉川相见时前者的描述中出场。从罗大方与卢嘉川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他“费尽力气托了不少朋友花了上千的大洋”才把罗大方保释出来,唯一的希望就是“老老实实地给我读书”。但对于与自己政治立场对立的官僚资本主义,罗大方对即使刚刚救了自己的至亲也这样说道:“父亲,你可赔了本了!我不值一千大洋,也不值得你那些朋友的隆情盛意,更值不得上美国去镀金。”“倒霉的不一定是谁,你这块同胡博士一起到美国镀过的灿烂的黄金,不准哪一天就要变成粪土呢……”[20]以阻挠罗大方参与革命事业的叙事目的存在的罗父,很快在这种正面出击中被弑杀,已经坚定了革命信念的战士毅然决然地走向了与父辈的决裂(此处文本明确指向罗父及其朋友,意即官僚资本主义的党羽)。罗大方和罗父的正面交锋也是小说中“子”对“父”旧日权威颠覆性弑杀的典型代表。
与此同理,胡梦安所含有的包办婚姻、官僚资本主义等叙事元素,也在林道静的拒婚及成功走上革命道路的结局中被彻底弑杀,但与此同时,他所象征的官僚资本主义还在戴愉身上得到了延伸。戴愉同时处于“官僚资本主义”和“叛党者”两个范畴的中间地带,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使他无法融入官僚资本主义隐喻性的政治能指象征,而只能以一种被支配者和延伸物的形式存在。戴愉身上不仅背负着“保父”的罪责,还运行着对革命之“子”的背叛,因此如果说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只作为叙事目的出场,以一种目的旁落的姿态被“弑杀”,那么戴愉所犯下的更加不可饶恕的错误则将他引向了肉体及其代表物的双重消亡。
谁知就在这时,一条粗大的麻绳已经套在他的颈脖上,而且越拉越紧。他再也喊不出声音来,可是,他却还能够听到王凤娟的声音:“你这废物!连一个王忠都领导不好!把北平的学校闹得一团糟……”她突然把声音提高,“送他回老家!给他一个整尸首!”汽车飞驰这开到了郊外。在荒漠的昏黑的野地里,戴愉又被从汽车里摔了出来。惨淡的星星仿佛嘲笑般的还在对他僵硬的尸体眨着眼睛。[21]
游离在“父”与“子”之间的戴愉遭受了“父”与“子”双方的遗弃,为了保持“子”一辈革命者们的光辉形象,杨沫在文中对戴愉被弑杀方式的叙述中刻意强调,“这不是共产党员江华,这是他的情妇兼上级王凤娟。”戴愉被他投向的官僚资本主义弑杀,从叙事意义的角度,可以说是比较彻底地完成了对旧的父权编码中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解构。就像林道静只有经过漫长而痛苦的“自杀”过程而将自己融入革命集体中一样,作者借戴愉的结局向我们展示了投奔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唯一下场。在《青春之歌》中,戴愉是唯一以“叛徒”的身份出现的子一辈革命者中的异类。与此相对应,我们发现,以对立的政治面貌出现的其他旧父权的舵手在文本中都不是单一的,作者不仅对其中的个体进行重点描绘,也有不少时候安排他们以集体或多主体的方式出场,比如林伯唐、余敬唐、和林道静在农村“历练”时期遇见的宋郁彬、宋贵堂父子,都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典型代表,罗大方爸爸和官僚朋友们、胡梦安、鲍县长等,都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这些人物及其代表的阶级在文章中以革命对立面的方式不断出现,用于烘托和反衬革命者的正义、顽强、大公无私,革命道路的艰险、光辉和唯一正确性。但唯有从革命者内部分化出的“叛徒”的角色由戴愉一己承担,这才能涉及“子”一辈父权的重组问题——“子”一辈的革命实践革命应当是纯洁的、先进的。
三、拯救
革命叙事决定了“子”对“父”的主流态度必然是弑杀。或者说,“父”主要作为旧父权权力体系的能指而存在。但在现实中,“父”一辈成分是多样的,为给读者呈现旧父权走向光明的空间及可能性,抑或是为了再次确认知识分子的觉悟性和改造价值,与林道静的成长相呼应而维持叙事的完整性,杨沫在《青春之歌》中也设计了几位旧父权组成中的“异类”,其中重点刻画的代表是王晓燕的父亲王鸿宾。有意思的是,父权与子权的“异类”代表以父与子、主与客的方式在王家会面,分别背叛了他们本应隶属的权力结构,作者视角的文本也许是想通过揭示二者结局的反差性向我们再一次印证“子”的反抗必将取得胜利,尽管在今天看来,王鸿宾的被拯救过程也许包含更多当时社会泛文本语境影响下的语义。
在得知戴愉被杀之后,作者紧接着便叙写了王家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叙事主导并不是与戴愉关系最亲密的王晓燕,而是已经坚定朝向革命道路的王鸿宾。片段开头,王鸿宾就以“主角”的姿态首先出场:“王鸿宾教授在他朋友狭窄的屋地上,背着手不停地走来走去,显得很烦躁。”在王晓燕道出两人情侣关系的破灭时,王鸿宾已经按捺不住,不辨信息真伪地开始破口大骂。
王教授抬起头突然把手一挥,把眼一瞪,好像戴愉就站在他面前,他凛然地呸了一口道:“我明白了!奸细,叛徒,原来是伪君子,是无耻的走狗,我们干我们的工作,量他还能怎么样我们?最后再看谁胜谁负好了。”[22]
一系列的语言动作进一步表明了王鸿宾的政治立场朝向,在对戴愉叛徒身份的批判中,对“子”的朝向不仅战胜了对“父”的惯性顽守,甚至战胜了“父性”,王鸿宾因此而被异化成政治话语的代言人。王鸿宾对于这一角色的承担实际上是不符合革命叙事规范和《青春之歌》全书的叙事惯例的,它本应当由真正的“子”一辈革命者来充当。但此处为了突出这一父辈中的“异类”所具有的极高的思想觉悟和成为革命者的潜质,王鸿宾承担了这一功能。面对女儿在爱人是叛党者和已经去世的双重打击下的精神崩溃,王鸿宾唯一明确指向女儿现状的安慰只有一句“燕,可不要消极呵!”而这句话与其说是王鸿宾从担忧女儿情绪状态的角度出发给出的规劝,不如说是为下文政治话语的输出所作的铺垫。
“ ,还没有问你,共产党方面不怀疑你吗?还可以相信你吗?”教授皱紧双眉庄严地追问了一句。[23]
作者在描写王鸿宾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无意识地把他当作真正的“子”一辈革命者看待了,因此王鸿宾“皱紧双眉”“庄严”地以革命卫道士的姿态询问王晓燕。作者在此不知不觉地应用了对革命者进行描述的话语体系。王鸿宾与王晓燕之间关于“党是否信任”的问话,其实是“子”一辈革命者所建构的权力中心党的自问自答:党面对一个曾经受叛徒误导,与叛徒结为情侣的“有罪者”的态度,是苛严不近人情的吗?不是,“你问共产党还相信我吗?相信!完全相信!不是党来拯救我,我就真的完了。”作者把党的宽容和感召力的语义融入王鸿宾和王晓燕的对话当中。
与此同时,作者对王晓燕的自白的叙写,也许是想由读者视角再次表现党的巨大感召性,并以这种感召性为契机,引导王鸿宾最终以父辈的身份参与学生运动,完全将自己从旧父权的编码中抽离,而以子辈的面貌出现,但事实上,杨沫早在王鸿宾与王晓燕的这一段对话中就确认了其革命者的身份。
关于《青春之歌》所展示的知识分子在五六十年代的处境和面貌,有学者认为这是作者将林道静的“小布尔乔亚”的情感叙事被革命叙事改头换面这一安排所集中体现的效果[24],但就文本而言,作者对王鸿宾投身革命事业过程的叙述更加能够突出这一隐性命题。在文章的末尾,主角林道静作为一个“准革命者”,对北大学生运动的领导是她的成人仪式;对王鸿宾而言,这也是他脱离旧父,投向新父的告别礼和接风宴。《青春之歌》第二部第四十四章中,完整记述了王鸿宾从在党的感召下的自我检讨、自我矫正到投身运动的全过程。从知识分子群体象征的层面而言,这一章就是整部《青春之歌》林道静成长轨迹的缩影,且在开头部分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罪数”进行了更为明晰的清算。
在起这样一个念头之前,他当然不无矛盾。他想到了反动统治者的淫威;想到了多少爱国人士只为争取起码的自由和民主而身陷囹圄,甚至因此上了断头台;他想到了他也许因此而被学校解聘而失业,甚至被捕入狱,那么妻子、他心爱的女儿们,将失掉丈夫、将失掉父亲;而他自己呢,也将吃到从没吃过的苦头……虽然当年由于和胡适的接近,受过他的影响,许多问题认识不清……[25]
文本中叙述的王鸿宾的“矛盾”和所受的胡适的影响,其实是作者杨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这一点在林道静身上,表现为面对男性革命领导者她一次次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幼稚”,每一位男性革命领路人的出现都是林道静思想上的一次重大洗礼,男性领导者的到来也往往意味着现实困境的解脱和被拯救。但由于性别视角、阶级出身视角的差异,林道静身上背负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被弱化和被遮蔽的状态,换言之,作为主角,林道静身上背负的命题更加复杂化、多元化,因此对于知识分子的象征性而言必然是要被削弱的。王鸿宾虽然背负着父与子对权力的争夺,但毕竟卸下了性别叙事,阶级叙事在文本中也没有被突出说明。因此他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其象征性是比较纯粹、集中的。当王鸿宾加入学生队伍的运动时:
第一次,王教授像一个姑娘般脸红了。他望着这些青年学生纯真的热烈的眼睛,忍不住热泪盈眶、喉头哽咽。他频频向人群挥着手,一边挥手一边拉着妻子,像个小学生似的,慢慢地羞怯地走进排好了的队伍当中去。[26]
作者在这里所运用的一系列比喻的喻体:“一个姑娘”“小学生”,是明显与王鸿宾的身份和性别不符,甚至相割裂的。作者有意无意运用的妇女儿童的形象,在时代语境下带有明显的弱势象征,在这里,王鸿宾并不以“北大历史系教授”的身份存在,他真正代表的精神内涵蕴含在妇女和儿童的喻体之中,曾经的旧父权体系中的因子在投向革命道路时呈现出的孱弱,是这一系列在男权视角看来甚至带有羞辱意味的描述存在于文本的深层原因。
四、结语
本文所提供的从父与子命题讨论革命叙事中旧父权编码的解构,注定只是从革命视角全部解读的一个侧面。在这一逻辑架构下,还有女性视角下“子”一辈革命者对父权的重组的命题。在旧父权的消亡和新父权的建立间,《青春之歌》所展示的女性“独立”“自由”仅仅只是一种幻象。这种幻象因为时代的变迁在当下已经不复存在,但在作品面世后的五六十年代,却呈现出巨大的感召力。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也应当有所认知的。本文所选取的解构视角,意在为持续不断的《青春之歌》研究提供一种新视角和新思路,在这一道路上,其解读无疑还有更多的可能。
——以林道静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