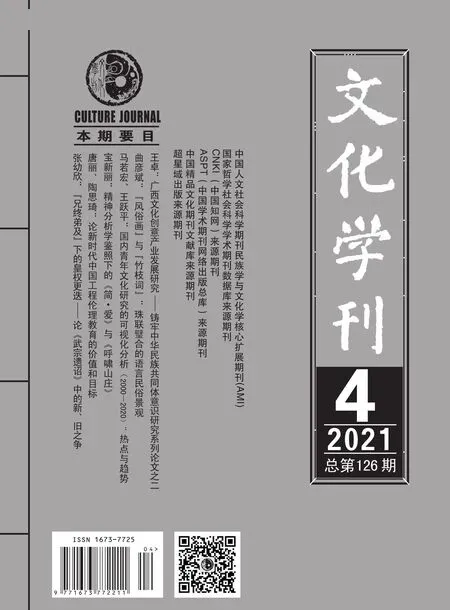“不知观”下《阅微草堂笔记》文本叙述风格探析
张雯玉
中国古代志怪小说自魏晋发端,至清代已蔚为大观。在此背景下,以编纂《四库全书》著名的清代巨儒纪昀,创作了可与《聊斋志异》比肩的《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阅微》)。蔡元培认为:“清代小说最流行者有三:《石头记》,《聊斋志异》及《阅微草堂笔记》是也。”[1]因广泛流传与持久的影响力,《阅微》成为后世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但关于文本叙述中体现的“不知观”却少有探讨,对“不知观”体现的叙述风格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本文选取中华书局出版的“经典藏书系列”《阅微草堂笔记》,韩希明译注版本进行研究,此版本仍然保留原本的内容框架,选稿依据纪昀在原著各卷的侧重点采编,在众多选本中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一、《阅微》概述及“不知观”理论内涵
笔记体小说作为中国古典小说最初的存在形式,至清代已有千年的历史,《阅微》正是在这千年历史文化积淀下创作的。“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2]是鲁迅对《阅微》的评价。《阅微》的传世价值颇具争议,王刚曾评价:“纪公《阅微草堂》四种,颇无二者之病,然文字力量精神,别是一种,其生趣不逮矣。”[3]王刚认为纪昀在写作时,既没有恢宏的叙事,亦无文字的精工雕琢,《阅微》的文学价值较《聊斋志异》相距甚远。对于王刚的评价,有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阅微》“瑕难掩瑜,妍尤胜媸”[4]。纪昀以小笔触书写大道理,用百姓最能接受的方式将价值观融进字里行间,与其说《阅微》是一部文学性不强的作品,不如说它是一部承载着中国封建传统道德的文化巨著。
中国传统道家思想认为无胜于有,有生于无。冯友兰提出:“一切有名都是由无名而来。所以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5]从中国古代传统语境来看,“不知”可以被分为三类:其一称为“应知之无知”,其二为“不知之无知”,其三为“不知之知”。这三种分类构成了“不知观”的三个类别,构建了一种完善的价值观念。
“不知观”的第一类表现为“应知之无知”。“无知”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解释为“缺乏知识,不明事理”,故“无知”是知识的欠缺与匮乏。“应知之无知”的意思是本应知晓的道理,因其个人原因而表现出愚昧、不知晓。这一类的“不知观”表现的是主观上的无知,更多的是作者以自我为中心,将对象融入虚构人物中,从而展开讽刺、嘲笑与批判。
“不知观”的第二类体现为“不知之无知”,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婴孩时期未受教育的“无知”,展现出本真的个性特点。道家的“无知”不含有贬义的色彩,而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出万物本源、灵魂透彻、未受世俗浸染的精神特征,如“圣人皆孩之”,但这却产生了悖论,因为婴孩永远不可能成为圣人。所以由“不知”引发的“无知”实则是人成长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体现在读者不知,主要表现在作者没有对文本的人物、情节进行设置,用共性替代个性,导致读者不知。如果说前一种是主观上的有意“无知”,那么后一种则是客观层面的无意“无知”。
“不知观”的第三类表现为“不知之知”。前面两类“不知”的表现形式都是“无知”,而最终层面上,“无知”与“知”的表现形式还是不同的。此时主体已经有意识地将自己与“无知”区分开来,不仅认识了“知”的层面,也看清了“不知”层面的深刻哲理。“不知之知”最早是由庄子提出的:“孰知不知之知?”[6]“知”的最高境界即是体悟到人生的大道是不可知的,故知大道不可知的境界是“不知观”的第三类。《阅微》是我国笔记小说体裁的佳作,在其中潜藏着“不知观”的玄机,值得进一步探索研究。
二、《阅微》中“不知观”的文本呈现
“不知观”在《阅微》中的文本呈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为人物不知、读者不知与作者不知,三者既相互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
首先,人物不知是指文本叙述中,作者主观设置的人物不通晓事理与人情,后通过文本中其他人物的告知或者劝解,达到“有知”的层面,或直接进行批驳以达到讽刺效果。例如,文本中描写了一位“所至但饮一杯水,今无愧鬼神”的官员,被阎王以“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告知。这体现了人物本身不知,经另一人的告诫,从而达到“知”的境界。再如文本中描写了一位讲经授学的私学讲师请求颜回讲述《诗经》的奥义,颜回答道:“君小儿所诵,漏落颠倒,全非我所传本。我亦无可着语处。”除作者评点外,故事戛然而止,直接讽刺了这位志趣浅薄的讲师,未解惑而使其仍停留在“不知”的层面上。人物不知主要表现为“不知观”的第一类——“应知之无知”,人物通常因其自身的愚昧无知或假作谦虚,最终体现出“无知”。
其次,读者不知表现为人物姓名的不知,或是对事物性质的不知。纪昀在写作《阅微》时,因体系庞杂、人物众多,大都没有联系,所以他经常将人物姓名虚化,使读者不知,如以“献县史某,佚其名”“鬼名某,住某村”“郑五,不知何许人也”等来呈现主要人物,弱化人物性格特征。纪昀在创作时,并没有强调人物的个性化特征,多在表现适用的共性,以期达到教化的目的。读者不知不仅表现在姓名层面上的虚化,也有情节或事物性质的不知,例如“迄不知九幽之下,定谳如何”,纪昀没有详细叙述阴间断案结果,但他自己早有结论,或在结尾设置开放式结局,引发读者思考。例如“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将乌乎质之哉”,将知与不知的界限模糊化,由读者展开思考。纪昀以虚化情节为手段,达到读者不知的目的。读者不知在“不知观”层面上表现为第二类——“不知之无知”,作者因主观刻意隐藏,而使读者进入其营造的主观境界中。
再次,作者不知具体表现为无法论证,或是体悟到道是无法用个人的“小知”感受到的。例如,《如是我闻》中描写了王相御的儿子一被人抱,天上就会掉下钱财,不久这孩子就夭折了的故事。纪昀未详述其中缘由,而是借文中众人之口表达猜测,如:“或曰:‘王生倩作戏术者搬运之,将托以箕敛。’或曰:‘狐所为也。’”但纪昀在篇末写道:“正不必论其真妄也。”纪昀认为此类事只需禁止,因难以用常识解决,故不必晓其因果,表现为作者不知。作者不知还表现为作者体悟到万物生长的规律不可捉摸,如:“凡望见此花,默往探之则获。如指以相告,则缩入雪中,杳无痕迹,即(属刂)雪求之,亦不获。”作者描绘了雪莲的生长状态,但怎么得到雪莲的方法却不可知,作者以“草木有知,理不可解”表达草木有灵有知,用情理无解的观点。纪昀认为自然与人一样,其生长规律不能有意探求。作者不知表现为“不知论”的第三个层面——“知之不知”,以知论无知,从而体悟人生的哲理。
人物不知,读者不知,作者不知从表面上分属于“不知观”的三种类别,但实际上却有内在的联系。作者设置人物不知以达到告诫与讽刺的效果,设置读者不知以达到神秘化、陌生化的效果,而作者不知同时又体现了人物不知与读者不知的两个层面,可见三者不能割裂来看,三者融合体现了《阅微》的整体虚构叙述风格。
三、《阅微》的虚构叙述风格
叙述是作家把世界“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出其中的意义”[7](注:笔者译)。叙述的方式是讲故事,落脚点是讲道理,目的是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阅微》是笔记体志怪小说,属于虚构叙述的范畴,而通过分析“不知观”在文本中的体现,可以了解《阅微》总体的虚构叙述风格。
第一,纪昀试图以弱化人物、弱化情节的方式形成神秘化的虚构叙述风格。笔记体体裁因篇幅所限,不能与传奇或是杂剧相提并论,不仅在情节描写方面需要大幅缩减,在人物外貌、语言、动作和心理描写等层面上也较为简略,这就无法展现形象生动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但《阅微》不同,一方面,其描写的人物大都姓名不全,故事情节也多有“隐化”。例如,有一则笔记写的是小吏王某善于用刑律巧取钱财,但他所得都会被意外耗去,有两个鬼吏盘算着耗去他钱财的方法,其中一个说“一翠云足矣”,后又借道童之口叙述:“但不知翠云为谁,亦不知为谁销算。”紧接着在后文中回答:“俄有小妓翠云至,王某大嬖之。”以此来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由此可看出,纪昀善以第三人之口铺设悬念,后在结尾处设答,以构成情节的不可知与神秘性。另一方面,《阅微》常设开放式结局。《如是我闻》中,吴林塘与僧人关于神明的对话,作者在结尾处说:“当时未闻呼名字,今无可问矣。惟记其语音,似杭州人也。”为营造神秘性,作者以吴林塘儿子之口叙述当时的情形,但未直接提出结论,而是给读者一个模糊的线索,其可能是灵隐寺济公,但不能确定就是济公,作者刻意提供线索,营造开放式的结尾,使读者主动思考结局,目的是使叙述保证真实性。这种叙述风格能够使读者进入作者虚构的意象中,并在脑海中构建故事图景,这其实是作者提前预设好的结论,所以说,神秘性是作者本人构筑的。
第二,在叙述中形成“共同隐含作者”,从而达成伦理转向。“隐含作者是体现文本意义——价值的‘拟人格’。”[8]221也就是说,作者有意将自己隔绝在文本之外,却在文本中构筑了一个隐含作者,布斯认为,“‘隐含作者’会为读者选择需要阅读的内容,这种选择可能无心,可能有意,而读者也会理所当然地将作者视为理想的、文学化的人,它体现着真实作者的另一面”[9]。《滦阳消夏录》卷首:“昼长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体例。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为达“劝惩”的目的,作者用其“第二人格”来代替主观人格进行伦理教化。例如,《滦阳消夏录》卷一:“一身之穷达,当安命,不安命则奔竞排轧,无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桧,即不倾陷善类,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借道士之口表达作者的教化思想,形成这一篇中的隐形作者。作者将自己的伦理观念借由文本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进行表达,这类人物承担的是“共同隐形作者”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其实是作者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
第三,为追求真相以达到虚构叙述文本与经验世界的二度区隔。布鲁纳认为:“逻辑或者是科学的建构可以被证伪,故可以证实,可能世界和实在世界的关系,可以证伪。但是虚构世界却不可以被证伪,因此所叙述的事件也不能被证实。”[10](注:笔者译)虚构叙述不能证实,这与纪昀表达的形式虚构、内容真实恰好相反,所以纪昀通过各种手段尽可能达到真实叙述。比如,不论是人物或者是情节,都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叙事,显得故事素材更真实。纪昀并不会使用“我看见”“我听闻”等词汇,而是采用“某县的县吏某某说”。“无论是作者自叙或转述他人见闻,都明确标明故事亲历者或讲述者的真实姓名,这些亲历者或讲述者大多为作者亲友,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真实人物,作者此举的用意无非是想表明书之所录皆真实无妄、信而有证。”[11]以这种叙述方法叙事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真实性,却也使读者和文本之间形成区隔。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纪昀采取了一定的叙述方法,其基本内涵如下:
作者先主观分化出一个人格充当事件的叙述者,叙述者通常承担的是将经验世界向虚构世界转化的功能,这是读者与文本间的“一度区隔”,将现实世界与虚构文本区分。这种叙述方法必然会导致虚构文本的信息发出而未被接收,所以作者需要再分化一个人格充当信息的接收者,而接收者对于叙述者的信息接收是读者与文本间的“二度区隔”。“二度区隔”并没有将读者与文本、作者进一步割裂,相反,它增加了文本的真实性,“二度再现的目的,是有意误导读者,让他们觉得二度世界与一度叙述的世界没有区别”[8]76。纪昀通过营造文本中人物的不知,使读者反思自身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再以文本中人物的结局或者他人对人物的讽刺来警示读者,使读者达成反思、向善,从而误导读者,让其认为他就是文本中的人物,以达到作者写作的真实目的。
作者充分利用了读者的心理,而读者之所以会陷入二度区隔的陷阱,根源是因为其“不知”心理,因为“不知”,所以会恐惧;因为恐惧,所以会约束行为,从而按照纪昀所传达的价值观约束自身,所以二度区隔理论在纪昀文本中的使用是至关重要的。
综上所述,人们排斥通俗文学,通常是因为文人的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纪昀实践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虽然多被诟病,但却不伤大雅。《阅微》虽然是一部描写生活琐事、宣传伦理道德的文学作品,却在内容与结构上有着独特之处,推动了笔记体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