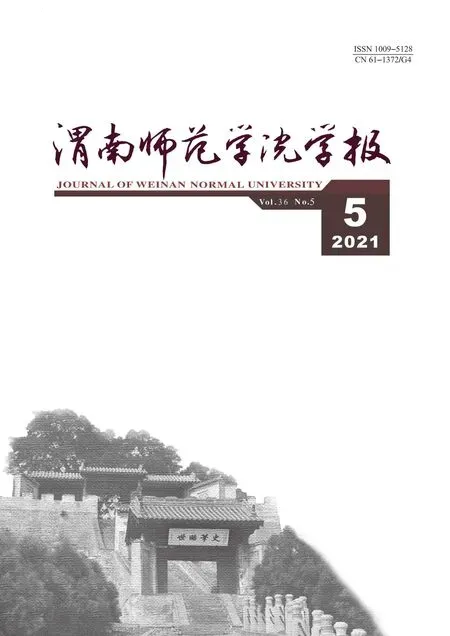论儿童游戏空间的同辈文化生产与再生产
田力力,梁燕玲
(渭南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空间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儿童游戏空间是同辈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同辈文化又来源于儿童群体的日常游戏互动。正如亨利·列斐伏尔所提出的著名空间生产理论,空间并不是静止的“容器”,而是社会历史文化实践的产物,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等特点。作为儿童同辈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场域——游戏空间亦是如此,它承载着同辈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内在逻辑。因此,文章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探寻游戏空间中儿童同辈文化的基本属性,揭示同辈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运作方式。
一、儿童游戏空间的新转向
随着人们对传统空间认识观念的转变与演进,空间已不是自然地理学科的专属名词,“空间研究不仅局限于自然地理学研究的尺度,而是综合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研究尺度,强化了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1]。因此,“空间生产”理论革新了人们对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认知,其并不是静态不变的自然空间,而是具有生产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关系社会。
(一)传统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不足
游戏空间是儿童生命成长的特殊形式,对儿童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传统儿童游戏空间研究更多地从规划类、建筑类、设计类和园艺类等学科的角度审视。其实游戏空间应投入丰富的材料以及将不同空间类型组合划分为不同的单元。儿童游戏空间的“三大尺度是幼儿园、居住区和公园,研究的重心在儿童游戏空间的规划、设计和景观改造”“儿童游戏空间的突出特点是关注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自然地理特性”[2]。由此,从传统儿童游戏空间研究来看,儿童游戏空间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游戏空间的生产主体、创造者往往是教师等成人,而非儿童本身。儿童在游戏空间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等待者、外来者,而非真正的游戏主体,其最终的指向是儿童的成人化发展。另一方面,将儿童游戏空间的特点等同于自然地理属性的特点——冰冷、刻板、机械的客观地形之中,即从“人—地(自然)”建立某种联系,将其生硬地、不间断地发生着某种聚合与离散的社会关系,“遮蔽了空间的主观性和社会性,遮蔽了空间与主体、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3]。虽说这类儿童游戏空间研究遵循心理学发展的年龄阶段、特点规律,强调儿童空间的体验感,注重物质材料的投放与精神环境的相衬,但以成人策划与设计,是成人思想、文化制度的再现,忽略了儿童创造性的游戏文化。因此,以成人为生产者的游戏空间,关注物质的生产,潜藏着成人文化的主导权。实质上,这是从传统二元对立的视角将“儿童”与“游戏空间”孤立分开,致使儿童游戏空间成为规训儿童身体和精神的“储存器”,将之塑造为社会需要的个体,游戏空间就成为塑造儿童社会化的文化空间。“自然属性的空间经过特殊的构造之后,能够支撑起隐性的权利机制,伴随着一个明确的在场和缺席体系,可以使这种机制对空间中的个体实施长久的监视与规训。”[4]因此,“空间意识的缺乏使我们很少把环境和人的行为视为一个整体,很少反思到空间本身意味着关系、情感,意味着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更少考虑儿童对周遭的体验和反应。”[5]儿童游戏空间成为“成人化的景观”,其中表达着成人的思想感情,蕴含着特定内涵的成人文化。
(二)现代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新转向
随着“空间研究”的转向,“空间不是一种地理或物理的事实性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表征实践的产物,因而对空间的理解离不开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6]。为了阐释“空间生产论”,亨利·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性”概念,即一种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以空间作为生产对象而进行的生产,社会再生产表现为社会空间的生产,空间生产理论更加关注社会中的冲突和不平等,关注享有文化资源优势的群体如何实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空间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7]48这就意味着空间具有复杂的特性,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集合体,被赋予了比物质更广阔的意义,同时它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空间生产的内在需求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与转换。“空间”成为人的社会经验事实,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实践的产物,在社会关系中不断地被调整与建构。社会关系是空间的本质属性,更加侧重空间的主体意义。空间主体将各种关系联结到一起,这些关系服从于对联结的需要和强制,从而被仪式化、被形式化。“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也要凭借空间中事物的关系才能展示出来。”[8]48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时,这些关系才得以存在,它们把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得以固化,在此过程中也就生产了关系空间。“关系空间从地理空间发生发展,并在空间内部充斥着各色各样的权力关系,还有社会与人能动性的关系。”[4]“空间与地方不是文化的‘容器’或‘载体’,而是意义、价值、 意识形态或文化规范形成以及产生效应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人们不仅给特定的空间或地方赋予了文化意义,且许多价值、规范与身份认同的形成本身蕴涵了对空间或地方的再认识与再定义。”[9]
儿童游戏空间是特殊的空间形式。当儿童以游戏主体身份参与其中,这些关系网需要在游戏空间中巩固、加强与发展。游戏空间中的关系,衬托出种种文化特征,儿童并不是简单地对成人现实生活照镜子似的“模仿”,而是对成人文化的诠释与创新。游戏空间孕育着丰富的儿童社会关系,即“儿童—成人”“儿童—物体”“儿童—儿童”,潜藏着为儿童创造的游戏文化与儿童创造的游戏文化之间的博弈。游戏空间的生产就是儿童同辈游戏群体社会化空间的过程,只有以关系社会为主的游戏空间,才能使儿童游戏空间不断地从自然空间转向人的空间。因此,空间生产理论下的儿童游戏空间研究,不仅立足于内在文化体验的关键性隐喻,而且将群体性文化作为特殊文化实践方式,折射出外在的文化表征深意。
二、游戏空间的基本属性
游戏空间是儿童同辈群体文化的产物,是儿童在与社会文化不断的互动中形成的。“正是由于人类在生产、生活结成各种社会关系作用于实体空间,而使实体空间具有社会性,形成社会空间。”[10]那么,在日常游戏中,儿童与成人、同伴等群体的互动关系作用中,使其空间社会化。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产物,游戏空间就像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许多儿童社会文化生活与变化的棱角。
(一)生产属性
“双主体关系、游戏关系、两界关系是儿童游戏空间的本质。”[11]我们必须关注游戏空间中客观实物与儿童是一种双生生产关系。儿童与他者的关联,不仅体现在空间中物质文化的塑造,同时也通过儿童自身所携带的文化性塑造着空间本身。“‘空间实践’,即空间性生产,指特定的社会空间中人们实践活动的发生方式。”[12]如儿童游乐园不仅内容丰富、气氛热闹,儿童之间的打趣、嬉戏、互动都会发生在其中,而且还有不合、冲突、评价、信息的交流与外来参与者的矛盾等,成员之间缺少互动。游戏空间物质便利的无对象性、场所的无障碍性、空间使用的无排他性,使其产生了某种稳定的交往关系,发生在儿童的集体决策,对这个地方赋予了意义,产生了地方感,诸如共享、合作、冲突、和解等。因此,使儿童之间的关系得到调解。换言之,被调解的关系,再生产了关系社会。儿童的同辈关系安排有序,有明确的组织结构。这种关系是一种参与社会行动形式,置身于儿童选择、参与到游戏空间与社会文化制度的变式中,进而具有了一定的秩序感。可以说,这是儿童游戏不断探索和确证自我生存方式的过程,势必会引起儿童如何探索、运作周边的社会关系网。自我的产生是关系社会的结果,意味着个体在群体内的互动与他者的合作。“自我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并非与生俱来。”[13]152因此,作为社会实体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必须把它当作整个社会系统的组成要素,只有个体通过社会关系才能产生新的自我。
(二)文化属性
游戏空间中环境布置、材料罗列组合、呈现方式等,其本身蕴含着物质文化因素,使游戏空间具有文化性。如衣服、书籍、艺术与文字工具、玩具等,以成人文化为核心统领的综合性文化丛,促使参与者进行一定的文化实践。“文化与空间的关联导致文化和人的一定生存方式的一致性,形成了文化认同,文化身份的认同。”[14]由此,儿童遵循成人预设的文化空间社会化,这种单向度的文化空间,简单地将儿童与游戏文化空间割裂,使儿童游戏空间文化序列化,是成人文化生活预演的规训。作为主体儿童,以创造性文化为线索,展开一系列的权力博弈,却恰恰使儿童形成一种“街头智慧”,创造属于自己的游戏文化空间。儿童创造的游戏文化,决定了其游戏文化的价值。“文化空间是人及其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场所,是文化的空间性和空间的文化性统一。”[15]可见儿童游戏空间具有文化性。儿童生产的各类关系表现在话语、行为、需要等一系列的儿童群体文化中。“文化空间生产是指运用文化的象征、想象、意指、隐喻等手段,建构空间文化表征的意义过程。”[16]199即一种文化实践方式。当儿童开始进行游戏时,离不开人类的物质文化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及所使用的符号。自儿童来到这个世界,就会面临周围种种文化系统的影响。人类身体本身带有鲜明的文化烙印,即文化的规定性。因此,儿童进行游戏时必然会携带一种文化活动。“儿童自己创造的游戏文化,它属于儿童这个群体,更多能体现他们自己的能力、情趣和审美。”[16]31
综上,儿童游戏空间是儿童群体文化的产物。游戏空间不仅是物质文化的集合体,更是儿童关系社会中表征的文化空间,儿童以兴趣、需要、话语、行为、价值观念等为中心进行着一系列的“空间化的文化实践,实现社会化的空间实践”[17]。
三、游戏空间中儿童同辈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
同辈文化是儿童游戏文化存在的基本样式。“同辈文化是由儿童与其同辈互动过程中创造并共享的一系列相互稳定活动或常规、产品、价值与利益关切。”[18]112具有集体性、公共性、行动属性、凝聚力等特征。科萨罗提出的“阐释性再构”理论为我们理解游戏空间中儿童同辈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理论尤为关注日常游戏中同辈之间所创造的文化。阐释性再构是“儿童创造性的习得了成人世界资讯的过程”[18]3。“阐释性再构抓住了儿童社会参与中的创新(Innovation)与创造(Creative)的特质。”[18]19儿童在参与“重要他者”文化过程中,并不是全部接纳,而是不断选择、革新,从而整合成属于自我群体特色的文化。因此,从例行化与区域化的维度分析游戏空间中同辈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机制,对我们理解同辈文化如何被个体生产与集体性再生产具有指导意义。
(一)例行化的游戏空间与同辈个体的初次生产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儿童都默默地沉浸于被既定的游戏空间,同辈文化不是在被动的观念中生产出来,也不是所有的儿童都会按照例行化的游戏空间顺利完成生命周期中的游戏行为,有相当部分儿童会因为无法参与到游戏空间中而陷入“问题情境”。“以实践意识为基础的例行化概念是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中的关键所在。”[19]133儿童游戏行为的发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并没有刻意去谋划与计算。
如强强和勇勇正在幼儿园沙坑区玩塑造城堡游戏,琦琦小朋友也想加入,但得到了否定。(1)资料来源于某市某幼儿园沙坑游戏活动。
此时的琦琦由于未加入到同伴的游戏空间中,遭遇到了“问题情境”。当儿童来到这个世界中,首先面对的社会群体是家庭成员,儿童会潜移默化地遭遇来自家庭中“他者”文化的权威与规定。“儿童对自己早年在家庭中获得安全感的‘维持努力’,是他们同辈文化形成的基础。这种‘维持努力’也是儿童在评估他们同辈文化与友谊关系中的参与和共享时的重要因素。”[18]36因此,已在游戏空间中的儿童会形成一种“维持努力”感,从而会共同抵抗其他参与者的加入。其儿童互动过程可能被多种因素打断,游戏者希望维持对游戏空间的控制。这种“维持努力”明确了“儿童—其他者”的关系,界定了游戏空间所有权。儿童所形成的游戏空间是不允许任何人侵犯的,儿童会用语言声明哪些地方是共享的,哪些是禁区。“作为文化的基础,最重要的符号就是语言,语言也是阐释性再构理论强调文化形成的关键。”[20]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儿童已将游戏空间的所有权固化,实际上是儿童掌握了游戏空间的控制权,儿童陷入了紧迫与不安感的“紧要情境”,游戏空间的结构内隐着紧张、兴奋。当儿童迈入初始同辈文化时,面对的信息都是预先经过成人调整、规划好的,儿童总是持之以恒地试图掌控自己的生活,并且与同伴分享这种“掌控”。
儿童作为社会积极能动的社会革新者,他们在既定的文化规则中会进行二次调整,最重要的关切是抵制和挑战成人文化的权威,赢得对成人规则的控制。
如:琦琦在一旁观察,并没有空手闲着,而是朝向沙坑的另一边,边走边绕。琦琦看了强强几秒后,说道:“我们是朋友,对吧?”强强并没有抬头看琦琦一眼,而是继续塑造城堡的顶部,犹豫了一会儿淡然地回答:“是的。”听闻强强这样的回答,琦琦进一步走近强强,拿起另外一个铲子,往铲车上装沙子,并向强强说:“你们周围的沙子不够用,我这有很多沙子,我来给你们运沙子。”强强于是转向勇勇说:“我们三个都是建造师,对吧?”“对”,勇勇回答道。三个孩子一起继续玩了大约15 min,直到教师宣布游戏结束。
从成人的角度分析,看似儿童拒绝其他玩伴的行为是自私的,但其实质是为控制分享游戏空间所维持的努力。被拒绝的琦琦,并没有放弃参与其中,而是伴有复杂的语言和一系列准入策略。值得注意的是,琦琦第一次被拒绝所遭遇“问题情境”后,琦琦的准入努力首先是非语言性的,琦琦单纯地站着并观察着;其次是环绕勘探,在没有获得回应的情况下,琦琦继续观察,并围绕沙坑走动;最后是适时介入,重新界定游戏情境,调整游戏空间结构,琦琦看似熟练、得心应手地做动作。琦琦的准入努力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策略使用。尽管琦琦的准入策略堪称成功,但一开始也遭遇了拒绝,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而是更多地观察,并选择再次进入游戏空间参与互动,明确使用了语言表达情感关系。强强的回应看似正面,但并没有公开邀请琦琦一起共享游戏空间,琦琦于是重复之前的策略,看似老练地做出该游戏的动作,并用语言明确告诉强强他在做什么。这次,强强以准入的方式回应琦琦,告诉琦琦他需要一些沙子继续塑造城堡。强强进一步界定新的游戏情境,说:“我们三个都是建造师,对吧?”而这一点,得到了勇勇的肯定。可知,当儿童进入到游戏空间时,他们会监控反思自己的行动,使之符合社会秩序,生产出同辈文化之间的利益关切,这种利益关切是不断地调整与改革。
(二)区域化的游戏空间与同辈集体性再生产
吉登斯从区域化探讨共同在场情境下的互动如何在时空维度延展,对于我们分析游戏空间中同辈文化的再生产具有重要的启示。前文中,琦琦和强强、勇勇同时陷入了“问题情境”,且在反思性监控中实现了同辈文化的初次生产。家庭作为高度情境化的共同场所,行动者会受到家庭成员中各种文化规则的约束与限制。同辈文化的兴起与发展,其重要特点是儿童在尝试理解和不同程度地抵制成人世界过程中形成的。因此,这也就是琦琦和游戏空间中强强、勇勇同时陷入“问题困境”中的根本原因。即使他们在游戏空间中共同活动,都会形成专属于自己的区域化游戏空间。区域化游戏空间被安排得全面细致,并不希望任何外来者打断,而琦琦在被拒绝之后,并未放弃游戏空间的准入,适时抓住准入的机会,顺利参与到游戏空间。在互动中,强强和勇勇扮演了“前台”的角色,而被拒绝的琦琦通过“后台”进入到游戏空间。区域化的游戏空间,引起了同辈集体的价值利益关切。如当第三方想加入游戏空间时,被拒绝的第三方以及已在游戏空间中的儿童陷入“问题情境”,都会引起他们集体性的反思。而同辈群体的集体性反思实现了儿童同辈文化的再生产。因此,从儿童游戏空间的实践过程可以探析出同辈文化在游戏空间中经历了四个阶段的生产与再生产。第一阶段是游戏空间控制与保护。琦琦以第三方的身份试图加入游戏空间,却遭到了游戏空间中其他同辈的拒绝,而同辈群体为了保护游戏空间已有的结构,掌握了游戏空间权,进而生产了同辈文化的利益关切意识。第二阶段是游戏空间遭遇的压力感与情境冲突的生产。首先,被陷入“问题情境”的琦琦遭遇同辈群体的拒绝;其次,由于琦琦作为第三方的准入,使游戏空间中其他同辈群体生产了“维持努力”的不安感与焦虑感的“紧要情境”,进而增加了琦琦与游戏空间中其他同辈群体关系的紧张。因此,这就使被拒绝方与拒绝方同时陷入冲突的情境,引起了游戏空间中同辈群体的不安与集体性反思。简单地说,儿童期望他们正在分享的玩具、媒介等不被其他人打扰,甚至将其他人的参与、加入看作是对游戏空间的威胁。第三阶段是游戏空间结构调整、分享过程。在游戏互动中实际再生产了一种共享意识(即对游戏空间的控制),儿童将这种共享意识理解为某种归属感。(“我们是朋友,对吧?”)不过,被拒绝的儿童希望坚持加入其中,并成为共享游戏空间的一员。由于持续不断的准入遭遇拒绝,大多数儿童会在挑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套复杂的准入策略。如琦琦一系列准入策略生产成功地加入了游戏空间,得到了同辈们的准许与分享,进而重新界定游戏空间的结构,再生产了游戏空间。第四阶段是同辈文化的自我认同、分化的再生产。从琦琦的游戏策略准入失败来看,使得那些被规则化的成人游戏文化被不断地调整与修改,并通过集体的反思性卷入游戏互动中。如琦琦被拒绝后生产一系列准入策略,实现了儿童同辈文化的自我认同感,进而实现了被成人规定的文化规则被分化。
当儿童及同伴在参与游戏空间中习得了准入策略,这些准入策略是他们今后迈入成年生活的基础。对于儿童而言,通过第三方玩伴准入策略的参与,朋友不再是特定“儿童”的标签,儿童开始意识到有一些东西是共同拥有、共享的。因此,友谊观随之发生改变,是儿童在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与同辈文化之间的集体建构。将友谊观看作是集体性同辈文化再生产,按照这种观点,文化不但影响儿童如何交友、如何成为他人朋友的变量,而且友谊建构深深地根植于儿童对他们周遭文化的阐释再构之中。从被成人标签为特定的儿童,转向可观测的共享游戏空间的事物,积极利用并拓展了儿童—成人之间的关系中获得了社会认知。在游戏空间中,儿童逐渐认识到他们可以自由经营、主导、控制游戏空间,在准入、协商后决定谁可以共享游戏空间,并不断建构他们自身的社会身份,这样的参与将同辈文化进行了分化,进而生产出新的同龄群体文化空间。因此,儿童游戏空间不仅仅蕴含着控制、冲突,共享与分化的再生产机制,它还隐藏着儿童同辈文化共同行事的内在逻辑。
四、结语
儿童游戏空间作为生产与再生产同辈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儿童确证自我身份的重要场域,它记录着同辈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创造与繁荣、传播与演进。同辈文化是动态持续发展与革新的,同时也为儿童开启了他们在自己文化中建立成员资格的过程。正是同辈文化的能动性,需要我们关注儿童游戏互动的过程而非结果,这样才能为同辈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提供一定的条件和机会。同辈文化空间是儿童这一游戏群体在同辈范围内所生产与再生产的,能够让同辈文化具有再生产的功能。由此,只有当我们欣然接受了儿童在游戏空间中创造的“大同”和“小异”同辈文化,放弃对儿童群体文化的忽视、侵略,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儿童改革、创新文化图谱中细致的纹理,才能在平等和谦逊中审视同辈文化的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