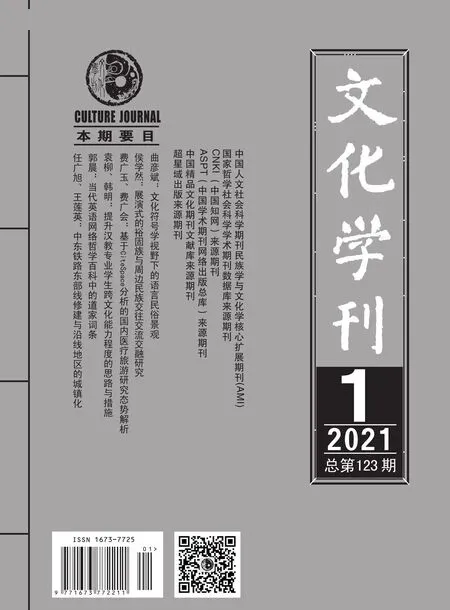机械和诗意:论郑小琼诗歌的工业与自然
成之珍
出生于1980年的郑小琼,是中国第三代“打工诗人”,她于2001年南下广东省开始打工生涯,曾在家具厂、五金工厂做过流水线工人、仓库工、业务员等。诗歌创作是她贫苦艰辛的打工生活中主要的乐趣。2005年,郑小琼开始在各刊物上发表诗歌,作为“打工诗人”,她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十几年来,国内对郑小琼诗歌的研究热度虽然不高,但也不乏研究成果。现有研究郑小琼诗歌的论文达百余篇,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创作论,研究其诗歌生产机制和写作姿态;二是研究诗歌主题,如身体书写、工业主题、劳动主题、苦难叙事、生命主题等;三是对诗歌意象的研究及阐释。作为底层劳动者和诗人,郑小琼的诗歌不是对厂区劳作和生活细节的铺叙,她的诗歌具有悲剧性,既有俯瞰时代的深度,又极具抒情力量。郑小琼诗歌中不乏现代工业符号,如钻孔机、气压机;同时还有诸多温情的自然意象,如月亮、旷野、星星……工业机器的冰冷与自然意象的清丽产生巨大的诗歌张力,融合巧妙,毫无突兀之意,有一种属于当今时代的悲悯诗意。
一、对工具理性的反抗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文明的最主要特征是理性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物质和金钱成为人们的追求,于是工具理性走向极端化。工业文明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运行机制之一后,人与物、土地、劳动的关系开始变化,工厂机制使作为劳动力的人们逐渐被专业化、职业化、功能化,流水线上的工人每天重复简单机械的操作,工具理性化的衡量标准不再聚焦人本身,而是功能、效率。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打工者,指的是从各地前往经济发达地区的务工人员。20世纪90年代,“打工文学”就已经出现了,一批在生产一线进行文学创作的“打工诗人”也于21世纪进入人们的视野,郑小琼便是其中之一。与其他诗人的工业叙事诗歌不同,“打工诗人”的诗歌创作具有自我体验和超体验双重视角。郑小琼在谈论自己的诗歌写作时说道,要坚持在打工现场写作,这不仅是在亲身体验基础上的书写,同时还是超越现场的,鸟瞰整个工业社会去思考、审视生命与时代。
艾伦·退特(Allen Tate)在定义张力时认为:“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1]他将外展解释为“指称意义”,将内包解释为“情感意义”,当具有对立关系的语汇、意象组合在一起,会产生十分强大的张力效果,其中互斥的形象可能具有共通的情感色彩。郑小琼的诗歌中,工业和自然两个概念是冲突和摩擦的,但它们又在某个维度上表现出情感、意蕴的一致性,在表达对工具理性的反抗上面,工业意象和自然意象的对立张力以及进而释放的残酷的诗意尤为突出。
诗歌《月亮冲向雾中的气压机》,标题中有三个意象,即“月亮”“雾”和“气压机”,这三个意象营造了一种极具冲突的视觉氛围。“气压机”所代表的冰冷机械的生产工具和天然、柔和的“月”“雾”所代表的自然天气意象形成一组概念互斥的关系。材料、工具象征着工业文明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示自然绿化的退化和让渡。因而在这一语境中,工业和自然无法达到和谐的共存。诗歌的第三节:
黝黑的机台推动野天鹅的脖子,嘶嘶——
它的哀鸣在孤独的车间模仿七月的郊野
异乡之花盛开在黑机油与碎料机之间
红褐色的铁锈迹围着忧郁的蕊,白墙与
铁丝网囚禁的夏日,飞鸟从机台上逋逃
切断的铁块在冷却液里安栖,疼痛在凝固[2]279
“机台”和“野天鹅”互相挤压、撕扯,释放出极具破坏力的痛苦情感。天鹅的“哀鸣”和“车间”的作业声,“花”“机油”和“碎料机”,“铁锈”和“蕊”,“飞鸟”与“机台”……短短六行就有四组对比强烈的意象组合,充分表现了工业化机床、流水线、生产车间对自然生命的扼杀。工业意象对自然动植物意象的扼杀,实质上是工具理性对个体人性的消磨。在工厂的生产车间里,每个个体是以劳动力的形式存在,他们重复简单机械的操作,只是快速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工厂劳动把人们工具化、功能化,一个人的全部价值仅能体现在他的功能理性之中,打工者不再被关注其作为人的实体,而只被关注其功能、劳动价值。工具理性追求效率,在这个宗旨之下,每一个鲜活而个性的生命被固定的工作时间制造成一模一样的工作“机器”,和车间里的那些无生命的机台、车床、冷却液一样,留下的只有功能价值。
在工厂生产机制中,人们的价值、情感甚至尊严逐渐被剥离。在郑小琼的诗歌中,“月亮”隐喻遥不可及的纯粹,“野天鹅”隐喻高洁与自由,“鸬鹚”隐喻勇猛的生命力,这些自然意象的内涵或感性意义都表现了生命固有的属性,即纯粹、自由和鲜活,但这些“生命”的、自然的东西都被切割、被扼杀了。郑小琼把两组意象置于“杀”与“被杀”两个对立地位,哪一方是当权者显而易见,然而,这个“杀”的动作却保持着进行状态,并没有结束,也没有出现自然意象的死亡。如《工艺品》中:“将它从一棵树、一块矿石变成艺术的幻想/用日本的道具削出它们的风雨、滴露、阳光。”[2]277自然不会被消灭,自然在被定义,用艺术之名定义自然事物,这隐喻工厂生产机制以工作的功能价值定义打工者个体,不断打磨个体生命原本的独特性,逐渐将其同质化、功能化、工具理性化。
在《从生活》中,诗人将生命的流逝视作“安静地航行”“你手指间的螺母正拧紧孤独的金属片/覆盖着冷霜、月光、青春以及生活的真相”[2]284。由此可见,“螺母”“金属片”等一个个零件成为碾碎生活本质的工具。自然的“冷霜”“月光”早已与疲惫的打工者无关,正值青春的生命与对生活的热情也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劳动中被消磨殆尽。
工业符号“铁”隐喻工业文明社会体制和话语权力,一方面,工业建设破坏了生态资源;另一方面,工厂制度消磨了打工者的斗志。这种无休止的工业建设对自然、个人的“暴力”被掩盖在了现代机制和工业话语体系之中。
二、何以为“家”的阵痛
郑小琼曾谈到:“乡村是脆弱的,柔软的,像泥土一样,铁常常以它的坚硬与冷冰切割着乡村,乡村便会疼痛。”[3]郑小琼于2001年离开故乡南下广东省打工,何处是“家园”是她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探寻的主题之一。工厂的生活切割着郑小琼,工业城市的建设同样也切割着乡村。
打工者从农村到城市务工、生活,却始终无法融入城市。除了户口簿上的类型区分,这类人群更多的焦虑在于没有归属感,以及对于故土的依恋。打工者漂泊在工业城市,城市生活和工厂劳作是一种祛乡土的文化[4],背井离乡的打工者渴望在城市重新安家,而现实是城市中的一切都无法接纳他们,他们也无法获得身份认同,只能在异乡苦苦挣扎着。“打工诗人”郑小琼首先是一个在场的打工者,其次是在场的书写者,在她的诗歌里,对漂泊异乡和身份的焦虑,在工业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之间不断拉扯着。《针孔里的远方》集中呈现了这种思乡情结与工厂麻木疲惫的生活之间的矛盾。
祠堂旁嬉戏的孩童,小贩推着三轮车
穿越荔枝林与寒溪铁桥,一小片菜地
…………
我从一枚螺丝,一张订单上感受万物
如此紧密的联系,却又彼此孤立
…………
走向遥远的陌生人,穿越针孔样的
生活之门,小小的卡座,来不及开始
便分别的爱情,明月样的孤独、乡愁
异乡的迷茫,有时订单和机台会向我
谈论远方陌生的世界,像在四川乡下
他们谈论广东的工厂、风景、大海
我倾听却不心动,唯有停止工作的针孔
带来一片小小的安静,让我欢欣[2]288-289
车间里不停歇的针孔下,有远方的人、远方的爱情、远方的生活,而那些遥不可及的是远方的家园。“针孔”和“明月”这组意象十分有趣,它们同样是圆形的,一近一远,针孔之下是低头疲惫工作,抬头却看不到夜空里的明月,而想象中故乡的月引起了乡愁,使人感到孤独。在此处,工业与自然不再是完全互斥、对立,而是既交融又离析。作为打工者,眼前只有无休止的工业机器、机台和做不完的订单,而故乡四川却和订单上的地址一样遥远,可望而不可即。工业此时不仅是冰冷的铁床,它带来一丝遐想,带来梦中家园的气息,然而诗人却十分冷静,她知道这些都是身处异乡的幻想。广东不是她的家园,她在这里无法产生憧憬、向往和归属感。
这首诗明确提及了郑小琼的故乡——四川省南充市的乡下。郑小琼在广东省的工厂里打工,无法回到自然的村庄,“荔枝林”作为南方特色的植物,并不能吸引她。人一旦离开故土、离开长期居住的地方,将会产生某种和土地的断裂感,这是恋地情结的影响,因此当诗人的精力几乎被工厂机制消磨殆尽时,脑海里自然而然生发出对故土的眷恋,这是她作为自然人在如此高压、高强度的淬炼之下仍然完整保留的天性。
雅各布逊认为具有诗性功能的语言是自我指涉。好的诗歌不指涉外界,更多的是对自我的指涉,对内在体验的指涉。郑小琼在书写工业时代的汗水和泪水时,不以上帝视角旁观,也不挞伐城市,她更多的是在探寻内心世界的焦虑,一方面对城市的祛乡土文化感到迷茫,另一方面对在城市务工而无法获得身份认同感到痛苦,她指涉的是作为一个流水线上的打工者的漂泊体验。郑小琼在诗歌《火车》《生活》中都写下了在工业与自然之间的挣扎,在都市与乡村之间撕扯的痛感。
我的体内收藏一个辽阔的原野,一列火车
正从它上面经过,而秋天正在深处
辛凉的暮色里,我跟随火车
辗转迁徙,在空旷的郊野种下一千棵山楂树
…………
远近的山头站着衣裳褴褛的树木,散淡的不真实的影子
…………
(《火车》)
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
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
…………
安慰一颗孱弱的灵魂,如果月光来自于四川
那么青春被回忆点亮,却熄灭在一周七天的流水线间
…………
(《生活》)
诗人在《火车》中,运用“原野”隐喻内心。山楂树主要分布在北方,和诗人“南下”相对。“火车”是离家的交通工具,在此处代表生命的历程。诗人离开四川省去到广东省,把家园和亲朋留在了身后的北方,在辽阔的内心世界中,属于故土的回忆越来越遥远、模糊。在这首诗中,工业没有直接出现,似乎只有自然的隐喻,事实上,工业在这里是半隐藏状态,这列经过原野的“火车”正是通往现代社会工业制度的,通往充满钢与铁的城市。现代社会的工业制度与城市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然而属于工业制度的一部分的打工者却无法属于城市。正如《生活》中“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异乡人的孤独与痛苦在于身体被机床与螺丝钉捆绑,而精神却飘浮在城市上空,寻不到落脚之处。打工者无法离开现代社会的工业制度,他们需要以劳动换取薪水来维持生计,他们的一念乡愁——来自“四川”的“月光”还来不及停留,就因“流水线”而“熄灭”,这都是郑小琼对自我内心的指涉,“山头”“暮色”是她每日所见的风景,也是她内心关于家园的记忆。
在郑小琼的诗歌中,四川省既是故土,又是唯一的“家园”,广东省是她工作的城市,无法被她视作家园。同样,城市无法从身份上接纳打工者。这种身体离开故土,精神却无法迁移的撕扯感,让每一位疲惫而孱弱的灵魂只能在漫长时间里,通过一颗颗钉子、一块块铁块,感受生命的活着状态。
三、淬炼主体的诗意
郑小琼在《在电子厂》写道:“对于这些在无声中活着的人/我们保持着古老的悲悯,却无法改变/时代对他们无声的冷漠与嘲讽。”在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郑小琼也在对自我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进行书写和反思。她曾说,自己诗歌写作要坚持在工业流水线,要将自己置于大环境中,去探寻更加自由的写作,去呈现个体对世界的感受。海德格尔指出:“在作诗着和运思着的人类本质中,走近人之本质,在一个惟一的位置那里达到人之本质,而在这个位置上,人诗意的漫游已经获得了宁静,为的是在这里把一切都保藏人追忆之中。”[5]诗歌创作是诗人以主体性对世界的审美观照,郑小琼在工业时代进行“打工诗歌”创作是将自我的主体性投射在世界,在书写过程中淬炼自我主体性,指涉自我内在感觉体验的过程。
在诗歌《诗艺》中,郑小琼实践了“在场性”写作,这是非常直接地将工厂工作与诗歌创作动机的关系剖析出来的一个作品。
液压机笨拙的喘息仿佛我诗歌的节奏
沉重的力沿词语降落,直至把铁块的现实
砸出诗的形状,把诗艺编进机床的程序间
车床滑杆进退回转,语言的车刀雕刻[2]285
郑小琼的诗歌产生于生产车间的每一次操作,每个动作带来的体验和情绪化成当下的诗绪、诗意。工业意象所产生的冰冷情感,在郑小琼的词语库中不断变化。在《诗艺》中,“沉重”“笨拙”的液压机、机床不再破坏人本有的情绪,恰恰相反,它们激发出了这种即刻的诗情。加缪的“荒诞哲学”认为,当个体直面世界的变幻无常,面对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产生主观体验时,激情就生发出来。郑小琼在这里描述的诗情,就是在这样沉重压抑、冰冷的生产车间里,在铁块的摩擦与重压之下生成的一种“激情”。机械的流水线生产是一种空间极为有限的生活环境,日复一日的车间生活,面对着无数的零件、铁块、液压机,这是极为枯燥的。而人的情感、情绪和思想是无限的,当无限的意识被迫锁在有限的空间和重复的时间里时,这种诗意的“激情”便被激发出来。
郑小琼的诗意转化为“诗艺”,除了高超的对于汉语语言的把握和驾驭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世界和生活的思考引发的诗情。诗人在流水线上的“在场写作”表现了废名诗学中的“当下”。1934年废名在《新诗问答》(后集成《谈新诗》)中强调新诗的“当下性”,它指“每每来自意料之外,即是说当下观物”,诗人写诗时的情绪更多强调个体经验的时间性和主观直觉性。在这一层面,废名提出的新诗的“当下性”是一种既结合了物理时间的时刻性,又结合了心理情绪性的概念。在工业生产的当下,诗人思考自己的诗情如何产生。在钢铁的碰撞之间,在自然和工业的摩擦之间,在人的主体性逐渐被生产车间挤压和打磨之间,诗人对工业时代的反思和反抗就产生了。
郑小琼身处工业文明的核心之处,她就是巨大时代齿轮中的一颗钉子,被裹挟着前行,而写诗让她在工业的核心腹部切开一道口子,窥探它真实的内涵,从而观察、审视当今时代和世界。在单调的工作中,许多“打工者”的情绪和思考会被冲刷掉,身心的疲惫和麻痹容易摧毁人的意志,而诗人在此时必须保持清醒,冷静地想和写。这是郑小琼作为“打工诗人”在场写作的一个重要特质。在车间里、在机床前,工作要求郑小琼成为“钉子”,但同时,她内心仍然抱有“羽毛”般的轻盈与自然,这是诗人抓住瞬间的诗情所需要的一种情感上的敏锐。在高强度劳动中,诗人不断在工业的枷锁中逃往自然的自由的思想,诗歌的技艺在“淬炼着诗的杂质”,实际上,是诗歌本体不断淬炼着作为主体的人的意志、思想,这些意识和思考再经历词语的淬炼便成为诗歌。
工业与自然的不断对抗和撕扯,迫使诗人成为二者之间争夺的对象。一方面,作为工业社会的劳动力,郑小琼迫切需要这份工作,这份工作和经历也使她时时刻刻思考着、书写着时代的痼疾;另一方面,作为胸中有诗情、笔尖有诗意的“打工诗人”,郑小琼担负着书写被时代淹没的声音的责任。郑小琼曾写道:“我用一枚钉子,一根羽毛缝补破碎的天空。”[2]278天空何以破碎,是有着自由思想意志的主体,内心逐渐被生产工具切割破碎,而诗人在这里用手中的“钉子”在工厂务工谋生,用“羽毛”(即对自然和生命的渴望)去缝补破碎的裂缝。正如江腊生所说:“关键在于作家以虚静之心来面对喧嚣的一切,将自己与生存的现场保持一定的距离,使自己的身心能够在诸多事件之间往来穿梭,最后跳出世俗的生存状态,拷问人性的复杂与深邃。”[6]郑小琼不仅以诗歌书写表现生活的文学,更凭借敏感、虚静的美学心态,对工业社会进行审视。在她的诗歌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丰厚的文学意蕴、底层劳工的心声,更是一个鲜活的、有着深刻思想的生命对工业机制、自身所处时代环境以及自然与工业关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