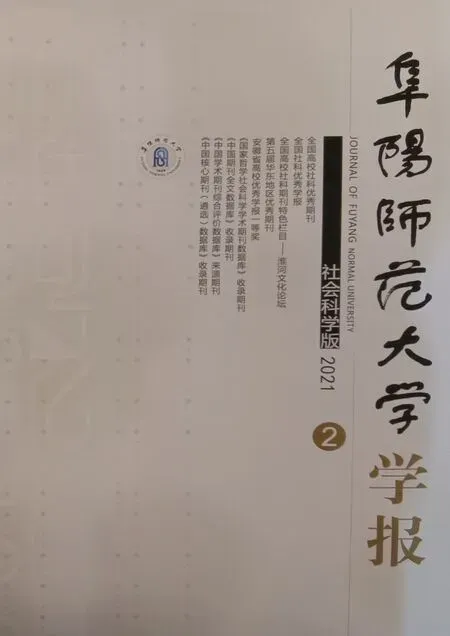绿色探索语境下安德鲁·马维尔的生态思想探析——以《花园》一诗为例
王 卓
绿色探索语境下安德鲁·马维尔的生态思想探析——以《花园》一诗为例
王 卓
(阜阳师范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维尔被评论家赞誉为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伟大诗人,他将16世纪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爱情诗中的浪漫主义情调和18世纪古典主义的理性艺术相融合,他的诗歌跨越了两个时代,标志着从文艺复兴后期向古典主义的过渡。本文以《花园》一诗为例,通过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艺术与自然等维度分析马维尔诗歌中蕴含的自然观和生态意识,旨在解读马维尔前瞻性的生态诗学思想及其在英国生态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奠基作用。
安德鲁·马维尔;绿色;生态;花园
在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当中,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的名气虽比不上玄学派领军约翰·邓恩,但当属该诗歌流派中具有鲜明风格特色的一位代表。玄学诗歌在17世纪繁荣兴盛,在18和19世纪备受忽视和冷落,马维尔的诗集在刚出版时也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随着20世纪玄学诗歌的复苏和玄学诗人从历史的尘封中重见天日,马维尔作为其中的一员逐渐引起公众的关注,其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才被人们所挖掘和赏识,特别是诗歌营造的优美意境及其散发的清新的自然气息和生态意蕴,历久弥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
马维尔一生中诗作数量不多,一共60首左右,而其中脍炙人口的诗歌不过早期创作的三四首,其中《致他娇羞的女友》和《花园》为最著名的两首代表诗作。这两首诗歌无论从主题、内容,还是从结构、形式上,都体现了马维尔独特的艺术风格与玄学才智,是他跨越“抒情诗风”与“理性时代”两个诗歌潮流的标志,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更值得一提的是,诗歌中花草树木、山川溪流等一系列自然意象不仅具有文学层面的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既勾勒了17世纪英国文艺复兴晚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也反映了马维尔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艺术与自然等关系的思考,对英国生态文学的发展具有前瞻性的启示。
一、花园境界——人的理想世界
马维尔“不但继承了伊丽莎白时代爱情诗中的浪漫主义传统,成为一位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而且开启了18世纪古典主义的‘理性时代’”[1]246,因而,马维尔的作品更具特色。他的诗歌诙谐、优美、浪漫,又不乏理性的哲理风格,为17世纪英国玄学诗歌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和生机。
《花园》是马维尔的代表诗作,该诗意象生动、文字优美、音韵和谐,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学界对该诗有多种阐释,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讲,这首诗反映了马维尔超越时代的生态意识。品读《花园》,犹如漫步在一幅充满田园气息的美丽自然图景中,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诗人用沉思与智慧描绘的生动的心灵画卷,陶醉于那静谧优美、和谐融洽、纯真无邪的自然风光。诚然,这一花园境界是马维尔对现实花园的冥想而产生的,它代表了马维尔向往的理想世界,也是马维尔逃离英国内战(1642-1651)等诸多社会现实,在想象中构建的一个纯粹、美好的世界。
在《花园》开篇,马维尔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婉转地谴责了世俗世界中人们的贪念与虚荣。他认为,世俗社会中人类的很多行为是忙碌且没有意义的,最终只会陷入迷途。很多沽名钓誉之人“不停地劳心劳力”,终日营营,只为获得高官、战功等所谓的胜利,却不懂得享受花园的美景与快乐。马维尔意在说明现实社会中人们为了追求各种功名利禄把大量时间花在狂热的努力上的行为是错误、徒劳的,最终带来的只有身心的疲惫,美丽的花园境界才是人的理想世界,自然界中的草木是神圣、美好的。
人们为赢得棕榈、橡叶或月桂
使自己陷入迷途,何等的无谓,
他们不停地劳心劳力,以便
最终从一草一树取一顶胜利冠,
这顶冠遮荫既短,而且又狭窄,
无异是对他们的劳碌作无言的谴责;
与此同时,一切花,一切树,彼此相联,
正在编制一顶顶晏息的花环。
(杨周翰 译)
马维尔在第一个诗节的第一行便使用了自然界中不同的植物名称来隐喻人类社会不同领域的荣誉,随之用“既短,而且又狭窄”来进一步说明这种功名利禄的徒劳和虚无。从传统意义来说,棕榈编织的“胜利冠”用来奖赏大无畏的勇士,橡叶的“胜利冠”属于杰出的政治家,月桂的“胜利冠”用来嘉奖优秀的诗人,这些世俗社会的“胜利冠”都取自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树”。“胜利冠”是现实社会人们为之追逐的荣誉和胜利的象征,此处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马维尔通过这些植物编织的“胜利冠”意象一方面表达了对大自然中植物生命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传递了“一切花,一切树,彼此相联”整体联系的生态意识。
尽管马维尔并未提出任何的生态理论,在当时也并不懂得后人定义的生态主义,但在字里行间已经鲜明地流露了前瞻性的生态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马维尔肯定了自然的地位,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一切花,一切树,彼此相联”,共同为人类营造一个休憩身心的自然花园。“生态文学的核心思想是生态整体主义。”[2]58马维尔正是体现了这种生态的审美价值观念,他否定了人类自我中心论,反对人类把自己摆在与自然相脱离或对立的地位,强调在整个生态系统内部,个体之间是相互联系且地位平等的,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些思想在当时的年代无疑是进步的、超前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为后来英国生态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启示。
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让马维尔选择了逃避世俗,在诗歌的意境中创造一个远离纷争与污浊的理想世界。社会现实与人生理想形成了一对张力,这也是清教思想与人文主义张力的体现,马维尔的诗歌不管采取何种形式,这一张力多贯穿诗歌的始终,这首《花园》也不例外。现实世界的腐朽、贪欲与理想花园世界的淳朴、清新形成了强烈对比,这一对比论证强化了马维尔对人生理想世界的追求,从中我们也可以洞察马维尔的社会意识和政治危机感。据考证,《花园》这首诗可能创作于1650—1652年期间或稍前,马维尔经历了1642年和1648年的两次内战,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对内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继续交锋,对外与荷兰、西班牙等外邦作战,在这一时代语境下,马维尔表现出了对政治现实的逃避和对自然理想世界的追求。
在接下来的第二个诗节,马维尔通过“幽独”与“人群”的对比,进一步抒发了对“天真无邪”的大自然的向往。在这里,马维尔发现了“美好的宁静”,一个远离人群的花园境界,仿佛是找到了寻觅已久的恋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和崇拜之情。
美好的“宁静”,我终于在此找到了你,
还有“天真无邪”,你亲爱的女弟!
我久入迷途,一直在忙忙碌碌的
众人之中想和你们相遇。
你们的神圣的草木,在这世界上,
只有在草丛中才能生长;
和这甜美的“幽独”相比的话,
人群只可说是粗鄙、不开化。
(杨周翰 译)
马维尔使用了“美好的、宁静、天真无邪、神圣的、甜美的” 等一系列形容词来描绘他所发现的这一花园境界的“幽独”之美。大自然的圣洁属性与现实社会的“忙忙碌碌、粗鄙、不开化”形成了一对张力,更加突显了马维尔对城市与自然传统认识的颠覆。一般来说,城市是文明的象征,而未开发的自然尚处在“幽独”的状态当中,而马维尔反其道而视“幽独”的自然比喧嚣的人群更开化、文明,认为这种花园境界才是理想的世界。
杨周翰教授认为:“《花园》一诗属于所谓‘牧歌’(pastoral)传统。牧歌近似田园诗。”[3]193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经过文艺复兴和17世纪、18世纪的流行与发展,直到19世纪仍连绵不绝。有的评论家认为20世纪的文艺作品中很多也具有牧歌传统,诗歌、小说等不同文体的文学作品,甚至是不同形式的休闲生活设计和旅游宣传产品都包含牧歌精神,“这些评论家认为牧歌是一种精神的度假,或径称逃避主义”[3]193。
马维尔写《花园》一诗的真正目的可能正是逃避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环境,经历过内战的英格兰失去了以往的平静和快乐,诗人似乎在用一个理想的艺术伊甸园来对抗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花园给人以宁静和遐想,在马维尔看来,现实花园带给人的感官愉悦并不是他真正向往的,他更企盼从现实行动的世界退隐,走进“幽独”的自然花园,获得心灵的愉悦。在17世纪英国诗歌中,花园常被隐喻为人们的沉思之地,特别是诗人们通过花园境界来表达对矛盾、纷繁的社会现象的逃避心绪。对于沉思花园的描述,正是马维尔所向往的生活状态和理想的世界,这与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表达了马维尔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意识。
二、“美丽的绿色”——女人与自然的对比
马维尔众多诗作中有很多属于爱情诗,例如《致他娇羞的女友》,这种爱情诗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基本是男方向女方求爱的诗歌。艾略特曾高度评价《致他娇羞的女友》,称其以巧思见长,意象多样化、多层次,并且以逻辑的三段论法进行创作,融巧思和想像为一体。“回顾文艺复兴初期以来的情诗,好手如云,大多走甜美一路,只有在多恩(邓恩)和马韦尔(马维尔)手里才进入一个从内容到诗艺都不同的境新界。”[4]255在这首诗中,马维尔假想抒情主人公坠入情网,向恋人求爱,表达了对她的无限赞美之情。
……
我的植物般的爱情可以发展,
发展得比那些帝国还寥廓,还缓慢。
我要用一百个年头来赞美
你的眼睛,凝视你的蛾眉;
用二百年来膜拜你的酥胸,
其余部分要用三万个春冬。
每一部分至少要一个时代,
最后的时代才把你的心展开。
只有这样的气派,小姐,才配你,
我的爱的代价也不应比这还低。
(杨周翰 译)
《致他的娇羞的女友》和《花园》是马维尔最著名的两首诗,前者属于爱情诗,后者属于田园诗的范畴。浪漫的爱情与纯美的花园哪个更重要呢?在《花园》的第三、四个诗节,马维尔给出了答案:
不论是白的,还是红的,看来
总不及这美丽的绿色那么可爱。
那些痴愚的情人,像欲火一样
残忍,把女友的名字刻在这些树上。
可叹他们并不知道,也不注意
女友的美岂能和美树相比!
美树啊!我如要伤害你们的树身,
我也只刻你们自己的芳名。
当我们炽热的情欲已经消去,
爱会在这里找到最好的影息地。
……
(杨周翰 译)
接着,在《花园》的第五个诗节,马维尔通过引用两则希腊神话,意在说明当炽热的情爱消失,大自然才是最终的归属。树的美远远胜过女友的美,女友的凡脂俗色无法同美树的绿色相媲美。因此,《致他娇羞的女友》末尾表现的那种狂热与激动的爱欲终于在大自然的花园中找到了“影息地”,在“苹果”“葡萄”“仙桃”“群花”的簇拥下抒情主人公开始享受大自然的曼妙多姿:
我过的这种生活多美妙啊!
成熟的苹果在我头上落下;
一串串甜美的葡萄往我嘴上
挤出像那美酒一般的琼浆;
仙桃,还有那美妙无比的玉桃
自动伸到我手里,无反掌之劳;
走路的时候,我被瓜绊了一跤,
我陷进鲜花,在青草上摔倒。
(杨周翰 译)
在这里,马维尔似乎沉浸于花园带给他的感官享受,流露出了古典的、人文主义的倾向,花园中的植物可以给人带来感官的愉悦,马维尔似乎也未能完全超越世俗的观念,感官享受仍是其追求的目标之一。评论家勒古伊因为本节诗的感官享受描写而把马维尔与19世纪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联系到一起。
本节诗从结构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从内容上马维尔通过圣经隐喻似乎在暗示自然界的花园是现实的花园,在自然界的花园中,人们可以获得感官的享受,但这只是表面和低层次的,人只有通过沉思,精神与自然相通后才能飞向理想的“花园境界”,这才是真正幸福的境界,这种花园境界不是凭理性能到达的,更不是女性的美所能相比的,甚至“有的(评论家)除了认为此诗写幽独之外,强调它表达对女性的憎恨”[3]195。此处,马维尔虽未直接表明对女性的态度,但从“苹果”——“落下”——“摔倒”以及“青草”等的圣经隐喻可以看出他对女性的批判和不满,对“美丽的绿色”的钟爱和颂扬。
三、“绿色思想”——至高的精神境界
马维尔在现实花园中享受感官愉悦的同时,从对自然的直觉感受慢慢过渡到有意识的深入思考,在《花园》的第六个诗节,诗人发现了精神领域最重要的东西——绿色思想:
与此同时,头脑因乐事减少,
而退缩到自己的幸福中去了:
头脑是海洋,其中各种类族
都能立刻找到自己的相应物;
然而它,超乎这些,还创造出来
远非如此的许多世界和大海;
把一切创造出来的,都化为虚妄,
变成绿荫中的一个绿色思想。
(杨周翰 译)
来到乡间花园,尽管没有了都市的繁荣,少了很多“乐事”,但是头脑却因此得到了更多的休息,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智,因而感到幸福。在这远离喧嚣的花园境界中,诗人的身心得以放松,不断摒弃世俗杂念,静观花园中的绿色,精神进一步升华。
绿色是马维尔常用的形容词,它象征天真无邪,预示着希望与生机,是马维尔心目中理想的颜色,它代表的思想也是精神领域最崇高的思想。在《居鲁士的花园》的序中,托马斯·勃朗曾说:“万物的翠绿状态是复活的象征,要想繁荣茂盛,我们必须首先像种籽那样被撒到腐败之中。”[3]197摔倒促进了人自身的反省,挫败和逆境让人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了。“头脑是海洋”,能够“创造出来远非如此的世界和大海”,马维尔意在说明人的头脑不仅仅是理性的躯壳,更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能够创造一切,可以将物质转化为非物质或精神的东西,即所谓的“虚妄”,并升华至最高的精神境界——绿色思想。
绿色代表繁荣、和平、宁静和快乐。马维尔在对“纯洁甜美的”自然进行描述的同时,剖析了人生与自然的关系,向我们展示了他向往的理想世界,最终,“在这儿”——花园的绿荫下,在潺潺流动的泉水旁边,在果树的根前,在“幽独”与“人群”的张力中,马维尔找到了人生理想的归宿,一个“用碧草与鲜花来计算”时辰的想象空间:
多才多艺的园丁用鲜花和碧草
把一座新日晷勾画得多么美好;
在这儿,趋于温和的太阳从上空
沿着芬芳的黄道十二宫追奔;
还有那勤劳的蜜蜂,一面工作,
一面像我们一样计算它的时刻。
如此甜美健康的时辰,只除
用碧草与鲜花来计算,别无它途!
(杨周翰 译)
王佐良教授曾分析过马维尔此处描绘的理想境界:“在这里时间仍然有效,人也仍然要像‘勤劳的蜜蜂’一样工作,只不过要用碧草与鲜花来作衡量标准。”[5]151历史上日晷、沙漏都曾被人们用来计时,可它们在马维尔看来似乎只是世间庸俗的东西,与美丽的花园世界毫不匹配,更不能用来计算时间,在这里,花园境界中的一切都是神圣美好的,时间也是“甜美健康的”。日晷是时间的象征,花园又是一个空间的场域,两者的结合意味着时空的合一,并暗示着现实花园与沉思花园的相通,人的精神与自然的相通。在17世纪英国政治、社会大动荡的历史时期,诗人在无邪、纯洁的大自然中寻找到了一种宁静与永恒的美,在这样的沉思花园境界中,马维尔不仅获得了感官的快乐和满足,更是升华到了一种精神上的狂喜,人与自然实现了深层次的沟通,人的精神与自然融为了一体,实现了合一。
结语
《花园》这首经久流传的名诗具有丰富的内涵与象征意义,它承载着古希腊罗马神话等古典文化传统。在马维尔看来,花园既是淳朴大自然的象征,也是理想精神境界和纯美艺术的象征,它充满着原始的纯洁和快乐,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乐园。但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关系遭到破坏,人与自然逐渐朝着二元对立的趋势疏离,并且随着工业文明的进展,人们的环境意识越来越淡薄,人与自然的关系渐行渐远。此外,花园或许还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马维尔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经历了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王政复辟两个历史阶段,因此,《花园》一诗可能被赋予了比较强的政治象征意义,正如韦治伍德在其著作《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的评述:“这首最可爱的花园诗是对英国失去了的和平的一首挽歌。”[3]198更重要的是,马维尔超越了传统思维局限,融入了玄学诗歌独特的巧智与奇喻,使用了一系列叠加的花园意象,在沉思中构建了一个甜美、幽独的理想花园境界,展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艺术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考,表露了自己追求的理想花园境界和艺术审美,其在花园的绿色探索中萌芽的生态思想对英国生态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意义。
[1]李正栓.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
[2]王诺. 欧美生态文学[M].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4]王佐良,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5]王佐良.英国诗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On Andrew Marvell’s Ecological Ideas in the Context of Green Exploration:Taking the Poemas an Example
WANG Zhuo
(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41, Anhui)
17th-century English metaphysical poet Andrew Marvell is praised by some critics as a great poet connecting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He combines the romantic elements in the love poems of Elizabethan period in the 16th century with the rationalism of classicism in the 18th century. His poems have crossed two times, mark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late Renaissance to classicism. Taking his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Marvell’s view of nature and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n and nature, man and society, art and nature, aiming to interpret Marvell’s forward-looking ecological poetics and his foundation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rew Marvell; green; ecology;
2020-12-26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8YJC752035);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K2019A0817)。
王卓(1978— ),女,满族,辽宁绥中人,副教授,硕士,主要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I106
A
2096-9333(2021)02-0083-05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1.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