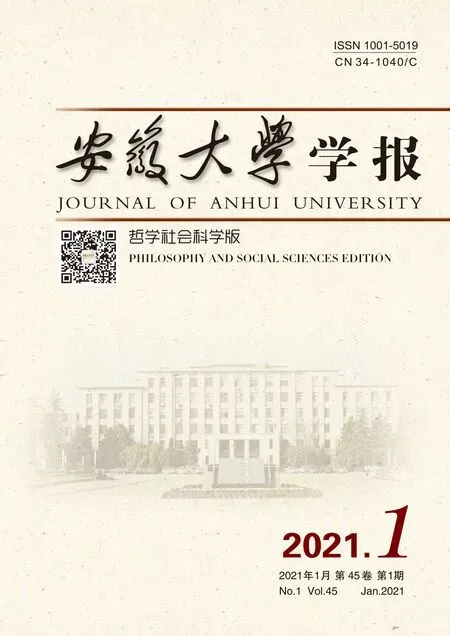论明代诗学的“声教”观念
文 爽
“以声论诗”是明代一个非常显著的诗学现象。如李东阳明确指出“论诗取声,最得要领”,林兆恩、郝敬、赵宧光则分别提出“诗贵声”、“诗主声”、“诗以声调为主”的观念;明代的主流诗学之一——格调派诗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诗歌的“声调”问题;明人选唐诗或者明诗亦常用“音”“声”来命名,如高棅《唐诗正声》、潘光统《唐音类选》、胡震亨《唐音统签》、黄佐《明音类选》、穆光胤《明诗正声》等等。诚如萧驰所言:“此是继建安至永明间乐论影响诗学之后,音乐观念再次入侵,导致中国诗歌理论重建的重要文化事件。”在明代复古诗学的浪潮中,明人“以声论诗”总将其立论依据追溯到诗三百的诗乐合一状态。如上述赵宧光即曰:“声教之与义学,古昔圣王并行而不悖。余故曰:韵语之作,声而非义。汉人而下,以义夺声。”所谓“声教”与“义学”,即略等同于朱自清《诗言志辨》中的“以声为用”与“以义为用”。朱自清认为二者皆为中国古典诗学“诗教”观的两个重要命题。其中,“以声为用”的诗教传统主要来源于乐教传统,而“以义为用”的传统则与诗、乐的分流相关。考诸相关文献,在古籍中仅出现过“诗以声为用”和“诗以声为教”两个命题,其中,“诗以声为用”由宋人郑樵首先提出,而“诗以声为教”则为明人所独创。但可惜的是,据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学界尚未有人关注“诗以声为教”这一诗学命题,学者们关注的与此相关的学术问题是:在明代的格调论诗学思想中,儒家诗教论是否还有一席之地?反对者有之,如张健认为“在明代,儒家诗学的政教传统失落了”,前后七子倡导复古,“他们注意的中心在诗歌的形式风格方面,而不是政教传统”;王顺贵认为“清代格调论与明代格调论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格调论诗学体系中引进了‘诗教’这一重要内容”,言下之意即明人的格调论诗学缺乏“诗教”内容。提倡者亦有之,如张立敏认为在明代,“诗教”理论是“艺术形式探索者没有遗弃的理论”,明人对于“诗歌形式技巧的探索必须服从于诗教原则”。其实,如果了解了本文所言的“诗以声为教”观念,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那么明人的“诗以声为教”观念是在何种背景下兴起,其具体内涵如何,与郑樵“诗以声为用”的观念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朱自清所言“诗教”之“以声为用”的内涵与明人的“以声为教”相关吗?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乐教”与“诗教”的历史源流说起。
一、从“乐教”/“声教”传统到“诗教”/“义教”传统
(一)“乐教”/“声教”传统的兴起
根据现存文献,“乐教”首次出现于《礼记·经解》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广博易良,乐教也。’”在《经解》篇中,“乐教”是作为与“诗教”“书教”“易教”“礼教”“春秋教”等相并列的“六艺”之“教”中的一种被提出的。据有关学者考证,《礼记·经解》篇“应该属于战国的作品”,因此,“乐教”说的正式提出大致是在战国时期。但是作为一种教化方式,乐教大概在文字出现之前就产生了。《尚书·舜典》记载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相传是舜帝的典乐官,《礼记·乐记》曰:“夔始制乐以赏诸侯。”由此可知:第一,至少在尧舜时代,“乐教”即已占据教育的统治地位,“夔”作为乐官,创造了以“歌舞”形式为主的“乐教”。第二,此时“乐教”的首要功能为“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即沟通人与天地、神鬼的关系,这与初民的原始宗教信仰有关。“乐”在上古时代的产生具有巫术性,“原始民族对自然所施加的巫术,表现在声音上就是歌乐,表现在动作上则是舞蹈”,“音乐歌舞”是初民与“神秘的自然进行交往的唯一方式”。商人亦推崇以声为主的“乐教”。《礼记·郊特牲》记载云:“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阙,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所谓“殷人尚声”“声音之号,诏告于天地之间”均是指原始“乐教”功能的宗教性。
在周代以前,“乐教”处于一个绝对的统治地位。周公制礼作乐之后,乐逐渐纳入礼的范围,于是“乐教”也就服从于“礼教”,这从周代“六艺”之教以“礼教”为首、“乐教”次之的顺序即可看出。周代“礼乐教化”的特征是一方面继承了前代“致鬼神”“沟通神人”的功能,另一方面则着重突出教民、化民的功能,例如《周礼·春官·大司乐》曰:“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以致鬼神,以和邦国,以谐万民。”所谓“致鬼神”即为带有初民巫术宗教信仰的原始“乐教”;而“和邦国,谐万民”则成为周代“礼乐教化制度”下的新兴“乐教”。“乐教”之教从“宗教”之教转变成了“教化”之教。原始“乐教”与新兴“乐教”一起,共同构成了后世礼乐教化的核心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和邦国,谐万民”之乐教。
同时,与“乐教”并存的还有另外一个同义概念——“声教”。“声教”主要就是指“乐教”,这是由于音乐本身即是“音声”的缘故。例如《尚书·禹贡》首见“东渐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之语,刘勰《文心雕龙·练字》篇有“先王声教”。二者所谓的“声教”其实都是指传统的声乐之教,后人在引用“声教”概念时往往仅取其“教化”之意,而忽视了“声”的作用。古人以“声教”代指“乐教”,可能与音乐在最初产生之时仅有声而无辞有关。孔颖达曰:“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呼,纵令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所言即为此意。
刘师培曾经这样评价“声教”与“乐教”:“古代教民,口耳相传,故重声教。而以声感人,莫善于乐。……古人以礼为教民之本,列于六艺之首。岂知上古教民,六艺之中乐为最崇,固以乐教为教民之本哉。”刘师培此言非常明确地点明了“口耳相传”之“乐教”/“声教”在古代礼乐教化中的重要地位。
(二)诗乐分合关系影响下的“乐教”与“诗教”
同“乐教”一样,“诗教”的概念亦首次见于战国时期的作品——《礼记·经解》篇中:“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但以“诗”为教的传统亦远在战国之前即已产生。从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看,“诗教”的发展大致可以诗、乐的关系为依据分为三个阶段:
从西周至春秋中叶,诗、乐合一,礼、乐亦合一。诗教、礼教、乐教三教并存,而以“乐教”“礼教”为中心,“诗教”从属于“乐教”。《礼记·孔子闲居》中“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的记载,孔子《论语》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记载都是对这一时期诗教、礼教、乐教并立关系的生动说明。
春秋中叶以后,“礼崩乐坏”,诗、乐开始分流,一方面,雅乐逐渐遗失,另一方面,《诗三百》的文本日益成熟,新的用诗方法开始形成,春秋时期出现的“赋诗言志”现象,是“重义”思潮的突出表现。孔子论《诗》“重义”与“重声”兼有:“重义”者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重声”者如:“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声义兼重者”如:“《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可指声音中正平和,又可指其所蕴含的“发于情,至乎礼仪”的中和性情。到战国中后期,诗乐彻底分流,孟子用《诗》提出“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两种论诗方法,已完全陷入“以义为用”的阶段。“随着乐教的衰落,礼教的兴盛,用诗活动中以礼教为旨归的‘义用’原则渐起,逐渐代替了以乐教为旨归的‘声用’原则”。
汉代以后,经学兴盛,“礼教与诗教并立,诗教为礼教所用,礼教占据了社会政教话语的中心地位,乐教趋于破产”。从三家诗到毛诗,《诗大序》最终确立了影响中国数千年的“诗教”义用原则。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区分“诗教”与“乐教”即是在此诗乐分流,义用代替声用的大背景下而言:“若以声音干戚以教人,是乐教也。若以诗辞美刺讽谕以教人,是诗教也。”孔颖达所谓“声音干戚以教人”,即是指“声用”之“教”,“诗辞美刺讽谕以教人”即是指“义用”之“教”。
诗、乐虽然分流,“二者之间天然的联系却并没有被切断,‘乐理’以隐形的方式帮助‘诗’全面行使着‘诗教’功能”。“诗歌”不应该也不会单纯依靠“义理”之用来施行教化。“诗以声为用”与“诗以声为教”观念的产生就建基于“乐论”的隐形影响之下。
二、“诗以声为用”观念的提出与发展
宋人郑樵首先提出“诗以声为用”之说:
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
,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
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不幸腐儒之说起,齐、鲁、韩、毛四家,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
。……古诗之声为可贵也
。……继三代之作者,乐府也。……今乐府之行于世者,章句虽存,声乐无用,崔豹之徒,以义说名,吴竞之徒,以事解目,盖声失则义起,其与齐、鲁、韩、毛之言诗无以异也。乐府之道,或几乎息矣。这段话有几个要点值得注意:其一,郑樵“诗以声为用”之“用”是“使用”“功用”的意思,偏指燕飨祭祀之时的以声歌为用;其二,郑樵在论述时采取了“声”“义”对举的方式,这就为朱自清论诗教提出“以声为用”和“以义为用”相并举的说法提供了历史文献的支撑;其三,郑樵论“声”“义”关系,有明显的价值取向,概言之即褒“声”而贬“义”,“诗贵声”(“古诗之声为可贵”)、“诗在于声,不在于义”的说法表明了此种倾向;其四,郑樵“诗贵声”之“诗”内涵丰富。在此段论述中,“诗”主要指“诗三百”与“乐府”。在其他论述中,“诗贵声”之“诗”还可扩展为一切泛指之“诗”,如其曰:“古之诗曰歌行,后之诗曰古近二体,歌行主声,二体主文。诗为声也,不为文也。”郑樵以为“歌行主声,二体主文”,所谓“文”即“文辞”,延伸而指“辞义”,所以郑樵明确提出“诗为声,不为文”,其内在含义仍然是“诗为声,不为义”。以此为基点,他反对古、近二体主文不主声/乐的做法。从《诗三百》到“乐府”“歌行”再到“古近二体”,郑樵皆以为“诗在于声,不在于义”,将“诗贵声”的说法推到极致。客观来说,郑樵此言有矫枉过正之嫌。所以后来朱熹有与其相反的观点。朱熹认为“古乐散亡,无复不考”,“欲以声求诗”,无异于“画饼充饥”,而且“诗出乎志者也,乐出乎诗者也。然则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末也”,朱熹立足于诗乐分流之后“古乐亡逸”的现实,以“志”为诗之“本”,以“乐”为诗之“末”,这与郑樵“声本义末”的说法有本质区别。其五,郑樵描述了“以声为用”(声歌之学)向“以义为用”(义理之说)流变的大致过程,认为“义理之说日盛”导致了“声歌之学日微”,却忽略了“声义并存”或者说“义理之说”的重要性。
稍晚于郑樵的吕祖谦则对“声义并举”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季札来聘,鲁请观周乐。鲁使乐工为之歌诸国之《风》,及历代之诗如小大《雅》《颂》之类。札随所观,次第品评之。有论其声者,有论其义者
。如所谓“美哉渊乎”“美哉泱泱乎”“美哉沨沨乎”“广哉熙熙乎”之类,此皆是论其声
也;如所谓“忧而不困”“思而不惧”“乐而不淫”“大而婉”“险而易行”“思而不贰”“怨而不言”“曲而有直体”之类,此皆是论其义
也。以此知古人之诗,声与义合,相发而不可偏废
。至于后世,义虽存而声则亡矣。大抵诗人之作诗,“发乎情性,止乎礼义”,固其义也。至“声依永,律和声”,则所为诗之义,又赖五音六律之声以发扬之,然后鼓舞动荡,使人有兴起之意
,如“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季札生当春秋末年,正处于诗、乐分流的关键时期,《左传》所记载的“季札观乐”,所观者亦是作为乐歌之《诗》,吕祖谦认为季札观乐/诗,有“以声论者”,亦有“以义论者”,所以“古人之诗,声与义合”,正是“声、义兼用”的表现。按其意见,其所谓“义”者,乃是指“发乎情性,止乎礼义”,季札所言“忧而不困”“思而不惧”“乐而不淫”等均为此类;其所谓“声”者,乃是指“五音六律之声”,季札所言“美哉渊乎”“美哉泱泱乎”“美哉沨沨乎”“广哉熙熙乎”均是对乐歌之声动听的描述。吕祖谦还认为诗之“义”需要依赖“五音六律之声”而“发扬之”,从而起到“鼓舞动荡”“兴人之意”的作用。在这里,吕祖谦认识到了在诗歌中“声”与“义”“相发而不可偏废”的关系,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所谓“义之用”乃要靠“声之用”发扬而广之,二者共同指向“鼓舞动荡”“兴人之意”的诗教目的。吕祖谦又言:“至今清庙之诗,其义虽存,而一唱三叹之音何在?然音虽亡而义存。学者亦可涵泳其音节,使有所兴起也。所谓‘工以纳言,时而扬之’,五音六律,今之世固不可求,须想象;所谓‘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庶几声义交相发。”指出“音亡义存”之后的诗歌依然可以通过“涵泳其音节”而求得诗歌“兴”起人意的重要作用。此处所言之“音节”其实在实质上代替了其所言之“义存声亡”中的“五音六律”之“乐声”,成为后世诗乐分流之后“以声为用”中“声”之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吕祖谦对诗歌“声”“义”关系的看法相比郑樵过分重视“声”/“乐”,朱熹过分重视“志”/“义”来说是比较辩证的。而且从吕祖谦对于声义关系的论述可知,前期以声为礼仪等级区分的礼乐意义之用已经转变为“鼓舞动荡、兴人之意”“陶养性灵”的声情之用。这一点正是“以声为用”与“以义为用”的交叉点。明人对于诗声之用的观念更多地继承了吕祖谦的观点(详见下文)。
综上,“诗以声为用”的观点主要由宋代郑樵首先提出,郑樵基于“义理之说日盛,声歌之学日微”的诗学现实,提出此种观点,在诗学史上主要有两重意义:其一,是突出了“声”对于诗歌的重要意义;其二,明确点明了诗声之“用”最初主要指代的是作为礼乐之《诗》的燕飨、祭祀之用,它代表的是一种礼仪等级的区分作用,而不强调教化人心之“用”。

郑渔仲谓:“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又谓:“古之诗,今之词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不幸世儒义理之说日胜,而声歌之学日微。”马贵与则谓:“义理布在方册,声则湮没无闻。”其言皆有见。而朱文公亦谓“声气之和有不可得闻者,此读诗之所以难也”。夫乐之义理,诗词是也。声歌犹后世之腔调也,两者俱诣,乃为大成。
陆深此段最有见地的说法是在引用郑樵的基础之上,又征引马端临与朱熹之语说明“诗”与“乐”的不可截然分离,然后提出对于诗歌而言“声义倶诣,乃为大成”的看法。
无独有偶,晚明费经虞对于郑樵之“声贵”说亦有一比较客观的评价。其《雅伦》曰:“郑樵序《乐府》,以声歌言最为高识。……而以齐、鲁、毛、韩,序训为腐儒之说,抑又过矣。经传引诗,多言其义。……子思、孟子引诗亦以义言。而以诗止可言声歌,而不宜言义理可乎?故经虞以为赋诗者有文词,歌诗者有音节,解诗者有理义,三者缺一不可,而后论诗之旨备矣。”费经虞指出郑樵“诗贵声”的说法其高明处在强调“声歌”之重要意义,而短漏处则在于其对诗之文辞与义理的忽视,费经虞强调“文词、音节、理义”对于“论诗者”来说,缺一不可。陆深和费经虞的说法表明明人在引用或者阐释郑樵的“诗以声为用”观念时,除了突出“声”之重要性的一环外,并未忽视诗歌文辞与义理的作用。在更多地情况下,“以声为用”与“以义为用”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诗歌,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诗教”。
因此,明人提出“诗以声为用”的说法在一般情况下皆是为了强调“声”对于诗歌的重要性,而不考虑宗庙祭祀之用,这是其“诗以声为用”的核心内涵。同时,明人对“诗以声为用”的理解又不仅限于此,明末侯玄泓在《秋笳前集序》中还提出了“诗之为用者声也,声之所以用者情也”的说法。这句话的前半句是郑樵“诗以声为用”的变体,后半句以“情”来说明“声之用”,这就将“诗以声为用”引向了“诗以声为教”,因为正是“情”奠定了“声”由郊社、宗庙、宫廷、祭祀之用到声情教化之用转变的理论基础。侯玄泓所言其实正是对明人“诗以声为教”核心内涵所作的总结。
三、“诗以声为教”观念在明代的正式提出
明人继承前人“声教”与“诗以声为用”的观念,在诗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诗以声为教”的观点。例如叶春及在《李惟实诗序》中曰:
诗以声为教者也
。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人有志则形于言而为诗;诗必有长短之节,谓之歌;歌必有高下清浊,谓之声;比声而筦弦之,谓之乐。故三百篇皆乐章也。后世其声不传,立于学官,博士弟子所隶,惟理之为解,失其本矣。汉犹近古,降而魏,又降而晋,又降而唐,去古弥远,而皆有一代之声。君子于宋而弗诗之,亦理故也。……斯学盛于弘正间,而李何为之冠。洎近世,一二君子自相雄长,傲倪当世,呼于垤泽,能令人宋之乎?叶春及为嘉靖三十一年举人,在此之前,已经有以李、何为代表的前七子格调派诗人提倡“以声论诗”,畅言“时代格调”,所以叶春及有“斯学盛于弘正间,而李何为之冠”的说法,所谓“斯学”即是指“声学”。再看其“以声为教”说,显然并没有指出“声教”的具体内容,而是以《尚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之说立论,指出志、言、诗、歌、声、乐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与《诗三百》的“诗乐合一”特征。之后叶春及又论及后世“理学”的兴盛与“声学”的衰落,宋以理盛故无声,这与郑樵言称“诗以声为用”而以“义理之学日盛,声歌之学日微”为现实依据的思路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正是在郑樵“诗以声为用”这一“重声”观念的影响下,明人依据相同的思路提出了“诗以声为教”的观点。
与叶春及相似,张师绎《于喁集序》亦从“志、言、诗、歌、声、乐”的关系提出“诗以声为教”的说法,在论述的过程中亦指出“乐之渐失”与“理之兴盛”,其曰:
诗以声为教者也
。人有志,形于言则为诗,诗有短长之节则为歌,歌有清浊高下则为声,比声而被之管弦则为乐,故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还相为宫,而诗三百篇,大抵房中郊庙之乐章也。夫子业已删诗矣,其自卫反鲁,乐正而后作,而曰雅颂各得其所。汉魏来,乐失其传,乐府犹存其意。至宋而肄,在学官博士弟子者唯理,声依非子言之诗也。这段说辞与叶春及唯一不同的是张师绎引用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说法说明了“诗教”、“礼教”和“乐教”的统一,从而点明了“以声为教”之论题。但无论是叶春及还是张师绎,二人皆没有涉及“以声为教”的具体内容。陈第与陈际泰则不同。作为明代古音韵学研究的大家,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开篇即言“诗以声教”,而且还点明了其内涵:
夫《诗》,以声教也
,取其可歌、可咏、可长言嗟叹,至手足舞蹈而不自知,以感竦
其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心,且将从容以抽绎,夫鸟兽草木之名义,斯其所以为《诗》也。所谓“可歌、可咏、可长言嗟叹,至手足舞蹈而不自知”乃化用自《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此段话表明了诗歌言情达志的本质特征,而言、歌、咏、长言嗟叹、舞等皆是言情表意的途径。陈第在引用时省略了“言志表情”的部分,只特意拈出“歌、咏、长言嗟叹”等表“声”的部分,且用“以感竦……之心”的表达方式将其与孔子“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说连接起来,这表明在陈第看来,诗歌的“以声为教”,就是以“歌咏长言嗟叹”之“声”起到“感竦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心”的作用,“感”是诗歌“以声为教”的关键
。而“诗声”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作用还是因为其本身具有“言情达意”的属性。因此,尽管陈第没有引用《毛诗序》中的“言志表情”之说,实际上却已暗含了此种含义。晚于陈第的陈际泰更为直接地说明了“诗以声为教”的关键在“感”:
古诗之流,以声为教
。夫声者,感人密深而风移俗易,盖其致不在理义也。……声之为道,感人在理义文字外矣。这里陈际泰明确指出诗歌“以声为教”的内容为“感人密深”和“风移俗易”,所谓“感人密深而风移俗易”,实出于西汉王褒的《四子讲德论》:“夫乐者,感人密深,而风移俗易。”这与《礼记·乐记》《荀子·乐论》中“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史记·乐书》中“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的说法基本一致,陈际泰以“声”字替代“乐”字,表明其“诗以声为教”的观点依然是来源于“乐论”。另外,陈际泰还将“声”与“理义文字”分开来讲,认为“声教”的“感人”在“理义文字之外”。这就在突出“声教”观念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字言辞”的“辞意”之教,但很明显的问题是陈际泰认为“声”之“感”远比“义理”的“教化”更为直达人的内心。因为真正有效的教化是从内至外的“感化”,而非礼仪、义理所强加的道德人伦规范。这也是为什么“乐教”与“诗教”均强调“言情达志”的原因。
关于声之“感人”的属性,前代诗人对此已有论述。如宋代曾三异《因话录》曰:“声者,气之精华也。一纸之隔而气不能达,墙垣之间声可得闻。声之感
通者甚神!故诗
能动天地,感鬼神,乐
能治神人,和上下,皆主其有声
也。”按曾氏意,“动天地,感鬼神”,乃“诗教”也,“治神人,和上下”乃“乐教”也,二者之所以有如此功用,乃在于其“皆有声”,“声”乃沟通“乐教”与“诗教”的关键。曾氏还进一步指出“声”之所以具有此种属性的原因乃在于“感”,是所谓“声之感通者甚神”,“声”之本体乃在于其是“气”之“精华”,“气”的流动性形成了“声”之“感通”性。曾氏的这种说法与侯玄泓的“声之所以为用者情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因为“声”本身乃“情”之所发,“声”才可能具有“感化人心”的作用。在对“声”之“情”与“感”属性的认识上,明人解决了“诗以声为教”这一观念成立的逻辑前提
。如宋濂即曰:“古之人教子多发为声诗,何哉?盖诗缘性情,优柔讽咏,而入人也最深。”非常明确地指出声诗“入人”,“感化人心”的功能与“缘于性情”的关系。四、“诗以声为教”理论提出的现实背景与真实意涵
除了以上所言之理论基础,明人提出“诗以声为教”的观点还基于明代“乐教”作用的不作为。明王朝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礼乐的作用,但历经礼乐混乱的元代,明代之乐难达古雅,礼乐制度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明史》记载,明乐“大抵集汉、唐、宋、元人之旧,而稍更易其名。凡声容之次第,器数之繁缛,在当日非不灿然俱举,第雅俗杂出,无从正之”。面对“雅俗杂出”这种失效的礼乐制度,明代诗人希望通过诗家之声韵建立“一代之乐”,起到一种接续替代作用。这种说法主要体现在李东阳的相关论述中。李东阳曰:
古雅乐不传,俗乐又不足听。今所闻者,唯一派《中和乐》耳。因忆诗家声韵,纵不能仿佛赓歌之美,亦安得庶几一代之乐也哉!
所谓“古雅乐”,即指周代为礼乐制度服务的乐舞,强调音乐的“中正和平”;而“俗乐”则指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相对雅乐而言的民间音乐。李东阳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古雅乐不传,俗乐又不足听”的时代,唯一流行的是《中和乐》。学者孙之梅对此乐有较为详细的解释:“《中和乐》是明代的圜丘迎神曲。圜丘,是帝王冬至祭天地的场所。圜者,象天圜也。迎神曲句式有齐言、骚体两种……这样一种乐歌及乐曲成了当时很流行的雅乐。”对于这种过度单一的程式化乐歌,李东阳显然是不满的,在他看来,这一时期能弥补不足、担当“一代之乐”的合适替代者就是“诗家声韵”。他甚至将其与帝舜在位时大臣百官诗歌唱和的“赓歌”传统联系在了一起,这就将诗歌放置到了一个宏阔的历史背景之中,语虽简短却内涵极深。
理解此段话,需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是其所言之“诗家声韵”并非指我们如今所言的“平仄格律”,而是指“有巧存焉”之“声调”,是诗歌讽咏之时自身所呈现出来的音乐属性。其二,是李东阳将“诗家声韵”比拟为“一代之乐”,带有以诗声之教代替乐声之教的意图。这一点可从其诗文辨体论时认为诗歌区别于文的特点在于“以其有声律讽咏,能使人反复讽咏,畅达情思,感发志气”一句看出。所谓“畅达情思,感发志气”正是“诗以声为教”的主要内涵。具体而言,是“取其声之和
者,以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所谓“声之和”,不仅是指声音的平和,还指声音的雅正,而这种“声之雅正”则来源于作者的“性情之正”,高棅《唐诗正声》所提出的“情正声正”理论是这一说法的典型代表。李梦阳进一步描述了这种雅正平和之声所能带给读者的生理反应(“动荡血脉”)与心理反应(“流通精神”),乃至超越生理与心理的极致无意识反应(“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这种“和缓”“和谐”的音乐特征,影响到人,就会使其生理反应、情感流行同样呈现出一种与诗歌声韵相应和的“和缓”“和谐”特征,这是由“声之和”到“心气之和”“情性之和”的必然过程,也是诗歌音乐性之声教功能的最初层次。所谓“人能学诗,则事理通达,心气和平而能言”,正是言此。稍晚于李东阳的李献忠则在《山中集跋》中建立了一个“心正→辞顺→声和→温柔敦厚”的“诗教”模式:“诗之教,曰温柔敦厚。夫心正而后辞顺,辞顺而后声和,声和则温柔敦厚举之矣。”其中“心正”可拓展为“情正”,情正则声和,声和则温柔敦厚之诗教可以成行,凸显的亦是从作者之“心/情正”到诗之“声正/和”再到“陶写感发”读者之“性情心志”的“声教”观点。除了“声之和”,声之“抑扬反复”亦是“以声为教”成行的另一前提。李东阳比较了“正言直述”与“反复讽咏”在诗歌接受方面的不同作用,认为“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唯有采取比兴手法将“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诗歌创作才能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的效果。稍晚于李东阳、同属茶陵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顾清曰:“诗本人情该物理,其言近而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吟咏”的“抑扬”不单单是声调的抑扬,同时亦是诗作本身所蕴含情感的抑扬,诗歌声音的高低起伏变化直接可以影响人情绪的高低起伏,而“吟咏”的另外一个特点“反复”,则在一遍又一遍地入人耳,入人心,“重复”的频率由此加深了诗之“声教”的感人程度,也就在另一方面提高了“声教”的速度。此《乐记》所言“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人有“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识”,声教(偏于耳识)与义教(偏于意识)相比,更加直观地诉诸于人的听觉,也更加容易引起人普遍的情绪。所以,明人所关注的第一个重点便是诗歌吟咏对于人心感发,性情怡养的作用。
在以上的养性情、致中和之德的过程中,自然也就内涵了“诗以声为教”的第二层内涵:美风俗,化天下。李东阳曰:“诗者,言之成声,而未播之乐者也。其为教本人情,该物理,足以考政治,验风俗。”既指出诗与乐的不同又点明诗歌之声教的另外一层内涵:考政治,验风俗。李东阳在论述完诗歌“有声律讽咏,能使人反复讽咏,畅达情思,感发志气”之后,自然提出“取类于鸟兽草木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在提出诗歌“比之以声韵,和之以节奏,则其为辞,高可讽,长可咏”之后也立即指出其“近可以述,而远则可以传”的传播性与普及性。就此点而言,李东阳之诗声政教论是较为突出的。
总之,李东阳对于诗歌作为一种音乐文学所应具有的教化作用的认识,整体上可用唐顺之的两句话来概括,即“陶养性灵,风化邦国”。
除了李东阳,明人的这种以诗教接续乐教的主张还可从胡缵宗、黄佐身上看出。胡缵宗和黄佐分别辑有唐诗总集《唐雅》与《唐音类选》。《唐雅·序》曰:“诵唐诗而律之以雅,斯成一代之音以续三代之韵。”又有叙云:“欲备一代之音,取意于乐,故以雅名。”黄佐序《唐音类选》曰:“唐诗以音名矣,音由心起,与政通者
也。……呜呼!《三百篇》之遗轨,其犹存乎?”二人皆以唐诗作为诗教的代表性文本,指出以“雅”/“音”命名唐诗的原因皆“取意于乐”,一者欲“以一代之雅音续三代之韵”,一者欲以唐诗续“《三百篇》之遗轨”,以“审音知政”。“雅音”与“审音知政”的主张毫无疑问均来源于乐教。以之论唐诗,其实正反映出二人以诗之声教接续乐之声教的期望。黄佐还进一步指出以“声教”代“乐教”的原因:“诗也者,乐之始也。乐也者,诗之成也。自乐律不传,今之所知者,诗律而已。”所言之“诗律”既指“杜少陵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之平仄格律,又指在平仄格律基础上透过字音、音节句式、篇章结构而呈现出的带有诗人个人性情特色的整体艺术风格。如其曾经以“诗律”比拟于“乐律”,曰:“尝窃评三曹、阮、陶、谢之诗,优游雅淡,其音律如黄钟大吕。王、杨、卢、骆之诗,繁缛清绝,其音律如无射应钟。兼是二体,如《周官》之大合乐,庶几其集大成乎?古今大家,亦惟少陵乃能与于此。”将“优游雅淡”之音律比拟于“黄钟大吕”,“繁缛清绝”之“音律”比拟于“无射应钟”,明显是以音声风格立论。同时,他还认为兼有这两种风格的“音律”之诗可比拟于“《周官》之大合乐”,这就与李东阳所言的“诗家声韵”可比拟为“一代之乐”思路一致了。要之,李东阳、黄佐二人皆看到了“诗乐分离”之后“礼乐制度”的失效(乐律的失传)问题,二人以诗家声韵接续代替礼乐之乐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五、明代“诗以声为教”观念的价值和影响
出于对诗乐本源关系的重视,明人基于传统的乐教理论在诗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诗以声为教”的观念。“诗以声为教”之“声”,不是指诗歌的“格律”,而是指诗歌讽咏之时呈现出来的自然音乐属性。明人的“诗以声为教”变宋人“诗以声为用”中的郊社、宗庙、宫廷、祭祀之用为“声情教化”之用。这种“声情教化”之用主要是通过声情感化人心而施行的,其媒介是“声音”本身所具有的“情”(声之所用者情也),因此“声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教化。明人认为“情正/和则声正/和”,“声正/和则情正/和”,在对诗歌进行反复的声律讽咏过程中,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其个人的“情思”得到“畅达”,“精神”得到“流通”,“血脉”得到“动荡”,“心性”得到“净化”,进而起到“移风易俗”“风化邦国”的重要作用。
同时,明人“诗以声为教”的观念还需与“以义为教”的观念合而观之,结合二者的正是明人“声教”“声用”理论中对“情”的充分关注。《荀子·劝学》篇曰:“《诗》者,中声之所止也。”杨倞注云:“诗谓乐章,所以节声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表明此处所谓“诗”,正是以诗、乐相兼而言,“乐以和通为体”,“诗”亦是“中声所止”,“诗”与“乐”同具“中正平和”的本质属性。而根据明人“情正声正”的诗声理论,“诗教”对诗的音声要求实际上已包含了“性情的中正和平”,由此,明人“以声为教”的内涵便具备了“以义为教”的要旨。所以,赵宧光《弹雅》中才会提出“声教与义学并行不悖”的诗教理想。明人重视“诗以声为教”,是基于自汉代以来“以义学敝其声教”的诗学现实而立论的,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历史的根源性,同时也是明人“以声论诗”的一大特色。
明人这种源于“乐教”而“以声为教”的诗学观念在后世诗学中亦得到了明显继承。比较典型的是王夫之和沈德潜。如王夫之曾经指出“世教沦夷,乐崩而降于优俳。……乐语孤传为诗”,所以“明于乐者,可以论诗”。从“声教”的角度,王夫之倡“贞情”而斥“淫情”,提出“缓”而“不迫”的诗歌“雅正”观念。沈德潜论诗既主张格调,又主张温柔敦厚的诗教,而其温柔敦厚的诗教则是蕴含了“声教”与“义教”的统一体。其《唐诗别裁集》序言宣称自己的选诗标准为“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音节……大约去淫滥以归雅正,于古人所云微而宛和而庄者,庶几一合焉”,“宗旨”涉及“义”,“音节”则涉及“声”,“雅正”则是“诗教”对诗歌声、义的共同要求。又在晚年重订《唐诗别裁集》时强调“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审音节、继论神韵,而一归中正和平”,此“中正和平”亦是“声”“义”并重的。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文章开头的问题:在明代的格调派诗学体系中,儒家诗教论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明代的格调论诗学家论诗畅言“雅正平和”之音,希冀以雅正平和之声达到“陶养性灵,风化邦国”的诗教目的:前述李东阳自不待言;前七子的王廷相评价刘节之诗“本乎性情之真,发乎伦义之正……梅国之诗,有风雅之遗教”;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指出诗歌应“不之于情,则止于性;达适其趣,而和平其调”,一方面“以性约情”,另一方面“和平其调”,亦带有高棅所谓“情正声正”的意味。
朱自清所言的“以声为用”是经历了明代“以声为教”观念浸染的“声用”观念,其主要内涵应是指声情教化之用,朱自清言诗教“意念的核心是德教、政治、学养几方面”,又言“诗教不能离乐而谈”,因为“声音感人比文辞广博得多”“温柔敦厚是个多义语,一面指诗辞美刺讽喻的作用,一面映带着那诗乐是一的背景”,凡此种种表述,皆与明人之说一脉相承。朱自清之所以用“以声为用”而非“以声为教”这种表述,原因可能有二:其一,“诗以声为用”从宋代郑樵提出以后,即在明清两代广为流传;其二,“诗以声为教”的内涵从明代起即被纳入“诗以声为用”的范畴,例如前文所言之明末侯玄泓说“诗之为用者声也,声之所以用者情也”,以“情”凸显“声情教化”之用。清人沈德潜亦在此种意义上言称“诗以声为用”:“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根据沈德潜对温柔敦厚诗教之说的一贯推崇,可以推测此“以声为用”即是要达到其所言的“诗之为道,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之用。
综上,明代诗学中的“声教”观念已成为后世诗学研究“诗教”意涵无法回避的一环,“以声为教”与“以义为教” 并行不悖,方得其中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