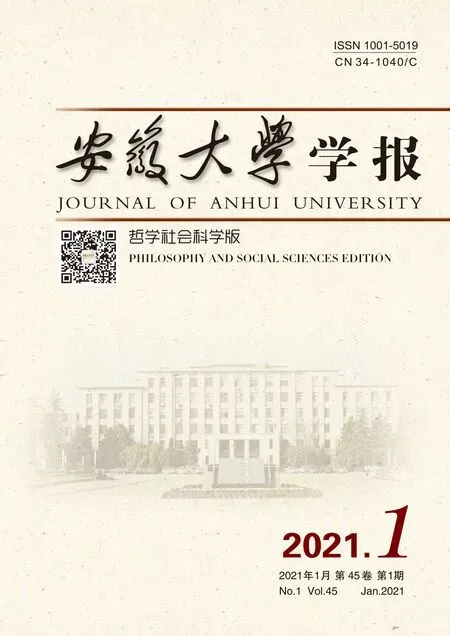金榜的礼学思想及其社会史意义
徐道彬
清代乾隆壬辰科状元金榜(1735—1801,字蘂中,号檠斋),出身于徽商之家,以聪慧才智博得科举功名;凭扛鼎之作《礼笺》而成为乾嘉汉学的中坚人物,奠定了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以居乡仕宦的行事作为而振兴世风,化民成俗,使学风笃实,人心诚信;通过器物制度到思想文化的探求,以存亡继绝的礼学著述,对礼乐兵刑之大、人伦日用之常,皆能融会新知,正本清源,借以重振人伦纲纪,拯救世道人心,为复兴传统礼仪秩序和导引民风渐趋良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社会背景与个人心志
明清时期的徽州,虽“僻陋一隅,险阻四塞”,但钟灵毓秀,儒风独茂,故有“东南邹鲁”之誉。作为典范的宗法家族制基层社会,乡邦先贤的《朱子家礼》与都图村落的乡规民约,使生活在徽州的民众极其重视岁时祭祀、宗祠修葺、婚丧操办等人伦教化之事,乡间的一切活动都笼罩在儒家淳风化俗的礼仪之中。正如徽州世家谱牒所言:“吾等士庶家,自有士庶之礼,向来祖制所遗,皆本《文公家礼》而少为之参订。虽行之难云尽善,要亦行之可以无弊,故数百年来卒未有易之者。盖礼不取乎文,贵取乎实,不重其末,而重其本。如祭祀以敬为本,一切祭品祭器祭献之节皆末也;丧礼以哀为本,一切丧期丧服丧制之节皆末也;冠婚以揖让为本,一切送迎登降酬酢之节皆末也。”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特定的风土人情与礼仪生态的文明程度,正是几百年来儒家敦崇礼让思想和冠婚丧祭礼仪教化的结果,以至于此地“不学礼,无以立”,“冠昏丧祭,多遵《文公家礼》”。如此光前裕后的浓郁儒家礼仪之风,使得重峦叠嶂的秀丽徽州,几无禅林道观的立足之地。
徽州的世家大族和士绅阶层俱遵儒家礼制礼仪,极少有受佛道影响者。唯近世稍有棚民小户混合儒释道的民间祭祀活动,或茹素诵经,或斋醮功德,大多是为祈福消灾或超度亡灵时的偶尔之用,但也遭到程朱阙里之士的强烈不满和抵抗。究其原因,乃在于“歙为程朱阙里,士大夫类能受孔子戒,卫道严而信道笃,卓然不惑于异端”。民国歙儒许承尧对此现象解释道:“徽俗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斋醮耳,无敬信崇奉之者。所居不过施汤茗之寮,奉香火之庙。求其崇宏壮丽所谓浮屠老子之宫,绝无有焉。于以见文公道学之邦,有不为歧途惑者,其教泽入人深哉。”徽州作为“文公道学之邦”,自然以孔孟之道、儒家伦理为社会纲常和民众意识的核心内容。在乡村层面上,“尊祖敬宗睦族”乃民众“终生以之”的为生之本;“事业从五伦做起,文章本六经得来”则是士子成长历程中的坚定信念。作为社会精英的士绅学者,则深负着经世致用的职责与使命,努力从经典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入手,“考经求礼”,“即器明礼”,体国经野,开物成务,为立功立德立言的经世思想注入了丰富内涵,并引领一个时代的观念变革与民众的价值取向。金榜即是其一。
金榜少负伟志,博学深造而为通儒,本不欲溺没聪明于科举之学。年三十一,乾隆南巡召试,以呈献诗赋蒙恩擢授内阁中书,在军机处行走。越七年,又以状元及第而授翰林院修撰,供奉朝廷。稍后以丁外艰,归乡不出,“杜门养疴二十一年”,“徜徉林下,著书自娱”。对此,人们揣测和评判颇多,以为其抛却仕途利禄,不可思议。然纵观金氏家族,大多为行商在外者,尤以寓居杭州为多,由科举走仕途者仅三五人而已。故金榜退隐故土后,一直以操持家族商务、教育子弟和著书立说为业,以敬宗睦族的儒家礼仪指导金氏家族及周边民众的日常行为,使得尊祖必叙族谱,敬宗应修祠墓,睦族则理当赈济贫困,将儒家仁与礼的要旨贯彻到耕读营商的事业之中,使内则“耕读传家”,外则“贾而好儒”,“一乡之中,皆彬彬兴起于学”,呈现出“世道今还古,人心欲归仁”的穆穆儒风。
金榜的祖父辈皆为“贾而好儒”的儒商,虽然寄命于商,但“动循理法”,对儒生文士极为亲敬。其祖父金公著“自以托迹市廛,不获读书为憾,及见儒生文士则悚然心亲而貌敬之。于是贤士大夫习见其内行无失,外应有余,皆乐与之交游。所居僻介丛山,村人以樵牧为务,而府君独市典籍,延师儒课子孙以进士业。其后子孙既贵显,而一乡之中,皆彬彬兴起于学焉”。其叔父金长洪“善持筹,而动循理法,取利必以义,不欲竞锥刀,以割剥愚懦。自处甚约,而多急人之难,尤厚于族姻里党。不治经生家言,而诸孙所习文艺,辄能披览其大略,有所指斥,必中其窾要。其于天下之务、时事之利弊,较然明白,如自视其掌。遇事之盘错,其精神常镇定,而卒能有剖决,以解其纷。见人有争讼,或手足骨肉相伤残,能以片言感悟之,使卒归于和好。盖其理人之才又如此。惜其不得尺寸之柄,使施之家国天下也”。由金氏祖孙三代的经历可以看出,金氏家族虽“托迹市廛”,而“于天下之务、时事之利弊”能够“剖决解纷”;尤重“延师儒课子孙”,贾而好儒,为典型的徽商之家。金榜出生在如此家族,在经商盈利后,购置义田、族田,救济贫困,泽惠族党;并通过建祠堂、增祭田、修族谱等一系列物质和精神上的慈善,强化宗族血缘纽带的凝聚力;又以其“理人之才”而施行于世,以言传身教影响周边,以儒家道德礼仪指导家族的日常行为。
金榜居乡读礼期间,曾先后邀约同邑吴定、武进张惠言等学者坐馆家学,研覃学问。吴定“家本贫,屡试不售”,曰:“曩(金)先生尝招余馆于其塾,训其少子童孙,漏三下,往往犹相与讲学论文不辍,甚相得也。”张惠言“少孤贫,年十四即为童子师”,得寓金宅后,“修学立行,敦礼自守”,“所居橙阳山,门前有小池,夫渠盈焉。时五六月间,每日将入,两生手一册,坐池上解说。风从林际来,花叶之气,掩冉振发,余于此时心最乐”。在授徒之余,他们相与研讨经学,阐释义理,取长补短,相得甚欢。张氏前后居歙凡八年之久,得金氏“割宅以居,推食以食”,而能静心“专治《易》《礼》。言《易》主虞氏翻,言《礼》主郑氏康成,微言奥义,究极本源,于古今天人之统纪,言之皆亲切有味”。故“其学要归六经,而尤深《易》《礼》,弟子从受《易》《礼》者以十数”。对于金氏在学业和经济上的恩惠,张氏铭记终生,自道:“嘉庆之初,问郑学于歙金先生。三年,图《仪礼》十八卷,而《易义》三十九卷亦成,粗以述其迹象,辟其户牖,若乃微显阐幽,开物成务。”对于金榜为何在功成名就之后,能够“浩然勇退,杜门深山”,张氏解释为“古人著书,感发不遇;先生不然,颐志养素”。对聪明蕴藉的金榜而言,“颐志养素”之说最为合理。就儒家社会而言,士子以“仁”为修身之道,而以“礼”为经世之法。正因为“礼”能够“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语),故金氏择取礼学为终生为学鹄的,矢志不渝,卓然大家。故时人称其“幼与戴东原从事于江布衣慎修之门,得其说《礼》之旨。著《礼笺》三卷,徽之士翕然从之”。李慈铭亦赞之曰:“阅金辅之《礼笺》,古义湛深,研究不尽。国朝状元通经学者,以辅之为巨擘。”金氏能够抛弃仕途,退居林下,沉浸于枯燥艰深的礼学研究,则其治学思想的源泉与经世用意,自然与其所生活的徽州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家族的教育和影响,密不可分。
二、“圣人之道,一礼而已”
金榜一生仅存《礼笺》一书,该书内容遍及天文历象、宫室建制、礼乐兵刑、赋役河工、政法文教、膳食车服、农商医卜等,林林总总,无所不包,甚至如“周易占法”“三江”“汉水源”等涉及易学卦爻、山川水地之学也囊括其中,可谓自天地万物到宇宙人生,包罗万象,周纳备至,一如凌廷堪所言“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充分体现出儒者通经致用、关注时政的历史责任感。
金榜研治礼学始终坚守阐明制度,含摄风俗,一反宋明诸儒将礼学脱离人伦日用而趋向内省化及“舍事而言礼”的做法,自称治《礼》宗郑氏学,长而受学于江永,“遂窥礼堂论赞之绪。其间采获旧闻,或摭秘逸要,于郑氏治经家法不敢诬也”,“《礼笺》之名,盖首其义”。此乃乾嘉时代学术风气的典型表露,即厌弃主观的臆想而尊崇客观的考实,通经博古,经世致用,以此推动乾嘉以后礼学研究在经典文本考证和复兴礼学思想上的发展,确立学以载道,以文化人,“以古礼证今俗”的致用方向。如《周礼·天官》有论及赋税之说,即“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金氏《礼笺》卷一《九赋九式》之“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条下曰:“待,犹给也,此九赋之财给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稍秣,即刍秣也,谓之稍,稍用之物也。丧纪,即丧荒也。赐予,即好用也。”金氏承郑玄之说而更为之补充证实,以为前六赋皆以远近为别,以征土地产物。故称“万民之贡,即九赋所敛者是也。九赋给九式之用,其藏中余见者,则职内叙其财,以待邦之移用,若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仓人掌粟入之藏,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皆其充府库者也”。金氏以万民之贡以充府库,不仅涉及赋税收入,也兼有分配、贮备和荒政,乃至于还有“遗人”“仓人”的职掌与“以待邦之移用”的问题,对于关市山泽币余之赋和征诸商旅矿渔林业税赋,从《周礼》的制度体系出发,揭示赋入和赋出的民生实用。金氏精通量地均土分民之法,结合九赋九式之解,所言简要赅括,颇为孙诒让《周礼正义》认可。孙氏曰:“金榜云:九式者,冢宰以岁之上下制之,其式凡九……丧荒,《大府》作丧纪凶荒,事出非常,不可预为节度。遗人、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仓人辨九谷之物,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故耕三余九,耕九余三,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此治凶荒之道也。”孙氏摘取金榜所引《周官》《墨子》和《国语》的文献为例证,以证明天子之田九垓,以食兆民,王取经入焉,以食万官。《周官》以九赋待九式之用,禄食宜在九式中。《墨子》有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凶则损五分之三,饥则尽无禄,以为上古之遗法。金氏精通《周官》,深知“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意,故其《礼笺》也志在以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追溯古礼,以“礼学经世”,将徽州谚语“九章大学终言利,一部周官半理财”蕴涵在经邦济民的社会实践中。
经世致用是历代学者为人为学的终极追求,除了少数人享有朝廷经筵之席而具治国理政的机会外,更多的学者关注点多在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问题上。如冠婚丧祭、井田乡遂、兵农赋役,乃至于一器一物,皆事关民生。金榜研治礼学,随处体现出现实需求和人性关怀。如《礼笺》卷一《周官军赋》,在引用《周官》本文,旁征《左传》《司马法》《荀子》和《刑法志》后,指出《小司徒职》“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乃为《小司徒》与《遂人》之联事通职,不以乡遂都鄙异制,可谓经史贯通,条分缕析,观点新颖。金氏深知“济民”之“用”,必先“通经”之“体”,由质测通几而至事功实用,认为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其言用民之数与《小司徒》上中下地,可任人数本相出入。即如《左传》子产所言:孔张有禄于国,有赋于军。则有禄田即有军赋。足见金氏论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为江藩《汉学师承记》称赏和节录;后世胡培翚、黄以周、孙诒让、曹元弼等礼学名家也竞相采摘引用之,更为当下研究礼学者所尊奉。事实上,《礼笺》名为考古笺疏,但所涉猎皆为国计民生之事,举凡礼乐铨政、赋役漕运、军伍屯田等富国强兵的举措方略,均可由此窥见其渊源脉络,从中可知作者的政治眼光和用心所在。譬如,张惠言坐馆金榜家学之时,就曾秉承金氏论说《周官》之意,拟作乡村规范条例,包括“储公费”“专责成”“杜扰累”“谨编审”“谨巡更”诸事务,并作“十家牌式”以为村民自治之法,即以十家为一联保门牌,共相亲睦,互相稽察,举不法者以告官究处,如若知情不报,则十家同罪。此法上承古制,变通施行,于乡村治理颇为有效。故张氏曰:“(金)先生为乡里,奋身创此良举,幸而抚军廉正主持于上,又幸而郡县之长皆臂指相使,搢绅之族皆同心俯首,相与协力于下”;“愿先生条其利害,酌其便宜,更咨抚军,请札饬到县,遵照奉行,则可以必行而无弊。先生之功于乡里,岂一时哉?”金榜以翰林居乡,在操持家务族事的同时,仍以国事为重,急国家之所急,因地制宜地制定乡村规则。同时,利用朝野人脉关系以及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巧妙地与地方官吏和谐沟通,“出死力为乡里捍卫”。并针对“方今官吏愦愦,惟利私是骛,民生之计,视若越人之肥瘠”的现实境况,出谋划策,“绸缪民政”以兴利除害,以成关心民瘼、保境安民之效。
金榜出身“东南邹鲁”的徽州,深知社会风尚的改观、徽商立世的法则,需要具备比别处更为凸显的儒风民俗来为“礼仪之邦”的形象做理论的支撑,故其治学不离天道人伦与儒家政治理念,而尤重礼仪与礼制的研究。如《礼笺》卷二《冠衰升数》就探讨了丧服“练后服制等差”的典制问题。金氏首先胪列《仪礼》中的《丧服》经文,认为“斩衰二章、齐衰四章、大功二章、小功二章、缌麻一章,咸未着其冠衰升数”。而“后儒因齐衰、大功、小功各具三等,遂分降服、正服、义服当之”。并且“《丧服经》大功布衰裳,三月,受以小功衰。传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大功章具有降服、正服、义服,同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则五服冠衰升数,不以降服、正服、义服为差审矣”。又案:“传者于斩衰菅屦下,但言衰三升,足明君父至尊,衰同升数,则三升有半为布带绳屦者言之,是为斩衰二等。”金榜所述,依据《仪礼》所述由初死至练的冠衰升数之变,由此可以明了练后服制之等差。此说颇为后学黄以周、曹元弼、陈寿祺等所称道。黄氏《礼书通故》曰:“金榜云:传于‘斩衰菅屦’下,但言衰三升,足明君父至尊衰同升数,则三升有半为布带绳屦者言也。江筠云:三升有半之服,专以公士大夫之臣言。益其衰之升数为三升有半,以异于三升之凡为君者,正别嫌明微之意。又《经》不缀于臣为君之后而独着之末条,则等杀亦从可知矣。以周案:金、江说亦备一义。”父母之服制,于丧礼最重。《仪礼》丧服中之正尊降服等问题,历来莫衷一是。明清学者多从礼贵变通的角度对实践礼学予以“权”与“变”的往复辩证,寻绎推阐,颇有发明。金榜囊括典制,坚守原典,遵循“礼时为大”的基本原则,在固守大经大法的前提下,从容践履礼仪过程中的经与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既能摆脱礼教纲纪的教条桎梏,也使得古礼能在现实生活中落到实处,且使礼学自身也具备了一定的文献印证与实证的活力。

三、礼以经世,化民成俗
金榜生活的时代,考据学已经成为主流学术,学者研治礼学也一改前朝盛行的《书仪》和《家礼》之类的“私家仪注”,而趋向以经典文本考证为法式,辅以器数、仪节等实体物的直观参证。作为“皖派”江、戴之学的中坚人物,金榜深知“礼之原于性,所谓致知也”,必先习其器数仪节,然后“行之出于诚,所谓诚意也”。金榜生于礼仪之邦,深怀致用精神和经世情怀,以为己为人之学奉献社会,以求矫正人性偏弊,整饬社会秩序,进而达到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的目的。这也是承平之世的清儒“事功”之学得以切实施行,礼仪之道得以“人文化成”的具体体现和展示。如《礼笺》卷二《降其小宗》论及《仪礼·丧服·记》“为人后者于兄弟降一等,报;于所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这一问题时,金氏本着“夫礼,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以及“缘情制礼”的丧服观,注重个人之情与家族之谊。在经籍文献考证上努力发掘上古宗法秩序,以新的情理观与落后的“存理灭欲”学说相抗衡,在反对过度欲望的同时,也引导人之情欲的正常诉求,成为近代礼教批判的理论先河。金氏论之曰:“所为后之子谓为人后者,自所后之兄弟目之为所为后之子,其服之如子。今本作‘于所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记》言小功以下为兄弟,是兄弟为小功以下通称,不得更称兄弟之子。唐石经误与今本同。兹据贺循为后服议校正。斯无疑于小功以下为兄弟之义矣。”民国学者曹元弼深信金氏此说,曰:“为人后之礼,言人人殊,惟金氏此说与经传吻合,确不可易。”吴廷燮则从石经校勘的角度,对金氏所言提出驳议,增进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补充和丰富了经文考证的内涵,曰:“若所释《仪礼》‘为人后者于兄弟争一等’一节,据贺循‘为后服’议,作‘于所为后之子兄弟若子’,遂改经文。胡氏《正义》谓戴氏校《仪礼集释》,程氏《丧服足征记》因之,说虽不同,皆以石经为误。卢氏《详校》、阮氏《校勘记》亦用金说。胡氏力引凌氏说辟是书改经之非,谓《通典》刻易淆,未可据以改经,则是书亦有可议者。”君子秉礼以修己,先王制礼以治人。古人如此汲汲于古礼字句的探研,看似与国家兴亡无关,实则可以窥见学者胸中志向时刻记挂于天下万世,揖让进退之节中寄寓了继绝学、开太平的深沉之思。
金榜之学以“六经皆礼”为主导思想,秉持着礼以经世、含摄风俗的理念,潜移默化地引导学术思想、社会风俗和道德纲常的和谐有序发展。故其研治礼学多溯本求源,从经典文字的考证上探求圣贤本义,既不昧于系统思想的提炼,也不会在器物制度的考释上流于空疏,二者相互证发,所言之意多为后学者所承用。如《礼笺》卷二《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问题,金氏针对宋以后儒者竞相“以理释礼”,甚或篡乱经籍的做法,十分反感,故倡言以汉唐笺疏为本。认为“何有命为母子为之三年乎?故知主谓大夫士之妾与妾子也”。又因为“其使养之,不命为母子,则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者,与《小功章》曰“君子子为庶母之慈己者”,笺注皆谓:“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嫡妻子。彼谓嫡妻,子备三母:有师母、慈母、保母。慈居中,服之则师母、保母服,可知是庶母为慈母服,《小功》下云其不慈己则缌可也,是大夫之嫡妻子不命,为母子慈己加服小功。若妾子为父之妾,慈己加服小功可知。若不慈己,则缌麻矣。”金榜以郑玄笺注为准,分别师母、慈母、保母三种不同情形,将复杂的事情条分缕析,各得其所。并进而阐明了“《丧服》小功章中,君子为庶母慈己者,郑玄注引《内则》三母,而独言慈母,举中以见上下,是知大夫有三母也。为之服小功,若诸侯之子,三母则不服也。虽在三月之前,其实三月之后,养子亦当然也”。金榜所言“《礼笺》之名,盖首其义”于此可见一斑。此论也多为其后胡培翚、朱彬以及黄以周、孙诒让等所采择。虽然后出转精,然金氏筚路蓝缕之功亦不可忽视。如胡氏《仪礼正义》取金榜该书“嫡子妾子同”之说,而不取其君子专指士之说,曰:“今案此庶母慈己之服本为嫡妻子而制,故此注主嫡妻子言。但妾子养于他妾亦为慈己,故齐衰三年章注又兼妾子言。昭十一年《左传》‘其僚无子,使字敬叔’,此妾子养于他妾者也。金氏谓嫡子妾子同,是矣。至君子之名,各书多以称士,不必定指大夫。此注言大夫子而不及士子,与金氏专指士子言,皆偏也。《丧服》‘慈母如母’及‘庶母慈己’二条,盖皆大夫士之礼,诸侯以上无之。《曾子问》‘子游问慈母,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郑注:言无服也。此指谓国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孔疏引熊氏云:士之嫡子无母,乃命妾慈己,亦为之小功。知者,以士为庶母缌,明士子亦缌,以慈己加小功,故此连言大夫士也。是郑亦兼士言之矣。”胡培翚乃凌廷堪高弟子,于学术辈分上可谓金榜之再传,不仅在学问上传承“皖派”之脉络,更在学术道理上秉承前贤“惟实学”“求真是”的精神风范,敢于对前贤“所持论相抵牾”和“尚不敢附”,体现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空所依傍的精神。金榜以《礼笺》独立于清代学术之林,虽然所言未必全是,仍有可商之处,也可因此而追溯原始,讨论问题症结所在,以便后学者进一步的探究和提升。
金氏《礼笺》一书长于质疑,本于求是,虽忠于郑注,间有辟宋之绪,但无过激之弊,每一篇每一说皆足以承前启后,而乾嘉礼学之精诣亦汇聚于此,故其影响后学也在在可见。凌曙在《礼论略钞》的三十余篇中,较多地选取了徐乾学、金榜、程瑶田诸儒的论文,其中金氏竟占三篇(“小功章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阴厌阳厌”“丧服小记附于其妻”),对金氏所论汇辑罗列,钩沉阐微,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民国张锡恭《丧服郑氏学》就直接引用金榜之说达二十余处,文中多见“金氏此说至为精确”“金说为是”,间或也有“误说,不可从”之语。金氏之后的礼学家如金鹗、凌廷堪、胡培翚、张惠言以及朱彬、黄以周、孙诒让等,对金榜之说尤为推崇,针对疑难问题,前说而后证,证伪或存真,促成了清代三礼学研究的蔚为大观。至于金氏礼学成就如何,可以姚鼐之言作为归纳,当是恰如其分。姚氏曰:“歙金蘂中修撰自少笃学不倦,老始成书。其于礼经,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断。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于郑义所未衷,纠举之至数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见其善而后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尽其真也。岂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鼐取其书读之,有窃幸于愚陋夙所持论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闻,得此而俯首悦怿,以为不可易者;亦有尚不敢附者。要之,修撰为今儒之魁俊,治经之善轨,前可以继古人,俯可以待后世,于是书足以信之矣。”可以说《礼笺》的学术价值及其社会史意义正在于此。正如钱大昕所论学术之用道:“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后以法律约之,夫然后可以羽翼经史,而传之天下后世。”明道经世,阐幽正俗,也正是金榜之辈作为富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居乡绅衿的使命所在。他们着眼于宗法重建,依凭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与信念,固持修齐治平之理,灌输为善之心,以此“振兴久废之礼,提撕彬彬之仪”,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彬彬有礼”的士绅社会,其自身也成为雄踞一地的文化世族和乡邦桢干,国人于此观礼,四方于此问俗。对此现象,王汎森曾有过描述:“士”的阶层靠着儒家的“礼”与僧、道区别开来,他们为了与僧、道在思想及生活礼仪方面竞争,在猛烈地批判佛、道及深受佛道浸染的思想及生活文化的同时,致力于建立“真正的”先秦儒家传统。但是因为魏晋以来佛、道之说已渐渐渗入儒家,为了与它们作更深刻的区分,他们发掘甚至创造更为纯粹的传统,以确立自己的独特性。“士”阶层这种追求纯粹的、好古的、强调儒家独特性的倾向亦日益趋古,行为方面则要求回到古代儒家礼仪,他们以严谨的文字训诂、文献考证来建立一个更忠于原始本义的儒家传统及生命礼仪,以之与佛、道或流俗思想文化与生命礼仪相竞争,甚至企图加以取代。金榜之辈如此全力为儒家经典和正统文化“循名责实”,以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对抗流俗,弘扬正气。同时将“皖派”礼学传承下去,因此而博得乡邦后学的极力称扬:“吾乡铿锵说礼经,曰若慎修江先生。山林肇辟起南国,提唱后学经昌明。同时高弟海阳戴,羽翼先生功亦宏。吾生也晚未及见,徒尔仰企心怦怦。传经幸赖有耆宿,依归得侍夫子程。柘田殿撰共探讨,时聆奥诣开昏冥。后来继起凌进士,群经纷纶莫与京。”由此可见乾嘉汉学得以兴盛,徽州礼学与有功焉,其中金榜礼学的“奥诣开昏冥”也功不可没。
“传家礼教敦三物,华国文章本六经。”金榜出身于徽商之家,抛却功名,退隐居乡,在操持家族的繁杂事务之余,又以研治礼学作为完善自身、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其《礼笺》一书意在“存古”而志在“开新”,更新于汲古、自振于流俗,引领当时周围学者把目光由内在礼学思想和伦理道德的争论,逐渐转向对外在社会制度和人性优劣的密切关注,为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支持。金氏在阐释建邦立极、治国理政之类大问题的同时,也时刻不忘关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深层文化根基,解决民众的现实生存和精神信仰问题。皖南的徽州也正因为有了如金榜一般居乡之士为人为学的模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潜移默化中给予了这块宗法制度的乡村社会以指示和引导,使之成为敬宗睦族、恤党赒里而文质彬彬的礼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