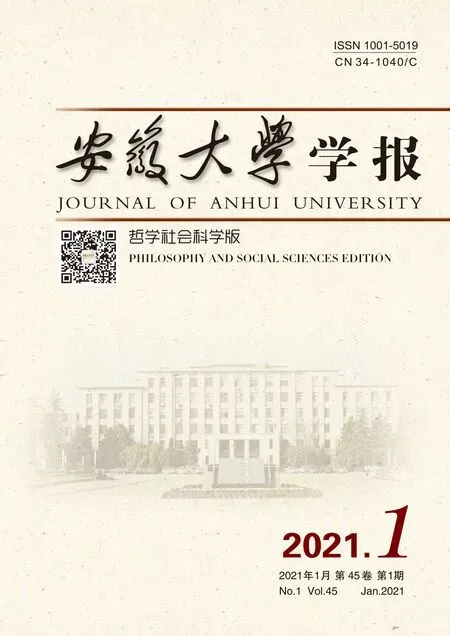徽州谱牒中“溢真”现象的文本解读
——以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族为中心
周晓光,江一方
徽州多世家大族,历来重视家谱的修撰工作,素有“三世无读书,三世无仕宦,三世不修谱,则为下流人”的民谚。清人赵吉士称:“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丁繁衍与死亡、迁徙与出继、族产增减等,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旧谱的记载在一段时间过后便不再适用于宗族的现况,宗族的现状需要新谱记录以备将来查阅,这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宗族需要续谱的基本原因。徽州家谱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家谱修撰中“求真”与“溢真”特性并存,亦受到学界的关注。但关于徽州家谱“溢真”原因的探究,尚有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以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族(以下简称“江氏”)为中心,通过考察该宗族万历四十四年(1616)《重修济阳江氏族谱》(以下简称“万历谱”)以及乾隆五十五年(1790)《重修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谱》(以下简称“乾隆谱”)所载内容,对徽州谱牒的“溢真”特性以及“溢真”现象背后反映的宗族史建构加以探究,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新安东关江氏宗族及其谱牒修纂
东关江氏为徽州望族。据“乾隆谱”载,江氏迁居徽州始于唐代中叶,始迁祖江湘,“唐十贡元,太和年间授建康刺史,宦游新安,居郡城东关,为吾族始迁祖”。自始迁祖以下传至十八世,子孙逐渐繁盛,十八世后分为“文、行、忠、信”四派。明初以降,江氏人才辈出,代表人物有正统戊辰(1448)科进士、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江真,正德年间西平县令江珙,万历年间福建都转盐运使司运使江大鲲等,清初则有新安画派代表人物僧渐江、西安知府江濯等。江氏崇尚儒术,重视教育,南京户部右侍郎方弘静(1517—1611)称:“余自生发初燥,即闻歙之有江,以经术起家。”据我们统计,江氏在明清两朝共有进士2名,举人13名,另有大量国学生、郡廪生、邑庠生,宦者多有美名。例如二十五世江珙,“歙县人,正德末知西平县,公廉勤俭,积日所为,朔望率其属以告于神,人有馈生鱼者,计其直授之,由是私馈遂绝。秩满迁去,百姓立祠祀之”。江氏多与世家大族联姻,万历年间族长江存梅妻即出自东门许氏,为名宦许国同宗。嘉靖《徽州府志》载:“江氏宗祠有二,一在龙舌头,一在桃源坞。”龙舌头、桃源坞均位于歙县东关江氏聚居地附近,相距不远,且两座宗祠在江氏族谱中均有载,可见该族在当时有较大势力。
江氏重视谱牒的修撰。据“乾隆谱”记载,从北宋元符年间至乾隆五十五年,江氏先后九修宗谱,前七次所修谱牒均已亡佚,今存“万历谱”和“乾隆谱”。
万历四十四年《重修济阳江氏族谱》为一部典型的晚明徽州士大夫所修谱牒。该谱为家刻本,共八卷,内分《凡例》《祠规》《宗支世系》《诰命》《节孝》《隐德》等节,现存六卷,藏于国家图书馆。关于该谱的修撰情况,从所载序文中可见一二。方弘静《重修新安济阳江氏族谱序》载:“民部江君(来岷)俨然造焉,手出一函而肃容请曰:‘家叔祖鲲,生鄣山,籍楚雄,守石阡,越万里而寄八行,将因旧谱而新之,敢乞夫子一言以光首柬?’”可知族人、时任石阡知府江大鲲提出新修宗谱的建议,并致书方弘静请序。江大鲲一方面担心谱牒长期未修,“岁久而迹无征也,谓人众而心难合也”,另一方面受到自身“生不逢辰,家遥万里”经历的影响,希望通过修谱的方式寄托思乡之情。他在福建都转盐运使司运使的任上借省墓之机总理谱牒的修撰,具体编辑工作则由户部浙江清吏司主事江来岷负责。方弘静序作于万历甲辰(1604),谱牒付梓于万历丙辰(1616),可见江氏此次修谱历时十余年之久。该谱《凡例》云:“徽地窄人稠,间有迁徙,为何故、迁某处,各纪其实,令迁者不忘所自,而居者不忘所迁。”为此,该谱专门列出一节《迁移》,详细记载迁徙人员信息,这在存世明代徽州家谱中并不多见。
乾隆五十五年《重修新安东关济阳江氏宗谱》为木活字本,共二十四卷,具体又细分为《表敕》《凡例》《祠规》《古世系图》《世系图》《诰命》《旧谱序》《传》《绅士录》等内容,现存二十卷,藏于上海图书馆。该谱的纂修分工明确,由族人江国忠、江淳英总修,候补训导江上锦编辑,另有八人负责分修、七人校梓,并有专人负责绘图工作。此谱的《墓图》一节较有特色,该节图画绘制精美,数量多达28幅。除墓地情景外,还录有该墓地地契、地税等相关文书,记载极为详细。据江国忠《重修家谱自叙》载:“今所信守丙辰本也,椒聊蕃衍间,亦不常厥居。”该序又载:“倘不急收而使不离散,则他日将有相视如涂人,而为眉山苏氏之所悲也。”可见江氏在万历丙辰之后人口流动性增大,族内存在人情淡薄的趋势,故亟须一部新的族谱以“联属族义”。江氏此次修谱活动是以“万历谱”为依据的续修,两者相隔一百七十余年,具有延续性与关联性。
二、清代新安东关江氏族谱中部分“溢真”现象考辨
“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相较于“万历谱”,新安东关江氏“乾隆谱”的卷帙大幅增加,除接续一百七十余年间各支各房的世系传赞外,还补充了大量“万历谱”未载的内容。经我们考证,“乾隆谱”增补的一些内容可信性值得怀疑,也就是说存在明显的“溢真”现象。
首先,在世系图方面,“万历谱”的世系自始迁祖江湘始,“乾隆谱”则由始迁祖追溯至得姓之祖江元仲,并对“万历谱”中记载的早期祖先事迹予以一定程度的修改,列举部分如下表:

表1 新安东关江氏族谱中祖先身份的变化
由表1可见,“万历谱”对早期祖先的身份记载较为简略,“乾隆谱”对早期祖先的记载则趋于丰满,并且对“万历谱”所述先世身份、官职等级的记载有所提升。据“乾隆谱”载,江氏自八世起有多人“举明经”。如“举明经”事为真,历代府志、县志应当有载,但在弘治《徽州府志》卷六《荐辟》、嘉靖《徽州府志》卷十二《荐辟》、乾隆《歙县志》卷八《荐辟》中,江氏在明朝之前的人物均未收录。换言之,这些江氏族人的“举明经”身份并未得到徽州府官方的认可。显然,“乾隆谱”记载的这些人物事迹可信度存有疑问。
除早期祖先事迹的记载外,“乾隆谱”世系图中关于仕宦封赠的记载也存在不合礼制之处。明太祖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定文武官员封赠例,一品封赠三代,二品、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一代”。以“乾隆谱”中二十六世江墉为例,“赠奉直大夫、南京户部浙江清吏司主事”。南京户部浙江清吏司主事是江墉之孙江来岷的官职,“奉直大夫”为明代从五品文官升授散阶,户部主事则为正六品,两者均未及三品。故按常例,江来岷可封赠一代,其祖父不能获赠其官。此外,“万历谱”未载江墉获赠之事,“乾隆谱”卷十五《封赠目录》中未收录明廷封赠江来岷祖父母的敕命,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一《恩荫》、乾隆《歙县志》卷十《恩封》中仅载江来岷父江文锦获赠知县,亦未有江墉记载。因此,“乾隆谱”关于江墉“获赠”的记载,似有夸耀之嫌。
其次,在家传方面,据“万历谱”目录所载,该谱首传传主为二十世江仲实。“乾隆谱”与追溯得姓之祖相呼应,增加了一些江仲实之前人物的传记,这些传记中的记载亦有可疑之处。据“乾隆谱”载,江氏始迁祖江湘之五世祖江彦绍,“字允隆,唐贞观初,举进士第一,历官礼部侍郎,配谢氏”。然而,江彦绍在“万历谱”中无任何记载,为佐证这一人物的事迹,“乾隆谱”在家传中新列出一篇《彦绍公传》:
江彦绍字允隆,本考城人,居金陵,少以文学名。内行修洁,人咸以孝友称之。贞观初举进士第一,历官礼部侍郎。初为护国兵马使时,尝随文皇帝讨李密,经考城,上见汉巨孝墓颓坏,问其子孙,俾修厥墓,友人孔颖达为奏曰:“此即陛下小臣彦绍远祖也。”遂召彦绍,赐钱五百缗以整之,树碑曰“大汉巨孝江革墓”,彦绍因以余钱营产备祭祀焉。孔颖达撰。
这段文字中有多处疑点。其一,唐初是否有“护国兵马使”之职存疑。据严耕望通过墓志等史料考证,兵马使一职出现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玄宗开元时代,节度使府已有都知兵马使”。且唐代兵马使前缀多与兵种、行军阵列、后勤任务相关,如“马军兵马使、前军兵马使、营田兵马使”等。其二,唐太宗讨伐李密一事存疑。《旧唐书·李密传》载:“时右翊卫将军史万宝留镇熊州,遣副将盛彦师率步骑数千追蹑,至陆浑县南七十里,与密相及。彦师伏兵山谷,密军半度,横出击,败之,遂斩密。”可见李密于武德二年(619)叛唐后为唐将盛彦师所杀。《旧唐书》太宗本纪亦不见太宗讨伐李密的记载。其三,孔颖达上奏一事存疑。《旧唐书·孔颖达传》载:“属隋乱,避地于武牢。太宗平王世充,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唐太宗平王世充是在武德四年,孔颖达在此之后才入唐太宗麾下,又如何在此之前向太宗上奏?此外,“乾隆谱”还在卷首列出一篇江彦绍《上唐文皇帝表(并敕)》,此文落款时间为“贞观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江彦绍的职务为礼部侍郎。据严耕望考证,自贞观六年(632)至贞观十五年,礼部侍郎一职均由令狐德棻担任。令狐德棻在《旧唐书》《新唐书》中均有传,若江彦绍曾担任礼部侍郎为真,《旧唐书》《新唐书》便应有其传记或其他相关记载,然而在这两部史书中却无江彦绍的任何痕迹。唐代林宝所修《元和姓纂》中有江总、江溢父子的记载,但亦无江溢之子、曾担任“礼部侍郎”的江彦绍的记述。“乾隆谱”新增的江彦绍事迹可信性值得怀疑。
“乾隆谱”中还增加了东关江氏始迁祖江湘的传记《刺史江湘公传》:


再次,在谱序方面,“乾隆谱”对“万历谱”所载谱序内容做了一些改动,以“万历谱”所载宣德三年(1428)唐子仪序文的部分内容为例:
今考谱,托始于十贡元湘,来自建康,因官于歙,其后遂为土著。由兹溯而上之,往谍失传,莫可知其世次,不可以臆度,当阙其疑也。下而至四世学谕藻,七世郡马复亨尚郡主,官学士,十八世副使巳翁,至我圣朝洪武年间,廿世弘六公子任以志人召,除广西之横州永淳县知县。
“乾隆谱”中将这段文字改为:
今考谱,托始于十贡元湘,来自建康,因家于歙,其后遂为土著。下而至四世学谕藻,七世郡马复亨尚郡主,官学士,十八世副使巳翁,至我朝洪武年间,廿世宏六公子任以人才选召,除广西之横州永淳县知县。
可见“乾隆谱”将始迁祖江湘迁徙原因由“因官”改为“因家”,并删去“由兹溯而上之,往谍失传,莫可知其世次,不可以臆度,当阙其疑也”一句,删除“我圣朝”的“圣”字,“弘”字避乾隆帝讳(弘历)改为“宏”字;又将序文中关于江子任出仕的记载修改为“以人才选召”,表明江子任是在众多人才中脱颖而出,被朝廷选中而担任县令。相比于“以志人召”,“乾隆谱”的记载进一步美化了江子任的才能。
此外,“万历谱”唐子仪序文中其他内容也有或多或少的修改,如落款日期将“宣德三年,龙集戊申,春二月花朝前”改为“宣德三年二月”。而“万历谱”另外一篇序文《尚书总公序》中关于陈朝末代宰相江总的事迹则被大幅删改,其像赞均被删除,文章篇名改为《江黄门先世真容序》。可以说,“乾隆谱”中所载这两篇序文已非原貌,而这两篇序文也是“万历谱”的“旧谱序”,“万历谱”在修撰时是否对旧谱中的原文有过修改?由于“万历谱”之前的江氏宗谱已佚,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乾隆谱”对“万历谱”的内容做了修改,乾隆年间江氏进行了宗族史叙事的重构,而重构又缺乏相应的史料支撑。
三、清代新安东关江氏族谱中“溢真”现象原因探析
新安东关江氏“万历谱”中也有“溢真”现象,如唐代江氏始迁祖江湘的画像后附有南朝梁新安郡守任昉的像赞(“乾隆谱”改作唐歙州刺史任宇),落款时间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的《尚书总公序》中出现“杜工部诗之”之语,等等。但是,较“万历谱”而言,乾隆五十五年江氏续修宗谱时出现的“溢真”现象更为普遍,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宗族自身原因来看,存在以下三方面情况。
第一,入清以后,江氏人丁日众,但出现了原先赖以起家的儒业后继乏力的状况,“乾隆谱”的修撰者希图对宗谱叙事体系进行修改,通过进一步颂扬先世业绩的方式激励族人。在科举上,截至乾隆五十五年,清代江氏仅出了一名进士,三名举人,其中的进士江发、举人江遥光只是祖籍东关,数代前已入籍浙江乌程(今湖州)。“乾隆谱”修撰者之一江上锦说:“吾宗少为文章雄伯者。”在仕宦上,据我们统计,入清以后的140多年间,江氏入仕人数不及万历年间的一半,自康熙年间江发以后,年轻一代族人向学、出仕者更是寥寥无几,并且职级同明中后期江氏族人差距悬殊。为此,江氏设立文会,以“崇奖冠裳,合一姓之俊髦,而泽以诗书者也”。在此背景下,“乾隆谱”构筑了江元仲—江革—江统—江总—江湘的叙事体系,将史籍上有美名的江姓人物作为本族的先祖囊括其中,又通过对唐、宋、元代先祖事迹的重塑,希望进一步起到敬宗收族、激励后人的作用。
第二,“乾隆谱”的内容需要与叙事体系及宗族的现实情况相匹配。如前文所述“万历谱”唐子仪序文中的“由兹溯而上之,往谍失传,莫可知其世次,不可以臆度,当阙其疑也”,表明作者认为江氏自江湘以上的世系已经失传,不应随意猜测,有疑当阙。又如,“万历谱”刘定序文中有“又奚必眷眷建康之远祖也哉”之语,表明该序作者赞同不述远祖的做法。这些内容与“乾隆谱”追溯江湘以上世系的做法相矛盾,故“乾隆谱”将其删去。据“乾隆谱”载,清代大量江氏族人向苏浙一带迁徙,因商而迁的可能性较大,乾隆丁酉年(1777)的江氏族长江理亦有从商经历,“公以家累故,弱冠弃举子业,就贾于桃城,已而迁东海”。“万历谱”方弘静序文中对徽人从商颇有微词,这些看法在“乾隆谱”中被删除,或许即有此方面的考虑。

就外部原因而言,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乾隆谱”的修撰受到官方“谱禁”政策的影响。乾隆四十六年,安徽布政使下令严查宗谱内容,除避讳外,一些词语如“肇兴大业”“王父”“王大父”“天佑”等,被视为“僭妄”需要更正;而“凡谱内尧、舜、禹、汤、文、武圣讳及四大贤人,帝、圣、君、皇、王、后、朕、御、龙、凤等字,概不许取名”。“万历谱”载二十八世江自春“配张氏,生六子:一尧、一舜、一禹、一汤、一文、一武”,而“乾隆谱”则载江自春“配张氏,生子六:一荛、一蕣、一禹、一汤、一玟、一珷”。可见,“乾隆谱”的修撰者将江自春四个儿子名字中的“尧”“舜”“文”“武”改为“荛”“蕣”“玟”“珷”,应是为了遵守“谱禁”政策而做出的修改。又如,“万历谱”方弘静序中“况江之先姬之胤也”,在“乾隆谱”中被改为“况江之先伯益之裔也”。周文王、武王姬姓,清世宗名胤禛,这句话的改动也是为了应对“谱禁”而做出的修改。
第二,“乾隆谱”的修撰受到徽州统宗浪潮的影响。乾隆五十一年,以歙县地区济阳江氏为主的二十四支江氏宗族修有一部《济阳江氏总谱》(以下简称“《总谱》”),其中就有东关江氏。“乾隆谱”的修撰者江国忠、江上锦等人参与了此谱的编撰,东关江氏规定“廿四族江村会修总谱两本,统贮一匣封锁,藏宗祠内”。经比对,“万历谱”中所没有,“乾隆谱”卷十六中增加的一篇《汉谱序》、卷首《上唐文皇帝表(并敕)》、卷十七中《彦绍公传》以及江湘之前的人物传记,均与《总谱》中这些内容的记载一字不差。因为《总谱》修撰时间在“乾隆谱”之前,故“乾隆谱”中这些文章出自《总谱》的可能性较大。前文我们已经考证过《上唐文皇帝表(并敕)》和《彦绍公传》两文存在疑点,而《汉谱序》同样也存在较为明显的疑点。该序载“尚书省以(江革)孝行奏闻”,落款时间为永元八年(公元96年)。东汉初期如何有“尚书省”机构?又,此序落款“襄阳郡守裔孙相拜撰”。据乾隆《襄阳府志》载:“东汉建安中,魏武(曹操)得荆州,分南郡编县以北及南阳之山都,置襄阳郡。”可见襄阳郡的设立要到汉末,永元八年无“襄阳郡”这一行政区划,落款者的“襄阳郡守”身份亦存有疑点。歙县《总谱》中的《汉谱序》又似在乾隆三十一年婺源《济阳江氏统会宗谱》中永元八年《汉谱序》的基础上改动而成。“乾隆谱”的修撰者未经仔细辨识,而将此三篇文章原封不动地抄录到本族新修谱牒中,对新修家谱的可信度产生了影响。
四、关于徽州族谱“溢真”特性的认识
综观存世徽州族谱,江氏续修宗谱中的“溢真”现象并不是特例,其他徽州宗族续修的宗谱中也存在同样情况。换言之,在宗谱纂修发达的徽州地区,修谱者借续谱之机删改旧谱文献、对宗族史进行重构是一个普遍现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谱序的改动,从而凸显了族谱“溢真”的随意性。
比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休宁青山张氏在修本支谱时,录入嘉靖十二年(1533)《新安休宁岭南张氏会通谱》中的汪玄锡《岭南张氏会通谱序》,但删除了汪序中关于南宋绍兴丙辰年(1136)张成信旧序内容的大量论述。经查阅嘉靖谱世系图,张成信非出自青山张氏一支,而青山张氏修撰的《新安休宁青山张氏世谱》亦未收录其序。基于支谱的性质,青山张氏删去了汪玄锡序中与本宗关联性较低的内容。婺源官源洪氏所修谱牒中关于姓源、郡望的不同记载则更为典型。乾隆五十三年刻本《官源洪氏总谱》载程敏政所撰《歙西洪源家乘序》曰:“洪氏世望丹阳,在唐有讳经纶者,德宗朝为河北黜陟使,议罢方镇兵,左迁宣歙观察使。”明代万历年间官源洪氏修撰的《新安洪氏统宗谱》所载该序内容则为:“洪出共工氏,受封河内之共城,子孙推本水德之绪,加水于左,世望丹阳。在唐有讳经纶者,德宗朝为河北黜陟使,议罢方镇兵,左迁宣歙观察使。”而程敏政文集中的《洪氏族谱序》载:“洪出共工氏,受封河内之共城,子孙推本水德之绪,加水于左,世望燉煌。在唐有讳经纶者,德宗朝为河北黜陟使,议罢方镇兵,左迁宣歙观察使。”可见,万历《新安洪氏统宗谱》将程敏政原文提及的洪氏郡望由燉煌改为丹阳,而乾隆《官源洪氏总谱》进一步删去了程敏政关于洪氏姓源的论述。徽州洪氏姓源、郡望有二,一为“共(工)洪”,郡望燉煌;二为“‘弘’改洪”,郡望丹阳。自明代嘉靖年间以来,经过多代学者的辩论,洪经纶属后者已基本取得徽州洪氏的共识。与叙事体系相应,万历、乾隆年间官源洪氏谱删改了程敏政原文提及的洪氏姓源与郡望。
此外,已有学者考证,乾隆四十七年严田李氏修谱时对旧谱嘉靖年间金达序文改动明显,使之失去了原意;乾隆五十年庆源詹氏修谱时也对成化年间旧谱王汝舟序文进行了修改。上文提及的婺源《济阳江氏统会宗谱》中永元八年《汉谱序》作者为“文公”,在1919年婺源济阳江氏续修的《济阳江氏统宗谱》中则加按语“开化谱载:文公班固撰”。班固在永元四年即已去世,又如何在四年后撰文作序?显然,该句按语记载的可信度存有疑问。
谱序改动之外,徽州家谱的“溢真”还体现在家谱的世系、家传、文献等方面。本文讨论的江氏族谱,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
谱牒虽为“一家之史”,但与传统意义的史书有所不同。早在明代正德年间,休宁人程曾就指出了谱牒与史书的区别:“史则善恶备书,谱则载其善,而过失略焉。”可见,徽州谱牒是根据“载其善”这一宗旨而修撰的。家谱面向的是本宗族成员,前世的辉煌无疑能够引起后辈的共鸣,先祖的业绩越高,教化后人的榜样作用也就越强。而“宗族要在社区立足,要争面子,亦需要修谱、续谱”,基于祖先崇拜以及宗族发展的现实需要,重构宗族史叙事体系、重塑祖先事迹是必要的,续谱无疑为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族谱中的“溢真”现象是谱牒“书善不书恶”特点的产物,也受到了宗族本身及外部因素的影响。从修谱者角度看,“溢真”对宗族发展有积极的一面。但作为“一家之史”,“信史”应该是其基本要求,而谱牒中擅改族史、虚构人物、夸大事迹等“溢真”现象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一方面使得家族的历史严重失真,另一方面也使得家谱作为家族史研究资料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徽州地区存世族谱极为丰富,其中不乏同一宗族在不同时间修纂的多部谱牒,这为后人考辨家谱所载内容的真伪提供了便利。家谱中的“溢真”内容虽然可信度不高,但亦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分析比较,可以揭示其背后隐藏的人为建构色彩以及宗族、社会变迁情况。从整体上看,徽州家谱的修撰理念较为丰富,除受“谱为一家之史”观念影响外,宗族现实需要以及外部环境亦在谱牒的编修中发挥重要作用。史学研究者在使用家谱文献时,当采取谨慎的态度,通过与正史、方志记载比对,以及家谱不同版本间的校勘等,考辨史料真伪,并加以合理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