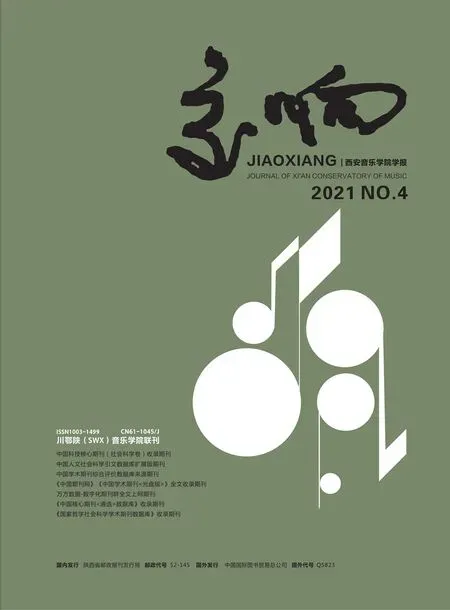游走的边际:诺曼·莱布雷希特音乐批评理路探赜
●张 晨
(沈阳音乐学院,辽宁·沈阳,110818)
诺曼·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1948-)是当今炙手可热的古典音乐评论人、专栏作家、小说家。他生于伦敦,曾担任过《旗帜晚报》的助理主编,为《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华尔街日报》《卫报》等报刊撰稿,他的十余本有关音乐的著作被翻译成17种语言,其中包括优选热销的《大师的神话》《谁杀了古典音乐》《音乐逸事》《永恒的日记》等。他的博客Slipped Disc是英语世界阅读量极大的古典音乐自媒体。由于他在音乐评论方面的卓越表现,其作品逐渐引起国内古典音乐从业者、爱好者的关注,诸多作品已被翻译为中文。2019年,上海音乐学院获批国家艺术基金《歌剧理论评论人才培养》项目,莱布雷希特于同年7月7日到访该项目组,进行了有关音乐评论者的资质、音乐评论的职责与方法、写作实践等相关内容的讲座。通过对他的言论和诸多文论进行分析,可见他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已形成了一个相互映衬、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共同体。本文试图针对莱布雷希特近年来出版的作品,从他的写作方式、音乐批评理路与叙述策略进行深入思考,试图以此来审视其音乐批评的写作方式和读者随着时代而转变的解读视角。不可否认,后现代理论和潮流已经浸入到当代每个人的生活和思考中,莱布雷希特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股潮流的影响。
一、时代的追问:谁是中心?
莱布雷希特的写作范畴以评论古典音乐著称,其作品独具特色,在时代大潮中一跃而起。他的音乐评论具有广泛意义,视角犀利,语言尖锐。他将这种文体运用得游刃有余,成为精彩的样本,当然也受到过不少非议。音乐批评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地理解,它是专业写作的一种类型,通常是为了即时发表、评估,涉及到音乐和音乐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广泛地说,它是一种评价音乐的思想,可以对音乐做出与评价有关的描述,并运用于专业的批评写作,这些思想在音乐教学、音乐对话、个人反思以及音乐史、乐理和传记的写作中都可能出现。[1](P670)音乐批评的解释性问题一方面包括批评语言与音乐、听众体验的关系;另一方面包括批评语言与艺术批评、文学、哲学等其他话语之间的关系。主观性和客观性兼具是音乐批评行为所预设的文化能力,读者在诠释和评价的过程中会反观叙述的主体。这样就形成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音乐史的研究往往和音乐批评相混合,史学家发表的观点恰恰是他所阐发的评论,这是一个写作者作为叙述主体的时代,现在的人们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20世纪的学者在承认过去的确真实存在的同时,在现代史学不断扩展的观念引导下,对史料有了崭新的理解。新的观念认为,研究历史的史料收集者、考古者、编撰者无法完整地书写历史,他们能掌握的不过是历史洪流中的某一片段,甚至是片面的。而恰恰是历史的书写者以自己掌握的材料、书写方式将他所认识的历史写下——尽管他们尽量地做到公正与客观。也是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叙事理论与研究兴起。由于史料不能完全涵盖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加之史料的遗存性,因而对于史料的态度、视角及看法成为了书写的要旨。在一战前,美国的历史学家致力于对史料的搜集考订,而在六十、七十年代以后,如何结构、如同建筑师般运用这些史料成为风潮。这股风潮兴起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史料越来越多地被挖掘,找到新史料越来越难。这同样适用于音乐领域,大历史的著史观促进了音乐历史书写的转变。
“史料”与“史实”的关系可以显现于对重构论、建构论、解构论的不同解说。视角的转变对于研究结果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重构论者呼吁,历史学应当还原历史的原本风貌,兰克的名言“如实直书”很精确地表明了此观点。该学派认为,史料中隐藏着已发生的历史真相,如果史家能够排除偏见和固有观念并秉持史学家法来看待问题,过去的真实片段自然会呈现出来。而另一方面,建构论者宣称,重构论朴素的经验主义套路不具备揭示过去真实存在的能力,历史学家也做不到想象那般客观中立,或许反而会妨碍过往历史的呈现。解构论是在前两点之外引发的,映射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史学领域的显著效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使西方史学理论发生转折,它将关注点由历史解释的模式转移到了贯穿于历史学家工作始终的历史学的文本性特征研究上,这就使历史文本化了。既然历史是回不去和不可再生的,那么史料即被纳入广义上的文本范畴。解构论的要旨是,作为产品的文本无法真正使我们接触到过去,历史学研究的终极产品是与文学家创造的产物一样,同为文学制品。[2](P151-153)在这种情境之下,研究者对历史真实性的渴求转化为对文学制品制成方式的探测,史学家的写作与文学家异曲同工。
原始材料或直接材料会以固定人群的视角,为了明确的目的,裹挟着读者的期待和想象写成。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自由”“进步”将人类历史视作一个连贯的、有目的的、有意义的过程的观念是被后现代主义斥为虚妄无边而要加以解构的“宏大叙事”或“伟大故事”。“历史”一词,除了有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之外,还有对这些事情的记载、考订、描述和解释之意。我们也是通过后者才对前者有所了解。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将解释凌驾于事实之上,在对史料性质方面有更为深入的理论认识的同时,将历史文本化,以致于用解释来主导事实,形成历史解释上的多元论立场。它在使传统史学根基发生动摇的同时,也为接受者以反思精神对待历史学的理论问题带来了契机。
至此,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下莱布雷希特的作品。他的写作并不追求“再现”,反而突出“我”的贯穿,这在《为什么是马勒?》中达到了顶点。从早期作品开始,他结构文论的方式已较传统论述有所偏离。比如,《永恒的日记》的时序安排以“日”为轴,在一个特定的日子中集合了不同年份发生的跨越十个世纪的事件会被并列在一起。作者也没有进一步阐述,只是列举了音乐史中各类由作者所择选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和“未来”被淡化,读者可以重建一个完整的故事,用共时叙述代替了历时叙述,以此献给音乐编年史之父尼古拉斯·斯洛尼姆斯基(Nicolas Slonimsky,1894-1995)。再如,《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是由他的诸多篇随笔并列而成,书名是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表达了作者被美国封杀的气愤,而与其他文章无关。这些文章的关联无踪可循,并无法指向“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这个中心。可以说,莱布雷希特的叙述策略已经偏离了历时和中心原则,代之以理想读者重新构建起的故事结构,作者、读者在其中承担着各自重要的责任。
二、走下神坛:后现代视角下的写作与创作
历史的叙述正在死亡。基于海登·怀特的学说——“同一件事可以成为诸多不同历史故事的不同要素……在三个不同的故事里,国王之死可以是开头,可以是结尾,也可以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事件。”[3](P10)无独有偶,艾玛·卡法勒诺斯认为,“现实世界里的时间可以想象为一块布或一条缎带,历史学家只切割其中的片段。切割部位决定着他们的阐释。”[3](P180)可见,现代主义已经进入了“去时间化”的阶段,重新结构意味着故事结局的改变。与此同时,话语与真实存在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学家不停地对历史世界进行加工提炼,从而根据资料来源的情况增补或重写叙事,被推测的事件并未被视为肯定的事实,但或许会实现。历史相对主义在历史世界的不完整性里获得了扭曲过去的必然空间。
莱布雷希特正是这股后现代风潮的经历者,尽管他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他的诸多作品,无论是视角层面,还是叙述方式上,都体现出了强力的趋向。他的写作特意夸大了某些个人因素,尤其是《谁杀了古典音乐》①,在受到欢呼的同时受到多重质疑。比如,有匿名者认为:“莱布雷希特如此描述古典音乐的心态对于古典音乐来说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方式削弱了这一概念,也因此削弱了流派的魅力。”[4](P40)米夏尔·怀特说:“作为对一个确实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的严肃回应,它失败了,部分原因是莱布雷希特的方法是狭隘的。固定在他想得出的结论上,部分原因的结论本身过于简单。”[5](P9)杨忠衡认为:“在《音乐逸事》中莱布雷希特显然轻鄙资本社会的虚伪,却也对社会主义的缺乏自由存有偏见。他希望借批驳眼前的人与事,烘托心中纯真的音乐乐土。遗憾的是,他太忙着表达自己的不以为然,却无力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尤其把古典音乐没落原因上纲到人性沉沦时,就再也无法从实务面去寻求解决之道。”[6](中文版序P3)莱布雷希特的确以自我为中心,他认为评论需要有明确的观点,但不求正确与否②,以此来满足“片面的深刻”。喜欢他的人,说他的文字另辟蹊径;膜拜他的人,说他的批评针砭时弊;当然,恨他的人巴不得马上送他去蹲牢房。
如果斥责莱布雷希特在写作中没有音乐分析,继而无法通过音乐来证明其观点的话,这或许恰恰是他的独到之处。莱布雷希特指出,“在‘二战’之后的六至七年里,西方音乐中讲故事的权利被学院派学者从社会史家和专家们的手中剥夺了,他们从整体上清除了音乐中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只专注于五线谱上的蝌蚪符。《音乐逸事》于1985年在伦敦和纽约首印,正是希望通过重现音乐万花筒中最多彩的传记逸闻来矫正前面提到的失衡状态。”[7]在他的作品中,作者和叙述者是可以区分的。他明显知道自己的部分观点过于偏激,却用叙述者的身份将作者身份进行掩盖。因而,作品的实际作者不应该和叙述者混同,文章中“说话的人”需要和生活中的写作者区别,这个写作者不是真实存在的人。被创造出来的叙述者脱离了作者,成为作品要素之一,与此同时,真实作者已从作品中剥离。从读者的角度观察,意义的来源脱离于作者,作品或读者也不是它的全部,在文本与读者的交流过程中意义得以彰显。一方面,文本提供了意义的潜在性,并通过读者的阅读实现意义,没有读者的参与,文本的意义永远是封闭的;另一方面,文本又只对懂得如何阅读它的人才有意义,他们知道应该在作品中寻找什么及如何阐释它。在此基础上,文本和读者共同创造意义。[8](P38、189)正如莱布雷希特所言,“普通民众看到音乐家详细、尖锐的评论,反而争先恐后地去现场观看演出,亲眼目睹后再次思考与评论。因此,评论者的另一个职责,是要引领公众参与到评论中去。音乐评论的对与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个可以供更多人争论、讨论音乐的平台。”[9]
莱布雷希特敢于直面危机,他在写作《谁杀了古典音乐》之时认为,“长久以来,音乐史的学者都避免谈到有力人士的恶行,而当今乐坛的丑态,同样地也被略过不谈。基本主要的工具书,像《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和《古今音乐》,都不提乐坛的权利掮客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样的躲避,让人无法正视乐坛的危机。如果不先揭露以往的丑态,那么新的罪行也将被掩盖。”[6](P3)尽管莱布雷希特的许多材料来源于《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但他的叙述主线、叙述方式却与纯正的古典音乐研究成果、音乐史的叙述方式截然不同。这或许是他博人眼球的过人之处。令人瞠目的事实、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或以调侃的方式轻松地说出,实则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尤其是被誉为“神圣”的古典音乐。此时,我们会反思——事物犹如硬币的两面,以往人们看到的是光鲜的那面。犀利的笔锋正如他所言,是一种责任——他想揭露谎言。比如在谈到波里尼(Bernhard Pollini)时,莱布雷希特写道:“在《新格罗夫辞典》里他被形容为‘国际水准的管理人’。他其实是个刻薄的老板和骗子。”[6](P49)他在叙述中打破均衡而表现出的张力和失衡越大,所得到的体验感越强烈,以此来满足阅读快感。因此,在均衡越向张力和失衡靠拢之时,读者获得的体验感越剧烈(见图示)。

音乐评论关注热点话题的讨论,作者的“偏激”或“超前”行为可以在受众群体中唤起波澜,张力增强与失衡体验激起人的欲望,这在19世纪音乐评论家舒曼的《新音乐报》、汉斯利克《论音乐的美》小册子中同样可以深刻感受到。该情况继续在20世纪延续,甚至愈演愈烈,先锋音乐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1908年以来勋伯格的无调性试验被质疑,1913年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引起骚动,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音乐评论,创新与转折之路都不是那么平坦,探寻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音乐创作主体走在前沿还是评论家走在前沿?作曲家在创作,评论家的写作就不是创作了吗?音块、无声是否能归为音乐,标志着理性认知走向了另一个维度。如何理解、审美角度决定了最终的答案。音乐不仅是一种审美途径,还是一种技术手段。莱布雷希特认为,“如果你听到瓦格纳对自身音乐的解读,你将会有毁灭世界的冲动,如果你掌握了布列兹研究音乐的手段,那么意味着你掌握了毁灭世界的工具。”[9]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成为瓦格纳或布列兹的复制品。
三、案例分析:身份的选择与认同
音乐作品的审美过程在经历了知觉维度的审美活动之后形成判断,需要呈现维度来体现,即选取评价的角度、进行系列分析,最终体现为文字表达。评价角度的丰富性是审美活动的迷人之处,每个时代都能在同一个作曲家或作品中找到该阶段所需要的不同批评元素。音乐家及作品所体现的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始终焕发生机,正是由于其中诸多需要深入探索的内容而引发的,它可以使研究的层面取之不尽。[10](P151-152)批评过程中的切入点很重要,随着时代而更新、细化、深化的观点更重要。阿多诺的“社会批判”标准认为,好的音乐应该揭示社会矛盾、充满社会批判精神,不应该反映商品化的小资特质以及标准化的文化产业。[11](P170)音乐评论的标准同样涉及到叙述者选择的身份、角度,并成为作品成败的基础。
《谁杀了古典音乐》是莱布雷希特的力作之一,它所涉及到的叙述者与经历者、音乐史中的主流与支系、史料与阐释等等之间的关系通过文字表述清晰可见。该书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古典音乐刚有萌生之势便走向衰落之际,对于该现象的产生,莱布雷希特给出了大胆的推测,标题和内容皆极为醒目和夸张。作者认为,谋杀古典音乐其真凶便是他在书中揭露的凶手——创造虚饰繁荣的企业、受到追捧的明星、商业化的唱片界和老谋深算的经纪人。从推手到杀手,作者在对古典音乐世界进行细致解读和观察之后,将其前因进行梳理,在理性分析后娓娓道来现实世界中的隐藏关系。莱布雷希特说:“音乐经纪人缺德、唱片业唯利是图、音乐家名利熏心,联手把古典音乐搞成金钱游戏。不但扭曲过去纯朴真诚的欣赏环境、破坏音乐自给自足的健康生态,也因音乐品质沦丧而流失听众。”[6](中文版序P1-2)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震惊于作者大胆而有理论推论性质的表达。无独有偶,他的《大师的神话》《科汶特剧院秘闻》都是幕后揭秘的另类作品。
《谁杀了古典音乐》以观点独到、视角独特、语言犀利著称。对于普通读者乐见的话题,作者可以用生动的、纪实的语气说出,仿佛他经历过那一切一样。在叙述的同时,莱布雷希特有倾向地掺杂着个人的分析和评价。这样,“入境”与“出境”、“局内”与“局外”在他的叙事中张弛有道,涉及到艺术与商业、音乐家与经纪人等博人眼球的话题。他的叙述线索是不断转换的,从一个事件到另一个事件,从一个个链条式的人物关联,叙事得以连贯进行。他并没有以某个大师作为切入点,而是以他的经纪人作为突破口,从而引出不为人知的一幕。他关注的不是“艺术”,而是“金钱”,这会诱发人的窥视心理,也勾起长久以来人们对于艺术背后商业运作的好奇心,以及“阶层”的垄断与形成。鲜为人知的幕后事件让人感觉仿佛从未真正了解古典音乐。他在挖掘音乐史的“边角史料”的同时,兼具了人文内涵、审美品格和批判意识。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莱布雷希特从特别的题材和撰写体裁出发,使写作别具一格。阅读这些文字之后,会觉得它更多展现出当代作家而非学术作家的特点。这或许与莱布雷希特的经历相关——他未受到过系统的音乐训练,不擅长乐器演奏,也不会指挥,而这些使他必须以“观察者”或“门外汉”的角度来看待音乐。由此,对于那些质疑他不进行音乐分析的声讨也就不必惊讶了。他坚信,音乐评论者所从事的是另一门类的实践,在一定量积累以提升自己的音乐品位之后,才能去品评和鉴赏。[9]
如果说《谁杀了古典音乐》是对当下的古典音乐界进行块面剖析的话,《音乐逸事》则是历史的、点状的、侧面的、多维的。莱布雷希特在这本书里努力破除音乐神殿的围墙,让已经僵硬的历代大师以本来面目走向读者,片刻花絮勾勒出圣俗交响着的丛林。从11世纪意大利阿雷佐地区的僧侣规多开始,直到20世纪先锋派作曲家施托克豪森,莱布雷希特将梳理的近千部著作尽收眼底。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曾经充斥在成千本音乐传记、回忆录及通信中的逸事由于早已绝版,在现代研究中少有提及……在本书之前,还没有过任何通过重要音乐家的逸事来考察音乐的系统尝试。本书的目的是:重现音乐史上久被遗忘的事件,时而揭示不为人知的插曲,通过这种曲径来纠正当下音乐史研究普遍存在的不平衡现象。”[6](中文版序P1)作者的叙述并非反传统或具颠覆性的,而是加入了更富生机的色彩,进而形成真实感受。他的准备工作十分谨慎,在保证这些逸事的真实性的同时并不太过纠缠于细节。每则逸事都仿佛是目击者俯瞰了某位大师生命中的重要时刻,通过对行为的观察反射其性格。
继探讨了古典音乐缘何衰落——《谁杀了古典音乐》之后,莱布雷希特又探讨了马勒为何复兴——《为什么是马勒?》。二者都是以“疑问”作为出发点,而相比前者,后者的写作方式更具有古典传统意味。它仍旧具有非常浓重的“莱布雷希特风格”。约翰·加德纳在谈《为什么是马勒?》一书时说:“我不知道音乐学家会如何看待它,但我很喜欢它。这是莱布雷希特近年来最好的一本书——没有他对指挥家、歌剧院和古典唱片业的揭露那么粗俗,那么尖刻,那么有倾向性。不是书中的所有内容我都同意,但作为对‘为什么是马勒?’问题的回应,我发现它的真诚和福音般的热情令人感动。”[12](P241)马勒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复兴,感动现代人、困扰现代人。历史似乎摇摇欲坠地被现代性所冲击,更加打破了对马勒的传统认识。从莱布雷希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坚定的理论——马勒感觉上是,而且也确实是一个现代的人。就像他所说:“音乐厅里有三千个人,而在马勒作品演奏的时候,你仍旧感到孤单。”[13](P246)加德纳认为,这是对一位极具吸引力的音乐家的一种迷人的幻想,他的魅力可能持续到可预见的未来。[12](P246)
莱布雷希特坚信,音乐的历史与音乐的发展历程并非同一概念,后者是学校教条式的知识罗列,而前者则涉及音乐家自身的诸多方面。借助自传、回忆录以及学术界的相关材料,研究者才有望真正读懂历史,才能认知历史与音乐家之间的深层关联。他常逛二手书店,读马勒那个年代的书、杂志,去寻找所有能找到的有关马勒的英语、德语、法语等文献资料,并且亲自步入马勒故居,将自己置身于作曲家生活的处境,在不同季节用脚步丈量歌剧院与家之间的里程,根据相关史料力图还原马勒当年工作与生活的场景。他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背下马勒每天几点几分需要做什么,还曾经踏入马勒泡澡的浴缸寻找岁月的痕迹与回想、回响……总之,他所做的这一切无非是为了通过接触被马勒物化过的条件,更深层地进入马勒生活的世界,去了解其生活节奏动力、动机,最后思考并探索这一切如何与马勒的音乐发生关联,从而发挥对马勒音乐的联想与认知。[9]基于这种视角,对于马勒的研究与叙述怎可能脱离了“我”?
莱布雷希特之所以选择研究马勒而不是布鲁克纳,是因为他在欣赏马勒的交响曲时产生了巨大共鸣。这可以追溯至莱布雷希特对于马勒及其作品的理解。他在《马勒表演的可变性》一文中指出,马勒演出了70场自己的交响乐作品,如果能研究一下马勒每次排演时性格上的变化(虽然很费时间),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他的诠释,这将会很有意义。比如,他的《第一交响曲》就凝聚了作曲家最具个性的创造,作曲家指挥这部作品要比《第三交响曲》多了15次。最初,它被当做作曲家青年时代经历的记录,逐渐在他自己的表演过程中演变成了最终的“对造物主强烈的谴责”。[14](P302)可见,莱布雷希特研究马勒及其作品的过程完全是主观的和动态的。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曾对“同一个故事”的观念提出有力的挑战。她指出,每一次重述,哪怕用同样的媒介重述,都是一个不同的版本。分析媒介对叙事文本的复杂影响是第二阶段或“后经典”叙事学必须面对的一个任务。[3](P205)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每当读者以一个动态的视角重新看待历史或文本之时,都会有一个新的发现。
结 语
在后现代理论思潮影响下的莱布雷希特,以其独特的批评写作获得了时代的首肯。在读者中心论的视角下,莱布雷希特的写作特色昭然若揭,作者逐渐退居幕后,信息的接收者在文本意义生发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文本和读者的交流中,文本更新了自身意义,叙述者脱离作者而存在。文本在流通过程中是可变的,其过程中的意义会更加丰富,它通过参与进程主体的加入而唤发出多姿魅力。另一方面,作者将“我”代入进历史,其叙述过程中无法规避“我”的存在,这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历史是发展的,范式是更迭的,我们无法要求一件事物永恒静止。在历史的冲刷和洗涤下,必定会有一批人、一波思想重新降临,洗刷尘封已久的故事。我们所认知的作曲家、作品也会随着写作者的不断理解、解读生发出新的意义。文本是流动的、思维是更新的,莱布雷希特的作品带来了一股独特的、给予人类重新认识自己的勇气。他将历史赋予了时代的气息,让音乐史有了温度,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史料。他的作品之所以脱颖而出,在于其不拘一格的思想、开拓的眼界、多维的人生体验,审美批判性视角将音乐史完全带到了另一个空间,进而使我们反思他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作者的成功带给当今的批评家、史学家新的思考——他游走于两个范畴的边际。音乐学的写作需要新的理念、视角,他以批评审美充实史学研究,以史学研究推动批评审美。身处后现代,我们不知不觉被其感染,音乐写作的思维方式、思想理念都已经跨入一个新的时代。莱布雷希特的音乐批评理路与叙述策略正是这个时代的反映。
注释:
①Who killed classical music(1996),其中译本《谁杀了古典音乐》(查修杰、施璧玉、陈效真译,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以犀利的语言和视角揭示出当代古典音乐的兴衰。
②当然,“不求正确与否”这个词并不是哗众取宠,而应理解为一种智慧型的评论方式。基于大量的客观因素,支持主观判断。(笔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