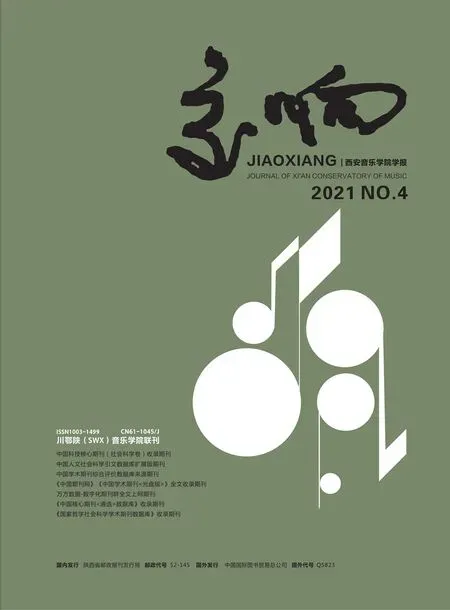唐曲《王昭君》研究
●庄永平
(上海艺术研究所,上海,201103)
王昭君远嫁匈奴是我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事件之一,也是流传十分深远的故事之一。有人统计,古往今来反映王昭君的诗歌就有700余首,与之有关的小说、民间故事有近40种,当初王昭君的远嫁还颇富戏剧性。据有关史书及民间流传,由于当时宫廷中宾妃宫女众多,大都由画工画像后供皇帝挑选,才能获得宠幸的机会。因此,宫女们都纷纷贿赂画工以求画得出色些,而王昭君却没有这种潜规则意识而被丑化。后来匈奴单于向汉庭提出和亲的请求,汉元帝答应并下了一道命令,谁愿意嫁到匈奴去,就认作她为亲身女儿,这时只有王昭君主动提出离宫去匈奴。等到出嫁的那一天,元帝才发现王昭君竟然如此的美貌,与画像上的模样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惜此时虽然懊丧不已但已无可挽回,于是只能迁怒于画工毛延寿,将其处死。自然,我们现在从音乐角度出发,关注的是此事记述中的某些说法与用词是否真实、妥当。更重要的是历史上流传有关王昭君的乐曲,是否有解译的可能性与准确性的问题。
一、王昭君和番释义
历史上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昆莫(国王)猎骄靡,后又于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将楚王之女解忧公主嫁昆莫之子军须靡及弟翁归靡,这大概是有史可稽的我国与西域国最早的通婚之事。到了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才出现了汉宫女王昭君嫁匈奴单于的婚事。问题在于汉后不久,历史记载已有将这前后几桩婚事的情景混淆了起来。据东汉班固(32年-92年)撰《汉书·西域传》(约76年中成书)记载,当时汉遣乌孙公主嫁昆莫是“赐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数百人,赠送甚盛。”《汉书·元帝纪》载王昭君嫁单于事:“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向)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后南朝范晔(398-445)撰《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载:“王昭君,姓王名嫱,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兴山县)人。匈奴呼韩邪单于阏氏。她是汉元帝时以‘良家子’入选掖庭的。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五女赐之。王昭君入宫数年,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显然,乌孙公主嫁昆弥时的欢送场面有数百人,所带礼物也非常丰盛,而王昭君嫁匈奴并未记载有这种盛大欢送场面。另,东汉傅玄(217-278)《琵琶赋》并序:“《世本》不载作者。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1](P3454)傅记述的显然是乌孙公主嫁昆弥之事。现在我们所关注的:首先,“赠送甚盛”是乌孙公主嫁昆莫事,并不是王昭君嫁匈奴之事。其混淆的始作俑者就是离汉代不远的,那个奢靡无度的西晋石崇(公元249年-300年)。他在《明君辞·序》中说:“王明君者,本为王昭君,以触文帝讳改之,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明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2](P413)这一“想当然”(“亦必尔也”),也就将两件婚事混淆在一起了。其次,在乌孙公主嫁昆莫婚事队伍中带有各种乐器,这才是我们今天研究琵琶史所关注的。上述傅玄讲是“故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这里,一是现代所作的标点似乎并不正确,因为琴、筝、筑是我国固有乐器,箜篌是外族外国流传进来的乐器。前者是放置在“案”或“几”(后来用“桌”)上演奏的较大型乐器,后者是骑在马或骆驼上抱着演奏的便携式乐器。因此,应将它们二者分开且后面所用的一个逗号或可取消:“故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才合适。二是这个“载”字,后来就有用“裁”字的。如唐杜佑《通典》(801年编成)卷144《乐四》载:“琵琶,傅玄《琵琶赋》曰:‘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琴、筑为马上之乐”[1](P3450)。同样,后晋刘昫等编《旧唐书》(945年成书)载:“乃裁筝、筑为马上乐。”[1](P3450)从字面上看,“载”是可能的,但像中国古代那些平置弹奏的乐器体积庞大,放在单匹马上看来是不可行的,只能放在四马轿车上才行。而“裁”字则是不可行的,乐器可以裁剪那是无稽之谈,正如“分瑟为筝”的传说那样,显然是想当然说说而言的。而且,如果说那时中外通婚场面中所带的乐器,边送行边演奏有否可能?中国的那些乐器看来是不可能的,只有那些外族或外国流入的便携式乐器,在游牧民族中一直是有这种演奏习惯的。后来人们甚至还混淆了短颈曲项与长颈直项两类琵琶,后者其实早就不称为琵琶了。如宋俞琰(1258-1314)《席上腐谈》:“王昭君琵琶怀肆,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浑不似’,今讹为‘胡拨四’”。正像傅玄所言琵琶在那时指的是长颈类直项琵琶(即后来的阮类乐器)。宋王㮊《野客丛书》卷10《明妃琵琶事》:“则其弹琵琶者乃是从行之人,非行者自弹也。今人画明妃出塞图,作马上愁容,自弹琵琶,而赋诗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鲁直《竹枝词》注引傅玄序,以谓马上奏琵琶,乃乌孙之事,以为明妃用,盖承前人误。仆谓黄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词》故耳。”[1](P3467)
二、《王昭君》曲及结构比对
关于《王昭君》曲,前辈丘琼荪大致作了归纳:即清乐之《明君》,汉、晋间曲,歌舞曲,琴曲。据《隋书》卷15“清乐”条载:“其歌曲由《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明君》,汉、晋间曲。”据《旧唐书》29载:“武太后之时,(清乐)犹有63首,……今其辞存者,……《明之君》《雅歌》各二首。……自长安(武后年号,701-703)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转缺,能合于管弦者,惟《明君》……等8曲。……武太后时,《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传二十六言,就之(《唐会要》作“渐渐”)讹失,与吴音转远。”[3](P33-35)《乐府诗集》“相和歌”中有《明君》(亦琴曲);《唐会要》载太常别教院所教之法曲十二章,其中为首即《王昭君》一章。《乐府诗集》卷29:“《古今乐录》曰:‘张永《元嘉技录》有吟叹四曲,二曰《明君》。’又曰:‘《明君》歌舞者,晋太康中季伦所作也。晋宋以来,《明君》止以弦隶少许为上舞而已。梁以清商两相间为明君上舞,传之至今。’王僧虔《技录》云:‘《明君》有间弦及契注声,又有送声。’谢希逸《琴论》曰:‘《平调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拍,《清调明君》十三拍,《间弦明君》九拍,《蜀调明君》十二拍,《吴调明君》十四拍,《杜琼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琴集》曰:‘《胡笳明君》四弄:有上舞、下舞、上间弦、下间弦。《明君》三百余弄,其善者四焉。’又《胡笳明君》别五弄:《辞汉》《跨鞍》《望乡》《奔云》《入林》是也。《明君》为汉曲,绿珠所歌者仍为汉曲,惟词系新制。南朝所歌者即石季伦新制词,其曲依旧是汉曲。”[3](P59、63)然而,《王昭君》乐曲在日本雅乐中却被留存了下来,那就是日本琵琶谱的《五弦谱》与《三五要录》谱所载。当然,在其他的一些乐谱,如《仁智要录》筝谱等中也有留存。但是,由于自汉以来,《王昭君》曲的曲调众多,节拍纷繁,流传的情况也就比较复杂,为今天的解译增加了难度。下面就将《五弦谱》中的一首;《三五要录》谱中的一首及“同曲”一首,共三首来进行分析比对(见文后谱例)。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在记谱上唐时乐曲的结构与节拍关系十分的密切,正所谓“拍板即乐句也。”例如,今天小节节拍的一小节,约等于唐时的一拍(以“百”字标记),今天的单位拍(即四分音符为一拍,小拍)为唐时的一个“字拍节”(单谱字,单音)或“音拍节”(多个谱字,多音)。[4](P507)这样,现在以《三五要录》谱所载曲为准,来标记小节(即“百”)。其实,谱中曲名下已有文字说明:“拍子八,无舞,新乐,中曲,返黄钟调弹之。”但从谱中看不止8个“百”字,有15个“百”字(书中漏校了最后一个“百”字),现解译为拍子十五。经对照此曲其实是前后两遍,具体对应是第1-7小节与第8-14小节乐句旋律相同,第15小节4小拍与曲前不完全小节4小拍,构成八均拍式(8/4拍),看来此曲的旋律结构还是比较单纯的。其次,《五弦谱》中的一首反复就较多,一开始的两小节就运用了反复,这里,它没有采用简约反复符号记写,而是将第二遍全抄写了出来,实际就是一种“换头”(谱中加标此两字)反复结构形式。这样,对照《三五要录》谱此曲,反复的两小节半,就不能标上小节序号了。谱面的第7小节后,标有“第一、第二同”的提示,说明又是运用了反复,这显然是从第1小节开始反复为第二遍。因此,这一反复比《三五要录》谱此曲最后多出了4小拍长音,现也没有标上小节序号。这4小拍与开始不完全小节4小拍合为八均拍,说明仍是一种不完全小节反复形式。接着,第8小节则标有“第三”,第9小节尾部还标有“以上两遍”的提示。说明第8、9小节还要反复一遍,与第1、2小节反复相同,只是去掉“换头”的4小拍。到了全曲尾部又有“第四、第三同”的提示,这里,以前笔者从叶栋将“三”字拟作为“五”字解,即“第四、第三(五)同”[4](P65),现在笔者认为非是,这仅说明第4遍就是从第8小节起直至结束,与第3遍完全相同并无第5遍。这样,全曲不计反复是拍子二十(11+9),这种前后节拍不均现象,在宋张炎《词源》中已论述到。[5](P15)那么,《三五要录》谱此曲的“同曲”,曲名下文字说明:“一说拍子十,八拍子此曲(后面几个字抄写不清,难解其意)”。从现谱面看,此“同曲”确实是有10个“百”字(小节),说明是拍子十而非拍子八。但是,它采用的是四均拍,即今天每小节有4小拍的4/4拍,这样,与上述8/4拍相对照,开始4小节旋律是完全能对应的,后面的乐句旋律音符有所跳跃对应,只能说是基本上能对应的。显然此“同曲”没有作全曲反复,因而是拍子十不是拍子二十。从二者的小节划分来看,也不是八均拍直接分解为两个四均拍,其间是有所交叉的。这样,《五弦谱》此曲照实记是拍子二十,正如上面“一说拍子十”反复一遍那样。《三五要录》谱曲照实记是拍子十五,按拍子八反复一遍应该是拍子十六,这样就少了一拍。如果把《五弦谱》此曲第6-7小节之间,与第12-13小节之间各多出了一小节计入(共两拍),这样又成为拍子十七。因此,只有将《五弦谱》曲第7、8之间多出4小拍计入,即增加4小拍以与曲前4小拍合为八均拍,这样前后构成拍子八,合为拍子十六。可见,这些都是拍子十与拍子八对应产生的矛盾。值得关注的是,《五弦谱》此曲由于反复较多,前后节拍交叉得较厉害,故而只能用文字来加以说明。这种情况在其他乐曲如《夜半乐》曲中,用“同”“同同”“同同同”那样,都是古人用于反复的提示。这种反复用今天的各种记号来表示,也还有一定的困难且繁琐。因此,笔者对以前发表所标的反复记号作了修正,一律不用现代反复记号加以标记。
三、旋律调式及节拍、节奏比对
首先,《三五要录》谱中此曲一开始就标有“返黄钟调弹之”的字样,说明此曲用的是返黄钟调。但在它的“同曲”中出现了用“ヒ”不用“マ”谱字的现象(出现的两个“マ”谱字实是一种经过音)。从谱字运用来看,谱字“ヒ”比“マ”低了半音,“マ”的首调谱面是#fa音,“ヒ”的首调谱面就是fa音。用“マ”谱字是雅乐音阶返黄钟调,唐乐称为大食调,D调商调式。用“ヒ”谱字是运用清乐音阶,对应唐乐是雅乐音阶平调,G调羽调式。那么,问题在于这里并没有像其他乐曲那样,如果“同曲”出现调性调式变化,通常是要注明的。例如,《庶人三台》曲注明是“大食调,琵琶返黄钟调”,在“同曲·乐拍子”后,又有“同曲,琵琶黄钟调弹之”。返黄钟调与黄钟调虽然定弦相同但调性低了五度(或高四度),前者用D调后者用G调。看来,实际是原谱此曲的“同曲”后面漏了“琵琶黄钟调弹之”这七个字。具体音阶排列为:音名e.#f.#g.a.b.#c.d/雅乐音阶唱名 re .mi.#fa.sol.la.si.do,D商调→音名e.#f.g.a.b.#c.d/清乐音阶唱名re.mi.fa.sol.la.si.do=雅乐音阶唱名 la .si. do .re.mi.#fa.sol,G羽调。不过,后者仍用D固定调谱面,不用G首调谱面。其次,关于节拍、节奏方面,(日)林谦三在《敦煌琵琶谱的解读》中讲到:“还有一点可以从日本雅乐想象到的,那就是在依照这正常节奏的奏法之外,还有两个变奏的节奏存在着:一个叫做‘只拍子’;另一个没有专门的名称(一说叫做‘乐拍子’)”[6]。其实,《三五要录》谱中的《河南浦》曲有关提示,出现了:“‘乐拍子’句与‘只拍子’句不同,是从宜切句之故也”的解释。我们见到的“只拍子”作为基础拍子,通常未专门写明是“只拍子”,而在“只拍子”曲后面,常常出现“同曲·乐拍子”的字样,这是一种旋律加花、节奏繁复的形式。当然,在此曲中没有“同曲·乐拍子”可对照,它的“同曲”也不是“乐拍子”形式,与前曲是犹如类似今天民间乐曲“头板”与“二板”的关系,说明速度加快且仅奏一遍。下面,笔者先对谱中某些谱字关系处理作了调整加以说明。笔者在《唐乐琵琶古谱考辨与校译》一书中对此曲进行了初步的考辨,但并没有深究。现在把三谱纵向排列起来,仔细对照发现仅从《三五要录》谱此曲出发,根据相同乐句旋律等来进行划分节拍、节奏,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例如,第1拍第1、2小拍与第7、8小拍同为相差八度的两谱字,前者的“”谱字带点,通常就处理成与前面谱字合为一个谱字位:“”,也就是两个八分音符合为一个四分音符时值。后者“八”谱字因为不带点,就处理为两个四分音符时值:“”以合符拍式。现在根据三曲的比对,显然它们正好是相反。也就是前者是两个四分音符时值(“”),后者才是两个八分音符合为一个四分音符时值(“”),现标“▲”与“▼”表示已作调整。同样,第2小节两组“コリ”谱字均未带点,根据拍式必须前一组为两个四分音符时值,后一组为两个八分音符合为一个四分音符时值,现标“◆”与“●”表示已作调整。还有第14小节的“”调整为两个四分音符时值(“”);后面的“コリ”调整为两个八分音符合为一个四分音符时值(“”),现标“■”与“★”表示已作调整。总之,可以说类似这种情况在没有其他同曲可对照的情况下,是很难作出正确判断的。当然,这些也仅是在这两份琵琶谱上的对照,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可参考其他的一些乐谱,如筝谱、笛谱、笙谱及筚篥谱等来进一步对照确证。为此,与有关节拍、节奏方面的比对,大致说明如下:
1.根据相应的节拍,在一个“字拍节”单位上可以与一个“音拍节”相对应,这样,就出现一个谱字(音)对应多个谱字(音)的现象,那么,只要其中有一个音相同,就可视为是相对应的。例如,第1小节后半的4小拍,即第5小拍仅是高低八度音的不同,八度音历来认为是相同的;第6小拍是#fa音,前面的la或sol音应视为是加花之音。在《三五要录》谱中,我们可以发现本曲与“同曲”相比,后者就常在前者谱字(音)前加上另一个音,成为一种特定的、常见的加花方式,可以认为相互是对应的。第7小拍类似本音与加回音或波音的对比,这种形式在“同曲·乐拍子”中最为常见。也就是慢奏一个音或演奏一个较长的音,同时加上左手较大幅度的揉吟,在谱中常就被记成波状的三个音(“下波音”)。这种奏法与音响在日本传统音乐中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由此可见,我国唐代音乐的奏法与音响可能与此相去不远。第8小拍不仅纵向相差八度,而且自身横向也分裂成相差八度的两个音,这完全应该视为是相对应的。
2.如果几个音中都没有可对应的音,则要看旋律线的进行,很可能其间出现变奏或用音及抄写错误。例如,第7、14小节中第3、4小拍的两音不同,出现了大二度的相差,可能是五弦琵琶与四弦琵琶不同定弦指法造成的,在此不能断定是哪一方出错,只能参考筝、笛等其他同曲基础上再来定夺,还有像第6小节的首音也是这样。笔者在研究《敦煌乐谱》时发现,往往出现相差四、五度音与大二度音,很可能与调性相差四、五度或大二度有关,就会出现这种用音上的错误。至于相差半音、三度音、六度音等,则有用音错误或抄错的可能,这些主要需依靠旋律趋向等大环境方面提供的条件来甄别。另外,像第4-11小节、第5-12小节、第6-13小节《三五要录》谱此曲前后旋律都相同,《五弦谱》此曲自身旋律前后理应也相同,但实际并不相同。
3.从节拍上而言,《三五要录》谱此曲的“同曲”,与《五弦谱》曲是相同的,都是“拍子十”,但《三五要录》谱此曲是“拍子八”,这就产生出一些旋律上的不同。如果将“同曲”加上第二遍,大致也还是相对应的。当然,有些旋律细节有所不同,主要是对《五弦谱》此曲而言的。
总的来说,从大的趋向上看,这三曲还是基本对应的,只是里面一方面涉及到“拍子八”与“拍子十”的不同,这在《三五要录》谱的时代,已经有这两种说法了。另一方面,从它们自身来看都是可以单独成立的。